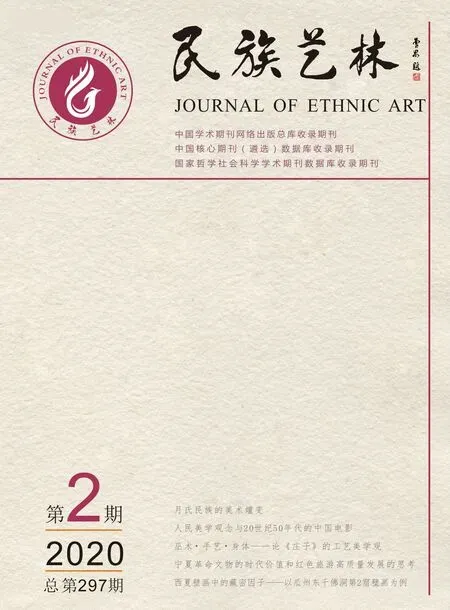西夏壁画中的藏密因子
——以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壁画为例
(宁夏大学 美术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东千佛洞第2窟考察
东千佛洞又名接引寺,属于敦煌石窟体系范畴,位于甘肃省瓜州县桥子乡东南方向的长山子北麓,距县城约80公里。“东千佛洞始建于西夏时期,内容以密教题材为主”①,石窟分布于峡谷两岸,“与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多利用前代旧窟重修不同,是西夏在河西地区仅有的新开凿的一处石窟”②。目前,东千佛洞石窟现存洞窟23个:东岸9个,西岸14个③。由于地处连接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瓜州东千佛洞虽然在洞窟规模、形质、数量以及壁画表现内容、风格及面积上不及敦煌莫高窟,但其艺术价值却与莫高窟等量齐观。之所以如此评价,正在于东千佛洞石窟“在壁画上把显教经变与密教曼陀罗并列一窟,把汉密与藏密排在一起,把中国菩萨和印度、尼波罗菩萨同画一壁,目前发现只有榆林窟和东千佛洞有所保存”④。由此可见,东千佛洞藏密佛教壁画的集中出现,以及更多、更系统地表现和发展,已然完善了敦煌佛教壁画艺术的完整性。
第2窟位于河谷西岸,坐西朝东,为东千佛洞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洞窟,窟内现存西夏壁画也最为完整与集中。“依据窟内壁画中的供养人、西夏文题记、壁画风格以及西夏仁宗朝(1140-1193)大规模依据梵本重新校勘、翻译佛经的史实,可判定此窟为西夏中晚期所开凿的洞窟。”⑤
东千佛洞第2窟整窟壁画是对汉藏、显密佛教内容进行综合表现,将一直以主角身份出现在石窟壁画中的大乘佛教经变画降到次要地位,加大了密宗图像的描写内容。洞窟墙面与窟顶绘满壁画⑥:窟门甬道顶部有龙、凤、莲等图案,甬道两侧墙面分别绘西夏盛装的男女供养人像各6身。洞窟主室藏密氛围浓烈,东壁南北两侧绘三面四臂观音变和三面八臂观音变;南壁绘东方药师经变、十一面八臂观音变各一铺;北壁画西方净土变、八臂观音变各一铺。洞窟天顶中心为曼陀罗藻井,四披壁画大多已脱落,从现残存壁画形象来看,画面所绘可能是四方曼陀罗。中心塔柱东壁绘坐佛16身,两侧及背壁画有菩提树观音与涅经变,甬道口上方各绘一铺布袋和尚。后甬道南北两壁绘水月观音各一铺,顶部为卷草和莲花图。洞窟西壁(背壁)正中绘说法图一铺,两侧画药师佛各一铺(图1)。

图1 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平面示意图(卯芳绘)
二、东千佛洞第2窟的藏密风格壁画
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主要是指从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区的佛教造像传入藏区后,与当地艺术相结合而逐渐形成的佛教造像风格。由于党项民族与吐蕃长期以来的历史交往,受后弘期西藏艺术的影响,“高度程式化的严谨构图、明艳的冷暖纯色对比”⑦,成为西夏藏传风格绘画的主要特征。较之汉式绘画艺术的表现,东千佛洞第2窟前室壁画表现继承卫藏风格,诸多经变画的构图样式和菩萨造像,具有明显的藏密风格。壁画中主尊佛像绘于中心,主尊背龛样式与11~12世纪的西藏唐卡一样,将菩萨数和佛龛进行简化,呈现出一种高度规范化和极其简洁的装饰性风格。壁画中胁侍菩萨坐立于莲花宝座,环绕于主尊周围,人物之间几无空间。无论是尊像面容的刻画、身姿的扭动、配饰的繁缛,还是基座的规整、画面整体的组合,均排列紧密,层叠有序(图1)。与汉传佛教经变画中的构图形式及空间布局大相径庭,显著区别于前甬道和后室所绘的汉系风格壁画,体现出浓郁藏密绘画特点。

图1 东千佛洞第2窟东方药师变
“藏传绘画背景中出现了大量的图案、格式化的山峰形象,诸多的山峰被概括、简化为密集排列或组合的彩色条状,有些还在条状山峰上,绘制出小涡纹或小圆洞等装饰,成为藏传绘画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⑧。在东千佛洞第2窟中,大量的图案和格式化的山峰形象做背景衬托予以呈现。简化、概括的尖楔状山峰造型,以藏传佛教惯用的红、黄、蓝、白等色涂染,形成密集排列的色块与线条(图3)。其中,有些山峰上有明显小涡纹或者小圆洞的绘制,这种简洁、装饰感强的绘画样式在黑水城出土唐卡中均有表现(图四)。

图3 东千佛洞第2窟西方净土变局部

图4 黑水城出土唐卡的断片
各经变画中,众菩萨头戴发冠,身配璎珞,丰乳,细腰,肥臀,身材婀娜,姿态夸张。面貌、姿态和佩饰方面,与黑水城出土的藏传风格绘画中菩萨造型高度一致。人物身体裸露、体态夸张,体现着一种清纯韵致与娇柔妩媚,并与整体画面对比强烈的冷暖色彩一起构成瑰丽的视觉效果。壁画中人物形象特定的排列方式、异域风格的菩萨造像、浓烈幽暗的色彩,也共同营造出东千佛洞第2窟前室壁画神秘的藏密宗教氛围与诡谲的异域绘画风格。
“纵观第2窟各经变画,尤以绘于中心塔柱南北两侧的两铺菩提树观音最具特点”⑨。关于这两尊菩萨的描述,张伯元先生在《东千佛洞调查简记》中最早出现⑩:
北壁画一依傍花树,身体略微倾斜的菩萨像一身,壁画已模糊。南壁画一依傍花树,身体略微倾斜的菩萨像一身,左下角画有夜叉鬼魔张口吮接从菩萨手拿瓶中的倒出物,形象真实生动。

图5 菩提树观音 东千佛洞第2窟中心塔柱南壁

图6 菩提树观音东千佛洞第2窟中心塔柱北壁
画中菩萨脸形方中带圆,眉毛弯曲成微微波浪形,眼睛俯视,面带微笑,下颌微含,头戴宝冠,身体配波罗冠饰,下着裙裤,双腿相交而立。中心柱南侧菩萨斜倚树下,脸微侧朝向主尊,眉眼微垂。菩萨上穿蓝短衫,下着红短裙(现已脱落呈白色,只存零星红色),有宝石璎珞垂于脚下。右手胸前结印,左手自然下垂,手持花枝,身姿苗条修长,扭转略呈“S”状,腿部有印度赭石色海娜粉的纹绘。菩萨身躯婉转动人,身后是挂满枝叶的杨柳,枝条茁壮,随风摆动。身后祥云涌动,下方有孩童接取宝物(图5)。北边菩萨头部向主尊一侧倾斜,脸呈正面状,穿浅绿色短袖衫,着绘有花纹的超短裙,与中心柱南侧菩萨相一致,红色短裙也脱落仅存白色。其配饰与南边菩萨相近,有宝冠、臂钏、璎珞作装饰,身体以“S”形扭动斜立于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下。菩萨右臂上举弯曲至头部,轻捻手指,左臂自然下垂,手提净瓶。一腿微微弯曲,将全身重心落在另一腿上,站立于莲花宝座之上。身后簇簇白色小花盛开在树枝叶丛之中,左下饿鬼正吮接甘露,远处白云涌动,近处绿水盈盈(图6)。两菩萨面部丰润,慈眉善目,面带微笑,衣裙紧贴身体,尽显女性优美曲线,体态婀娜优雅。腰肢及手臂的适度摆动,与头部的微微倾斜形成了柔和律动的人体轮廓与优雅姿态,极具风韵。画面的独特造型与精湛技艺,在所有石窟壁画作品中并不多见,极为珍贵。“从风格来看,尽管倚傍的树、云霭以及饿鬼、贫儿的形象是敦煌传统的汉地样式,但两尊菩萨像的楔形叶冠、冠两侧的小花、轮状耳铛、臂钏、微闭的眼形、贴体短裙以及掌心施色等,无疑透露出东印度波罗(Pāla)艺术的特点”11。“可以说这两铺壁画表现了西夏画师对于印度波罗风格本土化的一种尝试”12。
三、西夏佛教壁画的藏密影响
东千佛洞中藏密风格壁画的集中出现,与其所处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公元1138—1227年),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萧关,北控大漠”13,在宋、辽(金)、回鹘、吐蕃之间,境内有汉、吐蕃、回鹘等多个民族杂居。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西夏与周边民族在文化上不断进行交流与融合,促使西夏文化具备非常浓郁的多民族色彩。西夏信奉佛教,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佛教势力最大,地位最高,在西夏境内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同时,西夏统治者也对其他民族宗教进行兼收并蓄、容纳吸收,使“西夏佛教形成了多来源、多宗派、多层次的特点”14。并且,西夏与吐蕃的交流与来往也由来已久,藏族文化对西夏文化与宗教有深远的影响。到中后期,随着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入,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藏传佛教,并大力倡导,使之地位不断提升,最终形成了在西夏宗教信仰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藏传佛教”的局面15。《黑鞑事略》记载:“西夏国俗,由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16虽有夸大之词,但足以反映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深刻影响。“由于统治者的倡导,积极从西藏引进喇嘛教”17,随之藏传佛教绘画也逐渐渗透到石窟壁画表现中。因此,在佛窟中较多出现密宗题材的壁画。“这种所谓‘藏密’题材和风格的壁画,对西夏佛教画坛影响甚大,它给已经陷入严重程式化而一蹶不振的西夏佛教画坛注入了新的血液,使濒临于衰败的西夏佛教壁画艺术重新振作起来。同过去相比,‘藏密’题材和‘藏密’风格的壁画艺术的出现与流行,不能不是西夏佛教和佛教壁画艺术一个崭新特点”18。
与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相一致,“西夏佛教既接受中原显教艺术,也接受藏密艺术”19,“藏密则多为藏传佛教后弘期”20。在西夏中后期的壁画内容中体现出显、密结合的特点,并在壁画表现中融合了汉、藏、回鹘等其他民族艺术形式,使得此时期的石窟壁画呈现出多元包容的文化状态,其中尤以藏传佛教的影响最为显著与深远。因此,在这样的宗教氛围、文化历史背景下,已有深厚汉文化影响和汉系佛教绘画传统底蕴的敦煌地区,其石窟壁画绘制与表现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藏传佛教绘画元素的极大影响与渗透,以致在瓜州东千佛洞众石窟中,藏传佛教绘画元素在壁画中大量出现。李月伯先生曾在其所著的《谈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夏晚期藏密图像——以榆林窟第3、第29窟为中心》一文中明确指出,瓜州境内藏密风格壁画之所以极盛,除了与西夏在瓜州设监军司统管河西有关外,唐蕃古道的藏密传播也是直接原因。
藏传佛教不同于汉传佛教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宗教神秘氛围的强调,西夏佛教艺术是在集中融合了中原、西藏、西域及印度各个流派之后,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佛教艺术。东千佛洞第2窟壁画在技法上虽与宋画一脉相承,但造型、赋色却具有鲜明的西夏艺术风格,显示出浓郁的藏密色彩特征。自唐以后,佛教艺术在中原地区的世俗化倾向日益强烈,影响到敦煌众多壁画的描绘重点演变为佛国净土。满壁充满庄严极乐氛围的西方净土世界被描绘得富丽堂皇、绚丽多彩,其实这些只不过是广大民众对极乐净土的世俗性想象与精神向往,表现的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慈悲境地或极乐世界,呈现的是理想中的“人间天堂”。而与汉传佛教艺术不同,注重宗教的神秘与不可测是藏传佛教艺术的表现主旨,为保持信仰世界的神圣与威严,拉开与现实世俗生活的距离,藏传佛教艺术强化了佛教绘画境界中的抽象元素和诡异色彩的特征。因此,当这些藏传佛教艺术因素渗入到敦煌地区石窟壁画中,在有别于传统佛教壁画表现的同时,留给观者更是不同寻常的理解,带来的是一种异于汉传佛教艺术的神秘感知。如东千佛洞第2窟前室壁画将众多形象密集排列,尤其图中几何状的山石,以明快艳丽的颜色刻画,与前期敦煌壁画中熟悉、亲切的山石形态风格迥异,凸显出藏密绘画的神秘气氛。明王、菩萨体态夸张,衣装华丽,装饰繁缛,色彩明艳。其中,菩萨身体扭转幅度夸大,姿态呈“S”形,充分体现出女性特征,反观汉系佛教艺术中的菩萨造像,完全是不同的绘画语系。
相对于汉系佛画,藏传佛教绘画的程式要求更为详细、严格。“为了使宗教绘画与世俗绘画相区别,藏传佛教绘画有一系列必须严格遵守的规范,《大藏经·工巧明部》中的‘三经一疏’(即《绘画量度经》《造像量度如意珠》《造像量度》《佛说造像量度经疏》)对这些规范作了详细的描述,它们是画工们必须依从的规则”21。这一点在东千佛洞第2窟前室壁画中有突出体现,壁画表现强调对造像仪轨的尊崇,注重构图的程式化和色彩的强烈感。同时,较之汉系佛画艺术表现,藏传佛教绘画突出的特征还体现在富有性别特征躯体的描绘上。佛、菩萨紧裹的袈裟后面,可清晰地看到身躯的起伏与变化,注重形体的动态与韵味,极具线条的变化与律动。女性神灵身姿极其优美,以舞蹈姿势或坐或立,女性特征表现也更为突出:丰乳、细腰,四肢修长,髋部扭动夸大——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图7)。其基本造像特点如“苗条夸张扭曲的身形,特殊的珠宝装饰,尖顶的头冠,臂上的三角装饰,线条形体的强调”22。前文所述中心塔柱南北两侧的树下菩萨及前室众菩萨形象便是典型体现。“这样的随侍菩萨及坐姿菩萨在黑水城出土的唐卡和版画中多次出现,其艺术风格属藏密佛画,并显示出受印度波罗风格佛像造型的影响”23(图8)。

图7 东千佛洞十一面八臂观音中的站立菩萨

图8 黑水城出土唐卡金刚座上的佛陀中的站立菩萨
四、结语
西夏和西夏以后佛教思想总的特点是汉藏结合、显密共修。西夏石窟壁画在敦煌石窟群中又属独立体系,“内容上讲一窟之内显密同在、汉藏并存,风格上讲中原风格、西藏风格、回鹘风格并存,但以前二者为主。这是印度、尼波罗蜜教绘画与西藏苯教相结合的藏密特殊风格”24。从东千佛洞第2窟佛教壁画可以看出,汉传和藏传佛教的信仰交汇在西夏晚期石窟壁画艺术中得以充分体现,壁画中的表现题材以汉密或汉显及藏密共有,浓郁的中原风格和西藏韵致得以完满呈现,形成了具有民族与时代特点的西夏晚期石窟壁画艺术风格。敦煌学者段文杰先生曾指出,这种显密杂呈的风格是汉藏兼具的西夏佛教信仰的必然结果。张宝玺和萨莫斯约克则认为:西夏佛教美术以在中原、西藏(吐蕃)、印度和西域(中亚)风格中寻找统一与和谐的表现基础为目的,这是西夏文化的特殊性所使然25。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的壁画艺术,是佛教发展上千年的产物,是在前代传统绘画基础上,融合多民族文化与多民族艺术流派之后形成的具有西夏民族特点的佛教艺术。“藏传佛教绘画因素的渗入,为敦煌壁画敷上一层神秘诡异之美,但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以适应敦煌壁画总体风格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接纳与改造的共同作用下,敦煌西夏时期石窟壁画显示出独特的时代面貌”26。瓜州东千佛洞藏传佛教艺术比重之大,风格之显著,展示出鲜明的艺术风貌和民族特色,第2窟也由此成为展现西夏石窟艺术价值的经典范例。
注释
①③王惠民:《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敦煌研究》1994年第一期,第126页。
②牛达生:《西夏石窟艺术浅述》,《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二期,第96页。
④段文杰:《榆林窟党项蒙古政权时期的壁画艺术》,《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13页。
⑤早在陈万里《西行日记》(1926)中就提及当地口传,得知东千佛洞“有西夏洞窟”,见陈万里著,杨晓斌点校:《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6、141页。
⑥张伯元、宿白、张宝玺、王惠民、刘永增、郭佑孟等学者先后对此窟壁画做了记录或识读,本文主要以王惠民先生先生《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一文为主,见《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第127页。
⑦21顾颖:《西夏藏传风格绘画与西藏佛画的异同比较》《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94页。
⑧王艳云:《西夏黑水城与安西石窟壁画间的若干联系》,《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05页。
⑨常红红在《论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施宝度母图像源流及相关问题》一文将其认定为施宝度母,《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总第172期)。
⑩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简记》,《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第111页。
11 12常红红:《论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施宝度母图像源流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总第172期),第73页、87页。
13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二。
14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3页。
15陈庆英:《蒙藏的早期交往及西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85页。
16彭大雅撰,徐霆疏:《黑鞑事略》丛书集成初编本。
17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4页。
18刘玉权:《略论西夏壁画艺术》,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0—11页。
19牛达生:《西夏壁画艺术浅述》,《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93页。
20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编辑部主编:《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3页。
22巴勒:《西藏艺术:洛杉矶郡立博物馆艺术品图录》,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23徐庄:《西夏艺术——异形之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4段文杰:《榆林窟党项蒙古政权时期的壁画艺术》,《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12页。
25王晓玲《跨世纪西夏佛教美术研究论略》,《大众文艺》,2011年第24期,第52页。
26顾颖:《西夏时期敦煌壁画的变调与创新——敦煌壁画研究中被忽视的方面》,《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