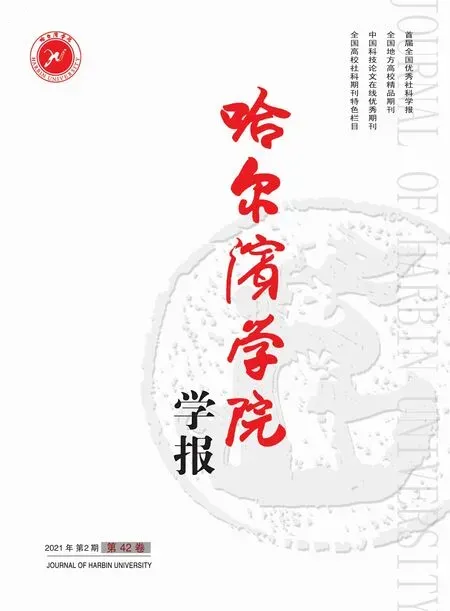行政强制执行和解的实现:以制度设计为抓手
庞圣浩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一、行政强制执行和解的含义与理论支撑
“和解是私力纠纷解决机制,意味着当事人希望通过互相让步的方式定纷止争。”[1]该制度最早出现于民事和行政复议领域,但随着“执行难”问题的出现,逐渐被引入执行程序中,随后《行政强制法》又以法律的形式开创了执行和解立法之先河。
执行和解的研究应以强制执行为基础展开。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国家运用强制力保障行政决定的实施,是“损益性”的公权力。[2]随着现代法治化的推进,强制执行的方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柔性”的强制执行和解制度便应运而生。《行政强制法》于2012年明确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指在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就执行标的的部分或全部,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达成的执行协议。[3]该协议以化解纠纷及实现行政决定为目标,仅指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对履行的时间和方式进行协商进而达成的执行协议。该制度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还以其独特的“柔性”化解了纠纷,符合现代政府执政方式。
然而,现实的制度落实往往需要理论上的长期博弈与支撑,从执行和解理论的提出到制度落实经历了数十年,这意味着立法者对相对人权益保护的谨慎,也体现了公权处分的理论障碍。传统观点坚持行政权不可处分,但随着执政理念的转变和公民权益诉求的增加,实践中的执行和解已屡见不鲜。一方面,为了确保个案正义,我国行政领域引入了自由裁量权,针对具体案件可以进行适当的权力处分。同时,为了促进行政执行手段的多元化,“又引入了行政指导、行政合约等柔性执法方式”,[4]这无疑承认了行政权的可处分性,也为执行和解的设立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因协商民主论的兴起,国外的“柔性”执法早已成熟完备,如美国的ADR模式以及法国调查专员制度,[5]这也间接的促进了我国执行和解的发展。笔者认为,执行权作为公权力实际上来源于私权利的让渡,所以两者在根源上同出一处,并非不可处分,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协商,进而达成执行协议。
二、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化解纠纷,还丰富了我国行政执法方式。但由于对具体制度的规定匮乏,导致在实际运用中仍产生不少问题,使得制度初衷未能很好实现。
1.缺乏对和解主体的相关规定
行政执行和解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利益的平衡需要当事人之间的充分协商,不仅要求协商涉及的内容全面,还要求参与的主体全面,要求有利害关系的适格主体必须参与其中。然而《行政强制法》仅规定了一般情况下的行政参与主体,对于实际运用中的特殊情况未预先规定,这不仅加大了执法成本,还不利于相对人权益的保护。
2.缺乏对和解协议形式、效力和性质的相关规定
和解协议作为执行和解的结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立法规定匮乏,以及相对人的法律意识不足,往往导致协议执行的中止或中断,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还会激化固有矛盾。主要存在下列问题:首先,立法没有规定协议应采用书面还是口头形式,口头形式不仅容易引起纠纷,还容易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其次,立法缺少对和解协议的效力规定:(1)并未规定和解协议一旦达成执行程序就应当停止,这意味着和解协议及执行程序同时对被执行人生效;(2)并未规定在恢复强制执行后和解协议是仍然有效、当然无效、还是应当依法解除;(3)并未规定协议对参与主体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将产生何种效力。
3.缺乏对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
程序不仅是参与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重要保障。但由于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导致了行政诉讼法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典,在执行和解领域亦是如此。立法未规定程序的发起、内容的协商、协议的签订与备案等具体程序,不仅不利于规制行政行为,还无法保证执行和解制度的落实。
三、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从和解主体、和解协议与程序设计出发,完善制度上的不足。
1.明确执行和解的适用主体
执行和解的参与主体包括:行政主体、相对人、人民法院、第三人。首先,法院并不是行政行为的作出者,没有实际的处分权,所以不是执行和解的适用主体。对于第三人而言,为了保护其权益、节约诉讼成本,应赋予其一定的异议权促使其参与到协商之中。相对人必须与协商内容有一定利害关系,享有对自己利益的处分权。因行政活动的特殊复杂性,主体资格往往会发生变化,下文主要针对行政主体资格展开论述,参照行政诉讼的被告来确定。
(1)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行政复议实际上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纠错机制,由上级机关对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行为做出改变。若复议决定是维持,那就意味着复议机关没有行使处分权,此时的和解适用主体是原行政机关;若复议决定是改变,那么就由复议机关和相对人来进行协商和解;如果在期间届满后,复议机关仍未作出处分行为的,实则是复议机关的不作为,那么此时原行政机关是和解的适用主体。
(2)作出执行行为的机关被撤销。和解的适用主体原则上是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和相对人,但难免会出现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导致行政机关被撤销,此时由其职权的承受机关来代替其主体资格;若不存在职权承受机关,则由作出撤销行为的机关来参与协商和解。
(3)经批准的案件。该类案件是由下级机关来具体实施,但上级机关才是权利的享有者,理应作为和解的适用主体,具体以对外生效的法律文书上的签名盖章者为准。
(4)执行行为由派出机关或派出机构作出的案件。首先就派出机关而言,法律明确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可以独立行使权力并承担责任,所以派出机关理应作为和解的适用主体;而派出机构则要看是否授权其相应的主体资格,如果有明确的授权,那么派出机构可以作为和解适用主体,若没有授权,则由机构的设立机关来参与协商和解。
(5)组建或受委托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案件。组建机构往往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但实际上却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不能独自承担法律责任,此时应当由相应的设立机构作为和解适用主体;而受委托的行政机关在本质上和组建机构一样,虽然在受委托的情况下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但也应由委托机关来作为和解适用主体。
(6)多个机关联合执法的案件。该类案件意味着多个机关同时对某一活动作出行政行为,这些机关都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根据民法的相关原则,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些机关都应当是和解的适用主体。
(7)和解协商的内容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案件。若是协商的结果纯粹是有益于第三人或者并没有对其利益产生影响的,那么协商并非需要第三人的参加,此时其不是和解的适用主体;但协商的结果有损第三人合法权益或增加其负担的,则应通知第三人作为和解适用主体参与协商过程。
2.完善和解协议的形式与效力
和解协议是行政与民事合同融合下的产物,从性质上来看是行政合同。作为执行和解的核心内容,完善和解协议相关规定可以确保执行和解的有效落实。
(1)明确和解协议的形式。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在规范行政行为的前提下保障参与主体的利益。例如,在相对人利益保护中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相对人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时须以书面形式表达,体现了行政权的正式与严谨。笔者认为,执行和解本质上也影响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采取书面形式不仅有利于证据的收集与认定,还有利于事后对案件的监督与审查,可以确保执行和解的有效落实。
(2)明确和解协议对执行程序的效力。和解协议不仅影响实体,还对程序产生相应的效力。应借鉴民事诉讼中相关规定,倡导以行政立法的形式明确:一旦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应裁定中止执行程序;当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时,裁定执行程序终结,进而赋予和解协议对执行程序的法定效力。具体则由行政机关来裁定中止或申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
(3)明确恢复执行时协议的效力。当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应恢复执行程序,此时协议应当主动依法解除而非无效。首先,只有合同违反法律或损害公共利益时才会导致无效,而当事人的不履行并非合同的无效事由,所以协议依然有效,不履行一方构成违约。其次,如果认为协议当然无效,那就意味着不履行一方不构成违约,这间接给予不履行行为以正面肯定,导致了理论上的悖论。
(4)明确和解协议对实体产生的效力。首先,和解协议具有对被执行人的约束力。和解协议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签订的,协议一旦生效,便对被执行人产生相应的拘束力,其必须在协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并积极履行义务。当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时行政主体有权恢复强制执行,这无疑也体现了对被执行人的约束。其次,还要明确和解协议没有执行力。一方面,协议是双方合意达成的结果,并非行政权的单方意思体现,不具有强制执行性;另一方面,和解协议的存在也没有终止原有行政法律关系,从相对人不履行就恢复执行来看,协议并非执行的依据。再次,协议具有对行政主体的规范力。虽然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先权,但这种权利仅在为了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方能行使。在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不得随意改变,体现了对行政主体的有效规范”。[6]法律并没有规定行政主体违反和解协议的制裁手段,导致了立法上的漏洞。最后,对第三人在特殊情况下的执行力。和解协议的达成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协议内容纯粹有利于第三人,那么该协议始终对其产生执行力;但当协议损害其权益时,未经第三人同意,该协议不对其生效,不具有相应的执行力。
3.完善执行和解的程序设计
完善具体的程序设计可以保障执行和解制度的有效落实。因我国的执行分为行政自行执行和申请法院执行,所以对应的执行和解制度也存在些许差别。从总体的程序设计而言,主要包括和解的发起、主体资格的审查、协议的协商、签订、审查、公告等内容。
(1)发起。执行和解的发起主要包括发起的主体和时间。首先,就发起的时间而言,行政法上规定为“实施行政强制执行阶段”。笔者认为该规定不够全面,容易误让人们以为和解的发起必须在行政机关决定或法院裁定强制执行之后。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催告以及执行的决定阶段皆可适用执行和解。所以应明确规定:无论行政自行执行还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在催告发出后到执行程序终结前,都可以提出执行和解的申请。其次,关于发起的主体,笔者认为应从和解协议的性质来分析。和解协议具有双方性和灵活性,任何一方皆可发出执行和解的请求,但都需经相对方同意后方能达成协议,而且参与方需享有相关权利的处分权。因此,可以采取行政机关依职权、相对人依申请相结合的发起方式。此外还要明确,法院并不能作为和解的发起机关,但在具体的适用中可以享有一定的建议权。
(2)对请求主体及内容的审查。为了保证和解请求权的正确行使,防止作为拖延执行的规避手段,行政主体应及时对请求主体和内容进行审查,看是否有损公共利益或涉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请求的内容涉及案外人合法权益,应及时通知其参与和解协商过程,保护其合法权益。一方面应审查其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及相应的处分权,另一方面还要审查其是否主观上愿意履行,但却存在客观上的履行不能。如审查结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应驳回其和解请求,继续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此外,为了有效防止制度滥用,还应主动区分请求主体的主观意愿并规定相应的申请次数。如果请求主体主观上是恶意,那么应当及时恢复执行并且剥夺其和解申请权;但如果其主观上是善意,此时在行政执行效率的要求下,只能给予其特殊情况的申请权。
(3)协议协商。参与主体应秉持自由与公平原则进行充分协商,所达成的合意不得违反公序良俗或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行政执行效率,应明确和解的时间限制,原则上应在和解的提起阶段完成。比如,相对人在催告期间提出和解申请的,理应在执行决定作出前达成和解协议,否则行政机关有权终止和解并作出强制执行的决定。如果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则可将和解期限延长至执行程序终结前。
(4)协议签订。协议的签订暗含着当事人对权利义务分配的认诺,并通过法定形式赋予合意相应的效力。因此,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明确记载双方当事人的名称及权益分配,方便事后的证据收集与认定。此外,为了确保执行和解的行使规范,还应明确和解的请求和协商形式。关于和解的请求,原则上双方当事人都应采取书面形式,但考虑到相对人存在书写困难的情况,可赋予其相应的口头申请权。但为了实现高效便民原则,对协商的形式不易做过多规定,只要能够确保协商充分,都应承认其形式上的合法性。
(5)协议审查。和解协议的达成源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权力的行使势必要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督。笔者认为,对和解协议的审查需要明确审查的主体和审查标准。就审查主体而言,对于行政自行执行案件,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审查;而对于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则应当由被申请法院和上级机关联合审查。这是因为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仅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往往会导致合理性的审查缺失。关于审查的标准,一方面要审查双方协商是否自愿,另一方面要审查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内容是否合法。
(6)协议公告。执行和解必须遵守行政公开原则,确保整个过程的公开透明。具体应完善公告制度的适用,如应在主体资格审查后或协议签订后及时进行公告。公告可发挥社会监督的效力,还能保证利害关系人的及时参加,不仅降低了执法成本,还可以确保执行和解的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