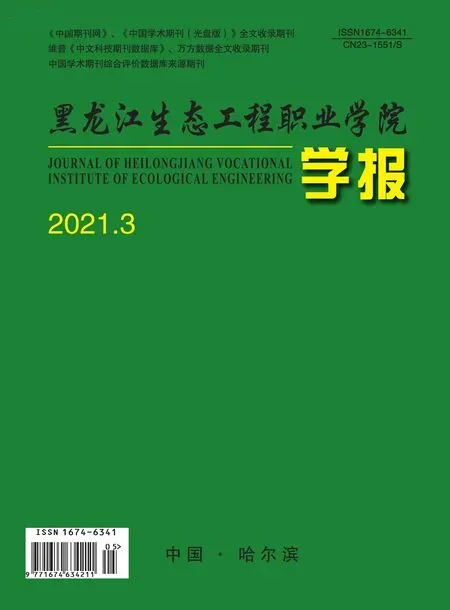“关系”视角下的青少年“网络圈群”研究
卓皓洁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网络圈群”是一个新兴名词,与其相关的研究较少,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给“网络圈群”下了不同的定义。段洪涛和赵欣认为,“网络圈群”通常意义上是指网友群体因某种特定原因组合而成的网络聚合空间,它分布广泛、类型多样、话题丰富[1]。刘广乐认为,“网络圈群”是指人们利用微博、微信、QQ等自媒体平台,以兴趣、地缘、工作事务等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网络社交圈群[2]。高丽静和王秋慧认为,所谓的“网络圈群”指在网络空间中因共同的爱好、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原因组合而成的聚集空间[3],在原有的现实社交圈之外,重建社会关系,再融合形成新的网络群体空间。从以上学者的定义中可以总结出“网络圈群”的核心概念:“网络圈群”指人们在共同的或相似相近的爱好、学习工作生活需要、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观点、社会认知等因素的驱动下在网络空间中集群结社,整合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聚集场域。
“网络圈群”由于网络的参与,其建立不受地域、时间等限制,交流的方式和“圈群”的种类更新潮多样,“圈群”的加入和退出也更为灵活。随着个性化浪潮袭来,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不断提高,在网络上披露喜好、日常生活、态度看法、心情好坏等行为,给青少年带来“分享”的愉悦感。并且,青少年是社会中的人,有从社会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不断流动和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化的需求。由此,门槛低、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自由度高、涉及面广和承担一定个体与群体联结的“网络圈群”备受青少年群体青睐。
1 “关系”视角下青少年“网络圈群”的类型
根据成员之间关系联结的强弱程度,可将青少年“网络圈群”类型分为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
强关系型“网络圈群”往往是青少年基于现实生活中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建立的,如家庭群、班级群、师门群、宿舍群、同事群等。这类“网络圈群”更多是以QQ群、微信群等形式存在,建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联系、交流和分享信息。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重合,以及相对封闭的信息传播环境,使得成员之间呈现出强关系,覆盖精准,互动频繁。强关系型的“网络圈群”稳定,不仅表现在成员之间的关系稳定,还表现在成员的数量稳定,成员角色定位清晰,“网络圈群”中具有组织的目标和稳定规则,而且“存活”时间也较长,常规情况下只要社交媒体平台不消失,强关系型“网络圈群”就不会解散。青少年在强关系型“网络圈群”中多参与与生活、学习、工作相关的活动,真实身份的参与意味着每个人是实名制的,成员之间都是互相熟知且了解的,这无形中给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造成一定的约束。
弱关系型的“网络圈群”大多是青少年基于兴趣爱好或者对热门事件的讨论在微博、贴吧、论坛等公开性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的。相较于强关系型“网络圈群”,弱关系型“网络圈群”往往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更大;同时,投入的热情和时间成本也更多,有些青少年甚至会牺牲休息的时间。这类“网络圈群”虽然相对不稳定,随着兴趣的消逝和事件的平息,成员会频繁地加入和退出,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角色定位也相对模糊,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规则,但其中交流的信息对青少年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影响很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青少年能够迅速领会“网络圈群”中的信息和价值,并作出行为反馈,这类“网络圈群”的影响力甚至超过老师、家长等传统权威。弱关系型“网络圈群”中的成员之间处于一种“暧昧”状态,身份的缺席也会导致情感的缺失,但身份的缺席以及基于兴趣的狂热容易使青少年发生偏离正常轨道的行为。青少年在“网络圈群”中,不论是与组织还是个体的社交关系往往是“若即若离”的,彼此之间的“距离”虽然近了,但“心”却远了。
2 青少年“网络圈群”的关系分析
2.1 虚实共生
从交往场景的角度分析,“网络圈群”是网络上虚拟的社群,同时依托现实关系存在。青少年基于地缘、血缘、趣缘等因素在网络空间建立圈群,从而突破现实场景中交往的距离,增加交往的粘性。青少年在“网络圈群”中发布信息、寻求同伴,将二次元中的活动延伸到三次元,可以拓宽和丰富青少年现实中的社会关系,青少年“网络圈群”中虚拟和现实交往场景共同存在。
从青少年社会化的角度分析,在真实的情境中,青少年会通过相对熟悉且彼此包容的共同体或组织与“大社会”建立联结,形成“个体—共同体—社会”的基本结构,这里的共同体既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学校或其他组织[4]。青少年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学习文化知识、形成价值观念和掌握生活技能,与共同体或组织互动学习,最终发展健全的人格,从而完成社会化[5]。现实生活中的共同体或者组织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和约束性,但追求个性、强调展现自我意愿的青少年,需要更加便利直接的与社会对话的平台。由此门槛低、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自由度高、涉及面广和承担一定个体与群体联结的“网络圈群”备受青少年群体“宠爱”。“网络圈群”帮助他们在一个比以往更加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和社交,厘清个体身份和群体归属,发展形成自己的个性从而成功参与社会生活。
概言之,青少年通过网络这个虚拟的工具,联结人际关系和完成社会化,“虚”与“实”并不冲突,两者是一种共生关系,相辅相成,两条“线”将青少年的社会关系串联起来编织成为“网络圈群”。
2.2 封闭排他
从宏观角度来看,网络空间具有开放、共享的特征,技术的发展使得青少年通过搜索引擎具体化搜索就能找到想要进入的兴趣圈群。但从微观上来说,网络空间被细分为若干个“网络圈群”,不同“网络圈群”之间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旨趣以及目标,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排他性。
封闭排他性一方面体现在进入“网络圈群”存在一定的“门槛”,需要通过特定的认证。例如,加入部分QQ群需要填写认证信息,管理员通过后才能被允许进入;加入粉丝群需要提供关注该明星所有微博超话的截图,购买该明星代言产品的记录,发表应援和支持该明星的微博等来证明粉丝身份。这些“网络圈群”是通过设定一定的“准入机制”的方式形成群体关系,使得圈群的封闭排他性较为突出。
另一方面体现在“网络圈群”中青少年信息获取的局限性和信息传递的加密性,导致信息封闭性增强。信息在进入“网络圈群”时需要通过一张“过滤网”,青少年主动筛选自己关注的信息进行接收,其他无关信息止步于圈群外。由此带来了青少年所了解到的信息高度相似,同质化严重。并且,“网络圈群”内语言的符号化使得圈群外的人无法“破译”青少年传递信息的话语,例如运用一些缩写字母、表情、颜文字等符号来交流,青少年会赋予这些符号以特殊意义,只有同一圈群的成员才能读懂这些符号的含义,就如同给信息加上了密码,这样一来圈外人很难知晓圈内的话题讨论内容和成员结构。
2.3 套嵌叠加
青少年“网络圈群”虽然具有一定的封闭排他性,但并不是绝对的,多数圈群的“边缘”较为模糊。学者李彪认为,圈群是指社交网络中所存在的不同圈子之间相互嵌套、叠加所形成的多重现象。圈群的概念一方面承认独立的社交圈子的相对闭合性,另一方面更强调这些圈子之间的嵌套、叠加的存在方式[6]。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人群社交结构的“差序格局”与“网络圈群”嵌套叠加的特点相似。他认为个人以“己”为核心向外推出的层层叠加由近及远的圈子就是“差序格局”,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仿佛扩散出去的一个个圈子,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7]。青少年处在“网络圈群”的中心,通过与不同的节点(兴趣、获取信息、表达思想等)连接嵌入到不同的“网络圈群”中,并随着圈群的扩大不断拓展自己的社会网络。例如,班级群根据目标的不同可以分化成宿舍群、卫生小组群、课题作业群等,青少年在不同的群里与不同的同学达成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粉丝群根据对明星不同类别的喜爱分为唯粉①群、CP粉②群、妈妈粉③群、男友粉或女友粉④群等,这些圈群之间存在一个交叉互嵌关系。青少年可以既是该明星的唯粉,也是该明星的妈妈粉,可以喜欢多个明星,同时活跃在不同的粉丝群里。
3 青少年“网络圈群”社交的关系隐忧
3.1 社交圈窄化
社交媒体的智能化致使大部分APP中存在“猜你喜欢”“你曾浏览过类似的”和“你关注的人关注的”等页面,即使没有设置这些页面,在使用时也能感觉到系统推送的内容都是自己所喜欢的,会情不自禁地一直浏览。一方面,这种智能推送确实能够节省用户的时间成本,省去了用户自己搜索的精力。用户对APP的满意度提高,同时APP也实现了留住用户的目的,达成了表面上的双赢。青少年也通过社交媒体认识到更多有着相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甚至相似的三观的“知己”,看似拓宽了青少年的社交圈。但另一方面,这些APP的智能化只是让用户活在自己喜好的世界里,因为只有用户乐意点开的内容才有流量。长此以往,人人皆将成为“井底之蛙”,天真地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网络圈群”的封闭排他也使得圈群内外的信息传递闭塞,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中所谓认识的“新朋友”,进入的“新圈群”可能并未跳出原来的圈子,社交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拓宽并有逐渐窄化的隐忧。
3.2 虚假充实与真实孤独之间的恶性循环
相关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孤独程度与青少年对一些社会化媒体如微信的使用频率呈正相关。陷入社会化媒体沉迷中的青少年会产生短暂的“虚假的充实感”,然而当他们从这种“短暂的快感”中苏醒过来后则是面对现实更多的茫然与孤独,形成虚假充实与真实孤独之间的恶性循环[8]。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种社交软件、短视频APP、游戏等的层出不穷,丰富了人们消磨闲暇时间的方式。有网友通过改编歌词“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手机”来调侃现代人的社交现状。青少年在“网络圈群”中获得了乐趣,满足了社交需求,反而可能疏忽了对现实中的友情和亲情的维系。“网络圈群”毕竟是虚拟的场景,太过于沉迷其中会与现实社会脱节。互联网的发达使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获得一切需要的资源,这也是近年来患“社交恐惧症”的人数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青少年在“网络圈群”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自由,却也忍耐着群体缺失的孤独。网络世界中的“社交达人”可能是现实中的“孤僻者”,网络社交的低成本和易得性使青少年易产生友情“唾手可得”的错觉,彼此尊重的交往原则逐渐模糊。
3.3 隐秘越轨与集体失范
“网络圈群”的匿名性和隐秘性,给了心怀不轨的人谋害他人的“舞台”,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肆意“表演”,来无影去无踪。韩国发生的“N号房”事件中,犯罪分子利用聊天软件Telegram不能追溯信息源头的特点,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寻找未成年少女拍摄淫秽、虐待、色情的视频,在聊天室中公然向各国网友贩卖。据韩国官方报道,有74名女孩受害,其中16名女孩儿未成年,最小的仅11岁。而“N号房”的创建者竟是一名高中生;已逮捕的运营者中年纪最小的12岁,其中主犯“赵博士”才25岁。该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犯罪分子利用聊天软件的匿名性和隐秘性进行集体犯罪,其中不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存在青少年群体。青少年心智尚不成熟,易被错误的价值观和信息所误导,青少年接触越轨群体越密切,自身产生越轨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3.4 公私模糊
青少年通过发朋友圈、发微博、发QQ空间动态等方式在各种社交软件中塑造自己的“软形象”。许多自媒体人和“网红”也通过剖露自己的私人生活或分享自己的日常爱用品来吸引眼球和流量,有一部分影响力的还可以通过品牌推广获得收益。这些行为在展示个性的同时也在挑战着公共伦理:当私人生活公共化能带来利益时,在网络上“自我披露”的行为就变质了,人们不再单纯地记录生活,一切行为都被染上了“商业色彩”。在这其中,私人生活暴露在大众视野中,更有甚者为了博得关注做出违反法律和伦理的行为。在这种网络氛围中,青少年会沉迷于扭曲的个人主义,逐步迷失自我,丧失应有的价值判断,而原本能够带来新鲜思想、产生文化碰撞的“网络圈群”也会逐渐变得“娱乐至上”“乌烟瘴气”。
4 青少年“网络圈群”社交的关系重建
4.1 合理规范监督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首先,政府要完善相关立法,加强网络执法力度,对违反公共伦理秩序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2020年4月7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公布了主播黑名单,被列入黑名单的主播将在行业内禁止注册和直播,封禁期限5年。这一行为不仅对有违规行为的主播进行惩罚,同时也给在规则边缘试探的主播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提高法律意识,有效掌控影响力。其次,网络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各大游戏和自媒体平台等的规范管理。目前青少年使用较频繁的社交软件、游戏软件和视频软件等均推出了实名认证和青少年模式,为青少年用户营造了绿色健康的网络空间,同时也限制了青少年上网游戏、娱乐的机会和时间。最后,落实网络举报制度。多数APP均设有举报制度,但落实力度还不够。用户举报之后,难以确保被举报的信息是否及时封禁,发布违禁信息的人是否得到警告和惩罚。良好的网络环境是青少年在“网络圈群”健康活动的“氧气”。应扩大相关部门的人员配置,及时处理举报信息,优化网络资源,为广大青少年提高道德素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4.2 正视网络社交行为
愈来愈发达的网络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和社交方式趋向智能化和虚拟化。指出“网络圈群”中的隐忧并不是要扼杀它,合理利用使它带来更多便利和益处才是明智之举。应该认可青少年通过社交软件新形成的各种“网络圈群”,在这里不同的思想和观点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有助于锻炼青少年的发散思维和辩论思维,建立新的社会化平台。2020年1月18日浙江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芳根在会上对与会的教育工作者发出的灵魂拷问走红网络。他提到青少年当下喜爱度较高的几款游戏,较受青少年追捧的明星演员和青少年常用的新潮的网络用语并提问台下的教师是否了解这些,认为如果不了解,就引领不了青少年。网友纷纷为该厅长的发言点赞并善意地调侃“他知道的太多了”。要想更好地引导青少年,就需要深入了解青少年,了解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专属语言,了解他们的追崇和信仰,打入青少年“网络圈群”内部。
4.3 强调“自治”
一方面,应该相信青少年具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因为,在风来的时候适当地放线,风筝才能飞得更高。青少年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教师、家长和朋友可以给与建议和引导,但不能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是否具有自我治理能力是“网络圈群”能否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网络圈群”简单的权力结构,使成员之间互相平等但存在一定的约束。“网络圈群”是由于相同的喜好和价值认同而形成的,这在无形中也是一种约束。“网络圈群”内部也存在成员们共同认可的“公约“。微博“超话社区”中的“超话”管理员在置顶帖中发布“超话”规章制度,发言内容不符合规定的便会被禁言处理或者屏蔽,严重者甚至会被踢出“超话社区”。充分发挥青少年个体和“网络圈群”的“自治”能力,强调主体意识,提高青少年信息素养,是处理好各种网络“关系”的根本。
5 结语
“网络圈群”作为一种独特新颖的组织形态,既可以成为青少年与群体和社会联结的“桥梁”,帮助青少年积累社会资本;也可能成为青少年群体失范和违法犯罪的“沼泽”,引发青少年的越轨行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以积极正面的眼光看待“网络圈群”中的社交行为,以严格的标准把准“网络圈群”中的风向,把握好“虚”“实”之间的度,使“网络圈群”成为青少年拓宽社会关系、完成社会化的优质场域。
注释:
①唯粉指只钟爱单一明星.
②CP粉指想象该明星与其他明星为“情侣”.
③妈妈粉指将明星看作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以妈妈的心态喜爱明星.
④男友粉或女友粉指将明星想象为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