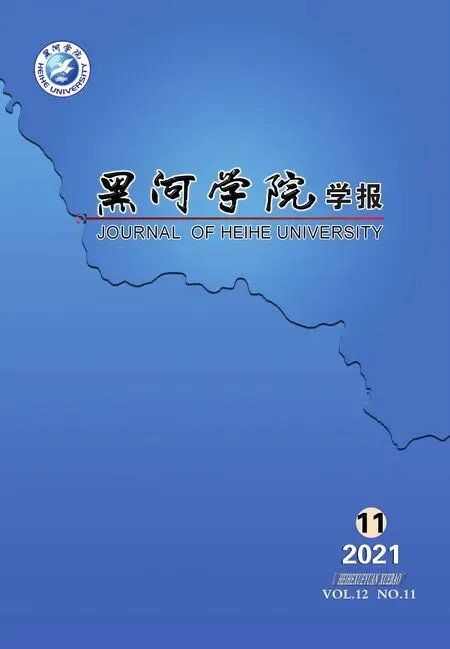浅谈从歌剧《蝴蝶夫人》中表现的东方主义与性别问题
张 倩
(谢菲尔德大学,英国 谢菲尔德 S10 2TN)
19世纪末,普契尼作为威尔第之后又一意大利歌剧的代表人,其作品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在歌剧创作中,一方面,沿着意大利歌剧的传统路线,继承了意大利歌剧以旋律流畅的管弦与色彩丰富的和声为作曲基础,在歌剧中加入现代元素与东方主义。另一方面,普契尼作为一名具有代表性的真实主义歌剧作家,在其作品中选材总是来自底层的弱势群体,尤其体现在歌剧中塑造的多个带有悲情色彩的女性形象中,由此来展现出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普契尼在歌剧中通过音乐语言刻画人物的心理描写,使人物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大部分的女性角色在歌剧的末尾都以结束生命来成就戏剧化的效果,使歌剧在内容上达到将戏剧性与抒情性相统一。虽然1904年在斯卡拉首演时是失败的,但普契尼最终用艰难又漫长的创作历程成就了至今依旧在欧美各国剧院表演的《蝴蝶夫人》。至少从流传度这一方面上,能够体现这一作品是成功的[1]。但对于从未踏足过东方国度的普契尼来说,这部歌剧在创作上与艺术加工的处理上是用西方人想象的日本以及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创作的。描述的东方是带有自己主观性而并非真正的东方,这种并非将东方作为故事主体的角度带来的影响是有限与短视的,这也就使普契尼在歌剧中对东方艺术的处理有失偏颇。
桑德拉·库马莫托·史丹利(Sandra Kumamoto Stanley)认为,《蝴蝶夫人》这个故事不仅是一个东方主义的故事,也是一个展现跨越国家、种族和物质界限文化碰撞的故事[2]。这说明在整个歌剧的研究中,应将用东方主义的思路去审视分析作品。因此,为更好地理解歌剧《蝴蝶夫人》的东方主义文化与性别的联系,笔者将对歌剧中表现的东方主义进行分析。首先,探讨东方主义的概念,并以《蝴蝶夫人》为例探讨歌剧中体现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及作品与东方主义的联系。通过歌剧中的角色、音乐、情节等方面谈论歌剧中对东方女人的刻板印象。其次,批判性思考,为什么《蝴蝶夫人》展现的是东方主义,而非传达文化的多样性问题。最后,通过查阅相关学者的研究,讨论普契尼所创作的歌剧中的悲剧性角色,批判性思考这部歌剧所表现的性别问题,并且思考东方主义中的父权制思想对女性的影响。
一、《蝴蝶夫人》中的东方主义
1.东方主义的内涵
1978年萨义德(Said)出版的一本受到争议与批判的著作《东方学》,第一次创造性地使用了东方主义这一名词。在书中萨义德首先定义东方的范围,认为由于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不同,将亚洲定义为东方,包括近东、中东、远东地区,甚至还有俄罗斯和原来的东罗马帝国。虽然萨义德主要指的是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文明,但其理论同样适用于任何非西方的文化,因为萨义德批判的主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 东方主义是指西方对东方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的研究。可理解为西方作家、艺术家对东方的描绘与模仿。例如,东方主义者专注于伊斯兰法、印度宗教、中国语言等东方事务[3]。在《东方学》中,萨义德首先质疑了西方研究东方这门学科中,对东方的研究是基于西方立场的想象的建构,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蔑视东方文化,用一种以西方中心式文明的,高高在上的视角俯看边缘的、野蛮的、低级的东方,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带有偏见性的一种思维方式。
在近几百年来,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飞速崛起,使欧洲取得了世界的话语权。在同一时期的西方人带着坚船利炮到来探索东方时,整个亚洲毫无工业可言,最发达的东欧也只处于半工业化时代。这样使东方地区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东方主义中东方代表着落后,弱小,不理性的,欧洲则与之相反[4]。所以,强大理性的、成熟的、积极的西方人为东方人担负起再现历史、文化及未来命运的使命。从185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通过粗暴的制定法律,建立针对东方的研究机构,来控制并统治东方。由于东方主义涉及东方国家几乎都是旧殖民地,而西方国家作为旧宗主国,在赛义德的视角里,东方主义就体现了后殖民主义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不平等关系。本意上是西方人想在文化、思想、精神上控制东方,例如,在印度、埃及等东方国家进行殖民,并承认这种行为的合理性。
换句话说,东方主义是西方人自我构建了一个面目全非甚至本来可能不存在的东方。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的观点同萨义德有些相似,认为西方男性将政治、经济方面教育和控制东方作为集体目标,尤其体现在对东方女性和对充满神秘的东方的追求与探索。本质上,东方主义既是整个西方社会尤其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对拥有东方的外在欲望,也有对东方的内在欲望[5]。关注东方具有吸引力的一面,但这些所谓的吸引力往往是西方人自我想象出来的非客观的东西。在“西方”的观念、制度和政策中,长期积累的那种将“东方”假设并定义为专制的、异质的思维,甚至将东方放置到西方的对立面,可以说,“东方人”是被动地被西方人自我构建出来的一群人,用来区别自我与他者。通过赋予“东方”不属于西方的、异域风情或野蛮的特质,来确立西方的主体性和优越地位。不可否认,当今在文化上的话语权还是由欧美主导,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在影响着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弱势文化,在这样背景下,东方主义无疑是颠覆性地存在,是一套话语,其真实性取决于哪一方面更有话语权。
2.《蝴蝶夫人》中东方主义的体现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舰队驶入江户湾,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在美国的坚船利炮威吓下,被迫打开了国门。歌剧《蝴蝶夫人》的背景发生在1900年的长崎港口中,近藤道林(Dorinne K. Kondo)认为,《蝴蝶夫人》作者把“亚洲女人”和“西方男人”的关系与“亚洲”和“西方”的关系相提并论[6]。因为日本的“开放”并没有建立起与侵略者相同地位的“开放,所以,作品中巧巧桑与平克顿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平克顿是以俯视的方式和蝴蝶相处,认为自己是一个“流浪的北方佬”,无论在何处都能在想要停留的地方抛锚。平克顿在畅想得到一个日本女孩的快感,一个来自殖民国家的男性可以无视被殖民国家女性的权益。在平克顿的心中,一个美国的白人妻子,才是应该得到其妻子身份的人,而蝴蝶对其来说,只是一个天真烂漫给其异国情调与征服欲的新娘,在这里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自大、轻浮,同时,也为后面蝴蝶的悲剧做了铺垫。
一直以来闭关锁国的日本此时对西方人来说是新鲜、神秘而特殊的。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认为,普契尼的《蝴蝶夫人》(1904)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对日本所有事物感兴趣的结果[7]。但这种感兴趣并没能建立在平等的视角上,《蝴蝶夫人》第一部分中,作者运用西方人听起来具有日本色彩的五声音阶和调式和声,将蝴蝶描绘成既甜美天真,又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艺伎。在歌剧《蝴蝶夫人》中第一幕第一场就是巧巧桑演唱的第一首小咏叹调,这样的音乐背景给后面的悲剧结局做了前期铺垫。巧巧桑的唱段是 44拍,舒缓又优美的唱段表现此时其是沉浸于幸福与喜悦之中的。这时的巧巧桑想要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自己心中的爱人,完全没有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如何,轻信于平克顿的甜言蜜语,沉浸在自己想象的美好世界中。在音乐中能够感受到巧巧桑对平克尔顿的爱慕与崇拜,这样的崇拜在 16 岁有着天真烂漫新娘的心理,小咏叹调能够将女主人公本身性格的天真烂漫与忠贞不渝的特点表现出来。拉尔夫·洛克(Ralph P.Locke)认为,最能体现东方主义者的一处是,唱到:I am the happiest woman in Japan,东方女性渴望爱情与美好生活,能嫁给带她走出困境的美国人,才是最幸福的人[8]。在这里也是令人伤感的,亚洲女性是需要要被白人男性拯救的,同时,亚洲女性成为取悦西方男性的一种商品。巧巧桑的性格与品质都表现在在普契尼描绘的真实和虚构的日本民间旋律的使用中得到了表现。
巧巧桑在与平克顿的婚礼后完全屈服于其丈夫。在一个戏剧性的时刻,蝴蝶的叔叔,一个佛教牧师,进来谴责蝴蝶决定抛弃她的祖先,接受基督教。即使被家人反对与抛弃也选择跟随平克顿的信仰,信仰基督教并且认同美国,巧巧桑将自己当做美国人。巧巧桑认为她与平克顿建立的是了美国式的婚姻,事实上,巧巧桑从未得到过平克顿对其身份的认同。平克顿认为,巧巧桑是一只蝴蝶,尽管蝴蝶表达了其对外国习俗的恐惧,因为在那里蝴蝶被“用针扎了”,但平克顿向其保证,这只是为了防止蝴蝶飞走。在这里也象征着东方需要西方的拯救才能脱离困境,然而巧巧桑最后的结局还是切腹自尽。正是有这种观念在先,在歌剧《蝴蝶夫人》中巧巧桑成为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在普契尼的歌剧中,女性的死亡是必然性的,尤其巧巧桑是需要取悦男性客人的日本艺伎。史蒂文认为,这是对日本女性的典型西方比喻[7]。像大多数西方人创造的日本人一样,白人男性给予的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甚至超越了生命。当巧巧桑在院子里看到一个白人女性,便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这就等同于丧失了荣誉与希望。为了荣誉巧巧桑一定会为之付出生命。最后死亡的结局也是以固有的形式出现的,巧巧桑是切腹自尽的,这种自杀方式在西方通常与日本联系在一起,在西方固有印象中,日本人是谨小慎微,谦逊而沉默的人,生命如蝼蚁一般脆弱。歌剧中蝴蝶说的话和做的事强化了人们对“日本女人”这一类别的刻板印象:忠贞、顺从、无悔为白人男性付出。蝴蝶夫人正如其名字一样死于刀下。
在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普契尼所创造的《蝴蝶夫人》中所表现的东方形象与性别问题,一直存在在美国文化中[9]。20世纪以来,用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义,虽然这一现象从二战后有所衰退,但依旧在艺术作品中有所体现。东方女子被西方征服者玩弄并最终被抛弃,但其却无怨无悔地爱上了薄情的西方士兵,有着甘愿献出一切甚至包括生命和尊严的悲惨命运。正像从歌剧《蝴蝶夫人》到音乐剧《西贡小姐》,虽然《西贡小姐》中的克里斯(Chris)与金(Kim)是真心相爱的,但为了让孩子享受美国的香甜空气,金出于母爱的表现选择了自杀。歌剧《蝴蝶夫人》中平克顿对待巧巧桑就是玩物的态度,如果平克顿不知道还有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在,他一定是不会与巧巧桑见面,这何尝不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表现。史蒂文认为,夏普勒斯(Sharpless)的态度是一种未经检验的文化霸权态度[7]。作为这部歌剧的第三个主要角色,夏普勒斯是连接平克顿与巧巧桑的纽带,一方面,代表着比平克顿的成熟稳重,又包含对巧巧桑同情的声音。认为将孩子带到美国才是能为孩子带来美好生活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考虑巧巧桑的感受,尤其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男孩应该回到美国的想法。 被丈夫抛弃,孩子也被夺走,巧巧桑的自杀是绝望与无奈的。在歌剧中《蝴蝶夫人》的结局是残忍与凄美的。虽然《西贡小姐》在整个感情色彩上比《蝴蝶夫人》更温暖一些,金的自杀则更富有人情,没有明显的“谁统治了谁”。但这两部作品中,巧巧桑与金都以底层的东方妓女形象出现,都是为白人男性牺牲自己乃至付出生命的结局,这是西方艺术家对亚洲女性的刻板印象。《蝴蝶夫人》不但在作品中表现出了东方主义,也使得整部作品的感情基调就像是东方妇女控诉自己命运的悲歌。
3.批判性思考文化多元性与东方主义的不同
在很多中国文献中,只要是谈论蝴蝶夫人的,就一定以普契尼加入日本音乐要素为论点,论述普契尼创作的歌剧是文化多元性的一种体现。虽然在很多文献中都认同在意大利歌剧中加入日本的元素,是传达他国文化表现多元文化的一种方式。并且在对于与20世纪之交的欧洲,欧洲对日本的事物很狂热,甚至日本艺术被当做欧洲艺术家灵感来源的一部分[10]。但相比已经流行于欧洲百年的歌剧文化,刚完成明治维新日本在文化对外影响远不及经过巴洛克、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的欧洲艺术。日本还在学习西方的艺术与文化,从而获得西方对日本艺术的认可。在欧美很少有人承认日本的艺术形式,通过歌剧这一载体确实是一种向西方观众传达东方文化的一种途径。但多元化是要求保留其原有的文化与身份,每种元素都能在采用相同的地位呈现[11]。虽然在音乐剧和歌剧中用了笔墨去描绘了越南文化与日本文化,是歌剧刚开始出场的三个卑躬屈膝的日本仆人,以及为白人男性付出生命的巧巧桑,在这样一种艺术表现中,东方文化并不是艺术主体,而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主体则是欣赏歌剧的欧美白人。音乐剧《西贡小姐》的前身就是歌剧《蝴蝶夫人》,这部作品至今仍在各大剧院具有极高的演出率,桑德拉认为,虽然西方人已经把这个关于为美国男人而死亡的故事变成了极力推崇的作品,但在日本并不会大力宣扬《蝴蝶夫人》[2]。正是因为这部歌剧突出的是西方占主导的地位,白人男性可以玩弄具有顺从的、弱小的东方女性的种族化幻想事实上东方主义从来不是弘扬东方价值。以歌剧中东方女性对西方男性的忠诚,坚守与一厢情愿,提高白人种族的地位,传达西方价值。因此,在《蝴蝶夫人》中,以西方人的视角来描绘的日本并不是多元化的体现,而是东方主义的表现。
二、东方主义中的性别表现
1.普契尼对巧巧桑的悲剧性形象塑造
《蝴蝶夫人》中的东方主义还体现在用西方视角来描绘东方女性,给予东方女性刻板的印象。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是根据大卫·贝拉斯科(David Belasco)的同名话剧改编的,凭借饰演巧巧桑这一角色走向西方舞台的日本女高音三浦环(Tamaki Miura)是一个身材矮小,有着幼稚声音的女人,吉原真里(Mari Yoshihara)认为,正是因为东方主义者对日本女性有着刻板印象,作为歌手的缺陷也变为了恰到好处的适宜[12]。在普契尼的作品中,爱情是最直观的主题,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通过生动而具体的刻画和描绘,表现底层女性的悲惨境遇。由于普契尼本身属于真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样就会影响其所创作的歌剧内容,具有十分明显的真实主义倾向与真实主义思想。在普契尼的歌剧作品中,其用尖锐而集中故事情节和扣人心弦戏剧性冲突,给予观众悲剧性结局。例如《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角咪咪病死了,在《托斯卡》中,托斯卡壮烈地跳楼而死。而歌剧《蝴蝶夫人》是一部十足的悲剧,悲剧却又往往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悲剧的根源是来自于心中对美好事物的期待与热爱被抛弃或被破灭,所引发出一种强烈的痛苦。真实主义歌剧正是对现实人生悲剧的摹仿与表现。
歌剧一直与性别问题有着联系,南希·斯威夫特·弗洛蒂(Nancy Swift Furlotti)认为,《浮士德》与《蝴蝶夫人》中相似的部分,是因为巧巧桑和美国军官之间的故事代表着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浮士德内心与对理想女性结合的渴望,在平克顿的心中,得到一个美国白人妻子才是他应有的归宿,《蝴蝶夫人》所表现普契尼的内心世界,正是他的对女性的爱与矛盾[13]。普契尼也曾有过居无定所的生活,将现实的苦痛表现在戏剧中的内心呐喊,创造向观众传达悲痛与思考的悲剧性艺术角色。蝴蝶就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蝴蝶从天真善良的孩子变成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母亲,蝴蝶变幻的情感和思想使普契尼的歌剧成为一部的心理音乐剧,随着每个危机的困境展开,描绘了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的悲怆,以及她令人心碎的衰落勾勒出巧巧桑的柔情与绝望。也正是由于人物悲惨又充满戏剧性的遭遇,使得表现出作品凄凉的美感。
2.《蝴蝶夫人》中父权制的影响
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在欧美剧院内不断循环上演,象征着这是一部受欢迎的历史作品,涅维斯(Nieves)认为,作品中传播的性别歧视的问题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4]。诚然,这部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歌剧仍在发挥其影响,但并非这种影响都是积极的。巧巧桑受男权思想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巧巧桑完全顺从于美国丈夫,她放弃自己原有的信仰,在平克顿返回美国时,巧巧桑依旧等着丈夫,甚至穷困潦倒时拒绝别人的求婚。巧巧桑在意识到自己被抛弃后选择用生命保全荣誉,为了其美国丈夫,巧巧桑付出生命代价。在这里巧巧桑是没有有主见与自我意识的女性,甘心于女性的附属地位。父权制将女性置于夫权的统治之下,女性不应有获得各种权力的愿望,表现自我的欲望和发展独立的自我的行为,即女性要顺从、娇弱、温柔、体贴,不得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人们用传统的父权文化所规定的社会性别角色来衡量女性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所以,巧巧桑自杀行为即是对男性权力中心的顺从,也是父权社会所接带来的必然结果。
桑尼(Sunny)认为,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是欧美对亚洲殖民战争导致的结果,在以男性为中心和男性主导的场景中,亚洲妇女被视为满足西方消费和欲望的“商品”[14]。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将女性定位 于被动的“第二性”和“他者”,并要求女性“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将自己置于男性的保护和照顾之下。《蝴蝶夫人》刚开始像童话一样美好,巧巧桑以为她遇到了能够拯救其脱离苦海的人,不用继续从事艺伎来取悦男人。不幸的是巧巧桑看不到她所处的现实,也看不到向其走来的危险,从一开始巧巧桑的日本艺伎身份就没能获得平克顿真正的尊重。
吉原真里在她的文章中说道,《蝴蝶夫人》这部歌剧成为日本通过巧巧桑形象向西方展示的凭证,日本人用努力创造自己本民族的蝴蝶,一方面,象征着对西方霸权的抵抗;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父权性别政治和适合现代国家的女性形式的讨论[12]。一个符合传统父权文化标准的女性兼具女性气质的同时,按照男性的意志行事。歌剧中另一处表现男权主义的地方在于,巧巧桑受父亲的影响,为了保全荣誉,选择同父亲一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史蒂文认为,巧巧桑把剑对着自己,这正是一种男性至上的表现[7]。作为一个被遗弃的妻子和母亲,巧巧桑甚至不畏惧死亡,也想结束所谓的屈辱。没有意志掌控自己的命运,自杀是她唯一的权利。然而,在整个故事情节中,巧巧桑除了轻信了平克顿的誓言并没有什么过错,在男权社会中,以牺牲女性来结束这场悲剧的这一事件本身就具有悲剧性的。
三、结语
歌剧《蝴蝶夫人》是一部有着明显东方主义特征的一部作品,虽然这部歌剧已经跨越一个世纪仍然活跃在欧美剧院上,但这并不能说明这部作品是完美的。这部作品是以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刻画出巧巧桑这一角色,在歌剧中出现多处戏剧性表现,展现巧巧桑由一个天真美丽的少女沦落为被抛弃妻子的悲惨命运。在歌剧中可以看到巧巧桑受平克顿的影响,巧巧桑完全以平克顿为中心,丧失了自我,这个可怜的东方女子选择以自杀保存所谓的荣誉。另一方面,巧巧桑受到武士父亲的影响,选择和父亲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在西方人的眼中,日本女性应该是顺从,善良 听命于男性的。正因如此,普契尼才创造出一个受到男权主义思想影响的东方女性的。西方用高高在上的眼光俯视西方人认为的低级的东方,通过这部作品正是展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西方对东方的主体性与优越性地位,也可以说这部作品是非常典型的东方主义代表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