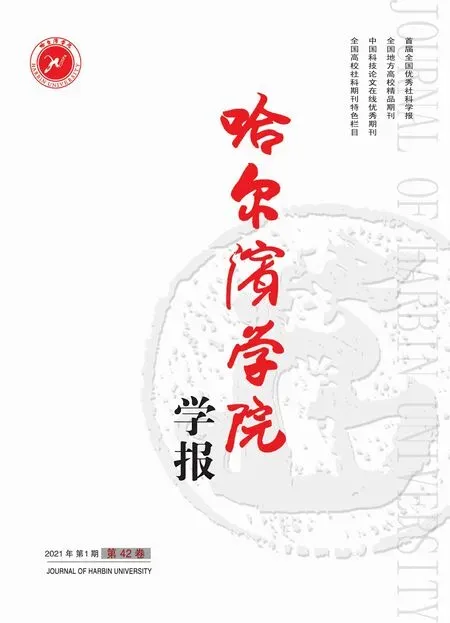赵树理小说创作对读者的预设研究
乔军豫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一、“铁笔”定位:“写农民”和“为农民而写”
从接受美学上讲,作家和读者是一对双向互动的关系。作家在创作时,潜意识中隐含阅读对象,希望自己的作品赢得更多的知音。这就需要作家对读者进行精心预设,盘算自己作品产生“磁场”的位置。反过来,读者也具有强烈的阅读期待,作品要合乎自己的“胃口”。在此愿望和要求下,作家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事先设定安排创作题材和内容以适应读者的需要和吸引读者的目光,从而使小说创作与读者的阅读期待能够契合。赵树理立志做一个“文摊作家”,真诚“写农民”和“为农民而写”。他出身农村,十分熟悉农村的现状,对农民的性格特点、思想感情、行为习惯、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细致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因此,他的小说具有特定的焦点,聚焦于其家乡晋东南地区,表现那里的新生活、新思想、新旧矛盾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他早年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后自觉调整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创作格局,重建了一种新颖的写作范式,如同毛泽东期望的那样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写农民”是指赵树理立足于乡土民间和农民立场,农民真正成为小说里的主人公,以崭新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出现。“为农民而写”是赵树理的情怀,其创作的标准和目的是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从两个视角设计和规范“农村变革中的农民”:一是从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描写农民,树立典型形象;二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揭露农村落后、愚昧的现象,批评农民错误的思想意识,规范农民的言谈举止,提升农民的阶级觉悟。在双重视角规制的作用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独具特色。
赵树理将农民预设为读者对象,近乎固执地站在农民的一方,以通俗化的笔法教育、启蒙农民,改造他们陈旧的思想意识,帮助他们建立起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农村物质生活的穷困导致了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和单调。如何培养农民的“精气神”?如何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促进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作为一名“接地气”的作家,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发挥小说的“载道”功能。赵树理的阶级出身和成长环境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带给他一生受益不尽的三件宝:一是全身心融入农民,与农民的情感息息相通,与农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二是十分熟悉农村,对农村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三是通晓民间的艺术。[2](P12)从这些创作的“资本”中可以隐约看出赵树理的“雄心壮志”:“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3](P18-19)封建气息浓厚的“小唱本”无法让农民“精神起来”,无法使农民走向文明的境地。相反,只会将他们变得愈来愈保守、愚昧。欲改变这一现实,赵树理使出“铁笔圣手”,将自己的创作锁定农村,把新思想、新观念传播到广大的农民兄弟中间。小说鼓舞农民的斗志,增强他们的主人公意识:翻身解放后走上了政治的大舞台,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赵树理从不以“作家”自矜,只说自己是个“热心家”。可见,他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对农民即预设的读者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
赵树理视农民为“衣食父母”,在创作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其小说融合了民间的艺术,运用讲故事和评书体等形式,将说唱技巧发挥得恰到好处,形成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风格。赵树理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板话”,在表现严肃而重大的社会问题上,不板脸孔,不虚造声势,不机械呆板地说教,而是采取诙谐、幽默的笔法,寓庄于谐,令人忍俊不禁,又觉意味深长。小说的语言干净利落,把复杂的农村故事叙述得一清二白,乡村的烟火味弥散其中,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清草的芳香沁人心脾。他不是故意用方言来炫耀地方特色,也不是卖弄自己的“铁笔”“圣手”,而是将晋东南地区原汁原味的口语提炼成韵味十足的“白话”作为小说的“书面语”。在五四时期,胡适主张向传统的白话小说学习,改良拗口僵死的文言文;傅斯年则倡导向西方学习,欧化白话文。二人语言革新的主张在特定时代具有合理性且起到较大的作用,但产生的弊端在后来也愈加明显。赵树理审时度势另辟蹊径,从民间口语上找突破口。他深刻认识到,写作用的语言,自然的应多一些,加工的要少一点。加工的语言更适合“说”的特点。小说呈现口语化的特点,不仅表现在人物的对话上,也表现在故事的叙述中。因此,小说非常适合农村群众的“胃口”,他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借此“解个闷”,既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又得以娱乐和放松。赵树理淡泊名利,不求在文艺界“立案”,只要预设的读者对象有所收获,也就心满意足了。
二、“别有用心”预设读者对象
典型的农民形象是赵树理小说的一大亮色。“他的农民形象显著地区别于‘五四’代表者。他强调的不是苦难,而是乡村人们的活力。”[4](P199)“乡村人们的活力”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促使他建立写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显然,他预设的读者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向土地讨生活的底层农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大众化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把创作思想、文艺情怀、写作立场完全转移到人民群众中来。赵树理早先自觉实践通俗文艺创作,后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完成了大众化的转变。赵树理走的是文艺通俗化道路,在文化和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俗化拆除了文化殿堂和大众之间的障碍,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文艺走向大众化的重要途径。赵树理为什么走这条路呢?他想把新知识、新思想输送到农民中去,却发现周围的群众对他推崇的五四新小说一点也不感兴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就要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西北农民的“两极”状况明显,文化素质极低,文盲率极高。“西北地区除几个地主、官僚、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读书写字;文盲大概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5](P189)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没有能力去欣赏那些“阳春白雪”,自然也就无兴趣可谈了。为了让他们感兴趣,赵树理自觉承担时代的使命,主动调整自己的创作立场和创作方向,义无反顾走文艺通俗化道路,降低文本阅读的难度,改变小说传播单一的方式,引入说书人的中介,向不识字的农民讲述故事,甚至还考虑将小说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总之,小说对农民而言,能看懂则看,看不懂则听。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我是写小说的,过去我注意让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因此在语言结构、文字组织上只求农村一般识字的人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人一听就懂,这就行了。”[6](P313)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赵树理小说通过视听媒介的转化,将无声的阅读变成有声的讲述,增强了故事对听众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别有用心”地预设了读者对象,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将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写/读”模式转换成“说/听”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赵树理的这一创作策略很好地解决了文学与广大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五四新文学悬而未决的问题。[7]
赵树理秉笔锁定农村,倾情挚爱农民,对农民的赤诚和热心呵护,至今仍动人心弦。小说《套不住的手》虽离现在已久远,但读后仍感到文中流淌着的脉脉温情。斯人已逝,其文永续;文如其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该小说创作于1960年,反映了人民公社成立期间发生的事情,主人公陈秉正是一个质朴勤劳的农民,在获得“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后却有着不居功自傲的高风亮节。赵树理高度赞扬像陈秉正这样的正面人物,但对那些像“哈哈哈”郝合和有缺点的小人物也给予温情的描写和善意的批评,不在政治上“上纲上线”给人“套帽子”,不对有缺陷的人格过分挖苦、嘲笑、贬损。赵树理与同时代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作家不同,他来自底层农民的家庭,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对农民的悲惨命运和苦难人生感同身受。这种个体成长的经历化为作家的生命记忆,成为作家创作财富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他对农民遭遇的书写,对农民心理的揣测和把握,对农民形象的塑造,都远远超出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乡土作家。赵树理坚持初心,只为做好一件事,自始至终围绕农民展开创作,不遗余力讲农民的故事,为农民讲故事,希望借此改变农村,让农民过上幸福的日子。作家创作的动机是高尚的,忠于农村生活,忠于自己的良知,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担当意识,不歌功颂德,不粉饰现实,不虚与委蛇,创作态度端正、真诚,令人感动,在今天对当下的作家仍有借鉴意义。
毫无疑问,农民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对象和预设的读者。但是,他预设的读者和实际读者一致吗?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值得我们深思。傅雷在通读了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后发表了一篇评论,其中写道:“赵树理同志深切地体会到,农民是喜欢有头有尾的故事的,其实不但农民,我国大多数读者都是如此。”[8]傅雷深中肯綮,论述得极有道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习惯的确如此。根据傅雷的判断,实际的读者会远远超过预设的读者。赵树理对读者满怀信心,依他的观点,他的小说是写给识字较少的农村人看的,还期待识字的人阅读后讲给不认字的人听。小说的阅读难度较低,理解是不成问题的,作品与预设读者的交流应该畅通无阻。再者,语言的乡土味十足,句式较短,简练,大段描写环境的句子较少,农民易读懂。照此说篇章内容不需要解释,或者说解释会显得画蛇添足。但令人费解的是,小说《邪不压正》里出现使用方言后加上括号解释的现象,似乎给文本提供了自相矛盾的反例。如这篇小说第一章中“顾住顾不住”后面加上了一个括号来特意标明“就是说能顾了家不能”。[9]从这个括号的设置可以明显看出叙述者的“别有用心”。赵树理早已表明了自己的民间立场,早已预设了读者对象,难道农民对“顾住顾不住”这种经常使用的简单的措辞看不懂吗?农民需要这样的解释吗?这样做是不是多此一举?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赵树理小说预设的读者未必都是农民,加上括号可能是为了让农民之外的读者能看得懂,这种做法无形之中扩大了读者对象。
三、预设的读者和实际读者的“间隙”与错位
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特别强调“读者意识”,预先确定读者,然后再确定写法。[10]他在小说《邪不压正》发表后随即谈了自己创作的感受,言及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是总结“土改”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想让“土改”中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读后能趋利避害,不瞎折腾,少走弯路,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受到损害。他心中装的是农民,甘心为农民代言,为百姓做实事,十分明确预设了这篇小说的读者,直截了当指向农村“土改”中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最终,赵树理的主观愿望和这篇小说带来的客观效果如何?作家本人非常清楚,农村“土改”过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不是“红头文件”能完全解决的,命令式的“压服”不如不温不火的“说服”。赵树理在认真思考后认为,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需要小说来助力,政策的解读需要小说才更形象。希望小说比“红头文件”的宣传更具体更有吸引力,更让群众清楚明了。但他可能也知道,小说终究无法代替“红头文件”,基于“土改”政策和小说之间差别悬殊的认识,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只能配合“土改”运动。“配合”的地位仍然赢得了读者信赖的目光,受到了不止是基层干部和农民读者的肯定,还得到文艺界人士的赞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土小说呈现出“一江洪峰”的局面,彼时作家的眼光不约而同投向农村,笔耕乡土,采用一种知识分子现代话语关照下的乡土写作模式,叙述视角居高临下。[7]可惜,农民读者因自身的局限对此有点“高攀不上”。何况,他们作品中的一部分农民是“想象”中的,很少有像赵树理小说塑造的农民那样可亲可爱。前者更多是作家创作意识、理想、价值观念的主观投影和镜像筹码。因此,农民成了被想象、表现和言说的客体,彼时作家没有像赵树理那样与农民打成一片形成互动的力量和亲密的关系。而赵树理弥补这一创作的缺憾,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采用平视的叙述视角,笔下的一系列农民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对应,显得格外生动、活泼。赵树理深入农村,时常会在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目的是通过调查研究寻找写作素材。由于农民自身积极参与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实践活动,如经常和作家接触、话家常,对作家的创作情况及时反馈,二者互通有无。某种程度上讲,农民也成为了创作的主体、言说的主体。由此可见,二者是一个相互学习、交流、启发的创作共同体。后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民的思想觉悟、认识水平、文化素养不断提高,许多人加入了革命队伍,有的成为文化的骨干力量和领导者。他们的身份改变之后,一如既往喜欢赵树理的小说,依然对他的小说爱不释手。读者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也产生预设的读者和实际的读者不一致的现象。
赵树理的小说发表后,解放区乃至全国不少行业和阶层掀起了阅读的热潮,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作家本人的预料,实际读者远远大于预设的读者。弄清这一点,对理解当时赵树理小说“走红”的现象是有所助益的。真正喜欢赵树理小说的读者,不仅仅有他预设的初通文墨的读者和不通文墨的听者,还有其他不同阶层的群体。而给予赵树理小说高度评价的,恰恰是那些文化素质较好、文学鉴赏水平较高、审美经验较丰富的读者。直到今天,仍然有一部分人在阅读赵树理的小说,这些对赵树理小说热情不减的人,大多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因为这类人,不追求故事的离奇曲折,不赶“文坛”的时髦,能对小说“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这样写”等方面作出较为客观的考察、分析。[10]数十年后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连作家也没有预料到,其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这类读者恐怕也没有预设过。概言之,赵树理小说创作不得不面临实际读者和预设读者的“间隙”与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