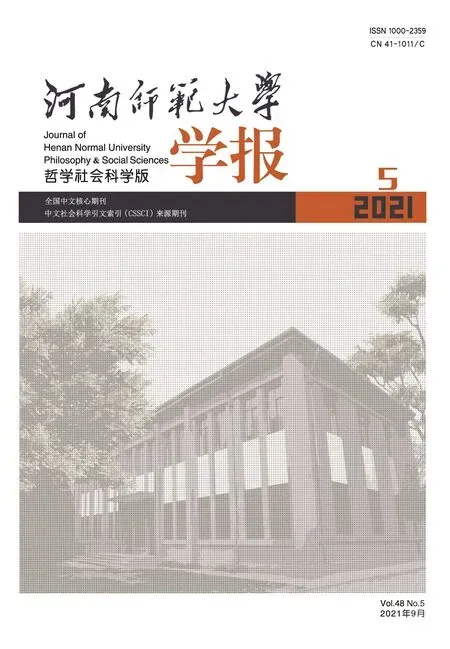“有益”与“有味”:论吴趼人新小说叙事的双重意旨
晋 海 学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1905年,陈景韩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新小说应具备“有益”和“有味”两种“原质”,所谓“有益”,即是“开通风气之心”,所谓“有味”,则是“小说本义”,并最终认为只有同时兼有两种“原质”的新小说,才能称得上是“开通风气之小说”(1)冷:《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上)》,《时报》,1905年6月29日。。藉此考察吴趼人的小说,无论是历史小说《痛史》《两晋演义》,还是写情小说《恨海》,无论是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石头记》,还是滑稽小说《立宪万岁》,皆能体现新小说“开吾民之智慧”(2)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页。的主旨,也是小说家“开通风气之心”的文学表达,是为“有益”。由于吴趼人强调小说要有“足以动吾之感情”的感染力,并一直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追求,所以,他的小说读起来并不枯燥,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云:吴趼人“所著《吴研人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能令人泣,能令人怒,能令人笑,无不风行于时”(3)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页。。这些小说正体现了“小说本义”的精神,是为“有味”。如果说陈景韩的反思意在为新小说在“有益”与“有味”之间寻求一种力学平衡的话,那么,在新小说普遍忽视了趣味性的创作语境中,如此受到民众喜欢,“无不风行于时”的吴趼人小说岂不正是达此“平衡”的典型代表?由此重返近代,借助“有益”与“有味”这两个文学视角,我们或能看到小说家为寻得这一“力学平衡”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
一
吴趼人最初以短文成名,但最终给他带来声誉的则是《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新小说。鲁迅先生明确地将其小说成就与清末小说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光绪二十八年新会梁启超印行《新小说》于日本之横滨,月一册,次年,沃尧乃始学为长篇,即以寄之,先后凡数种,曰《电术奇谈》,曰《九命奇冤》,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名于是日盛,而末一种尤为世间所称”(4)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页。。“次年,沃尧乃始学为长篇”与“而末一种尤为世间所称”句,即说明吴趼人始于小说界革命之后的长篇创作,不仅是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之作,而且是小说界革命的实绩之一。吴趼人赞同新小说的启蒙功能,但对于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那就是“恢复我固有之道德”。吴趼人的小说或者寄寓历史,或者批判现实,或者想象未来,但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所展开的“有益”叙事。
第一,寓于历史之中的现实关怀。《痛史》是小说家“别有所感”的历史之作,它的最终旨趣不在于历史的讲述本身,而在于籍此而抒发的现实之“痛”。元朝的兵力虽然强大,但南宋军队的抵抗也异常顽强,以致形成势均力敌之势。可恨的是,贾似道、吕师夔等人的倒戈投降打破了这一难得的对峙局面,南宋也正是因此迅速走向了灭亡。小说家在这里表现出了他的价值取向。张国威、张贵、张顺、李才等守城将领,力拒伯颜大军,战败后或“死于乱兵之下”,或被“乱刀砍死”,或“投江而死”,或“自刎而亡”,却没有一人投降敌军,小说家赞之曰:“念了大义,灭了亲情。”(5)吴趼人:《吴趼人全集:历史小说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68页。张弘范、吕文焕、吕师夔等人投降元军,受人驱使却不自知,真可谓“忘根背本的禽兽”,小说家骂之为“一班龌龊无耻全没心肝的小人”(6)吴趼人:《吴趼人全集:历史小说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66页。。如此,张国威、张贵等人不惜为国捐躯的爱国品质,便与张弘范、吕文焕等人背主求荣的禽兽之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考虑到西方列强在1900年对北京的入侵,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痛史》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让读者在体验了那些“忘根背本的禽兽”给予南宋种种灾难性惨痛的同时,借由对与之相对应的张世杰、文天祥等人爱国品质的礼赞,唤起了民众在国家危亡之际充当起民族脊梁的爱国热情。在这层意义上,《痛史》既是写南宋灭亡之痛,更是写清末国家危亡之痛,它没有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在一个精心挑选的历史框架里,述说或倡导具有启发民智效用的某种动议和设想。
第二,直面“怪现状”社会的现实批判。作为先进的知识者,吴趼人基于现代视野看到了清末社会中“反常的世界”,这是一个由种种“怪现状”组成的社会,透过它们,小说家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互信的丧失,《近十年之怪现状》中伊紫旒、乔子迁和李仲英盗用山东招远金矿的名义,在上海公开招纳股份。作为伊紫旒的好友,余有声不仅没有想到这本身就是一场骗局,还天真地为他们做起了“书启”的事务。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伊紫旒在盘算这件事的退路时,不仅不考虑余有声的安全,而且把这位好友玩弄于股掌之中。小说家更看到了个体道德的彻底丢失,《上海游骖录》中屠牖民、屠莘高、王及源和谭味辛都是清末新型的知识者,他们追求新学并非为了报国,而是为了图利。前二人还在去日本留学的路上,便已商量如何用钱购买文凭,以及如何用“新名词”赚取家人信任的计策了;后二人逢人便谈革命话语,可是一见有利可图便露出本来面目。很明显,清末社会的种种“怪现状”是不会自己现身的,它只有在“固有之道德”的视域下才可呈现,所以,无论是对社会“怪现状”的揭露还是批判,都并非叙事的关键所在,唯有藉此而来的道德之“恢复”才是小说家最终的思考目标。
第三,乌托邦想象中的“文明境界”。乌托邦书写是一种关于理想的书写,它当然包含了小说家对于现实的不满,但更多却是对于其思想的展示。吴趼人强调“恢复我固有之道德”,其要义有二:一是“我”的问题,即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扮演的是主体角色;二是“固”的问题,即“我”作为主体,自有“我”的传统习惯和伦理标准,所有外来的思想观念只有在经过“我”的“固有”的过滤之后,才能成为“我”的传统。《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就是小说家理想政治的绝佳呈现。其一,坚守儒家文化的核心地位,这里所说的儒家不是宋明理学,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思想。小说的后半部分几乎都是老少年关于儒家伦理的叙事,从牌坊阴面所刻的“孔道”两字,以及分别用“仁、义、礼、智”“刚、强、勇、毅”“友、慈、恭、信”“忠、孝、廉、节”“礼、乐、文、章”来命名“东、西、南、北、中”(7)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社会小说集(上)》,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48页。五地区的做法,就能看出这里所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程度。其二,坚持以我为主的策略。老少年认为在“道德普及”的前提下,国家可以实行专政体制,其原理在于“已经饱受了德育”的百姓,在成为官员之后应是懂得道德伦理的官员,他们很难再成为“暴官污吏”(8)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社会小说集(上)》,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73页。。其三,坚信传统文化的超越价值。作为最具现代性的事件之一,战争以其非人道的残酷性受到了人们的谴责,但《新石头记》却以蒙汗药水来行“仁术”,在不伤害人员的前提下,实现对敌人全数的生擒活捉。在两军阵前所实施“仁术”,完全是儒家“仁”学在现实中化用的结果,相比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这难道不是对西方文明的超越?总之,小说家寻求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主体性,这是一种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建构方式,但恰恰是基于对儒家传统的重新观照,让这一文化主体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现代价值。
二
吴趼人的小说很“有味”,也很耐读。这里所说的“有味”是前文陈景韩语境中的“有味”,它并非一个严谨的文学概念,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一个代表了民众对某一篇小说的喜爱程度,却又无法说得清楚的模糊称谓。它的外延虽然广泛,但并非是大而无当,只不过因文而异罢了。在吴趼人的语境中,“有味”就是指小说的“趣味性”,而在具体的文本中,“有味”则既可能是历史小说中的引人入胜,也可能是社会小说中的戏谑之词,更可能是乌托邦小说中的大胆想象。
第一,引人入胜的情节叙事。《两晋演义》据《通鉴》《晋书》《十六国春秋》而成,却较它们有意味,其中的关键就是情节的建构。小说家在这段并不太长的历史中,抽取贾后擅权与藩王兵变作为核心情节,首先便给人以豁然清晰之感,然后再紧紧围绕它们铺陈文献、“点染其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譬如,小说第二回“正中宫贾妃要册立”,其中一个“要”字便可吊起读者的胃口,是惠帝不同意册封贾氏,还是其他人有不同意见,为何说“要册立”呢?小说家认为贾后擅权标志着晋朝衰落的开始,而她上位的不正当更是起始中的始点。晋武帝驾崩之后,廷臣们根据“尚在苫次,不宜册后”的传统,取消了将贾妃晋为贾后的动议,但是贾妃非但不认同,而且异常跋扈地命令中书监和内侍“当面草诏”“当面钤印”,并“逼着惠帝,次日吉服祭告太庙,册立贾氏为皇后”(9)吴趼人:《吴趼人全集:历史小说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4页。。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渲染之言,尤其是在“自贾妃册立为宫之后,而宫廷之祸愈亟”(10)吴趼人:《吴趼人全集:历史小说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4页。的历史判断下,这样的“渲染之言”不仅起到了呼应主题的功能,更起到了吸引读者的作用。
第二,戏谑滑稽的复调叙事。吴趼人是一个有趣的人,曾云:“余向以滑稽自喜。”(11)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友人亦云:“予友南海吴君趼人,性好滑稽……往往以片辞只义,令人忍俊不禁,盖今之东方曼倩也。”(12)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吴趼人将他的滑稽才能融进了小说创作之中,尤其是他的社会小说最能让人体会到这一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苟才在做观察时受藩台的压制,以至于“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使,穷的吃尽当光了”(13)吴趼人:《吴趼人全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7页。,但为了在客人面前保持体面,他便去租了一套袍褂,却没想到在送客时被孩子给弄脏了,“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他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14)吴趼人:《吴趼人全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55页。,由于担心店家看出痕迹,他就让家人把这“两块油迹”尽快处理一下,不成想却弄巧成拙,不仅没有洗去“油迹”,反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当店家看出来以后上门要求赔偿时,他就让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15)吴趼人:《吴趼人全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55页。,而店家则在他的公馆门前破口大骂。苟才的租衣行为在逻辑上类似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他一味要撑起自己的面子,却不顾“穷的吃尽当光”的现实处境,谁料这种虚伪被尚且稚嫩的孩子无意戳破,真是滑稽至极。
第三,大胆想象的乌托邦叙事。《新石头记》是吴趼人所写的一篇乌托邦小说,其“有味”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穿越时空的人物交流。《新石头记》是对《红楼梦》的续写,它沿用了《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如贾宝玉、薛蟠和焙茗。他们穿越历史时空,不仅相逢于清末,而且共同参与当时的义和团运动,如此新旧人物的相互交织,怎会不给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的感受。其二,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展示。《新石头记》中的现代科学不仅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且被普及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文明境界”对每家每户实行统一供食、统一供水,人们吃的是食物精液,喝的是经过蒸汽处理之后的无色之水。这里的人在家可以用助聪筒进行远程联系,出门可以乘坐随时出发、随时停靠的飞车。至于其他如司时器、地火灯、电梯等现代科技,更是令人目不暇给。其三,奇异的情景设计。贾宝玉驾飞车猎获大鹏与坐猎艇大战海鳅是小说最具魅力的两个情节,小说家不仅插入了多种功能强大的战具,而且为贾宝玉等人设定了可以与这些战具相匹配的对手:大鹏与海鳅。大鹏的体积很大,海鳅的个头也不小,贾宝玉和老少年虽然手持现代战具,但是在它们面前并未占有绝对上风,单看大鹏抓住飞车的上架,弄得飞车“荡漾不定”(16)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社会小说集(上)》,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79页。,海鳅缠住猎艇,“撼的全船震动”,就能知道当时场面的激烈程度。如此集人类智慧与动物勇敢、现代科技与自然力量之间较量的奇幻叙事,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不会过时吧。
三
吴趼人小说中的“有益”与“有味”并非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叙事,恰恰相反,它们既相互交融,又彼此关心。譬如,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苟才租借衣服的行为被自家的小孩无意间戳破时,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苟才的滑稽瞬间,还有像苟才那样虚伪做人的虚假,更有小说家希望人们做一个诚实的人的道德期冀。如此既“有益”又“有味”的叙事,失去其中的任何一项,恐怕都很难达到上述的效果。然而,如果进一步考察吴趼人的小说,我们还会发现小说家无论是对“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倡导,还是对“趣味性”的执着,乃至对“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17)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的说辞,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可贵的是,小说家并不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论述这些问题的,而是将其弥散于各类叙事的张力之中。
前文曾述吴趼人小说中“有益”叙事的核心思想是“恢复我固有之道德”。这一思想的张力主要体现在小说家对中西文化既赞同又批判的双重态度上。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他或者以批判的方式,从反面说明了儒家伦理的先在性,或者以赞美的方式,从正面阐述儒家文化的完美性。但与此同时,他又激烈地批判宋代儒学,或者说它是束缚人们精神的罪魁祸首,或者说它空乏无用。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认同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也认同西方的民权思想,更强烈批评时人对西方文化的拒绝态度,但与此同时,他也洞见了西方文化中的野蛮性质。这或许是吴趼人在面临西方文化入侵时建构文化主体的一种策略,但如此既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却“并不是死守旧学”(18)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社会小说集(上)》,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547页。,既承认西学的昌达,却又拒绝“崇拜外人”的张力思维,怎能不给他的叙述带来困难?为了清楚表达这一内蕴丰富的思想观念,吴趼人不得不多面出击,应战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和质疑,他的小说因此而受益,并呈现出了复杂的思想样态。
吴趼人对于小说趣味的理解也表现出了复杂的一面。趣味性本就是小说的原质之一,这也让小说成为人们最喜欢的文体之一。然而到了清末,人们对于小说的看法趋于复杂,他们要求小说在思想和趣味之间取得平衡。以吴趼人的历史小说而论,《痛史》重视虚构,它常常为了增加情节的感染力而“蹈虚附会”,但《两晋演义》则依据史实而鲜有虚构。由此来看,吴趼人的趣味观并不狭隘,更不拘泥于对趣味的某一点理解,有时多一分虚构就能引起读者的情绪,有时多一分史实则会给读者带来新的知识,但其中有一个分寸感的存在,那就是重视虚构,却不能像《万花楼》《封神榜》那样极端附会,看重史实,则又不能像《东西汉》《东西晋》那样简略叙事,而是要始终在虚构与史实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点,才不致偏颇。
然而,对于吴趼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最大的困难需要面对,那就是如何在小说中寻找到“有益”和“有味”之间的平衡点,这其实意味着,他的小说既要符合改良社会的需要,又要让民众读起来觉得有趣。考虑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在当时的影响,人们其实已经在小说的功利与消闲之间作出了取舍,但吴趼人却始终坚持“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的观念,比较好地把握住了“有益”和“有味”的平衡点。首先,当“有益”的思想获得正面展示的机会时,吴趼人不放过任何“有趣”的细节。《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游历“文明境界”,每去一处都有老少年的详细讲解,这既是吴趼人“恢复固有之道德”思想的展示,同时也是融新奇和趣味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的展览。尤其是贾宝玉驾飞车猎获大鹏与坐猎艇大战海鳅两个情节,吴趼人更是给予身临其境般的叙述,而其中所包含的种种惊险与刺激,恐怕早已超越了趣味性的体验。其次,当反向表达“有益”的思想时,吴趼人则经常使用他人转述的方式来叙述“有味”的细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味”的细节几乎到处都是,但这些细节却都经过了小说家精心的处理,尤其是那些可能会涉及“轻薄无行,沉溺声色”(19)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6页。的情节,基本上都是叙述者在转述,而不是他的亲眼所见,如“怨女痴男鸳鸯并命”由文述农讲起,“施奇计奸夫变凶手”则为何理之所说。吴趼人可能正是为了避免读者专注于这些容易引起负面影响的细节,而代之以人物的转述,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失一些“趣味”性的东西,但由此却为小说赢得了“有益”的叙事,其间的取舍还是值得的。再次,杂糅传统与现代的叙述模式,在尊重读者传统阅读习惯的同时,给予他们新的阅读体验。中国的小说读者本有其熟悉的接受模式,且不说章回体的结构形式与骈文体的目录排列,单是看到那些说书人的套话如“话说”“却说”“且说”“看官”“正是”,以及“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读者就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吴趼人的小说在这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叙述模式,但是也进行了现代叙述的探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份的出现,可能更会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而叙述分层所带来的叙述者身份的变化,则可能因新叙述者身上所携带的情感因素,而起到影响或启发读者的效果。
总之,自清末小说界革命之后,新小说的创作并不尽如人意,“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20)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吴趼人以为这些小说太过重于改良社会的责任担当,它们因为疏于对“趣味”的关注,而失去了可读性。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无法触动民众感情的小说,怎么会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其实,小说中“有益”和“有味”的问题并非清末所独有。明代胡应麟就已经注意到了二者的兼容问题,所以,他在重视小说“风刺箴规”(21)孙逊,孙菊园:《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页。功能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它们的“文采、文辞、阅读趣味性等内容”(22)温庆新:《目录学视域下胡应麟的“小说”认知与分类思想》,《齐鲁学刊》,2020年第5期。。近代以后,这一问题更是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当中,不同时期的小说家们往往会基于时势而偏重于其中的一极,或重于“有益”的书写,或强调“有味”的叙述,却很难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兼顾的平衡。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吴趼人的小说,这样的叙述可能显得陈旧,但是如果从兼顾“有益”和“有味”的视野来看待的话,那么,它们在把握这两者平衡之分寸感时所作出的努力,则又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试验。这或许正是吴趼人的小说为两种叙事的平衡所做出的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