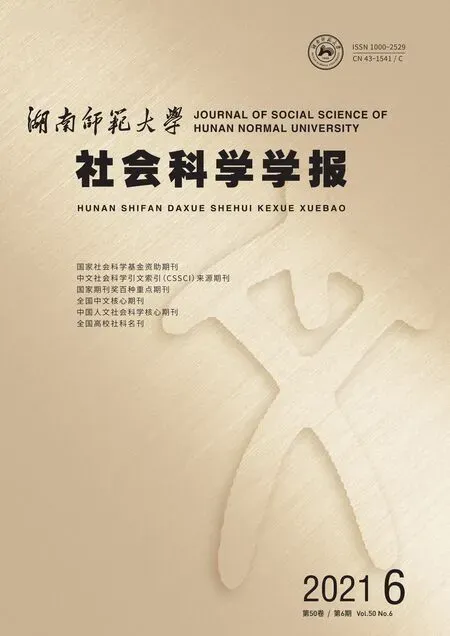巫鬼文化与中国现代启蒙作家的审美探索
易 瑛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开篇中说道:“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1]这一段话深刻地呈现了启蒙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一方面,启蒙可以使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给人带来理性、解放与自信;另一方面,启蒙想“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神话的瓦解和想象性的压抑,对文学创作来说,确实体现了“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的事实。启蒙的积极作用和启蒙对于文学审美的压抑的矛盾也表现在中国现代启蒙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启蒙,输入了西方科学、民主的现代思想,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得以解体。正如胡适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2]但是,“五四”知识界对科学的过分赞赏,对启蒙内涵理解的偏激,带来了“唯科学主义”和理性至上主义。“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3]在“唯科学主义”观影响下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张扬科学理性的文学启蒙运动,他们力图用科学理性在中国重建一种包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在内的新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在这一推崇科学理性的时代里,古老原始的巫鬼文化被视为愚昧、迷信、反现代性的文化,遭到否定性的批判,作家要“让理性之光驱散民众思想上的蒙昧、昏暗,让理性之光照亮民众的头脑和心灵”[4]。
在文学的启蒙精神被大力倡导的时代,作家的创作突出的是启蒙的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的现代性。“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唯科学主义影响下,出现了茅盾所说的“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5]的偏激。科学与理性分析的倾向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强化,已经到了周作人所说的“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6]的程度。启蒙文学自觉接受了科学理性的统驭,崇尚写真写实的写实主义,而相对忽略了以宗教的、艺术的、想象的方式去把握世界。
如何在启蒙与审美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如何在倡导科学进步的同时,挣脱“审美的贫困”,保留文学的情感,肯定人性中的非理性?早在“五四”以前,梁启超的“新民说”和王国维的“纯文学”观之间内隐的冲突已经表现了“启蒙”与“审美”之间的矛盾。“五四”时期“理性启蒙”至上的偏激,使文学的审美被压抑。而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启蒙运动中“唯科学主义”观念初步反思,科学和宗教、科学和文学的区别得到了“五四”作家的关注。周作人谈到文艺上的异物——“僵尸”时说:“唯物的论断不能为文艺批评的标准,而且赏识文艺不用心神体会,却‘胶柱鼓瑟’的把一切叙说的都认作真理与事实,当作历史与科学去研究他,原是自己走错了路,无怪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7]在《文艺批评杂话》中,周作人再一次强调:“拿了科学常识来反驳文艺上的鬼神等字样,或者用数学方程来表示文章的结构:这些办法或者都是不错的,但用在文艺批评上总是太科学的了。”[8]茅盾也指出:“大凡一个人种,总有他的特质,东方民族多含神秘性,因此,他们的文学也是超现实的。民族的性质,和文学也有关系。”[9]对文学不同于科学的“奇异”的肯定和对“东方民族多含神秘性”的认识,使一些现代启蒙作家对一往无前、狂飙突进的理性思维保持了警惕,通过对文学的情感、想象、梦幻、敬畏、神秘等非理性的审美探索,表达了对科学唯理主义的纠偏。
一、隐喻式的审美思维
人类学家格尔兹曾说过:“在仪式里面,世界是活生生的,同时世界又是想象的……然而,它展演的却是同一个世界。”[10]在巫师的眼里,现实的世界之外,存在一个超现实的神鬼世界。巫师要运用物体、图像、灵符、咒语等特殊符号系统来进行巫术实践,与超现实的、想象的世界进行沟通。在民间巫鬼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中国现代启蒙作家,在剖析民族灵魂,表达个人心曲,突破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时,运用携带远古文化密码的象征符号与仪式程式,与先人的智慧相连接,并寻找现代自我的身份认同和表达方式,实现了现代小说从叙事的写实到隐喻式象征的转变。
在鲁迅小说中,长明灯、社戏、祝福、无常、女吊、人血馒头等已经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世界,无常、城隍、五猖、社戏、目连戏等组成的是一个想象的、人鬼相通的奇幻世界。种种巫鬼意象与民间信仰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物象和普通的民俗写实层面,具有浓郁的象征色彩和鲜活的生命力,使鲁迅创作的启蒙小说具备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厚重感和蕴藉感,达到了超越具体历史环境,指向未来的美学高度。
“巫术思维是一种意象性活动,限于具体事物与事件,对意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归类,在叙事过程中更接近原始的意象、远古意象。”[11]在鲁迅的小说和散文中,与“死亡”相关的意象有很多,如“血”“鬼魂”“尸体”“棺材”“坟”“墓地”“墓碑”“地狱”“乌鸦”等,使作品充满了沉重、冷峻、压抑的色彩。这些死亡意象,与“上坟祭奠”、吃“人血馒头”治病、“吃人肉”“入棺”“迁葬”“祭祖”“祝福”“出殡”“迎神赛会”等相信“死后有魂”“重死轻生”的中国民间信仰观念和仪式等相联系,形成了较为密集的意象群。
首先,鲁迅通过“吃人”——“被吃”的巫术行为形成的象征意义,既对封建礼教“吃人”的“蛮性的遗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也揭示了“‘觉醒的人’与‘吃人’的世界(现实世界)之间的对抗与统一关系”[12]。《狂人日记》中“我”的大哥、赵太爷等是要“吃人”的人,他们要吃“我”的肉。活人的肉体和鲜血被吃,按照弗雷泽所说的“接触律”巫术,是人们“相信自然具有一种特性,能将人和动物所吃的东西或他们感官所接触的物体的素质转移给人和动物”[13],“通常还吃死人的血肉,以吸取那些死人特有的勇敢、聪明或其他素质,或是认为勇敢聪明等素质是在某个被吃的特定部落。”[13]面对“吃人”这一巫术行为形成的文化事件,作为反抗旧礼教、旧传统的“狂人”,“我诅咒吃人的人”“要劝转吃人的人”,然而“我”也发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也“难见真的人”。与“死亡”相纠缠的“吃人——被吃”,将狂人启蒙的呐喊——“救救孩子”、对残忍的吃人世界的彻底否定,与对启蒙者自我的理性反思与“原罪”审判相结合,既表达了对“礼教吃人”的批判,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启蒙者觉醒后无法逃脱的“绝望的反抗”的悲剧宿命。
《药》则更加深了鲁迅作为启蒙者的寂寞。“药”既是治疗痨病、“救救孩子”的一味药;又是革命启蒙者夏瑜被杀的鲜血。民间巫术与医术的密切联系,使《药》中出现的“血祭”是“一次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医疗—祭祀’活动”[14]。革命者夏瑜为了推翻封建统治,拯救民众,投身于社会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鲜血,却成了民众治病的药——“人血馒头”。在民众眼里,如同吃了大恶人的心脏可以壮胆的巫术仪式,吃了人血馒头可以“什么痨病都包好”。最终,夏瑜和华小栓都走向了“坟”的终点,留下了两位可怜的母亲清明来给儿子上坟。
从启蒙者的立场出发,鲁迅对权力阶层通过民间信仰来宣传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等级观念,利用鬼神信仰仪式的社会化控制功能来实现其专制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对于人们在愚昧、麻木之中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祭献国家权力的祭品,他感到深深的悲哀。就像《长命灯》里的那个清醒的“疯子”,他要以启蒙战士的姿态,坚决吹熄土地庙神殿里的那盏灯,同时对启蒙者“反抗绝望”的生存处境又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
其次,死亡意象也给予了启蒙者“向死而生”的力量。鲁迅将文本中的“幽魂”“女鬼”“墓碣文”等死亡意象,赋予了对黑暗、丑恶、和过去的“自我”进行反戈一击的力量。《野草》中的《墓碣文》一文,“我”的梦中出现了墓碑、孤坟、死尸等与死亡相关的意象。墓碣阴面和阳面的文字,显示了鲁迅对自我的解剖。他冷峻而清醒,无奈而又痛苦,在热与寒、有与无、绝望与希望、光明与黑暗之间呐喊、彷徨、挣扎。“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殉颠”,化为长蛇的游魂,自啮其身,即是对自我的解剖,暴露了“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15];也是“极憎恶他,想除去他”[15],要与“毒气”“鬼气”同归于尽的象征。墓碣阴面的文字“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反映了对自我进行解剖的悖论。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抉心自食”,欲“知其本味”,这是何等的痛苦?然而,“本味”永远不能自知,“自我”与“本味”都是难以感受到的存在,“徐徐食之”的执着是无用的、荒诞的,“自我”将永远处在彷徨、痛苦、孤寂之中。最后,死尸从坟墓中坐起,说“待我成灰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表现了要与黑暗和虚无抗争,同时与黑暗和虚无一起毁灭,化成灰烬的欢喜。“墓碣文”本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鲁迅将自己灵魂的“毒气”“鬼气”凝聚成一具丑陋的死尸,把“自己的血肉”暴露给人们看,体现了向死而生的勇气和对自我解剖的冷静、残酷。
再次,与死亡相关的仪式行为的重复出现,在鲁迅小说中形成了仪式原型,使鲁迅对启蒙意义和启蒙者悲剧命运的思考,在连接现代与远古祭仪的文化空间中显得含蓄、凝重、深远。
在鲁迅的作品中,“牺牲——祭祀”的仪式原型经常出现。《药》由“牺牲”“献祭治病”和“上坟祭奠”几种仪式行为组合而成,它们将“牺牲者”与“祭祀者”无法沟通的悲哀深入地表达了出来。革命的先行者、启蒙者夏瑜被砍头,他的身体和鲜血成了“献祭”的祭品,以护佑作为祭祀者的民众。然而,主持砍头仪式的是凶残、粗俗、市侩的刽子手康大叔;围观血祭仪式的是众多冷漠、麻木的民众。启蒙者夏瑜的“牺牲”并未唤起民众在神圣的牺牲中疏散自己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更谈不上产生崇高和庄严的情感。这注定了是一场失败的“献祭”仪式。启蒙者为了群体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然而他的牺牲,只满足了无聊的看客们内心嗜血的欲望,成为华家茶馆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夏瑜的鲜血,变成了治疗华小栓肺病的人血馒头,启蒙者被民众送上了死亡的祭台,成为被吃的“祭品”;而吃下“祭品”的小栓并未得到康复,反而走向了死亡。鲁迅所表现的是启蒙者即使“献出自身”也不被民众理解,而祭祀者在无情、冷漠中加速走向死亡的双重悲哀。
在《野草》中,鲁迅的《复仇》(其二)描写了“神之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场伟大的“献祭”仪式。耶稣面对来自四面的人的敌意、辱骂、戏弄、讥诮,他并没有退缩,反而以大悲悯对待这些可悯之人的悲哀,以大欢喜承受钉杀的大痛楚!走上祭台拯救人类的“神之子”,却葬身于被拯救者的人之手,延续的仍然是“献祭者”巨大的悲哀!
在《野草》的另一篇《复仇》中,鲁迅让广漠的旷野中一场面对面杀戮的“献祭”仪式走向了静止。作为“祭品”的他们面对面站立,没有牺牲的鲜血和暴力可以被欣赏,甚至没有“献祭”仪式的任何动作,就这样静止地面对面站立着,既不拥抱,也不杀戮,让那些围观的看客们无聊到觉得“干枯”,而献祭者则“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鲁迅清醒地意识到“献祭者”和“祭祀者”之间永远无法沟通的悲哀。他在愤激之中,让他们不再将自己祭献于祭台,反而将“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的古老的“献祭”仪式,改写成了一个向“祭祀者”或“看客”进行精神复仇的事件。
隐喻“是将本来的意义隐蔽在某种标志物后面或者经过某种比喻,曲折地反映某种信义的象征。正是由于隐喻的力量,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根本性的意指功能,赋予了巫术神秘幽邃及顽强的生命力”[16]。隐喻式的审美思维,究其源头,要追溯到早期人类通过具体、有形的事物和手段来与抽象、无形以及神秘的力量进行沟通、交流形成的巫术思维。运用巫鬼意象符号,内隐巫术仪式原型等呈现出的隐喻式的审美,使中国现代启蒙作家能够突破启蒙功利主义的目标,在创作中达到理性与感性、有形与无形、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使小说兼具写实与象征的双重品格,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和文化蕴涵。
二、重视情感性的审美
巫术思维是一种情感性思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以情感为内驱力的思维。弗雷泽在《金枝》中分析了巫术赖以建立的“相似律”和“接触律”这两种思想原则,建立了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超自然的力量之间隐秘的联系或感应,“这种关于人或物之间存在着超距离的交感作用的信念就是巫术的本质……巫术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相信心灵感应。”[17]情感性是“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的核心。“在这种巫术性的思维投射中,人与外物处于一种互惠、互感和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中,他们构成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编织这个关系网的‘材料’是人的情感:人并非被动地安处在这个‘关系网’中,而是积极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并用巫术行为促进或改换这种‘关系网’的结构,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的主观愿望。”[18]人的情感倾向,成了巫术行为的动力。在巫鬼文化中保存的这种“永恒潜藏的感性文化氛围”,启示了现代启蒙作家关注到理性之外的感性,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去寻找相互的情感联系。
鲁迅早在1907年留日期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就肯定了“普崇万物”的中国民间信仰,提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一观点,表达了他对“唯科学主义”的怀疑。鲁迅认识到了民间信仰带给民众的情感慰藉和主体自信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人们对死亡心存恐惧,通过举行一整套程式化的仪式,可以修复死亡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紊乱,安抚生者的情绪,强化人伦亲属关系等。《明天》中单四嫂子在街坊邻里的帮助下,完成了宝儿的丧事。宝儿入殓时,她给他穿上顶新的衣裳,在他的小棺材里,放入他平时最喜欢的玩具。《祝福》里,祥林嫂在土地庙捐了门槛后,减轻了内心沉重的罪孽感,变得“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伤逝》中,子君的葬礼上,“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愤恨于“他们的聪明”,但“我愿意真有所谓灵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用“遗忘”和“说谎”来寻求新的生路。集体参与的丧葬仪式,使死亡带来的痛苦、恐惧、被抛弃的负面情感被稀释、被释放、被转移直至忘记,能让人们在绝望无路之中继续前行。
1936年9月,鲁迅在大病之中完成了《女吊》。目连戏里出现的“女吊”即女性的吊死鬼,她是“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与演大戏不同,“目连戏”是演给神、鬼、人看的仪式剧,观众可以参与到仪式中去。鲁迅不能忘怀自己当过“义勇鬼”的童年经历,还有看到的“跳男吊”“跳女吊”的表演。“跳男吊”时,气氛紧张,镇山门之神的“王灵官”必须在场,以防招来真的“男吊”;而“女吊”出场,粉面朱唇,身着红衣,“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有时,她忘记了复仇,而只是“讨替代”。鲁迅在预感到自己已经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相继完成了《死》《女吊》等篇章。童年扮演鬼卒的酣畅淋漓,“女吊”具有的强烈的反抗、复仇的精神,给大病之中的鲁迅以情感的亲近、抚慰和抗争现实的力量。
周作人说过:“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19]在“五四”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当“五四”同仁高扬“反儒”旗帜时,周作人却敏锐地发现了:“我们可以看出野蛮思想怎样根深蒂固地隐伏在现代生活里,我们自称以儒教立国的中华实际上还是在崇拜那正流行于东北亚洲的萨满教。”[20]周作人所说的萨满教,实际上就是指古代原始宗教的巫术,在他看来,“国民的思想里法术的分子比宗教的要多得多”。萨满教的思想仍控制着国民,造成了国民的疯狂和麻木,成了“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21]。他一再强调,解决的办法就是“提倡科学,破除迷信”。
但是,充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坚决反封建、反传统的周作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又写下了《文艺上的异物》等篇章,从民俗学的角度、审美的角度来探讨民间宗教信仰与民间文学。周作人曾谈到:“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19],“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也自有其美与善的分子存在”[22],“我是不了解什么教的,但对于原始宗教却曾经很有兴趣,对于巫师的法术觉得稍能有所领会”[23],等。他的《药味集·上坟船》记载了浙东绍兴清明节上坟祭祀的仪式。《立春之前·关于送灶》对南方和北方的送灶习俗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周作人还多次谈到河水鬼、僵尸等。他说:“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24]“僵尸”在周作人看来,“这是学术上的好资料”[25],我们“能够于怪异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7]。周作人是从“情感逻辑”而不是“理性逻辑”出发,从人性人情的丰富自在去体察民间巫鬼信仰的价值,因而“对旧生活里的迷信且大有同情”[19]。
重心灵、重情感的审美思维,使现代启蒙作家返回民间,发现了民间信仰中蕴藏的民众的“本心”,体会到了“无常”的勾魂而有情,可怖又可爱,“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的反抗意志,“放河灯”、祭祀、游神赛会等巫鬼信仰仪式给民众带来的狂欢和情感的抚慰等。他们以自身生命的体验和反思的深切,脱离了启蒙理性至上导致的粗暴的文化批判,表达了对民间巫鬼信仰体谅性的理解和审美心理上的认同。
三、人鬼互渗的神秘
“五四”现代启蒙者在进行激烈的文化批判的同时,感受到民间巫鬼信仰的存在对民众生存的重要性,意识到人把握世界的方式除了理性的方式之外,还有想象的方式,体验到巫鬼信仰中“互渗”的神秘思维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奇幻诡异之美。这使他们对巫鬼信仰的批判,有时竟显得有些犹疑不定,甚至表现出矛盾重重。
“五四”乡土作家王鲁彦对“冥婚”这一巫术仪式所表现出的蒙昧、迷信的色彩显然持批判态度。但基于对“出于这冷酷之中的人性之爱的伟大”的理解,作者又表现出深切的认同感。《菊英的出嫁》不单纯是对“冥婚”的批判,也不仅仅是对母爱的讴歌,而是既包含了作者对民众迷信、愚昧之举的悲哀、痛苦,又蕴藏着对民众无以言说的爱的温暖。老百姓相信“人尽管死了,但也以某种方式活着,死人和活人的生命互渗,同时又是死人群中的一员”[26]。王鲁彦在小说中不仅表现了这种“死后生存”(即死后的“鬼”能和人活着时一样生长)、人鬼互渗的原始思维,钳制了乡民的观念,造成了民众的愚昧、迷信、落后,又试图以民间的信仰思维去体会、理解底层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作家情感的矛盾也表现于艺术形式的微妙变化上。菊英的娘尽其所能为死去十年的菊英准备“冥婚”的嫁妆。“她进进出出总是看见菊英一脸的笑容。‘是的呀,喜期近了呢,我的心肝儿’她暗暗地对菊英说。菊英的两颊上突然飞出来两条红云。”“羞得抱住了头想逃走了。‘好好的服侍他,’她又庄重的训导菊英说:‘依从他,不要使他不高兴,欢欢喜喜的明年就给他生一个儿子!对于公婆要孝顺,要周到……’”。王鲁彦大胆将存留在民间巫鬼信仰中的原始思维引入小说创作中,打破了生死界限,让菊英的母亲在现实和想象时空中自由穿行,营造出人鬼同台、虚实相生、真幻结合的艺术效果。茅盾非常敏锐地发现了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审美探索,他说:“在这里,真与幻想混成了不可分的一片,我们看见母亲意念中有真实的菊英在着。我们也几乎看见真实的菊英躲躲闪闪在纸面上等候出嫁。像这样的描写真与幻的混一,不能不说是可以惊叹的作品。”[27]
与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一样,台静农《红灯》也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文化批判。小说细腻地描写了母亲的心理活动,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生存艰辛的同情,和对伟大深沉的母爱的肯定。在表现手法上,台静农《红灯》和王鲁彦《菊英的出嫁》这两篇小说都抓住了底层民众拥有的原始互渗的巫术思维,将现实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真幻合一的特点。《红灯》中,七月十五中元节(俗称“鬼节”)“放河灯”据说可以给在黑暗中的鬼魂照路,超度亡灵。得银娘在鬼节放河灯中得到了巨大的安慰,“在她昏花的眼中,看见了得银是得了超度,穿了大褂,很美丽的,被红灯引着,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人鬼相遇,真幻交织,构成了唯美、奇异的画面,悲哀中不失温暖和神秘,体现了作者对底层民众富有悲悯意识的人道主义的同情。
民众对鬼魂的信仰心理,使“实”与“灵”的界限模糊。台静农的《天二哥》写天二哥暴死后,烂腿老五等人听到了他的鬼魂发出哼哼的声音,因担心天二哥的鬼魂作祟,马上吐唾沫来驱鬼。《拜堂》写汪二和守寡不足一年的嫂嫂半夜子时成亲。两人虽然已偷偷结合,并已有身孕,但为图吉利,他们仍想按照民间习俗行拜堂之礼,只是选择在半夜偷偷进行。他们请了邻里田大娘、赵二嫂在家里主婚。“烛光映着陈旧褪色的天地牌,两人恭敬地站在席上,顿时显出庄严和寂静。”“男左女右”,烧黄表,向死去的祖宗、阴间的妈妈和哥哥磕头,一丝不苟。在他们向死去的哥哥磕头时,双烛的光辉突然黯淡了下去,他们两人脸色突变,但仍然完成了向亡者磕头的仪式。仪式,将生者和死者联系起来,生与死、人与鬼、想象界和现实界之间的界限通过仪式被跨越。在庄重、虔诚的氛围中,生者表现出对死者既敬又畏的情感。正如孔范今所说:“(《拜堂》)所表现的就未必是什么愚昧,更多的倒是民间草民对仪式的敬畏之心和对生命的认真态度。”[28]
人鬼互渗的原始思维,形成了强烈的情感经验,激发了作家丰富、奇异的想象力,使现代启蒙作家突破了只重视文学启蒙现代性的偏狭,克服了启蒙文学创作理性过强、写实意味浓,而缺乏多样化的探索的局限,进入到艺术自由的精神境界之中,表现了民众跨越生死的界限、人鬼相融的生命体验,使文学作品具有超越现实的奇异、神秘的审美色彩。
中国现代启蒙作家对文学审美的探索,与思想启蒙、文化启蒙运动同行。“五四”张扬科学理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自晚清以来应对“亡国灭种”危机的救亡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启蒙的功利价值和“实用性原则”。坚持启蒙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力张扬科学与民主,致力于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很多时候,现代启蒙者多从现代性的反面去理解现代性,作家们通过批判与现代文化特征相对立的传统文化来确立现代性。但实际上,传统仍然活在现代,它会通过种种渠道出现。传统“首先是通过思想模式的渠道出现在每个人的身上,思想模式与我们的潜意识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现代性有时还会依靠最远古的思想模式来战胜最新或较新的思想模式”[29]。启蒙者对传统的巫鬼文化的理性批判,和巫鬼信仰、巫术仪式在民间存在的事实、启蒙者对民众“本心”的关注、“巫术思维”对作家创作潜在的影响同时并存,使启蒙者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矛盾与悖论。
当中国现代作家从启蒙的激情狂热走向对启蒙本身的反思时,遭到现代意识质疑和否定的民间信仰文化开始在文学中寻找到了新的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作家们认识到巫鬼信仰对民众生存的意义及其人类学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奇幻的巫鬼意象、原始的巫鬼信仰中人神不分、生死合一的原始思维等,给作家创作带来了艺术创新的动力和资源。而作家们在文学艺术上的创新又为主体精神的建构和审美呈现寻找到了出路。在审美中形成的自由天地和重视个体自由、解除外在束缚的启蒙精神之间形成了呼应。
总之,自新文学诞生以来,中国现代启蒙文学主要依附于文化启蒙,重启蒙、轻审美,重主流文化、轻民间边缘文化成为“五四”以来很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但实际上,由于作家自觉承担了思想启蒙与美学启蒙的双重使命,并在寻找着可供现代文学借鉴的文化资源和文学资源,使得启蒙与审美的矛盾、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选择的矛盾一直贯穿在中国现当代启蒙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