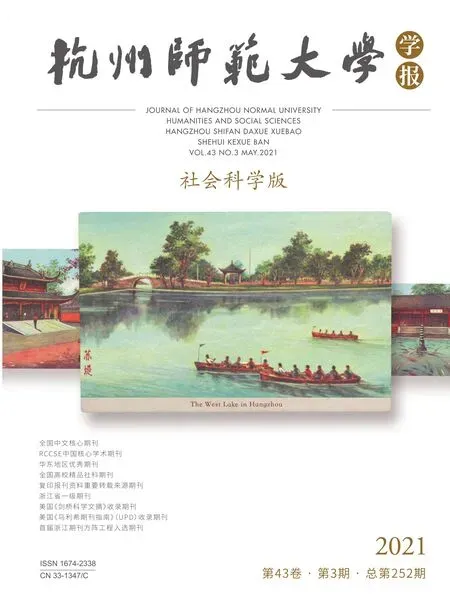“天地之妙文”
——咸同时期杭州歌谣《天籁集》
陆建德
(厦门大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白话文运动由胡适提出之后,国语、白话文学地位为之一变,而方言的意义也为新型学者所认识。(1)胡适曾言:“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见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胡适文存》(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第153页。1918年2月,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北京大学日刊》从5月20日起陆续登载刘复(即刘半农)编订的歌谣。[1](P.44)顾颉刚当时是北大学生,读了颇吃惊:“歌谣是一向为文人学士所不屑道的东西,忽然在学问界中辟出这一个新天地来,大家都有些诧异。那时我在大学读书,每天在校中《日刊》上读到一二首,颇觉耳目一新。”[2](《自序》,P.2)这年6月上旬,顾颉刚休学,回苏州后仍从天天收到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读到新鲜的歌谣。翌年2月,顾颉刚就在家中搜集苏州一带歌谣,叶圣陶、潘家洵和郭绍虞等人闻知此事,也将他们所知道的歌谣寄给他,9月回北大复学时,已积有苏州地区歌谣近200首。1920年夏顾颉刚留校,到图书馆就职。那年深秋,吴歌在北京《晨报副刊》经郭绍虞之手陆续发表52首。年底沈兼士、钱玄同和周作人发起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刘半农主其事。(2)据上海社科院狄霞晨查考,刘师培(1884-1919)在20世纪头三四年就关注歌谣,堪称现代歌谣运动先驱。详见复旦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下的刘师培文论》。刘师培病逝时北大歌谣研究会尚未成立,不然成就更大。《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为该会所出国立北京大学和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丛书”首部,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半农作序,附录五种则是顾颉刚、魏建功、沈兼士和钱玄同的研究文章以及通信讨论。刘经菴的《歌谣与妇女》也收入“民俗丛书”,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周作人为他作序(所署时间是1925年10月5日,初刊于当年11月《燕大周刊》)。书中引证的歌谣多取材于《歌谣》周刊,其余则由编撰者自己在河北卫辉搜集。刘经菴批判性地从十个方面观察女性的家庭社会关系,并在自序中指出:“民众的文艺,尤其是歌谣一部分,妇女的贡献要占一半,且其中又多是讨论她们本身的问题的——妇女的文学与妇女的问题。”(3)笔者使用的是台湾地区1971年影印本。当今倡言传统文化者避而不谈旧礼教压迫下的女性,还不仅仅是出于选择性的遗忘吧。
一
周作人留日归来后,在杭州教书时写了《儿歌之研究》,发表在1914年1月出的《绍兴教育会月刊》。(4)鲁迅对民国初期征集谣谚事业的发端也是有贡献的,他在发表于1913年2月北京《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册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建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见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4页。他在文中写道,有一类儿歌为“体物之歌,率就天然物象,即兴赋情,如越之鸠鸣燕语,知了唶唶叫,萤火虫夜夜红。杭州亦有之,云:‘小焰虫,的的飞,飞上来,飞下去。’或云‘萤火萤火,你来照我!’甚有诗趣” [3](P.5)。在他用来举例的歌谣集中,有一种名《天籁》:“若淫词佚意,乃为下里歌讴,非童谣本色。如《天籁》卷一所载,‘石榴花开叶儿稀’,又‘姐在房里笑嘻嘻’皆是。” [3](P.8)
笔者杭州人,家中有一册同治八年(1869年)浙江书局刊印的芝秀轩藏版《天籁集》,写刻本,郑旭旦辑,许之叙校并序,名义上录歌谣48首,实收46首(均标号,缺36和46两首)(5)第7首恐系两首歌谣的串合:“小小一只白公鸡,头又高来尾又低。相公不杀我,留我五更啼。五更不见啼,花猫驮在竹园里。竹里梅花带雪开,东风吹下一枝来。邻家有个花娇女,嫁与聪明小秀才。”后四句是不是独立的歌谣?比较娄子匡采编的《越歌百曲》(也收入北大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1辑,第5种)第三部分“生活歌”第34首:“小小一只高冠鸡,头又高来尾又低。相公叫我五更啼,我乐五更勿肯啼,花猫拖到竹园里。”。郑旭旦自撰序、跋(分别6页和7页),并集“天籁集醒语”18条置于自跋之后,还在每首歌谣前后留下长短不一的评语,最长一条字数多达七百左右。可以说,郑旭旦这些文字成了《天籁集》的一部分。这册歌谣末页是作于同治八年的补序,与正文字体不同,由普通刻工刻印。周作人所举两首短小的“体物之歌”就是集中第28首(“萤火萤火”)和第47首(“小焰虫”)。 但是,《天籁》卷一所载“石榴花开叶儿稀”和“姐在房里笑嘻嘻”似应指两首“下里歌讴”的首句,笔者这册《天籁集》中第12首的头两句是“石榴花开叶儿稀,打扮小姐娘家嬉”,未见以“姐在房里笑嘻嘻”起首的歌讴。周作人或许凭记忆写下这两句歌词,没有查核原文。也不排除另一可能:他所读的《天籁》与浙江书局的《天籁集》版本不同,后者是不分卷的。(6)“姐在房里笑嘻嘻”是山阴悟痴生编录的《广天籁集》中第3首。《广天籁集》中歌谣主要来自周作人故乡绍兴地区。中原书局于1919年将《天籁集》和《广天籁集》合编出版,“上海悲增标点”。这本合集现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近据民俗学专家查核,至今未见关于《天籁集》的文章,笔者不妨借《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一些粗浅的介绍,或可丰富我们对乡邦文化的历史记忆。下文所引《天籁集》中序、跋、歌谣等均出自同治八年浙江书局刊印本《天籁集》,不另出注。
在此书正文第一页,两位辑校者直排并立的名字上是大一号的“钱塘”二字,可见他们是杭州同乡。许之叙还作一短序:
苗硕两言,孔圣取之;沧浪数语,孟氏述之。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郑君名旭旦者,吾乡名士。苦志十五年,郁郁无所遇,乃著是集。共四十八章,缺二章,不知何意。观其自序暨跋语,确有明人代笔意。噫!此所以触造物之忌欤?然其体验人情,详悉物理,虑正言庄,论之不能动听,而假村言俚语以宣之,暮鼓晨钟,足使庸愚醒悟,诚不得谓无功于天地也。集中所采歌谣,半皆童时时诵之词。吾愿世之抚婴孩者,家置一编,于襁褓中即可教之,则为之长者,口传耳熟,自警警人,良知良能,藉以触发。庶几为师箴瞍赋之一助云尔。郑君家世无可考,或别有著述,予未及睹,将归而询之父老,再当为之作传也。
咸丰丁巳三月展上己同里许之叙撰于永定署斋
“咸丰丁巳”即咸丰七年(1857年),许之叙当时是湖南永定的县令,几年后不幸死在任上,没有机会回杭州了解《天籁集》辑注评点者郑旭旦的家世并为他作传。许之叙并未交代书稿如何辗转到他手中,多少让有意查考《天籁集》来历者失望。从郑旭旦自撰的序跋(未署时间,不合惯例)判断,《天籁集》在他心目中重于生命,即使他英年早逝,郑家也不会轻易将书稿委弃或托付他人。本着胡适先生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的精神,笔者怀疑郑旭旦是不是一位虚构人物。传统读书人重诗文,贱视山歌俚曲等俗文学的表现形式,像冯梦龙那样收辑民间时调,在士大夫眼里有失身份。郑旭旦会不会就是许之叙中举之前的另一个自我?易言之,许之叙也许曾“不售”,落寞之际以搜集家乡歌谣为寄托,书成后又不愿署名,因他更看重自己的《芝秀轩吟稿》。(7)纯系猜测之言,尚祈方家指正。
许之叙序中说“集中所采歌谣,半皆童时时诵之词”,表明道光甚至嘉庆年间,书中半数歌谣已在杭州流行。附在书末的《天籁集补序》作者许郊子说起此书版刻的缘起:
《天籁集》者,钱唐郑旭旦编次,余从弟彝伯为付梨枣者也。彝伯与从兄培之暨余皆同岁生,幼各就傅,彼此戏投笔札,署称同年。先君子见之怒其顽。业师仲平汪先生冁然曰:“童子何知,此真天籁也。”后彝伯领己酉乡荐,乙卯以知县拣发湖南,历权永定、石门县令,以积劳成疾,遽而委化,剧可哀矣。彝伯有手辑《酒阑灯炧谭》二十四卷,拟梓未逮。其《芝秀轩吟稿》弟妇高氏已为付剞劂。《天籁集》亦刻自湘中。今年夏弟妇携板回,余得见之,为重加校阅。此集所编皆吴越谣谚,忆幼与彝伯、培之歌咏欢笑,才如昨日,今彝伯已亡,培之登甲子贤书,将有四方之志,惟余两鬓渐衰,一衿尤困。年来从事书局,尚理帖括,同年之说,竟成戏语。然则覩斯集也,岂独彝伯之可哀也哉!余亦感慨系之矣。
同治八年己巳重九日许郊子社甫识于浙江书局之校经庐
这里说的“彝伯”就是许之叙,他己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乡试中举,乙卯年(咸丰五年,1855年)赴湖南永定当县令,后调石门,在任上“遽而委化”,“芝秀轩”系他室号。《天籁集》在太平军战乱期间刻印传世,他是第一功臣,遗孀高氏能将印版从现在的张家界、常德地区带回杭州,也十分不易。从这篇补序来看,初版是湖南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册),刊刻时间为同治元年(1862年)。这位许郊子和堂兄弟许之叙、许培之同年出生,许之叙已去世,许培之在甲子年(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而作者是科场失意之人(“一衿尤困”),在浙江书局的校经庐谋得一职。这篇补序与正文(许之叙序、郑旭旦序、跋以及自撰醒语)不同,系刻工刻印。
二
《天籁集》多数歌谣都是即物起兴的,头两句与后面的歌词毫无联系。第1首就很典型:
墙头上,一株草,风吹两边倒。“今日有客来,舍子好。”“鲫鱼好。”鲫鱼肚里紧愀愀。“为舍子不杀牛?”牛说道:“耕田犁地都是我。” “为舍子,不杀马?”马说道:“接官送官都是我。”“为舍子,不杀羊?”羊说道:“角儿弯弯朝北斗。”“为舍子,不杀狗?”狗说道:“看家守舍都是我。”“为舍子,不杀猪?”猪说道:“没得说。”没得说,一把尖刀戳出血。
杭州方言“舍子”即“啥子”(什么,什么东西)。教儿童认识牲畜的作用固然必要,但是屠宰的主题以及集中后面一再出现的怨毒之言对里巷小儿是不合适的。儿童以前就是“小大人”,他们诵习的歌谣里颇多现在看来属于“少儿不宜”的文字,父母并不在意。儿童的概念直到晚清有了中外文字之交后才渐渐被中国读者认知并接受,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儿童文学。《天籁集》第一首歌谣末一句未免太血腥,不过也有讲仁爱的,如第25首:
螺蛳经,念把众人听。日里沿沙走,夜里宿沙村。撞着村里人,缚手缚脚捉我们。九十九个亲生子,连娘一百落汤锅。捉我肉,把针戳。捉我壳,丢在壁角落。鸡爬爬,响碌碌,玉皇大帝亲看眼泪纷纷落。
起头用“螺蛳经”三字,颇有释家众生平等的慈心。传统社会重各种美味,甚至有“八珍”之说,怜惜螺蛳家族的命运,就更加难得了。但是紧接着一首却是笑话佛教徒的:“乡里老娘旧病发,走到城里望菩萨。绿鞋子,红鞋跋。走一步,拔一拔。”老太太遭嘲笑,残疾人士就更不会放过了。第20首用的是矛盾修辞法,让读者眼睛一亮:“三十夜,月光朣朣,一个老儿偷了辣酥种。瞎的看见,聋的听见,哑的叫起来,瘸的赶将去!”
癞痢原是常见病,其实无非是真菌感染,用西药软膏一搽就见效,现在早已绝迹。以前患了癞痢,久久不愈,患者就被叫做癞痢。《天籁集》第32首夸奖癞痢勤劳当家:“癞痢癞,挑粪浇荞麦。荞麦开花,癞痢当家。荞麦结子,癞痢笑死。荞麦上磨,癞痢端坐。” 第5首讲的是一位美丽的姑娘要出嫁了,嫁妆丰厚,究竟嫁给谁呢?运气不好,新郎是癞痢。她没有父母,叔伯在决定她的终身大事,她也能将就。癞痢穷一点倒不妨,只要长得好:“高田水,低田流。叔母伯母当曙上高楼。高楼上,好望江。望见江心渡丽娘。丽娘头上金钗十八对,脚下花鞋十五双。金漆笼,银漆箱,青丝带儿藕丝裳。问鸳鸯,团团排,一转排着癞痢郎。只图癞痢生得好,不图癞痢藏珍宝。”
癞痢劳动有所得,应该开心。他的称呼说明受歧视,但是行为却得到认可,懒汉就不然:“日头黄,懒汉忙。日头竖,懒汉靠屋柱。日头谢,懒汉叫夜夜。”(第33首)忙来忙去的人也不一定能享福,有的人呆头呆脑,却像西湖里的土步鱼,不动也有食吃。第44首借鱼比人:“苍条潝潝豁,肚皮瘪搭搭;土哺呆呆,自然有食来。”苍条鱼游来游去,总是吃不饱。杭州西湖盛产土哺,即土步鱼,又名沙鳢鱼或塘鳢鱼,冬日伏于水底。消极对待生活的态度也见于第38首里的极端愤激之词:“田要少,屋要小,子弟读书不要考。免得杀,免得绞,免得商鞅饱。”科场失意者正好以此自慰。
《天籁集》所收歌谣,有几首精悍短小,如前引第27首:“角角啼,天亮哩。”第30首也只有六字,像是农谚:“杨柳青,粪如金。”与农耕相关的还有第29首:“牵牛儿上,牵牛儿下。氓蜂钉,截辣一声。”稼穑全赖牛力,农夫牵着牛儿,岂容牛虻叮咬。反观今日,浙江个别地区竟有牛二们故意牵出两头牛来互斗,从中取乐。如此残忍,一巴掌打过去,还太温柔了!《天籁集》的第34首和35首在书写季候的同时还反映了穷人过冬艰难:
大雪纷纷下,柴米都涨价。乌鸦满地飞,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
头九二九,相招不出手。三九二十七,凌丁挂半壁。四九三十六,才方冻得熟。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不要舞,还有春寒四十五。
集中有几首是非常简洁的白描,如:
三个官儿,在楼上吃酒,三匹马儿,在楼下吃草。两个老儿,在街上相打。一个隔壁老娘,摇手说“罢休罢休!”(第39首)
落雨丁丁,猪肉三斤。公来估估,婆来秤秤。(第31首)
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却多言外之意。官儿、马儿、老儿和老娘是三、三、二、一的递减,小儿可以借此辨识数字,而酒楼上的悠闲又衬托出街上小老百姓的艰难。郑旭旦对后一首的评语称得上短而精:“雨天寂寞,村居得肉,不啻海错山珍。公估婆秤,写尽欢呼节啬神理。”第11首白描江南水乡月夜景色,很有诗趣,可与“枯藤老树昏鸦”媲美:“月光堂堂,照见汪洋,汪洋水,漫过菱塘,风吹莲子香。”
《天籁集》中有些歌谣故意颠覆情理,就像英国谐趣诗人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 1812-1888)《胡诌诗集》中的作品(8)集中四行体的打油诗已由陆谷孙先生译出,见爱德华·李尔《胡诌诗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霍尔布洛克·杰克逊曾编《爱德华·李尔全书》(费伯-费伯出版社,1947年),四行体的打油诗仅为其中一部分,有些稍长的叙事诗幽默风趣而又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如《猫头鹰和猫咪》。。这类歌谣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节律感和自由自在的想象力,其实在各地都有。郑旭旦在简介第21和22两首时写道:“此与下篇皆随韵粘合,绝无文理,然绝世奇文有不必文理而妙绝千古者,此类是也。”请看:
一颗星,挂油瓶。油瓶漏,炒黑豆。黑豆香,卖生姜。生姜辣,造宝塔。宝塔尖,戳破天。天唉天,地唉地。三拜城隍老土地。土地公公不吃荤,两个鸭子囫囵吞。(9)比较《吴歌甲集》第13首《天上星》:“天上星,地上星,太太叫我吃点心。弗高兴,买糕饼。糕饼甜,买斤盐。盐末咸,买只篮。篮末漏,买升豆。豆末香,买块姜。姜末辣,买只鸭。鸭末叫,买只鸟。鸟末飞,买只鸡。鸡未啼,买只扦光梨。”开首三句和最后两句是头尾,其余三字句以两句为一对,共八对,每对最后的名词用作随后一对的起首。
夹雨夹雪,冻杀老鳖。老鳖看经,带累观音。观音戴伞,带累总管。总管着靴,带累爹爹。爹爹着木屐,带累瞎搕石。(搕石是方言,指乞丐。)
大概在1960年左右,杭州地区的儿童还玩一种语言接龙的游戏:甲起个类似“一颗星,挂油瓶”的头,乙接上,重复最后两字,造两个押韵的三字句,丙再如法炮制传下去。
第42首也是以“一颗星”起兴:“一颗星,半个月,虾蟇水里跳过缺。我在扬州背笼儿,看见乌龟嫁女儿。黿吹箫,鳖打鼓,一对虾儿前头舞。”“虾蟇”此处的音、义与“蛤蟆”同。为什么是“在扬州背笼儿”?或因扬州系古代水路交通要道。乌龟还有一层不大雅驯的意思,一为妻有外遇者,二为开妓院或在妓院执役的男子。“乌龟嫁女儿”还要讲排场,显然就有点滑稽了。郑旭旦的评语也有点刻薄:“当星稀月朗之时,适见乌龟嫁女之事。此时情景,最堪描画。然一着相,意味索然,必至丑不可耐。此文妙在先将星月生姿,借虾蟇作影,然后将正面一点,随即乘势推开,若鼋若鳖若虾,实则乌龟之类而借客陪主,尽掩其丑,只觉姿趣横生,此真化臭腐为神奇,不止五花八门,变化百出已也!”
“变化百出”的还有第23首。那是两位妇女之间匪夷所思的对话:
“唂咚唂咚咤,半夜三更来做舍?”“不吃公公酒,不吃婆婆茶。只问公公讨只狸花狗。”“卖哩。”“公公呢?”“死哩。”“舍子棺材?”“乌木棺材。”“舍子抬?”“两个蚂蚁抬。”“舍子鼓?”“鼕鼕鼓。” “舍子锣?”“疙疬疙瘩老虔婆。”
以象声词发端,在《天籁集》中绝无仅有。半夜三更有“老虔婆”来敲门,她的问话完全不受人际交往规则的约束。请看郑旭旦评语:
绝世奇文,惟其愈出愈奇,是以奇绝。当三更半夜,一媪突如其来,自言不叨酒茶,而惟讨狗一只,固已奇矣。此媪厌而以卖去覆之。彼媪亦可以告退,乃竟舍狗而问及公公。此问胡为乎来哉?斯时欲不应之,恐其缠绵无已,惟应以死,而彼将不复有词,而不料其竟有棺材之问也。此媪以彼媪认真,则又诡词以对。天下安有死而用乌木棺材者?则公公之不死可知。彼媪竟不理论,乃至问及抬者。而后此媪率性戏弄之曰蚂蚁,盖已奇幻入神矣。彼媪恬然不惊,而且问鼓,则随应之曰鼕鼕鼓。问鼓不已,而又问锣,势将无所不问矣。无所不问,虽至达旦而犹剌剌不休,天下有如是疙疬疙瘩老虔婆,而可以情恕者哉!势必一骂散场,而闻者为之绝倒。吾不知天下果有是事否乎?纵无是事而见此妙文,闻此妙语者,必无不绝倒之理。则其奇而又奇,以至于奇绝,夫岂人心思索之所能至者耶?
三
据笔者初步统计,《天籁集》中近半数(约20首)歌谣的叙述者是年轻女性,除了有一首感谢母恩,(10)第41首:“石榴花开叶儿青,做双花鞋望母亲。母亲耽我十个月,哪个月里不担心。”郑旭旦评道:“此文信天下之至文也。”两首情歌,(11)第8首:“一年去,一年来,又见梅蘤[案:花的古体]带雪开。梅花落地成雪片,开窗等雪望郎来。”第九首:“喜鹊哥哥尾巴长,偷柴偷米养姑娘。姑娘死在黄泉路,摇摇摆摆哭一场。”姑娘相思而死,也可以说是殉情了,但这是婚外之情。刘经菴对歌谣中情歌最多的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一般妇女的生活,太苦得不堪了!不但受公婆的虐待,小姑的诽谤,连自己的丈夫亦是动辄打骂的。除了她求别人的怜爱——情人可得些慰安,享些人生的乐趣,此外谁是她的保护者和慰安者呢?”见刘经菴编《歌谣与妇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26页。其余的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婚姻对女性决定性的影响以及旧家庭的负面形象,其中姑嫂不和最为典型。第2首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
月亮光光,女儿来望娘。娘道“心头肉”,爷道“百花香”,哥哥道“亲姊妹”,嫂嫂道“搅家王”。“我又不吃哥哥饭,我又不穿嫂嫂嫁时衣。开娘箱,着娘衣。开米柜,吃爹的。”
娘和爹都疼爱这位女儿,嫂子却不表欢迎,称她“搅家王”,或许她相信“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回娘家就会搅起纠纷。这位女儿伶牙俐齿,让嫂嫂明白她回娘家,吃用都是她父母的。(12)娄子匡采编的《越歌百曲》中“生活歌”部分第13首“吃爹饭,穿娘衣”写的也是女子回娘家。《吴歌甲集》第55首:“月亮圆圆,/荷花囡囡/出来张娘。/娘说道,‘金和宝转来哉!’/爷说道,‘宝和金转来哉!’/阿爹说道,‘敲背囡转来哉!’/好婆说道,‘荷花囡转来哉!’/嫂嫂说道,‘败家精转来哉!’/哥哥说道,‘搅家精转来哉,/搅得黄河水弗清!’/‘吃爷饭,/着娘衣,/朆吃哥哥窠里米;/朆着嫂嫂嫁时衣!’”类似例子很多,第56首也是。这一首里的哥哥叫她“亲姊妹”,还讲一点同胞手足的情谊。第3首的口吻是未嫁的女儿,以后她找一户人家,嫁妆是一大笔开销,哥哥因此叫她“赔钱货”,嫂嫂公然视她为“活冤家”:
青萍儿,紫背儿。娘叫我,织带儿。“带儿带儿几丈长?”“三丈长。”把娘看,好女儿。把娘(13)原文如此,或应作“爹”看,一枝花。把哥哥看,赔钱货;把嫂嫂看,活冤家。“我又不吃哥哥饭,我又不着嫂嫂衣。开娘盒儿搽娘粉,开娘箱子着娘衣。”
姑娘与哥嫂不睦,在歌谣中已成了固定的节目。第43首里嫂子缺席,十分醒目,只“阿哥”一人骂她“赔钱货”:“缸豆儿,开紫花。大姑小妹嫁人家。嫁人家,娘哭的,娇娇女;爹哭的,一枝花;阿哥哭的赔钱货。不哭得,意不过。”这是在离开娘家的时候,到了婆家又如何?妯娌之间新一轮的争斗还在等着她。末一首即第48首讲的是姑娘出嫁了,打扮得漂漂亮亮,婆家兄嫂竟骂她“野猪精”:“石榴花,系红裙。女儿十五做新人。郎看看,‘活心肝’,婆看看,‘喜新娘’。阿姆看看‘野猪精’。我又不替阿姆同床宿,我又不替阿姆共枕眠。我家寒舍少花钱。不搽粉,比不得阿姆白;不搽油,比不得阿姆黑。不曾做惯,比不得阿姆能干。”
这里的“阿姆”就是郎的兄嫂。(14)据吕祖谦《紫薇杂记》,弟妻呼兄嫂姆姆。妯娌之间的持久战从见面之日就开始了。脸不搽粉,发不搽油,表明她以本色出现在新家。究竟娘家是不是“寒舍”,究竟“阿姆”长相如何,还不知晓。新人不是惯做家务,反而说明家境较好。既然阿姆勤快,以后就多做做吧!这首歌谣的格调与第2、第3首基本一致。编者站在新娘一边教训“阿姆”:“吾曾以此观世之好毁人者,未有不自中其身而为天下笑者也。一人之意见,必不能乱千古之是非,而肆口讥评,自鸣得意,卒之遇彼才辩之士,其机锋捷于发矢。显则热斥,微则冷刺,究亦无如之何。”无端毁人导致反击,无言以对,自取其辱。
女儿归宁,看嫂子脸色,生出一股怨气,她的情绪又传给自己的儿子。第15首描写的是外孙去看外婆时受舅母羞辱:“黄花儿,着地生。我是外婆亲外孙。外公出来叫请坐。外婆出来叫肝心。舅舅出来不做声,舅母出来努眼睛。一碗饭,冷冰冰。一双箸,水淋淋。一碟菜,二三根。打碎舅母莲花碗,一世不上舅母门。”(15)娄子匡采编的《越歌百曲》第一部分“儿歌五十曲”中的第8首《黄栀花》主题也是外甥不满于舅妈的招待。有两句是“一双筷,水淋淋。一碗饭,冷冰冰”。外孙因舅母小气发怒,竟然打碎饭碗,发誓不再去舅母家。童子学唱了这样的歌谣,不是在接受仇恨教育吗?他今后就不再想念外婆了吗?
姑嫂之间的不和在各地歌谣中都有反映,而一代代儿童唱着这些歌谣,又在潜意识中强化了对姑嫂间恶感的预期。小姑出嫁前依仗母亲做靠山,欺压兄嫂,嫁人后回娘家又受嫂子气,一报还一报,形成恶性循环。在刘经菴编撰的《歌谣与妇女》中,连父母也骂女儿“赔钱货”,他们甚至卖送女儿,还和公婆一样殴打女儿。(16)详见刘经菴编《歌谣与妇女》第2章至第4章。《越歌百曲》第三部分“生活歌”里的第30曲题目竟然是《养囡养强盗》。溺婴陋习的牺牲者几乎都是女婴,与此也有关系。《天籁集》未载女儿、媳妇挨打的文字,说明地区差别,也许是郑旭旦编选歌谣时已将有的歌谣排除在外。
旧式婚姻缺不了“媒妁之言”,婚姻不幸,媒妁就成了诅咒的对象。第4首是《天籁集》中最长的,共114个字,诉说的是受了媒婆的骗:
石榴花,花簇簇,三个姐儿同床宿。那个姐儿长?中间姐儿长。留下中间姐儿伴爹娘,伴得爹娘头发白,三对笼,四对箱,嫁与山村田舍郎。咸鱼腊肉不见面,苦珠蚕豆当干粮。一封书,上覆爹。一封书,上覆娘。一封破书上覆媒婆老花娘。长竹枪,枪枪起,枪凸媒婆脚板底。短竹枪,枪枪出。枪折媒婆背脊骨。
这位女性婚后生活艰窘(“苦珠蚕豆当干粮”(17)苦珠即苦槠树果实,可食。),没有自己娘家吃得好(“咸鱼腊肉”),就向父母诉苦,还写信给媒婆责问一番,恨不得拿起长短竹枪戳穿媒婆脚底板,折断她的背脊骨。“山村田舍郎”人品如何,却不是她的关心所在。选一个婆家,毕竟也是为自己大半生的利益投资,可恨“老花娘”竟不以实情相告。难怪刘经菴在《歌谣与妇女》中写道:“多半的媒妁,徒以吃喜酒、使礼钱,为他唯一的目的;把两家的儿女的终身大事,把戏似的,任意的玩弄,随便的哄骗。” [4](P.14)媒婆骗人,待字的闺女只盼来说亲的不会被钱收买,如第6首:“烟护烟,烟上天。红罗裙,系半边,谁家女儿立门前。绣鞋儿,尖对尖,土地公公不爱钱。祷告你,阴中保佑与我做姻缘。” 土地公是民间信仰体系里象征公平的神明,只有他,这位姑娘才信得过。
婚姻固然不幸得多,但是少女到了及笄之年,还是想出嫁。第17和第45两首都是表述了她们对婚姻的憧憬:“黄狗黄狗你看家,我在院中采红花,一朵红花采不了,双双媒人到我家。‘我家女儿年纪小,不会伏侍大人家。’爹哎爹,不要忧;娘哎娘,不要愁。看我明朝梳个好光头。前边梳了盘龙髻,后边来到看花楼。看花楼,好饮酒,他弹琵琶我拍手。”第5、6两句表示女儿婚事不急,是父母婉谢媒婆时所言。女儿听了先安慰他们“不要愁”,她是否知道现实生活远比“梳个好光头”复杂?第45首的叙述者年纪还小,内容也单纯:“竹公竹婆竹爹娘,今年让你长,明年让我长;你长无用处,我长嫁儿郎。” 第16首里的姑娘也要出嫁了,她在盘算着自己的嫁妆:“红布衫,绿布裙,外公替我做媒人。受了多少苦。大阿哥,许我大阪田。小阿哥,许我小阪田。大阿嫂,许我八朵珠花。小阿嫂,许我四朵珠花。八朵珠花戴在面前。四朵珠花,戴在半边。我也不要大阪田,我也不要小阪田。我只要十二个箱子箱箱满。”郑旭旦写出了她的复杂心态:“村中女儿,勤苦当家。年已及时,闻说亲事。满肚皮打算,又得意,又疑虑,又计较。至理至情,如是如是。”
第13首始于美好的盼望,终于势利的鄙夷:“推槎过,慕才郎,正值哥哥上学堂。尖尖笔,做文章;读书子,状元郎。花对花,柳对柳;破粪箕,对笤帚。盐荠菜,下浑酒。放在大门前,那个肯来吃一口。”粪箕是典型杭州话,也叫畚箕,即簸箕。这首歌谣前后两部分讲的是两种命运:读书人前景好,所以姑娘“慕才郎”;下半段她脸色突变,要让家里只供得起“盐荠菜”的穷汉掂掂自己的分量,不要做梦(“那个肯来吃一口”)。不过“才郎”将来功名之路走不通,也会沦落为孔乙己之类穿长袍的穷措大。物质条件在婚姻中的决定性因素又在这首歌谣里直白地显露出来。
有几首女性口吻的歌谣内容比较特别。第12首里的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回娘家,路上受到勾引和侮辱,她以严词捍卫自己的贞洁:“石榴花开叶儿稀,打扮小姐娘家嬉。梳好头,穿好衣。‘保佑你的丈夫早早死。早早死,我与你,做夫妻。’‘喷你雪,嚼你蛆。我的丈夫死相随。’” 第14首是5位已婚女子聚在一起吃喝聊天,四娘出言伤人,五娘最为年轻,不甘示弱,辩白说自己是明媒正娶,婆家接亲档次高,还出了体面的礼金:“蔷薇花儿朵朵开,大娘吃酒二娘筛,三娘摆出果子菜碟儿来。四娘骂我狗奴才。‘我又不是挨来的,我又不是走来的。我是花花轿儿抬来的。十锭金,十锭银。十个梅香来接亲。哥哥抱上轿,嫂嫂送到城隍庙。’”杭州话说“挨来挨去”是表示碰到不那么吸引人的东西,大家推来推去。这一表述也见于上海话。
歌谣里发声的女性身份、地位不同,心愿也不同。第40首就反映了婢妾的心愿:“龙生龙,凤生凤,麻雀生儿飞蓬蓬。老鼠生儿打地洞,婢妾生儿做朝奉。”我们的社会一度流行出生论,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听说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首歌谣的全文,人们却不甚了了。《天籁集》这首儿歌带有明显地域特色,肯定异于北京的版本。编者在“婢妾生儿做朝奉”后评注:“奇。徽州称商曰朝奉。”据《汉语大辞典》,宋朝有朝奉郎、朝奉大夫等官职,宋人因以朝奉尊称士人,南宋后用以称富豪、店主,清以来则称老板和当铺店员为朝奉。徽商做生意,往往要到江浙寻找机会,他们在这首儿歌中留下印记,说明杭州的婢妾中也有徽州一带的女性,她们希望自己所生的孩子长大经商,发财致富。郑旭旦在诗后如此评论读书人(“士”)嫉妒商人的现象:
……乃今之为士者,见商之多财,而己之无所取资也,往往屈抑卑下之,而商遂俨然自置其身于士之上。不知先王置商于四民之末,良有深思,诚以为富不仁,商居其九,夫是以贱之。古之所贱,乃为今之所荣,亦可以见世变矣。吾曾细玩“龙生龙”一章,而知斯人之大有羡于朝奉也。彼意龙凤之所生,自应如彼;雀鼠之所生,自应如此;则婢妾之所生不应有迈种之奇也。乃龙凤雀鼠各有所生,而婢妾生儿,居然朝奉,则诚诧异之甚者也!彼又恶知古之人贱之,置居四民之末,固宜婢妾之子之为之者哉!虽然朝奉亦竟有不可及者。彼夫临财廉,取与义,好施不倦,恭俭下人,虽士有不如其行者,而亦岂在所贱之中。
大家庭内部多弊病,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出现一些反省,如林纾《闽中新乐府》最后一首《百忍堂·全骨肉也》起头就是“百忍堂前善气祥,百忍堂后戾气殃”。“家督”张公但求和睦,却总有不周到的地方:“焉能以己心,尽体人衷曲。”他的疏忽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家里的不睦大都因女眷对小家庭的地位特别敏感所致,而她们的焦虑又产生于潜在的自卑和不安全感。
在此应该引入传统社会中妇女生活状况的话题。康有为是我国最早发出女权思想的人之一,《大同书》(陆续完成于光绪年间)戊部(“去形界保独立”)第一章就是《妇女之苦总论》。康有为列举种种女性所受压迫。在广东,做人新妇苦不堪言:“自妇之初来也,或以明慎始之义,张严威以临之,或以重家法之名,行苛礼以苦之。始具榛栗枣脩以见姑也,跪拜而下,则严陈约法,问其允否。其强之见族人也,则自小叔、女妹、犹子、侄孙,无不献茶行礼,日至四五。其献尊长必行拜礼,甚至于姑之婢妪亦强跪拜,而平等之叔伯强行四拜之礼无论矣。乃至宾客在席,亦跪地献酒而皆坐而受之。此非奴而何?”[5]可悲的是受人欺压的记忆往往发酵为伤及心灵和社会的毒素,一旦“媳妇熬成婆”,昔日的受害者又转身而为施害者了。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傅兰雅等传教士带动下的反缠足呼声日益高涨,妇女问题才逐渐在男权社会文化语境下浮现出来。1918年《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即第4卷第6号),刊登《娜拉》(即《玩偶之家》)等剧作以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终于给予传统的家庭和婚姻观念沉重一击。刘经菴的《歌谣与妇女》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产物,他在结语中发出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声:“妇女为产生歌谣的母亲。因为她们在旧礼教、旧习惯之下,受环境的压迫,使她们成为人们的牺牲者;要知作人们的牺牲,按情理是谁都不肯承办的,但是到了虽不甘心,而亦不得不如此的时候——所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她不平的情感,要如何的悲愤呢?在这个当儿,她所呼吁出来的语言,要如何的沉痛呢?……我信有许多的歌谣,是她们感怀自己的身世,悲愤交加,以血泪所歌成的。我们知道文艺的作品,多是放情歌唱出来的,不是强要发表而发表的。歌谣所以有文艺的价值,就是在此!由这看来,世之欲研究社会问题——妇女的问题——和民众文艺者——妇女的文学——都不可不研究歌谣哪!”《天籁集》为这个论断提供了佐证。
四
《天籁集》刻印后若干年,山阴悟痴生编录的《广天籁集》问世,所收多是绍兴歌谣。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90年2月将两集影印,并作说明:“本书为《天籁集》(郑旭旦辑)和《广天籁集》(悟痴生编录)两种之合编。中原书局1919年版影印。附《各省童谣集》(第一集),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中原书局影印这两种集子的时候,正值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猛烈展开之际。卷首《重印天籁集序》(未署名)写道:“这两部书,都是荳腐干式的小册子,清同治八年浙江书局初印本,竹纸铅字,字迹都很清楚,但这书在十年以来,是早已绝迹于坊间的了,有没有再版,也不得而知。”
这些文字留下一些疑点。笔者未曾见到《广天籁集》原初的版本,但是手头这册《天籁集》(“清同治八年浙江书局本”)系写刻本,高23.7公分(修补时上下还稍稍裁去一些),宽15公分,绝非“小册子”,更不是“铅字”排印。影印本《天籁集》未收许之叙序,第一首之后有“原评佚”三字[6](P.2),而笔者藏本第一首之后有176字的评语,论及语言、人与物的关系。显然,影印的《天籁集》所用版本比较粗劣。1919年这两种歌谣集的合集标点者“上海悲增”应该也是书前8页《重印天籁集序》(未署名)的作者。这篇序言可以视为《天籁集》和《广天籁集》传布史上的重要文献。作者是白话运动的拥护者,他虽褒奖集中歌谣,(18)“我们用新文学的眼光看起来,实在首首都是绝妙好词,不愧他的集名天籁二字。”见《重印天籁集序》第1页。对郑旭旦的评语却无端诟谇一番:
每一首前后,都有拖泥带水极酸腐的评语,而后评较前评,其八股气更重,大概还不是一个人的手笔。但是把这些极酸腐的东西,放在极清灵极活泼的妙文后面,反而可以相映成趣,譬如吃蟹蘸些酸,转增风味。……至每首中间,尚有许多夹评,都是金圣叹式的妙—妙—奇—极趣—等语,但有几句还算中肯,能搔着痒处,比起前后两位十三经蛀虫要高明多了,也自然照样嵌在里面。 [6](《重印天籁集序》,PP.1-2)
序言作者尤其看重集中随口凑合毫无意义的歌谣:“这一类既无意义,自亦无文学的价值可言;但我人平日说话作文,大都先有所为,而后方有所谓,若无所谓时,若无所为时,决不能有所谓,独有这一种歌谣,并无所为而竟有所谓;盖其动机只在于要唱,并没有想到要唱些什么也。……这一类无意义的才算真正的天籁呢!” [6](《重印天籁集序》,P.6)这位序言作者也透露出一点个人信息:
记得二十年前,那时我至多不过八九岁罢;正在家塾里念孝经。晚上散了学,坐在天井里乘凉的时候,有一大丫鬟名巧儿的常常教我唱什吗“萤火虫,夜夜红”之类的小歌,我也自然很高兴。巧儿会唱的歌很多,不止十几只,因此我常想世界上学问最深的人,除掉教我孝经的老师以外,大约就要算巧儿了吧,可是有一天我在父亲的书柜里,忽然翻到了这两本小册子,那时天籁的籁字还没有认识,只念他做天懒,翻开这本天懒集一看,真使我欢喜得双脚直跳。偷出来,一个黄昏就记熟了;明天唱给巧儿听,谁知她大半跟不上来,于是我更加得意,颠倒做了巧儿的老师,压倒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问家。过了几时,这两本小册子忽然又失了踪,忽忽二十年没有发现过。直到去年年底偶然打扫书室,才又在一个书架的顶上老鼠屎里找着了。已经烂去了一角,幸而没有损及正文。于是把二十年前的旧课,重行温理了一遍,觉得趣味仍很浓。因此又想起那巧儿,她在我祖母故世的那年嫁给一个裁缝匠,听说她近况很好,已经生了五个儿女,现在或者她那最小的女儿,也会唱“萤火虫!夜夜红”了罢? [6](《重印天籁集序》,PP.7-8)
这篇序后收有不足百字的文言评语六则,作者分别为“蕺山老叟”“明湖钓叟”“粥粥子”“弇山外史”“求自足斋主人”和“天隅遯客”,都是为《广天籁集》而作。
尽管前面已表示对《天籁集》辑评者郑旭旦的身份存疑,最后还是要谈谈他。第27首(“角角啼,天亮哩”)后评中有此一句:“吾生才廿二,而作客五年,其间困苦流离操心虑患者,不知凡几。”他为何失意落魄,流落他乡?为什么语焉不详?再看《天籁集》自序中这几句:“吾尝刻苦读书以求闻达矣。其始也孳孳,其继也勉勉,而卒至于尽瘁而无成。每独夜篝灯,发书朗诵,一有所触,涕泗横流。以十五年苦功,竟掷诸空虚无用之地。穷途回首,能不痛心!”这一年他想必在科场受挫,竟至于将“闻达”寄望于《天籁集》:“吾愿天下后世之锦绣才子,窈窕佳人,同心扬扢此文,毋令风流歇绝,则不惟吾人与天地长存,虽一切鸟兽草木,皆将永有生趣,而吾乃得以逍遥于天地万物之间而无所大苦也。此又我之恋恋于中而大不得已者也。”自跋的宗旨不变,但对于《天籁集》必传后世的信心愈益坚定:“古今无不死之人,而天下有必传之话。旷览宇宙,至理只在眼前,妙文不越俗语。其诙谐也,能令人喜;其激发也,能令人怒;其凄切也,能令人哀;其畅达也,能令人乐。喜怒哀乐,发之自我而感之自彼。我又乌知我之此集不又有以感人乎?想天下后世,必无无情之人,则必无见此集而不触发其喜怒哀乐之人,必无触发其喜怒哀乐而不以此集为妙文之人,则必无以此集为妙文而不思此集者为妙文之人,然则我虽穷饿以死而终无所恨也。”然后他举出都将不免一死的七类人物(贵人、富翁、豪侠、权谋、胆略、圆融、风韵),自己穷饿以死,何辱之有?然而《天籁集》必将传世,沟通古今:“且夫天地之妙文,不必我为之传而自足不朽。世或有忌我疾我而摈斥是集者,然天地之妙文必不以斯人摈弃之故而遂湮没不传,则是天地一日有文字,而古之有心人一日尚存,斯人一日能语言,而古之有心人一日未泯也。苟斯世而不以吾言为然,吾以质之苍苍者。”他几乎时时刻刻都流露出没世无闻的焦虑乃至绝望,功名心扭曲人格的力量也在这些凄惨的文字里展露无遗了。笔者选取“天地之妙文”作为本文的题目,也是纪念这位不见于任何史传的家乡人物。
——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