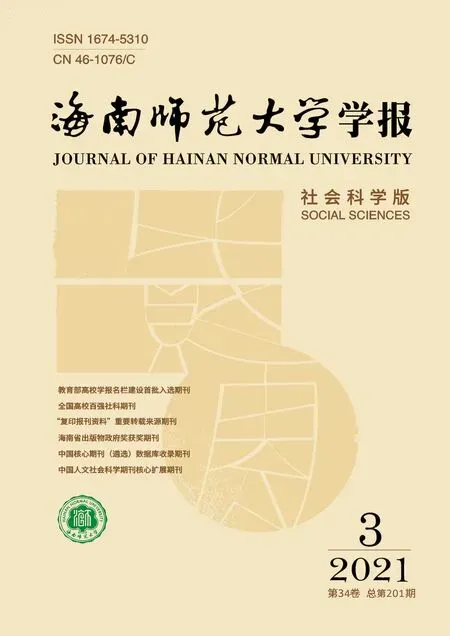技艺、性别与女性主体之思:论王安忆《天香》中的“刺绣”书写
田雪菲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王安忆的《天香》讲述了晚明时期的上海巨富申家从建造“天香园”到开创“天香园绣”,后申家家道中落,申家女性以绣家养生计,最终使“天香园绣”光大天下的故事。《天香》自2011年出版至今,备受评论家青睐,小说有不少引人注目之处,如作者回溯晚明上海的“前史”记忆,小说写作中的纪实与虚构,“大观园”式的女性景观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美学等,既有的评论文章也多围绕这些方面来谈论。《天香》的核心要旨是刺绣与女性,作者以绵密的“刺绣”书写来营造女性群像,王德威就指出,“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当然是刺绣,而刺绣最重要的实践者是女性。”(1)[美]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事实上,王安忆曾在访谈中表示:“‘顾绣’里最吸引我的就是这群以针线养家的女人们,为她们设计命运和性格极其令我兴奋。在我的故事里,这‘绣’其实是和情紧紧连在一起,每一步都是从情而起。”(2)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这足以说明,“刺绣”书写与女性的塑造间有着丰富的表征关系。
出自女性之手的刺绣是传统社会的“妇功”“女红”之一种,经线与纬线掌握着女性语言和欲望的编码,一针一线的编织行为建构的是独特的女性体验和女性言说。本文从“日常习行”的行为视角出发,对《天香》中的“刺绣”书写做一整体考察,认为其在文本中表现出三个层次。首先,刺绣以日常行为实践的方式介入女性情感世界,发挥出“物”的文化功能意义,使女性情感经历物化的淘洗后获得精神独立与情感自足;其次,尝试引入“习行”概念来解读女性刺绣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刺绣习行不仅规训女性身体,还促进其个性表达,在女性经验的形成、女性主体的自我构建方面有着积极意义;最后,当针线女红嬗变为维持生计的技艺生产,刺绣显现出超越“内外”界限之别的意义,女性的刺绣行为具化为一种道德活动而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三层意义在小说中渐次展开,集中反映了刺绣与女性的深层互动,指向了女性主体之思,为我们深刻理解传统社会中闺阁女性的生存图景及其主体地位的演进提供了一条文学想象路径。
一、从“闺阁”到“绣阁”:刺绣与女性情感
刺绣古称“黹”“针黹”,又称“刺绣”“扎花”,因多为女子所作,也称为“女红”。所谓刺绣,是指用针将丝线或其他纤维或纱线以一定图案和色彩在绣料(底部)上穿刺,以缝迹构成花纹的装饰织物。在古代社会,刺绣是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着“男女有别,男外女内”的性别文化观念,是规训女子的理想方式。尽管刺绣工作要求女性被隔离与固定,但仍然为她们提供了私人性的隐秘空间。图案和花纹的来回穿梭诉说着欲望和体验,一针一线的编织行为建构的是独特的女性言说与表达,正如白馥兰指出:“织物可能是最具有隐喻倾向的事物,因为世界上的所有社会都将纺织和联结与拆解的行为联系在一起。”(3)[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刺绣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极富隐喻性的意义表达,尤其在建构女性空间、形成女性经验、确立女性地位等方面都蕴含有丰富的文化意涵。在小说《天香》中,刺绣首先作为了女性情感表达的媒介,申家女眷在婚姻失意后纷纷寄情于绣,将主体情感投射于刺绣的行为过程之中,这一行为机制为观视女性情感的转换提供了路径。
刺绣技艺最先由申家长子(申柯海)的妾室闵女儿传入。柯海在苏州游历时偶遇闵女儿,经友人的撮合将其纳进府中,二人并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闵氏出身刺绣世家,她的嫁妆自然也是精美的刺绣织物,作者对此有一段细致描写:
带来的妆奁一件件打开,都是娘亲手一件件放进去的:一箱笼白绫,一箱笼藕色绫,一箱笼天青色的娟,再有一箱笼各色的丝,还有一个扁匣,装的是一叠花样,一个最小的花梨木匣子放的是绣花针。(4)王安忆:《天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女子嫁妆本具有自我表征的意义,其告诸了闵氏闺阁绣女的人物身份和细腻巧思的女性性格。又因为“嫁妆是女性亲属之间关系的联结物——超越强加在其身上的空间隔离界限,打破婚姻造成的分离。”(5)[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第209页。婚后的孤寂重建了闵女儿与娘家的情感联系,她日日与绣相伴,刺绣俨然构成她抵御现实情感失意的另一美学世界。如小说中所写:“睡莲的影铺满白绫,从花样上揭起,双手张开,对光看,不是影,是花魂。简直要对闵女儿说话了,说的是花语,惟女儿家才懂,就像闺阁里的私心话。”“那浮莲的淡香便渗透盈满。身上,发上,拈针的手指尖上都是,人就像花心中的一株蕊。”(6)王安忆:《天香》,第61页。诸如此类的“化境”营构出“物我同一”的意境,绣物与女性进行对话,同人类主体相互交融,创造出一种和谐统一的景象来克服冷漠与孤寂。闵女儿与绣为伴,同绣相依,凭借刺绣技艺纾解苦闷,累积起人缘。可以认为,刺绣作为情感表达与传递的媒介介入了女性生存空间,重塑了闵氏在夫家的日常行为实践和人际交往关系,弥合了她因缺少丈夫疼爱而造成的情感空缺。她在与刺绣的互动中获得内心的安定与情感的自足,这正显示了刺绣的文化功能意义,如批评家阿伦特在论述物人关系时所说的物(尤其是艺术品)拥有的“显著的永恒性”能够为人类提供“稳定而恒久的感觉”,从而形成一种“稳定人类生活功能”的意义。(7)韩启群:《西方文论关键词:物转向》,《外国文学》2017年第6期。
在谈到《天香》的创作时,王安忆曾说:“其实我的长篇里情节还是在步步推进,可能没有那么显著的运动性,但我自觉得是人尽其能,物尽其用。”(8)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这里的“物”便是指刺绣,“物尽其用”表明作者在建构刺绣的文化蕴涵上所作的努力,这尤其表现在对另一女性人物形象小绸的塑造上。在男性普遍三妻四妾的年代,柯海的发妻小绸得知丈夫纳妾后毅然与之决断,此后埋首习绣。她把对丈夫的过往深情都化进绣中,将刺绣技艺引向更为典雅的文人绣、诗画绣的品格风貌。同样是在这一“移情”过程中,刺绣再次发挥物的文化功能意义,其将“极具主观意义的人类情感当作文化‘隐疾’进行深度疗救”,有学者称作“物治”功能,其功能意义在于“将人类情感进行极大程度的物化后而转向精神与实体之间的真正交合状态”(9)白文硕:《物尽其用——物的文化功能建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这是对人类精神层面另一种维度的解读。小绸将现实的失意倾注于绣中,以情语作绣语,这正是其情感物化过程的体现。与此同时,她重新投入到刺绣美学意义的建构中,为自己建构出新的主体身份——“天香园绣”的开创者。“天香园绣”因情而起,是申家女性情感内化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女性在现实世界之外的情感庇护。换言之,刺绣作为女性主体的行为实践,帮助她们打破由男性施加的情感镣铐而获得新的身份体验,以此来疗愈现实情感的失意与苦闷,唤起女性内在精神的独立。
我们不难发现,小绸、闵女儿这样的女性形象继承了王安忆一贯推崇的女性特质:坚韧、自觉的主体意识,即使处在被动地位也依然追求自我超越。在《天香》中,女性的自我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刺绣”书写得以表现的。如小绸和闵氏将身为一家之主的丈夫柯海“悬空”与“搁置”,反映了女性抛开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视阈的钳制而开始关注内在自我的真切感受,甚至申家男性也自觉地“趋同于投身于女性文化的制约之中”(10)丁帆:《男性文化视阈的终结——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女权意识和女权主义批评断想》,《小说评论》1991年第4期。。显然,刺绣充当女性“移情”的对象和情感转换的媒介,它为我们想象深闺女性的生存图景提供新的想象与诠释:内闱高墙内的失意女子如何通过刺绣技艺来建构超越闺阁以外的情感世界。正如学者颜敏指出,“王安忆的奇思妙想在于,她既看到了女性要求自我空间的艰难,又认为中国女性有将禁闭的空间转换为自我空间的独特策略。”(11)颜敏:《王安忆〈天香〉中的女性生存图景及其价值》,《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8期。对此,小说中关于“绣阁”的书写正是进一步印证。
如今她们几个相聚绣活,多是在天香园西南角上的白鹤楼……有要看绣活的,不必四处去找,就往这里来。渐渐地,就有人称它为“绣楼”,柯海以为不雅,兀自改作“绣阁”。到六七月,红莲开了,映得池水好像一匹红绸,绸上是绣阁,何其旖旎!(12)王安忆:《天香》,第92页。
抬眼环顾,周围丽人绣罗,想这园子从名字起,就有娟秀气息,桃林、莲池、如今又有绣阁,样样件件,繁衍生息,渐成巾帼天地。(13)王安忆:《天香》,第98页。
“绣阁”坐落在天香园一隅,环境清丽、纯净,“巾帼天地”诉说着“去男性化”的特征,这样一个静谧自如的女性天地正是伍尔芙所言“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隐喻,其标识了申家女眷凭借出色的绣艺建构出相对独立的女性空间来获得主体精神和技艺创造的双重发展,具有纠正男性中心的文化意义。除此之外,“绣阁”还作为了凝聚与共享的文化空间,它突破了女性内闱活动的私人性限制,让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和交流,这预示了刺绣技艺将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而实现代际传承,也进一步诉诸了由刺绣所沟通的女性情感空间更加独立和盈满。当女性不再被要求隔离与固定,而是能够在自己的精神领地中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这意味着“作为实践和知识的刺绣,单个妇女能够为自己以及其他妇女创造一个局部的、有限的赋权空间”(14)[加]方秀洁:《女性之手:清末民初中国妇女的刺绣学问》,王文兵译,《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
总体而言,小说第一卷中的“刺绣”书写是作者率先开启女性情感世界的一把钥匙。刺绣首先充当了女性情感表达与传递的媒介,以重塑日常行为实践的方式帮助她们获得新的主体身份,以此来超越男女之情的局限而唤起独立的精神与品格,女性也在刺绣的行为实践中实现了自我超越。
二、刺绣习行:女性主体的自我构建
“绣阁”的建立为申家女性提供了专门化的技艺空间,也说明刺绣事实上成为申家女性集体的行为实践。在传统社会中,大部分女性活动受制于儒家意识形态,但刺绣行为却在规训女性身体,培养主体个性方面独具文化意义。孔子早曾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指出主体的行为习惯与其心性品质的内在关联。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继承孔子思想,推崇“习行”说,强调在实践和练习中获取知识,以达到格物致知。在现代行为科学研究中,“习行”(Practice)有着更为具体的含义,它是指“人们由于多次重复或反复练习而巩固下来的足以体现人的品质的习惯行为方式。它是构成个性的一个重要部分,表现着一个人的稳定的心理和品质。”(15)贾轶峰等主编:《行为科学辞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页。“习行”既是人的行为的产物,又对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它使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去完成行为动作,深刻关联着行为主体的自我构建。以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托的著作《日常生活实践》为例,他采用“日常习行”(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的视角,反思普通人的行为实践并非只是简单按照权力所规划和倡导的模式进行,而是可以通过采取“策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来发挥个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颇具启发意义。在小说《天香》中,申家女性不一而足的刺绣行为可以概括为“刺绣习行”,如女子端坐在绣棚前自我约束、反复练习,蕙兰以发代丝的“辟发”行为,女性自我落款的行为等等,引入“日常习行”的视角对此分析,不仅为我们理解小说中的女性行为提供开阔的视野,也能深入体察王安忆如何刻塑女性人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长期存在,刺绣、纺织等工作天生被视为女性专职,也是待嫁女子所必须掌握的“妇功”。《考工记》中记有:“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16)闻人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妇功”是国家规定的六职之一,从官方高度被赋予了性别角色。在西方文化中,刺绣同样具有规定性别角色、塑造女性性格的意义。以罗西卡·帕克(Rozsika Parker)的著作《颠覆之针:刺绣与女性塑造》(TheSubversiveStitch:EmbroideryandtheMakingoftheFeminine)为代表,他从“刺绣者天生是女性,二者具有天然的联系”这一角度探讨了刺绣与女性气质的建构,“天然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弗洛伊德的研究。弗洛伊德指出女性刺绣的潜意识动机是为掩盖其身体天生的缺陷,“身体毛发彼此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步骤被保存下来,而成为使各线条相互交织的编织活动。”(1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自我意识》,石磊编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他们二人都敏锐地意识到刺绣行为与女性特质间的隐秘关联,女性在这一行为机制下能够变得“温柔、顺从和热爱家庭”(18)Rozsika Parker,The subversive stitch: Embroide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London:The Women’s Press Lrd,1984,p.11.。加拿大学者方秀洁(Grace S.Fong)则观察到刺绣对女性身体的干预,“从事琐碎、细小的工作要求耐心、专注以及勤奋。它需要生理以及视觉的训练:在刺绣机具前长坐,或捧着绣棚,随着手指在绣面上精细地缝纫而密切注视着正在成形的图案。这是无穷无尽、不断重复的一种活动。”(19)[加]方秀洁:《女性之手:清末民初中国妇女的刺绣学问》,王文兵译,《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这些观点都足以证明,刺绣习行在形塑女性主体性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们能够注意到,《天香》中所展示的蔚为大观的刺绣美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王安忆对一整套刺绣话语的熟稔。在前行研究中,小说中的“刺绣”书写或许因过于繁琐重复而容易一笔带过,但若仔细分辨的话,作者对刺绣话语的运用实际上颇有巧思,这其中暗含着女性主体性的构建逻辑。如小说中屡次出现的绣阁、花棚、刺绣图式、辟丝、分色等话术,不仅标识了女性在专业领域内的“权威”,更意图表现她们是如何进行高度的身心训练与自我创造。首先,刺绣对外部环境就有一定的要求。如拈针前要净手焚香,要保持房间的干燥、整洁,理想的习绣条件传达出肃静、净化的氛围,以此唤起女性在精神方面的持续和专注,与刺绣行为有机地联系起来。然后,就女性具体的刺绣过程,作品中有着大量精彩描画,这些描写并非作者的“闲笔”或是无谓重复,而是其构建女性主体性的重要参照。如以下关于配色和辟丝的一段:
小配大,短配长,繁配简,丽配质。没有两朵是重样的……再是配色,已有的颜色都不够用了,要将细得不能细的丝辟了又辟,然后再重合,青蓝黄并一股,蓝绿紫并一股,紫赤橙并一股,橙绛朱并一股,于是又繁生出无数颜色。单是一种白,就有泛银、泛金、泛乳黄、泛水清多少色!(20)王安忆:《天香》,第124页。
又如对“辟丝”过程的描写:
因是单色,必要细分,才可从一种黑里化出许多层,不至于呆板枯索。所以,一根丝非辟成十六、甚至三十二,犹如蛛丝。头一辟,就要辟得极匀,如此,再二辟四,四辟八,略有一毫厘的偏倚,便无法辟下去。眼见得一缕丝披成一披,雾似的。呵一口气就要散得无影无踪。(21)王安忆:《天香》,第344页。
在“习行”视角下,重复、繁琐,近乎修行般的刺绣习行训练着女性的身体和心灵,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充分展示了令人钦佩的女性美德:勤奋、细心、忍耐和专注。在一遍又一遍拆解和联结的编织行为中,她们不断强化个人主体意志,每一次绣品的完成也是一次新的自我完成。在帕克看来,刺绣无疑是“加强特定的精神状态和促进自我体验”(22)Rozsika Parker, The subversive stitch: Embroide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p.11.的行为实践,它们帮助女性抵抗外界的干扰,养成缜静和稳定的心性品质,“静”与“定”也成为框定贤淑之女的行为准则。
在塑造申家第三代刺绣传人蕙兰时,作者对她的行为书写更上升至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奉献。蕙兰是婚后新寡,和婆婆、幼子相依为命,生活惨淡不景气。她通过给寺院绣佛像来接济家用,更别出心裁地以发代丝,令人耳目一新。王安忆此处引入“发绣”书写,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观照女性的行为实践,诉诸的是女性独特的个性表达。“发绣”在古代社会早有渊源,古人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23)胡平生、陈美兰译注:《礼记·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1页。的说法,故而通常以留长发、打发结、梳发辫、绾发髻的方式以示珍重。发绣佛像的出现,受到佛教中尽孝行,寻求人生慰藉,祈愿来生幸福的思想指引,断发人以奉献自己的身体来显示恭敬虔诚。小说中,蕙兰“辟发”的行为,既是她自证贞洁、不做他嫁的象征,也具有以发代丝、寄心于绣,祈求幸福之神守护的宗教意味,同时更是“充满才气的艺术创作、女性纯洁与真诚的标志和对自身涵养的修炼”(24)[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蕙兰做发绣的目的是以融入身体气血来寄托人生理想,极大地改变了申家“妇功”的劳作意义,代表了一种个人化和更高层次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深深刻印了她将身体、道德与理想等同起来的愿望。正如小说中写道:当发丝穿过针,“刹那间,蕙兰的心静下来,气息也匀了……那大罗汉的眉眼轮廓渐渐显出来,慈悲中带着俏皮,好像在与世人说:没什么打紧的!”(25)王安忆:《天香》,第370页。“没什么打紧”,正是蕙兰作为寡居织女希望在刺绣习行中寻求人生慰藉,以获得心灵平静的自我表达。
不应忽视的是,申家绣艺最先由闵女儿带入,虽然她绣工华美,但若没有小绸奠定文人绣的品格风貌,至多也不过是出色的闺房女红,也就不会有“天香园绣”。“天香园绣”是《天香》的叙事核心所在,天香绣之所以能够名扬四方,正在于其表征的是申家女性的自我创造与个性表达。至第二代传人沈希昭时,她开创性地以绣作诗书,使宋元诗画皆成绣品,终使“天香园绣”成为天下一绝,世人重金难求。技艺兼具学问的“天香园绣”倍受称赞、珍视与推崇,给申家带来无限荣光的同时也赋予了女性地位和尊严,其中缘由在于“天香园绣”已化身为专业领域内知识和学问的象征。作者对此有所暗示:“天香园绣与一般针黹有别,是因有诗书画作底。”(26)王安忆:《天香》,第392页。这一“精英化”的识物眼光展示了申家女性在知识学问和文化实践领域内的地位。另外,作者对刺绣落款与个人名号的书写也饶有意趣。沈希昭并不跟随其他人一样落款“天香园绣”,而自题“武陵绣史”,这一落款行为既是她独特的个性表达,也是一种自我选择。出嫁后的蕙兰同样另择“沧州仙史”作为自己的落款,其自我认证的用意不言自明。希昭和蕙兰分别作为天香绣的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希昭的诗画绣将针线女红提升至艺术商品的价值高度,蕙兰则创造出佛像绣,落款本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赋权”,独一无二的落款名号既是她们对自我创造力的认可和期许,也代表个人在这一领域内拥有的专门学问与技艺之长。她们在致力于让申家绣艺“开枝散叶”的同时,也以更加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建构了刺绣实践丰富的文化意义。尽管刺绣内容本身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这一活动却增添了新的含义——“表现个人创造力的一种自我选择方式”(27)[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83页。。
三、技艺、女性团体与社会关系
在小说中,申家的男女两性关系基本表现为“阴盛阳衰”“女强男弱”的模式,女子大都心气高、主意大,出品的天香绣更是享誉四方;男人们却大都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往往一事无成。王安忆这一“男性弱化”的笔法并不陌生,早在其诸多作品如《流逝》《长恨歌》、“三恋系列”中便显露可见。在《荒山之恋》中,王安忆谈及两性关系时表露出女性主义的观点:“女人实际上有超过男人的力量和智慧,可是因为没有她们的战场,她们便寄于她们的爱情。她愿意被他依赖,他的依赖给她一种愉快的骄傲的重负,有了这重负,她的爱情和人生才充实。”(28)王安忆:《荒山之恋》,《十月》1986年第4期。在类似这样的关系文本中,王安忆总是将女性置于一种大格局和高境界中,来给“男外女内”“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关系松绑。在《天香》中,这一女性观点得到了延续,而饶有意味的是,因《天香》的故事场景设定在晚明时期的上海,我们便需要借助历史与文本的“中介”——“刺绣”来深入叙事肌理,同时需要一种历史眼光的参照,来考察“刺绣”书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构塑女性主体性,我们从中又能获得怎样的文学想象。
申家家道中落后,男性渐次退场,女眷以刺绣来家养生计,共同的刺绣习行促使女性结盟,使同性团体的意义得到凸显。当闺阁女红嬗变为支持经济的技艺生产,女性的身份角色和主体地位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在传统社会,女子出阁即意味着分离,不仅因为从此与娘家相隔一方,即便嫁进夫家,与丈夫的相处时间也十分有限。相比男性早早进入学堂,并伴随着科举赶考、拜访求学、结交冶游等外出活动,女性的活动则常常被限制在家宅空间内,大部分时间与妯娌、姑嫂一起度过。在封闭有限的交往空间内,刺绣活动使家宅中的女子能够聚集在一起,通过彼此“握手论心,停针细语”(29)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 初集》(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072页。,甚至共同完成一件出色的绣品,为女性情谊的结交搭建了平台。《天香》的叙事围绕着女性情谊,王安忆也坦言,自己“确实是在写女子间的感情,并有意让她们结为闺密。”(30)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闺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同性团体的建构,意味着闺阁女子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开始获取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那么作为女性亲密友谊的联结物——“刺绣”是如何来凸显女性团体的意义的?又如何使女性与社会生计发生关系?这其中的幽微关联值得探究。
申家第一代女性团体主要由小绸、闵氏和镇海媳妇三人组成。三人先后嫁入申家,作为妯娌本就容易心生嫌隙,刺绣行为却将三人深刻联结。闵氏将绣艺传入,申府上下便兴起一股刺绣风,三人交流学习,日渐结为妇党,“天香园绣”的诞生便是她们结盟的见证。共同的刺绣习行凸显了女性团体的意义,在镇海媳妇去世后,小绸与闵氏日夜为其赶制入殓装裹,所绣花样是“当归”,寓意所盼之人能够回归。这足以证明,“刺绣和织物的图样传达着以其他方式无法表达的爱和团结的信息,维系着有血缘关系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妇女之间的纽带。”(31)[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第212页。织物表达了保留和给予的意义,其将死亡带来的失去转化为延续,这一延续便是“天香园绣”的代际留传和同性团体间亲密关系的构建。申家女性因刺绣而紧密团结,刺绣成为亲密“共同体”的象征与代言,对此,小说中的一处书写颇可深味:
原本,家中女眷是不必见客的,但申家的女眷不比别家,天香园里的桃林、墨厂、竹园,相继萧条,惟绣阁一枝独秀,远近闻名。今日的碧漪堂又是以绣为题,所以女眷堪称巾帼英雄,就在堂中专设一桌。申夫人告病,以小绸为首,领二夫人、桃姨娘、闵姨娘、阿奎媳妇、阿昉媳妇和阿潜媳妇,再加上蕙兰,花团锦簇的一席人,增添不少喜气,祥瑞得很……架顶上立一绢人,也是天香园绣阁中的手工。人物为八仙,第一桌是铁拐李,第二桌为汉钟离,第三桌张果老,第四桌正是小绸这一桌,就是何仙姑……每一仙的器物上都有一样绣件……宾客惊叹连连,哪里是针线女红,分明神仙点化。(32)王安忆:《天香》,第220页。
在古代,家中女眷自然是不会抛头露面的,“假如一位妻子在丈夫以她亲自准备的酒筵在她自己家里宴客的时候出现在满堂宾朋面前,此事便会成为众人的谈资。”(33)[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第73页。而在申家,我们却看到以绣结盟的女性团体不仅享有和男性同座的社会地位,她们的绣品还被作为了公共展示。这一刺绣展览并非作者的无心偶出,在小说第一卷中有一处细节,作者写柯海本想向闵氏多讨一件绣品赠予朋友阮郎,却遭到闵氏抵触:“本来是给你的,你却给了阮郎,阮郎是你的朋友,终还说得过去,他的朋友是谁呢?拿了我们家女人的东西,再去显摆,再引来朋友的朋友!”(34)王安忆:《天香》,第91页。女子绣物本就是内闱私物,其天然地标识“内部”属性,一般并不示人,更何况是在陌生男子面前作为“显摆”。而王安忆恰恰在此处“显摆”式的书写显然有悖于前,这一细节流露出作者的叙事意图。作者有意让天香园的绣品作为被外界赏玩的公共展品,从而消解“私人”物的限制而突出物的公共联结作用——一种跨越“内外”界限之别的意义。换言之,作者此处所展示的是作为公共成果的“天香园绣”而不再是私人性的内闱绣物,刺绣品的“公共”“外部”意义得到凸显,这为小说接下来的叙事走向做出铺设。与此同时,申家女性作为“天香园绣”的持有者从“闺阁”走向“厅堂”,象征着她们被整合进连结外部世界的社会关系网中,女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建构。作者这一叙事策略不禁让我们想到学者高彦颐在其著作《闺塾师》中做出的反思:难道封建社会的女性尽是“祥林嫂”吗?难道她们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吗?高彦颐考察的对象是中华帝国晚期江南社会的闺塾师,他颇有见地的指出了这一群体如何“超越了闺阁的空间限制,从而经营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35)[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第4页。这无疑与《天香》中女性的刺绣习行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女性凭借刺绣技艺,同样可以破除男性强加在其身上的空间界限而建构内闱高墙以外的社会关系。
如果说在第一代、第二代刺绣女性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刺绣对女性情谊的联结与同性团体建构的力量,那么在第三代女性蕙兰身上,我们则看到了另外一种象征力量——维护传统的社会道德秩序。小说中,刺绣在不同的女性团体间承载了不同的功能意义,在小绸、闵氏一代,申家仍然殷富,女子刺绣多是闲雅生活的体验,“手里的针线不是为了活计,倒是打发时间,就像是沙漏,一针一针,一个白昼过去了。”(36)王安忆:《天香》,第98页。而到了希昭、蕙兰一代,申家家道中落,昔日百闻难得一见的天香园绣终究用来家养生计。当闺阁绣品变为买卖商品,这意味着女性的身份角色也发生了转变,昔日的闺阁绣女如今如“妇工”一般赶制生产,她们名副其实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持者,这集中表现在女性人物蕙兰身上。相比申家其他女性,蕙兰的人生历程可谓十分曲折,但作者并未在她的生活困苦上多作停留,而是以此为背景,着意呈现蕙兰担当家庭生产者这一身份角色的意义。
清代流行的女性教科书《女学》的序言中记录了这样的观点:“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始。”(37)[清]蓝鼎元:《女学》,沈龙云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版,第19页。这一观点表明妇女的个人修养(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被纳入与国家秩序和家庭生活紧密同构的统一体中。美国学者曼素恩曾考察明清社会推崇“女工”(主要集中在家庭纺织业)的经世文章,总结了“妇女纺织”在帝国晚期社会的多重意义所指,如儒家正统的道德观,家庭经济的物质支持,为妻为母的象征,家庭的道德核心等。她举出孟母为例,认为其被官方认证的道德模范意义不仅在于她是教子成材的楷模,还同时担任着家庭物质支持的提供者。在小说中,蕙兰俨然是被塑造成如“孟母”一般的角色:作为寡居织女独自抚育幼儿,照顾老人,还需要发挥一技之长成为家庭稳定的物质支持者。蕙兰身上的坚韧、忍耐、忠贞等女性美德自不待言,但她作为家庭经济支持者的角色意义却常常被评论家所忽视。与蕙兰这一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社会对刺绣纺织的道德规范意义的强调,与曼素恩所说的“具体化于纺织生产里的道德活动”(38)[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第202页。如出一辙,这正构成了王安忆“刺绣”书写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王安忆始终抱持的女性主义观点的再次强化。
蕙兰的刺绣习行凝结了充满象征性的社会力量。出色的技艺保证她能够获取稳定的经济来源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履行照顾幼儿、赡养公婆的责任与义务。辟发绣佛的动机更召唤出一种“献身”精神,它显示寡居孀妇的贞洁,并以此确立被官方认可和推崇的特定女性人格。因而“贤德孀妇们的传记总是要提到她们从事纺纱织布的技艺何等出色”(39)[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第185页。,并总是将她们与埋首纺织的孟母形象联系起来,这暗示了刺绣纺织工作被奉为社会评判女性道德高低的标准。当一名女性开始学习刺绣时,她不仅是在锻炼一门技艺,同时也是在学习勤奋、整洁、忍耐这些美德,学习如何履行好为人妻和为人母的责任,而当她的技艺转化为生产价值时,她的道德意义也再次得到了强化。蕙兰的行为实践正显示了刺绣技艺如何作为一种生产之力使女性进入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序列中,但其中隐含的张力在于:传统女性虽然无法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准则,却能够通过行为实践开辟出给予她们意义、安慰与尊严的生存空间。对此,《天香》的结尾进一步有所显明。蕙兰受到社会道德的规训,恪守寡妇的职责与义务,不仅撑持起自己的小家,甚至还开门授徒,将刺绣技艺传授给戥子、乖女等更加不幸的弱势群体,让她们能够安身立命,自立天地。至此,“天香园绣”被赋予强烈的道德色彩,其最终命运指向了社会的生存大计。这也再次带给我们启发:如果不再一味强调封建女性“受压迫”的印象和范式,而是反思“对抗”“沉默”的女性书写模式,从日常生活领域重新考察女性生活及其社会地位,一种争执与通融的视景呼之欲出。以《天香》中的“刺绣”书写为例,女性利用这一有限而具体的资源,在日常行为实践中构设出自足自在、给予意义与安慰的生存空间,这一过程所显示的文化意义远非“内外”“尊卑”“上下”所能涵盖。从社会意义上讲,女性的刺绣技艺能够支持和运转经济,这不仅与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风气相通,也是女性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体现;从日常行为实践来看,女性在刺绣习行中自我表达、自我创造乃至自立天地,这正是她们获取主体性的重要时刻,我们不应忽视。显然,王安忆赋予“刺绣”超越日常经验的文化意义,也让我们对业已熟知的受压迫的传统女性形象保持了一定距离的思考。
四、结 语
不同于王安忆的其他作品,《天香》的故事发生在晚明上海,在遥望这段“前史”时,我们需要激活作家创作、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因此也就需要寻找并借助叙事的“中介”来深入作品脉络。本文选择“刺绣”视角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刺绣”作为《天香》的核心叙事线索,具有统摄、提领的功能意义。与此同时,“刺绣”书写与小说女性人物的塑造紧密相关,尤其在观视女性情感转换、营造女性生存空间、构塑女性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与文化想象,并进一步指向了女性主体之思的议题。通过引入“日常习行”这一概念,更有助于探讨女性的行为实践与主体性建构间的意义关系,为作品的解读增添了别致面向。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刺绣亦是关于“物”的文化实践活动。《天香》中蔚为大观的物质文化书写显示出作家追求“以物观人”“物我同一”的理想境界。小说中的绣物描写不断表露作者的“物”观,即以物情通融人情、以物性修补人性的理念。在“物”的观照下,刺绣与女性的关系显出别样旨趣。王安忆多次强调申家女性的“锦心绣手”,一方面是指她们努力雕琢技艺,提升艺术水准;另一方面则意在凸显女性的格局与境界,她们用心揣摩和体察物理、物途,与物同心同德,遵循物德并保持敬畏,当天香园被夷为平地后,“天香园绣”却悠远流传,最终升华了小说的题旨——物质不灭,生机不息。“锦心”与“绣手”相互补益,这生机最终触着了“浩浩荡荡的大天地”(40)张新颖:《一物之通,生机处处——王安忆〈天香〉的几个层次》,《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天香》的大格局自然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