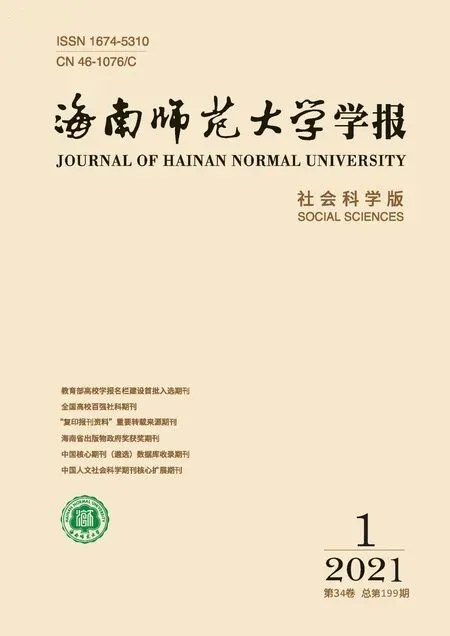《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与中国文化及“国民性”
——兼论“吃人”是否中国风俗
[澳]张钊贻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历史与哲学探索学院,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市 4072;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24)
一、“吃人”的两种看法
对《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就笔者所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礼教吃人”;另一种是中国社会或中国人“吃人”。小说将“仁义道德”与“吃人”相联系,是这样叙述的:“……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严格来说,最早对小说做出“礼教吃人”评论的是吴虞(1872—1972):“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3)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出版),第580页。当然,鲁迅后来在1935年也评论此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所以,“仁义道德”也可以等同于“礼教”。但“仁义道德”如何“吃人”?“仁义道德”“吃人”是什么意思?这两个问题应该是理解《狂人日记》的关键。不过,小说中也用了很多“吃人”的事实来说明问题,那么“吃人”就不仅是“仁义道德”的后果,同时也是直接的“人”的行为。但人吃人的事实显然跟“仁义道德”的“吃人”并非同一回事。按照“仁义道德”“吃人”的思路,小说中的“吃人”应该是一种象征意义。在《灯下漫笔》中,“吃人”的象征意义比较简单,就是“凌虐”“摧残”。(5)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20世纪50年代,孙伏园(1894—1966)就认为《狂人日记》“是象征性的或譬喻性的作品”;对“吃人”的问题,孙伏园认为,“‘人’的发现,在世界上也是近代史开端(结束封建统治)的事…… ‘人’既然发现了,自然第一步是不该‘吃’了,第二步是不该‘残杀’了,第三步是不该‘奴役’了……”(6)孙伏园:《五四运动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第19页。。王乾坤不同意“吃人”是实指人吃人的事实,认为“吃人”是象征性的,他进一步提出鲁迅的“立论”主要建立在“现代个性自由与发展”的意义上;“鲁迅用个性自由界定‘人’”,所以得出中国社会、文化“吃人”的结论。(7)王乾坤:《关于“吃人”》,《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第4-9页。按:王乾坤先生后来向笔者说明(2019年5月11日电子邮件),他“并非不同意实指,旨在强调容易被忽视的层面”。简而言之,“礼教吃人”就是指“仁义道德”窒息和摧残个性,礼教压制个人自由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要求。
《狂人日记》引述人吃人的事实,有的来自中国典籍的记载,也有的是社会实事的报道。吴虞则补充了些中国史实,也略加解释(8)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出版),第578-580页。;新近,李冬木更详尽挖掘了鲁迅留学日本时“周边”的吃人“言说”。(9)李冬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原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附录于李冬木、房雪霏译注[日]芳賀矢一:《国民性十论》,香港:三联书店,2018年,第214-257页。这些事实跟“仁义道德”有什么关系,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很清楚。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人们可以对《狂人日记》产生第二种看法,即小说似乎也可以解读为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或中国社会有“吃人”的习俗,或中国人是“吃人”的民族。(10)另,据王乾坤引述,有人认为“《狂人日记》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两个字”。参见王乾坤:《关于“吃人”》,《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第4页。事实上,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就说过:“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11)鲁迅:《180820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5页;另据[日]藤井省三考证《狂人日记》发表前的五月,北京《晨钟报》(即《晨报》前身)登载一连串北京吃人的社会新闻,多为割肉疗亲,也可能令到鲁迅产生这个结论。参见[日]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东京:三省堂,2002年,第61-62页。,因而写成《狂人日记》。钱理群就很注意鲁迅这几句话。虽然钱理群并非不同意王乾坤等的看法,并且反复说明跟后者观点一致的鲁迅“立人”思想立场,但按照鲁迅在信中给许寿裳的话,以及鲁迅与许寿裳热衷于讨论“国民性”问题的事实,钱理群从 “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切入探讨《狂人日记》“吃人”问题,再联系新近的历史和现实,则“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论断,就能带给“改造国民性”和“吃人”更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钱理群强调鲁迅所说的“吃人”,“或者说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不仅是象征,而且是实指:中国人真的是在‘吃人’。”(12)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157-178页。
王乾坤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认为《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是象征,并不是实指;钱理群则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看,认为“吃人”是“实指”。表面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互相矛盾,但他们都认为鲁迅思想是以现代的“立人”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所以,虽然他们对“吃人”的看法不同,但实际上只是侧重不同,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他们对鲁迅思想现实意义理解的差异。这是笔者的理解。然而,由于双方并非在一起讨论问题,所以并无观点的交流。也许正因为如此,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吃人”与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看“吃人”,这两种观点给人的感觉似乎可以互不相干,而且延伸下去甚至可以越离越远。事实自然并非如此。两者其实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历史文化的问题实在庞大,联系到“国民性”就更加复杂,还可以有进一步解读的空间;另一方面,“国民性”主要是历史文化在精神心理层面沉积所成,也离不开对中国历史文化问题的探讨。换言之,如果笔者对两位论述的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上述对《狂人日记》“吃人”的两种理解,在“立人”的基础上其实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本文即试图按笔者所理解的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看法,将“吃人”的两种理解连接起来,希望能提供一个兼顾这两面的解读。但在连接两种看法之前,我们需要分析一下《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事例在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究竟是什么意义。笔者认为,这些事例有必要对照外国,例如欧洲国家和日本“吃人”事例,方能对现实中国“吃人”事例作出合理中肯的解释。
二、四种情况下的“吃人”与中外对比
《狂人日记》所述的出现在中国的“吃人”事例,大概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战乱时期发生的“吃人”事件。例如春秋时期楚国围困宋国都城,造成“易子而食”的惨况。吴虞补充的例证是唐朝张巡(709—757)守睢阳被围粮尽吃人。《曾国藩日记》载“洪杨之乱”中江苏卖人肉等事,均属此类。第二类是报仇雪恨的“吃人”事件。徐锡麟(1873—1907)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845—1907),后被捕就义,遭恩铭卫队挖心炒食,属于此类。(13)按:吴虞还补充了《汉书·鲸布列传》中所记刘邦杀彭越,剁成肉酱,分赠诸侯。此事勉强也可归入此类,但此例或只为杀鸡儆猴。不过,刘邦和诸侯好像并没有吃,只是作态。参见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出版),第579页。成语“食肉寢皮”也属此类。第三类是认为“吃人”有医药疗效的迷信,与第二类略有重叠。被归入金代“二十四孝”版本的“割股疗亲”典故也属于此类,与第四类也有重叠(14)1979年,山西移山马村4号墓出土二十四孝陶塑是金代流行的“二十四孝”的版本,与后来元代的“二十四孝”定本不尽相同。参见百度百科“金二十四孝故事陶塑”(https://baike.baidu.com/item/金二十四孝故事陶塑),金代是鼓励“割股疗亲”的。参见《四库全书·史部》所收《大金国志》卷35《割股孝梯仪》:“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妹、舅姑割股者(奴婢为家长同),并委所属申覆朝廷,官支绢五匹,羊两腔,酒一瓶,以劝孝梯。”(按:标点为笔者所加。)参见http://c.sou-yun.com/eBooks/四庫/欽定重訂大金國志%20宋%20宇文懋昭/卷二十五%7e卷四十一.pdf.(按:本文所引网上材料,均于2019年3月取阅或下载)。。第四类是忠孝吃人。鲁迅还举了易牙为讨好齐桓公(?—643)而蒸了自己的儿子给他吃的例子,此事一般等同于“割股侍君”的忠君行为,姑且先从俗归入此类。
《狂人日记》中的这些“吃人”事例其实都不是社会常态,若以这些事例来说明中国文化是“吃人”文化,中国社会是“吃人”社会,只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显然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就以第一类战乱、围城时出现的吃人悲剧事件为例,古今中外都有。公元前70年,罗马兵团围困耶路撒冷期间就发生过类似事件。据罗马犹太人史学家约瑟佛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37—100)在《犹太战争》(TheJewishWar)所记,有一个“来自伯利苏巴村的玛丽(Mary of Bethezuba)”由于围城饥荒而吃掉自己女儿。(15)Josephus in Nine Volumes, tr. H. St. J. Thackera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66, Vol. 3: “The Jewish War, Books IV-VII”, pp. 435、437.此类事件在古代显然并非个别孤立事件。(16)据Bill Schutt研究,欧洲在793—1317年间就发生过11起饥荒引起的人吃人事件。参见Cannibalism: A Perfectly Natural History, Chapel Hill: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2017, p. 294.《圣经》就记载了撒马利亚(Samaria)被围时发生过“易子而食”,又记录了上帝恐吓、诅咒过那些不信他的人会遭围困饥荒而食自己的女儿。(17)“The Old Testament,” “Deuteronomy”, 28; “The Second Book of Kings”, 6, The Revised English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pp. 173、318. 中译本参见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出版的《圣经》2003年版,《旧约》,第247、453页。中世纪,那不勒斯被围时,一些商人曾整桶整桶地卖人肉。(18)Francis Bacon,Sylva Sylvarum, or, A Natural History, Ten Centuries,London: William Lee ,1670, “Natural History, Century I”, p. 6.直到现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饥荒吃人的事,更是到处都有发生。苏联列宁格勒被围两年多,就有不少吃人记录。(19)Anna Reid, Leningrad: The Epic Siege of World War II, 1941—1944,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pp. 287-292.第二类也与战争有关,即发生在敌对群体之间或军队之中。1098年,十字军攻陷叙利亚的马阿拉城(Ma’arra),那些基督教士兵就吃了当地的穆斯林。(20)Sarah Everts, “Europe’s Hypocritical History of Cannibalism”, Smithsonian.co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4 Apr, 2013,http:∥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europes-hypocritical-history-of-cannibalism-42642371/.法国宗教战争期间(1562—1598),一名新教徒遭天主教徒杀害后,五脏被掏空,“心脏剁碎,拍卖,烤熟,最后被大块朵颐”。(21)Richard Sugg, “Eating Your Enemy”, History Today, Vol. 58, Issue 7 (July 2008),https:∥www.historytoday.com/archive/eating-your-enemy.现代史中较有名的是“父岛(Chichi Jima)事件”或“小笠原群岛(Ogasawara)事件”。1944年9月,美国一架轰炸机在父岛被击落,9名飞行员中除了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老布什(George H. W. Bush, 1924—2018)外,全部被抓,其中四人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22)Jeanie M. Welch, “Without a Hangman, Without a Rope: Navy War Crimes Trials After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val History, Vol. 1 No. 1 ,April 2002: http:∥http:∥www.pegc.us/archive/Articles/welch_naval_MCs.pdf; Charles Laurence,“George HW Bush narrowly escaped comrades’ fate of being killed and eaten by Japanese captors”, The Telegraph (26 October 2003):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2/06/george-hw-bushs-comrades-eaten-japanese-pow-guards/.对于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吃人罪行,田中利幸(TANAKA Toshiuki, 1949—)有详尽的记录。(23)Yuki Tanaka,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6), pp. 111-134. 按:田中利幸的英文著述署名“Yuki Tanaka”。又,抗战期间日军吃人事件,有一例见于2000年松井稔监制的纪录片《日本鬼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LVQdVyGMk.)。松井稔采访了14名“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前日本军人,其中榎本正代讲述他强奸了一个中国少女后,把她切成一块块煮给他手下的士兵吃。
至于“吃人”的药用(吃食敌人本身也附带有药用的迷信),在前现代的欧洲各阶层其实也颇盛行。(24)Richard Sugg,Mummies, Cannibals and Vampir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2nd edition), pp 14-58; Bill Schutt, Cannibalism: A Perfectly Natural History, pp. 207-242.不过先要指出,西方所谓cannibalism,狭义指人吃人,但也泛指吃食同类的行为。就人吃人而言,吃食对象包括人身任何部分,如胎盘、人血、尸体等等,并不一定是杀害别人而食之的行为。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关注“木乃伊有强力的止血功能”(25)Francis Bacon,Sylva Sylvarum, p. 210. 按:对木乃伊的药用的迷信(后来延伸到死尸),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Bill Schutt, Cannibalism: A Perfectly Natural History, pp. 207-218)。。欧洲富贵人家吃人尸骨和血液成药,也都被归入吃人及认可吃人的一类。在17世纪,丹麦和一些德语地区处决犯人时,人们就围着争一杯血,因为他们认为死于暴力的人的新鲜血液对治疗癫痫很有效。(26)Mabel Peacock,“Executed Criminals and Folk Medicine”, Folklore 7,1896, p.274. Philip Bethge, “Europe’s History of Cannibalism” (30 Jan,2009), tr. Christopher Sultan, Spiegel Online: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zeitgeist/europe-s-medicinal-cannibalism-the-healing-power-of-death-a-604548.html.这跟鲁迅小说《药》(1919年)里的“人血馒头”没有什么区别。(27)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3-272页。欧洲这些吃人治病的做法,到20世纪初仍未绝迹。
笔者不厌其烦引述“外国也有的”例子,并非要说明中国人和其他人都一样,所以中国人吃人也没问题。人吃人自然有问题。但不通过对比,我们就不能排除那些纯粹出于政治敌对和种族歧视的评论,就不能对吃人在中国算不算“风俗”有更清楚的认识,就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吃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吃人”乃中国“风俗”?
中国是否有“吃人”的风俗,用战乱之类非常态事件来做例证,自然很成问题。维基百科英文版“吃人在中国”(cannibalism in China)词条引起尖锐的争论,原因之一就在于此。(28)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nnibalism_in_Chin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lk:Cannibalism_in_China##.此词条的客观中立性受到质疑,还因为采用了一位曾被派到中国留学两年(1907—1909)的著名东洋史日本学者桑原隲藏(KUWABARA Jitsuzō,1871—1931)1919年关于中国吃人的文章,考虑到晚清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质疑就并非无故。但桑原隲藏到底是位学者,他的观点也需要认真对待。桑原隲藏将中国吃人的情况分成五类,除上述对《狂人日记》归纳出的四类,还加了“风俗”一类。(29)[日]桑原隲藏:《支那人の食人肉風習》,《太阳》第25卷第7号(1919年8月6日)。参见 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372/files/4270_14876.html.词条另外还采用了一位美籍韩裔学者郑麒来(Key Ray Chong,1933—)的著作。郑麒来将吃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求生性吃人” (survival cannibalism),另一类是“习得性吃人”(learned cannibalism)。尽管郑麒来认为在“求生性吃人”方面,中国与其他文明没有什么区别,但在“习得性吃人”方面却与众不同,尤其是在上流社会烹饪美味方面。郑麒来还认为吃人也是儒家教条的延伸。(30)Key Ray Chong,Cannibalism in China,Wakefield: Hollowbrook Publishing , 1990, pp. viii、pp.170;郑麒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黄燕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这样一来,吃人似乎不仅是中国人的“风俗”,而且还有文化基础。当然,若只看“割股疗亲”之类“尽孝”的吃人,郑麒来列出了相对于比其他类别高的比例数据,那么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据,但这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本文稍后再论。
在中国古代吃人事例中,药用吃人已被证明是世界“风俗”,并非中国特有。若不包括药用吃人,又暂时搁置“尽孝”的吃人,再排除“求生性吃人”,以及“习得性吃人”中的因“仇恨”“惩罚”和大部分发生在战争时期因“忠诚”而引发的“吃人”等非常态例子,剩下的“吃人”是否称得上中国特有的“风俗”,恐怕就很成问题。这里先举一例。郑麒来参考过唐朝张鹫的《朝野佥载》,引述书中唐太宗(598—649)赐任瓌(?—629)两个侍妾一事,但不知何故,竟然忽略了《朝野佥载·补辑》中诸葛昂和高瓒为炫富烹小儿及爱妾宴客的恐怖记载。(31)[唐]刘餗、[唐]张莺:《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程毅中、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5页。表面上,此事可支持郑麒来所谓中国“吃人”的特色之一,即上流社会烹饪美食。然而,我们更不应忽略这个可怕事件中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细节,那就是客人的反应:“坐客皆攫喉而吐之”“皆掩目”。他们的反应只能说明,吃人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可怕的。反过来说,诸葛昂和高瓒是不正常的、变态的。以变态人物和事件来说明“风俗”,恐怕就很难成立。
随着国内外石油、煤炭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得国内整体能源的价格也在提高,能源和动力采购方面的费用增加,西部矿业企业地理位置偏僻矿山因更多的能源消耗支付更多的费用。
一种历史悠久的“道德文化”自然非常丰富复杂,但“风俗”归根到底是道德价值观念的反映,而要观察一种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念,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两方面,即从“高等文化”(high culture)和“普及文化”(popular culture)着手,才能对一种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两方面郑麒来都注意到了。先说“普及文化”方面,郑麒来引用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两部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吃人故事。因此,小说中“人吃人”的事情在中国广为人知,这是肯定的。但郑麒来没有指出很重要的一点:那些吃人的要么是强盗,要么是妖怪。既然吃人的都是些坏人,或者不是人,那么他们也就不见容于社会,不见容于一般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如此一来,人吃人在中国“普及文化”层面上,就不可能是一种大多数人都接受的事情,也就不可能是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履行的“风俗”。事实上,“普及文化”有吃人故事并不限于中国。且不说佛教的吃人恶鬼和希腊神话中的拉弥亚(Lamia),欧洲一些著名童话中也有吃人故事,吃人者自然也是些坏人或妖怪(32)参见Matt D. B. Harper,“Dark Lessons: Cannibalism in Classic Fairy Tales”, https:∥owlcation.com/humanities/Cannibalism-in-Fairy-Tales, updated on February 27, 2018.,他们大抵是管教儿童的工具,或是一种道德教育的“反面教员”,并非要教人以平常心对待吃人,更不是鼓励吃人。至于中国“高等文化”方面,郑麒来其实已经引用了《孟子》“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33)《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4页;Key Ray Chong, Cannibalism in China, p. 46.孟子“不忍人之心”的“仁”(34)《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690-2691页。,自然与“人相食”是相反的。可见中国传统的、主流的、“官方”的道德准则,也并不容许吃人的“风俗”。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郑麒来认为,跟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中国的吃人与宗教没有多大关系(35)Key Ray Chong,Cannibalism in China, p. 171.,但巴雷特(T. H. Barrett)在书评中质疑了这个观点。巴雷特指出隋、唐时代有吃年轻人内脏可升仙的迷信,到清代仍令政府头疼。(36)T.H.Barrett,Book Reviews——Cannibalism in China by Key Ray Chong / The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by Philip A. Kuhn,The China Quarterly,1991,No.128,pp.836-837.这种想吃人升仙的行为,看起来很像是“邪教”活动,如果是属于社会异类的“邪教”活动,能否纳入一般大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也是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撇开不管。查《大清律例》有“采生析割人”的刑律,对“取生人耳目脏腑”“析割其肢体”,包括“己杀及己伤”,都要被“凌迟处死”。(37)《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28-429页。所以,为升仙而吃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也说明社会不能接受这种行为,要通过法律遏制它们的普及和传播,遏制它们成为“风俗”。相对有趣的是,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时,指责他们“吃人”,因为《圣经》叫人吃“人之子”的肉和喝他的血。上帝的要求现已成为一种叫“圣餐礼”(Eucharist)的仪式,血肉以面包和红酒代替,每星期天公开举行。(38)参考“The New Testament”, “John”, 6: 53,The Revised English Bible, p. 86. 中译第122页; Bill Schutt, Cannibalism,pp. 123-132; Kenneth S.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Ltd,1964, p. 82. 神学上的解释主要认为那是“寓言性”“象征性”语言,血肉是“属灵的粮食”。参见得维逊(F. Davidson)等编:《圣经新释》(合订本)卷3,李玉珍等合译,香港:证道出版社,1976年,第142-143页。
从这些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不可能完美无缺,一个社会总有异类。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内部总有对立的势力在较量,有种种原因导致吃人事件的发生,但同时也有制止吃人的法律和道德。如果药用吃人算是风俗,那么西方能逐步摆脱这种风俗,大概要归功于启蒙时代科学的发展。(39)Bess Lovejoy,“A Brief History of Medical Cannibalism” (7 Nov 2016),“Roundtable”, Lapham’s Quartery,https:∥www.laphamsquarterly.org/roundtable/brief-history-medical-cannibalism.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社会文化是向着科学和人道不断改进的,但中国似乎不是,至少鲁迅认为是这样。所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宣讲他所理解的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的进化论,呼吁中国人要进化成“真的人”,不再吃人。(40)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52页。但如果鲁迅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并非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像“五四”普遍认为的那样,那么他是怎么看中国社会文化没能像西方那样“进化”、不再吃人这个问题的呢?
四、“吃人”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堕落
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点与“吃人”有关。(41)参见[澳]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3-230、235-248页;[澳]张钊贻:《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第42-98页。第一,文化传统是有历史发展的,会变化的。第二,文化的根本是人的精神,鲁迅称之为“内曜”(42)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7-28、29页;《摩罗诗力说》中有“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隐曜”显然是“内曜”的另一说法。按:鲁迅所论“心声”“内曜”与《毛诗序》所谓“情动于中”“手舞足蹈”(《毛诗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0页),并无不同。,是人的活力的根源,也是文化发展的能源,也表现为一种精神力量,即“诚”,或“认真”,是鲁迅所关注的中国“国民性”中比较核心的问题。第三,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遭遇过反复的破坏,尤其是多次遭到外族入侵,作为文化传统守护者的知识分子,其中的“认真”者遭到不断的杀戮,已无力担起文化更新改进的任务,另一方面,其中的巧猾的“聪明人”将文化传统变成获取私利的“敲门砖”,为异族入侵者提供“人肉的筵宴”(43)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2-229页。, 而这一切又恶性循环变成以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和培育“国民性”的材料。换言之,中国文化的变化不但不是向科学与人道改进得更好,反而是连同“国民性”一起,日益遭到毒害而堕落。
就以“礼教”为例。儒家以礼治国,礼是一种制度。最能体现这种制度的,莫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4)《论语·颜渊第十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3-2504页。对照鲁迅引《左传》,参见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7-228页。此语历来为人诟病,认为是维持一种僵化的等级制度。(45)例如陈瑛等:《中国伦理思想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然而孔子补充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6)《论语·八佾第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8页。《礼记》亦有所谓“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47)《礼记·礼运第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22页。这表明“君君,臣臣”等等各有本份,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负责的关系。但到了后来,这种关系却变成“尊”与“贵”对“卑”与“幼”的绝对权威和压迫。(48)这是王乾坤对[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解读,见其《关于“吃人”》,《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第6页。这是对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和破坏。以“孝”为例,后来人们只讲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其实并非《孝经》的教导。“孝”是为了维护“礼”,父母若有“不义”,子女“从父之令”反而不孝。君臣关系也一样。“尊”与“贵”道理上并无绝对权威。(49)《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58页。因此,礼教并非完美,也不见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如果说礼教限制个人的发展,那是所有制度本身的功能,它当初并未造成后来“家族制度”的“弊害”,还不至于完全窒息个性,也就是并不至于“吃人”。
郑麒来从“忠”“孝”入手,发现很多“割股疗亲”“割股侍君”的吃人案例,他也注意到元朝禁“割股疗亲”(50)Key Ray Chong,Cannibalism in China, p. 99;郑麒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黄燕生译,第103-104页。查《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礼部卷之六典章三十三,在《行孝》一节下,有“禁割肝剜眼”、“行孝割股不赏”、“禁卧水行孝”。郑麒来称元朝政府仍继续奖赏这些行为,所以虽禁而仍然有增无已。但郑麒来所据 “Shih lin kuang chi jen chi (chüan 1)”(中译作《事林广志》),未知何书,或为宋末元初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内有《人纪》(jen chi),但那是在“卷之七”并非“卷一”(chüan 1)。经检索,《人纪》并无割股行孝内容(该章全文见维基文库,https://zh.wikisource.org/wiki/事林廣記/前集/卷07)。又,注释的出处作“《元典章》卷三十三行孝部”,与上面禁令出处相同。但既然禁止这种“行孝”,怎么又会奖赏?查《元典章》“禁割肝剜眼”一条,是对申报这一孝行的回复。申报中引述“旧例”要求奖赏,赏赐物品与前引《大金国志》卷35《割股孝梯仪》基本相同,只多了一瓶酒,但无“土地一顷”(“land (one ching)”)。《大金国志》卷35并无只字提及“割肝剜眼”。,但没提禁止理由。其实禁止的理由很值得大家思考。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行孝割股不赏”一条下指出(按:标点为笔者所加):“割股旌赏体例,虽为行孝之一端,止是近代条例,颇与圣人垂戒‘不敢毁伤父母遗体’不同,又恐愚民不知侍养常道,因缘奸弊,以致毁伤肢体,或致性命,又贻父母之忧……今后遇有割股之人,虽不在禁限,亦不须旌赏。”(51)参见“搜韵”网站之“影印古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第12册,http:∥archive.org/stream/02087989.cn#page/n64/mode/2up.所谓“圣人垂戒‘不敢毁伤父母遗体’”(按:“遗体”此处不是“留下的身体”即尸体的意思,是指“诞下的身体”)应是指《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52)《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45页。换言之,“割股疗亲”只是接近元代的“近代”才出现,尽管有政府旌赏鼓励,有人体药用的迷信,并非真正传统的孝道,甚至是后来违背“高等文化”所设定的道德规范的行为,但却大行其道。(53)清代有孝子还向外国人显示伤疤炫耀。参见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larged and Revised Edition),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0, p.178.
鲁迅在抨击《二十四孝图》时,是看到孝道这种变化的。鲁迅对“子路负米”“黄香扇枕”等例子虽然语带调侃,但他显然认为这些孝行可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出自真情者均可勉力而为,因此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对另外几个故事则不一样。鲁迅狠狠批判了“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这类违背科学和现实生活常识的教育。《二十四孝图》标榜了“孝”与“诚”,所谓“孝感动天”,但哭竹是生不出笋的,卧冰只会冻死也得不到鲤,其教育效果也只能是诈伪和瞒骗。鲁迅又揭露了“老莱娱亲”原本被“后之君子”改到不近人情,及至“郭巨埋儿”,已违反人性和常理,实际是教人不要做孝子。鲁迅慨叹说:“后之君子”“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54)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然而,“郭巨埋儿”这个连《孝经》“教民亲爱,莫善于孝”的原则都违背的故事,却成了“孝子教科书”的内容,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55)参见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第258-264;鲁迅:《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3-341页;《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56页;参见[澳]张钊贻:《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第66-70页。
对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引用的易牙蒸子讨好齐桓公一事(56)参见《二柄 第七》《难一 第三十六》,[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页;[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下册,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第800页。,吴虞只抨击齐桓公严守礼教却又吃人,表里不一,并未点明这件吃人事件的要害。“易牙蒸子”与介之推(?—前636)割股奉君及类似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晋公子重耳(前697年—前628年)落难无粮,介之推割股食之是舍己救主,是患难时期忠心的表现。(57)[汉]韩婴:《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遟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8页。此事不见于《左传》《史记》。而易牙蒸子则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为了讨齐桓公的欢心,目的只是谋权力,是最极端的一种“马屁精”,属于鲁迅所谓的“聪明人”,是歪曲利用文化传统来谋私利的人物。易牙这样做实际上是陷齐桓公于不义,也是在破坏礼教。管仲评论说,“夫人情莫不爱其子,今弗爱其子,安能爱君?”(58)[战国]韩非:《第十五卷·难一第三十六》,《韩非子》,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138页。其实点出了鲁迅所谓“后之君子”的“以不情为伦纪”“教坏了后人”的后来发展。吴虞忿忿于“他们这类人,在历史上,在社会上,都占了好位置,都得了好名誉”(59)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出版),第579页。,也正好说明了鲁迅对当时中国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遭到长期破坏,只知谋私的“聪明人”占了主流,“国民性”被这样的文化培育下不断扭曲……中国事实的吃人事件和象征性的“吃人”状况,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和延续的。
五、结束语:“吃人”与“不再吃人”的较量
中国有吃人的事实,传统文化后来也能在象征意义上“吃人”。然而,文化内部是有各种倾向在较量的;传统是可以变革更新,与时俱进的。《大学》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60)《礼记·大学第四十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3页。,“维新”一词就出自《诗经》和《书经》。(61)参见《尚书·胤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8页;《诗经·大雅·文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503页。《中庸》还批评“愚而好自用,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62)《礼记·中庸第三十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4页。这些话完全有助于推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改革。然而,当道的总是“聪明人”。反复的战乱,使有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即使逃过“聪明人”的暗害,也只能在“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中疲于奔命(63)鲁迅:《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7页。,而“修补老例”的文化只能自然停滞(64)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自然无法纠正弊病,更新发展,与时俱进。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很难获得民众的支持和信赖。(65)作为文化守护者的知识分子,即使并非“聪明人”,还常常陷入自我毁灭的境地。例如,前引元朝有“行孝割股不赏”和“禁卧水行孝”等法令,帮助制定这些法令的人物,应该是很懂中国文化传统,也是很有识见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可能是汉人。但不论这些禁令有多合理,经受过入侵者制造“人相食”灾难的民众,大概只会鄙视这些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虚伪和他们为虎作伥,更不可能相信他们能够保卫和发展中华文化传统。这种知识分子自然也无法承担文化守护者的职责。如此艰辛,是否真的说明中国文化有问题?例如,为什么不能防止连年战乱?让那些坏人和变态狂魔无法无天?也许真有问题,但战乱也会平息,什么原因?好像也很难单从文化上确定。又如,为什么齐桓公会让易牙让他吃人?也许文化真有问题,因为易牙拍马成功了;但也不能确定,因为到底有管仲一针见血的评论留给后人。但后来的“马屁精”和“聪明人”越来越多;但正直认真的人并未绝迹…… 所以,即使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已经堕落,即使中国吃人事件比其他地方多(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姑且先从坏处想)(66)中国历史上吃人事件收集最详尽的,应是黄粹涵辑的《中国食人史料钞》(无出版社,《序》作于2004年);世界范围内的吃人事件,有维基百科的“List of incidents of cannibalism”(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ncidents_of_cannibalism.,但肯定并非全部,对照本文所引Richard Sugg等的著作可知。,我们至少还可以说,也只能这样说:中国“吃人”和“不再吃人”的力量还在较量。与文化关系紧密的“国民性”是否有“吃人”倾向,自然也受“吃”与“不再吃”两种倾向和力量较量背后的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也受教育、媒体、道德、法律等的影响和塑造。
中国文化传统或礼教本来不是“吃人”的,是可以改造革新,变成为“真的人”服务的,并不一定是“不再吃人”的障碍。鲁迅的“不再吃人”的“立人”主张,表面上更接近现代西方,但很多人认为是西方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却是中国本来就有的,所以他说“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67)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他在《文化偏至论》主张个性解放的文化改革中,就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68)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 页;对照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1页。,其中自然有选择和批判。儒家的“仁”和“民为贵”的思想,尽管与现代西方的人道精神和民主理念非常不同,但不是不可以改造、借鉴。即使原来没有,在鲁迅看来,只要是有益的,也可以像汉、唐时代的人那样自信地把有益的东西“拿来”(69)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211页。,而创造出与现代接轨的“真的人”的价值理念,塑造出“不失固有血脉”而又具有符合现代要求的“国民性”的新人。而这种“拿来”的精神,是中国“固有之血脉”。
文化传统与“国民性”是复杂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从前“吃人”,并不等于以后还会继续吃。可能因为改变过程漫长反复,而且手段只有手中的笔,所以,鲁迅对改造“国民性”很悲观,只能用小说呼吁“救救孩子……”(70)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55页。,寄望于缥缈的未来。但到了现在,中国除了普及否定吃人的科学知识,也增强了反对吃人的道德和法律力量,只要不出现战乱,吃人大概只是个别变态病人的罪行。至于要克服象征意义上的“吃人”,自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原因更复杂,困难也不限于中国,但已超逾本文讨论范围,从略。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若要使吃人事件和象征意义上的“吃人”不再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那么在社会制度经过现代化改造后,中国文化传统还需要继续批判继承,剔除糟粕,吸收精华(71)原文为:“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68页。,而中国“国民性”还应该继续“改造”。笔者认为,这是《狂人日记》为现实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72)补记:两个吃人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吃人与不再吃人的较量其实并没有终结,不再吃人也不可能彻底完全胜利。比尔·舒特(Bill Schutt)指出,吃食同类在自然界并非罕见,而人类不时出现返祖现象,所以在平和时期也不时会发生吃人事件(Bill Schutt, Cannibalism, pp.287-288. Schutt大概按照郑麒来的书,认为中国对吃人没有禁忌,并非事实,已见本文分析)。而且,有两个案例表明,依靠法律制裁和社会道德也不一定有效。第一件:2001年,德国北部郊区一个孤独的电脑技术员阿明·迈韦斯(Armin Meiwes,1961—),在网上登广告征求壮健的人,自愿跟他性交后让他杀死吃掉。居然有人应征。事发后,迈韦斯却难于定罪,因为应征者自愿,不能控谋杀,而德国当时也没有吃人罪。检控方最后只能以协助自杀而判他八年。结果引起公愤。重审后才改控为满足性欲而杀人,判无期徒刑。(参见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min_Meiwes.)。第二件:1981年,佐川一政(SAGAWA Issei,1949—)在巴黎杀掉他的女同学后吃了她。法国法官认为他是疯子,驱逐出境了事。佐川回到日本后,只是被送到精神病院,但病院判定他完全正常,把他放了出来。由于法国方面已取消控罪,并将档案封存,日本方面没有积极跟进,社会舆论也没有出现公愤,佐川因此便成为无罪之人。此后佐川还将此事写成书,并多次接受传媒采访,摄制了数部纪录片,甚至应邀上电视烹饪节目,到大学研讨会发言讲话,参演虐杀狂的成人电影,成了日本和欧美的红人。(参见“Issei Sagawa” i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sei_Sagawa; Stephen Morris, “Issei Sagawa: Celebrity Cannibal” (2007-09-20), in New Criminologist: The Online Journal of Criminology,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4172725/http:∥www.newcriminologist.com/article.asp?nid=17;Barak Kushner, “Cannibalizing Japanese media: The case of Issei Sagawa,”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Oxford Vol. 31, Issue 3, (Winter 1997), pp. 55-68.按:若联系到文化问题,这篇文章不妨一读:Leslie Helm, “Seeing Japan 'Through the Eyes of a Cannibal’”, Los Angeles Times (28 Jun 1992),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2-06-28-mn-2009-story.html. 又可对照前引《日本鬼子》中榎本正代的暴行。)假如鲁迅还活着,不知道他对这两件事件有什么感想?在新版的《狂人日记》对人类进化的理论会怎么说?也许,他会补充几句:进化不是可以袖手旁观等天上掉下来的,不再吃人的社会文化是要大家不断争取和捍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