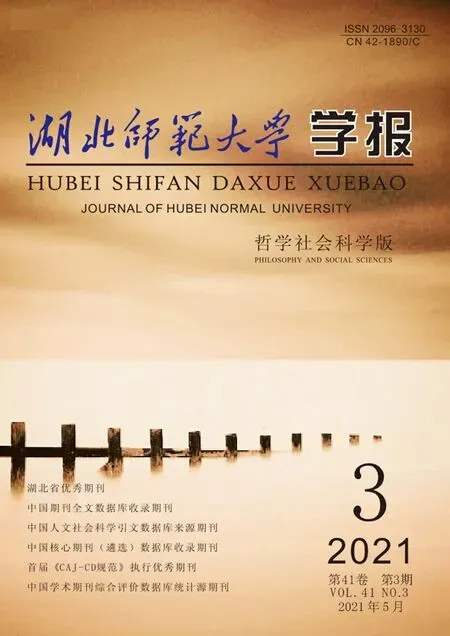黄春明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刘秀珍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黄春明(1935-),台湾宜兰人,曾担任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台节目主持人、电影编剧、儿童剧场创办人及编剧、电视节目主持人等,于1962年步入文坛,即以小说创作誉满海内外,被称为当代台湾乡土文学指标性作家。曾建民指出:“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关怀社会、关怀乡土以及关怀底层民众的文学精神,在文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年代中,起了开创性和启蒙性的作用,成了‘乡土文学’的范本之一。”[1]
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黄春明跨界游走于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儿童文学等多种领域,创作成果丰硕。在其丰富多姿的艺术形式和驳杂多变的题材书写背后,始终贯穿一条特质鲜明的精神主线,即执着观照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命运,不断诠释与理性承传优秀中华文化,并以农业乡土文化为其关注的核心。
一、主体品格的儒家文化承续
一是自觉的入世精神与使命意识。黄春明创作版图的持续拓展,既出于创作主体的艺术自觉,更源于其承继儒家文化传统的使命意识。20世纪70年代,台湾影像阅读兴起,“对小说写作感到无力感”的黄春明主动转拍电视纪录片《芬芳宝岛》,希冀引发乡土文化关注;80年代则直接参与电影拍摄与改编工作。而早在70年代,黄春明即坚持“艺术这样的东西,也应该对社会的进步有帮助的才有价值”。“希望成为一个作者,……和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献身。”[2]这一文学信念被充分贯彻于其文本之中。初作《清道夫的孩子》(1956)即注目乡土与人文关怀,也是他最为熟悉的题材。受现代主义影响所写《把瓶子升上去》《男人与小刀》等小说,则被作者自认是脱离土地、“把原先凝视社会的焦距移到自己,放大自己,捏造自己的苦闷,和弥补苦闷的怪诞行为。”[3]1966年后创作乡土系列小说《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看海的日子》等,黄春明在《文学季刊》朋友圈陈映真、尉天骢等人影响下对文学创作与社会关系认知愈发明朗,开始以更为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追求思想性甚于趣味性,浪漫精神亦有所消退,“我的心灵才有一点成长,开始会多思想。无形中,作品也慢慢地有了转变,写的东西不再考虑文学通的趣味。”[4]反对西方殖民经济与文化侵略遂成为其小说新主题。《苹果的滋味》《小寡妇》《莎哟哪啦,再见》《我爱玛莉》等经典之作完成于这一时期。黄春明亦由此确立“为人生”的创作价值取向。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他撰写了大量散文,既反映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乱象并加以批判,也探讨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的当下意义。9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在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思潮、消费文化及政治波动影响下,多元与无序并存,传统价值观消解、生活意义平面化,社会普遍性认同危机凸显。黄春明敏锐察觉这一变化,“90年代,我觉得大人没救了,救救小孩子,我开始从事儿童读物和儿童剧场。”[5]着手推动儿童教育领域的传统文化承传,鲜明展示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生理想和勇于践行的担当精神。
二是儒家人文关怀精神的贯穿。被称为“小人物代言人”的黄春明,作品始终倾注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元素。“在小说创作上,我是绝对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底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6]他关注最多的不是都市繁华与流行议题,而是乡土文明被倾轧侵蚀下底层人物的卑微生存状态及顽强、善良、坚韧、不甘堕落,对他们为“有尊严”生存而拼斗的人生予以客观呈现和深刻理解。青番公在大水灾后家破人亡,依靠勤劳的艰苦耕作重建家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白梅,凭借梦想与努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锣》里的憨钦仔形象既有鲁迅对“阿Q”式的嘲讽,更多是感动与尊重;阿盛伯为挽救清泉村“龙目”阻止街仔人开挖泳池的堂吉诃德式抗争;《鱼》表现穷人生活的艰难与坚忍意志;《两个油漆匠》中谋生城市的农民工,在一次偶然中失去生命;为生活所迫充当广告玩偶的坤树,以本来面目出现却不被儿子认识……这些遭遇农业经济转型期的小人物,以形形色色的姿态努力抗争社会变革的冲击,为维持既有价值观或者生存,或卑微或悲壮地活着,作者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无限温情与感动。出版于90年代的小说《放生》则集中关注因移民都市造成的农村留守老人现象,对他们的失落、孤独、沉闷和落后生活给予深刻表现。《打苍蝇》里林旺丛老夫妇,为给在台北的儿子还债卖了房地,只能苦等寄钱维持生活;《现此时先生》里日日聚会于三山国王庙的老人们,每天听读的都是过期甚至虚矫的“新闻”;《售票口》中为享团聚天伦之乐,病弱的老人们在寒冬夜半排队买票,火生仔与“七仙女”在下葬时与孩子的“团圆”,悲剧里蕴含了同情与微讽。《毛毛有话说》为婴儿代言,旨在理会孩子的世界认知;童话《小驼背》里的金豆,被现实世界羞辱排斥最终悲惨死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深受童年经验影响的黄春明,在作品中对老人和儿童群体倾注了最大关怀。散文《干杯,战士》(1988)则是一篇视角独特的散文。这篇收入台湾语文教材的作品,超越族群纷争与汉族本位视野,对大山深处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几代人被迫卷入不同战争、既荒谬又充满悲剧性的命运,表达了深切悲悯。既包含传统儒家文化的仁爱之义,也融入了富于现代性的人道主义情怀。
三是强烈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感。主要体现于两类作品:一是黄春明70年代批判殖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小说,二是对消费文化进行旗帜鲜明批判和思索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系列散文。前者以《我爱玛莉》《苹果的滋味》《莎哟哪啦,再见》为代表,描绘“美援”殖民主义经济在台湾扩张的时代,西方价值观念涌入、崇洋媚外思潮盛行,塑造了陈顺德、江阿发、马善行等经典形象,充满犀利嘲讽与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黄春明深刻感受到殖民文化对民族精神与民族自尊的侵蚀消解,目睹资本主义商品化思潮席卷一切的乱象,不仅以小说揭露时弊发人深省,还以呐喊呼吁的杂文抨击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渗透和侵略。“某些人高喊的‘全球化’其实是一种‘美国化’,是美国利用其经济、军事强权对别国文化殖民的结果”。[7]《再见吧,母亲节》《乡愁商品化》《吞食动词的怪兽》批判社会追逐物质、轻视传统亲情、一切沦为“买”之对象的异化人生;《城乡的两张地图》斥责台湾社会的金钱至上观,追逐金钱背后是家庭温情与传统孝悌美德的失去。“我们中国有那么丰富的饮食文化,而我们的孩子却只认‘麦当劳’,我们中国有《西游记》这样杰出的儿童文学,我们的孩子却只爱读 《哈利·波特》。长此以往,我们的国人将会失掉出生地的认同、族群的认同、国家的认同。”[8]因此,黄春明多次强调荣格认同理论对其人生成长的指引,推崇其三重认同学说,认为一个人必先认同原乡,然后推及民族与国家认同,否则人格成长、社会基础都会受到扭曲破坏,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也将面临赓续危机。“世界上,没有一粒种子,有权选择自己的土地。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肤色。”[9]
二、农业文化眷恋与理性守护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成与承传,根植于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基础。台湾的乡土社会,一方面是华南地区移民带去的稻作农业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受到台湾自然与历史发展影响,其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其文化伦理认同、价值观念、乡土习俗,无不带有浓厚的中华文化特质和地域色彩。黄春明作品中,无论富于浪漫精神的田园文化呈现,传统文化被工业经济冲击溃颓的惋惜,还是“神秘”乡野经验的书写,都呈现了对传统文化价值与审美理想的坚守。
一是作为生命力量与价值源泉的乡土。在黄春明笔下,“农业不是一种生产形式,而是蕴含了台湾人生活型态、伦理价值、情感、心理的一种体系”(柳书琴)[10]。执着相信生命教育必先从土地开始的黄春明,以自身经验反复呈证健康人格的塑型与生命泉源乃是来自对家乡、对土地的深切认同。在成长过程中,即使离乡者走上邪路,“但是深埋在心底的那一份爱乡土之情,会转换成土地对他的呼唤,而让浪子回头”。[11]乡土不仅是哺育生命成长、赋予生命原初经验的摇篮与母体,也是生命救赎与回归之地。被大水灾吞没的家园在青番公的勤劳耕作下重焕生机,延续人生希望;漂泊风尘、受尽耻辱的白梅回到生地,在淳朴乡人的温情接纳下开始新生活;失去老伴的甘庚伯热切而滔滔不绝地向精神病儿子讲述脚下土地的变化,那份顽强意志与默默忍耐正源自土地汲取的生存力量,俨然中国传统典型农民的形象缩影。黄春明以充满感情的浪漫笔触描绘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行走黄昏旷野中的甘庚伯父子背影,青番公在稻田里深情而颇具神圣仪式感吮吸露珠的情形,《银须上的春天》近乎神话般的和谐美好……这些近乎膜拜的土地情感书写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美化”可谓异曲同工。如乐蘅军所言,黄春明将人物置于自然视境中的写作倾向,乃在于使人物“保持心性的原始,而接近宇宙大地,同时也是作品‘境界’的着落处”,“自然视境以它本身的生动广大,鼓动了人们,使人们从它那里面吸取生命力”。[12]
二是乡土文化伦理的展演。追溯中国现代文学乡土写作传统,鲁迅等人重在揭露国民精神痼疾并加以批判,而沈从文、废名等京派小说家却旨在美化乡土记忆,黄春明虽创作了“憨钦仔”这一类似“阿Q”性格特质的人物,却明显给予包容和理解,突出其顽强求存精神与可爱之处。对黄春明来讲,最可贵的是传统社会的“人格特质”,具有传统气质类型人物或许无知而缺乏自信,但善良、活得心安理得。黄春明笔下的农村人物群像,更倾向于沈从文的审美价值取向,缅怀与珍视乡土伦理传统。相较于沈从文刻意“美化”的人物塑造,黄春明注重审美也致力写实,介于契诃夫批判现实主义描绘与沈从文唯美“牧歌”书写之间,“有点苦也有点甜,象巧克力”。[13]在他看来,乡土人物既代表着乡土文化与广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也代表了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黄春明是慷慨乐观的,“他永远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现作为一个人的可爱可敬的性质”。[14]坤树、白梅、阿力、猴子等等,无论他们身处窘境或是堕落风尘,却始终保持传统美德。他们吃苦耐劳、心地善良,重亲情,坤树与妻子的相濡以沫,阿梅和生母的母女情深,青番公对小孙子阿明的疼惜,林旺丛老夫妇吵骂中的互相爱护等,即使是憨钦仔,也有他可敬的坚持。相比较代表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则表现不佳。尉天骄《论黄春明作品中的教育问题》[15]一文罗列了一系列“忘本”的丑陋知识分子形象。白梅当妓女供养父母家弟妹上大学,却被他们视为“烂货”;留洋博士不回来给父亲奔丧却要求把奠仪寄给他;热衷当洋奴的大卫·陈,媚日的大学生,为老鸨们“出谋划策”的留学生“马善行”等皆被黄春明无情嘲讽批判。黄春明笔下最能体现农业文化性格与文化传统的是老人群像塑造。青番公、甘庚伯们与恶劣条件和乖蹇命运抗争的坚忍不拔、勤勉、敬天、惜物精神,誓死捍卫水源时“那种信念寄附在阿盛的躯壳使之人格化了的,无形中别人也会感到阿盛伯似乎裹着一层什么不可侵犯的东西”的凛然气质,本质皆是源自笃定的传统文化信仰。不识字的阿盛伯即说“孔子公说的话我倒听人说几句,那就够我用了”。[16]巡视在兰阳平原稻田的青番公们,日日聚在村庙里谈古说今的老人,皆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与化身,他们身上所保留的那些象征传统文化价值的美好情义世界与深厚文化内涵,正是作者极力凸显的核心所在。《最后一只凤鸟》中吴新义一生至善,处处原谅和帮助伤害自己的异父兄弟,忍受屈辱为母尽孝;而其母吴黄凤即使健忘仍惦记原乡,象征现实社会中眷恋乡土的“最后一只凤鸟”。前者也如孝道文化沦丧下“最后一只凤鸟”。《死去活来》中渴望享天伦之乐的粉娘两番死去又活过来,面对家人的疑惑不耐,粉娘感到抱歉并以发誓口吻说:“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黑色幽默的结尾透露作者深沉的悲悯。《售票口》老人自称为“孝子”“老奴才”,同样批评了年轻一代身上传统亲情文化的淡漠与削弱。而那些称为“乡野传奇”“神秘经验”的写作,则描绘了人、神、鬼及自然间的深刻交融关系,试图通过民间信仰中的风俗、神灵崇拜等现象来探索其所附着的传统伦理元素。小说《众神,听着》写供奉了三十七位神灵的春木既虔诚祷告,又因神灵未能满足心愿而抱怨不休。“春木透过他的信仰,无论是参杂着多卑微、俚俗的功利色彩,但他其实是把个人的心灵融汇进传统文化与伦理价值的传承里,从而获得精神的归属感。”[17]《呷鬼的人》看似令人悚然的鬼故事集锦,实际透露了乡民生存法则与世事判断的传统价值观。《有一只怀表》以“怀表”作为象征,充满对旧时代的悼念气息与怀旧氛围。现实与虚幻交织,传统与现代想象糅合,是新世纪黄春明对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悼词。
此外,黄春明不仅在小说里呈现大量方言、歇后语、民俗事象、民谣俚曲以及地方色彩浓郁的景观,也撰写了一系列介绍宜兰风物的散文。有介绍生物人文的《姑婆叶的日子》《新娘的花冠》《在狗尾拔桲仔树上》《匏仔壳》等;有追忆昔日风俗旧事的《枸杞燉猪肚》《人猪哥,草也猪哥?》《帮你看电影》等,在彰显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形象呈示了闽南文化在台湾的发展与流变。多彩的地域文化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版图,凸显了黄春明小说的民俗文化价值。必须强调的是,主张提炼优秀的伦理道德与文化精神,以为今日社会的精神救赎汤药,方是黄春明倡导传统文化之主旨。“将农业当做经济价值来看的时候,也就窄化了农业”。[18]“表面上是一个农业文明的讴歌者,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怀旧的感伤主义者,主张永远保持农村社会的落后与愚昧。他的着眼点不是放在‘经济’的利益上,而是从经济的着眼点提到伦理的层次。”[19]
三、重构乌托邦:以文学教育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承继
从事教师和传媒人的职业经验,对黄春明创作影响深远。前者传播其教育理念、塑造灵魂,具公益性质;后者宣传其文化理念,推销商品或推广观念,谋利性与公益性混杂。而这两类职业个性在黄春明创作中可谓并行不悖。如果说80年代之前黄春明主要以小说创作实践文学理想,90年代后他更倾向以文学教育挽救人文精神萎颓的商品社会,投身儿童文学领域,以创作和演剧方式重建富于民族气质的“精神乌托邦”,矫正被日益异化的后现代人心灵。
黄春明反复强调生命教育对人格健康成长的重要性。生命教育乃是探索和反思生命存在意义与价值进而自我定位,并内化陶冶人格情操,建立完善人生观与价值观,从而正确处理人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其核心即是“认同”。
一是自我价值认同。从首作《清道夫的孩子》开始,黄春明即关注儿童自我认同对其个性生命的影响。被老师惩罚扫地的吉照,联想到父亲的清道夫职业,产生强烈的恐怖与自卑感;《小巴哈》中老师则以机智应变的故事讲述,疗愈孤儿修明的受伤心灵。对人生伊始的儿童而言,培养积极自我认同尤为重要。童话《我是猫也》中,养尊处优的黑猫黑金在大小姐家衣食无忧,不识老鼠为何物。沦落村庄后黑金因不捉鼠且偷鱼吃遭到痛打,被主人和村人斥为“不是猫”。为了证明自己,黑金到处照影,镜子、溪流、水沟,甚至冒着危险爬到塔顶照月亮。最终在老猫的提醒下,捉住鼠王的黑金受到村人赞美,“猫”身份也被确认。可见黄春明肯定的绝非商品社会的享乐主义认同,而是符合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黑金依靠“抓老鼠”发挥价值获得自我认同,有机会返回大户人家时选择留下,凸显了对这一价值观的赞扬与传承期许。自我认同既是内在价值的认同,也包含对存在形式即外貌与形体的认同。儿童剧《外科整型》中,拥有“全世界名模都不会有的‘胖的可爱’的气质”的河马小姐,却一心想整形减肥,换上纤细水蛇腰、修长鸵鸟腿与长睫毛的硕大骆驼头,变成了四不像,隐喻了对热衷身体塑型的“人造美女”及所谓时尚潮流的讽刺。真正的美应是由内而外的美好呈现。“米勒画中的农村妇女,虽不是时尚追求的美女,可是她们表达出的母爱、勤劳形象,美得像雕像一样”。[20]童话《短鼻象》中为避免嘲笑的短鼻象通过隆鼻、增高、戴消防水龙头、吃减肥药等来增长鼻子均告失败还造成身体损伤。结果在抢险中吸水救火的短鼻象,突然发现鼻子变长了。作品强调自我认同应当重内在价值、轻外在形象,重视传统美德,批评华而不实;更深而言,则要建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不要一味崇洋媚外,不要盲目追随依赖“整容医院”“增高器”“减肥药”等来自西方文化话语建立的审美观,要重建民族审美自信心。这正是黄春明以儿童文学形式期待传递的人生价值观。
二是传统文化认同教育。面对西化思潮泛滥、传统文化日益衰微的台湾社会,谈及儿童教育,黄春明有很强的紧迫感:“小孩接受本土以外的事物并没有不对。但是,之前必须打上自己文化的底子,他们才会有自信,对生长的环境才能了解,对这片土地才有爱,然后也才能分辨人家的好坏,决定接受或是拒绝;否则,孩子只是一个空的杯子,别人轻轻一碰,便应声倒地。因此,我们应该赶快为孩子做一些什么,不然就来不及了。”[21]在黄春明所创作的儿童文学里,大都以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中已有原型故事为基础,或改编或依据历史框架充实细节内容,或撷取原作核心要旨,重新编写符合儿童心理的情节。比如“稻草人”这一意象就取自农业时代一个普遍性文化表征;《爱吃糖的国王》以楚王宠信奸臣靳尚、驱逐忠臣屈原而亡国的历史故事为原型,以“吃糖”和“吃盐”的有趣方式辨别忠奸,既劝诫小孩子少吃糖,也在儿童心灵播下分辨善恶、忠诚爱国的种子。《小李子不是大骗子》系“黄大鱼儿童剧团”经典剧目,讲述儿童小李子如何误入桃花源、与鳗鱼精和解,帮家乡重新找回安宁祥和的故事,提炼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核心主旨,表现人们对和平、安居乐业生活的永恒向往。作品在发扬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注入了崭新内涵:“桃花源不用找,它就在我们脚踩的这一块出生地。”[22]启迪受众从爱护与建设脚下土地开始,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自信心,达成民族文化认同,将理想中的“乌托邦”变成现实的“桃花源”。《小麻雀 稻草人》中,老农夫带着孩子们扎稻草人,在操作中感受古老农业文化的趣味性,而稻草人和麻雀们达成的“秘密协议”(麻雀只在老农夫不来时吃稻子)明显超越了传统实用功利视野,更强调田园景观的和谐浪漫之美。“如果有一个夏天,一遍辽阔金黄的稻田,竟听不见小麻雀快乐的歌声,也看不见稻草人傻傻的模样,这将是多么寂寞的夏天,又是多么寂寞的丰收啊”![23]显然,黄春明强调的不是农业文化的经济重要性,而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与农业文明内涵之美,为现代人塑构了一个涵蕴传统文化精粹的“精神乌托邦”世界,试图为现代社会持续发展注入不竭的民族文化动力。
结语
以乡土文明为载体,黄春明致力发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力图以传统文化改造日益异化的后现代社会人精神现状,既批判都市政商乱象,也关注乡村世界变迁;既努力以文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聚焦儿童文学教育领域,将理念与实践相结合;并以家乡宜兰为本,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剧演与地方文化建设活动。在当代台湾文学发展历程中,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旗手,抨击新殖民经济的代表作家,学界关于小说家黄春明的独特性已形成共识。而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视与承传议题尚待深入探讨。其创作实践已非“小说家”头衔所能涵盖之,在当前推动两岸四地文学融合与中华文化共同体建设语境下,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