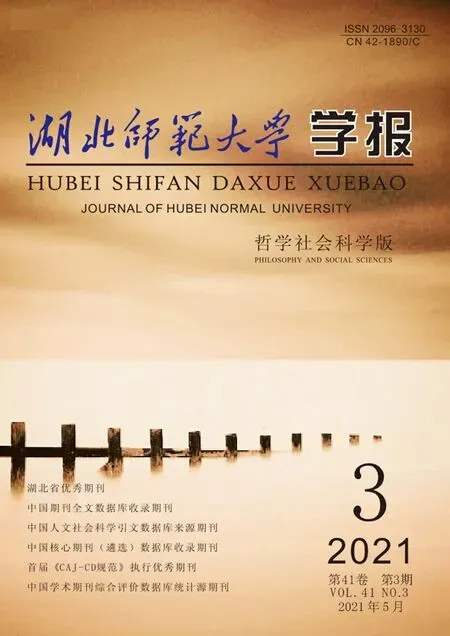《洛神赋》赋画传播的孳点透视
吴福秀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魏晋时期政治更迭,战火纷起,文化界却名流辈出,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号称“建安之杰”的曹植在其《洛神赋》中以无声的符号描写了“我”与洛神之间的真挚恋情,其文化深意不仅“明显地贯穿于作品的生产,而且也贯穿于接受过程”。[1]从考察作品的生产、构成到接受过程,对我们深入研读文学作品,从新的理论视角去认识一些文学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把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看作一条曲线,探讨其中每一阶段的传承特点及成果转化过程,对拓展文学艺术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中所说的“孳点”,是指文学作品在其传播过程中“经历了知识聚合,读者接受及文化消长之后突破原作品进入创新转化的重要阶段……它立足于原作品在被接受传播过程中的增殖点,解决的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变体问题。”[2]本文拟以《洛神赋》的赋画变体现象为基点对其孳点予以探讨,并进一步深化这一方法在诗画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一、审美符号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所指是指反映事物的概念,能指是指声音的心理印迹(音响形象)[3],二者共同构成了符号整体。语言符号同样有有声和无声之分,有声语言符号如有声文学作品等,不以文字为主要表达手段的艺术表现形式均在非语言符号范围之内。根据皮尔斯对象征符号的阐发,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但是图像和符号之间却体现出一定的关联性。符号的运用实践首先表现在言语活动,它通过对符号到符号的侧面关系的深入,“使符号当中的第一个成为能指的,意思只能交叉地出现,并似乎只是在词的间隙当中出现。”[4](P66-67)
曹植选用诗赋这种文字符号,创作了经典的《洛神赋》,赋中表达了“我”对洛神惊鸿、游龙之美的高度赞扬,同时作者也借洛神这一美好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关于《洛神赋》的创作意旨,历来有曹植自身的恋情表达、寄心君王、以幻境反抗残酷现实等不同主题的解读,但它的故事题材来源却非常广泛,先是有《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出现,其后有《楚辞·天问》所载有虞氏二女溺于洛水的传说,《文选》注也曾提及伏羲氏女溺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5],与河伯上演了一场伤情的爱情故事,至于《淮南子》中真人“妾宓妃,妻织女”的描写更是为洛神故事披上一层神异的面纱。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中所记载的巫山神女故事,是人神相恋的代表作品,虽然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与洛神无关,但赋中“怅而失志”,与神女梦期的片断描写为《洛神赋》的人神相恋模式奠定了基础。此后应玚、王粲、陈琳等人的同题作品《神女赋》,徐幹、缪袭的《嘉梦赋》等等,虽然时代有异,但故事中所描绘的神女之美,二人一见倾心,人神道殊,悲情结局等描写如出一辙。从故事的承传过程到《洛神赋》与《洛神赋图》的赋图传播,一方面完成了从文字到图像符号的转化,另一方面,转化后的图像符号又与原文本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是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来完成的。晋代之后,《洛神赋图》改变了辞赋这种单一的符号形式,尝试使用一系列符号新变来完成从赋到画,从现象到情感的另一种诠释。
(一)线性符号
所谓“线性符号”,大略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绘画和书法中的线条构成和线条造型,它主要通过人的本能脑提取信息,通过视觉形象直接显现。二是指时空中的“线性”结构及连续性,它主要通过人的逻辑脑进行理性分析而获得。这里所说的线性符号主要指前者,也就是绘画和书法中的线条。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线条叫“皴法”,人物画中的线条叫“描法”。丰子恺先生说:“线是中国画术上所特有的利器。”[6]它是整个绘画造型中最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画家通过绘画的颜色与线条“感染我们”,并借此与我们身上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对话[4](P70)。宗白华先生也认为,抽象的线条能以其流动、回旋、曲折、匀称的方式表达生命的诉求,并借此深入作者和读者的心灵[7]。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顾恺之的绘画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势态”[8]。他所使用的线条不易受到实物的限制,表现出较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正是其绘画价值所在。因为“任何有价值的绘画”从不会满足于“简单地再现”,“创造性的表现”于画家而言即是一种创新,而一个出色的画家“每天都在实践这种创造性的表现。”[4](P75)例如《洛神赋图》中的线条形状细长而密,多呈圆弧形,体现了画家对线条的创造性理解。更重要的是,“落在画布上的色点及线条”有“整体当中的效果,这种效果与那些色点及线条并没有共同的尺度,因为这些点和线几乎什么也不是,但却足以改变一幅肖像或一幅风景。”[4](P71)
《洛神赋图》中的线条一方面被赋予了浓厚的个人情感,疏密有致的线条把原文本符号中的个人情感及生命意识完整地传达出来。整个赋图通过系列符号展现了魏晋时期文人故事画的特点①。画中的洛神明眸善睐,同时画中还有许多奇珍异兽,这些都是通过线条的繁密有力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洛神赋图》中的线条又继承了传统绘画的汉画元素,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洛神赋》中的人物形象与情感通过线条的粗细、柔缓来展现,形神臻化,深得艺术妙境。
(二)象征符号
用文字符号形象叙事并赋予图本以丰富的象征意义是《洛神赋》赋图转化的又一重要特征。《洛神赋图》中的树木铺排错落有致,树的造型也极具奇幻色彩。张彦远在《论画山水树石》中说:“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9]这与原文本更注重人神情感的传递大有不同。在《洛神赋图》的第十一段场景之间,用山石和树木两种符号分界。画卷中除了第二场的一棵松树之外,只画了两种树木,其一是柳树,其二是状如扇形的大叶树。台湾学者陈葆真认为这里的第二种树是银杏树[10],但《洛神赋》并没有提到银杏树,这一观察焦点的转换颇具深意。因为《洛神赋》中出现了一系列喻体:惊鸿、游龙、秋菊、春松,却没有状如扇形的树。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可叹》一诗中写及宓妃,说她“愁坐芝田馆”[11],可见,在唐人的观念里,“芝田”是与宓妃连在一起的,而且具有特殊的寓意。因此,《洛神赋图》画幅中的大叶树应是“芝田馆”符号化的布景,也就是灵芝的象征,寓示着这里是神仙的居所,为“我”与洛神的相遇相恋营造了特殊的环境和氛围[12]。这种语言符号的视觉转换将图幅本身的焦点旁引,图像叙事中别具深意。
在传统诗画文学传播领域,光有这些形象符号是远远不够的,莱辛在其《拉奥孔》中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13]:大抵我们能在艺术作品中发现可称之为美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直接由眼睛所能观察到的,更多的是由我们的想象思维透过眼睛所看到的表象来完成的,这体现了观感与想象的完美统一。《洛神赋图》中所描摹的山水树石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如山的突兀隔阻、树的神韵与内涵等等,都须借助一定的想象来实现。学者孟宪平举了《洛神赋图》中存在的点叶树和蘑菇树的例子,认为这两种树的空间对峙不但加强了人神关系这一主题,而且还象征着人神之间的沟通和互融[14]。
“当一个符号对另一个符号显示出它们与其他符号之间的意思差异时,它们当中的每个才表达一个意思。”[4](P63)其中最能将意思差异表达清楚的文字符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仅有思想,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文字将其传达出来,那他将面临着一大堆自己“独特”的想法而不知所措。正如梅洛·庞蒂在其《眼与心》中所说:“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我们的真理的那些东西,我们永远只能在一种象征的背景当中来静观它,而这个背景为我们的认知推定日期。”[4](P66)这说明象征性的背景符号在信息传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洛神赋图》中,首先表现的是人神分离的场景,但其中还有一组长长的赋文,这组赋文就像一堵“墙”竖在人与神之间,阻隔着画面中人与神的交流,从图像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一绘写赋予了图像丰富的象征意义。一方面它象征着人神之间因身份、地位悬殊而形成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它又暗示了人神之间最终以“道殊”而收场。另一方面,横亘在人神之间的文字又赋予了二者因恋爱被隔阻而又无可奈何的内心世界,它象征着人神之间隐于幽微而不被人理解的落寞情怀。
在《洛神赋》中,洛神仙气缥缈,却游移彷徨,长吟之声哀厉而绵长,神光乍离乍合,令人难人捉摸[15]。虽然文字不能像画面那样清晰、直观地表现洛神的表情变化,但读者却能在象征符号所营造的画面中,通过脑像重构,感受到洛神因曲终人散而痛苦绝望的哀伤。在《洛神赋图》中,作者一方面以图像符号直观地诠释了这种情绪,同时又遵循绘画的原则,为观者留下想象的空间,画中的空白同样赋予图画以丰富的象征意义,它有效地激发了观者的多重联想,同时又营造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画意境。如果说《洛神赋》中的文字是一种无声的符号,那么《洛神赋图》则是以一种静态的视觉符号将情感再现。不论是原赋的形象叙事,还是赋画之间的关系阐发,《洛神赋图》都是一个从诗赋向图画转化的典型范本,它带来了文学审美范式的变化。
二、叙事焦点
理查德·巴雷特将人的大脑分为本能脑、逻辑脑和心灵脑三部分,在认知和感知事物的过程中,本能脑往往走在认知的最前列,这一脑分区部分所感知的形象或色彩最直观,记忆也最深刻,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拓宽诗画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通过本能脑来认知的图像或其他符号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所以在诗画文学传播过程中,一些形象、画面感很强的诗歌作品更适于通过画面来呈现。第二,因为本能脑在人的认知功能分区中起着最直接的作用,因而对诗画作品优先进行直观的画面和色彩呈现,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三,在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诸要素中,形象直观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而诗画作品以大众所熟知的故事或形象作为传播元点来展开或强化处理,更有利于诗画作品的深层次传播,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发读者情感深处的共鸣。
宋人郭熙、郭思曾在《林泉高致·画意》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16]古希腊诗人西蒙奈底斯也以“诗是有声的,而画是无声的”等言论来论述诗画二者的关系,这说明了诗画文学在中西传播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相似度。二者不同在于,诗使用精炼的语言抒情达意,而画则以线条、色彩等符号以形传神。欧文·潘诺夫斯基认为,研究图像的“最终目标”是要挖掘作品的深层次的含义。基于这一理解,研究图像对深化文学作品的研读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样,研究《洛神赋图》对文字符号的改变带来的审美转化,对我们深入理解《洛神赋》文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视角主体
《洛神赋》所创作的东汉末年,烽烟四起,曹植随父征战沙场,目睹了很多残酷的现实。在他的笔下,洛神其实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首先,作品中的“我”与洛神互相倾慕,但囿于人神道殊,最终抱憾分离。赋中人神恋的悲剧结局代表了作者心中美好理想的幻灭。《洛神赋图》中,顾恺之打破了传统绘画以复述文本为主的创作模式,开始转换叙述视角,由原赋中作者的视角转化成画家或观众的视角,使图文表达的主体翻转过来。其次,在《洛神赋》中,曹植是这场爱情故事的直接参与者,而在《洛神赋图》中,曹植和顾恺之都是在场者,画面中除了曹植的主动参与之外,还有画家的间接参与,隐性“他者”的合理存在,将观众带入到故事中,从而产生了一种与原赋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最后,《洛神赋》的视角主体是以“我”来全面观照曹植在返程途中偶遇洛神,既而互生情愫,最后无奈分离的落寞心境。《洛神赋图》中除了以洛神和曹植为画面主体之外,还刻画了鱼龙、女娲、雷神等不同于凡俗的神人形象,同时又配上现实的舟车、树石、远山、流水等不同场景,让潇洒灵动的仙堕入凡尘,这样处理既增加了画面的缥缈仙气,又增加了观者的凡尘之想,为仙人入凡,最终又为世俗礼法所拘,暗示了最后“有情人”终不能相守的悲情结局,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
(二)空间布景
《洛神赋图》虽然微妙地刻画了与《洛神赋》相符的人物动态关系,但《洛神赋》中所描写主要人物强烈的内在情感,及表现人物内心痛苦挣扎的表情和眼神却无法显现出来。针对这一特点,图本对《洛神赋》文本进行了再创作。第一,《洛神赋图》移步换景,分段连续地将不同情节放置于同一画卷中,不同形象借助不同的画面布景来呈现,如山水自然景观都用线条体现,而画中人物关系则由不同层次的技法来表现。画中描绘了驷马并驾齐驱拉车,仆夫就驾,而主人公却盘桓不去的场景,图中曹植坐于车内,旁边四个士兵护卫着曹植驾车东归,全部人物活动在场景的转化中凸显出来。先是想要离开,而后不舍回头,再到最终离去,整个过程中曹植不时地回头观望,那种眷念难舍的情感随布景转换,将主人公欲离而又不舍的心绪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中国画的精髓在于以形写神,形为阴为体,神为阳为用。绘画技法中的阴阳虚实之法具体体现在:线条为实,空白为虚,深色为实,浅色为虚,浓墨为实,淡彩为虚。《洛神赋图》借助传统的阴阳之法,将具体的人物、树石加以区分,将线条与留白,笔墨的深浅与浓淡结合起来,实现空间的布景转化。如以圆润的线条彰显核心人物的存在,以写实之法来完成,同时又将原赋中的比喻物象,如惊鸿、游龙等形象通过虚笔向背景转化,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绘画空间,另一方面又以虚衬实,突出画面的主体核心。
(三)人神关系
在曹植以前描写人神相恋的作品中,人神关系通常体现为一种人对神的爱慕,神于人而言是高高在上而具有优越感的存在,这种人神关系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到了六朝时期,受玄学影响,画家创作开始比较注重自身的体验与感受,而士人们也将个人的情感投放到自然景物中,追求物我交融的境界,体现了人神之间一种新的逻辑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
就“我”与洛神的关系而言,一开始作者就将二人的相遇放在了一个特殊的现实背景中。曹丕登基为帝之后,对手足兄弟曹植痛下杀手,曹植七步成诗,勉强活命之后,又被外放为藩王,不经奉诏不得回京。在闲暇时光倍受监视,曾经的下属朋友也是接连出事,兄弟、朋友连番遇难,这对曹植的心理和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下,他虚拟了一场无望的恋情,在“寄心于君王”的前提下,他们的恋情最终只能是无疾而终。于是,洛神在失去恋情之后,她“践椒途”“步蘅薄”“戏清流”“翔神渚”,长吟之声哀厉而长,原赋合理地传达出一位深情的女神面对残酷现实的那种无力之感,匏瓜无匹、牵牛独处等更是将失去爱情之后脆弱的人神关系一一呈现。《洛神赋》在叙写了作者与洛神的相遇、相恋和离别之后,又将洛神与现实环境中那些美丽而又受到世俗羁绊的女性形象联系起来。一开始,洛神回应了他的求爱,但她恪守礼法传统,信修、习礼、明诗。这种礼法约束让“我”与洛神只能“指潜渊为期”[15],这也为后文的“人神道殊”、最终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洛神赋图》通过对爱情神话题材的剪裁处理,对天人关系转化的细腻捕捉,赋予了这一作品以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时空关系
就诗画文学样式而言,一般诗歌所论及的范围较为宽泛,在诗歌里我们可以驰骋想象,丰富的意象、深刻的人文精神都可在这里交汇。而绘画更多地运用线条和实物来表现主题内容,这种通过实物符号表现出来的内容往往受到时空的限制,一方面画家的思想表达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观者的期待视野和思维拓展都受到明显的影响[13]。《洛神赋图》以《洛神赋》为创作底本,用图像叙事,将文字符号变成有形的图画,使作品的时空关系表现出多样化特征。
(一)线性时空架构
首先,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洛神赋图》卷为宋代摹本, 它以长卷、连环图的形式讲述了这一人神相恋的故事,画卷按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顺序连环构图,形成一种线性的连贯。一方面,这种构图展示的画面非常宏阔,不能由单幅图体现,只能采用连卷的形式。另一方面,构图本身在辗转强调一些故事情节,因此特别注重情节的连续性。这种连环画形式更注重故事的前因后果,对我国古代人物画及山水卷轴画的构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所形成的线性时空叙事方式在古代绘画作品中受到广泛关注。
其次,《洛神赋图》成功地实现了直线型的时空重塑。在时序安排上,作者将山水、树木、鸟兽等自然景物合理呈现,将不同情节用图景分布在同一画卷中,故事主角随着原赋顺序依次出场,每个故事像珠串一样环环相扣,形成一幅首尾呼应的完整画面。画面中大面积的山石、树木,还有背景化的比喻物,更像是将整个故事画面串联起来的纽带,使人物行动、故事情节不至于散乱。
最后,《洛神赋图》卷轴形式设计直接从中间卷开,从两段收起。卷轴宽距小,长距可延展范围广,观赏者可以从右往左按顺序看,随着叙事顺序逐渐进入这个故事中去,从而使观者在一种线型的思路中体会到人物之间丰富的情感。
(二)曲线时空变体
中国古代哲学习惯用阴阳来诠释道[17],在绘画及文学表达方式上,阴阳、虚实、明暗等流动因素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与原赋相比,《洛神赋图》所体现出来的人神关系是有变化的。画中的人与神在同一时空出现,不再是曹植的那种对洛神的可望而不可及,体现了符号层面的人神平等。其次,人与神进入同一空间实现了平等对视,二者之间的物理距离可由画家依场景合理调配,这一改变弥补了原赋之中人神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感。最后,人神二者在平面共存与空间对视,目光交叉,视角切换,实现了人神在空间里的自由流动,如此一来,二者的交流与沟通就有了多种可能。如在平面共存的第一个场景中,画家将两位主要人物的目光设计成两两相对,形成一种共时的连续性。但在同一时空中,二者的目光却又有所隔阻,他们不能无所顾忌地宣泄内心的情感,而只能采取一种迂回的曲线方式。在最后离去的那个场景中,曹植不再是拨开仆人向前平视,而是恋恋不舍地回头凝望。画家以强大的宏观把控能力,以目光贯穿始终,将赋中的洛水、奇峰、怪兽、树石等铺排在整体构图中,为主人公的情感表现不时点染,形成语图交融的艺术妙境。
从整体构图上来看,《洛神赋图》也以灵活的方式改变了之前的时序,一方面,它依据原赋的主题感受重新布置时空场景,构图遵循了《洛神赋》的形象叙述,继承了曹植对洛神形象的描写,另一方面又将惊鸿、游龙、秋菊、春松等物象通过图式背景化处理,借此烘托出洛神之美,从而更好地完成了从赋到图的转化。这种手法充分展示了文学创作中隐显之法的妙用:第一,从原赋中提到的“长寄心于君王”[15],我们知道曹植在原赋中是有所寄托的。曹丕即位后,他不断遭受到政治打压、小人迫害,这样的环境根本无法让他真情直露,因此,他这个隐性的人只能在幻境中向显在的洛神表露心声。而在《洛神赋图》中,故事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显性的,“洛神”与曹植深情款款,在同一场景里,两人互赠信物定情。在不同场景里,两人又可以打破时空限制,用深情的眼神互相交流。这样从赋到图,隐显之法相得益彰。第二,《洛神赋》原文中的曹植是以一个隐性叙事者的方式出现的,故事中人物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都是通过这个隐性人来感受的。而《洛神赋图》的男主人公曹植则是以一个显在的身份同女主人公洛神同时出现在观赏者的视野中,他所观察、感受到的喜乐哀愁都不能像原赋中那样深层次地表达,而必须借助其他显性的标志物来呈现。第三,原赋中曹植的语言叙事将整个故事合理连缀,他的“隐在”身份成就了故事的连续性。赋图中曹植的在场限制了他全方位的表达,更多的情绪要交给“不在场”[18]的画作者和观赏者去体味。原赋中的主人公“不在场”时,时序连接,情感呈自然态发展。图本中男主人公“在场”时,他受到时空、场景的限制,出现了平面视野内的时空断裂,如此一来,他所看不到、不能感受到的,就需要虚拟空间来完成。画作者的隐性存在正好弥补了这一间隙。
四、结语
从《洛神赋》到《洛神赋图》的赋图转化,揭示了作品创作中潜含的文化元素,客观展现了这一作品在文学、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研究这一变体现象对突破交叉门类研究的壁垒,开拓诗画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对进一步深化诗画文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关于《洛神赋图》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歧见颇多。本文认为《洛神赋图》是顾恺之的作品,代表了魏晋时期的绘画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