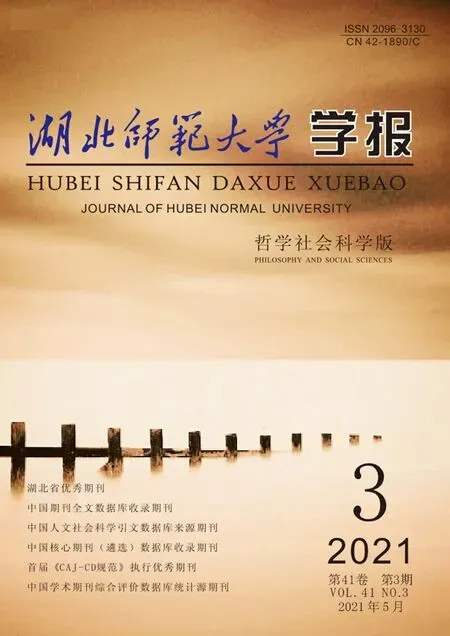风景的一般形态及其构因与可能
柯弄璋
(重庆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
面对“风景”一词,人们首先不禁要追问风景是什么?或是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客观真实的自然(如山水、动植物、气候),或是在人的意识中生成的、与现实脱离的“观念中的风景”(如《西游记》里腾云驾雾的风景)[1](P1),或是成形于艺术家之手的“艺术风景”,或是现代工程建设所创设的“技术风景”(如美国棕榈泉的“风之牧场”)[2](Pii)。风景的具体所指可以千变万化,可当我们把一切看作了风景,却对它们变得熟视无睹起来、变得很少去思考风景的意义时,就遗忘了风景的起源意义。
正如有学者指出,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其起源便被掩盖了起来[3](P12)。其实,无论风景是指向什么,它都意味着一种对象性,人们既然可以观赏、改造、创造它,也会不免破坏、损毁它——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并不少见。因此,要正确对待风景,既要避免因泛化风景而遗失风景意义,又要突破对象化思维、从而避免破坏风景。并且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统一的,即只要打破了对象化思维,就能避免不断延伸风景的所指链,并在此基础上有可能阐明风景的意义、寻得保护风景的正确方式。对象化思维本质上是主体-客体思维,而对主客二分思想的有力冲击主要来自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他在反思、批判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基础上,指出人的存在(“此在”)其实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人总是与他人、他物不可分割地共在,他人、他物因他的联系而显现在他的“世界”中。运用这种间性思想来突破风景的对象化,意味着风景总是以各种关系与方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或意识中。基于此,本文试图分析其间的诸种构造性联系,并探究其成因和其他可能性,旨在还原风景的本真意义,与此同时,也为建设和谐宜居的环境提供一定的理论可能。
一、风景的呈现形态及价值
在古代,人们一方面将风景视作外在于人的“物”,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它与“人心”的关联,认为“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构成物动心、心感物的圆环结构。受此影响,陆机指出人们会“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风景可以触动人们的情绪、情感,还指出“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深”,情感越沉郁,对风景的感知就越深刻。后来的刘勰也看到了情与景的这种关系,指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他还强调诗人应使二者相结合,“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明代的谢榛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胎,合而为诗”。清代的王夫之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性指出“景生情”“情生景”,说明二者存在相触相生的关系,还认为存在“情中景”“景中情”的相互包含关系。无论是相互触生,还是相互包含,情与景的落脚点应当是二者交融后的那种状态。钱钟书认为《三百篇》“有‘物色’而无景色,涉笔所及,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楚辞》始解以数物合布局面,类画家所谓结构、位置者,更上一关,由状物进而写景”。[4](P613)由此,情景融合后的状态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单个景物或多个同质景物形成的能够刺激人物情感发生的审美意象,比如人们无意间见到鲜花而心生欢喜,这是一种瞬时、短暂的触碰式情感体验。第二种是由几个不同景物构成的、画面内容丰富的、能够满足人物情感体验的审美意境,比如人们失意的时候见到凋零的花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枯败的枝叶、瑟瑟的秋风、昏暗的天色等而感到无比落寞,这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具有情感纵深度的沉浸式情感体验,不同景物之间的空白由情感灌注而联络成为一个整体即意境。尽管情与景具有相互触生、相互包含及相互融合的关系,但是情与景的关系在数量上并不一一对应,不仅存在如第二种情形中的多景对一情,而且存在一景对多情,即面对一处景物,人们可能产生多种复杂的情感,就像刘勰所言“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或者面对同一景物,不同的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对此,后文还有涉及。无论是哪一种具体形式,人对于风景的移情都会使人感受到外在世界的圆满[5](P16),从风景中获得一种寄托和满足、追寻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情态。
古代的人们还很早就在探求自然风景背后的规律,认为景中有理。比如八卦的创造就是以抽象的简化符号指代自然景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巽代表风,震代表雷,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这些卦象符号又都是由阴爻、阳爻的不同组合而成,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自然风景形成的普遍性规律。清人张谦宜在《絸斋诗谈》中指出“诗中谈理,肇自三颂”,认为《诗经》开始了诗歌释理的道路,不过一般是“有句无篇”,只有哲理诗句,而少有以哲理构局谋篇者[6]。《诗经》片断式的哲理阐发不少都借用了自然风景(“比”)。在《诗经·小雅·车辖》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高山大路讴歌新娘美丽的形体和坚贞的德行值得敬仰。这种表达也贯注在楚辞的“香草美人”模式中。作为以景比理关系,景与理之间必须存在显在的形似,而且这种理不像景中有理那样指向景本身,必定是景物之外的,进一步言之,二者的相似点只是景的某一局部特征,无法代替景物整体。随着自然山水意识的自觉,魏晋以后的人们逐渐形成了由景悟理的观念。所谓由景悟理,景为辅,理为主,相比景中有理而言,它并非为了阐释景,相比以景比理而言,它的理与景之间不存在显在的相似点,它需要人们在对景物整体观照之后进一步获得某种哲理启示,这种启示往往与人的生死、历史的兴衰、人性的规律相关。在玄言诗、佛理诗中可以见到许多由景悟理的现象,而且它们的理会在文末显现、提示出来。比如在著名的《兰亭诗》中,王羲之有言“仰望碧天际,俯盘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早期的山水诗、田园诗中也有此种由景悟理,比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理-景关系的出现及发展表明人们已经将自然风景“二元化”,一则意指“那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同时又意指“那只能被心灵感触到的力量”,“自然受到喝彩,不仅是因她形、色迷人,而且也因她表现出经久不变的秩序”[7](P332、336)。正是通过后一种“力量”及其对外部世界的“秩序”化,早期人类克服了来自外界的生存威胁和恐惧,并且在后来的进化史中,不断依靠它征服和改造外部世界。
人们还能够在现实风景的基础上主观构造另一副“景象”以寄托自身的意志。这类“景象”关系可上溯至创世神话当中。创世神话往往构想了天昏地暗、山河始成的景观,比如“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五运历年纪》)这些景观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诞生的奥义的一种想象式解决。这种玄妙“景象”还体现在老庄的作品,以及后来的玄言诗中。《山海经》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神奇“景象”。作为一部“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表现着现实世界与神话时空交织的内容”[8]的奇书,《山海经》于虚实之间构造了诸多景象,其中,《山经》以四方山川为纲,按照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描绘了许多怪异的草木鸟兽;《海经》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这些“景象”虽也带有一些神话色彩,却并非为了显示玄妙之理,反而张扬了景象的反常性、异常性。反常的“景象”还流传于民间大众的朴素思想中。为民众所熟悉的《窦娥冤》里的三桩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就塑造了经典的民间诉冤模式。可见,“景象”的反常意在揭示某种情境、状态以及生存境遇的异常,而众多反常的集合又内含着一种包容性。“景象”有时还是理想的化身。在中国,最经典的乌托邦“景象”莫过于桃花源式田园乌托邦,于别有洞天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桃花源诗》)。在西方,也存在柏拉图、莫尔等提出的“城市型乌托邦”。这些乌托邦“景象”都一方面充满了“感官享乐性”,另一方面又充斥着一种“高水准的伦理学意义上的超然性”[9](P72)。对“景-象”的开掘使得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自然形成了“精神漫游”“田园的诗意生存”的审美观照,自然风景在其中扮演了“精神取向的意象”“精神栖息的母体”的角色[10](P12)。
二、风景形态的构因分析
人对自然的认识大致形成了神化自然、征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三种模式:早期的人类赋予大自然以神的力量,并把人自身所有的活动都看作是自然显现的一部分,以追求自然本性的符合为最高目的。自公元前8世纪,西方社会开始主张征服自然,并试图与自然相抗衡以展现人类的伟大,特别是在后来的工业革命时期,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达到了历史顶峰。由于“战胜”自然的同时又受到自然的无情报复,人们后来逐渐意识到要想在这个地球上持续生存,就必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11](P30)。在神化自然模式中,风景往往蕴含着一种超人意志,它既可以表示与风景相匹配的客体化的道理,比如天地风雷等蕴含的八卦原理,以及玄言诗、佛理诗、山水诗、田园诗中由风景所透露出的玄理、佛理、生命之理、生活之理等;也可以指在人的想象中支配风景形成的神灵力量,比如《五运历年纪》里展现的盘古创世神话。即便人类社会迈过了神话时代,但神化自然模式的影响尚存,中国儒家的“天人感应”说、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乃至佛家的“万物皆有佛性”等都意味着风景背后存在一种神秘意志,而且有时它还能与人相通,就像李白诗中所言“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说明景中可含情。相比西方文化中萌发的征服自然观念,中国文化中持续影响的神化自然理念更能促进人们对风景的发现。有人认为“风景诞生于中国”,其中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宗炳的《画山水序》写道“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最早产生了对“风景”的明晰思考[12](P55)。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它们都体现了“自然的人化”过程,“所谓的‘人化’主要指对自然的实践化,除此之外,人在感觉层面将自然纳入认识范围;在情感方面作为主观情志的寄寓;在伦理层面作为主体人格的象征,这些都是自然‘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P7)在这一过程中,风景都被深深打上了主体意志的烙印,“那些被开垦的、平滑的、安静的、和谐多样的渐进是‘秀美的’。它们是有边界的,因此也就是可知的风景”,“那些荒野的、崎岖的、超越人们想象的、广阔无垠的风景是‘崇高的’,因为其无限性使人们生发出充满敬畏的情感和永恒的观念”。[13](P53)风景不光与人发生情感联系,还产生了伦理、象征等关联。所以,人与风景相应地具有情-景关系、理-景关系、景-象关系。
在自然“人化”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风景本身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其中,有两种流行的、广为人知的看法。首先是观看风景,它是指绘画风景以及以绘画视角观赏风景,“呈现一个旨在表现超验意识的意象”,其中包含着人类视觉领域循序渐进的发展[14](P1),不论是画家还是一般的观赏者,他们的视线都如取景框,首要关注形式、轮廓、构图、光线、色彩、景深等,通过身体感官的激发,风景从模糊的背景定格在他们的前景意识中,并且他们总是怀有“多多少少自觉的美学态度”,不是因其题材、功能而珍视它[15](P139、154)。在此视域下,风景与人的关联更多是一种感性的、直觉的关系,具体来说,特定时空、特定形式的风景(比如“柳条”)能够触发人特定的情感(“惜别”),并且对此风景,无论是置身景中的人,还是景外的旁观者,都怀有一种“美学态度”,因而情景极富隽永。阐释风景则与观看风景相反,它“倾向于把绘画和纯粹的‘形式视觉性’的作用去中心化”,把风景看成是心理或者意识形态主题的编码,树木、水、石头、动物等景物都可以被看成是宗教、心理或者政治比喻中的符号[14](p1),以及不同的风景结构与形态同样蕴含着互不相同的文化属性。风景在此意味着人如何为风景赋予意义或者建构一定文化意义的过程,其意义包括了民族性、阶级身份形成、地方的文化建构、共同记忆与历史、身份认同等[16]。显然,在阐释风景者的眼中,风景中包藏着诸如宗教、政治、生命等各种道理,比如春秋时期的人们对于自然灾异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认为诸如地震、雨雹、日食等自然景象预示、对应着人世的某种变易,《左传·僖公十五年》曰“震夷伯之庙,罪之也”,指出夷伯庙被地震震垮是由于他先犯有罪过。而正因为景中有理,人们不仅可以由景体悟理,而且反过来可以通过具象化的景来比喻、阐明抽象的理。此外,由于风景在阐释者眼中还表征着民族、身份、地方、地域等,人们可以选择从这些方面建立人与景的关系。比如长江黄河和万里长城体现出一种民族情感,大漠戈壁和小桥流水均带有地域自觉,以及所在区域地理要素决定域内景观特征的道理。
从神化自然到天人相通,直到现代生态观念的形成,随着对自然和风景认识的变化与深化,人们越来越把自然、风景当作一种理想的、审美的生活方式的途径和手段。作为理想的生活形态,在中西方文化中,无论是“城市型乌托邦”还是“田园式乌托邦”,相同之处在于“四周都由水系和深山环抱,或如极乐净土那样远离尘世,给人造成别有洞天的印象”。[9](p72)也即是说理想的生活必定要有山水等风景的环绕,必定是由风景将之与世俗隔离开来。这意味着人们愿意主动去接近、亲近风景(旅游),乃至将风景作为装饰物带到室内(风景画)。于是,原本横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那道鸿沟逐渐消失,人与风景变得如此亲密、亲昵,风景有时成为人的静谧的倾听者,如“泪眼问花花不语”(欧阳修);有时又像隐默不语的沉思者,如“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波德莱尔);有时还是似人一样的舞动者,如“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周邦彦)。然而,这种审美化的生活追寻虽然加强了人与景的种种关联,与此同时也遮蔽了另外一些人与景的关系,而这些遮蔽和空缺在今天现代风景学的反思性观照中得以敞开、浮现。针对“田园式乌托邦”,就有西方学者指出“具有审美愉悦的田园风光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把农业过程、农业劳动者,甚至整个村庄从视线里清除出去,留下无人的、如画的风景,使特权观赏者能够观赏纯粹的画面”,“受过教育的手和眼睛建构、接受、诠释一番景色,而忙碌的底层劳动者也在建构、接受、诠释另一番景色。经过社会与美学高低标准的过滤,透过表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视角’,决定了哪些人能看到哪种景色”。[13](p30、13)人们广为称颂的风景其实往往都是由“特权阶级/有闲阶级”所发现和制定的,他们往往占据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和闲暇时间,为此,他们才具备发现风景的可能。如果要具体到最先发现风景的人,在西方或许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学者彼特拉克,在中国是东晋时期的兰亭集会参与者[12](P12、55),与会者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无疑,他们均属于社会上的“特权阶级/有闲阶级”。
三、风景的其它可能形态
斯本认为“景观中包含着许多信息和故事”,“它们揭示出自己的起源,彰显出那些建造它们的人的信仰,它们肯定或反驳某种思想,它们也存在于艺术与文学中”,“景观的含义是复杂、多层次,且多义的”[17]。作为景观设计与规划专业的教授,她所说的“景观”(Landscape)偏重于人为之景,但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所说的“风景”其实也并非是自为之景,同样与人相互关联(它对应的英文翻译一般也选用Landscape)。因此,不妨认为风景的含义也是多层次、多义、开放的。风景的开放性反过来意味着关于它的任何一种看法都有其局限性。
当人们从形式、轮廓、构图、光线、色彩、景深的视觉角度捕捉风景的客观化图层时,有时会受到“欺骗”,把某些风景视为天然如此、自然而然的,而忽视了它们在地球进化史中的变迁,比如河流的改道、山体的升降;有时也会低估风景的意义,将某些风景当作纯粹的视觉冲击、感官愉悦与震撼,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独特的地质、地貌、气候等方面的构造原因,比如云贵高原的喀斯特溶洞、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波浪谷,从而难以企及风景的深度与自然的奥义;平面化的观看有时还很难说清一座山与另一座山、一条河与另一条河、一座森林与另一座森林的区别,以致出现许多同质化风景。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作家的视野中,山西的山林——“吕梁山的一条支脉,向东伸展,离同蒲铁路百十来里的地方,有一座桦林山。山上到处是高大的桦树林,中间也夹杂着松、柏、榆、槐、山桃、野杏”(《吕梁英雄传》),与山东的山林——“在山东昆嵛山一带,到处是连绵的山峦,一眼望去,像锯齿牙,又像海洋里起伏不平的波浪。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繁茂稠密的草木”(《苦菜花》),就大同小异,看不出什么变化[18]。
透过风景的视觉化外观层,人们往往会去寻得一种审美愉悦和满足,正所谓“良辰、美景”,又好比“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达致美景与美好情感相融的境界。然而,一旦面对一些特殊的风景对象时,这种情景的融合有时却难以实现。比如一无所有的空地、丑陋腐败的树木。前者没有结构、也无从考证其历史(历史空白),甚至没有命名,这种看似不存在的虚空却又占据着现实的一定空间而成其为风景对象,对此,我们的审美落空,哪怕再热烈的情感也被虚空稀释、化为乌有。后者则要略微复杂些,因为它涉及不同时代人们对“美”“丑”的认知。有现代学者对“丑”提出了几项反思,认为“丑是相对的,随时代、文化而有别;昨天不能接受的事物,明天可能被接受;被视为丑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助于整体的美”。[19](P421)在过去,人们可能接受了“玉树临风”的风景,以传达美好与喜爱之情,而对丑陋腐败的树木不屑一顾;到了某天,人们忽然又能够接受丑陋腐败的树木,在诗歌中尽情描绘它(比如西方现代派诗歌)。如前文所述,对于风景的审美满足还存在一个问题,当部分人(“特权阶级/有闲阶级”)感受到风景的美好,而另外的人却丝毫不为所动,甚至极度厌恶,土著人眼里的“穷山恶水”反倒成为观光客眼中的“乡村风情”。
风景成为一种文化中介后,当它也成为民族、阶级、身份认同的表征时,它相比文学、艺术等中介形式的特殊性在哪里?首先,风景的意义的获取方式比较特殊。风景“既有视觉美的一面,也有触觉美的一面。如果说前者是人眼捕捉到的风景形态,或说是大自然的伫姿,那么称后者为‘可用身体感知的风景宜居度’应该没有问题”[20](P14),风景是一种可以观看也可以触摸、人置身其中的现象,人们是站在风景内部来感知风景,并且人与风景之间存在相互调适的可能。另外,风景的意义的最终指向也较为特殊。有学者指出,景观中包含着同时发生并共存的两种不同过程:“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前者指为景观赋予含义的过程,然而,“人类自发或自觉地改造环境,建设理想家园的过程归根结底是景观的‘物化’”,这是“景观生成的目标与结果”[21](P31-32)。风景亦然。现代风景学是“为创造和保障人类的生活空间提供帮助的一门学问”[9](P115),风景不仅仅关联着人的品位,而且关系着和谐的宜居环境、勾联着人类未来的家园。风景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够再单纯按照阅读文学、艺术的思路来阅读风景,将风景加以语言符号化,为风景无限赋义,遗弃风景的物化目标,使得风景往主观纯粹化的歧途渐行渐远。
既然任何一种看法都有其局限性,那么要想降低局限性,就只有尝试将几种看法综合起来,以揭示风景形态的其他可能性。新的风景可能还受到如下观念的影响,即认为“风景生命”具有三个层次:“自然(地质、变迁、季节周期......)、社会(人类活动的历史)和个人(也就是你和我,那些正在欣赏着真实风景或将风景描绘出来的人)”[12](P18)。在这里,暂时将这种新的可能形态命名为“景-文”关系,“文”同时包含“文字”“文化”“文学”三重含义。其中,“文字”是指风景的外观,既包括形式、轮廓、构图、光线、色彩、景深等显性文字,还包括地质、地貌、气候等隐性文字,显性文字体现着个人的感受,隐性文字则透露着地球的“集体无意识”。“文化”是指风景的文化意义,既包括民族性、阶级身份形成、地方的文化建构、共同记忆与历史、身份认同等风景的象征涵义,也包括身体在场的获景方式和风景物化的目标等人类付诸风景之上的种种实践及其历史。“文学”指风景的审美特性,既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审美情感、审美直觉,也包括审美落空、审丑等特殊形态。在“景-文”关系中,就各个层面而言,“文字”说明风景的客观性,“文化”表明风景的主观性,“文学”审美则直接连接起主观与客观;而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充分揭示了客观与主观的结合、客体向主体呈现的状态,说明“风景只能通过心灵的统一力,作为无法用机械比喻来表达的实际景物与我们的灵感的结合而存在”[22](P172)。
“景-文”关系的价值还在于摆脱个体风景学的局限,走向一种“人间风景学”。人们过去对于风景的发现与理解偏向于个人角度,如里尔克这样描写风景(“山水”)被发现:“当人觉得,它是另外的、漠不相关的、也无意容纳我们的时候,人才从自然中走出,寂寞地,从一个寂寞的世界”[23](P90);无论是“情-景”关系,还是“理-景”关系,抑或景-象关系,实际上人们往往预设的都是单个的观景人。然而,既然风景作为向人的显现一种方式,就有必要考虑到人之存在的独特性。人之存在的根本结构、本质特征具有个体性、社会性的二重性,所以,我们对“风土”(风景)的理解应该从“人”之学进入到“人间”之学,突出风景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4](P12、245)。而“文字”“文化”和“文学”审美自身都蕴含着一种人类共通性、沟通性,也即是说“景-文”关系不仅像“情-景”关系、“理-景”关系、“景-象”关系将风景作为人与对象之间的构造性联系;更试图表明风景这种关系内部还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风景视作人际交往的一种隐秘场所,包括不同的人围绕同一风景产生的感受与观点的“对话”(既有兰亭集会那样的现实中的“对话”,也有不同时空下的人物虚拟“对话”)、不同的人共享着对某一类风景的认识(由于景观的“某些象征和指示具有独特的语境,只有某些群体熟悉”[25](P17),他们会形成一个风景鉴赏共同体)等。风景让人们得以沟通、交流,塑造某种人类共同体。
四、结语
面对“风景是什么”的追问,我们应该回答的不是风景究竟是指什么,而应是风景对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说风景会以何种形态向人呈现出来。通过以上考察发现,风景与人之间往往存在着情-景、理-景、景-象等诸种构造性关系,并且二者间是一种开放性状态,任何一种关系都有其局限,它们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关系可能。这种可能将是综合型的形态,比如“景-文”关系,它囊括了风景的显性和隐性外观、人类付诸风景的种种实践及其文化意义、风景的种种审美情态,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尤为重要的是,“景-文”关系力图摆脱个体风景学的局限,走向“人间风景学”,实现人与景、人与人的沟通对话。这些才是风景的本真意义。
在当下,人们还与风景之间存在着一种怪象,“人们可以把自家附近的河流弄得很脏,但与此同时又会涌到美术馆门前排队看美术展览”[9](P18),人们喜欢利用闲暇时间涌入国内外的风景名胜区度假旅游,人们还喜欢用盆栽、绘画、贴纸等方式在居所内营造微观风景。我们愈是追寻风景,意味着风景愈是远离我们,即风景的非日常性、人对风景的隔离感越来越强烈,归根结底在于我们一直按照主客分离的态度看待风景,将风景视为纯粹的审美客体、娱乐对象、休闲工具,因而我们也不免会破坏、损毁它。为此,我们更加有必要还原风景的本真意义,关注风景如何向人呈现,倡导人与景、人与人的沟通对话,进而建设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走向美好的人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