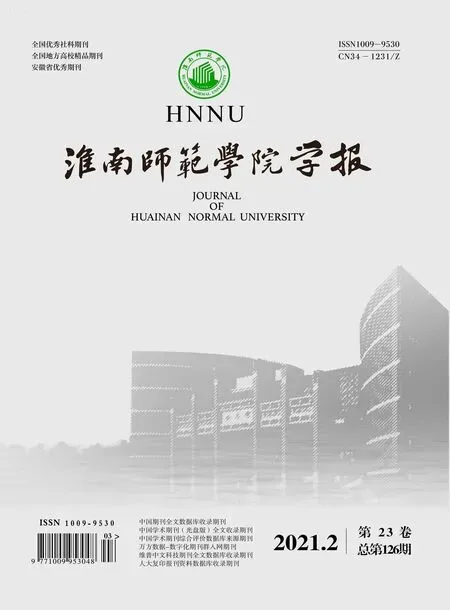皖北文化适应与认同:“准传教士”赛珍珠跨文化书写探源
赵丽莉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美国诺奖作家赛珍珠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桥梁, 早期主要以中国题材书写为跨文化传播媒介,在文学作品中向西方世界展现出不一样的真实中国。皖北宿州是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作品《大地》和《母亲》的主要背景地,这里被认为是赛珍珠文学事业的发轫之地。 与赛珍珠成长地镇江、工作地南京相比,学界对宿州的关注较少,研究方向较为单一。 以往研究者多是本地学者,如原宿州学院邵体忠和鄢化志教授, 多从宿州的地理和文化本位出发,探讨宿州厚重的文化底蕴、朴实善良的皖北农民和最具代表性的皖北农村现实如何影响和成就了赛珍珠的写作之路。 “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与宿州文化的渊源已经是有目共睹”[1], 已得到学界认同。姚君伟教授断言,“在宿州的数年生活给赛珍珠后来创作《大地》三部曲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2]。《赛珍珠传》 作者彼得·康也认为是宿州给赛珍珠提供了素材,“提供了使《大地》广为流传的人物和他们活动的背景。 ”[3](P62)过去研究中赛珍珠大多作为突然闯入皖北城乡社会的“异乡人”,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其“他者”主体的内在情感和主观能动性被忽略,这也割裂了赛珍珠的诺奖书写与皖北社会现实的互动影响关系,进而遮蔽了赛珍珠早期跨文化创作中的某些关键因素。
赛珍珠在中国辗转多地,生活了近40 年,又旅居过亚欧多国,有着丰富的中西文化生活经历。 百年前,这位金发碧眼的异乡客仅在偏僻落后的皖北宿州呆了两年半,为何能从这块寂寥之地发掘出中国乡村书写的灵感呢? 1938 年, 赛珍珠荣获诺奖后,作品风靡世界,国人也开始关注其人其作。可是彼时皖北宿州却没有条件和能力对此做出任何正面回应, 只有个别好事者街头巷议,戏言赛珍珠的宿州寓所风水好[4](P5)。 圉于种种原因,一直以来,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学者都把赛珍珠农村书写与皖北宿州的地缘渊源看成是自然而然、 理所当然的,似乎无需多说或无话可说。本文尝试从赛珍珠寓居皖北宿州的美国“准传教士”身份入手,回溯她在皖北城乡的传教士生活和工作经历,运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适应”理论探寻赛珍珠农村书写意识和跨文化创作意愿形成的根源,尝试从新的视角解读赛珍珠早期的跨文化创作。随着赛珍珠在中国大地生活印记的逐渐消失,这段暂居宿州城乡的历史珍贵记忆永远值得我们时刻探寻、回望和铭记。
一、跨文化适应的特殊群体:来华传教士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理论,也是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跨文化传播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国内的传播学领域指“跨文化传播”,外语界称之为“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传播正式创建于20 世纪5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的出版标志着该学科的诞生。 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末国内学者才开始陆续关注。 “从宏观上看,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涉及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如何形成,以及交流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鸿沟等多个层面。 ”[5]
跨文化适应的重点是“跨”,当个体进入陌生的异质文化世界,要跨越不同的种族、地域、文化、语言等多方面障碍,促成与“他者”的顺利交流和沟通。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的就是个体或群体在适应异质文化世界时的互动过程。跨文化适应研究对象一般分为两类: 一是长期居留在异质文化世界的群体,如移民和难民;二是短期居留者,即“旅居者”,如留学生、外派人员和旅行者等[6]。 西方来华传教士作为短期的旅居者,是跨文化适应研究的特殊群体。 传教士来华是以传播基督教义为主,实现中华归主的伟大目标,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印记。“从人类漫长历史长河来看,基督教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过程,对整个人类的跨文化交流进程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7]。 随着对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们文化身份和文化交流作用的认识加深, 上世纪80 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殖民侵略范式略显片面化,过于凸显研究的政治化视角。 从上世纪80 年代后期,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转变。 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及中西文化交流上[8](P7)。 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跨文化适应行为和调整策略,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据统计,“1920 年,在华外国传教士共有6 636人,其中来自美国的就有 3 305 人”[9],居欧美各国传教士人数之首。 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中,女传教士约占三分之二,赛珍珠即是其中一员。长久以来,赛珍珠并不认同自己的传教士身份,她一直对来华传教持反对态度,后期又公开与教会决裂。 赛珍珠即使不是一位正统的美国传教士,但无疑是位教会人士。 她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来华传教士群体里,从事与来华传教相关的活动, 曾多次在教会学校任教、在教会医院协助工作等。 因此,本文借用杨慧林教授的“准传教士”赛珍珠的说法[8](P2)。 赛珍珠的一生与美国传教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张春蕾所言, 传教活动像是赛珍珠身上无法磨灭的胎记[10],使她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观和多元宗教立场。刘丽霞认为,在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中,赛珍珠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传播媒介,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的热爱和传播,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层面“之间人”角色[11]。最重要的是,由于和美国农业传教士布克的第一次婚姻,赛珍珠才突然闯入了皖北大地的农民世界,正是传教活动使赛珍珠有机会踏入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鲜为外人熟知的皖北社会,找到了摹写皖北乃至全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绝佳蓝本。
1915 年, 出身美国农民家庭的约翰·洛森·布克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不久主动向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申请, 想以农业传教士身份去中国,被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委派到皖北宿州。 因宿州距南京仅二百英里,是种植小麦的穷地方,那里有一条刚竣工的铁路[3](P62),这里才会成为布克在中国的农业试验区。美国南北长老会是美国基督教在江苏传教的主要差会,从临近上海的苏州开始,在苏南、苏北地区逐渐发展传教事业,主要是沿大运河方向、在铁路建成的城市推进[12]。 赛珍珠之父赛兆祥便是其中一员, 是南长老会在苏北传教的先行者,先后在淮阴、宿迁、徐州等地传教,幼儿时期的赛珍珠和全家人随父亲多地辗转。皖北的传教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894 年, 驻南京的基督会和长老会派传教士到皖北地区考察,后选定涡、淮两水交会的怀远为皖北传教中心[13]。 1901、1902 年,柯德仁、柯德义兄弟先后来到怀远传教。 1907 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派遣美籍人罗炳生(Robistine)至宿城传播基督教[14](P7-8)。 美国传教士贾德(Cater)夫妇在宿州大河南街东段出资兴建了基督教堂(福音堂)。 贾德是柯氏兄弟的表兄弟, 在宿州还创办了含光初级中学。 1916 年,赛珍珠在传教士云集的庐山牯岭小镇度假时,结识了从事农业传教的美国青年布克。二人成婚后, 赛珍珠向教会申请以传教士妻子身份协助丈夫工作。 布克和赛珍珠便成为贾德牧师负责的宿州教会成员,暂住在大河南街福音堂教会大院内。
赛珍珠到皖北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尘土漫天的泥土地和灰头土脸的当地人[15](P144),这与她从小生活的秀美江南和学成归来的现代美国截然不同,对她来说是一片陌生到丑陋的景象。当时宿州教会的传教士们大多难以接受此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困落后的社会现实,纷纷离去。“有一样东西总是把赛珍珠和传教使团的其他人区分开”[16](P86)。 第二年开春时,“所有景物忽然在一夜间变得美丽了”[15](P145)。只是春天美景吸引了她的眼球和季节转换改变她的看法吗? 正如赛珍珠坦言,她颇费了些时间来适应这灰蒙蒙的丑陋景象[15](P145)。 赛珍珠不仅能坦然接受这个陌生到无法想象的世界,还在作品中真实地展现了皖北农村的生活现状,把这方积贫积弱的土地变成全世界读者心目中魅力无穷的“Good Earth”——“福地”。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从事文学活动,采用文字传教策略由来已久,特别是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多方创新。如1919 年《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汉译成功,促进了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民众中更大范围的广泛传播,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催化作用[8](P106)。 此外还翻译了基督教的圣歌、圣诗,创办了多种教会期刊,特别是极有影响力的《教务杂志》,译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刊发传教士们的文章,赛珍珠早期曾在这类刊物发表过多篇短篇小说。很多传教士也进行文学创作,而且作品“带有丰富的感情、旺盛的想象力和感人的力量”[17], 有些还颇具影响。 总体上看,西方传教士的文学创作大都以汉语为载体,为在华传教事业服务,作品带有明确的宗教教化作用。赛珍珠的写作完全不同,她是以英文为载体、以西方读者为受众群体的, 向西方世界展现她所看到的真实中国。 赛珍珠与众不同的跨文化创作意愿和书写方式与她在皖北宿州的文化适应经历是分不开的。
二、赛珍珠的汉语优势和交流意愿
跨文化适应是个复杂问题,也是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没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万能模式。 要想很好地融入异质文化环境,个体最好先具备基本的适应性条件。 单波教授提出,社会文化适应首先需要的是互惠性的文化知识和积极的 跨 群 体 态度[18](P132)。这里互惠性的文化知识一般指跨文化适应中必备的语言文化知识和交往技能。跨文化适应必须通过交往才能实现,交往本身就是文化的交流。“适应者与东道国成员的交往实际上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19]在文化交流中,语言的作用首当其冲。当文化交流转向更深层次时,可能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表象的语言沟通,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汉语是来华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必备工具,而差会早就意识到汉语能力对传教士的重要性。 从19世纪末,开始设立语言考核制度,要求传教士必须通过汉语考试才能留任[20](P115)。因此,学习汉语是传教士们到中国后的必修课。大多数来华传教士都精通汉语,他们为了掌握汉语,费心尽力。赛珍珠父亲赛兆祥热衷汉语学习,来中国的轮船上还一直在研习汉语。 他的汉语水平极高,能娴熟地用汉语布道和写文章,还试图把《圣经》翻译成通俗的汉语版本。 “汉语对他来说比他的母语还母语——因为他说汉语的时间要多得多”[21](P219)。赛珍珠丈夫布克会说的汉语很有限。 作为农业传教士,他经常要到农村做农业调查,赛珍珠必须随行充当翻译。 在皖北农村的田间地头, 赛珍珠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庄稼人,和耕作的农夫谈收成,和农妇们聊家常,和孩童们逗乐。 赛珍珠能和皖北农人们顺畅地交流,极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汉语优势和宿州方言的南北杂糅性质。 赛珍珠从小生活在镇江普通民众中,接受了当地私塾老师孔秀才的多年悉心教导,对中国语言文化有很深的领悟, 她自身的语言优势是跨文化适应的优越条件。虽然赛珍珠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但不说南方的吴侬软语, 却说着一口北方口音的官话。 当她来到宿州后,“他们幸好也讲官话 (北京方言),我只稍微纠正一下几个发音,就能与他们顺利交谈了。 ”[15](P148)其实,宿州人和镇江人在讲话方式上有极大的不同。镇江人讲话时,音节在唇部和舌头后部都可以进出, 但相对封闭落后的宿州农村生活节奏慢,农民们讲话也慢腾腾的,低沉的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16](P76)。 皖北宿州位于淮河中游,“地处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带”“兼受南北方言的影响”[22],在这里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交错并行。 当时皖北地区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文化教育事业几近停滞,民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赛珍珠在宿州城区居住时结交了不少好友, 有的出身名门大户却目不识丁, 更不用说那些整日在泥土地上挣扎谋生的穷苦农民了, 他们使用的语言必然是最原生态的方言体系。 赛珍珠能够和社会最底层的村妇农夫顺畅交流,从而真正体会到农村生活的本质面貌,部分原因可以归因于宿州方言的南北交融特征。
赛珍珠除了具备能够相互沟通的语言条件外,另一个优势就是双方都有和对方交流的意愿。一方面, 皖北地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之间的交融地带, 一直处于南北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前沿阵地,当地人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如赛珍珠所言,“他们性喜结交,又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充满好奇”[15](P148)。 赛珍珠后来发现,这里人很风趣幽默,性格无拘无束,与江南人不一样[15](P150)。的确,皖北人的性格兼具了南方人的柔软细腻和北方人的粗犷豪迈。由于长期生活在灾害频发的黄淮之间,他们对于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不幸,擅长用机智和玩笑化解,不失为一种难得的生活智慧,颇有老庄遗风。另一方面,赛珍珠转变了早期“异乡人”“异邦客”的心态,十分乐于与当地人交往。这里赛珍珠的态度转变是与其他来华传教士们最大的不同。很多来华传教士们一直对中国民众抱有偏见,赛珍珠周围传教士们也是如此。 他们一直生活在与当地居民隔绝的教会大院里,抱怨当地环境的脏乱差和民众的愚昧无知,对当地人避之不及,很少愿意与他们交往。 如赛珍珠夫妇最初居住的教会大院里,有一对美国医生夫妻,“但那医生的可怜的妻子憎恨中国人, 绝不愿走出家门一步”[15](P146)。 赛珍珠并不是第一个到皖北宿州的来华传教士,却是众多皖北人亲眼见到的第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在跨文化交流中,旅居者自身的心理意愿严重影响着适应过程和适应效果。“居留者在思想动机和心理倾向上是否愿意与新环境交流,会影响其对信息反应的敏感度、行动的持久性和对交流障碍的耐受能力。 ”[23]赛珍珠凭借自身优势和个人意愿, 与当地人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三、赛珍珠的教会工作和社交能力
有了文化适应必需的语言条件和情感意愿后,接下来就要落实到具体的跨文化适应行为上了。“塔夫特区分了两种关于适应行为的能力: 一是技术能力,二是社交能力”[23]。技术能力就是个体承担社会角色必备的行为能力,如技术、服务等;社交能力则是个人的人际交往能力。赛珍珠作为宿州来华传教使团的一员, 参与传教的相关工作是职责所在,也是快速融入当地环境的有效手段。 当时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不只是宣扬基督教义,还采取了教育、医疗、文化等多种助教传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东西方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大门。
赛珍珠首先加入了宿州教会学校启秀女校的教学工作,和美国传教士玛丽安·加纳德一起工作。她俩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无话不谈。1918 年,玛丽安结婚后返回美国,留下赛珍珠一个人负责宿州教会学校的教育工作。 她还主动招收当地的文盲妇女,教她们学习文化,私底下对学生们认真负责,和蔼可亲,学生们都和她相处融洽。 赛珍珠在宿州教会学校的工作正是当时来华女传教士的普遍做法。“美国女传教士来华前约有70%的人当过教师,因此对她们来说教育传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24]在当时女传教士的传教工作中, 除了教育传教外,还有送医送药、收养孩童等方式。 赛珍珠在自传中提到过,她曾充当过教会医生的助手,给中国产妇进行剖腹产手术, 还试图挽救隔壁上吊的媳妇、收留过流浪的乞讨儿童等。赛珍珠母亲凯丽也一直在践行着上述行为, 她曾收养过一名中国女孩做义女,是赛珍珠的义姐。 赛珍珠看似在完成当时来华传教群体的例行工作,而正是这些教会日常工作加快了她与当地人的人际交往,加深了她对暂居地异质文化环境的了解。 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暂居者与异质文化成员接触越多,就越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越能尽快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中。
作为宿州教会的重要成员,赛珍珠借助其传教士身份, 还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以至于现在外人都无法深入了解的皖北社会,“走进白人不曾到过的家庭, 访问千百年来一直住在偏远城镇的名门望族”[15](P155)。 她充分发挥了社交能力的优势,结识当地的不同阶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赛珍珠和两位邻居张太太、吴太太交往亲密,走动频繁。张太太是宿州城里大户人家的当家主妇, 娘家姓周,知书达理,性格豪爽,本来信仰佛教,后皈依基督教。张太太能力非凡,提倡女子读书,曾创办宿县女子第一小学,支持赛珍珠教会学校的工作,是赛珍珠念念不忘的良师益友。 吴太太温柔聪慧,见多识广。赛珍珠开始享受这深厚纯真的友情,“她们是那样精于生活之道,我很爱听她们说话。 ”[15](P150)赛珍珠从两位芳邻处见识到中国家庭相处的智慧和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原则,在小说《东风·西风》、《庭院中的女人》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四、对皖北农民的移情和认同
旅居者随着与异质文化成员交往的加深,会逐渐对异质文化生活有更深刻、 更客观的了解和评估,而不再以最初的价值体系评判他人。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他们会逐渐淡化双方交往中的文化差异性, 尝试寻找双方文化中的一致性和共通性,以期更好地交流与沟通。因此,跨文化适应发展到高级阶段就产生了跨文化认同[25]。戴晓东分析了多位西方学者的跨文化适应理论,提出跨文化认同理论。 “任何形式的跨文化认同都需要地方文化的支撑。”[26](P220)地方文化是本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积累和沉淀,有鲜明的地域差异特性。 赛珍珠在此体验到有别于江南水乡和美国社会的皖北文化语境,在跨文化适应和跨文化认同过程中培养了跨文化书写的敏锐性。
虽然赛珍珠在镇江生活时见过田里耕作的农夫,但她对乡村生活的记忆停留于江南水乡纵横交错的碧绿稻田或等待收割的金黄稻谷,多是以旁观者、俯视者的视角去欣赏、赞叹田园生活的浪漫,那只是对中国乡村生活诗意化的想象,“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人想象中诗意中国的土地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27]周宁教授认为,这体现了传教士们代表的当时美国 “恩抚主义”的政治态度。但是赛珍珠见识过皖北宿州农民生活的真实面貌后,她对中国农村的印象不可能还只是诗意的想象了。 宿州地处黄淮大平原的南端,境内河流均属淮河水系,河流众多,地势平坦,本应是地肥水美的鱼米之乡。 自唐宋以来,此地一直是兵家争夺要地,饱受战火之苦。 明清以来,黄河多次南泛,夺淮入海,淮水被迫改道,河床淤积,人为的因素又使此地缺乏必要的水利设施,造成了“雨多则涝,雨少则旱,十年倒有九年灾”的灾害现实。 近现代以来,淮河沿岸的皖北农民们几乎遭遇了所有的天灾人祸:水旱灾害频繁,军阀连年混战,匪盗猖獗,地主盘剥。 赛珍珠在陪同布克到皖北乡下调研时,他们到过宿州多地的乡镇、农村,如符离集(今宿州市埇桥区辖)、濉溪口子镇(今淮北市濉溪县辖)等,亲眼见证了当地农民的困苦生活。这里到处是破旧低矮的茅草房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农民,还有一个个泥污里滚爬、啃着沾满灰尘的瓜果、光着身子、搞不清排行老几的农家小儿。她和农夫讨论田里的庄稼收成,和农妇们闲聊些家长里短,和浑身脏污的小孩玩乐。赛珍珠真正深入到中国农民阶级的底层,了解了中国农民身上的苦难和悲情, 曾感慨:“这是在我童年之后最深入中国百姓的时刻。 ”[15](P146)。
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旅居者一般会从工作和社会交往开始,逐步融入到异质文化体系中,而双方情感的互通或移情是最难达到的。 “移情能力指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 体会对方的需要,在思想上与他人取得认同。”[23]要想达到移情是极具难度的,这要求居留者不仅能够深入到异质文化体系内部,亲身体验和感受,并能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与异文化成员的多层面交流。 更重要的是,外来者还要在了解异质文化的同时,对自己的母体文化进行反思,透过文化差异的表层现象,看到双方文化内在隐秘的精神实质。
赛珍珠在皖北宿州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到城外村庄里穷苦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 ”[15](P156)同样是看待尘土满身、土里刨食的农人们,赛珍珠不再觉得他们灰头土脸、千面一色了,她在《大地》中满含同情和赞美地描绘了在土地上辛苦耕作的农民。 王龙和阿兰带着头生儿子在田里干农活,在晚秋依然毒辣的太阳暴晒下,“女人和孩子晒成了土壤那样的褐色,他们坐在那里就像两个泥塑的人。 女人的头发上、孩子柔软乌黑的头顶上,都沾满了田里的尘土。 ”[28](P38-39)这生于土、长于土、死后又归于尘土的生活方式不正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吗?赛珍珠开始真正理解中国最底层的农民阶级,他们并非都一直良善,有时很残忍,像《大地》中的阿兰,在饥荒中亲手掐死了刚产下的女婴。阿兰心里自然是悲痛万分,“她不单是为自己的行为而悲痛,更为自己被逼到如此地步而悲痛”[15](P156), 那是灾荒现实逼迫她不得不那么做,即使是女婴留下来,在饿殍遍地、疯传“人吃人”的灾荒年景中,根本无法存活。 《大地》中的灾荒书写十分精彩,中国农民面对灾难时的坚韧不屈赢得西方读者的感动和认同,这首先归因于赛珍珠对皖北灾害现实的亲眼目睹和感同身受,才能从皖北这块灾难重重的土地上看到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
赛珍珠真正感受到皖北农民的艰难困苦和坚韧不屈,为这最特殊的群体——中国农民发声成了她的写作初衷,“正是为自己直到今天(1953 年)仍热爱和景仰的中国农民和普通百姓而积郁的愤慨,驱使我写下了这个故事”[15](P280)。赛珍珠在南京开始创作《大地》时,没有把故事背景放在富裕的城市,而是选取了偏僻的皖北农村。在赛珍珠笔下,王龙之辈的皖北农民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类, 没有被美化和掩饰,他们具有勤劳善良、智慧勇敢的美德,也有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人性弱点。他们身上没有伟大和崇高,只有对土地的尊崇、命运的抗争、生活的向往和生命的热爱,这才是人类生活的本真状态。
五、结语
来华传教士是处在中西关系中的特殊人群,尤其是在中国出生、成长、生活很长时间的这一批人,他们在中国的生活轨迹、对待中国的态度、传播中国印象的影响、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赛珍珠作为皖北宿州传教使团的普通一员,依托宿州的短暂寓居经历开始了跨文化创作之路。一方面,赛珍珠突然闯入陌生的皖北社会后,没有被皖北大地贫瘠落后的外表吓倒,反而借助其教会人士的特殊身份,深入皖北乡村,打破原有狭隘偏见,反思和重建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全面认知,带着尊重、 欣赏、 交流的态度发现了这块土地上独特的魅力,培养了跨文化书写的敏锐性和创造力,从此开启了别样的精彩人生。 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皖北一直是被遗忘、被牺牲的角落,贫困落后像是摘不掉的帽子,在“异乡人”的眼里,这些苦难现实却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光芒。在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在本土文化集体失语的状况下,一个“异乡人”用英语向西方世界讲述了一段真实的皖北农家往事,使多灾多难的皖北大地成为全世界读者心目的“福地”。
同时, 跨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问题,是一个从对立到统一的动态发展和双向发展的过程。个体对异质文化环境的适应和异质文化主体对个体的接纳、包容是同步进行的。 文化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不可能完全孤立地产生或成长,只有通过双方不断地联系才能实现全面的发展或达到一种完成的状态。 ”[29]赛珍珠皖北文化的适应过程可能会折射出如今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遇到的困境和挫折。文化对外传播并不是单纯的“送出去”或“拿过来”,必须要有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互动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都要不断做出调整和自我改变, 力求达到对异质文化的尊重、理解、适应、认同的理想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本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