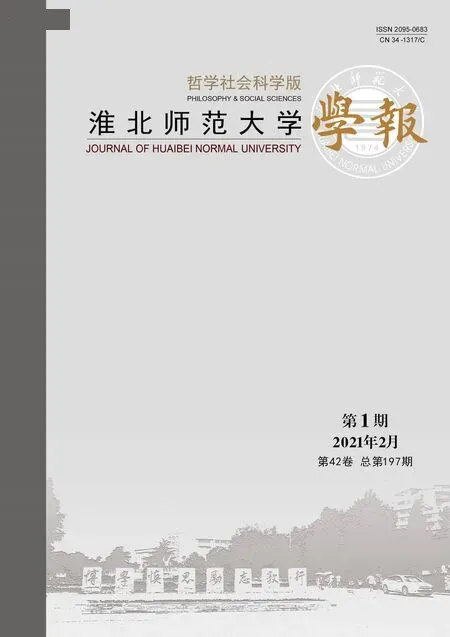原生态·散文美·哲理性
——牛汉源自生命的诗歌语言风格
乔军豫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354300)
牛汉被誉为诗坛上的“常青树”,在漫长的诗歌创作道路上艰辛跋涉,留下许多壮丽的诗篇和丰富的诗学启示。他在诗歌界长盛不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那闪烁着生命光泽显现出独特风格的语言。牛汉诗歌的语言展示他的诗歌理念和创作理想,是当下诗坛可资借鉴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从中总结得失、汲取经验,促使诗界去思考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诗学问题,诗歌如何从语言上摆脱“诗将不诗”的尴尬境地,诗人如何来建构自己的话语方式,诗歌如何走出口水化的误区,诗人如何在“个人化”的创作中,实现“自足性”“审美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牛汉的诗歌依然是诗坛上的一座灯塔,照亮了当下诗歌创作,为诗歌界提供了珍贵的写作经验。
一、鲜活的原生态
牛汉的诗歌语言呈现原生态,富有鲜活的诗性特征。诗人不事雕琢,不刻意遣词造句,却能收到一种意味深长的效果,给人以心灵的震撼。牛汉诗歌创作的悖论就在这里,恰恰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是与他的个体生命追求及其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生性倔强,宁折不屈不知变通,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依然不改本色,始终保持赤子之心,始终保持原生态的生命气质,始终追求生命的鲜活度,一辈子与诗相伴。牛汉曾认为作诗不是为了返回童年世界,而是为了创造一个童年世界。当然,这个童年世界指的是诗的世界。这意味诗人有生命的激情,崭新的眼光,好奇的心理,乐于进行新鲜的生命体验,在诗歌里找到生命的“栖息地”。他在《旧作和断想》中阐明诗歌创作与其本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有时亲密无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情况下诗生成得十分“痛快”;有时语言也跟诗人产生隔阂,诗人听从语言的召唤;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诗人和语言处于一个共同的梦境里好像听到远方的应答,望见一片令人神往的美景,双方情不自禁找到共同的契合点。[1]诗人似乎得到一种神助,笔底生津,诗意盎然。对牛汉而言,语言不是刻意追求、反复推敲出来的,贾岛式的苦吟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语言的生成与诗人的心灵感悟和生命体验是不可分割的。牛汉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不停地同生命进行对话、交流,语言为诗人的个体生命和被纳入创作视野中的生命“筑路搭桥”,成为生命的律动与共振的出口。呈现出原生态的特点。
牛汉和语言之间是一种真诚的“对话交流”关系,语言自身得到诗人的积极响应,诗人喜欢用“母性的虔诚”“生”“生成”“生命感”“旺盛的繁殖力”“分泌能力”“原生的状态和声息”等词语来书写他创作时获得最佳诗意的真切感受和心得体会。在诗人看来,“母性的虔诚”“生”“生成”“生命感”“旺盛的繁殖力力”“分泌能力”“原生的状态和声息”意味着一首诗从触发、酝酿至诞生的过程,仿佛一个“自在的生命”的降临。[2]当然,这个“自在的生命”需要凭借语言才能“着陆”,因此,就不能使用那些陈词滥调。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扼杀语言的“分泌能力”,就会消解语言的创造力,甚至泯灭诗歌鲜活的生命。诗人将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巧妙转化为活泼生动的语言,它携带生命的热气和活力,牛汉亲切地把它视同自己的“孩子”。正如牛汉所言:“每个字、词语,都是我生的,不是从传统的词典中取来的,我的散文和诗,没有取来的文字,都是我生成的,属于这个即将诞生的(艺术)生命所应有的。”[3]诗人在创作《三危山下一片梦境》有刻骨铭心的感受,诗中“艰难喘息”的语言与节奏跟诗人的情感亦步亦趋,喻示牛汉诗歌语言生成的显著的特色。牛汉在创作《麂子》一诗明确提出诗里的“结语”完全是对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的审视和谛听,即诗歌“自在的生命”的必由路径。一只美丽可爱的麂子闯入诗人的视野,诗人观察得格外细致。麂子在一片金黄的麦田里“似飞似飘”时,宁静祥和的气氛骤然凝聚,呈现一幅和谐美观的自然图景。可是当诗人敏锐发现埋伏在草丛中的猎手用阴森恐怖的枪口对准这只灵巧的麂子时,心弦一下子绷紧,一声发自内心的话语脱口而出,也自然安排成了诗的结束语:“哦,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麂子》)诗人的语气紧凑而急促,似乎内心的焦灼要爆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诗人极端的生命体验和表达习惯同生共存同气相求才产生的一种言说方式。牛汉反复强调语言来自生命本身——生命内蕴的抒发和灵魂的歌唱,独具“原生的状态和声息”。诗人对诗歌语言有一种原始、自然的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看重直接的、原始的反应,要的是那种热腾腾的、刚蒸出来的语言,读来神完气足,富有音乐性,像一场豪雨一气呵成,而不是断断续续的、零零散散的。”[4]
牛汉不断探索、拓展诗歌创作的空间,在“创作”“写作”“创造”等一系列专业术语中,他更青睐“创造”这个更富有内涵和生机的词语,这一措辞态度从侧面反映出他对“原生态”创作原则的坚持和追求。诗人在《学诗手记》里表明,每创造一首诗,都像是首次,那些苦苦经探索取得的情景、意象、韵律等,都是完全陌生的,仿佛闯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乡。[5]牛汉创造的情景、意象、韵律等与众不同,别人难以仿照,也难以比拟。每一首诗的创造与诞生都是一次生命体验的完成和告别,与他追求诗歌原生态创作原则相一致。诗人格外注重原生态的语言,把创造出来的崭新的语言组合在一起,产生意想不到的效应。这是其创作风格的一大体现。在牛汉诗歌语境中,首次创造与诞生的语言指的是非逻辑化工具的语言,“生成”“生”“生命感”“原生的状态和声息”等词语反复出现,用以表达诗人对充满原始创造力、“旺盛繁殖力”的语言的渴望和向往。语言的“旺盛繁殖”使牛汉的诗歌成为一个庞大的语言生产基地,扩展了语言的主体性,有效地吸引读者把注意力放在生命形象的塑造上。牛汉杜绝在语言上耍一些花招,常常采用直接切入的言说方式,建立自己的诗歌坐标。现举《我的家》一诗略作解释,“我要远行……//妻子痛苦/她不能同我一道/离开郁闷的南方//……妻子希望/我把出世十个月的孩子带上/她一再说/孩子诞生在地狱/让她到一个自由的旷野生长去吧。”这首诗较短,出现了诗人常用的字眼“诞生”“生长”,一下子把诗人倡导的诗歌精神联接到生命本身,与此同时,语言也就自然而然表现出“原生的状态和声息”。
牛汉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对诗的超常理解,使用“原生的状态和声息”的语言,创造出一条宽阔的诗歌江河,展示了诗人、诗歌、语言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他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的诗歌,冒着热腾腾的充满原始的血气,闪着晶莹透亮的现实感。牛汉在生活的激流中摄取生命的浪花,裹挟着动荡不安的情绪,表现或再现生命真实的情态。只有生命进入旺盛、饱满的状态时,才可以把诗的创造与诞生视为一个“自在的生命”,才能懂得他的语言只能是和诗的生命同声相应、和谐相生的语言。这充分体现了牛汉对诗歌本质把握和理解的独到之处,为诗人冲破语言牢笼而走向“原生态”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在牛汉看来,既然诗的创造昭示“自在的生命”的生成,那么表现诗歌生命的语言就有了其“自在”的生成规律。外在的任何强加给诗的语言都难以“天作之合”般地契合诗人的心灵,难以接近生命的本真,难以将活泼的诗的生命“接生”出来。因此,要解决诗歌语言和诗人之间的隔膜或冲突,促使二者达到和谐共存的境界,就必须走出把语言当作可以任性使用的工具的误区,尊重语言的自在性和生成性,让语言带有生命的热力,在生命里创造出来,语言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语言,成为鲜活的语言,生命成为富有语言特色的生命,成为创造的生命。这样,既保持了诗歌语言和诗人个体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也运用了诗歌作为独立生命在诞生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内在的生成规律,使诗的语言具有鲜活的原生态的特点,具有了生命的质感。
二、自由的散文美
“诗人首先是一位热爱语言者”[6],是天生的言说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7]这一论断在20 世纪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广泛的论证,人文学者热情而大胆地进行语言方面的探索。语言正是运用语法规律、法则构建,各个词汇组成不同的语句,表达不同的意义。毋庸置疑,语言是生命存在的家园,也是诗歌存在的第一要义。海德格尔始终坚持赋予语言以文本论意义,将“诗意与语言”两者的关系列入现代诗学的研究日程。诗人在语言里思考并获取存在感,沿着语言的线索找寻方向感。诗的活动领域凭借语言展现,要认识和理解一首诗须从语言处入手,从语言处打开一个窗口,让诗歌的生命世界和诗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完整体现。从审美本体上讲,诗是存在着的词语性创建者,诗歌语言保持着诗的本质属性。诗歌语言表现诗人的审美情趣和心理习惯,在主客观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下,牛汉自觉选择了诗歌语言适合自我性格的表达方式,呈现了散文的风格。散文不需要太多的修饰,不需要涂脂抹粉,需要的是健康,充满自由、散漫的气息,需要的是不徐不疾的笔调。牛汉诗歌的语言质朴无华,疏放自由,不怎么受韵律的限制,句子长短不一,于不规则处迸发出强烈的情感,于不经意处生成一股撼动心魄的力量。开阔的气势、无拘无束的体式以及散文美的语言,使得牛汉的诗歌具有了较大的松散度。
牛汉诗歌的语言散文美十分明显。我们不妨将他的《爱》这首诗作为例子来探讨一下。《爱》不再分行后稍作合并就变为:
小时候,妈妈抱着我,问我:给你娶一个媳妇,你要咱村哪个好姑娘?我说:我要妈妈这个模样的。妈妈摇着我,幸福地笑了……
我长大之后,村里的人说:妈妈是个贫穷的女人。
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没有向家人告别(那年我只有五岁,弟弟还没有断奶),她坐着拉炭的马车,悄悄到了四十里外的河边村。村里的人说:妈妈闯进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
从此,远村近邻,都说妈妈是个可怕的女人。但是,我爱她,比小时候还要爱她。
《爱》本来是一首叙事诗,用叙述性的语言将诗人的主观情感和外在的客观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母子之间的依依惜别的深情不是直接抒发出来的,而是以记叙的方式和手段娓娓谈出。朴素的诗句浸透着诗人的血泪和对母亲真挚炽烈的爱与眷恋,平实的语言充满着诗人对屠杀母亲的刽子手无比的愤慨和憎恨。通过举例说明,显而易见,《爱》这首诗如果取消分行的排列后就不折不扣成了一篇叙事散文了,并没有影响抒情效果,依然声情并茂,依然催人泪目。牛汉诗歌的语言的散文美的程度之深从中可见一斑。下面从五个方面来探讨牛汉诗歌语言散文美的原因。
(一)牛汉倔强的性格和强烈自尊的心理影响着他的诗歌语言。他一生不受拘束,天性刚烈,不服输,不拘泥于常识,力求自由创作诗歌,从不让自己陷于某一模式中,率性且大胆摈弃不利于自我表达的种种章法和规则,几乎没有固定不变的诗节,节与节的安置不是从诗歌建筑美学的角度出发,而是根据自己情感的起伏变化而设置的。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句。因此,散文的元素基本都具备了。牛汉诗歌的章法的建构随着生命的体验、内在情感和诗歌生命力本身彰显的需要而自如变化,诗歌自由精神的张扬和自由意识的流露很明显体现在语言艺术上。
(二)牛汉诗歌的语言本身质朴平易,显示散文美。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和创作体验的积累,牛汉的诗风“内转”,于质朴中充溢着丰沛的情感,于平易中蕴含着深切的关怀。诗人首先“内转”,转向生命本身,转向诗歌艺术本身,突入生活的底层揭示生命的内蕴,把生命与诗歌融合在一起,创立一种独特的诗歌生命美学范式。牛汉的诗歌里饱含生命的痛感,其中蓄满生命的纠结和苦涩,诗人礼赞高贵的生命,然而魑魅魍魉却纠缠周身;诗人追求生命的尊严,然而恶势力却胁迫他低头;诗人想在诗里饱满生命,然而风浪却把他冲向生命的荒野。愈是纠结和苦涩,就愈是对生命难以割舍,诗歌生命里的痛感是诗人苦难人生的隐喻,在隐喻和暗示中,人生之苦便有了深度和广度。同时,再加上其本身具有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诗人生命中的苦难叙事的效果达到极致。这种真切的感受通过质朴平易的语言表现出来,如《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一颗挂在树梢的枣子“红得刺眼”,人们站在很远的地方就能望见它。因为满树的枣子,一色青青,唯有其中的一颗满身通红。遗憾的是它不是长到成熟自然红,而是一只小虫子钻进去噬咬的结果——一夜之间被逼迫变红。这首《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的诗的语言通俗易懂,平常的词汇无一新奇地搭配在一起,诗意由此陡然生出,使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诗人生命中的痛楚和对生命无情流逝的缅怀。在《春天》里,诗人怀着对生命的无比热爱连续抛出了几个疑问:没有花吗?没有歌吗?没有火吗?没有热风吗?接着又分别一一作了回答,花在积雪的树枝和草根间生长,歌声在生命的内部里奏响,火在冻结的岩石间燃烧,热风正由南向北徐徐吹来,不是没有春天,而是春天就在冬天里,冬天还没有“溃退”。诗中选取“花”“歌”“火”“热风”这些跟生命有着密切关系的美好字眼,用平易近人的格调、和蔼可亲的语气向读者道出了春天的秘密和妙处,跳动着生命的脉搏,散发出生命的朝气。在牛汉的笔下,春天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季节,还象征着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冬天还没有“溃退”,春天怎么会来?等冬天“溃退”了,春天就必悄然而至。这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中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牛汉的诗歌朴实自然,亲切如同话家常;没有斧凿的痕迹,没有华丽的藻饰,一如他的人一样质朴真诚,平易感人。诚乃文如其人,言为心声。
(三)牛汉善于选用形容词和感叹词入诗,旨在使诗歌运行的节奏缓慢下来,语言因而就具有了散文美的特质。诗人在《二分硬币》中写道:“小小的硬币/在春天的阳光下/显得异常的苍白/是饥饿的面孔/是瞪得圆圆的眼睛。”短短的一节出现了“小小”“异常”“饥饿”“圆圆”等形容词,集中而强烈地描写了农民在旧中国曾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形象地表达了新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信心和希望。《一只跋涉的雄鹰》里使用了多个的形容词,“灰灰的/一望无际的荒漠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没有雷/没有闪电/充塞于天地间的只有浮尘/是沉默而混沌的时间/也是沉默而混沌的空间/外形多么像湿润的雾气/但它是干热而焦渴的/绞不出一滴水/它是一个窒息生灵无法解脱的噩梦。”这首诗开篇第一节出现了多个形容词,它们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读起来速度就变得缓慢了,节奏感减弱了,散文的格调就显露出来。同时,这些形容词在场景的设置上也发挥了优点。苍茫的荒漠不再意味着荒凉和混沌,反倒喻指为压在生命之上的一座大山。残酷压抑的生存环境,从侧面烘托出鹰躯体的渺小、行动的艰难、处境的凶险。视觉上形成的强烈的反差烛照出鹰孤军奋战的勇敢和雄强坚韧的反抗斗志。《眸子,我的手杖》里的形容词比比皆是,一切的诱惑,在眸子的透明的海里……苍白地腐烂了,像黑色的蝙蝠,蜷缩在阳光下,那里冷酷的孱弱者,在眸里的火苗里燃烧。只要我们目及诗人创作的具体场域,就会发现“苍白”“黑色”冷酷”等形容词盘踞在诗行里,正释放着语言的威力,不仅强调诗人所处的环境的恶劣,而且也揭示出诗人内心世界的忧伤和苦闷。《汉江和我们一同朗诵诗》里接二连三使用形容词,汉江跃动青色的嘴唇,哗啦哗啦吹着歌曲,我们几个亲爱的诗友,像青蛙敲着锣鼓蹲坐在江边,我们紫红的脸闪着光芒,紫红的大嘴巴喷出响亮的诗句。可圈可点的形容词让诗的节奏变成了散文的节奏,从高度的凝炼到疏放自由,如同一个腰被紧紧捆绑的人一下子把绳子松开了。汉江奔放豪爽的本性也就一览无余地跃然纸上。《鄂尔多斯草原》使用了多个感叹词,诗人慷慨大方地写道,向着远方,我的歌滚滚地奔流……发散着绿色的气息呵。我的歌,亲吻着那无边的草原的音浪——牧笛吹出的原始的粗犷的歌音呀。从草丛中,沙窝里,大风沙灰暗的门槛里,马蹄卷来的牧歌呀。羊的、骆驼的、牧狗的铃声呀……诗句多处使用了感叹词,语气响亮,格调活泼,情感强烈,毫无保留地表达诗人对草原的歌颂和赞美。同时,也是一种生命力的张扬与流露的助推剂。诗句中每“呵”“呀”一下,都要停顿一次,这样,诗歌节奏放缓,就有了抒情散文的味道。整首诗如果不分行将句子并拢在一起,就可能会出现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这究竟是一篇抒情散文,还是一首诗?迷惑度大,又可能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答案。总之,形容词和感叹词的巧妙使用,让诗的语言具有散文的特点,使语言在自由松散间有了更深的韵味,有利于诗人相应的情感的表达和强化。
(四)牛汉常用描述性的语言入诗,呈现出散文美。描述性的语言是比较详尽地写出事物的状态和事情发生的始末,其特点是对事物的细节及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较为详细而全面的描述,一般字数较多,对判断性的语言和分析性的语言起补充阐释作用,往往对事物的状态和事情的发展能够作出更为有力的证明。描述性的语言在诗歌中使用较少,一般用在小说中,在小说创作中占主要地位。但是,牛汉另辟蹊径,将描述性的语言大段引入诗歌,自有千秋。《彩色的生活》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诗中有这样的描述,商栈寂静凄清如同深夜,从边疆来的客商还没有醒来,正抱着卖淫女子打鼾,左邻右舍的收音机唱起了每个清晨皆唱的歌曲,肥胖的厨师坐在垃圾堆上杀鱼,屠刀淋着血。诗人惶恐地看一眼,想那一条死鱼,如果换成一个人,会不会猛然挣脱跑掉,蹦到天空大喊一声。诗人和伙伴默默地从商栈溜出,看门人的眼睛像狗一样盯住破大衣和露肉的小腿子。牛汉选取一个生活的侧面详细地描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和剥削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有力“证明”了“彩色生活”下的“暗无天日”。
(五)陈述式的语言的大量运用,也是牛汉诗歌的一大特色。陈述式的语言一般多用于记叙文,起着记人叙事的作用。牛汉不吝运用陈述式的语言,使诗歌的叙事成分得到加强,语言散文美的趋势随之进一步加大。如诗《梵哑铃》里讲到一位同志,他酷爱音乐,他对诗人说希望能有一支梵哑铃,每天早晨和黄昏,能奏几曲好歌。陈述式的语言体现在诗人和那位爱音乐的同志的日常对话上。牛汉运用陈述式的语言入诗,现再举一例略作分析。如《在监狱》一诗,诗人写道,在油菜花飘香的春天被关进监狱,他的母亲穿着一身黑布衣裳,从遥远的西北高原,带着收尸棺材钱探监。在监牢,隔着两道密密的铁栅栏,母亲伸出颤颤的手,可是怎么也无法握到儿子的手。母亲懂得儿子的心。狱里与狱外,同样是疯狂的迫害,同样有一个不屈的敢于“犯罪”的意志。这首诗叙事成分多,明确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故事发生的经过及结果,逼真呈现出母子两人在监狱里相见的场景。我们再大胆作一次假设,如果这首诗不以“行列”的形式展示,而是把这些句子前后以“段落”的形式组合起来,即便让一些有经验的学者来判断,都不一定得出我们想要的那个肯定的答案。这些陈述式的语言表面上看似乎累赘,没必要全部入诗,需要大幅度进行削减、锤炼,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无异于削足适履,确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这些陈述性的语言实则强调了时代给个人命运造成的悲剧,渲染了浓郁的悲情,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因此,我们要理解和重视陈述式语言所起到的作用——在铺陈叙述中增大了牛汉诗歌的整个语言的散文美的趋势。
三、哲理性的内涵
牛汉一生苦难相随,苦难源源不断给诗人赋予诗情诗意。“时代带来的厄运,精神所受的创伤之深和心理体验之广,使诗意达到了十分深刻的哲学层面。”[8]诗人在经历人生的大风大浪后并没有颓废消沉,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创作立场,自主性、独立意识、战胜苦难的斗志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他坚守历史的真实和生命的本真状态,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将最大的着眼点和精神关怀置于生命本身,置于尊严本身,从生命深处发掘价值和意义。牛汉在《蚯蚓的血》里指出,一条蚯蚓的生命中只有一滴两滴血,蚯蚓身体渺小,能量似乎稀少。但为了种子能早日发芽,为了阳光下大地的丰收,它聚起浑身的能量,默默地耕耘了一生。诗人说自已身高近两米,浑身的血何止几万滴。然而诗人自惭形秽,希望在自已的脉管里注进一些蚯蚓的血。牛汉向生命的内蕴深挖,向生命的艺境进发,在生命的世界里发现“大写的生命”,并且甘愿如蚯蚓一样辛勤劳作奉献自己的一切。蚯蚓的形体虽然弱小,但精神可嘉,看似渺小的生命却实现了伟大的价值和意义。诗人“别有用心”地向我们诠释的“小”与“大”的关系,并由衷表达了向蚯蚓学习、向蚯蚓致敬的感情。
认识生命,理解生命,让生命走向深刻。认识生命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站在局外观察,用较为理性的眼光看待。不足之处是难以切实感受处于“同一频道”的生命细微的起伏变化,缺少“毛茸茸”“血淋淋”的在场感。二是深入生命内部,以同理之心谋求生命之间的相互融通。缺点是感性偏多,观察和认识有失偏颇。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柏格森将第一种认识称之为科学的或理智的认识,将第二种认识称之为直觉主义。柏格森在直觉和理智之间更多的选择前者,因为他更看重前者在认识生命中所占的地位,所以主张深入对象内部,感受和体验生命的千姿百态和千变万化。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直觉就是一种理性的交融,使自己置身于对象之中,以便与其独特的不太轻易表达的东西契合。[9]牛汉通过第二种方式打开生命、认识生命,理解生命,将自我的生命深入整个生命的世界,在那里流连、驻足、探望,并开展平等的对话,生命与生命之间达成融汇贯通。但是,诗人又没有完全依靠直觉,这就避免了掉进唯心主义的泥淖,省思生命的同时,消解感觉的迷惑,以审美的眼光观照生命。正因为这样,牛汉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愈加全面、深刻。鉴于此,他的诗歌创作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语言被打上一层厚厚的生命底色,在表现思想和情感的深度上有所突破。牛汉不再受生命外在表象的纷扰,击穿层层迷雾准确把握生命的本质特征,分辨出生命质量的高低,觉察出生命不同的气象和境界。自此,他的诗歌语言上有了新的变化,语言留白,“召唤”读者去“填空”,显示诗歌较大的鉴赏空间。牛汉创造了自己的诗歌话语空间,富有哲理性的内涵,引发读者深广地思考。具有哲理性的内涵的语言包孕牛汉诗歌的血肉和精魂,开拓了他的那片绚丽的天空。
牛汉诗歌的语言直抵生命本身,在生命的深处生成,显示原本质地,自然就具有了深度。在朴素自然与深刻的传达中,诗意与生命互为表里。诗人有一种穿透力,一种对万物生命“等量齐观”的领悟力,语言表面看似朴素平易而实则深刻“炸裂”。牛汉是语言的能手,语言发挥了极大的艺术魅力,苦难的生命转化为傲岸不屈的生命,质朴的语言含有了耐人寻味的哲理。在平易却又深刻的诗句中,诗人自如地拓展了语言生成的空间,没有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也没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在践行生命超越的过程中成功完成语言向深度的“转身”。诗意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兼具,“诗无达诂”,诗有不同的“读法”。《空旷在远方》的诞生可以解释为诗人在语言艺术方面朝深意发展所做的努力。牛汉表明,空旷总是在远方,那里没有嘹亮的语言和歌曲,没有清晰的边界和轮廓,只有鸟的瞳孔和双翼开拓的天空。语言具有“旺盛的繁殖力”和强大的弹力,增加我们的“读法”,阅读期待的视野一下子开放,扩大了我们建构意义的空间。通过孕育、裂变,再生出深刻的道理,在感性的生命具象里捕捉智慧的情思,折射出诗性的光芒,让我们在省思的过程中获得审美情趣。这样说来,可谓“理趣”兼备。“理趣”兼备的诗在牛汉的诗集里占有一定的篇幅,我们还可以用《黎明》示例,诗人在《黎明》中写道:“黑暗并不能孕育永远的黑暗/而黎明必将从黑夜的腹腔中诞生。”非常有意思的是,“黎明”和“黑夜”是一对反义词,二者看似一组矛盾,互不调和互不相容,然而二者实则一体,相辅相成,相互缠绕而又逻辑分明——“黎明”是“黑夜”之后的“黎明”,“黑夜”是“黎明”之前的“黑夜”。这两个词被诗人赋予了哲理性的内涵,不再是仅仅表示时间的“单义”的词语。牛汉作为一名有正义感有良知有责任有担当的诗人一生都在驱逐黑暗追求光明,始终在“黎明”和“黑夜”的交接点上奋力挣扎、求索,始终在失望和希望的纠缠中执着追求进步和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平等的光明道路。《黎明》这首诗告慰人们“黑暗”并不恐怖,它是催生“黎明”的母体,没有“黑夜”,怎么能显示出“黎明”的可贵?更何况,“黑夜”终究无法阻碍“黎明”的降临。黑暗虽晃动在眼前,但它“不能孕育永远的黑暗”,只要坚定信心,为了黎明的到来勇敢地战斗下去,就必然有光明的前途。只要心怀希望,葆有生命的源泉,生命就永远不会枯竭,“黎明”一定会战胜“黑夜”,无论如何,“黑夜”是无法阻挡“黎明”的到来。的确,不经历“风雨”,就无法见到夺目的“彩虹”;不经历血的战斗,就无法取得革命彻底的成功。这是《黎明》向我们揭示的深刻的哲理,凸显了语言的艺术魅力,短短的诗行,包蕴千钧之力,让人过目不忘,令人回味无穷,催人奋起,给人百倍信心。
《空旷在远方》和《黎明》告诉我们,语言之所以有哲理性的内涵,就在于它处在不明朗的状态下,就像耸立在海平面上的冰山一样,上面看到的是皑皑高大的一座冰山,下面看不到的却是涌动的暗流。无论是表现论还是再现论,都会使语言变作一束束光,烛照出一个个真实的存在。牛汉通过语言来刷新现实,隐现出生命的世界和生命的意义。在抵达意义的过程中,诗人有意识增加抵达的难度,拉长抵达的距离,让语言放慢行进的速度,打破语言的惯性思维方式,推动语言往纵深处探进,这样的举措必然使语言有了深层的意蕴。
富有哲理性的语言还体现在意象的设计和运用上。牛汉将情感更多托付给意象,意象是语言和情感之间的一座桥梁。“感于事”“动于情”“兴于嗟叹”“发于吟咏”“兴于歌诗”,一系列的情感最终都通过意象聚焦在语言上,语言是抒发感情书写生命的最佳载体。把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与人的生命律动紧密联接在一起,借助生命世界使个人主体情感得以外延与投射,故而一切生命联动起来活跃起来。诗人善于经营意象,用意象来表情达意,通常有两种途径:放射和内敛。所谓放射就是诗人借助客观世界中外在的“象”本身蕴涵的象征意义,投入内在的情感,将创作主体的意志、信息、人格外化,如此以来,主体对应的“象”就具有了放射性的指涉意义。在创作主体的情感放射的过程中,客观对应物“象”表现“类主体性”,使主体本身存在的特征凭借客体属性表现出来,达到吸引、感染读者的目的。如牛汉笔下的一系列别具一格的意象,不用开花就能“沉默地结出拳头一样倔强的果实”的无花果,处在风暴的中心不惧死亡在荒漠里艰难跋涉的雄鹰,向大海深处的上空飞翔以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的蝴蝶,被雷电劈成两半仍昂首挺胸的半棵树,带着血爪试图冲破牢笼的华南虎,遭虫子噬咬而不得不“早熟”的枣子,悬崖峭壁上倔强生长的灌木,不畏酷寒的青桐,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汗血马,向下猛长扎入大地的树根,伤残后花朵仍怒放不谢的仙人掌,发着苦涩的气息但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芳香的枫树,虔诚地完成了一生的向日葵,等等。它们皆是牛汉情感外射后精心营造的意象。诗人的人格和情感意志凭借这些客观对应物得以传递和表达,主观情感和客体交融统一后,诗中的具体形象就具有一种超出其本身固有客观意义外的另一深层含义,烙印着诗人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审美体验和情感倾向。一言以蔽之,诗人赋予了客观对应物深度的个体意义。客观对应物凭借语言来完成它的设计和营造,语言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深层的涵义,促使创作主题进一步深化。
结语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人必须为创造语言而有所冒险,如采珠者为了采摘珍珠而挣扎在海藻的纠缠里,深沉到万丈的海底。”[10]牛汉为创造语言而沉潜到生命的不同形态中,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他的语言如生命最深处发出的一股清音,震荡在人们的耳边,他的语言像生命最深处冒出的一股新泉,流淌在人们的心田,具有生命的原本质地。诗人尊重语言的自在性和生成性,让语言带有生命的热力,从生命里创造出来,语言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语言,成为鲜活的语言。那么,生命成为富有语言特色的生命,成为创造的生命。这样,既保持了诗歌语言和诗人个体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也运用了诗歌作为独立生命在诞生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内在的生成规律,使诗的语言具有鲜活的原生态。牛汉自觉选择了诗歌语言适合自我性格和心理的表达方式,呈现了散文的风格。散文不需要太多的修饰,不需要涂脂抹粉,需要的是健康,充满自由、散漫的气息,需要的是不徐不疾的笔调。牛汉诗歌的语言质朴无华,疏放自由,不受韵律的拘囿,句子长短不一,于不规则处迸发出强烈的情感,于不经意处生成一股撼动心魄的力量。开阔的气势、无拘无束的体式,使得牛汉的诗歌呈现出散文美。诗人观照生命,理解生命,向生命的内蕴深挖,使语言走向深刻,富有哲理性的内涵。牛汉是一位无愧于时代的极具影响力的诗人,他的诗歌语言带给我们丰富而珍贵的诗学启示及教训,对纠正当下诗歌语言“口水化”、平庸化、粗浅化,对恢复诗歌诗性语言的特征,促使诗人“稍安勿躁”,促使诗歌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