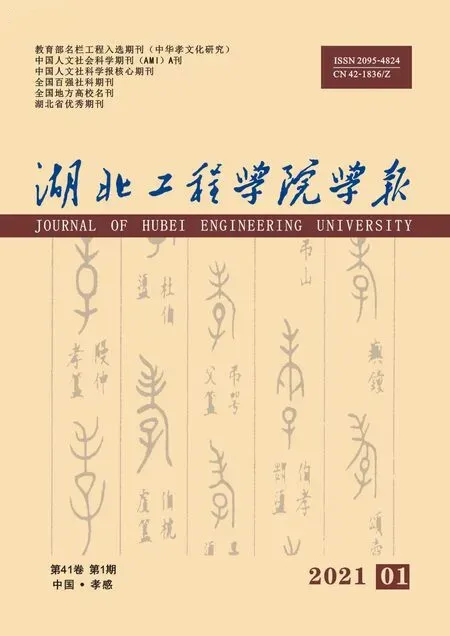《韩诗外传》孝道思想研究三题
衣抚生
(河北经贸大学 发票博物馆,河北 石家庄050061)
《韩诗外传》是汉代今文经学三家诗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唯一大致完整地流传下来的今文诗作,因而在我国经学史上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本文对《韩诗外传》中有关孝道的三个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一、仁、义、孝道:何者为先
《韩诗外传》在深入辨析孔子的父子相隐观点的基础上,讨论了孝道与仁、义何者为先的问题。《论语》记载了孔子与楚国叶公的一段对话,其中涉及到著名的父子相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篇》)[1]147
叶公所在的地方有一个正直的人,其父亲偷羊,作为儿子,亲自去告发父亲。孔子说,鲁国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的,如果发生了这类事情,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隐瞒之中自然有正直。直至今日,孔子所言充满争议,具体情况可参看郭齐勇先生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一书。笔者认为,孔子大概是认为亲情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也是人类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亲情一旦被破坏了,人类就会缺少安全感、信任感,社会秩序也难以得到维持。因此,相比于法律,孔子更加重视亲情。
后世儒家学者对此多有讨论,比如《孟子》的如下记载,说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2]293
孟子的一名叫桃应的学生,假想了一种情况,问孟子:最孝顺的天子舜,最公正无私的法官皋陶,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应该怎么办?皋陶又应该怎么办?桃应想讨论的其实是:在极端情况下,孝道和法律无法两全其美,那么要如何选择,尤其是作为统治者,应该如何抉择。这显然和孔子、叶公讨论的父子相隐是同一个问题,桃应举的例子也和父子相隐类似。孟子不想破坏法律,也不愿意放弃孝道,就想了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皋陶严格执法,抓捕舜的父亲;舜遵守孝道,放弃权力地位,带着父亲逃亡。这样的话,法律和孝道就能同时得到遵守。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孟子的两全其美之中,还是有倾向的,那就是孝道。在孟子看来,孝道比天子的权势重要,也比法律重要,所以舜可以丢掉天子的权势,也可以在付出一定代价的基础上破坏法律,而孝道必须得到实行。这是孟子和孔子的相似之处。当然,舜对法律的破坏是隐蔽的,不能明目张胆,这就是孟子强调的“窃”字;破坏的程度是有限的,瞽瞍要逃到海边,不能出来,不能再次作恶。和孔子有所不同的是,孟子对法律也非常看重,承认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不能明目张胆地、过分地破坏法律。
在孔子那里,孝道远远高于法律,到了孟子那里,孝道只是略高于法律。《韩诗外传》在这个问题上有进一步的思考:
子为亲隐,义不得正。君诛不义,仁不得爱。虽违仁害义,法在其中矣。《诗》曰:“优哉柔哉,亦是戾止。”(《韩诗外传》卷4第17章)[3]148
孔子和孟子都只是通过父子相隐来讨论法律和孝道的关系。《韩诗外传》则更进一步将仁、义一并引入进来,讨论仁、义、孝道的先后主次。《韩诗外传》首先指出,“子为亲隐”并非像孔子、孟子讨论的那样完美无缺,而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子为亲隐”违背了义,让不义之人逍遥法外,实际上是对国家和法律的不忠,结果就是“义不得正”。《韩诗外传》的这个发现非常关键:一定是父亲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罪,儿子才会面临是否需要为父亲隐藏的问题。这本身就涉及到正义是否能够得到伸张的问题。孔子和孟子都淡化了这一点,是有问题的。《韩诗外传》又指出,“子为亲隐”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国君的职责是要诛杀不义之人,就算儿子愿意为父亲隐瞒,最终结果也是被君主诛杀,“仁不得爱”,因此父子相隐的仁爱是无法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韩诗外传》紧接着用了一个“虽”字进行转折,“子为亲隐”虽然“违仁害义”,但是“法在其中矣”,“法”得到了维护,因而需要提倡“子为亲隐”。这里的“法”显然不是法律,原因是:“子为亲隐”是在破坏法律,而不是在维护法律。那么这里的“法”是什么意思?《王力古汉语字典》指出,“法”有5个义项:“法度,法令;准则;效法;方法;法术(后起义)”[4]。很显然,这里的“法”应该是准则的意思,也就是孝道的准则。在《韩诗外传》看来,孝道高于仁,也高于义。这无疑是对孝道的极大提倡和鼓吹。
我们将《论语》《孟子》和《韩诗外传》对比来看,就会发现:虽然都是讨论父子相隐的问题,《韩诗外传》在前者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论语》《孟子》讨论的是孝道和法律的冲突,而《韩诗外传》则深入到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孝道的比较。这种比较无疑更加精细,对我们辨析《韩诗外传》中儒家核心概念的主次先后也会有所启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分别是孔子和孟子的核心思想,其地位要高于孝道。但是在《韩诗外传》这里,孝道却是高于仁、义的。究其原因,可能和汉初重孝有关,即所谓的汉家以孝治天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韩婴的思想有其时代烙印,是对其所处时代思想的折射,而不是一味地跟从孔孟的脚步。
二、如何解决忠孝难以两全的问题
忠孝难以两全,是古人经常遇到的问题。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韩诗外传》极为重视孝道,孝道的地位甚至还在仁、义之上,当然也就更在忠之上了。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绝对的,《韩诗外传》也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韩诗外传》通过若干例子,来说明应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云:“夙夜在公,实命不同。”(《韩诗外传》卷1第1章)[3]1
在曾子出仕的故事中,《韩诗外传》认为“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曾子家贫,为了孝顺父母而出任小官,这个时候“重其禄而轻其身”,并非是俸禄或者忠重要,而是因为俸禄和忠是履行孝道的一个必要手段。当不需要履行孝道的时候,“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选择不出仕、不履行对国君忠的义务。因此,在曾子这里,孝道第一,保全自身第二,忠只能排第三。哪怕是齐、楚、晋等国给予高官厚禄,曾子也是如此。《孟子》中有类似的记载: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孟子·离娄下》)[2]186-187
先秦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5]。因此,保全自身也是孝道的一种表现,是次于直接赡养父母的一种孝道。曾子是这方面的代表。敌寇到来,会导致身体的毁伤,曾子选择躲避敌寇,哪怕是武城人“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对曾子很好,哪怕是这种避敌的行为“先去以为民望”,会产生不好的效果,曾子还是要坚持优先保全自身。因此,次一等的孝道也是超过高一等的忠的。当然,笔者也讨论过后世毁伤身体以孝顺父母的案例[6],这里就不赘述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将孝道放在忠之前时,《韩诗外传》加了一个重要前提:担任小官,“为之使而不入其谋”,不进入权力的核心领导层,不能既享受高官厚禄,又拒绝承担对朝廷的责任。这和孟子的说法有相通之处:“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2]224“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2]275君子在贫穷和饥饿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国君的馈赠,可以担任小官,这时不需要考虑忠。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如果得到了君上的礼遇,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楚白公之难,有庄之善者,辞其母,将死君。其母曰:“弃母而死君可乎?”曰:“吾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请往死之。”比至朝,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何不反也?”曰:“惧,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君子闻之曰:“好义哉,必济矣夫。”《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此之谓也。(《韩诗外传》卷1第21章)[3]22-23
庄之善的母亲显然是想要保住儿子一命,就劝他:如果为君上而死,就无法侍奉父母,也就违背了非常重要的孝,希望他能为了尽孝而不去送死。庄之善则认为,得到君上的礼遇,就应该“内其禄而外其身”,在君上遇到危险的时候,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至于孝,由于赡养母亲的财物都来自国君的俸禄,如果没有这些俸禄,也就没有孝。因此,君臣之义是孝的基础,哪怕是孝也要服从于忠。这和子思的选择是一致的:“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解释说:“子思,臣也,微也。”[2]186拿了国君的俸禄,成为国君的臣子,就应该为国君出生入死,此时的子思虽然是“微也”,年纪轻轻,却没有考虑到赡养母亲的事情。
这两则记载看起来是相冲突的:曾子认为孝高于忠,所以他选择了孝,而不是忠;庄之善的观点与之相反,所以他选择忠,而不是孝。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韩诗外传》的观点是:在最初的时候,人们有选择权,可以自主选择是孝还是忠。如果选择了孝,就要像曾子那样,不能获得朝廷的高官厚禄;如果选择了忠,就要像庄之善那样,优先履行对君主的忠,而要把孝放在忠的后面。《韩诗外传》没有强迫人们去选择孝还是忠,而是给了人们自主选择的机会,这无疑是很可取的做法。我们也可以看出,《韩诗外传》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观点,使之更加明确化。
三、《韩诗外传》的孝道思想与常山宪王刘舜的关系蠡测
《韩诗外传》非常重视孝,论孝的内容多达40余则,而且全书第一则就是讲孝。重孝是儒家的传统,比如《论语》记载了孔子多次论孝的内容,儒家还有一部专门论孝的经典《孝经》。但是《韩诗外传》阐释孝所用的篇幅实在是太多了,在思想上又较少创新,未免有些奇怪。笔者认为,这和韩婴担任常山宪王刘舜太傅一职有关。
《史记》《汉书》的《儒林传》都没有明确说《韩诗外传》的成书时间和背景,笔者认为应该是在韩婴担任常山宪王刘舜的太傅之后。证据来自《史记·儒林传》的如下记载: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汉武帝)博士。[7]3124
《韩诗外传》的写作时间,大致有三种可能性:韩婴担任汉文帝博士前、担任汉文帝博士期间、担任常山王太傅后。如果是前两种,那么《韩诗外传》一定会在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有较大影响力。但是《史记》明确记载,《韩诗外传》所流行的地区为燕赵之地,即“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在关中地区影响不大,这就说明《韩诗外传》是韩婴担任常山王太傅后所作。而且,《史记》在描写韩婴担任常山王太傅之后,紧接着就写韩婴作《韩诗外传》,也可以佐证。因此,我们可以认定,《韩诗外传》写于韩婴担任常山王太傅之后。
这里所说的常山王是指常山宪王刘舜。《史记》称:“常山宪王(刘)舜,以孝景中五年(前145年)用皇子为常山王。(刘)舜最亲,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刘)勃代立为王。”刘舜是汉代首任常山王,受封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由此可知韩婴是刘舜的太傅。韩婴的这一职务地位尊贵,但也充满挑战。刘舜是汉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虽然能得到皇帝的宽释,但是其下属未必能免受朝廷惩罚,刘舜对下属也未必仁慈。刘舜家族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不和。《史记·五宗世家》中有详细记载:
初,宪王有不爱姬生长男棁,棁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宪王疾甚,诸幸姬侍病,王后以妒媢不常在,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棁为子数,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分棁财,皆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及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棁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狱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问,逮诸证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有司请诛勃及宪王后脩。上曰:“脩素无行,使棁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致诛。”有司请废勿王,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7]2102
刘舜家族内部的问题,可以细分为:刘舜长子刘棁生母地位卑微,刘棁受到牵连,也受到刘舜的轻视,父子不和;刘舜多内宠,长期疏远王后,与王后之间夫妇不和;王后之子、太子刘勃因母亲失宠的缘故,与刘舜之间感情淡薄,父子不和;太子刘勃与长子刘棁之间兄弟不和。这不只是常山王室的家事,对常山王室的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王室长期内斗的结果是:太子刘勃在刘舜丧礼期间,犯下了居丧不哀、纵情酒色等罪行,被刘棁告发为不孝,刘棁的行为则是手足相残。汉政府调查后,有关部门上奏,要求诛杀王后和太子。汉武帝则认为王后“素无行”,长子刘棁“陷之罪”,太子“无良师傅,不忍诛”,最后将太子和王后流放房陵(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值得注意的是,王室内斗的结果,除了要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之外,还要重点追究“师傅”的责任。汉武帝既然认定太子刘勃“无良师傅”,那么太傅、太师显然是失职的,需要遭到严厉惩罚。
韩婴担任常山宪王刘舜的太傅,有两方面的危险:第一,刘舜娇纵跋扈,“骄怠多淫,数犯禁”,具有迫害甚至杀死韩婴而不受惩罚的能力。而韩婴不能得罪刘舜及其家族。第二,韩婴不能和刘舜同流合污,反而还要劝谏刘舜,否则会受到汉朝廷的惩罚。但劝谏刘舜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很危险,实在是进退两难。在这种背景下,韩婴能在昏聩无行的常山国当太傅而安然无恙,是需要智慧的。这一方面是韩婴学问高超,另一方面则是韩婴“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为人精明能干,做事情很公正,很有分寸,而且韩婴在和董仲舒的论辩中都不落下风,显然是应变能力很强。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韩诗外传》非常注重孝道,所针对的恰恰就是刘舜家族的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的环境。笔者认为,这是韩婴用来含蓄地劝谏刘舜、同时躲避朝廷追究的手段。我们可以参考龚遂、王式用《诗经》来劝谏海昏侯的事例来说明。《汉书·武五子传》记载:
(龚)遂叩头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居无何,征。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龚)遂,(龚)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籓;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8]2766
龚遂的事例表明,儒家学者跟统治者谈论《诗经》时,往往注重解决统治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其提供解决思路。韩婴和龚遂有相同点:都是面对着一个无道的君主,都是研究《诗经》的专家,都是通过《诗经》来规劝君主。因此,《韩诗外传》反复强调父慈子孝,应该不是偶然的。韩婴必须对常山宪王刘舜家族进行规劝,否则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汉书·儒林传》中王式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
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王)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王)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8]3610
王式的事例表明,在诸侯王犯罪的时候,负有教导之责的师傅会承担连带责任,除非是师傅有劝谏的证据,而王式吟诵《诗经》中的忠臣孝子之篇,可以作为减刑的证据。韩婴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他难道能不进行类似的准备吗?《韩诗外传》反复强调跟常山宪王刘舜家族有关的孝道问题,恐怕不是偶然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猜想:韩婴在《韩诗外传》中反反复复强调孝道,是有原因的。这一方面是对常山宪王刘舜家族的规劝,另一方面也是韩婴用来避祸的手段。
以上就是笔者对《韩诗外传》孝道思想的一点浅薄的认识,不足之处,敬请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