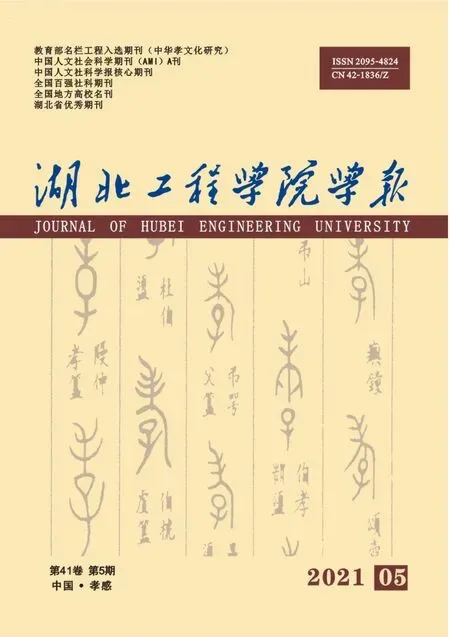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第三空间”和美华文学
许丽霞
(安徽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华文学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移民文学,文化冲突是其不可避免的话题,认同焦虑、没有归属感、异族通婚等主题屡见不鲜,华人作家将在异国文化中的迷茫诉诸笔端,通过文化书写来宣泄内心的无所适从。后殖民主义的兴起为美华文学提供了新思路,华裔作家根据自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他们在美国成长、居住的经验,在创作过程中积极利用两种文化资源,积极寻求与主流美国文化融合共处。尤其是“第三空间”理论的提出,为拥有混杂身份的美国华人以及美华文学提供了方向。
一、理论阐释
1.后殖民主义理论。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后殖民主义思潮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吸取后现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里的相关论点,后殖民主义逐渐掌握人文批判学中的基本话语权。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后殖民主义解释了一系列的理论标准和批判技巧,用以阐述之前西方强国的殖民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它们和世界的关联性;它探索了在非殖民过程中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效果,推进了反对强国文化霸权侵略的过程,也更多地表现出对西方大国中的少数族裔的关注。
当代后殖民主义的先驱是弗朗兹•法农,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中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念。关于种族,法农认为它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学分类,是对于某一群体的习惯性理解和表达。关于身份认同,法农认为身份认同是强国为了巩固自我地位而推崇的一种概念建构,要求在非统一性的概念中不停互动,最新的理论认为这一过程叫做“杂糅”,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相互混合的过程”[1]。
除了法农之外,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爱德华•萨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都对后殖民主义做出了相对独立的理论解释,提出自己的思考,以期解构西方帝国的殖民主义,消解欧美中心主义,进而重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为其发声。其中霍米•巴巴作为较年轻的批评家,他的理论受法农的影响较大,很多概念都是一脉相承并发扬更新。巴巴的第一本书《民族和叙事》以及第一本散文集《文化的定位》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出版,引发了全球关注和强烈反响,将后殖民主义研究带到了一个新领域,成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最新理论基础。
2.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由于自身的少数族裔身份,巴巴清醒地知道当今少数族裔在定位我是谁以及我在哪里这方面的困惑和焦虑,在《文化的定位》的序言中,他推翻了传统观念中的民族认同,认为不应该只依赖于本土文化传统和历史,而应该专注于发掘“居间”空间,为研究自我,无论是个体的自我还是群体的自我,提供新的空间,开启新的身份符号。巴巴认为所有的身份认同都是重构的产物,是一个不停杂糅的过程,文化不仅主导语言和文本,也渗透于日常生活,民族的不同、地域的差异自然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认识到影响这种现象的多种因素的存在,巴巴没有从“中心”或“主流”出发来研究后殖民主义,而是从“边缘地带”入手,形成三部曲:否定─协商─杂合。除此之外,他认为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之间差异与矛盾并存,但绝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杂糅,可以在介于两种文化的中间位置形成兼具两种文化的“第三空间”。它不推崇文化霸权,而是寻求一种部分性文化,最终让其所占据的少数民族立场得以发声,是一个文化混杂型、临时性、稳定性的空间,文化间的差异会在这个空间中交流、碰撞和相互渗透融合,因此,传统概念中的固定性、原始性和霸权主义被消解。“第三空间”对于解构后殖民语境中的偏见,即社会群体在生物学角度的优劣之分,比如西方优于东方,白人优于黑人等,有很重要的意义,表明文化之间的相互抵抗开始转向协商和进一步对话,与此同时,新的身份认同逐渐形成、改造并持续更新。“第三空间”产生的基础是文化的混杂性,在巴巴看来,“这个空间既不单属于自我,也不单属于他者,而是居于两者之外的中间位置,混合两种文化的特征”[2]。所有多元文化中的移民都能够在“第三空间”进行冲突融合,创作自己的身份认同。
二、“第三空间”和美华文学的内在关联性
霍米•巴巴从后殖民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出发,提出“第三空间”理论,提供了一种对抗文化霸权和构建民族身份的方法,挑战并超越了二元对立,提倡一种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文化融合方式,接纳文化对立和边缘族裔,契合了美华文学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模式,为其理论话语权提供了基础,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二者的内在关联性。
首先,美华文学本身是一种杂合型文学创作,具有浓烈的“第三空间”色彩。华裔作为有华人血统的美国人,虽然其文学创作的语境是美国,但又很难不受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样的双重性让美华文学既具有美国文学的创作特点,又表现出很多中国文学的创作元素,既无法进入美国文学的主流创作,又和中国主流文化若即若离。美华文学始于19世纪70年代,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没有形成气候,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移民人数增加,尤其是留学移民的增加大大提升了移民的文化素质,美华文学创作迅猛发展,无论是美国文学中的华裔美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中的美国华文文学,都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然而都改变不了美华文学在两种文学中的边缘位置,无论从哪一种角度进行界定,都属于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间”。
其次,美华文学的创作内容本身就是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地理空间上跨越美国和中国,文化上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天然的双重视域让美华文学成为两种文化沟通的媒介。于中国本土而言,美华文学让人们了解华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真实过程和具体情景,既有熟悉的中国因子,又有陌生的异国元素;对于美国社会来说,美华文学帮他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渠道了解中国。只是美华文学中传递的中国经验和美国文化与现实中的中国和美国又是有差异的,因为离乡背井,他们的中国经验充满了文化乡愁以及对中国故土的反思;因为身处异国他乡,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感知又是立足于中国的观察,和美国本土文化存在差异。这种双重经验使得美华文学对于美国和中国都同时处于一种解构、建构的过程,是一种既涵盖了对美国和中国的双重视域描写,却又表现出和二者相异的“第三空间”文学书写。
第三,美华文学属于流散文学,诞生的大背景是全球化发展,华人流散现象和族裔散居现象已然成为常态。“而越是流散,越是陷于属性上的分裂、破碎和不确定,对于一致和统一的追求和追问便越是强烈”[3]。在从中国到美国的流散过程中,美华文学游离于中国文化之外而在美国文化中寻找归属,在美国的边缘文化中开辟出一片既和美国文化相差别又和中国文化相隔阂的“第三空间”,中国文化为了融入美国文化进行异化和改变,美国文化也融合吸收了一些异质因子,两种文化在“第三空间”调整、磨合,成为独特的美华文学。
鉴于以上提及的关联性,霍米•巴巴认为美华文学的创作和书写很好地阐释了“第三空间”理论。因此,本文将结合美华文学的创作,更加详细地向读者展现中美融合的“第三空间”。
三、“第三空间”在美华文学中的体现
1.中美两种语言融合书写的“第三空间”。美华文学的主要创作语言是英语和汉语,对于华人作家来说,无论他们选择哪一种语言进行创作,都会受到来自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影响干扰。对于华裔来说,汉语是其母语文化,选择汉语进行文学创作自然更加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处在以英语为通用语的语境中,长期受英语语言环境的熏陶,受到英语思维的影响。而对于用英语进行创作的华裔来说,虽然他们一出生接触的就是英语环境,英语亦是母语,但是由于其父母多是第一代移民,在家仍然会用汉语进行交流,这样的家庭氛围就会时时影响到他们的英文创作。美华作家既受到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又要努力适应美国文化,双重文化压力迫使他们寻求最合适的生存方式,追求语言融合的“第三空间”,因此,美华文学创作很难坚守其语言的纯粹性,汉语和英语在创作文本中相互渗透,出现中英混用的杂交现象,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又相互渗透、杂糅,最后形成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这种语言杂交混合体正是语言融合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汉语和英文不再是相互对立,而是进行杂交和互融,既保留了各自语言自身的特点,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美华文学创作语言。
首先是中文创作中杂糅英语表达和单词。通常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专有名词,比如人名、地名、品牌名等。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谪仙怨》 中出现了Time Square(时代广场)、Paul Mall(保罗商场)、Westchester(韦斯切斯特——纽约地名)等,这些专有名词是属于美国社会的独有元素,直接使用英文更加便捷也更加真实。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4]中英文表达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只要你开心,我会do whatever it takes(尽一切努力),成全你的” ,“我很喜欢这句话: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来,我遭难,我存活)”。此外,在於梨华、严歌苓、曹桂林、查建英等美华作家的文学创作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第二种是传达真实生活情境的英语表达。两种语言之间虽然能通过翻译互通,然而不同的语言体系总有一些方面是不可翻译的或是翻译过后会完全丧失原有语境要表达的含义,《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Dress downday指的是周五上班可以穿便装,然而汉语中并不存在对应的表达,为了避免麻烦,直接用英语反而更加真实,更有现场感,同时也能展现出美华作家的美国经验,从语言层次展现“第三空间”书写。第三种是在中文书写中采用直译英语表达的现象。《考验》中写道“他暗暗佩服美国人‘闲扯’的本领”[5]。在汉语中找不到“闲扯”这个专门术语,没有实际意义且多数用作动词,在这句话中是一个名词且加了引号,皆因其是英语“small talk”的直译,而“small talk”在英语中指的是一种交流技巧,一种不太严肃的谈话。《又见棕榈,又见棕榈》[6]中出现了“都可以,我由你摆布”、“大人的意义,套句美国话,是站在自己的两条腿上”、“每篇文章都给作者一个可以思想的粮食”。从汉语追溯这几句话的英语思维分别是:I am at your disposal,stand on your feet,food for thought,很容易看出原文句子中这种明显的直译腔调,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原语言的特色,起到陌生化效果,让中文书写有了一种异国风情。
其次是英文母语书写中的中文元素。经过几十年的移民迁徙,很多华裔在美国出生、成长、接受教育,英语已然是他们的母语,自然就会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第一个开始用英语母语进行写作的是19世纪末的水仙花,之后更有黄玉雪、汤亭亭、赵健秀、谭恩美、任碧莲等,这些作家虽然出生在美国,接受的也都是美国文化,但他们的黑眼睛黄皮肤却永远告诉别人自己的根在哪里,生理上的华人特征让他们永远和白人之间都有着差异,心理上由于受到祖辈甚至父辈对过去回忆的影响,也不会像普通美国人那样看待中国文化,在他们的英文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混杂了中文思维,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通过混杂中文和英文书写,弱化英语的语言霸权,体现中文的感性元素。句法上会有一些中文思维的英文表达,比如“you tell that man don’t let dog do that”、“This not so easy say ”等,这些句子不考虑英文的时态,一句话中有多个主语,系动词缺失,几乎是对照中文字对字直译,是非常典型的中文化英语表达。词汇上会有一些中文词汇的英语直译。为了在英文书写中更多体现中国文化,美华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对很多中文词条都采用了直接的音译处理,比如badpiqi(坏脾气)、zongzi(粽子)、Waipo(外婆)、nuyer(女儿)、Kuomingtang(国民党)等。另一种是在英文书写中插入东方文化符号,进行东方化书写,比如red-egg ceremonies(满月酒席)、palanquin(轿子)、Festival of Pure Brightness(清明节)、concubine(妾)、First Wife(大太太)等,这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通过植入书写,让美国世界可以了解中国文化,两者互通共融,形成语言共同书写的“第三空间”。
2.中美两种文化杂糅书写的“第三空间”。经历了移民之初的中美文化冲突碰撞之后,很多华裔认识到这种介于两种文化边缘的特殊身份给自己带来了很多优越性,让他们可以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以更宽广的视角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确,处于中美文化边缘,拥有双语文化背景,让他们可以比一般作家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引发更多的文化思考,也享有更大的书写自由,他们可以在文本中自如运用中美文化资源,加以改写和移植,对两种文化进行并置处理,形成中美文化杂糅书写的“第三空间”。
华裔作家根据自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他们在美国成长、居住的经验,在创作过程中积极将两种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进行深度交流和融合,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中后期的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很多华裔作家开始觉醒,不再像之前那样因为自己的移民身份感到困惑和悲观,而是开始思考自身的权利和身份,探索新的方法来确认华裔族群的独特性,不断挖掘新的主题,拓宽创作领域,向主流文学靠拢,典型代表有汤亭亭、赵健秀等。尤其是汤亭亭,利用其对中国古典文化以及现当代中国作家都有所了解的优势,在文学创作中杂糅了各种中美文化资源,其对中国古典和文化知识的运用甚至超越了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包括引用中国经典文本,比如《道德经》《镜花缘》《三国》等;讲述中国古代传说或文学人物,比如花木兰、八仙、女娲等;论述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比如太平天国、孔子、林则徐等,以及转述中国佛经故事和民间戏剧故事,比如天仙配、狸猫换太子等。汤亭亭写作的最大特点是将各种中国文化的元素最大程度地杂糅进英文书写,将各种原材料进行改编再融入自己的文学叙述,其文学创作既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别于美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元素与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杂交后的‘第三空间’文化——华裔美国文化”[7]。
在《中国佬》中,汤亭亭对多个中西方的文学经典进行了改写处理,包括《杜子春》《镜花缘》《鲁宾孙漂流记》等。在“关于发现”一节,汤亭亭对《镜花缘》的故事进行了改写,删除了大部分历险的情节,保留并改编了唐敖在女儿国的经历,误入女儿国,被迫打耳洞、裹小脚并被打扮成侍女,这些都是中国元素。在“论死亡”一节中,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它们分别来自中西两种文化,但都是关于打破沉默承诺。西方故事讲的是半神人毛伊为使人类永生盗取黑夜之神海娜的心脏的神话故事。当毛伊拿到心脏从海娜的阴道出来时,一只鸟打破了万物保持沉默的规矩,导致毛伊死在了海娜的腹中。同时借鉴并改写了中国的神仙传奇故事《杜子春》,增加了转世投胎、出生成长的情节,删除了杜子春挥霍无度、经历折磨的细节,将原先故事中的佛教文化和道家精神改写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殉道精神,实现中美文化互融。书中还有另外一个具有中国风味的故事“罗笨孙”则是改自美国文学《鲁宾孙漂流记》,加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比如酿药酒、做豆腐、做毛笔等,通过这样的杂糅书写,颠覆了美国的话语霸权,实现了对抗主流叙事的文化书写,体现了两种文化共存的“第三空间”。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同样运用杂糅书写的方法塑造了一个具有西方特色的现代神话英雄——花木兰,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父从军,花木兰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人形神鸟的召唤进山习武,一练就是十五年,而她习武的目的也不是奔赴沙场报效祖国,而是为了和坏人斗争,为村里人报仇。在描写花木兰进山的情节时,作者穿插了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太子舍身伺虎”和“尸毗王割肉喂鹰”以及西方文学《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白兔情节,杜撰出了“白兔跳入篝火舍身献肉”的桥段,细节描写方面又借鉴了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花木兰学艺归来,父亲又在她的背上刻字,效仿中国文化中的“岳母刺字”。汤亭亭在进行女勇士的创作时,非常大胆而有意识地进行增删、改写和重组嫁接,用中西杂糅书写的方法讲故事,目的是要“书写处在文化夹缝中的空间错位感和孤独感,表达她们融入西方文化的渴望,消解美国主流文化,为华裔文学争取一席之地”[8]。华裔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融合了中国元素,体现了中国性的一面,但是其价值归属和意识形态又始终向美国靠拢,有很强的美国性,形成独具特色的“第三空间”书写,让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能够协商共处。
四、结 语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西方世界以文化创作和意识形态为载体,利用其在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对东方文化进行殖民霸权。从事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们积极探索摆脱强国霸权的方法,维护弱势民族的身份认同,他们强调要为少数族裔发声,打破文化霸权。霍米•巴巴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从边缘文化立场出发,揭示了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冲突、瓦解和重构”。[9]在“第三空间”里,认同是不同文化不断交往不断协商的过程,多元文化可以在同一空间里不断融合,逐渐实现文化认同。华裔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冲突之后,开始探求文化融合的可能性,逐渐体现出认同的豁达,既可以坦然面对美国,也可以自如地回首中国。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这种边缘文化向文化中心趋近的努力就是对文化霸权的抵抗,华裔作家在美华文学的碰撞与交融中体现出一种混杂性,一种居间状态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碰撞、互融、共存的,弱化了文化的二元对立。华裔作家通过书写“边缘─中心”权力的消解,努力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霸权,追求文化的交融与互通,在文化霸权的美国社会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存在。
通过研读美华文学的相关作品,本文从中美创作语言融合和中美文化杂糅书写这两方面入手,具体阐述“第三空间”理论和美华文学。首先,华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进行中英文混合书写,在标准英语之外呈现了一个“第三空间”,既认同了主流社会又强化了族裔特色,这种“第三空间”的语言既和标准英语协商互融,又向世人昭示它和纯粹的美国文本是有差异的,体现中国特色。其次,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元素进行杂糅书写,其笔下的中国文化并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土壤里异化的结果,是东方文化元素和西方文化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杂糅混血的文化正是“第三空间”理论的体现。对于华裔作家而言,文化书写中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象征,是族裔身份的符号,通过这些元素表明自己的族裔特征以及和主流社会的差异,消解美国社会固有的种族歧视和东方主义,为少数民族发声,争取合理合法的权益。因此,“第三空间”的文化书写是华裔作家缓解身份焦虑,对抗西方主流文化的积极尝试。开放包容的“第三空间”为拥有混杂身份的美国华人以及美华文学提供了方向,“不仅是确保跨文化交际顺畅进行的策略性手段,也体现着不同文化间交际时合作共赢、异中求同的积极态度和目标”[10]。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华人带着强烈的文化自信,他们利用其跨文化的优势,根据其对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了解认知,扬长避短,更好地进行“第三空间”文学创作。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