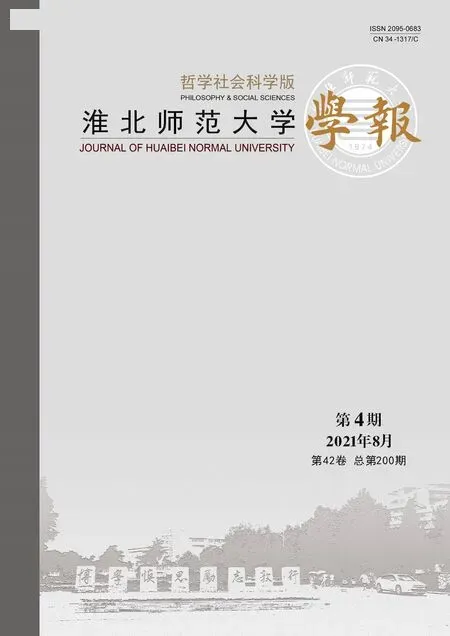叩问思想:研究陈垣的新路向
——评《陈垣史学思想与20世纪中国史学》
谢 辉
作为20 世纪中国史学大师之一,陈垣的学术成就与贡献,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关注。据初步统计,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已先后有5部有关陈垣研究的著作出版,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270余篇。然而,这些已有的研究普遍存在着一处不足,即详于论述陈垣在某一领域的具体工作和成绩,而略于深层次的思想提炼与分析。周少川、史丽君的新著《陈垣史学思想与20世纪中国史学》(人民出版社2020 年,以下简称《陈垣思想》),即是为数不多的一部从史学思想入手的陈垣研究力作。
某种程度上而言,当前的陈垣研究重史实而轻思想,也有其客观原因。在20 世纪的史学名家中,陈垣属于较重史料性、实证性史家。其早年治中国基督教史,即是从整理西学类典籍与编纂《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入手。其后因整理文津阁《四库全书》而编《四库书目考异》,因整理敦煌遗书而编《敦煌劫余录》,因考察年代需要而编《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都是工具书性质;由其首创的史源学,则源于一门考证实习课程。他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闻名中外的“古教四考”、《元西域人华化考》,也都是以考证著称,所以许冠三在《新史学六十年》中将其列为“考证学派”史家。后人若一味沉溺于此,很容易得出陈垣有实绩而无思想的印象。此种印象则类如段玉裁论戴震之学所曰:“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
实际上,陈垣具有很丰富的史学思想。按照《陈垣思想》一书作者的看法,陈垣虽不如他的乡贤梁启超那样思想尖锐、汪洋恣肆,也不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那样善于建立新的史学体系;但他的史学思想常常随着考证和对史实的表微有感而发,各种史学评论散见于他的论著之中,也可见到他在文献考据中为发凡起例而阐发的治史理念。然而,这些思想毕竟蕴含在陈垣大量的实证工作中,如何对其加以提炼,确实是一个富于挑战的命题。惟其困难,方显可贵。故该书的首要贡献,即是首次系统发掘阐述了陈垣的史学思想。
具体而言之,《陈垣思想》从历史认识和史学认识两大路径展开,构设了由民族文化史观、宗教史观、史料学思想、历史编纂学思想、治学思想与方法论等方面组成的陈垣史学思想体系。第一章《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文化史观》,论述陈垣有关中华民族多源形成、历史融合的思想,多民族共建中华历史的观念,以及既坚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地位,又承认外来优秀文化作用的态度。第二章《客观理性的宗教史观》,指出陈垣的宗教史思想特点为,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条件出发对宗教现象进行评价,既不拔高,也不苛求。第三章《陈垣的史料学思想》,总结陈垣重视搜集史料、考察史源、整理文献的突出思想特征。第四章《陈垣的历史编纂学思想》,阐明陈垣把史书撰述作为升华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秉持“因类例以明通识”的精神,以及讲求选题谋篇、体例表述等一系列思想。第五章《陈垣的治学思想与方法论》,指明陈垣以励志耕耘、力求创新作为基本治学精神,主张言必有据、实事求是,并提倡多学科综合运用的考史方法。通过以上内容,该书不仅从多层次、多角度对陈垣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分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各方面思想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内外交融的情况,从而将陈垣之史学思想构建为一个整体。在完成了对陈垣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后,《陈垣思想》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将研究的目光投射到了陈垣史学思想的演进轨迹上。第六章《陈垣史学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详细描述了陈垣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由早期的继承发展乾嘉考据之学,到抗战时期的经世致用、表彰民族意识之学,再到建国后服务社会大众之学。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陈垣史学指导思想的发展和他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行动,是其家国情怀以及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的思想基础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追求真理、具备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所具有的优秀品格,决不是一时兴起的所谓“应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特别关注陈垣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互动。在对陈垣的各方面史学思想进行研究时,多将其与同时代的其他史家,特别是与陈垣有交往的学者进行比较。如在第四章讨论陈垣的史料学思想时,即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作为比较对象,从而提出,相比20世纪其他史家,陈垣的史料学思想最为丰富。在该书结语中,作者集中对陈垣史学思想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系做了阐述,认为:新史学的科学精神、西方的新史观和治史方法、新史料的大发现、马克思主义史观等新思潮,以及同时代其他史家,均对陈垣的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陈垣从中取益,又反过来以其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以上这些内容,一方面说明了陈垣的史学思想,并非一个孤立的、静态的体系,而是与时代背景及人际交往息息相关,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与时俱进的活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比较的方法,突显了陈垣史学思想在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且独到的价值。总之,陈垣史学思想之内容、历程、背景、特色、价值等,该书的论述可谓包揽无余,真正实现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与同类研究相比,该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过程中坚持以思想为导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注重提炼思想,避免重复前人已有的史实研究。例如,在第二章《客观理性的宗教史观》中,本书并没有详细叙述陈垣从基督教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乃至犹太教等“古教”的研究路径与成就,而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其思想特点,即善于将宗教与历史环境相联系,进而从“主张信仰自由、宗教平等”“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论宗教史籍的史学价值”四个方面有序展开,发掘和总结陈垣宗教史观的具体内容。陈寅恪称完善的宗教史始自陈垣,故宗教史研究在陈垣的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近年来研究亦日益兴盛,一些细节问题如陈垣早期整理基督教类典籍的版本、陈垣宗教史研究与其个人信仰的关系等,都有学者探讨。然而《陈垣思想》的研究则并未沉溺于这些细节考察,而是牢牢把握住主题,由博返约,由表及里地叩问思想。书中所揭示的陈垣关于宗教与政治密切相关、互相影响,宗教是文化传播的先锋,宗教史籍可以为世俗史研究提供大量史料等观点,为今人的宗教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从而有利于开辟研究的新局面。
2.以思想贯穿陈垣的学术与著作。陈垣治学广博,在宗教史、元史、文献学、中外交通史乃至教育、医学等多方面均卓有成就。遗留至今的成果有专著,有古籍整理,有工具书,有论文,有讲话稿,有课程讲义,还有读书笔记、批注和未完成的文章提纲。如何找出这些表面上不相统属的论著之间的关系,发掘其中共有的史学观念和思想主旨,将其贯通为一?其关键仍在《陈垣思想》一书所秉持的“思想”二字。例如,对于陈垣之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该书统归之于考史方法论,并与其注重考证,主张求真求实、言必有据的治学思想联系起来。又如,陈垣编纂的《敦煌劫余录》《道家金石略》《二十史朔闰表》,一属目录,一属石刻史料汇编,一属历表,三者似乎毫无关联。该书却从中归纳出了陈垣“一人劳而万人逸”的史料整理观,揭示了其一贯的思想渊源和内在逻辑。凡该书各个章节,大都具有此类从多种不同材料发掘其中同一思想主旨,即以思想统领史实的特点,可谓以简驭繁,累累若贯珠。
3.注重从前人关注较少的史料中勾稽陈垣思想。陈垣一生著述甚富,大部分已收入多达23 册的《陈垣全集》中,近年来又有批注、手稿等新材料陆续出现。面对着如此浩繁的资料,学界研究的重点,却始终为少数几种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著作,对于一些篇幅短小的文章与未成文的文稿、提纲、书信,甚至采访录等,则关注较少。其原因无非在于材料太过零散,缺乏研究角度。而《陈垣思想》则从思想入手,挖掘出了这些材料的新价值。比如,对陈垣关于中华民族多源形成思想的发掘和论述,其中就利用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记者对陈垣一次重要采访的“访问记”材料。又如在第四章《陈垣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中,即以陈垣《广书林扬觯提纲》为主,分析了其对古书编纂体例的研究心得,归纳为“史文宜前后照应忌重复”“剪裁史料须文意通畅”等五个论点。《广书林扬觯提纲》原仅二十余条,每条不过数字至十数字,其下间有简短按语。《陈垣全集》整理出版时,将陈垣为作《广书林扬觯》而搜集的十四册资料上的批语辑录之,附于相关条目之后,但仍显得十分单薄,并不引人注意。然而,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出发,其完全可以被看作陈垣“事实要确实,文字要优美,意义要深远”的著史思想的具体表现,而其价值亦由此体现出来。
4.注重陈垣史学思想的“变”与“常”。陈垣一生,学凡三变,关于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述及。然而《陈垣思想》不仅讲其“变”之实迹,还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动因。例如,其早年服膺乾嘉学术,与其从读《四库全书总目》《廿二史札记》等书进入学术研究有关。但陈垣又不满足于琐碎的考证,而是力图从大量的考证成果中归纳出类例与通则,一定程度上又与20 世纪新史学思想的兴起与西方新史观新方法的传入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指出“变”中又有“常”者存。所谓“常”者为何?一是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文化史观与爱国情怀,亦即启功先生总结陈垣史学思想时所说的“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二是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不明其变,则不明陈垣史学发展各个阶段的特征。不明其常,则不知陈垣有始终如一的思想主干。只有“变”与“常”结合,方能全面揭示陈垣思想全貌。这也是该书的一项突出贡献。
总之,《陈垣思想》一书,一方面从陈垣众多的论著中总结其思想,另一方面又以思想提挈其学术,从而实现了对陈垣史学思想全面系统的总结。在文化事业持续繁荣、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史学研究的资料可谓实现了空前的扩充,但新的解释却往往滞后。或为考证而考证,或以新概念、新名词包装旧内容,而导致“新瓶装旧酒”式的形合神离。对此问题,陈垣其实早已提出了解决方法,即以考证为基础,由此贯通史实、得出新解和新见。立论本之于考证,则不至于高邈空虚;考证有理论为导向,则不流于琐细无用。《陈垣思想》正是继承和发扬了陈垣的这一理念,由此将陈垣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定程度上也为史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