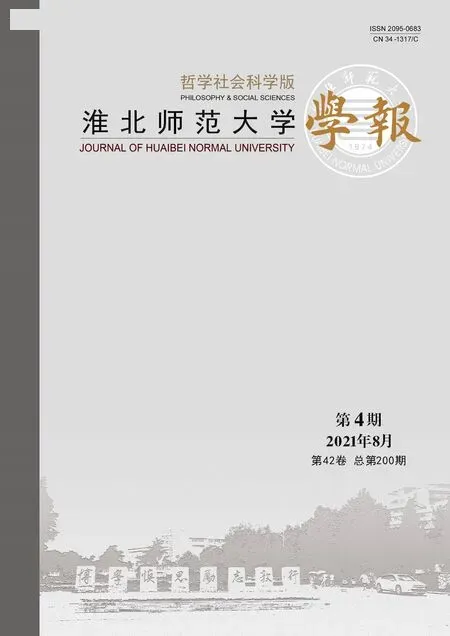形象学视域下《扶桑》英译本东方女性形象建构
李晓丹,周宝航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引言
在《扶桑》这部反映华人移民历史的长篇小说中,作者以旁观者的口吻描绘了“遇见”扶桑的故事。在作品中,作者运用了第二人称叙述。扶桑出生在湖南的一座茶山里,14 岁便与公鸡拜堂结了亲,从未见过自己夫婿,几年后被人以出海寻夫为由骗到旧金山。在这个当时华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美国社会,扶桑与白人男子克里斯和华裔男人大勇产生了一系列情感纠葛。
作者严歌苓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在美生活的20 多年经历让她对于移民华工的生存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创作《扶桑》之前,她翻阅了一百六十多本唐人街正、野史,逐渐勾画出一个在美国黄金海岸旧金山受尽蹂躏却依旧沉静宽容的东方女子形象——扶桑。1996 年,《扶桑》出版发行。2001 年,美国的东亚文学学者Cathy Silber 翻译的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在Hyperion 出版社出版,并被《纽约时报》评为2001 年全美十大畅销书之一。译者Silber 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忠实翻译,尽力塑造出与原作描述相融的人物形象。但作为西方人,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等影响,对于原文中的某些部分还是进行了删减、修正,导致译文中的扶桑形象与原文有所出入。扶桑形象中的受难、宽恕、包容等方面与西方社会的环境与文化有所融合,但原作要表达的某些文化内涵被弱化甚至忽略了,比如扶桑的自我救赎、母性等。本文从形象学解读《扶桑》英译本中东方女性形象的建构。
二、形象学理论概述
形象学由法国学者让·玛丽·卡雷提出,他主张在研究国际文学关系时,不拘泥于考证,而注重作家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不同国家人民间的相互看法等。因此,他把形象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而后形象学由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让·莫哈等人发展完善。同时对于形象学的研究也逐渐向着跨领域方向发展,对形象的研究也逐渐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相连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孟华教授将形象学相关论文编译成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出版。2016 年由本杰明出版社出版的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以形象学为理论基础,阐述了翻译研究中形象学的核心问题,即他者(other)与自我(self)形象的构建。[2]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imagology),侧重于对“异域形象”的讨论,主要分析某国形象在异国的文学流变,也就是说这个异国形象是可以被想象,重新塑造和流传的[3]。而这种形象的变化,通常是由于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导致的,也是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巴柔在《形象》中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描述,他认为一切形象都源自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极其微弱的。[4]“他者”,这个异国的形象是对某个民族精神、社会环境、文化底蕴的反映,也是“自我”,即译者个人基于自己感受感悟所塑造的一个新的形象。这个新构建的形象背后所隐藏的是翻译者的自我形象,这个新形象作为一个承载工具,反映了两个国家的社会差异与不同的文化认知。扶桑这个被拐卖至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名妓,在Silber 的重新演绎中,展现了东方女性原有的色彩,也体现出西方作者基于自己的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底蕴,对于东方女性的固有认知。
三、《扶桑》英译中的女性形象
(一)美与苦难共存的形象
扶桑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即美国出现淘金热的时期,在此期间,大批中国人移民美国,以求生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中国人作为外来人种,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承受着来自白种人的种族歧视甚至仇视。女性本就处于弱势,被命运所裹挟,在那样的社会中,扶桑所遭受的苦难更是不言而喻。扶桑血色的绸衣,畸形的小脚,受难的姿态被赋予了一种病态的美,但也正是这种美吸引了12岁的白人男孩克里斯的目光。
在原文中,红色事物的意象一共出现了五十多次,竹床上的“粉色帐子”“墙也漆成粉红色”“染成红色的西瓜子”“猩红大褂”“红绸衫”“浅红娟纱花”以及“深红的薄绫罗”等,从扶桑住所的摆设到衣衫,从浅红到深红,多样的红色刻画出一个受难却独具魅力的扶桑形象。红色,在东方具有热情、奔放的寓意,象征扶桑在受难中依旧的热情与迎合。然而红色,这个血一般的颜色在西方文化中也暗藏了罪恶的象征意义。
原文:克里斯和所有男人一样,亲近的是穿红衫子的她。[5]131
译 文 :Chris was just like all men the version of her they were drawn to was the one in red.[6]138
只有穿着红色衣衫的扶桑才能吸引克里斯,当扶桑被拯救会解救,穿着白色的僧袍,克里斯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着迷于这个扶桑了。直到扶桑重新套上红衫,克里斯才找回自己对于扶桑的迷恋。后文中再次提及“红衫子又使她圆熟欲滴”,突出了红色带给扶桑的独特魅力。红色意象激发了西方人脑海中对于“异域”东方美与魅惑的想象,这也是身着红衫的扶桑吸引克里斯的原因。但对于西方人而言,从“自我”或者说“本土”的角度来看,“red”通常象征着血腥、暴力甚至淫秽,比如“red battle”用来形容血战,“red light dis⁃trict”则表示花街柳巷。因而译者在建构扶桑形象时,对后文这一部分进行删减,减少了对穿着红色衣衫的扶桑形象的描写,以减少西方读者基于“本土”文化认知对扶桑形象的误读,但也弱化了红色衣衫的扶桑所表现的成熟女性热情迎合的形象。
除了红色的意象,东方人独有的裹小脚封建习俗也吸引了西方人的眼球。扶桑的小脚便也是吸引克里斯的原罪之一。
原文:扶桑自己坐下来,提一下裙子,两只红色溜尖的小脚一只架在另一只上。[5]11
译文:Fusang sat down,adjusted her skirt, and propped one tiny pointed red foot on top of the other.[6]12
原文多次提及扶桑的小脚,这个东方封建习俗的产物。为提倡女性的三从四德以及迎合古代社会对于女性奇特而扭曲的审美,让女性裹小脚,即缠足。文中将扶桑的小脚形容为“红色溜尖的小脚”,“溜尖”通常用来形容形状尖锐的,而“溜”字还有光滑、平滑的含义,用它形容扶桑的小脚,以突出扶桑小脚被长期摧残后骨骼呈现出来的突兀、尖锐。对于这段话,译者基本采用忠实翻译,用“pointed”以及“tiny”来突出扶桑脚的形状。而后原文中提及了“一切关于这只脚的谣传”,“谣传”被译为了“legends”。“legends”一词的使用,展现了在西方“本土”的译者在建构扶桑形象时对于神秘的东方“异域”文化的好奇,西方读者从“leg⁃ends”一词中也能体会到扶桑的小脚所暗含的传奇色彩。当扶桑的小脚近距离摆在克里斯的眼前时,他把这双小脚描述为:
原文:这是一种在退化和进化之间的肢体。[5]13
译文:They seemed to belong to a stage of evolution no one had ever imag⁃ined.[6]14
在原文中,这双小脚被称为“退化和进化之间的肢体”,退化凸显裹小脚这一封建习俗对中国女性的迫害摧残,而进化则突出这小脚似乎不属于人类,带有一种超凡特殊的美与魔力。在译文中,译者省去了退化这一层面的意思,强调了进化这一层面含义。东方缠足的封建习俗,是西方人眼中绝对的“他者”文化,他们大多未曾见过也难以理解,这一封建习俗对于女性的迫害,作为西方人的译者,也难以体会。因而在译者建构扶桑形象时,并未突出缠足对于女性的摧残,而突出的是这种受难带给扶桑独特的美。
(二)顺从迎合的扶桑形象
扶桑的艺术内涵可以看作一种作为弱势群体艰难求生的文化。[7]扶桑的美与她的苦难共存,她的美同样体现在她对待苦难的态度。
原文中时常出现人们对于扶桑的印象是有点痴傻的,她14岁便嫁做人妇,却从未见过自己的丈夫,娶她的少爷家喜欢的也是她的“口慢脑筋慢”[5]41。译者采用忠实翻译译为“slow of mind and speech”[6]45,这种慢与迟缓使得扶桑看上去似乎是痴傻的,好欺负的,没有什么攻击性的。当有人看向她时,她便慢吞吞地对人笑一下,整体动作缓慢而又迟钝:
原文:动作的稍微迟钝使你几乎是庄重的。[5]5
译文:The slight delay in your move⁃ments makes you seem almost dignified.[6]5
在生活的重担之下,扶桑的笑容却是显得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似乎对眼前的一切,对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满意极了,而实诚、迟钝的动作,甚至让扶桑这个生活底层的女性也显出了庄重。这庄重,在译文中被译为了“dignified”,而这个词除了庄重,还甚至有了些高贵,不容亵渎的意味在里面。在这一部分,扶桑的形象在原文与译文中基本融合,体现了译者对于“他者”身份进行构建时,对于“他者”形象本身所带有的“异域”文化特质的认同。
原文中多次出现扶桑跪着的形象,在苦难面前,扶桑跪着接受,甚至是迎合。当克里斯长途跋涉来找寻扶桑,却遇见了大勇,他避进了浴室,却为大勇面前的扶桑所扰心。扶桑跪着,安静梳理着大勇的辫子,这画面有着一种异常的美丽。文中多次出现扶桑“跪着的”形象,“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她跪着,再次宽容了世界”[5]242。第一句话在译文中被省略,而后一句译者忠实了原文,译为“she knelt there, forgiving the whole world once more”[6]250。基本与原文中的扶桑形象重合,也同样体现出译者对于“他者”形象的认同。
在克里斯老年失眠时,他回忆起关于扶桑的许多事,也开始懂了扶桑。
原文:她对自己生命中的受难没有抵触,只有迎合。她生命中的受难是基本,是土和盐,是空气,逃脱,便是逃脱生命。[5]243
译文:无
扶桑所受的磨难,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苦难已经与她的生命融为了一体,她对于苦难的态度,没有抵触,没有顽抗,有的都是顺从甚至迎合。译文里这段话被进行了删减,译者在构建扶桑这个“他者”形象时,对于扶桑刻在生命中的苦难以及受难后她坦然接受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美,缺少了明确的表达。
(三)闪耀的母性光辉形象
《扶桑》中多次出现大自然中树、海、沙、雾等意象来表现扶桑母性中的包容及奉献。严歌苓曾说过扶桑这个名字本身在美国文化中就含有一直向东走,可以看到的“sun-tree”,太阳树或者说神树的概念。而树这个意象也蕴含了孕育万物,滋养大地的意义。在描述克里斯偷偷去见扶桑的时候,作者巧妙地使用树的形象暗喻扶桑的女性形象。
原文:树身柔软,越向梢部越软,他脚踏上去,它便向一边谦让。[5]57
译文:The tree grew flimsier the clos⁃er he got to the top and bowed away with every step he took.[6]61
树身的“柔软”与“谦让”暗含母性的寓意,树的暗喻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承载了母性的包容与被依赖性。[8]
在扶桑接受苦难时,文中的描写多次提到了海潮、沙、雾的意象。在描述扶桑受难经过时运用了沙与海潮,以及雾的意象:
原文:像沙滩迎合海潮。[5]58
译文:The way the beach accommo⁃dates the tide.[6]62
原文:你当时不仅没有叫喊,你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5]217
译文:Not only did you not scream,you were as amenable as fog.[6]223
原文以海潮暗指给予扶桑伤害的男人,而扶桑像沙、像雾。她如同沙滩一般静止着,迎合着海浪的冲击,“迎合”在译文中译为“accommodate”,这个单词本意便有容纳、接纳之意,用以凸显扶桑母亲一般的宽容之心。同时,她又像雾,对雾的特性进行引申就是藏污纳垢的包容,这种母性特质是一种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宽厚。[9]
除了大自然意象所暗指的扶桑忍耐给予的母性,严歌苓也多次以女神胸像或神塑等意象来比喻扶桑,凸显其性格中如佛教地母一般的包容宽恕。原文中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进行自我剖析时,发现了自己对扶桑着迷的原因:
原文:竟是:母性。极端的异国情调诱使少年的他往深层勘探她,结果他在多年后发现这竟是母性。[5]100
译文:无
老年的克里斯在回忆过去时,突然明白了自己迷恋扶桑,竟是源于扶桑身上的母性。这母性,是蕴含在东方情调中最古老的母性,也是西方人眼中的神秘的东方文明。在扶桑身上的母性展现了东方女性如同古老佛教中受难、宽恕,甚至于情愿毁灭自身普度众生的母性形象。在译者所处的西方文明中,基督教义中也含有受难宽恕的概念,但其目的更多的是摒弃享乐、达到灵魂永生。[10]而并非严歌苓笔下扶桑的宽容给予甚至对于自我毁灭的情愿,因而依据形象学理论,译者在构建扶桑这个“他者”形象时,考虑到西方读者所处的“本土”文化,删减了这段文字,也忽视了其母性光芒。
扶桑遭受蹂躏后,依旧以博大的胸怀去宽容宽恕一切,她自始至终都明白克里斯也是唐人街对她施暴的人之一,但她一直埋藏心底。而当克里斯知道一切时:
原文:她有圣母一般的宽容?还是她编织了天罗地网,让他连人带心一块栽进来,永生永世逃不出去?[5]241-242
译文:A saint who could forgive any⁃thing? Or a hunter who set such good traps that he would never escape?[6]249
严歌苓使用了“圣母”这个意象来表现扶桑的母性,译者却翻译成了“saint”,圣人,虽然“saint”这个词也含有善良、宽容、神圣的含义,但却忽略了其母性形象。同时原文中提到的年轻又顽皮的母亲意象被直接省略,严歌苓把扶桑比喻为年轻顽皮的母亲,克里斯就如同她的孩童,扶桑把他犯下的罪恶看作是孩子犯的一个小错误,不告诉他这个秘密仿佛也就是母亲跟孩子一个温柔的哄骗,一个无关痛痒的玩笑。译者将其如同圣母一般的宽容,如佛教地母的大慈大悲形象进行了弱化甚至删减。这也会导致扶桑形象的不完整,西方读者从译文中能够感受到译者所构建的扶桑这个“异域”形象所包含的容忍与宽容,但无法体会其母性的光芒。
(四)扶桑的自我救赎形象
扶桑的自我救赎主要体现在扶桑对于自由的追求。对扶桑而言,苦难是可以承受的,但她无法接受建立在施救者与被救者间不平等的爱,扶桑和克里斯的结局似乎也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基因和思维差异的宿命性。[11]当扶桑被拯救会解救后,她换上了白色衫裙,呆在“小小一张蛛网也容不下的白房子”里。当大勇带着一帮中国人,诬陷扶桑是“天生的贼”,要带她回去时,扶桑不仅没有辩驳,反而承认自己是贼,心甘情愿跟着大勇一行人回去。在这段描述中,严歌苓描绘了在承认自己是贼之后,扶桑的一抹微笑。
原文:......然而她低下头,对自己深深一笑,为她得逞的一切,为她的自由。[5]137
译文:......yet she had bowed her head and smiled to herself.[6]142
这段话描述了扶桑被大勇等人带走时所呈现的典型的奴隶形象,然而,在这形象之下,扶桑却低下头给了自己一个深深的微笑,译文中省却了原文用于修饰这“一笑”的程度副词“深深”,弱化了这一笑的深意。在原文中,对于这一笑背后的原因有所提及:“为她得逞的一切,为她的自由”。扶桑的这一笑,是笑给自己的,她明白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在译文中,对于扶桑这一笑背后的原因,译者直接将其省略。从形象学角度来看,译者构建“他者”扶桑形象时,将这一笑之中所暗示的追寻自由的扶桑形象进行了弱化。在后续的描写中:
原文:你解放她或奴役她,她那无边际的自由只属于她的内心。[5]137
译文:Whether you set her free or en⁃slaved her, her freedom came completely from within.[6]142
这句话明确点出了扶桑自己心中的自由,无论别人解放她或者奴役她,她的自由只能由她自己给予。这句话的翻译中,译文省略了原文对于自由的程度形容词修饰“无边际的”,也同样是对于扶桑所追求的自由进行弱化。但译者基本上还是采用忠实翻译,建构出了自由只属于自己内心的扶桑形象。从形象学角度来看,这代表了译者对于“他者”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而克里斯,这个西方少年,怀揣着西方的骑士勇气,对于扶桑的感情不仅是喜爱,更是把扶桑看作一个需要他拯救的女奴。
原文:克里斯感到自己顶天立地,不是神话,而是现实中的忠勇骑侠。[5]187
译文:Chris felt himself of gigantic stature, if not a giant.But this was no fairy tale. He was a real,live knight,brave and true.[6]193
克里斯对于扶桑的感情有一部分来自于他心中的骑士精神,当他看见扶桑跪在大勇身前时,他的内心把扶桑看作一个需要拯救的弱势女奴,同时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勇敢忠义的骑侠。严歌苓旅美多年,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都有深入了解,因而“骑侠”一词将中国的侠义精神与西方的骑士精神相融合。然而,译者在构建扶桑这个“他者”形象时,基于西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将其处理为带有西方色彩的骑士“knight”,更符合西方读者心目中救世的英雄形象。
扶桑真正的自我救赎,体现在她所作出的嫁给即将判处死刑的大勇决定之中。
原文:爱情是真正使她失去自由的东西。她肉体上那片无限的自由是被爱情侵扰了,于是她剪开了它,自己解放了自己。[5]263
译文:He realized that when she cut the two of them apart, she was also cut⁃ting all ties....[6]272
原文中明确指出对于扶桑来说,阻碍了她的自由的东西,是带给她痛苦的爱情,她与克里斯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的爱情,带给她的只有痛苦。于是,扶桑选择嫁给已被判决的大勇,尽管她从未爱过大勇,但大勇妻子这个身份可以帮她抵御爱情的侵扰,她剪开了她的爱情,自己解放了自己。译文中仅仅处理为“cut the two of them apart...cutting all ties”,她切断了与克里斯的联系,也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原文的“解放”以及所暗含的救赎与对自由的追寻被删减。在大勇即将被行刑之前,扶桑最后一次为他梳发,他突然发现自己跪着,而扶桑站着,这个站着的形象打破了扶桑一直以来跪着的姿态。正如原文中,克里斯眼中这个“他者”扶桑,“健壮”“自由”而且“无懈可击”,这些词在译文中均被删减,弱化了扶桑形象中的强大与自我救赎。
结语
从比较文学的形象学角度来看,扶桑作为“他者”,在Silber的译文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与原文相比,大部分可以融合为一体,但对于扶桑的一些特质,译者依据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个人理解,进行了弱化删减,使其更容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西方读者通过《扶桑》,看到了十九世纪美国华人移民的生活遭遇,感悟和反思那段沉寂而扭曲的历史。这也是扶桑作为东方女性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呈现和融合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