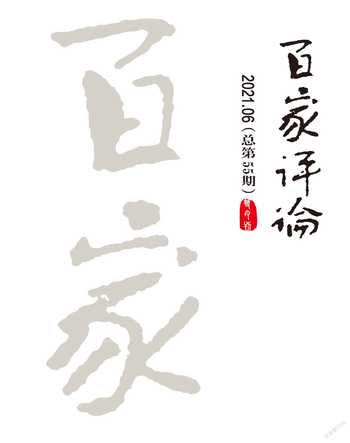你的手触到了我的伤口
周文艳
内容提要:西北于娜夜而言,不只是内容,更是底色,或是某种精神的战栗。长达二十多年的西北生活经历,使她的诗歌,在克制的激情中,呈现出一种幽暗。骨子里的忧伤,与女性的细腻融为一体,复生出丝绸般,冰冷而丝滑的孤独,以及身而为人的苍凉。女性的内敛与北方寒夜不着一字的冷峻,让她的情感,在急剧而强烈的散发中,戛然而止。她的抒情,是克制而隐忍的;她的诗意,是开阔而深远的;她的语言,是精致而斩钉截铁的。
关键词:娜夜 女性书写 克制的激情 理性 语言精致
娜夜,在当代诗人中,是比较特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女诗人,颇有女性主义色彩,甚至是女权主义。而娜夜,虽是女性的,有着女性的敏感、多情,与强烈的生命的呐喊。但她却是中性的,从单纯的“人”的角度进行思考。她是诗性的,亦是理性的,是幽微的,也是开阔的。
一、像我们的爱 没有内容
“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使得它的本质再次不可见地在我们身上升起。”①里尔克在《说明》中,写下这样一行诗。这痛苦和热情,是诗人的天赋,也是诗人的苦难。于诗人娜夜而言,亦是如此。
娜夜的诗,最大的特点是女性书写。这一切,均来源于她对女性身体,及生命体验的忠实。“女性书写”是在1970年代中期,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西克苏提出的。她认为,“女性必须书写自己:她必须书写女性,也必须引导女性书写。女性已经被粗暴地驱赶出了书写,就像被驱赶远离了身体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律法, 怀着同样的目的。女性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活动把女性写进文本,写进世界与历史。”②西克苏强调女性书写的合法性,落到创作实践上,又呼吁女性用感性、诗性的语言,书写并表达身体与内心的欲望。
女性自我内在的生命体验,是女性书写的根源,这正是娜夜有别于男性写作的地方。“我的写作从来只遵从我的内心,如果它正好契合了什么,那就是天意。”③在《与诗有关》一文中,娜夜写下了的这几句,恰恰说明了她诗歌的女性生命本体性。师力斌说:“娜夜的诗绝少知识、理论,她似乎本能地拒绝这些。她只相信感受、体验。女性经验是她天生的诗歌草原。”④正是如此。娜夜只为灵感,为内心瞬间的感触和冲动而写作,而别的什么,都与她的诗无关。她的感受是个人的,但在书写中,那些忠实于她个体生命的经验,却能够一直上升到整个女性群体,甚至人类的经验。
这便是娜夜。
娜夜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6岁起,跟着父母从辽宁到西北,自此与西北结缘。在此成长、工作、生活,在此恋爱,经历婚姻。之后到南京求学,如今,又移居到重庆。东北的冷峻,西北的辽阔,南方的温婉潮湿,既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又似乎从未属于过她。居所的游移不定,带给她的,是飘无所依的孤独。而这,也加深了她的虚无感。
常感孤独与虚无的诗人,总是会爱上黑夜。惧怕着夜的黑暗,又深爱这黑暗的复杂与兼容。黑夜,正是娜夜诗歌中最常出现的意象。夜是包容的,可以承受诗人内心,一切悲伤与虚无:“一个人/在暗处/让我把伤害 引向/自身”⑤。夜也是暧昧的,深谙一个女子内心的蠢蠢欲动。《睡前书》中,一位独居女子,躺在在清亮氤氲的夜色里,感受着空空荡荡的恍惚。微风撩动起身体的空,心间的悸动,与想象中的手,亲昵地依偎:
这一阵一阵的微风 并不切实的
吹拂 仿佛杭州
仿佛正午的阿姆斯特丹 这一阵一阵的
恍惚
空 事实上
或者假设的∶手——⑥
这女子,可以是她,又可以是任何一个女性。娜夜所书写的,是一种共通的女性情感。同为女性,我很容易被她诗中突然出现的一些瞬间,或者意象所吸引,在情感和意象的共鸣中,进入她所流露的情绪之中。一转眼,又似乎进入了自我的生命,陷入“我”的愁绪之中。此处,我仿佛进入她所营造的那种空茫。在暗香浮动的夜,触摸到一颗热烈燃烧,又冰凉如水的,无人解开的扣子。而那只手,总是时时浮现在夜里,“月光在窗外晃来晃去/像是在梦境里搜索/这一只手/是哪一只手?⑦”这手,如月光,如幻象,在她的夜里、梦里、身体里晃动。
身为女性,娜夜有着与男性诗人不同的母性、敏感、细腻、柔软和多情。有时,甚至有些脆弱,有些歇斯底里,但她并不拒绝这些。她喜欢回归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女性生命,去体验、感悟、思考,而后书写。无论写自己,还是她人,都是如此。
她写对爱情的感受,但爱情总是空茫。在遥远的地方,看到顺着风舞动的芦苇,她发出“野茫茫的一片/就像我们的爱 没有内容”⑧这样的感叹。看似轻飘飘的空茫背后,隐含着的,却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无目的的,对于爱情的决绝。
《想象》一诗,对于爱情的描写和感悟,又是那样深刻,甚至残忍:
我最好的爱都来自想象!
你不是我 也不是我渴望的∶受难的激情
同一条河流……⑨
是啊,最好的爱,都在想象中,又或者,在记忆里。有时记忆,也是一種想象。现实中的爱情,总是留有遗憾,或打了折扣。这是她对爱情的感悟和思考,后一句则上升到“人”的层面,写出人与人之间,天然的隔阂。一句“你不是我 也不是我渴望的:受难的激情/同一条河流……”,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那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⑩多么悲伤,而受难的激情,又是怎样飞蛾扑火般,滋滋作响?
娜夜写生活的那些诗,也反过来照出她的心境。在生活的别处,一个成年女性,于眼睛和心灵触碰到的一些小细节里,看见自己忧伤:“一个忧伤的肉体背过脸去”,那样无声;“使哭泣哭泣的那种声音/就要把我从岸上/拉下水了”,又透出某种隐忧和无助;而到《交谈》中,这种忧伤又多出几分绝望:
你不会只觉得它是一次简单的呼吸
你同时会觉得它是一只手
抽出你肉体里的 忧伤
给你看
然后 放回去
还是你的
多么残酷,多么现实。抽出你身体里的忧伤,让你看见,再放回去。“娜夜的诗中有一种源自生命本身的忧郁,这忧郁既区别于悲哀也区别于伤感。她似乎一直在为摆脱这种忧郁而努力,不幸却在这忧郁中陷得更深了。”就像这忧伤不增不减,还是你的,并没有因为被拿出来过,而随风散去。然而,你一旦看过,内心的绝望便不可遏制,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忧伤,一个深渊。这深渊,却只是日常生活中,一次再寻常不过的交谈。这忧伤,既是她个人的,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困境。这困境之中,包裹着短促决绝的爱,隐秘的激情,破碎的幸福,以及转瞬即逝的,微弱的快乐。
对于爱情,娜夜是反叛的,决绝的。对于生活,她是体悟的,忧伤的。她的灵魂之中,又隐含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疯狂,如《写作》一诗:
啊呀——你来 你来
为这些文字压惊
压住纸页的抖
柏拉图说,诗人在创作时,往往会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此时的诗人,恰在疯狂的边缘,用紧扼住的喉咙,无声地呐喊着:“啊呀——你来 你来”。那受惊的,不是文字,是诗人的灵魂。那抑制不住的“纸页的抖”,正是诗人生命的痛苦歌吟。而《干了什么》一诗中,那个一直在洗手的女子:“她把手都洗出血来了/她到底干了什么?/干了什么?什么?什……么?”更是近乎发狂的呓语。将这些滚烫的诗句,放在这里,我的灵魂似乎也在跟着诗人发热,发狂,颤抖不已。
娜夜是决绝的,忧伤的,疯狂的,在生活悲伤与虚无的间隙中,她又是幸福的。她站在生活的别处,反观自己,似乎洞穿了一切。也因此,常常为一些小小的,温馨的瞬间打动。《幸福不过如此》,那样安静、恬淡,似微风拂面:“我喜欢这一切/就像喜欢你突然转过身来/为我抚好风中的/一抹乱发/——幸福不过如此”。读到此处,我不禁会心一笑。是啊,幸福,不过如此,不过是一个小女孩斜倚着的,轻盈的往事。
“像幸福挨着幸福/我挨着你”,又是另一种简单的,日常的幸福。“一个老人/用谷粒和网/得到了一只鸟/小鸟也幸福”,小鸟也幸福,多好!哪怕,这只是她的希冀。一颗光秃秃的树,也幸福。那些幸福瞬间的放大,无形中,又多了些脆弱和破碎之感。
诗人娜夜无疑是重情的,不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她是孤独的,但并不孤单。她有一个在火车读书,在舞台上扮演唐婉的母亲。在西北,她还有一群诗人朋友,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诗歌群体。西北,是他们诗歌精神养成的一个关键。后来,阿信一直在甘南。古马、人邻等在兰州,而娜夜一直在流动。她在重庆写了一首《想兰州》,思念阿信、古马他们,她在诗歌里表达了这种珍贵的情谊。阿信的诗,也经常也到娜夜,和娜夜的辫子。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一种信任,甚至说一种激情,一种互相启发的友情。因为地缘因素,以及基于此的情感基础,他们在书写这片土地,书写彼此的时候,都带着很强的爱恋。这种爱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这种爱恋,客观来讲,是一种人间之爱,友情之爱。甚至可以说,它上升到了某种人间的大爱。
娜夜的诗,是生活无声的呐喊。她写生活,写爱情,友情,写婚姻,写一个女人暗夜里的情愫,写自己站在生活之外,对生活琐事,对爱,对人性的理解……有时冷静而冰凉,有时压抑且疯狂,甚至有种强烈的破坏性。有时,又是一种淡淡的,一切都已看开的恬淡与幸福。诗源于生活,诗人,又复归于生活。娜夜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叙述之中的抒情,更在于,她在叙述与抒情之中,从未停止思考。
二、在诗性与理性之间
一个诗人,他可能不是思想家,但一定要是个思考者。真正的诗人,一定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哲思意味的存在。思考着的诗人,会在潜意识中,在他的语言表面,都镀上他的精神之光。经过这种组合,他的每一句,或者说一首诗,都是极富精神性的。
从娜夜的诗歌样本来看,她是一个比较内省的诗人。在她的诗中,会处理到很多人与事,以及她身体流动的一些场域。但无论是一些意象也好,段落也好,在客观上,她有一个生活背后的精神建设。并且,这个建设她已经完成了。进一步说,她的诗里,有一种冷峻在。而且这种冷峻,在她的灵魂里已经沉淀下来,让她的部分诗歌,处于诗性与理性之间,形成了她比较个人化的风格。
关于娜夜,我之所以认可她,是因为《起风了》。但实际上,我最早喜欢的,是她那首《个人简历》,就三句话:
使我最终虚度一生的
不会是别的
是我所受的教育 和再教育
这首诗,就像汤养宗写他父亲除草的那首一般。娜夜所写的,虽说是一种非常个体的经验,但它又如此朴实。她借诗歌,批判这个时代的弊病,但这种表达又非常巧妙地借助于个人感受。同样的诗,还有《反抗》:
我的反抗 是一张哑孩子的嘴
他动了一下
又动了一下
——但世界啊 独裁的麦克风 你们什么也没听见
寥寥几句,如此日常,卻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病灶。当然,我并不只是为了说明娜夜诗歌的批判性。她更多地是通过短章,来表达那些特殊的、思想性的东西。但它又不是思想,也不是哲学,而是属于诗性哲学,或者说诗性的理性高度。在诗性与理性之间,如果把握不好,诗性就没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娜夜是一位低调而勤奋的天才,她希望用自己的孜孜写作修补生活的某些不足,把一个个躁动不安的灵魂从越来越商业化的世界中打捞上岸,这种意图使她的地方经验表达有着独具慧心的哲学意味,使其眼光可以从内心反观更宏阔的世界。”这里的宏阔,我觉得用开阔更为适合。这种开阔,实际上就是精神的开阔。只有精神开阔,才能用一个很小的短句,通过诗性的方式,完成一种扩大。昌耀也写过这样的诗,当然他的诗境,相对于娜夜而言,要更为辽阔。
娜夜的理性与思考,并不只在她那些极短的诗中。其他一些诗里,娜夜也时刻关注着她所身处的这个人间,并用她自由支配的笔,写下对社会的思考,对真相的追问。如《真相》一诗,真相拒绝了诗歌,小说,报纸,但“真相并不会因此消失/它在那儿/还是真相/并用它寂静的耳朵/倾听我们编织的童话”。这一刻,我看到一个理性的娜夜,她是冷静的,亦是清醒的。
在《生活》这首诗中,又能感受到她的眼神里,洞穿生活本质之后的无奈。“我珍爱过你/像小时候珍爱一颗黑糖球/舔一口/马上用糖纸包上/再舔一口/舔得越来越慢/包得越来越快/现在只剩下我和糖纸了/我必须忍住:忧伤”细细品读,会发现,这生活,不仅是诗人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那颗生活里的“黑糖球”,那个曾珍爱过的“你”,不过是我们在生活的苦里,所感受到的那一点点,并不持久,且稍纵即逝的甜,不过是我们在生活的夹缝中所偷得的,那一丝微弱的幸福。然而,这幸福很快便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还未脱离苦海的“我”,和一个空空的“糖纸”。就连着这“糖纸”,也仅是一个虚空的幻象而已。
这便是娜夜的特点。她擅于抓住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承接她长久以来的感悟。她的诗歌很小,又很大。小如针孔,小如一粒尘埃,一个呼吸,一滴清晨的露珠。但在“小”的背后,又延伸出一个很大的世界。她像一个生活的偷窥者,这些小小的意象,是她的猫眼。透过它们,她看到了活生生的人,看到了人世间的真实。如《合影》:
——这里,这叫做人世间的地方
孤独的人类
相互买卖
彼此忏悔
只一次合影,诗人便发出“孤独的人类/相互买卖/彼此忏悔”这样的感慨。短短几句,却让人愕然,陷入无限的静默和沉思。最后,又不得不感叹它的深刻与真实。这人间真实得,直教人生出悲凉来。
不得不说,娜夜是一个聪明的诗人,她很擅长利用她的个人经历和女性体验,去完成一种诗性的哲思。她将西北的苍茫,盛放在女性的敏感和空虚之中,隐隐地,就有了某种自由和穿透力。如《西夏王陵》,面对一座坟墓,她感受到的,是历史的空洞。但她又是自由的,超脱的:
西夏远了 贺兰山还在
就在眼前
当一个帝王取代了另一个帝王
江山发生了变化?
那是墓碑 也是石头
那是落叶 也是秋风
那是一个王朝 也是一捧黄土
这首诗中的空洞,与《青海 青海》“我们走了/天还在那儿蓝着/鹰 还在那儿飞着/油菜花还在那儿开着——”所表达的诗意一样,既蕴含自然的力量,又显示出诗人的哲思。“西夏远了/贺兰山还在”,在时间和自然之力面前,墓碑就是石头,落叶,亦是秋风,一个王朝,终会化为黄土。
娜夜就是这样,一路写,一路思考。用她敏锐的双眼,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人间,穿过人们的肉身,触摸他们的欢喜,忧愁,触摸他们的灵与肉。她写自己,写女性,也写人类,写人世间那种共通的情感、爱和创伤。她的思考,从自我的内心,引向世间的疾苦。她所处理的,是一种穿透历史,穿越时空的人的困境:即个体在时代,在人间的渺小与困惑,死亡和病痛。在时间的流逝面前,那种自然的,不可抗拒的趋势。
三、那些危险而陡峭的诗行
诗歌是最注重形式的文学,是语言艺术的精华。語言艺术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诗意性。对于诗歌的形式,兰色姆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认为诗的构架,犹如房子的结构,诗的形式就是装修。形式有自己的美,文学亦需要装饰。艾略特说,“忘掉那些哲学、伦理、功利、欲望,而专注于诗,这样的诗才叫真正的诗。”同时他也认为,“这种诗,以美的形式引人注目。”诗歌的形式,就是语言,以及语言内部的节奏、韵律、意象、张力,语言的内涵和外延等等。诗歌,也是最需要通过语言去打开意象的文体。我们读《诗经》,读《楚辞》,读唐诗宋词,读现代诗、新诗,或是外语诗,最鲜明的区别之一,便在于语言和韵律。朱自清说,诗不过是一种语言,精粹的语言。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诗之所以最难翻译,往往是由于,翻译会破坏诗在原语中的语言美和韵律感。
进入诗歌,首先应该进入它的语言。然而,中文诗又有其特殊性,这与英语、法语、俄语等,从古至今都是以词为单位的语言所写成的诗歌截然不同。中国新诗,经历了语言从古文到白话的革新,在形式上,与传统诗歌完全断裂。它是一种重新建立起来的诗的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坛又涌现出各种流行趋势。消费时代,诗人翻译腔泛滥,诗歌散文化,口水化甚至肮脏化非常严重。就在大家都裹挟其中,并纷纷效仿沃尔科特等诗人那种写法的时候,娜夜一改她在情感上的狂热,显得尤其冷静。她虽身处其中,又游离在外,拒绝了商业化,标签化和流行化。在诗坛的众声鼎沸中,她安静下来,归于最质朴的平静和低调,像黄土高原,一棵在急风中安静下来,独自修行的老树。
在静默的书写中,娜夜坚守了自己的诗歌语言,保持了她在现代汉语书写中的个性。不仅没有被翻译腔调吞没,还在孜孜不倦的书写中,反抗着文字的意义被日渐消解的潮流。她的诗,用词、用语都非常讲究。在语言上体现出珍贵的,汉语诗歌的特质。师力斌认为娜夜诗歌的魅力,“在于她不可替代的只属于她自己的语言方式。她不似欧阳江河的玄虚、西川的高蹈、臧棣的迂回、于坚的形而下、翟永明的晦涩、沈浩波的粗鄙。” 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对于一些细微的事物,娜夜有着女性天生的关注和敏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的诗歌的语言和体式。她的诗多为短诗,语言力求精致、简洁、甚至朴素,这种朴素之中,又隐含着力量。如《那一天 是哪一天》:
“太深了”我对自己说
你的手触到了我的伤口
“不是这 是这”
我拿着你的手
放在了心的位置
这样的语言,简练到近乎白描。这个分寸感,却很难把握,一不小心就会变得寡淡无味,毫无美感。但娜夜的诗,即便是简练如水,也是有美感的。这种美感,就在于她隐藏于这些朴实无华的句子背后,富有生气的画面感,以及这个画面里,那些已经浓缩了的情感及生命体悟的支撑。在这首诗中,面对伸进“我的伤口”里的一只手,“我”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冷冷地,静静地说:“太深了”。太深了,仅此而已。这种淡然,正如她对幸福的感悟一般。幸福就是,你突然转过身来,“为我抚好风中的/一抹乱发”,仅此而已。“娜夜总是这样,在立场上决绝,在情绪上婉约,在语言上精致细腻。她的诗是真正的抒情诗,省略一切多余的修饰,取消一切不必要的迂回。简洁、倾心、直抵人心。”这便是语言的魅力,语言的力量。
许是受北方严寒和冷峻的影响,使得娜夜的诗,即使是在抒情,语言也是斩钉截铁的。如《在这苍茫的人世上》,“寒冷点燃什么/什么就是篝火/脆弱抓住什么/什么就破碎”。如此简洁、直白,又饱含深意。语言如果失去了背后的意义,那一定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有时,娜夜的语言,又有着女性的婉约、旖旎,或者说绮丽。如“一粒尘埃/也有自己的心脏”,“有经验的雾 朦胧/是美的”,“疼痛的裙裾”“空荡的袖管里涌出细密的忧伤”(《地板上的连衣裙》),“从欲望里飘出/又隐入欲望/一团痴迷的舞/在感动自己的路上”(《一团白》),“月被寂寞成红唇/今夜 狡黠富有弹性”(《寂寞》),“在悬空的坠落和/动摇的弯曲中/被淋湿的眼泪/不再是眼泪”(《大雨滂沱》)。这些句子,这些词,是独属于女性才有的敏感和细腻,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神经质。但也许这就是诗性,是她对于自己的诗歌语言的追求。
娜夜的语言,像一个精致的瓮。但似乎总有一只手,时时冲动着,想要伸出去摔碎这个瓮。就像在夜里解开第二颗纽扣,放出那个疯狂的自己一样。除了那些简洁有力的,旖旎绮丽的文字,娜夜还有一些语言,是破坏性的。相比于那些精致,这些语言更像她精致的淡妆底下,所隐藏的那个有些邪恶,带着些戏谑,不加掩饰且富有恶作剧气质的本我。
在情感的表达上,娜夜是克制、隐忍且含蓄的,尽管她的内里是疯狂的,反叛的。她的诗,在看似恬淡的表象背后,有时却蕴藏着惊人的力量。她的情绪并不像火山那样喷薄而出,而是凝聚起来,隐藏在一片树叶的背后,或藏在一些漫不经心的词语里,微微地露出一些。真正看到的人,却往往会当场愕然。
情感的内敛,也注定她写不了长诗,写不了那种洋洋洒洒,泼墨般的抒情诗。她的短诗非常多,短诗中,又有很多极短的诗,如《独白》《个人简历》《大悲咒》等,最短的诗《尘世》,仅有两行:“没有幸福/只有带着伤口滚动的泪珠”。有时,我不禁会疑惑,这是诗吗?好像也是,总归是一种独特的、大胆的尝试。
对于诗歌的节奏,娜夜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模式。她的诗,大多是从叙述,到抒情,再到思考的“三段式”模式。最后一句,既是她的深思,往往也是诗眼所在。如《村庄》,先是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叙述:“她在门槛上打着盹/手里的青菜也睡着了”。紧接着抒发自己对这一情景的感受,主要是孤独:“孤独是她小腿上的泥/袜子上的破洞/是她胸前缺失的纽扣/花白头发上高高低低的风”。最后,再将主题升华到一个同理性的高度:“——只有老人和孩子的村庄是悲凉的”,这一句,与题目《村庄》遥相呼应,生成一种张力,让这首诗的内容和意象尽可能地放大。
总体而言,娜夜是一个敏感多情,又不失理性思考的诗人。她诗歌中的苍凉,空茫,幽暗和思考,贯穿始终。不过,我更喜欢她早期的诗歌,有种生命的蛮荒之力。“鲁奖”之后,她的诗中渐渐地多了一些大词、虚词,诗性也日渐平和下来。很少再有早年那种生命痛苦的歌吟,那种无声的呐喊。
注释:
①里尔克:《说明》,《里尔克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②“The Laugh of the Medusa.”Trans.Keith Co-hen and Paula Cohen.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4 (1976) :875-93.
③娜夜:《与诗有关》,中国诗歌网:http://bbs.yzs.com/thread-405423-1-127.html
④师力斌:《娜夜:那些危险而陡峭的分行》,《文艺报》,2013年11月11日第002版。
⑤娜夜:《悲伤和虚无之间》,《娜夜诗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⑥娜夜:《睡前书》,《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⑦娜夜:《哪一只手》,《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⑧娜夜:《起风了》,《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⑨娜夜:《想象》,《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⑩鲁迅:《小杂感》,《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1927年12月17日。
娜夜:《覆盖》,《个人简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
娜夜:《悲剧涌来的方向》,《娜夜詩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娜夜:《交谈》,《娜夜诗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娜夜:《写作》,《个人简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娜夜:《干了什么》,《娜夜诗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娜夜:《幸福不过如此》,《娜夜诗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娜夜:《我挨着你》,《娜夜诗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娜夜:《幸福》,《个人简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娜夜:《个人简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娜夜:《反抗》,《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张德明:《常态的性灵书写与非常态的诗歌意义——关于娜夜的诗歌精读与潜对话》,《当代文坛》2015年第5期、第6期。
娜夜:《真相》,《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娜夜:《生活》,《个人简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页。
娜夜:《合影》,《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娜夜:《西夏王陵》,《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娜夜:《青海 青海》,《娜夜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第158页。
娜夜:《那一天 是哪一天》,《娜夜诗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娜夜:《在这苍茫的人世上》,《娜夜诗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娜夜:《村庄》,《个人简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