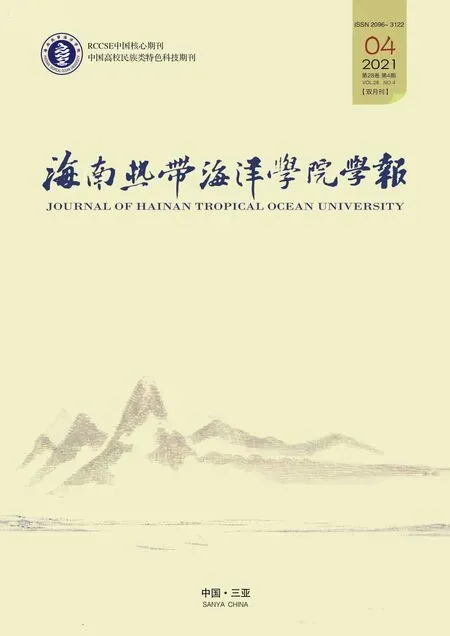晚清西沙航海指挥者的作用与西沙地图绘制的考察
郭 渊
(暨南大学 中外关系研究所,广州 510632)
近些年来,诸多学者撰文研究晚清时期两广总督派员勘查西沙及其历史意义等,对其南海维权的价值予以肯定。然而对李准、林国祥等舰船指挥者的身份和作用,以及在勘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不多。从航海技术、经验积累等方面来说,除李准撰写过回忆资料外,其他航海指挥者留下来的相关记录非常少,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晚清时期广东海上力量的有限和海洋意识的薄弱。另外,两广总督府“筹办西沙岛事务处”(以下简称筹办处)派遣的技术人员测绘西沙完毕之后,两广总督派人绘制的《广东全省经纬度图》、李准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出现了西沙群岛地名、经纬度等内容。此部分地图的完成不仅立足于西沙勘查,而且借鉴了国外的航海文献。这些内容对后来中国政府和其他社会阶层维护南海权益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探究在西沙勘查中李准、林国祥等人的作用及局限性,西沙地图的绘制与借鉴的国外航海文献的关系等问题,并总结经验教训。
一、 对李准、林国祥等航海指挥之考察
1909年5—6月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伏波”“琛航”两舰,负责再次勘查西沙。随即李准任命吴敬荣为“伏波”舰管带、刘义宽为“琛航”舰管带、林国祥为舰队左翼分统,李和林乘坐“伏波”舰。对这些人航海作用的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此次勘查的情形。李准为四川邻水人,1898年任广东钱局提调,翌年兼任广东海防善后提调和厘金局总办。直至1902年(一说1901年),为两广总督岑春煊赏识,由文入武,任广东巡防营统领,兼巡各江水师;1905年任南澳镇总兵官,署广东水师提督[1]79。李准长期任文官之职,对南海海上业务只有入江海武官之职后才有所接触。在晚清之际,海疆官员由文官、陆官担任属于常态。王秉恩为陕西华阳县人,时任广东提法史、广东按察使,精目录校勘之学,书籍外收藏金石字画甚富[2]。吴敬荣、刘义宽、林国祥航海经验丰富,能负航海指挥的重任。然而对于前两人,无论是李准的回忆录——《李准巡海记》,还是其他文献都着笔不多。吴敬荣,1874年入选清政府选派的第三批官学生出洋留学,被派往美国学习,曾任广甲管带,甲午战后被革职,后仍回广东水师,管带“宝璧”舰,时任署赤溪协副将。刘义宽,1882年秋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第二届管轮班,1884年入黄埔鱼雷局提调,1900年任广东黄埔船坞主管。两人航海经验丰富,但在1909年之前未有西沙航海的记录。1909年4月间,吴敬荣率人初勘西沙,两广总督张人骏据其报告,令筹办处组织大规模复勘行动;令人颇感疑惑的是关于吴敬荣初勘西沙的经过情形,无论是筹办处还是两广总督府都提及甚少[3]3。陈天锡在《西沙岛成案汇编》中仅做了概括性介绍:
因闻海南大洋中有西沙岛者,虑及长任荒废,亦将为东沙岛之续。于是(张人骏)始派副将吴敬荣等,驾轮前往查勘。旋据勘明复称,西沙共有岛15处。[3]3
按常理来说,吴敬荣初勘西沙之结果应该上报,以作为复勘行为的重要依据,陈天锡提及吴敬荣等查勘西沙有15个岛屿,此次前往西沙的船只是“借用”粤海关的[3]3,或许吴敬荣只是搭乘海关船只顺便前往西沙调查,海关船只另有任务需要完成,所以考察的时间短暂而匆忙,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他们为何留下如此少的调查资料。1909年3月24日,张人骏为东沙岛事致外务部的电文中提道:“既查明距粤海界甚近,且有琼海西沙岛对待之称。西沙岛现已派员,仍借用海关轮船往查。”[3]27虽说两广总督“借用海关轮船”勘查西沙,实则只派吴敬荣等少数几个人前往西沙进行调查。1909年5月4日,法国驻广州领事伯威在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记述1909年4月初两广总督府派人初勘西沙,乘坐粤海关“开办”号巡洋舰轮前往西沙勘查的经过,并且指出:“该巡洋舰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南部海岸履行巡查之责,船员对海南岛和北部湾海域非常熟悉。”[4]
笔者尚未查阅到吴敬荣勘查完毕后的呈文,但按常理应对两广总督进行报告,如果此论成立,那么其主要内容应为西沙岛上富有磷矿资源以及其他所见,这可以从筹办处勘西沙的《复勘西沙岛人手办法大纲十条》中得到证明,如其中说到“查该处各岛鸟粪,堪以化验磷质肥料”,“闻各岛潮汐涨落,每遇风日晴朗,成盐较易,良以大海巨浸之中,近岸黄水已净,每遇潮落,水存沙上。一经风日,即可成盐。且鸟粪多在高埠丛树之间,不在平沙浅滩之上”[3]5。这些内容应在吴敬荣的初勘基础上撰写的。正是根据这些初勘的调查结果,筹办处将经营鸟粪、修盐漏作为重要任务进行规划。筹办处对西沙开采资源的前景估计乐观,不仅勘查的队伍庞大,而且器物准备也多,但在复勘之际这些人和器物并未发挥多大作用,这似乎能看出吴敬荣等人初勘提出的信息并不准确。
李准在《巡海记》中特别强调林国祥的指挥作用。林国祥为广东新会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曾任广乙、济远管带,久历战事。1888年,钦州白龙尾一带,盗匪时肆抢劫,洋面不靖,两广总督张人洞命“安澜”轮管带林国祥等,“留驻白龙尾一带洋面,往来认真巡缉,有盗即缉,以安商旅”[5]。1909年勘查西沙时任广东水师提标左营游击,对广东海疆的治理做过贡献。据李准回忆,林国祥在西沙航海、勘查中做了如下工作。
首先,对西沙地理位置以及航海重要性的说明。李准说:“(林国祥)老于航海者也,言于余曰:距琼州榆林港迤西约二百海里,有群岛焉,西人名之曰怕拉洗尔挨伦(即Paracel Is)距香港约四百海里,凡从新加坡东行来港者,必经此线。但该处暗礁极多,行船者多远避之。”[6]2如果与筹办处规划“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张人骏呈文外务部对西沙地缘作用重要性的论述相比,林国祥主要从地理方位、航海等方面向李准简单地介绍了西沙情况。
李准上述之意,目的是为了强调林之“发现”西沙之功。然而无论官方文献还是李准的《巡海记》,均未交代林国祥上述之说的信息“来源”,但揭示了两广总督采取维权行动的信号,其缘由正如当时报刊所载,他国之人非法勘查西沙群岛[3]16,为避免东沙覆辙,两广总督决定派员查勘西沙,以加强海疆建设。《巡海记》说:“东沙岛之案交涉既终,因思粤中海岛之类于东沙者必不少。”[6]2准备海图、勘查之地的资料,对于经过专业训练或历经海战的航海者来说,是基本要求。笔者在查阅资料时,有一深深的遗憾,对于此次西沙勘查之行,除李准的回忆资料外,李哲浚将查勘情形按日记载,后禀呈总督府,然而“此件已无可考”[3]16;广东补用盐经历郝继业、补用盐知事陈晋庆,将考察榆林、西沙盐漏的情况禀报给两广盐运司,但仅有郝继业之禀文流传下来。前往西沙勘查人数众多,其中包括航海经验丰富者(吴敬荣、林国祥等),或知识阶层(测绘生、测绘委员),这些人是西沙航海、勘查和测绘活动的主要执行者,然而却少有文字留下,致使某些西沙勘查的重要历史场景无法得到还原。
其次,对船体及器具、绳索的安全检查。远洋船只临行前,必进行专业性检查,以保证航海的安全。此次勘查之行的两炮舰都是清廷广东水师舰船,伏波舰为木壳炮舰,由福建船政局1871年建成;琛航号为木壳运输舰,由福建船政局1874年建成。两舰参加过中法战争马江之役,战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后经修理转给广东水师。李准回忆在西沙勘查前林国祥检查两船时的情形:
此二船太老,行驶迟缓,倘天色好,可保无虞,如遇大风,殊多危险。余以急欲一行,故亦所不计。因偕林君下船,考验船上之锅炉机器,应修理者修理之。凡桅帆缆索,无不检查。其铁链之在舱底者,概行拉出船面,林君节节以锤敲之,其声有坏者,立以白粉条画之为记,概用极粗之铅线扎之,防其断也。[6]2
研究者对李准不畏艰难、勇于出海,林国祥之工作细致持肯定态度[7]。然而按一般舰船出海的例行检查来说,此类工作有专人负责,管带督促他人完成即可。李准、林国祥之所以如此,一因勘查队伍临时组合,颇为仓促,或许人手不够,来不及详细分工,他们只得亲自检查;或因二者责任心极强,事事亲力亲为。锅炉、桅帆、铁链等是舰船的重要部件,此外还应有锚、舵和测量仪器以及海上抢险设备等;尤其是操作测量仪器,需要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它们是此行勘查西沙的重要设备,李准对此未予介绍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其对这些仪器的陌生。再如李准等人原想乘舢板登陆晋卿岛,后在李国祥的建议下改乘“大号扒艇”,“国祥于海口购七八只之多,余初以为无用,今乃知为得用也”[6]5。扒艇是比舢板体积更小、轻便灵活的平底小船,适合在情况复杂的江河湖海边缘航行,以装卸物资、人员登陆。李准的上述之语,颇能反映出他对扒艇的性能以及西沙礁石纵横情况的不甚熟悉。
最后,舰船航海过程中的作用。在情况复杂的海域,航海者对于罗盘定位、海上观察以及航海图的准确利用,是保证航海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如前所述,西沙勘查队出发的时间为海上台风频发季节。从后来广东补用盐经历郝继业的呈文、李准的回忆来看,似乎勘查过程中海上风浪不是很大,但是西沙海域礁石纵横,对舰船管带等人的航海指挥,尤其是识别海中地物能力的要求很高,“此处暗礁极多,稍不慎,则全船齑粉矣”[6]5。林国祥能够根据海图和舰船速度,判断西沙航行的进程。李准对此回忆:4月11日下午4点启椗,7点时“忽见前面似一山行”[6]4,国祥判断此处向无山,必是鲸鱼,指挥舰船绕道避之;入夜后,林国祥、吴敬荣指挥舵工、瞭望者。林国祥认为,以船之速率及海程计之,此时应看到岛屿,故叮嘱舵工、瞭望者小心行船。桅杆顶持望远镜者不久报告,已见远处岛之黑影,“国祥、敬荣乃心定而直驶向该岛”[6]5。
这段航程虽无惊险,但从林国祥、吴敬荣对所见景象的分析和判断来说,可以看出他们恪守职责,且海上经验丰富。同时,由“此处向无山”“船之速率及海程”等语句来看,李国祥对西沙海图掌握比较深入,或许在其指挥下避免了很多航行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船只在岛屿(礁)之间、边缘航行之时,需要借助于海航图,并用罗盘针位、海上观测等方式综合把握航向,然而西沙勘查文献仅记载舰船航行晋卿岛的情形,对其他岛屿记载简略。同时,相关文献无说明勘查队“小工”(海南渔民)如何发挥“引水”作用,而能够“引水”无疑是雇佣这些人的重要条件;舰船之所以顺利进行,他们应发挥一定作用[8]。
吴敬荣、刘义宽和林国祥无论是参与筹备西沙勘查之时,还是勘查西沙完毕之后,几乎未留下海上航行的地图或回忆资料。据李准回忆,勘查西沙完毕后写成“《巡海纪事》一册,此外并有测绘之图,在辛亥革命时遗失”[6]1。这为我们研究问题带来了难度。林国祥指挥西沙航海,应参照海图进行,却未留下海图的线索。如与2010年代日本人平田末治等人“探险”西沙相比,就更能看出一些问题来。平田为进行“探险”,对西沙地图和资料进行了搜集,完毕之后对航行路线及所见均有记载。由于文献有限,李准、林国祥、吴敬荣等人在航海中的指挥情形难以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尤其他们对各种关系到舰船安全的因素如何把握更是语焉不详。此外,据1909年6月21日的《香港日报》(HongKongDailyPress)记载,西沙勘查完毕后所形成的报告,由李准呈报给两广总督,“一份关于西沙群岛的长篇报告已由负责最近西沙群岛考察的李上将送交总督。据说该报告包含了许多有趣的岛屿发展计划,包括建造一座钢桥,连接晋卿岛和琛航岛”。[9]2然而李准的呈报,并不见于西沙勘查文献的记载,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 西沙地图的绘制及借鉴国外航海文献
近些年来学者探讨了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又称两广督练公所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于1909年7月重新编制完成的《广东舆地全图》,参考吸收此次测绘西沙资料的情况[9]90。笔者查阅此时期的文献资料得知,广东包括西沙地图的绘制是清政府陆军部命令的结果。1909年6月21日《香港日报》刊登消息:“(两广)总督已接到北京陆军部的指示,要绘制一幅广东的军事地图,公文促请总督尽快准备好地图。总督已委派许多测量员进行这项工作。”[9]2
该报所述简略,应是西沙勘查前后两广总督接到了陆军部绘制广东包括西沙地图的命令。1910年8月28日的《顺天时报》刊登“咨测绘西沙岛详图”消息,内容颇为详实,报道说陆军部要求两广总督派员勘查西沙之后,应提供西沙地图的详实内容,如航线、各岛经纬度、面积等:
顷闻陆军部以粤省西沙岛,地处南极,现当筹办伊始,西及东斜,列各岛计十余处之多。所有航线、经纬、飓风、潮汐,亟应详测经纬线,度地势高低、广阔若干,面积大小若干,内外纱线、水泥深浅,附近明暗礁山多寡、大小形式,潮汐涨落距水面若干尺,四时泛大小尺寸,以及四季风侯,大小何者为多,本岛出入所经航路,某岛至某岛(距)离若干,系泥石底、石底或沙底,由西沙至三亚、榆林、崖州输运往来速率、晷刻均宜详查。日前已咨粤督请详细勘测,各绘一图,合绘一总图,并详加注说,以资参考,而昭慎重。想西沙岛交通由此异常便利矣。[10]
从《顺天时报》刊登的内容来看,与西沙筹办处制定的“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第一条相类似,并指出两广总督府要提供给陆军部西沙各岛图及总图。该报与《香港日报》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陆军部索要地图的动机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同时,从查勘西沙群岛的目的来说也是如此,筹办处拟定西沙开办八条大纲的第一条,指出西沙地缘位置在海防上的重要性:“查西沙各岛,分列十五处。大小远近不一,居琼崖之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中国南洋第一重门户。如不及时经营,适足启外人之觊觎,损失海权,酿成交涉。东沙之事,前车可鉴。今绘成总分各图,谨呈帅鉴。应请宪台进呈,并将各岛一一命名。书立碑记,以保海权,而重领土。将来东沙岛收回,亦请一律办理。”[3]3后来两广总督张人骏在给外务部的“奏报”,基本上将该内容写进去了。
清政府陆军部所要的西沙地图,应与《广东全省经纬度图》、李准编写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有关联。《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不仅精确绘制了勘查队登陆或瞭望的甘泉岛、琛航岛、中建岛、晋卿岛、珊瑚岛、东岛,还有未到过的玉琢礁、华光礁、浪花礁和盘石屿等岛礁。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图标绘出的西沙各岛屿的经纬度在此次勘测的呈文、回忆资料中并无具体说明。此外,还有如下因素不可忽视。(1)“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中有一条明确说明,“测试各岛,详测各岛经纬线度”[3]4;加之勘查队派遣16名测绘人员,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应测绘了所到各岛的经纬度,至于其他未登陆岛屿,在舰船经过之时,能否进行海上“遥测”则难以确定。(2)勘查队曾携带西沙群岛总、分图各两张,但未说地图的名称,以及是否为中文地图;勘测完毕后,勘查队又“绘成总分各图”,然而根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未能发现原图。学者周鑫[11]270-273认为《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的绘制借鉴了国外南海资料,其说有一定道理。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再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广东全省经纬度图》借鉴国外海图的情况。清末之前,中国对于西沙的地图绘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依然用“计里画方”的方式绘制南海诸岛,基本上未用经纬度制图,加之少有实测西沙的行动,致使清末勘测群岛时难以参阅到中国地图;19世纪末,英、德等国绘制的南海地图传至国内,如清末陈寿彭翻译1894年英国海军部海道测量局出版的《中国海航行指南》,节译中国海的部分并将其译成《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其中有关于东沙、西沙各岛屿及经纬度的内容。该书成为两广总督府确认东沙地理位置、属我的历史依据,亦是与日本交涉的重要根据,正是有此经验,从而使该书可能成为勘查西沙的参考资料。
与此同时,德国西沙水文勘测资料亦成为参考资料。1881—1884年,德国测量船对西沙进行精密的水文测量,1885年德国《海道测量及航海气象年鉴》第12册第12—30页《西沙岛》(Die Paracel Inseln)阐述西沙航海指南,绘制了西沙各岛屿、暗沙等。该图对英、法、美等国绘制西沙地图影响甚大[12]。广东补用盐经历郝继业给两广盐运司呈文中曾提到《西沙志》(1)郝继业呈文记载:“琛航”舰“(四月)十八日抵西沙,即西沙志所云罗拔岛(甘泉),十九日至大登近岛(琛航),二十日至地利岛(中建),均于各岛近处泊船。”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西沙岛成案汇编》,第19页。,陈天锡对此记述说:
近浏览西沙岛旧卷,清宣统元年盐经历郝继业等禀牍内,叙轮抵西沙,谓即《西沙志》所云罗拔岛。以此而知前人已有西沙岛著述,惟遍访坊间及知交处,欲一睹《西沙志》之书,殊不可得。究竞此书作于何时,无从考订。以意度之,所谓罗拔,本是西名译音,则其书出世,必非甚古。可以断定,独是《西沙志》即乏流传,而西人海图又非尽人可睹,西沙岛之位置虽长存于天壤,西沙岛之名词实湮没而不彰。[3]1-2
其次,国内报刊对《广东西沙群岛志》的宣传,可能使之成为西沙勘查的参考资料。近些年来,中国学者考证认为,郝继业呈文中的《西沙志》即前述德文《西沙岛》,中国报刊界将之译为《广东西沙群岛志》[1]85[11]270。国内较早刊载该内容(节译)为上海《时报》,分别在1909年5月14日、15日、16日的第2版连续刊载,名为《广东西沙群岛志》。根据该译者说,约在1900年,将德文《西沙岛》译成中文,“昔有一德人,因造航海水道图,曾至其处,悉心研讨,著为志,收入航海集中。余于十年前译为华文,以备查考,备置箱箧,不复记忆久矣。近日偶加检阅,觉颇可存,因特刊登报端,或足备调查该岛之一助也”[13]。
《时报》连续刊发《广东西沙群岛志》,或是对两广总督府1909年4月派员初勘西沙、随即酝酿再勘西沙引起的社会各界关注的一种回应。据笔者的查阅、对比,1909年6月下旬广州实业研究所出版的《砭群丛报》第3期刊出《广东西沙群岛志》,为《时报》刊载之大部分内容。1909年6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7卷第6期刊载《广东西沙群岛志》,内容与《时报》相同。从《砭群丛报》和《东方杂志》刊载的《广东西沙群岛志》时间来说,是两广总督派舰复勘之后了。该志记载的西沙岛屿、暗沙等30余处,主要岛屿记有经纬度。这些报刊公开发行,尤其是广东地方报纸《砭群丛报》关注地方时事动态,西沙勘查人员或许能够阅读此报刊载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报刊译介的该志没有地图,而根据上述分析其地图参考资料很可能是《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
最后,《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是近代以来较早以经纬度方式标注中国东、西沙岛的地图,这与以前的西沙笼统的述说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近代领海图的测定,主要由各沿海省份自行测量、研究、编撰。下面从两个角度分析《图说》的形成。
一是绘制西沙海图,应是遵循清政府陆军、外交、海军等部之指令的结果。早在1908年,清政府外务部根据外国舰船侵入渤海湾,我与之交涉无果的经验教训就指出:“亟应委派精于测绘人员,实地勘测凡中国领海权内,所有华侨殖居各岛及大小荒岛,绘具图说,标立石址,咨部核定,以便照会各驻使。嗣后凡中国勘定各岛,不得任意侵占,并咨沿海各该督抚,随时饬派军舰巡视情形,俾免损失海权,以维邦交,而资保护。”[14]勘测中国近海岛屿的领海之事,其执行者为海军舰船,海军部亦认为:“领海界线关系国家主权,现值扩张海军,振兴渔业,应将界线划清,绘列精确详图,宣布中外,共相遵守。”[15]李准在《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的“序”中说遵照指示绘制西沙:“去年(1909)军谘处檄行来粤,调查海防要塞。余乃命材武之士分道探测,幕下之宾分门编纂,踰时累月,始底于成。”[16]此内容为广东全省之总图和分图,是根据军谘处指示而划定,其中自然就包括西沙群岛的内容。
二是李准率舰队勘查西沙,目的之一是绘制海图,然后呈报,“当会商安帅亲往探明,绘成海图,以便呈鱼师、海港、军部、内阁立案”[17]。他在《巡海记》中也说明此情况:“所历各岛,皆令海军测绘生绘之成图,呈于海陆军部及军机处存案。”[6]8李准将其绘制的西沙海图,并视为自身的职责,其勘查西沙为形成《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奠定了基础。《图说》未对西沙进行战略定位,但强调琼州岛的国防上的重要性,这在20年前就被两广总督张之洞写进奏呈。仍应看到,因为当时清政府与各部、沿海省份才开始讨论领海问题,很多内容(领海基点、基线和范围)都未明确,故划定领海的“精确详图”目的难以达到。
上述两幅地图的制作者(集体或个人)具有一定的军事背景,其中包括对诸多之地的战略解说,这些地图的制作是建立在调查和查阅晚近时期资料而成的,因此对于一些主要地理标物进行了经纬度的绘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广东舆地全图》包括广州府、琼州府图等,均附有图说一篇,所属各州县地图均附图表,内含沿革、疆域等内容。从东沙、西沙群岛与广州、香港以及榆林、海口相对的位置,以及所经群岛航线来说,可见其地理位置及战略重要性。《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侧重于海上防守战略,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复取粤省旧图与西人新图互相参校,经今实测详备为多,为图二十有七,用以上闻,藉资考镜。凡险隘之远近、港湾之大小、沙线之浅深、营垒之废置、阴阳潮汐之变、江海内外之别,昈分鳞列,烂然异观”。[16]《图说》对江河、沿海险要之地进行了解说,但是对远洋岛屿的军事战略作用未予说明。这与两广总督府对两群岛缺乏深入的调查,尤其是将经略南海的“支点”放在榆林、三亚两港有直接关系,当时两港尚待建设,两群岛的开发只能置后了。
三、 西沙“安设无线电报”及其他问题
筹办处在西沙群岛“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中,提到要在西沙“安设无线电报”以通消息,但未提及该事的具体负责之人。根据1909年6月1日《图新画报》记载,筹办处为完成此任务,曾派遣专门人才“海口电报委员”刘镛参加勘查西沙。原文为:“该处风浪极大,来往船只,时多阻隔,必须添设电报,以便传递消息。查西沙对岸,即为崖州万县陵水各处。该处原已安设电线,现带同海口电报委员刘镛,随往详查辟岛事宜。”[18]而西沙群岛“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的名单上,并无列有专门的无线电人员,仅写有“广东试用通判刘镛”(2)在清朝通判也称为“分府”,管辖地为厅,此官职配置于地方建制的府或州,功能为辅助知府政务,分掌粮、盐、都捕等,品等为正六品。通判多半设立在边陲的地方,以弥补知府管辖不足之处。。两处资料对比,“海口电报委员”或许就是刘镛的真实身份了,“试用通判”从官阶角度来说近似虚职,此人的工作主要在无线电方面。
在勘办西沙办法中,可以看出筹办处认识了到无线电在边疆建设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前沿的想法。两广总督衙门及其所属南洋水师和沿岸海防要塞,早已使用无线电通讯,广东地区民用无线电通讯也开始使用。香港在对外发展航运业时,过往南海船只多受困于台风。在勘查西沙群岛后所列的“开办大纲”之中,单列一条说明“安设无线电,以通消息”之事,该条建议或许就是刘镛提出的。此前筹办处在“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仅说“安设无线电”之语,而在“开办大纲”之中说得较为全面,且当做重要任务来完成:
各岛皆相离窎远,一切公牍风信,非电不能迅传。拟请在西沙岛,设无线电一具。榆林港,设无线电一具。东沙岛,设无线电一具。省城,设无线电一具。轮船上,设无线电一具,以期呼应灵通。[3]17
这里面提到的“西沙岛”,即西沙群岛,筹办处计划在西沙某一岛屿上架设无线电,但没有说具体岛屿名称。西沙最大的自然岛屿是永兴岛,应为架设无线电、灯塔等工程首选之地。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海军部实地勘查西沙群岛后,决定把建设灯塔的地址选在永兴岛上。永兴岛建台为固守海疆之举,颇符合南海地缘形势的发展,当时国内报刊对此多表赞同[19]。前往西沙勘查的测绘技术人员,其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如下角度进行分析:筹办处在设计西沙无线电建设之际,又规划了西沙无线电与榆林港、东沙岛、广州(省城)等地互通消息的设想,既可以迅即传达政府、军队指令,又可以随时向过往船只通报海上台风情况,实现军、政、民之用相结合。榆林港为军港,广州为一省政治、经济中心,西沙、东沙为海防前哨(当时执政者和报刊未阐述南沙之作用),如此西沙、东沙就纳入国家管辖体系了(3)对于晚清时期两广总督府派员勘查西沙的国际法意义,英法日的航海文献、政府官员或学者是予以肯定的。参见张莉媛、刘永连《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调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8页。。而上述无线电台能运转,离不开技术人员的培训,直至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筹设东沙电台时,技术人员的培训就进行了,而此时西沙的无线电台的建设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也在筹划之中。
从南海经略、开发的角度来说,技术人员前往西沙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勘定各岛的地势地理,包括能否进行土地开垦、资源开发与运输、船只泊位、道路的修建、厂房和房屋建设等。筹办处特意提到技术人员要“勘定各岛。择其相宜,修造厂屋,并筑马路,安活铁轨,以资利运”[3]4。在这一总体部署下,参与西沙勘查的各种力量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航海、勘查以及维权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第一,在西沙勘查筹划过程中,筹办处居中协调各方、统筹全局,期望在勘查基础上,尽快进行群岛的开发工作,这在“开办大纲”之中有集中体现。而西沙开发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除社会有序、安定之外(此因素最为关键,但晚清时革命风潮勃发,政局动荡不安,开发群岛的社会环境复杂),还应包括对群岛的准确、详实的勘查,如群岛分布、资源情况、气候条件等,可以说勘查工作是否详实而准确,对政府的决策作用甚大。因为西沙勘查的时间不长,筹办处原来拟定的详勘各岛的计划未能全部实施,所以两广总督府劝业道酝酿进一步勘查群岛。在朝代鼎革之际,后来勘查西沙未能成行,但1909年两广总督府的西沙勘查为后来规划建设西沙奠定了基础。
自甲午海战之后,海军队伍的建设和技能的积累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地方舰船的建造、维修,以及海上队伍建设在这一背景下亦无起色。据中国近代造船专家伍景英讲述:“清代末年广东最大之舰为‘伏波’‘琛航’两舰,均为木质差遣舰式。”[20]34这两艘轮船亦年久失修,勉强可以前往西沙,别无舰船可用。至于说海军派遣人员,文献资料对此记载不多,这与广东海军基础力量的薄弱有关。《广东海军学校概况》描述清末民初广东海军学校时说:“广东海军学校因规模不大,学生人数不多,而且在广东的舰艇多是小型,实际力量不大。”[20]39这种状况决定了对榆林港、西沙的建设和设防难以进行。
第二,此次勘查使中国政府对西沙岛屿的分布、地缘位置和作用有所认知,初步明确了西沙群岛在中国海疆经略中的位置,以及对外来侵略的警惕,试图通过开发活动来加强西沙和内地的联系,并使之作为巩固边疆的重要手段。这体现了经略海疆思想的可贵变化,然而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并未明确开发西沙的依托对象,致使其视野主要局限于招商开发岛上资源,并未清醒意识到渔民、农民等阶层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如在海港、岛屿建设和开发以及在维权斗争中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等等,执政者并未对此进行认真思考。
20世纪初,磷矿(鸟粪)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开发、居住环境的恶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开发热情,这一矛盾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未根本解决。这体现了广东地方执政者依然用中国传统的治边理论来应对当时瞬息万变的南海局势,而对于列强即将到来的侵扰缺乏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尤其是执政者对领海主权、海权理论等前沿海洋理论不了解,当时英美等国经略海洋、殖民侵略,乃至于海上称霸恰恰是运用这种理论。可以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官员在时局转换面前落伍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其举措不合时宜就比比皆是了。例如西沙勘查人员对群岛情况的呈文或回忆,主要是一种地理事实的记述,几乎未能从航海专业角度进行述说或总结经验,这或许与他们的出身、经历有关,但更多的是经略海疆经验的严重不足。
第三,对于清末两广总督派舰勘查西沙之行为,自民国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报刊和学者对其历史意义均予以研究和宣传,尤其在出现西沙争执以及海疆危机时更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中国政局动荡,此时法国及其殖民机构挑起西沙、南沙争执,引起日法、中法之间的交涉,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宣传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多引用清末勘查和筹划开发西沙的历史。甚至30年代英国对中国西沙主权的支持立场,也源于1909年李准将军率领中华帝国海军炮艇来此群岛等一系列西沙主权宣示行为。[2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捍卫西沙、南沙主权舆论鼎沸之际,除李准将其1909年勘查西沙经历见诸于报刊之外,他人(林国祥1909年冬病逝于广东寓所[22])未见在报刊上阐发勘查、维权之行动。
前往西沙勘查之人有些后来还担任民国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应对20世纪20—30年代南海维权斗争有所了解。如西沙勘查时绘制西沙地图的海军测绘生,广东黄埔水陆师学堂第九期毕业生萧广业,1922年任广东水上警察厅科长、大本营舰务处军备科长、海军部专员,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海军部少将教育厅长,1934年任广东海军学校少将校长[23]。同为第九期毕业生孙承泗,1912年为广东海军练营营长,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部(闽系)驻汉办事处主任,1930年为海军部总务司文书科科长[24]。两人长期在粤任职,1920—1930年代初风起云涌的西沙事件、南海九小岛事件发生时,两人均在任上,却未发声,其缘由有待于进一步查找资料进行研究。此外还有吴敬荣、刘义宽,前者在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侍从武官,1924年4月晋升海军中将;后者于1913年初任广东海军学校校长,1921年7月充任海军警卫营营长,1929年8月2日为海军部轮机上校侯补员。当然,每个人在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面临的环境不同,对他国侵扰中国海疆的感知程度也不同,我们不能无端推测。
结 语
回顾此历史,可能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西沙勘查的记忆,更多的是一个民族走向海洋坎坷历程的一个片段,只有从本质上认识海洋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才能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更卓越地走向海洋,并利用各种契机开发海洋资源、巩固国防,以强国富民。这一过程是渐进完成的,随着南海局势的日趋紧张,执政者的海洋意识不断觉醒,正是在启蒙和维权的相互激荡中,才最终促使国人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化。同时,这种转化是痛苦的,须从两个维度进行认知,一是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限制了自身向海洋转向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这一切又是国力不足、千疮百孔的国运所决定。二是这种转化的被动性,是在列强不断渗透乃至于掠夺、侵占我领土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奴役和殖民的过程充满了血与火,而此过程又是与整个民族苦难的历史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