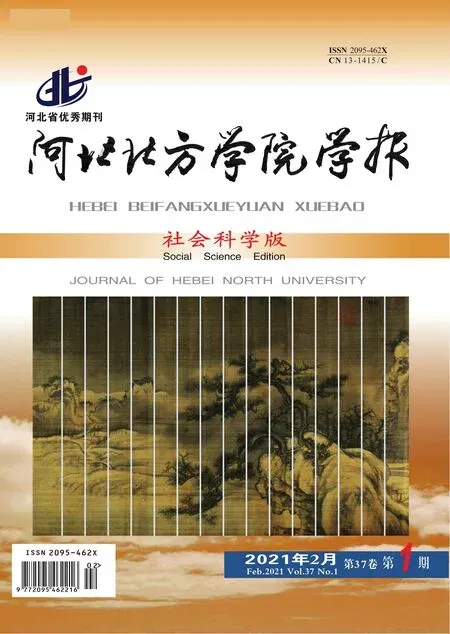唐传奇到宋话本中婚姻文化的嬗变
张 润 滋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婚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常是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唐传奇和宋话本中均有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显现出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婚姻观念,还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的婚俗礼仪。对比唐传奇和宋话本中以婚恋为题材的小说,探究两者在婚姻观念、婚姻中介以及婚姻习俗3方面的不同,可更好地理解唐宋时期的婚姻文化。
一、婚姻观念
门第观念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极为盛行,士庶以及良贱不婚已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在此影响下,男女双方谈婚论嫁极其注重门第。隋唐时,门阀观念虽较之魏晋南北朝有所减弱,但仍是男女缔结婚姻的基本准则。唐朝在婚嫁方面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如《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载曰:“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1],就直接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士庶有别,良贱不可通婚。这种横亘在男女婚姻中的士庶或良贱不婚的思想在唐传奇中多有反映。首先,门当户对是媒人说亲的必备前提。如《张老》中园叟张老想通过媒媪求娶韦氏长女时,媒媪怒曰:“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2]404,即直言告之他与韦氏长女身份地位不相匹配,不可说媒。其次,这种婚姻观念也影响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如《定婚店》中杜陵韦固十分在乎门第高低,遇见月下老人后便问自己可否与司马潘昉女成婚,在月下老人告诉韦固瞎眼妇人所抱之女为他的妻子后,他不仅骂曰:“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苟不能娶,即声伎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妪之陋女”[2]410,甚至还让其奴仆杀掉那个女孩。韦固因未来之妻与自己门第不配甚而企图杀之,更显现出当时门第观对于婚姻的影响。再如《李娃传》中,李娃看到本为士族子弟却因受自己欺骗而钱财皆空,为父鞭打几近丧命并最终沦为乞丐的荥阳生后,毅然决然将其带走照顾,并助他读书学习。在荥阳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2]108时,李娃却与他说道:“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2]108李娃最初是出于歉意与爱才帮助荥阳生读书学习,但她是一个清醒且自我认知明确的人,深知自己的娼女身份低微,并不是已成为成都府参军的荥阳生的良配,悬殊的身份地位差距使两人的婚姻绝无可能,所以在荥阳生功成名就后甘愿主动离开。离去之际,她还不忘劝说荥阳生与豪门贵族女子或家族的中外表亲结婚。由此可看出唐代门阀制度的残酷,也可看出士庶和良贱不婚的观念对唐代婚恋的影响。概而言之,有唐一代,重视门第且士庶不婚已为各个阶层所接受,是整个社会婚恋观中的一种普遍共识。
至宋代,士庶和良贱有别的观念逐渐消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科举取士数量的增多,寒门才子找到了更为便捷的跻身官场之路,这使宋人婚恋观逐渐摆脱了门当户对与良贱不婚观念的影响,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随着宋代城镇经济的极大发展,市民阶层也逐渐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也使长久以来形成的良贱体系趋于淡化。门第观念的消逝与良贱体系的淡化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婚姻中主要表现为人们择姻时由看重门第转而崇尚官爵与才学,良人与娼妓亦可通婚。这种不问阀阅与良贱可婚的婚姻观念在宋话本中有所体现。首先,媒人说亲时,已不必一定讲求门当户对。如《苏长公章台柳传》中,歌妓章台柳善文好歌,一日遇苏轼与佛印饮酒,苏东坡便与她说:“我今日出了题目与你做一篇,若做得好,纳了花冠褙子,便与你从良嫁人去,敢是我就娶了你。”[3]253此番话语是苏太守的醉中之言,酒醒即忘,但可见当时良贱不婚的观念已被打破,士人可与其他社会阶层通婚。虽然章台柳并未嫁给东坡,但她“寻个媒人,嫁与一个丹青大夫,姓李名从善去了”[3]254,也算是得到一个好的归宿。其次,婚姻中男女双方更不甚讲求门户。如《风月醉仙亭》中,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初识之时,司马相如“父母双亡,孤身无依”[3]261,但卓家却是“赀才巨万,童仆数百,门阑奢侈”[3]261。两人的家世地位有显著差距,并无在一起的可能。但当时司马相如已为文章大儒,“贯穿百家,精通经史,虽然游艺江湖,其实志在功名”[3]261。卓文君看重他的才华,认为他终有功成名就之日,便毅然决然与他离家私奔并结为夫妻。作者塑造了卓文君这一世家大族之女的形象,并详细讲述了她与司马相如私奔和结合的全过程,说明在宋代门第高低已不再是择偶的第一标准,人们的择婚观念已从重门第转而重才学与官爵。
唐宋两朝是婚姻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与门第观念的淡泊,从最初士庶和良贱不婚到之后不问门第与不论出处皆可结亲,这是唐宋两代婚姻观念中的一大不同,也是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二、婚姻中介
媒妁文化是中国婚姻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古代,人们就已充分认识到媒妁对于婚姻的作用,如《礼记·坊记》“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4];《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5];《孟子》“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6]。唐宋时期,媒妁文化更为兴起,《唐律·户婚》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正式将媒妁之言纳入法律条文。宋代官媒兴盛,据史料记载,宋代已有媒人行会组织。朱彧《萍洲可谈》记载:“熙宁年间(1068—1077)‘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掌议婚’。”[7]103可以看出,唐传奇和宋话本中关于媒人的描写十分常见。比而较之,两者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媒人形象的塑造上。唐传奇中对大部分媒人只有粗略的形象描写,而没有性格刻画,也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宋话本中的媒人形象塑造则更为完整与细腻,也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在对媒人形象的塑造中,可窥见媒人行业在唐宋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唐传奇描绘媒妁文化的篇章极少详细描写媒人这一角色。其中提及媒人的,如《霍小玉传》:“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余年矣。性便僻,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帅。”[2]76此篇记述了媒人鲍十一娘的出身与来历,使其形象较为完整。而其余大部分唐传奇对媒人的描写往往一笔带过,并没有详细的人物形象描写以及说媒过程。如《柳毅传》仅以“有媒氏告之曰”[2]65一句完成了对媒人这一角色的描绘,并以“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宰。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2]65简单几句,便讲述了说媒情况。之后,媒人未在《柳毅传》中出现。再如《莺莺传》,除从张生口中说出“媒氏”两字外,再也没有关于媒人的相关描述。至于《李娃传》和《枕中记》等较知名的唐传奇小说甚至没有对媒人这一角色的描写。由此可见,媒人在多数唐传奇中是一个“隐形人”,她们的作用仅是引出说媒的对象,功成便可身退。因此,作者通常对她们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特征不加详尽的叙写。唐传奇对媒人形象以及媒人行业特征的忽略无法全面呈现出唐朝的媒妁文化,仅从较少的小说中可看出,虽有唐一代媒妁之言已被纳入律法,但说媒这一行业在当时并未真正兴起。
宋话本中关于媒人的描写增加且更为详细,媒人种类繁多且呈现出高度职业化特征。现存宋话本中有《快嘴李翠莲记》《刎颈鸳鸯会》以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10余篇涉及媒人,在篇章数量已超越唐传奇。宋话本中所描写的媒人个性更突出,语言更活泼,形象也更加生动。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王婆是一个“与人收生,作针线,作媒人,又会与人看脉,知人病轻重”[3]308的全能型人物,她知道周胜仙与范二郎两情相悦,也知道胜仙得的是心病,所以劝说周母为救胜仙之命而结亲。王婆奔走周范两家,机智又圆通,充满了市井气息。由话本对于媒人的大量而细致的描绘中可见,宋代媒人行业十分发达。此外,宋代媒人分工也十分明确,一方面表现在对媒人性质的描写上。宋话本既写了专以作媒为生的私媒,如《西山一窟鬼》中明确提到邻居王婆“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3]25;又写了职业的官媒,如《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中裴太尉为女儿说亲时“寻两个官媒婆”[3]354。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媒人说媒场景的描写上。宋话本中媒人常两人同行,一道说媒,如《三现身包龙图断怨》“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3]405,但实际上说媒由一人主导,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中张媒和李媒一同为张古老去韦谏议家说亲时,便是张媒负责与韦谏议沟通。当韦谏议询问她们到来的目的时,张媒说:“有件事,欲待不说,为他六两银;欲待说,恐激恼谏议,又有些个好笑。”[3]405面对韦谏议的愤怒,也是张媒安抚道:“他说来,只问谏议觅得回报,便得六两银子。”[3]405综上所述,宋话本中表现出分工明确媒妁文化,正是宋代媒人行业发达的重要体现。
唐传奇与宋话本中关于媒人形象的叙写清晰地显现了唐宋时期媒妁的基本情况。较之唐传奇,宋话本中关于媒人的描写大大增多,形象塑造也更细腻。推而可知,宋代媒人文化较唐代更发达,宋代媒人在婚姻里的中介作用也更明显。
三、婚姻礼仪
婚姻是人生大事,对男女双方乃至两个家庭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一桩婚姻的完成常伴随着一系列的风俗习惯。宋代婚俗较前代有诸多不同,这体现在唐宋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与唐传奇中的婚俗相比,宋话本中的婚俗有两个极为显著的变化,即:六礼中继纳采与问名后“相亲”的出现;亲迎时新娘子“坐轿子”习俗的出现。
唐传奇以“作意好奇”和“始有意为小说”为特点,以“文采与意想”为归趣,因而对婚俗之事不以为意,常在叙述中一笔带过,进而转入叙述的重点。首先,唐传奇中男女双方或直接通过媒妁之言成婚,如《张老》中园叟张老通过媒媪求娶韦氏长女;或因两情相悦成婚,如《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柳毅传》中柳毅与龙女早已钟情彼此,媒人为柳毅和龙女说亲后,“毅乃卜日就礼”。其次,唐传奇中亲迎多乘车。乘车这一风俗在《南柯太守记》中被提及,如“生端坐车中”,“生降车辇拜”[2]90。总之,唐传奇中极少有对于婚俗的详细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唐一代世人对婚俗较不重视。
宋话本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以描写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主,因而对一系列婚俗礼节描写甚为详细,尤其对新出现的“相媳妇”和“坐花轿”有所提及。“相媳妇”习俗出现在《西山一窟鬼》中,媒人王婆为吴教授和李乐娘说亲,在问陈干娘要过帖子后,王婆便同陈干娘说:“你便约了一日,带了小娘子和从嫁锦儿来梅家桥下酒店里等。我便同教授来过眼则个。”[3]26这便是让吴教授“相媳妇”。到约定那日,乐娘与锦儿在东阁里坐,“教授把三寸舌头舐破窗眼张一张,喝声采不知高低”[3]26-27,当日便插了钗,代表“相亲”成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载曰:“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即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8]值得注意的是,相亲时男女虽可相见,但女子处于被动地位,决定权仍在男子手中。如《西山一窟鬼》“相媳妇”的过程中并没有描写李乐娘的态度,插钗之后,便“下财纳礼,奠雁穿书。不则一日,吴教授取过那妇女来”[3]27。由此可知,宋代新出现的“相亲”这一习俗仍有不足之处,而这在《张主管至诚脱奇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开封张员外“年逾六旬,须发皤然”,媒人将他的“年纪瞒过一二十年”,把“小如员外三四十岁”的少妇说与他作妻子。花烛之夜,少妇发现真实情况已悔之晚矣,这段婚姻的受害者定是这位不知真相的少妇。“坐花轿”习俗可见于《快嘴李翠莲记》中,李翠莲出嫁时来到门口,听到张宅先生念“香车宝马到门头”,暗示新媳妇是坐轿子出嫁。而后翠莲临出门分钞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先生与轿夫一干人听了,无不吃惊”[3]729。当到了夫家门首,媒人让翠莲张口接饭,“翠莲在轿中大怒”[3]729,直接表明翠莲出嫁时是“坐花轿”。此外,唐宋两代婚俗礼仪还有许多新变化。如程序的简化,古代一直延续《仪礼·昏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礼。至宋代,《宋书·礼志》记载:“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将六礼简化为四礼。再如嫁娶论财风尚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通婚书中除了写上男女名字和生辰,还要详细写明随嫁的田舍、资产及奁具数目[7]118。
总而言之,与唐传奇相比,宋话本小说在婚姻观念、婚姻中介以及婚姻礼仪3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唐传奇与宋话本中婚姻文化的不同是当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