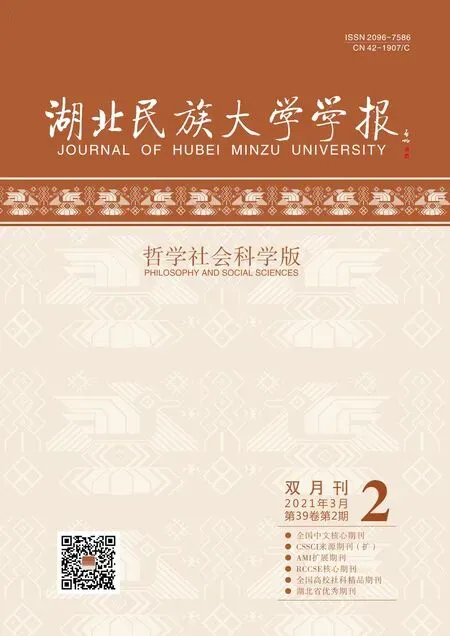贫而不困:当下中国农村不存在贫困陷阱
王志章 杨志红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贫困与人类社会进程相生相随,是困扰世界发展的重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不断扩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优化体制机制,取得了世界减贫史上前所未有的卓越成就。截至2020年12月,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动态清零,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十三五”脱贫攻坚的目标已如期实现,但脱贫与小康是两码事,小康与高水平的小康更是存在很大差异。大多数深度贫困地区刚走出原发性的贫困,还存在产业基础不牢,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任务繁重,因残、因病、因学、因婚致贫,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返贫的风险客观存在。同时,还有一部分因建档立卡时收入高于贫困线但摇摆在贫困线上下的边缘人口,极易因外生或内生的因素陷入贫困。对于这种贫困群体在“脱贫—返贫”中持续摇摆的现象,机会不平等的环境集合已不足以解释其成因,故而诸多学者试图从“贫困陷阱”假说去解释。
关于贫困陷阱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马尔萨斯首次在其著作《人口论》中对人口陷阱作了详细论述,他以美国的人口增长和英国的粮食生产为例,指出:“人口增长速度是呈几何比率增长的,而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则是呈算术比率增长,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明显缓慢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最终导致人均资本增长被人口增长所抵消,退回到初始水平。”(33)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J. Johnson, 1798,pp.13-18.此后,贫困陷阱理论开始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并被不断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别是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理论从供给面和需求面两个角度,分析了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和低资本形成率之间的循环过程。在欠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低下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同等下降,储蓄和购买力严重不足,从而限制了市场的扩大,并进一步抑制了市场规模的扩张,导致各个生产部门产出水平降低,最终再次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34)R. Nurkse,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pp.119-127.,正所谓“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纳尔逊进一步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会稀释人均收入水平,进而导致收入水平维持在低位。(35)R. R. Nelson, “A Theory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6, no.5, 1956, pp.894-908.在这之后,缪尔达尔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体系,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论。他利用扩散效应与回流效应分析了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间相互影响的循环累积关系,即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初期,回报效应的影响大于扩散效应,会导致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扩大,最终形成“循环积累的贫困陷阱”。(36)G. Myrdal,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us, London: Duck-worth,1957,p.26.这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贫困陷阱可能的形成机制,但都认可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是导致贫困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
显然,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理论低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忽视了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替代性问题。即使在人口增长无限制、生育决策为内生变量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仍然可以被不断积累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所取代。(37)G. S. Becker and J. B. Robert,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3, no. 1, 1988, pp.1-25;G. S. Becker, K. M. Murphy, & R. F. Tamura,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 5, 1990, pp.12-37.为了探讨这一问题,Galor和Weil(1998)在模型中设定了三种不同的制度,在第一种制度下人力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都十分缓慢,此时产出增长完全被人口增长抵消,经济处于长期稳定状态;在第二种制度中技术增长率增加的同时人口增长率稳定,此时人口增长吸收了大部分产出增长,但人均消费增长缓慢,最终导致人均收入出现倒退;在第三种制度中技术增长率提高的同时人口增长率减少,甚至为负增长,在这个阶段整个经济社会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一方面,技术进步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促进了产出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导致了技术进步放缓,最终导致社会在前两种制度中来回更迭。(38)O. Galor and N. D. Weil,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4, 2000, pp.806-828.Galor等的模型证明了技术进步和人口规模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关联,并依据模型完整描述了欧洲及其分支国家的发展过程。但这个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对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量现有技术可以通过进口的方式引入,摆脱了对人口增长的依赖,最终模糊了人口规模和技术增长之间的关系。Karagiannis等(2005)发现,如果技术的替代弹性(CES)和可变替代弹性(VES)足够低,经济稳态将会被破坏并长期维持在一种动态均衡状态。(39)G. Karagiannis, T. Palivos, & C. Papageorgiou, “Variabl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 in C.Diedbolt & C.kyrhsou eds., New Trends in Macroecomics, 2005, pp.21-37.这种动态的长期均衡将导致生产函数呈现非凹性,非凹的生产函数为贫困陷阱的存在性提供了直接证据。(40)S. Brianzoni, C. Mammana,& E. Michetti, “Local and Global Dynamics in a Discrete Time Growth Model with Nonconcave Production Function, ”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 Society,vol. 2012, 2012, pp.1-22.贫困的动态均衡表明贫困陷阱是“慢性或持续性的贫困”,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而不是仅仅在某一时刻的贫穷,是“任何可能导致贫困持续的自我强化机制”。(41)C. B. Barrett and M. R. Carter,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Traps and Persistent Poverty: Empir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49, no.7, 2013, pp.976-990.故农村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户、农户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贫困而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的情形。
随着国内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农村是否存在贫困陷阱这一命题。解垩采用2008到2012年CHARLS数据模拟出农户的动态资产积累路线,发现曲线成凹性并收敛于一个动态均衡点,并不存在贫困陷阱。(42)解垩:《农村家庭的资产与贫困陷阱》,《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6期。袁航等将地理禀赋向量综合成单一指标,利用半参数模型发现中国农村存在着“地理禀赋”的贫困陷阱(43)袁航、刘梦璐、刘景景:《基于健康营养调查(CHNS)对地理禀赋贫困陷阱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17年第6期。,但在其之后的研究中,他分别基于门槛模型检验和消费平滑检验方法,都未能找到贫困陷阱理论在中国的证据(44)朱烈夫、吕梦敏、袁航:《消费平滑假说检验:对农户贫困陷阱争议的解答》,《农村经济》2018年第2期;袁航、时卫平、刘景景:《农户贫困陷阱假说在中国的检验:来自面板门槛模型的新证据》,《统计与决策》2019年第6期。。周力等在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和空间随机性的基础上,利用1986年至2009年间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样本,发现农户资产始终趋向高水平均衡点,认为连片特困地区不存在多均衡状态贫困陷阱。(45)周力、孙杰:《气候变化与中国连片特困地区资产贫困陷阱》,《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也有一些学者认可“贫困陷阱假说”(46)史源渊:《新贫困陷阱: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政策反思》,《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邹薇、方迎风:《中国农村区域性贫困陷阱研究——基于“群体效应”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贫困陷阱是否存在的研究成果存在争议。
总的来讲,由西方学者创立并发展的贫困陷阱理论,拓宽了贫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无论是制度失灵抑或贫困文化问题,都多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其设计的模式也带有强烈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和价值倾向,缺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理论探讨。且基于家庭资产数据的微观实证仅发现中国农村不存在贫困陷阱,并未解释贫困陷阱不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故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历史层面、个体及社会文化层面出发,基于脱贫领域的事实来阐述当下中国农村不存在贫困陷阱的依据,以期为贫困陷阱理论提供“中国经验”。
二、贫困陷阱假说在中国农村不成立的五大依据
经典贫困陷阱假说实际上内含了一种国家层面的低水平稳态,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发展要求也由追求国民财富量的扩张稳步延伸到社会产出质的改善(47)李曦辉:《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稳中求进”的转变和实现路径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增长仍能为贫困减缓赋能。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48)《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造福人民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第1版。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主导下,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升,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型、重塑与贫困陷阱表现出的经济式微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笔者认为西方的贫困陷阱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制度下的现实。
(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高质量反贫困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从解决全民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应对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摆在国家战略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以科学的谋划和超常规的举措,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之路。(49)汪三贵、胡骏:《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正如习近平同志2020年3月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的,“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50)《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2020年3月11日,http://dangjian.gmw.cn/2020-03/11/content_33638376.htm,2020年4月10日。,这种政治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恰恰是保障中国不存在贫困陷阱的根本政治基础。
首先从根本政治立场来看,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永远的奋斗目标。作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制定的各种政策、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想办成而过去没有办成的大事”(51)孔小皖:《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学习时报》2019年2月25日,第2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总领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而这一切成绩皆源自共产党对人民立场的坚定。回首一路走来的历史,贫困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和民生大题,自改革开放之初小康社会的构想提出以来,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52)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求是》2020年第11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大背景下必须实现的硬任务,自此目标更加坚定,措施更加精准,效果更加突出,受益群体更加普惠。
再从反贫困具体工作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科学的顶层设计、合理的战略安排与密集的政策举措皆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党和国家破解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难题、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53)赵承、霍小光、张晓松,等:《习近平的扶贫故事》,《人民日报》2020年5月20日,第1版。这无不彰显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领袖不忘初心的人民情怀。在具体的工作中,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贯穿了“中央—地方—基层”整个系统,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央层面,党对整个贫困治理工作谋篇布局,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不断推动党在贫困治理领域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推动不同历史阶段的扶贫工作提供了科学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和方向指引,及时回应了贫困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地方层面,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把中央方针政策转化为具体实施的方案,做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等工作,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组织体系,推动了党政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新形势下多元减贫工作格局的健全完善,为完成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扶贫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尤其是处在扶贫、发展、小康第一线的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群众的实际情况与想法最为了解,有绝对的“带路”优势。作为农村基层各项事业和经济活动的领导核心,基层党组织在贫困治理的实践中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向,优化人员配备,形成了一批党性强、能力强、改革意识强、服务意识强的基层工作队伍,他们既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代言者,又是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取得的新成绩,深化了人民群众对“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盛中国”的认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54)《习近平到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强调: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把党和政府温暖送到千家万户》,2012年12月3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31/c1024-20060098.html,2020年4月12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基本实现且成效超出预期,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从人群看,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区域上,主要是深度贫困地区;领域上,主要是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短板明显”(55)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求是》2020年第11期。。即使绝对贫困已经解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是并且长期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关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贫困政策接续指明了方向,即使一些地区或部分群体返贫问题客观存在,但坚定的制度优势必能快速作出回应,使出政策“高招”,阻断返贫和落入贫困陷阱的根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贫困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具有高度的前瞻性,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减贫实践的高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贫困这个最大的短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高度,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拓展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为世界反贫困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我国取得的扶贫成就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丰富详实。
从制度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把整体利益置于社会首位,把人民放在社会发展的中心,这在根本上克服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的利益冲突与对立,形成并增强了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强化了治理机制“全国一盘棋”的道义基础和思想内涵。(56)秦刚:《抗疫斗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求是》2020年第12期。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不均衡的发展就不是高质量的发展,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扶贫工作开展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以党中央为核心,构建起“部门协同、地区协作”全方位、多层次的扶贫协作体系,如中央定点单位扶贫、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定点扶贫、山海协作、军队帮扶等形式,使欠发达地区有机会对接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减少社会资源内耗,通过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
从制度优势惠及经济增长与贫困缓解的事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实际的制度。贫困陷阱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互动失败的结果。宏观上贫困陷阱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可归结为市场不完善导致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及协调失灵。(57)解垩:《农村家庭的资产与贫困陷阱》,《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6期。在经济制度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善和市场信息不完备的重要补充,减少市场排斥持有较少资源者但又防止政府对市场过度把控而影响市场自身协调能力。在基本分配制度上,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重视再分配调节机制能较好地调节收入差距、改善不平,当贫困人口因无法改善现状而面临一种低水平的摇摆即将突破资产分布的门槛点时,再分配机制便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提升农户收益,对农户的资产产生一种正向的外生刺激,使其能有效抵御外在的负向冲击摆脱低水平均衡的状态,促进社会公平。(58)陈斌开、李银银:《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再从制度的开放性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倡导开放共享、互帮互助的制度。贫困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解决贫困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往往会势单力薄,“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集思广益,共同应对贫困问题的挑战”。(59)李应齐、韩晓明:《共谋发展,推动国际减贫合作——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综述》,《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4版。在国内集中推进减贫的同时,中国积极推进和加强国际减贫合作,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为国际减贫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巨大贡献。一是传播中国扶贫经验,助力国际扶贫合作伙伴增强自我减贫能力,中国及时总结、分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不断强化国际减贫体系的中国话语。二是中国对外超越传统的资金援助模式,完善、创新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丰富和拓展合作领域,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加强“中国—东盟”“中非”“南南合作”等减贫合作,提高与伙伴国家在贸易、投资、人力资本、医疗健康、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强度,推动中国和减贫伙伴国家形成益贫的增长环境。正如同国内精准扶贫过程中所倡导的,中国致力于国际减贫合作的“造血化”,一方面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摆脱贫困掣肘,另一方面有利于构建包容性的伙伴关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公共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增强中国扶贫经验的“软实力”。三是中国注重汲取经验,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跨越贫困陷阱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汲取了国际上优秀的反贫困经验与模式,动态改进创新贫困治理机制,形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之路,为应对相对贫困问题、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开放发展的理念,丰富了对外开放的内涵,也在这个过程中反向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为国内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创造了诸多机遇。
(三)减贫战略动态调适为不同阶段扶贫任务提供强大政策支持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减贫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和国家都能察觉不同时期反贫困形势的变化,顺势而为,及时对减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做出适应性回应和制度调整。阶段性的减贫经验不断累积、完善与自我发展,汇聚成强大的减贫基础,这个基础是循序渐进的,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和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也成为能够规避贫困陷阱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具体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内一穷二白的发展现实和巨大的贫困体量,我国相继出台了《1956-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文件,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战略。一方面通过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调动农民积极性;另一方面以人民公社为依托初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此阶段的减贫实践因缺乏经验未明显减少长期积累的贫困体量,但国民收入普遍平等的状态以及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益贫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减缓奠定了基础。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标志着体制改革扶贫的开始。为减少我国大量的赤贫人口,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10项政策》(1985)、《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4)等系列文件(60)罗平汉:《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5、180、187页。,解决农村整体贫困问题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在主要措施上,一是推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着力优化购销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二是通过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贷款、支持老少边穷地区贷款等7项资金支持政策,对特困落后地区展开有针对性的帮扶行动;三是改革城乡分异的户籍制度和就业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农民非农就业,扩充农民的收入来源。总体上,这一时期政策红利高度释放,农村贫困状况得到了较大缓解。
在总结前一阶段取得扶贫进展的基础上,国务院于1986年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后改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研究拟定扶贫开发工作的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扶贫战略,标志着扶贫工作进入规范化阶段。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首次制订了贫困标准线,确立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370个省级贫困县,持续增加专项扶贫资金,并派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贴息专项贷款。在1985至1993年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扶贫资金201.27亿元,年均增长16.91%。(61)数据来源:《财政部副部长解读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16年8月27日,http://tuopin.ce.cn/news/201608/27/t20160827_15302531.shtml,2020年6月20日。规范专业的扶贫手段取得了显著成效,按照1978年的贫困标准,到1995年末,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由1986年的1.31亿人下降至654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5.5%下降到7.1%。(62)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第346页。在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的背景下,以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标志,中国扶贫开始转向“扶贫攻坚”模式。“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扶贫目标确定在三个层面: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改善贫困地区科教文卫的落后状况,并强调“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时7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一由政府主导的、有纲领指引、有明确目标的扶贫行动,对这一时期的农村减贫发挥了重要作用。贫困发生率由1994年初的7.7%降至2000年末的3.5%,全国农村地区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进入21世纪后,为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升扶贫资源的投入效率,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推动扶贫资源进一步下移,从县域范围缩小为村级,实施以贫困村为重点的“整村推进”专项扶贫工作。2004年,国务院扶贫办出台了《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通知》,开始实施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工作(“雨露计划”),以职业教育、创业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劳动力解决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瞄准村域的扶贫模式使贫困县、贫困村的农户收入实现了迅猛增长,其中贫困村农户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1196元跃升至2008年的2485元,平均每年增长近13%。(63)张伟宾、汪三贵:《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到2010年底,按照2008年的国家贫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至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2.8%。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以《“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等文件为实施方针,我国逐步建立起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退出机制,脱贫质量明显改善,增强了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显著提高了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党中央的政策始终能关注到扶贫实践的最前沿,瞄准切实存在的问题,把扶贫资金、扶贫项目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确保扶贫对象(区域和个人)能够真正包容性分享资源,共享发展红利,全面解决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对制定新的历史阶段减贫战略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多元风险分摊机制为防范农户落入贫困陷阱筑牢安全网络
贫困往往与风险、脆弱性有紧密的联系,从个体视角来看,风险不确定条件下农户贫困陷阱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金融资本具有逐利性质,农户因资产数量或质量达不到金融资本风险评估的最低水平时,便会被正规金融排斥,一旦非正规金融也无法有效分担风险时,农户便完全暴露在风险之外,直接造成福利损失或降低,使农户陷入贫困而难以走出;第二,贫困农户自身资源匮乏无法选择高回报的生产项目,也难以承受高回报项目所需要的生产过程,只能采取一种低风险低收益的经营模式,与高资产指数的富裕农户差距愈来愈大,长此以往他们的资产陷入到一种低水平的稳态。(64)M. R. Carter and C. B. Barrett,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Traps and Persistent Poverty: An Asset-Based Approach, ” Social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42, no.2, 2006, pp.178-199.故微观层面上防范贫困陷阱是以防止这两个条件形成为前提的。
首先,正规风险分担机制是否有效。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小农传统和历史渊源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7月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汇总数据,全国农业经营户总计2.07亿户,小农户占比为98.08%,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全国农业从业人员数量的90%,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旧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65)阮文彪:《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经验证据、突出矛盾与路径选择》,《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1期。与二三产业相比,传统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模式具有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自身发展的脆弱性和产业发展的弱质性等特点,致使其在资本自由竞争的赛场上屡次败阵,从而陷入低水平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金融排斥是农户贫困的关键因素,这里面囊括了储蓄支付排斥、信贷排斥和保险排斥等。(66)尹志超、耿梓瑜、潘北啸:《金融排斥与中国家庭贫困——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0期。笔者2018年在云南、贵州、四川等西部十省(自治区)对1158户农户的调研发现,当提及农户向周边熟人朋友或者金融机构借到一定资金的可能性时,有6.39%的农户表示完全借不到,17.27%的农户表示大多数情况下借不到,43.95%的农户表示能借到部分。谈及不能借到资金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的房子不值钱,不能抵押”“不知道怎么去证明自己讲信用”等。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且正规金融对农户进行信贷配给的情形下,单独依靠非正规金融是很难起到风险分摊作用的,这一点得到了Jalan和Ravallion(1997)(67)J. Jalan and M. Ravallion, “Are the Poor Less Well Insured?Evidence on Vulnerability to Income Risk in Rural China,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58, no.1, 1999, pp.61-81.、You(2014)(68)J. You, “Risk, Under-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Assets and Dynamic Asset Poverty in Rural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29, 2014, pp.27-45.等学者的证实。所以,在中国情境下,微观角度贫困陷阱的第一个形成条件最终落脚点还是得看正规风险分担机制是否有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了金融支农的广度和深度,从金融基础设施数量上来看,截至2019年9月末,全国共有村镇银行1633家,其中中西部占65.7%,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1296个县(市、旗),县域覆盖率达到70.6%,其中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90.5%,户均贷款余额33.5万元,除农村信用合作社外,国家是金融支农的主力军;在政策性金融支农方面,截至2019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5.59万亿元,重点支持棉粮油收购、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等领域;金融机构支农方面,截至2019年末,仅中国农业银行一家便新增县域贷款5472.22亿元,其中在83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贷款余额10 914.4亿元;农业保险方面,从2007年到2018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由51.8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572.65亿元,提供的风险保障从2007年的1126亿元增加到2019年3.6万亿元,农业保险服务农户数由4981万户次上升到1.8亿户次,农险承保农作物品种覆盖270余种,累计向3.6亿户次支付保险赔款2400多亿元。此外,财政部还出台多项税收优惠支持农村金融和涉农小微企业发展,银保监会也出台了一系列办法,如《关于推进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通知》(2019)、《关于做好2020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的通知》等,力求缓解农户发展的金融需求,营造“三农”发展良好金融环境。从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来看,纵向上正规金融支农、扶贫效应明显,且在金融市场有序发展的前提下,往往能带动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基于此,我们可以作出第一个风险分担机制有效的判断。
其次,小农户是否能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改善经营模式壁垒?我国贫困地区大多数处于地势第一、二级阶梯上,地形以高原、山地和盆地为主,农业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部分地区人地矛盾比较突出,农业生产多以家庭为单位,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条件不足,产业基础薄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发展,“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已经逐渐不能满足产业现代化和家庭生活需要,但小农生产体量仍然巨大,“大国小农”仍是现阶段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国情,且脆弱性只是小农的一个面,小农仍在各种压力下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具有“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韧性,这种韧性一旦有了国家化、组织化两个方向力量的注入,便可进一步增强其韧性,在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上更好地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69)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从宏观政策导向来看,自2004年起,党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七年聚焦“三农”问题。从2003年到2016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从1754.4亿元增加到17 539亿元。农村公共事业水平也大幅攀升,2001年开始,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学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并于2006年、2007年扩展到全部学生,极大地提升了农村学生的教育保障水平;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试点,到2010年基本实现了农村居民全覆盖;2004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国推行,保障那些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户的基本生活。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小农户的致贫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更是被视为党的工作的总抓手,摆在了优先战略地位。近三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2018)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文件,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指明了目标,明确了重点,从宏观层面建立“国家与小农”的双向责任机制,筑牢了风险防范的政策网。
从现代农业发展特点来看,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方向,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这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相比,其更具市场敏感性和抗风险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鼓励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契约型、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小农户专业化生产,提高小农户自我发展能力。”这给了小农户一个多元化的思路。再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来看,农民日报社发布的《2019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经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认定的龙头企业数量达到8.7万家;截至2018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有217.30万家,是2012年的3.15倍,是2007年的83倍,实有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9.10%。在农民日报三农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555家合作社有效样本中,能够带动入社农户户均增收2000~4000元的合作社达到40.2%,户均增收4000~6000元的占比18.6%,增收6000元以上的达19.4%,辐射带动效应比较明显。可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合作社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三产融合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依托”功能,充当了小农户与现代市场经济交流的媒介,提高了他们谈判和抵御风险能力,从微观层面建立起“组织—小农”的双向责任机制,使得传统小农户有机会向现代小农转变,从而融入现代农业,由此可以作出第二个风险分摊机制有效的判断。
(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脱贫人口永续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虽然我们不能把贫困的成因单一地归咎于“贫困文化”的影响,但扶贫对象的思想观念、能力和参与形式通常被认为是关系内生动力的三大关键因素。(70)左停、金菁、于乐荣:《内生动力、益贫市场与政策保障: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真脱贫”的路径框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它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的重要精神支撑。(71)《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9年6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6/15/c_1124627379.htm,2020年4月17日。精准扶贫的实践证明,中华文化在贫困地区的弘扬与延伸对摆脱意识和思路上的贫困有着重要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情境下,传统道德、责任、荣誉、集体观等约束性思维不断注入,强大的文化认同氛围使得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演化机制生成为囊括核心价值观、自我观和脱贫行为倾向的一个层层嵌套而又相互接续的逻辑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核心价值观的指引是内生动力形成的核心要素。(72)傅若云:《脱贫内生动力: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14日,第3版。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良好的育人功能。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各民族前进的步伐参差不齐,但这个艰辛曲折的过程留下了无数先民与贫困抗争的痕迹,其中精华的部分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和内在力量,仍然能够在现代社会发展和治理体系中适用。优秀文化具有超时代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扶贫进程中展现出重要的“文化育人”功能,改善了贫困地区部分贫困群体文化贫困与精神贫困的现实,打破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个体发展的文化锁定。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革,伴随着时代政治语境转变及相应的文化传导与输送,形成了各民族间不同的心态秩序,从而演绎成不同的民族态度及行为意向。(73)龙金菊、高鹏怀:《民族心态秩序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2期。或许各民族物质意义上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但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演变中经济上日益相互依存,文化上不断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条件、共同物质基础、共同价值诉求、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从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民族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民族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和远景期许。我国后发地区和贫困高发区域多为民族地区,全面解决贫困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互帮互动,久久为功,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性事业,才能实现“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最终目的。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发挥着思想凝聚作用。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各级党委、政府在新时代民族工作基本方向指引下,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难题、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遵循,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繁荣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其次,在具体举措上,中央政府立足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注入帮扶资源,创新帮扶形式,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队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也积极投入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帮扶实践,构建起了多元参与的全国扶贫大格局,使少数民族群众也能平等共享发展成果,能够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迈进全面小康社会。最后,在思想意识上,伴随着扶贫大格局的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密度增加,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交流信任、共同携手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这种氛围内化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并外化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解决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问题的实际行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成为攻克贫困难题、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推动减贫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迈向更高水平。
三、居安必思危:已脱贫地区须防范贫困陷阱风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基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消除了绝对贫困,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制定的目标。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行采用的2010年贫困标准即“按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仅高于世界15个极端贫困国家的贫困标准,远低于世界银行2018年新补充的每人每天3.2美元的中等偏低收入贫困线,与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更存在一定差距。且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各地区的政策举措多具有“短平快”的特点,绝对贫困的消失也只是现行贫困标准上统计意义的消失,实现高质量脱贫发展任重而道远。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并未消弭,只要收入差距客观存在便有一定规模的相对贫困群体,这种贫困不单单局限于物质收入上的差距,还体现在精神意志、思想文化、社会资本等方面,会使处于相对贫困标准以下的群体容易产生“被剥夺感”,降低自身未来发展的信心,这将加大防范返贫工作的难度,亟需保持脱贫与返贫的动态平衡,减少返贫次数并缩小返贫周期,时刻保持防止贫困陷阱的警惕。
(一)贫困人口生计脆弱:返贫风险依然很大
摆在首位的应是返贫问题。返贫是一种贫困治理过程中常发生的客观现象,狭义的返贫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后又返回到贫困状态的过程,广义的返贫还包括濒临贫困的人口因各种因素而导致现状恶化陷入贫困的情形。一方面返贫削弱了脱贫攻坚的工作绩效,另一方面使得贫困群体的生计能力降低,减少了脱贫政策的获得感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一旦返贫周期变短而次数变多,陷入“返贫—脱贫—再返贫”的怪圈,就很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截至2019年底,还有近200万的已脱贫但不稳定户,近300万略高于扶贫标准的边缘户,受市场经济状况变化、劳动力供求变化、农业的自然风险、家庭意外事件以及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所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影响,这两个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这为巩固脱贫成果和防范返贫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我国近几年返贫现实情况来看,贫困群体因病、因残、因灾、因学、因疫等不可预期因素返贫占据返贫群体的主要比例。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比例达到44.1%,涉及近2000万人,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的比例达到45.7%,这部分人抗风险能力较弱,即使短期脱离贫困仍蕴含着较大的返贫风险。李长亮曾根据深度贫困地区某县的返贫数据估计发现,在2017年初统计的1316名返贫人口中,患大病和长期慢性病及残疾的人口返贫的比率分别是健康脱贫户返贫率的1.49倍和1.41倍。(74)李长亮:《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返贫因素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自然灾害对脱贫户的冲击一般来说次数较少,周期较短,但这种冲击若不能把握在可控范围内,一次冲击也很容易延伸为对脱贫的长期影响。按照《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十三五”规划》的进度,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上做到了“应搬尽搬”,还同步搬迁了500余万未纳入建档立卡的农村低保户、特困户等同步搬迁人口,迁入地生态要素明显变好,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泥石流、山洪、塌方等地质灾害和地方病发生的可能性,因灾致贫几率得以降低。但部分地区因自然条件限制,搬迁地选址受限,搬迁带来的风险分担能力不足,因而返贫也呈现出较明显的连片性、区域性、集中性特征。同时,大部分贫困地区灾害救助体系并不完善,应对灾害的公共设施建设欠账严重,救援队伍预警能力和业务能力有待提升,群众灾害意识也严重缺乏。且洪涝、旱灾、冻害、雹灾等自然灾害、农作物病虫害以及牲畜流行疾病等属于不可预期因素,导致收入不确定性较大。
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返贫也不可忽视。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曾把可行能力定义为“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75)B. Selwyn, “Liberty limited? A Sympathetic Re-Engagement With Amartya Sen’s Development As Freedom, ”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46, no.37, 2011, pp.68-76.,贫困被视为一个人基本能力的缺乏或是被剥夺。事实上,没有人是真正喜欢贫困的,但因匮乏的地理资本和差序化发展格局的限制,我国大多数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总体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封闭的贫困地区,他们缺乏摆脱贫困的可行能力。从外部视角来说,这种能力缺乏可能体现为地区总体经济发展较慢导致涓滴效应不足、贫困农户的机会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村庄内部结构分化排斥、市场经济波动加剧农户主体脆弱性等(76)许汉泽、李小云:《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其对策——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外部视角的缺失往往能够通过较发达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和主流扶贫实践来排解。内部视角的能力缺乏则包括贫困农户本身缺乏农业或从事非农行业的物质资本、缺乏满足行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接受能力低、个人身体素质较差人力资本缺失等,使得“能做的事情做不了,想做的事情做不好”。且这些因素容易在贫困户家庭中代际延续,即使这类群体脱贫了,受匮乏的生计资本和脆弱的风险抵御能力影响,其下一代仍存在较高的返贫可能性。
(二)贫困形态和结构变化:相对贫困问题凸显
当以物质收入为衡量的绝对贫困被消除后,贫困向常态化转型,但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相对贫困一般有物质和非物质两个维度,物质层面的相对贫困一般是基于需求资源(食物、衣着等)的比较,当一个家庭或个体的资源达不到参照群体的贫困标准时,便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77)J. E. Foster, “Relative Versus Absolute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8, no.2, 1998, pp. 335-341.;非物质层面则囊括了健康、教育、更深层次参与社会的能力等以及自我认同等。虽然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差距客观存在。两组数据可以说明:其一是基尼系数,2000年至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由0.409上升到0.467,一直高于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其二是居民收入倍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4倍,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20%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 401元,20%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0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的10.35倍。事实上,一个经济体中相对贫困的数量和程度与再分配机制有着紧密联系,是其制度效率的展现,但其影响却渗透于收入与非物质的各个层面。非物质视角的相对贫困则比较隐蔽,其量化和监测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由于相对贫困的动态性和延展性特点,一旦非物质视角的需求被“排斥”,会逐渐延伸至物质层面,使得个体陷入发展的怪圈,马太效应显现并不断自我强化,反过来加剧相对贫困,使得整个经济体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
第一是贫困体量的变化。从国际上目前相对贫困标准的划定经验来看,大多数还是以收入/消费为核心,采用居民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衡量,如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是居民平均收入的30%,一些OECD国家设置为家庭中位收入的50%,欧盟设置为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线,并按照这个标准估计得到2021年我国户籍人口相对贫困数量为1.06亿人,其中农村户籍贫困发生率为11%。(78)邢成举、李小云:《相对贫困与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改革》2019年第12期;叶兴庆、殷浩栋:《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改革》2019年第12期;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沿用与国际上相似的相对贫困标准不符合当前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和城镇化进程不完备的情形,货币意义上的相对贫困标准仅能够体现“贫”,故应该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指数来确定。(79)王小林、冯贺霞:《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3期。从我国居民收入现实情况来看,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6 523元,按40%的比例计算得10 609.2元,远高于现行绝对贫困标准,加之基尼系数仍然偏高,居民收入倍差较大,无论采取哪种测量方法,都面临着巨大的相对贫困人口数量。第二是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改变。从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来说,由于过去二元的发展格局使得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水平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与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若按照城乡一条线的划分标准,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仍占据较高比例。(80)沈扬扬、詹鹏、李实:《扶贫政策演进下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7期;沈扬扬、李实:《如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兼论“城乡统筹”相对贫困的可行方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宏观层面上国家没有陷入低水平的稳态,农户层面也未出现“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等恶性循环,即使少数地方有返贫现象发生,但周期较短,次数可控,故现阶段中国农村不存在贫困陷阱。但由于脱贫攻坚期各项政策举措具有冲刺的特点,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资源禀赋较弱,对政策刺激的反应速度较慢,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尚比较脆弱,还有极少数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不足,未形成可持续脱贫的体制机制,客观层面上存在返贫可能。虽然这些返贫可能是短期的,但若不施加政策干预或者是干预不当,极有可能演变为长期行为,从而有恶性循环可能。同时,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不再有贫困问题,区域间、微观个体间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事实,相对贫困问题凸显,相对贫困不仅意味着贫困体量的变化,还意味着贫困结构和贫困格局的转变。位于相对贫困门槛点的群体,极有可能在受到风险冲击后转化为绝对贫困。故尽管我国农村不存在贫困陷阱,但仍然面临一定程度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把握城乡格局变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机遇,顺应城乡居民消费拓展升级趋势,充分利用减贫过渡期内产业帮扶的相关政策,抓好本土主导产业发展,深化贫困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不断强化小农生产“韧性”,打牢脱贫地区持续减贫的物质基础。第二,防范返贫和脱贫攻坚同等重要,要在严格把握脱贫质量关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防范返贫的预警机制保障,提升预警能力,尽快把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两类人群纳入监测对象,可结合地区实际扩大监测范围,及时发现和解决脱贫后可能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第三,要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强化贫困群体的主人翁意识,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观引导,把“扶智、扶志、扶德、扶勤”的理念贯穿贫困治理的全过程,助力贫困群众摆脱思想之困,培育起主动发展的意识。第四,要按照乡村振兴的总目标,促进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移,及时总结经验、创新思路,把构建起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实施新的“两步走”战略中的重要任务,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相对贫困的治理方向,把“防贫与减贫”作为相对贫困的治理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