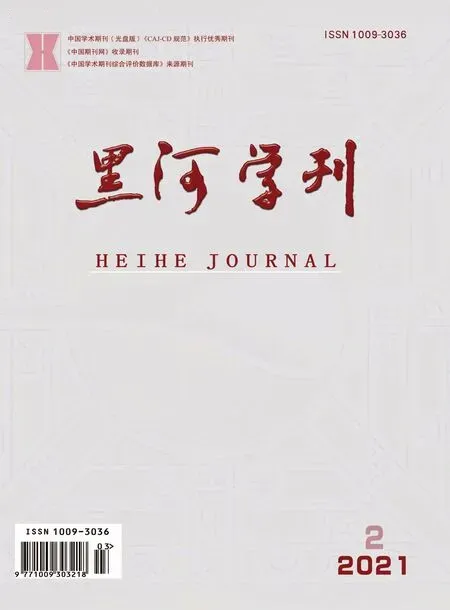试探鄂伦春民族“斗熊舞”的流变
王雪娇
(哈尔滨市南岗区文化馆,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
鄂伦春民族在以游猎为主体漫长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虽然带有浓烈的游猎民族的色彩,但也具有鲜明的鄂伦春民族的特征。鄂伦春民族没有文字产生了独有的口头文学形式和内容;鄂伦春民族的音乐的曲调、表达的情感都是他们独有的;鄂伦春民族的服饰常见的狍皮衣服与达斡尔民族的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舞蹈也不例外。追述鄂伦春民族的舞蹈艺术始见于《清实录》,更久远的无从查找。按照任何艺术都无不打上历史烙印的原则,一定要从鄂伦春民族在历史进程演变中追根溯源。但鄂伦春民族没有文字,只有把鄂伦春民族的历史和我国舞蹈史结合起来,才能查找出鄂伦春民族斗熊舞的源头,而我国的舞蹈史溯源于汉代。
本文是从狩猎角度出发,通过对历史、文献等资料的搜集中探寻鄂伦春民族“斗熊舞”的发生与发展,并对黑龙江省不同地区以及俄罗斯哈巴地区有关于“熊”舞蹈进行初探比较,希望能够为鄂伦春民族“斗熊舞”增添一点文字、图片形式的资料,同时能够为鄂伦春民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助一份微薄之力。
一、斗熊舞初探
鄂伦春民族舞蹈离不开其所生活的环境,特殊的环境蕴育着鄂伦春民族民俗文化。2009 年,鄂伦春民族的萨满服饰、萨满祭司、刺绣技术、口弦琴、斗熊舞等被列入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鄂伦春民族文化艺术以独特的形式展现给了社会各界,得到了更广泛的注视和认可。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是从悠久的历史磨砺中生成,它是一个民族区别另一个民族的特征,斗熊舞就是鄂伦春民族的象征之一。舞蹈艺术以独特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丰富着生活状态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体现出了鄂伦春民族亘古以来时空的变换。在一望无际的丛山峻岭、高山流水的茫茫原野中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民族繁衍生息了一代又一代形成的斗熊舞文化的民族性是不能忽视的,它代表着全地球所有的民族不可逾越的生产生活初始的阶段和方式。
“英国的生物地理学家西蒙斯在他的《文化与自然》中有过一个推测:在世界人口约为1 千万的公元前一万年左右,人类的生活都是以狩猎为主。直至公元1500 年左右,世界人口在增多的情况下,以狩猎为生的人口为10%,公元1960 年世界人口达到30 亿时世界狩猎人口却已经下降到0.001%。”[1]这是《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中的一段文字,从这个段文字可以看出,世界上狩猎生产既是人类文明摇篮的源泉也是文化萌芽的基础。有着原生态初态的狩猎文化的鄂伦春民族是“最后走出大山的人”,他们的狩猎文化“无疑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所以,作为狩猎文化的载体鄂伦春民族的斗熊舞得以流传到今天。
沿着狩猎文化的线索上溯斗熊舞的摇篮,追溯到的年代是很古老的,在最初人类发展史中先秦时代的远古时期,我国的祖先的繁衍生息生产生活方式靠的就是狩猎,这种猎取食物活动被人们模仿创作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舞蹈。舞蹈的源头没有文字记载,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成为了远古人们记录生活的方式。《没有地址的信》一文中有一部分就对劳动与舞蹈的来源深入的进行了探讨,普列汉夫这位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本书里就原始部落的舞蹈进行了逐个列举,其中的情形有:“舞蹈不过是对动物的一种简单的动作模仿。比如,澳洲土人的青蛙舞、蝴蝶舞等等,北美印第安人的熊舞和水牛舞也是如此……”[2]从此不难看到,舞蹈的生成是生产生活中对狩猎过程和成功的艺术加工,也是人们狩猎之后愉悦中对狩猎场景的再现。这种再现主要是模仿狩猎的状态、动作、拟声等,由于环境、狩猎对象、狩猎者等不同,从而逐渐造就出来了属于自己本民族的猎取食物的舞蹈。试图以狩猎文化角度发掘斗熊舞的本真面目是笔者的初衷。舞蹈艺术的成长与各民族的交往密不可分,如:迁徙中的交往;杂居中的交往;聚集中的交往。这样的交集逐渐的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这些方面的联系增加了舞蹈艺术的新元素、使舞蹈艺术得到了长足发展。我国自秦汉以来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影响舞蹈艺术促进其发展的《角抵·百戏》就出自秦、汉时期。
汉代百戏画石像左侧面有一酷似击鼓人,有一吹埙人,还有一鼓瑟人;右侧有一戴熊壮面具、腰间有仗、上举双手的舞者。[3]这是笔者查到的与熊相关的舞蹈图,表现的是熊与人的舞蹈。这些情形是在河南南阳出土石像中的,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有资料可查的斗熊舞的初始。所以,秦汉时期模拟动物再现狩猎情景的舞蹈已经出现了。
在舞蹈发展的历史中,与熊相关的舞蹈虽有也寥寥无几,其资料很是缺乏。尤其是秦汉时期之后查询不到与熊舞的记载。直到改革开放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到了繁荣。找到了杨海光先生拍摄的斗熊舞的纪录片。杨海光先生是鄂伦春民族影视纪录片第一人,在他的此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留最原始的斗熊舞姿态,鄂伦春族人们围成圆形,或是两人一组,模仿着熊的姿态进行舞蹈,时而欢呼,时而搏斗。可以说,这部于1962-1963 年拍摄的《鄂伦春族》纪录片富有价值,它记录了鄂伦春民族古老的民族舞蹈文化,为进一步探索斗熊舞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实资料。
二、鄂伦春民族与”熊”相关的舞蹈
居住在不同地域的鄂伦春民族对熊舞的称谓有所不同,“黑熊搏斗舞”是鄂伦春民族自治区域的称呼;“斗熊舞”则是嘉荫县乌拉嘎镇范围内鄂伦春民族与熊有关舞蹈的叫法。“鄂伦春人在长期的狩猎生产中学会了模仿野兽的动作,逐渐形成了舞蹈,具有代表性的狩猎舞蹈称之为‘狗熊搏斗舞’。”这是杨光海先生对与熊有关的鄂伦春民族舞蹈的定义。
(一)“黑熊搏斗舞”
公认第一部记载与熊相关鄂伦春民族舞蹈的是《鄂伦春社会发展》一书,这本书于1980 年10 月出版。书中表明的是与狩猎相关的“黑熊搏斗舞”,该舞是有三人参加模仿黑熊在搏斗时简单动作而形成的舞蹈。开始上场的两个舞者的共同而各自同时的基本动作:一是“上身向前倾,下半身略微向正前方弯曲”;二是“双手手心下放在对应的膝盖上”[6];三是“脚下做不停的动作”;四是“头与肩左右摇晃”[6];五是“嘴里要模拟动物的叫声发出‘吼吼’的声音。之后,第三个人以同样这些动作上场”,以酷似劝解吵架的形式的动作出现。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看出鄂伦春民族各个地区与熊有关的舞蹈虽有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与《鄂伦春社会发展》两本书中描写的黑熊搏斗舞模仿黑熊打架的[6]动作和发出的吼声是一样的,但前者一书说黑熊搏斗舞也叫野猪搏斗舞。
(二)“斗熊舞”
嘉荫地区斗熊舞为鄂伦春人一种娱乐形式,起初的斗熊舞是“即兴歌舞”,由此逐渐演变成“庆典”活动。鄂伦春族人在狩猎等生产之余大家聚集在一起以“斗熊舞”来唱和跳渡过闲暇。当“斗熊舞”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了就成为了庆祝狩猎等丰产丰收和婚庆的节目。该地区的斗熊舞的特点:一是“模拟野熊的各种神态、动作”;二是“表现鄂伦春猎人智勇双全捕获野熊的狩猎过程”[6];三是“舞蹈具有滑稽、有趣、欢快、跳跃的氛围”。“斗熊舞是先人传下来的,建国前我们鄂伦春人过着游猎生活,打猎归来常常三、五人在一起围成圆圈,或是两人相对一起唱歌跳舞。现在下山定居了,大家住在一起,虽然狩猎以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了,但每当有节日、婚礼等庆祝活动的时候鄂伦春人还会跳起舞唱起歌,用最原始的方式来欢庆!更值得高兴的是在2009 年,鄂伦春族斗熊舞由嘉荫县申报,成功被录入《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嘉荫县胜利村的杜春生如是说,他是鄂伦春民族斗熊舞传承人。
资料的记载大同小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记载,“斗熊舞用于狩猎等丰产丰收和婚礼喜庆之时”,表演的方式是一人扮熊居中,众人绕熊围园起舞,伴有男女对舞。舞蹈中模仿熊的行为、动作特点,这些生产性活动就在民族艺术中反映了出来”。[4]“斗熊舞动作特点是‘晃颤、拖步’,这也是斗熊舞的基本动作。‘熊’在大圆圈中动作为‘熊步’、‘熊晃’;围成圆圈的其他人动作为左右拖步、盖手颤步、弓手颤步、仰天等,最后的动作为驱赶野熊下场,以示斗熊成功”。[5]
通过资料和分析看,“黑熊搏斗舞”和“斗熊舞”的相同的地方有:(一)在表现内容上,两者表达的都是猎人与黑熊搏斗的狩猎方式。(二)在表演的形式上,两者体现的都是猎人狩猎成功“即兴而舞”的原始舞蹈[6]。(三)在舞蹈动作层面上,两者都是“以‘熊晃’为标准,以‘晃颤’为舞蹈基本动律”;[6]“身体略向前倾,两膝略向前弯曲,双手放在两腿的膝盖上,脚下的步伐作跳跃状,同时两肩与头左右摇摆。”(四)在音乐层面上,两者都是[6]“以呼号为背景,呐喊的方式以3/4 节奏的调式,一般是发出吼吼的声音,音色雄厚有力,并逐渐加速。”
“黑熊搏斗舞”和“斗熊舞”共有的动作和背景呼号以及其表现的鄂伦春民族文化,促使我们考虑两者只间的密切联系:一、虽然地域不同在称谓上也有所差别,但都是传流至今的鄂伦春狩猎文化的印记和见证。二、“黑熊搏斗舞”和“斗熊舞”的基础,“斗熊舞”是在“黑熊搏斗舞”的动律和基本动作的基础上得到了升华。但“斗熊舞”蕴含的鄂伦春民族狩猎文化和对世间万物的认知的信仰是没变的。
三、“熊舞蹈”的境内外对比
在俄罗斯境内的今天仍能找到鄂伦春族人历史的印记, 苏维埃港的达达村(“达达”译为乌嘞奇河)是最早建村的地方之一,是鄂伦春地区鄂伦春民族人口聚居的最大村庄之一。为此,我们进行了实地对比研究。
通过交流和观察,该村人们只会少许的鄂伦春词汇,但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可以看到桦树皮制作的手工艺摆件以及狩猎用的枪支。由此可见,该村的鄂伦春族人和我国的鄂伦春族人一样具有狩猎的习俗,他们同样曾以强壮的体魄、矫健的身手和勇敢的精神渡过了漫长以狩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时代。因为,中俄两国的鄂伦春民族人流淌着的是一种狩猎文化的血脉。之后,有幸见到了该村最为年长的66 岁的鄂伦春族老人。刚一入室就看到了与中国相同的器物,就像在中国的境内一样,一下时空转换到了原始之初的鄂伦春族一家人的岁月。这位老人说,关于宗教、图腾、民俗传说等鄂伦春民族文化是从她母亲那里听到的。目前,只剩下零星的一点点的记忆。值得庆幸的是她还记得对自然崇拜和对“熊”的祭祀的鄂伦春民族文化。她说,对“熊”的祭祀仪式活动叫“熊节”,对熊的敬仰与崇拜在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笔者通过在俄罗斯收集到的资料看,与“熊”有关的俄罗斯舞蹈,只是保留了基本元素拟兽[6]动作的舞蹈,不是完整的“斗熊舞。”对于模拟动物姿态的动作也只有舞蹈动作的小结,但与我国的鄂伦春民族斗熊舞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动作和呼喊。
由于地域的不同,每个地区有关“熊”的舞蹈都有所不同。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虽然在舞蹈的形式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其舞蹈所蕴涵的意义,传承的鄂伦春族文化却是相同也是相通的。从斗熊舞这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民族文化存在于两国之间,虽然时间流逝,历史的记忆并不是那么的清晰,但中俄之间有关于鄂伦春民族的“熊”舞蹈的历史文化,却带给鄂伦春族人们历史般的鉴证,似乎在用舞蹈肢体语言诉说着我们曾经是一家人,这就是舞蹈艺术的魅力,更是民族文化的魅力。
四、结语
从汉代的百戏舞蹈到如今流传中外的与熊有关的舞蹈中可以找到“斗熊舞”的雏形与流变的过程,随着历史的演变、民族的迁移、舞蹈形式的变化,鄂伦春民族斗熊舞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演变着,成为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舞台化形式的舞蹈作品,这是在原始舞蹈中加以对肢体动作的装饰和对舞蹈形式美化了的“斗熊舞”。舞蹈以独有的肢体语言记录了鄂伦春民族古老的狩猎文化,这需要我们每一个热爱舞蹈,热爱民族文化的人,将鄂伦春民族“斗熊舞”这一艺术文化瑰宝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