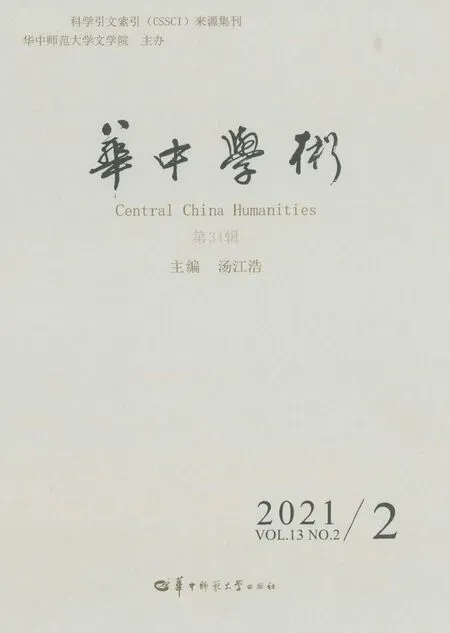《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译介
雷丽斯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引言
蒲松龄是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卓越的小说家。其著作《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在众多译文中,俄语译文影响颇大。《聊斋志异》的乌克兰语、塔吉克语、吉尔吉斯语、爱沙尼亚语译文都是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的俄语译文转译的。自1878年莫纳斯特列夫首次向俄语世界译介聊斋故事《水莽草》[1],至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斯托罗茹克仍在翻译《聊斋志异》未译篇目,《聊斋志异》的俄译已历时140余年。阿列克谢耶夫曾指出:“聊斋就是一部未被正式承认的《论语》,它里面说了孔子没有说过的话,指出了一条孔子经常提到的使人高尚起来的道路,对高尚的人来说,这条道路通向的世界并不比现实更可怕。”[2]
国内研究者对《聊斋志异》的俄译史、译者,以及《聊斋志异》中文化因素的翻译、形象性词语的翻译、小说标题翻译等方面均进行过探讨。中华文化典籍传播的有效性是衡量典籍译介和出版价值的重要标准,所以典籍的译介与传播这一课题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本文将探讨《聊斋志异》在俄国的译介史和传播经验,以及《聊斋志异》对俄罗斯文学产生的影响,希望为当下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译介过程
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中俄两国交往频繁,经清廷允许,俄国从1715年开始向北京派驻东正教使团,俄国汉学也随之产生、发展。最早将《聊斋志异》带回俄国的是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学员瓦西里耶夫。他是俄国汉学家中第一位院士,是俄国聊斋学的奠基人。他在专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1880年)中曾评价道:“若论语言之文雅以及叙事之简洁,则聊斋志怪小说(《聊斋志异》)颇受推崇。”[3]1883年,他翻译了5篇聊斋小说:《阿宝》《庚娘》《毛狐》《水莽草》《曾友于》,收录于《中国文学选读》。瓦西里耶夫翻译聊斋故事主要目的并不是体现原著的思想精神和优美的辞藻,而是将其作为学生的词汇练习材料,所以当时学生对蒲松龄作品的阅读更偏重于文意理解,谈不上赏析。而且,因为这几篇译文是收录在汉语教材中的,读者范围小,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1907年,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伊万诺夫翻译了《黄英》《李伯言》《考城隍》《瞳人语》《竹青》《画壁》《种梨》7篇小说,发表在《俄罗斯地理学会黑龙江部特罗伊茨克—隆甫斯科—恰克图分会丛刊》第10卷1-2期上[4],并且于190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单行本。
到了20世纪10—20年代,《亚细亚时报》上也陆续刊载了巴拉诺夫、丹尼连科、什库尔金的一些聊斋小说译文[5]。但需要指出的是,巴拉诺夫、什库尔金译介的目的是将《聊斋志异》作为研究中国宗教和民俗学的材料,他们的“大部分译文至今无法识别出原文”[6],更没有表现出《聊斋志异》独特的文学性,所以传播效果也差强人意。加之《亚细亚时报》是在哈尔滨出版的,传播范围也只局限于俄罗斯侨民这一特殊群体中。
1914年—1917年,俄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在这之后几年,俄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经济,学术研究工作严重滞后,俄国汉学步履维艰。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1919年,高尔基提倡成立世界文学出版社,并创办《东方》杂志,旨在推动外国文学在俄的普及传播,让外国文学走进普通读者的视线。他邀请了很多著名的学者担任顾问,苏联汉学的开创者阿列克谢耶夫也在其中。这也是《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真正意义上广泛传播的开端。1922年,阿列克谢耶夫在《东方》杂志上以《狐狸的王国》为题发表《婴宁》《胡四姐》《潍水狐》《狐惩淫》四篇聊斋狐狸故事译文,并撰有简短的序言,对中国的狐狸故事进行了简单介绍。同年,阿列克谢耶夫第一本译文集《狐媚集》出版。紧接着,世界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僧人集》(1923)、《异闻集》(1928)、《异人集》(1937)。这四本译文集的出版使《聊斋志异》跳出汉学圈,走到普通读者中间。阿列克谢耶夫希望聊斋故事不仅能够成为普通读者的中国文化启蒙读物,而且对有汉语或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文学性又丝毫不减少。他一再强调,《聊斋志异》不是中国的“童话”、不是猎奇故事,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他对译文准确性要求极高,目的是让“这些译文能够给汉语初学者当作教材,并结合汉语原文对比学习;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原作失去本来面貌,不让教科书式的俄语文学语言束缚住原作”[7]。他用“读起来不困难的俄罗斯语言”把聊斋故事带到普通读者面前,用他准确又高明的译笔为精英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930年代—1940年代前期,苏联国内经历了“肃反”运动,政治环境持续恶化,1941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期很多汉学家遇难,苏联汉学的发展一再受挫。阿列克谢耶夫被批判为“顽固分子”“伪科学家”,因为翻译《聊斋志异》被扣上“反动”和“搞神秘主义”的帽子。据阿列克谢耶夫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回忆,阿列克谢耶夫晚年一直在为聊斋再版做准备,不断修改已发表的译文。遗憾的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在1951年春与世长辞,没有等到《聊斋志异》再版。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在苏联掀起了中国文化热潮。在这一时期,苏联汉学家们积极翻译、不断出版或再版中国典籍和现代作品。1954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再版《异人集》,由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费德林担任编辑。随后,1955、1957年,国家文学出版社陆续再版了《狐媚集·异闻集》《神僧集·异人集》。此次再版总发行量约30万册,上架之后就被抢购一空,这让《聊斋志异》更为深入地走进了俄罗斯人的文化生活。但另一方面,与阿列克谢耶夫在世时出版的译文集相比,50年代再版的译文集改动较大,注释部分被严重压缩,阿列克谢耶夫的语言和节律被恣意更改,某些内容被改动得十分“俄罗斯化”。班科夫斯卡娅将这些改动称为“熊来帮忙”,意思是“帮倒忙”,认为“巨大的发行量带来了不小的坏处——把阿列克谢耶夫终生反对的异国情调植入了读者单纯的脑海中”[8]。可见,50年代的再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传播;另一方面,由于编辑的删改,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降低,用词准确度下降。
继阿列克谢耶夫之后,也曾有学者尝试继续翻译《聊斋志异》。1961年,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乌斯京和法因加尔合译的译文集《蒲松龄的小说》,共包括49篇故事,且都是阿列克谢耶夫没有译过的篇目。乌斯京是阿列克谢耶夫之后一位重要的《聊斋志异》的研究者,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蒲松龄和他的小说》,文末附有他翻译的二十七篇聊斋故事。可见,乌斯京翻译聊斋故事主要是出于学术目的。虽然该译本学术影响力无法与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比肩,两人也未将《聊斋》全部译完,但这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与突破。
1960—1970年代,中苏关系冷却,翻译作品数量锐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国家文学出版社仍然着手启动《聊斋志异》译文集的再版工作,于1970、1973、1983年出版三个译文选集:《蒲松龄:狐媚集》《蒲松龄:聊斋奇异故事集》《蒲松龄:聊斋志异》。这三本子集由阿列克谢耶夫的爱徒、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艾德林担任编者。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水平高超。更可贵的是,他时刻捍卫阿列克谢耶夫的每一个用词,绝不轻易更改老师的译文。班科夫斯卡娅称艾德林选编的译文集“可以作为典范引用”。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汉学家们推陈出新,努力找回丢失的20年时光。之后,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思想和文化价值观日趋多元,这极大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繁荣与发展。80年代掀起的一小股“中国文化热”,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在此期间,《聊斋志异》译文集进行了四次再版:《聊斋志异》(1988年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者为班科夫斯卡娅)、《蒲松龄:神僧集·异人集》(1988年由真理出版社出版,编者为费德林,该版是对1957年版本的修订)、《蒲松龄小说:接连不断的奇异故事》(1994年由教育新闻出版社出版,由索罗金担任编者)、《聊斋奇异故事》(1999年由圣彼得堡阿兹布卡出版社出版)。
进入21世纪,自2001年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两国在各领域中交往日趋活跃,互办中俄文化年、语言年,在俄罗斯掀起阵阵“中国风”,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十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典籍的重译和再版。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志异》是典籍再版中的佼佼者。2000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中心出版了《聊斋志异》合集,阿列克谢耶夫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担任编辑。这是目前收录最全,译文最权威的《聊斋志异》俄译本。2003年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智慧文选”丛书,《狐妖之术:中国神奇故事》作为其中一册,共收录46篇聊斋故事。2007、2008年,东方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蒲松龄:异闻集·异人集》《蒲松龄:狐媚集·僧人集》。2018年,俄罗斯T8出版技术控股公司策划了“东方图书馆”系列丛书,出版了三本聊斋故事:《蒲松龄:狐媚集》(2018)、《蒲松龄:异闻集》(2018)、《蒲松龄:僧人集》(2019)。同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聊斋志异:狐媚集·僧人集·异闻集·异人集》,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通讯院士李福清编写,是继2000年版本之后收录最全的《聊斋志异》俄译本。其后不仅附有阿列克谢耶夫的注释,还有编者的附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020年,俄罗斯T8出版技术控股公司时隔两年又对《聊斋志异》进行再版。第一套包括三本:《蒲松龄:狐媚集》《蒲松龄:僧人集》《蒲松龄:异闻集》;第二套包括四本:《蒲松龄:狐媚集》《蒲松龄:僧人集》《蒲松龄:异闻集》《蒲松龄:异人集》。这两套书相当于将阿列克谢耶夫的聊斋译文集全部重新再版。需要指出的是,T8出版技术控股公司是一家商业出版机构,于他们而言,销量是衡量是否再版的第一标准。所以,该公司两年之内又重新出版聊斋故事,这也表明《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读者群体基数很大。
除译文集以外,《聊斋志异》还被选进汉语教材。2016年,ВКН出版社出版了汉语自学教材《跟蒲松龄一起学汉语》,是伊利亚·弗兰克“阅读学习法”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教材中包括《王六郎》《阿宝》《崂山道士》《青凤》四篇故事,译者为阿尔乔姆·杰明和唐兰(音译)。因为是自学教材,书中原文为白话文,在每一句后标有拼音、译文和生词解释。书中的白话文翻译得相对简单,译文也很直白,而且为了方便读者学习,译文均以对译为主,以达到一种“平行对应”。2018年,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公司开始引进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风》中文分级系列读物,其中《“汉语风”中文分级系列读物(第2级):500词级·青凤》和《“汉语风”中文分级系列读物(第3级):750词级·画皮》这两本读物是根据聊斋故事编绘的。编者将聊斋故事编绘成若干小故事,并有词汇注释和配套练习。为了适应读者水平,同时也为了服务教学实践,编者把故事内容改编得更加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比如,书中编者将《画皮》拆分为《放假真好!》《一张画掉在小河旁边》等十三个小故事。虽然故事发生的背景仍然是在古代,但用词上很接近现代生活。例如,编者用“国家的考试”代替“科考”,而且出现了打工、蛋糕等古代没有的词语。故事中日常生活情节也更接近现代人的生活,学习起来并不吃力。聊斋故事走进对外汉语教材,无疑对《聊斋志异》的传播大有裨益。
《聊斋志异》至今也没有全译本,一是因为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过于精湛,在汉学界备受推崇,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二是《聊斋》小说语言精妙,书中包括大量的隐喻、文化典故,是一本“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要求译者不仅要“会古文,懂得语言的历史演变,懂得典故,了解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文化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中国人的世界观及其伟大的历史前途”,还要“自己的心理特征能包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世界观”[9]。值得一提的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斯托罗茹克教授目前正在翻译阿列克谢耶夫未译的篇目,相信《聊斋志异》俄译全本指日可待。
二、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志异》译文的特点
阿列克谢耶夫的《聊斋志异》译本语言精巧、文风独特,“凭借翻译文本与众不同的风格,使得译著不断再版,成为俄罗斯文学当中的经典,屹立在俄罗斯文学经典之列,获得了即便不能说是永恒的、那也是持久的艺术生命力”[10]。《聊斋志异》能够走进俄罗斯,并在俄罗斯“生根发芽”离不开阿列克谢耶夫的杰出贡献。对他的翻译特点进行总结、评述,分析译本特点形成的内在动因,是研究《聊斋志异》在俄罗斯译介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可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借鉴和参考。
1906年,阿列克谢耶夫来到中国学习,他到茶楼听说书人讲聊斋故事,请中国先生(“聊斋通”)为他讲解《聊斋志异》,并在先生们的帮助下将《聊斋》从文言文翻译成口头语言,也就是白话文。1907年,阿列克谢耶夫同法国汉学家沙畹游历中国,进行了一次学术考察,并写了一本日记《1907年中国纪行》,对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社会等无不详细记载。他运用敏锐的视角捕捉到最能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人和物,用尊重甚至是敬仰的态度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些经历都是阿列克谢耶夫翻译《聊斋志异》的基础。回国后,阿列克谢耶夫经常向当时在彼得堡大学任教的曹靖华先生请教,请曹先生将译作中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指出来。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主张和坚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聊斋志异》译本的特点。忠实于原文是阿列克谢耶夫翻译《聊斋》的第一标准,反映原作的原貌是首要任务。他曾在《狐媚集》的前言中写道:“如果他能以无愧于原作的形式、用易懂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传达原作内容,反映原作的真正面貌,不为迎合读者的理解能力而做出让步,那么他和读者就都满意了。”[11]阿列克谢耶夫主张进行有根有据地翻译,他“竭力在相关的古典文献和早已众所周知的文学典范中查找其间的引文及引文中个别字词的出处”[12],力求准确、完整地向俄国读者介绍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与当时欧洲其他汉学家将《聊斋志异》“本土化”的翻译方式截然不同[13]。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语言准确,注释详尽
阿列克谢耶夫重视准确性,但他反对死板的、逐字逐句的翻译。他的译文既准确又生动。我们尝试对比阿列克谢耶夫和伊万诺夫《画壁》中的一句译文:
原文: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14]
译文1:На восточной стене была изображена Небесная Дева, сыплющая цветами, и в ее свите какая-то девушка с челкой, которая держала в руках цветы и нежно улыбалась.Ее губы-вишни, казалось, вот-вот зашевелятся, а волны ее очей готовы были ринуться потоками.[15](Алексеев)
译文2:На восточной стене было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небесной девы, раскидывающей цветы.Одна из её служанок улыбалась, как живая.[16](Иванов)
“散花天女”是佛经故事中的神女。阿列克谢耶夫和伊万诺夫都将“天女”译为Небесная Дева。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夫对“天女”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天女——佛经中的人物。《维摩诘经》说:我们中有一位撒天花的天女,她将花撒在潜心向佛的菩萨身上,花会落地;撒在修行之人的身上,则花会附着在他们身上,不落地。这时,天女说:你们与尘世的联系还没有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花附着在你们身上而不落地。这些花不会附着在已了却与尘世一切联系的人身上。”[17]伊万诺夫对“天女”则没有任何解释。另外,“散花天女”中“散”这个动词伊万诺夫译为“раскидывающая(抛掷)”并不准确,“散花仙女”是撒落鲜花的仙女,不是抛掷鲜花的仙女,阿列克谢耶夫译为“сыпающая(撒)”十分准确。
后面蒲松龄对侍女的动态描写,读起来宛如一位少女站在眼前。“拈花”“微笑”“欲动”“将流”这四个动作,将少女描绘得活灵活现。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保留了这些动态描写:“在天女的侍女中,有一位梳着刘海儿、手持鲜花的少女,正在温柔地微笑。她樱桃般的双唇好像随时都要微启,明眸如波,好似流水一样流动。”通过这段描写,俄语读者眼前的这位少女好像真的要从壁画中走出来。而伊万诺夫的译文是:“其中一位侍女,像活人一样笑了。”伊万诺夫基本上忽略了对侍女的动态描写,只给出了一个描述性翻译,失去了原作的生动形象。
(二)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为汉语披上一层薄薄的俄语外纱”[18]是阿列克谢耶夫重要的翻译理念,也是他想达到的翻译效果。他反对译文中充满“异国情调”,认为“异国情调是一个消极的概念,是指其他文化中那些无法掌握的、神秘的、令人愤怒的元素”[19]。而对于俄罗斯的翻译来说,“悲剧在于刚跳出异国情调,就立即跳入了俄罗斯化”[20]。也就是说,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汉语作品即使翻译成俄语,也要保留“中国味”,而不是读起来像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
为了保留“中国味”,还原聊斋原貌,阿列克谢耶夫选择“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多使用音译、字面直译、直译加注等方法。例如《宦娘》篇中:“临邑刘方伯之公子,适来问名,心善之,而犹欲一睹其人。”[21]“问名”是中国古代婚姻礼仪“六礼”之一,《仪礼》上说:“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问名是古代婚姻过程的第二阶段,男家请媒人询问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以备卜筮合婚。在俄罗斯并没有相应的习俗,阿列克谢耶夫选择直译加注释的方法翻译“问名”,译为“正如常言道,问她的名字”,并在注释中详细地介绍了“问名”需要询问的事项及询问的目的[22],通俗易懂,便于俄罗斯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婚俗制度。
对于难以理解的一些概念,阿列克谢耶夫也会采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既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又将中国文化更加直观地介绍给读者,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例如,《婴宁》篇中王生说:“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23]瓜和葛都是蔓生植物,根茎相互缠绕生长,多用来指亲戚。阿列克谢耶夫首先将“瓜葛之爱”直译为“蔓生的南瓜之爱”,紧接着解释说“即生来的亲属之间的爱”。先异化再归化,既保留了“瓜”和“蔓生”这两个概念,也能使读者明白“瓜葛之爱”指什么。
阿列克谢耶夫在很多异化翻译前使用插入语,来提醒读者这是汉语独有的表达方式。例如上述两个译例使用了插入语как говориться(正如常言道)和что называеться(被称为)。阿列克谢耶夫追求给俄罗斯读者一部准确、完整、原汁原味的《聊斋志异》译本,在翻译过程中轻易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文化信息,所以译文中异化情况更多。这样一来,译本中就存在大量的注释和插入语,这对专业读者来说,如鱼得水,甚至可以把这本译作看作中国文化的工具参考书。但对于单纯想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普通读者来说,译文中陌生的表达和大量的注释会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让读者难以流畅阅读,影响阅读体验。1922年,《狐媚集》在出版之前,阿列克谢耶夫曾将译文交给高尔基亲自校订。高尔基将《聊斋》看作“源于可鄙的迷信”创作出来的童话故事集,把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改得面目全非,遭到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强烈反对。现在来看,高尔基当年对《狐媚集》的修改的确有诸多的不合理,但他提出“翻译要考虑读者水平”这一意见是可取的。
(三)灵活意译,创新表达
阿列克谢耶夫不仅采用音译、直译、注释的方法,他对很多译文的处理也十分灵活,在不改变原文意思的前提下,灵活意译,省去了一些注释的空间,读起来更加顺畅。尤其是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新的表达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例如《佟客》篇中,佟曰:“异人何地无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传其术也。”[24]“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儒家提倡人与人之间要遵守“三纲五常”,“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伦理纲纪严明。可见,儒家意义上的“孝”首要是尊重父亲,以父为纲。阿列克谢耶夫用了两个词表达“孝”的意义:“набожно-благочестивый”和“отцепочтительный”,这两个词都是阿列克谢耶夫造的新词。“набожно-благочестивый”意思是“虔诚地笃信宗教的”,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孝”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一种指导性准则,所以西方人认为,笃信上帝就要按照他所说的行为准则去做,那么“虔诚地笃信宗教的儿子”就是“孝子”。第二个词“отцепочтительный”是由“отец”(父亲)和“почтить”(尊敬、致敬)这两个词构成。这种构词方式对俄罗斯读者来说十分容易理解,符合俄语的构词习惯,同时,也将儒学文化中“孝”的内涵表达出来了。这是归化与异化的完美结合,看似简单的“孝”字,译者创造两个新词将中西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四)注重节律,兼顾忠实性与文学性
对于《聊斋志异》的翻译,在内容层面上,阿列克谢耶夫严格遵守直译原则,从不增删、改写原文内容。但他不拘泥于逐词逐句的翻译,在不改变内容的前提下,进行扩展性翻译,在保留原作的丰富多彩的形象性的同时,也使翻译出来的俄语句子更加自然,与俄罗斯文学语言相符。
从文体上来看,《聊斋志异》中“文备众体”,包含很多诗词歌赋、词曲对联、酒令小调等等。写作手法上夹叙夹议、行文骈散结合。这些中国小说特色在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中都得以保留。阿列克谢耶夫坚持将诗歌译为诗歌、词曲译为词曲,原文是什么形式,译文就是什么形式,不改变原作的文体。而且,阿列克谢耶夫在音节性和节奏感上也竭力追求原文与译文能够契合。例如,《乩仙》中的一副对联:“羊脂白玉天,猪血红泥地”[25],阿列克谢耶夫译为:Баранье сало — в белой яшме небо.Свиная кровь — в красной грязи земля[26]。译文上下联均五个实词,与原文五个汉字对应,上联共十一个音节,下联十个音节,几乎相等,对仗工整。《赌符》中的“异史氏曰”部分,蒲松龄笔法精妙,使用骈文,读起来振聋发聩。阿列克谢耶夫为与骈文中的四字句和六字句在形式上相近,多使用紧凑的短句,省略人称代词,凸显动词的作用。如“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27],阿列克谢耶夫译为:То, что в нашей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повергает ниц и уничтожает семьи, не знает более быстрого способа, нежели азартная игра.То, что в нашей Поднебесной разрушает добродетель,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не знает более силь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чем азартная игра[28]。第一句和第二句中均是十三个实词,第一句中四十个音节,第二句中三十六个音节,虽没有完全对仗工整,但具有极强的节奏感,能够给读者以原文般的紧迫感,同样达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三、《聊斋志异》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在俄罗斯受《聊斋志异》影响最深的,毫无疑问,是阿列克谢耶夫。他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1928年,阿列克谢耶夫仿照聊斋故事创作了两篇小说《楚生》和《千手(再续旧事)》。其中,《楚生》收录在《中国典籍〈易经〉》中。这两篇作品的原型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休茨基(Щуцкий Ю. К.)和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Б. А.)。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阿列克谢耶夫借“仿聊斋”故事与自己的学生交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与蒲松龄借聊斋故事表达自己的思想异曲同工。阿列克谢耶夫创作的仿聊斋故事有明显的聊斋痕迹:《楚生》中出现的蓝鬼教是仿照聊斋故事中的白莲教,而且阿列克谢耶夫的创作手法也与蒲松龄相似:蒲松龄借聊斋故事揭示、讽刺黑暗的现实,阿列克谢耶夫借《楚生》中的蓝鬼们讽刺学校里那些不学无术之人。在另一篇故事《千手》中,阿列克谢耶夫写了一篇后记,很有“异史氏曰”的味道:“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令人生气,做事情只有三分钟热情,仅此而已。”[29]
俄罗斯当代文学中也有明显受《聊斋志异》影响的作品。这种影响不仅仅是《聊斋志异》这部作品本身带来的,还有阿列克谢耶夫翻译风格的影响。20世纪末,俄罗斯作家乌斯宾斯基创作了勇士日哈利探险“三部曲”:《没有我们的地方》(1995)、《时间这个东西》(1997)、《派谁去寻找死神》(1998)。故事中一位重要的主人公刘七郎,就是聊斋故事中典型的穷和尚形象。
21世纪初,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历史学博士阿利莫夫和雷巴科夫使用笔名霍里姆·杂气克王合著《没有坏人(欧亚交响曲)》玄幻讽喻系列小说,目前已出版七本。两位学者创作的这些故事发生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古今交错的国家阿尔图西(Ордусь)。Ордусь这个词是由Орда(游牧民族)和Русь(罗斯)组合而来,这个国家的文化融合了中、俄、蒙三国的文化,所以这个系列小说的副题为“欧亚交响曲”。在阿尔图西,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和平共处。阿利莫夫在作品中善用中国神话的形象、情节、象征。本套书中有一部名为《狐妖案》,书名取自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集《狐媚集》,主题是讽刺一夫多妻制,书中出现了中国民间传说的重要形象——九尾狐。
俄罗斯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佩列文也受到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影响。他的长篇小说《狐媚的圣经》(2004)吸收了蒲松龄的狐狸故事情节:一只名为阿狐狸的千年狐狸精,靠吸食男人精血为生,以妓女身份为掩护,诱惑形形色色的男人,最后遇到了自己的爱人亚历山大。这部小说是佩列文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百科全书,他以童话故事为掩护,想要阐释关于真理和谎言的道德意义,这与蒲松龄借奇幻故事表达自己思想的写作手法如出一辙。
此外,俄罗斯当代女作家马尔丁奇克也写过“聊斋式”的故事。创作初期,马尔丁奇克和她的丈夫斯捷宾使用笔名马克思·弗拉伊写过许多文学作品和书评。早在1999年,马克思·弗拉伊就写过一篇评论性文章《聊斋的“衬裙”》发表在网络上。作者在文中引用了《禄数》《黄粱梦》《于中丞》《钟生》这四篇故事,主要想说明以下几点:1.蒲松龄使用高雅的文体讲述简单的故事,堪称典范,是同时代的先锋;2.蒲松龄的叙述手法高超,从聊斋故事中可以了解到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3.聊斋故事中善恶因果报应几乎是所有故事的构建基础,故事情节远远比“童年的童话故事”要精彩。2004年,他们出版了《童话与历史》一书,其中包括二人创作的短篇小说《狐魅(中国民间奇异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湖南的儒生柳生,家境贫寒,寒食节这天获得天庭奖赏的一块奶酪。正当他想恭敬地吃这块奶酪的时候,天降少女,身边围着许多侍女,弹奏琵琶、古筝,吹奏长笛。这位少女自称是柳生的表妹,祖上有亲,愿嫁与他,不求富贵,只求与他共享奶酪。柳生欣然应允,没想到这位少女一口将奶酪吞了下去,之后不见人影。柳生冷静下来,跑到寺院将整件事说与道士听。道士说:这必是狐妖。柳生大怒,回到县里,最终科举中榜,一生努力与狐魅对抗。小说从主人公的设定、故事情节俨然是一篇聊斋故事。唯一略显突兀的是天庭赏赐奶酪这一情节,十分西方化,与中国文化不符。
中国有关狐的传说和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蒲松龄笔下的狐狸故事脍炙人口,他赋予了狐狸精人性的善良和智慧。这与俄罗斯的狐狸故事中狡猾、贪吃的特点完全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引起了俄罗斯作家的兴趣,他们也尝试用“聊斋式”的狐狸讲故事,赋予它们人类的七情六欲,借他们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社会的期待。
注释:
[1] [俄]莫纳斯特列夫:《水莽草》,《新闻报》1878年第195期,第5页。
[2] [俄]班科夫斯卡娅:《聊斋的朋友与冤家(续)》,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1~127页。
[3] [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阎国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4] [俄]伊万诺夫:《聊斋志异选》,《俄罗斯地理学会黑龙江部特罗伊茨克—隆甫斯科—恰克图分会丛刊》1907年第10期,第48~46页。
[5] 参见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
[6] A.G. Storozhuk, “LiaoZhaiZhiyiinRussia”,JournalofSiberianFederal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12(10),2019.
[7] В. М. Алексеев,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Книга2,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 142.
[8] [俄]班科夫斯卡娅:《聊斋的朋友与冤家(续)》,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3期,第120~127页。
[9]Н. И. Конрад,Рецензия на 《Рассказы Ляо Чжай》,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Синология,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77,сс. 595-596.
[10] 谷羽:《阿翰林:针对翻译弊端的一剂良方》,《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8日,第20版。
[11] П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 (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 с кит.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СПб: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2000,с. 18.
[12] [俄]班科夫斯卡娅:《聊斋的朋友与冤家》,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1期,第128~140页。
[13] 如翟理斯,将《太原狱》译为AChineseSolomon(《中国的索罗门》)。参见Pu Songling,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Vol 2,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 A. Giles,London:Thos. DE LA RUE & CO,1880,p. 335.
[14] (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15] П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 (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 с кит.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СПб: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2000,с. 132.
[16] Пу Сун-лин,Повести из Сборника 《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 с кит. А. И. Иванов,СПб: Сена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1909,с. 65.
[17] П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 (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 с кит.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СПб: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2000,с. 132.
[18] В. М. Алексеев,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Книга2,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с. 142.
[19] В. М. Алексеев,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82,с. 331.
[20] В. М. Алексеев,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82,с. 332.
[21] (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022页。
[22] 参见П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 (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 с кит.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СПб: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2000,с. 257.
[23] (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61页。
[24] (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225页。
[25] (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619页。
[26] П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 (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 с кит.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СПб: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2000,с. 550.
[27] (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440页。
[28] П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 (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 с кит.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СПб: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2000,с. 164.
[29] [俄]班科夫斯卡娅:《聊斋的朋友与冤家》,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5~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