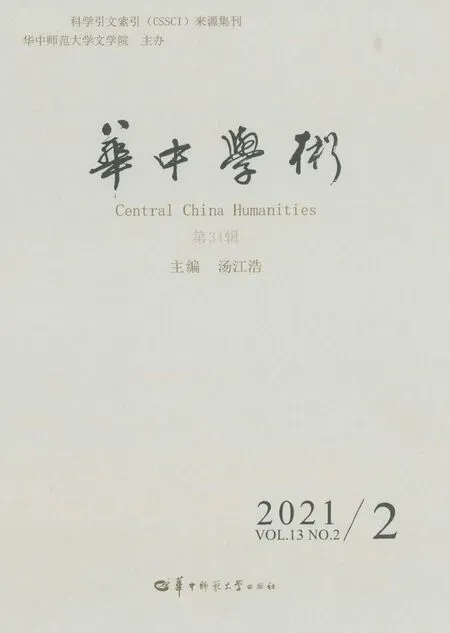“龙蛇化剑”母题来源及文化自洽
——从民国武侠小说仙怪母题谈起
王 立
(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014)
兵器的神性,往往同英雄的勇力等其他技能共消长。还珠楼主《蜀山剑侠新传》写孙同康随仙师在石洞中发现异藤似蛇蟠翘头,梢头为长圆形金果,他吃了金果后沉睡两日夜,神力大增,发现异藤缩入就费力扯出,虹光满地满壁乱钻:“是口从未见过的珍奇宝剑,那藤根便生在剑柄之上……”他把剑柄所附藤根灵汁吸干,那剑还往地下深剑匣里钻[1]。这异藤意象,从形式和质感上仍是剑为龙蛇原型的亚型变异。在古代神变幻化想象中活跃着一个龙蛇化剑母题,明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中亦妖亦物的兵器,多为英雄必要辅助,共兴衰,同命运;英雄手中兵器灵物互化的能量与英雄修为呈正比,构成故事类型。于是英雄侠义形象的塑造,伴随兵器神奇化,就不仅是母题要素,亦是形象异化、文化自洽的对象化。在龙蛇化剑母题叙事中探寻书写模式的神秘思维、英雄神圣化的民俗观念及思维惯性,龙蛇化剑与侠义英雄互补共生,其意义指向在对立统一中形成消解社会现代性的内驱力,亦即故事蕴含的文化自洽意义与影响。
一、龙蛇化剑与龙原型及神物崇拜
龙蛇化剑,最多莫过于以龙作为灵异本体了。冷兵器时代每每尽可能延伸人的手臂,便于攻守,作战者(尤其在马上)手持兵器大多为长棍状,形态与龙蛇形体相似,借助龙的神威也在情理之中。清代《飞龙外传》写赵匡胤未发迹时曾蒙张员外赠一条黄金锦织成的鸾带,说仙长所留“神煞棍棒”,无事时为腰间束带,用时念声“黄龙舒展”它便变成一条棍棒,且刀枪剑戟俱不能伤害,还可防妖术邪法,不用时能归原[2]。赵匡胤靠此宝物临危脱险,屡建奇功。此兵器神异功能有三,最主要的是便于隐藏携带,随时予敌突然袭击,攻敌护己,兼破邪法。此取《警世通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铁棒“护身龙”,把龙蛇的质性柔软与棍棒的坚韧相结合,当然也暗含假借龙蛇的神威。比较而言,明清小说中的龙蛇化兵器母题总体上呈现较为复杂的状态。
第一,龙蛇化剑,实为神物变形叙事,体现了神物崇拜的丰富性与久远性。神物崇拜观念较早。干宝《搜神记》卷九载:长安张氏室中有鸠自外入,张氏祝后鸠飞入怀,张氏遂伸手入怀,探得一金钩,自此家富财丰。此似与兵器制作神秘信仰有关。《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有人贪王之重赏,杀二子以血衅金制二钩献阖闾,一次钩师呼二子名,声落,“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吴王惊赏百金,此处的“吴钩”已具人血崇拜成分。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九龙池处第七》写猴行者过九龙池:“忽见波澜渺渺,白浪茫茫,千里乌江,万重黑浪。只见馗龙哮吼,火鬣毫火,喊动前来。被猴行者隐形帽化作遮天阵,钵盂盛却万里之水,金环锡杖化作一条铁龙。无日无夜,二边相斗……”[3]“金环锡杖”乃佛赐宝物,以佛法祛除馗龙邪魔,襄助取经大业。明代小说写胡参谋自夸宝剑:“此宝变化多端,神通广大,是俺向游蒙阴遇孙膑先生所授。”于是将宝剑化龙,这条龙比妖人草龙不同,“三停九似”,头至颈为一停,颈至脊为一停,脊至尾为一停;“九似”则为:发似马,角似戽,头似牛,鼻似狮,眼似虾,鳞似鱼,爪似鹰,尾似蛇,耳似鹿[4]。神物附剑有着多元化来由,与仙化的隐士形象结合。
剑为龙蛇化的深远文本来历,在意象母题历史性动态运行、扩散进程中,某一核心意象往往起着触媒、扩散辐射功能,而剑恰为“龙蛇化兵器”母题较直接的主导性触媒意象。李白《古诗五十九首》十六咏:“宝剑双蛟龙,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腾不可冲。一去别金匣,飞沉失相认……”此诗当来自鲍照《赠故人马子乔诗》五:“双剑将别离,先在匣中鸣。烟雨交将夕,从此忽分形。雌沉吴江水,雄飞入楚城……”清人王琦言,鲍诗是为故人赠别,重点在“神物”一联;李诗则是感知己之不存,其警策处即在“风胡”两语。以创作为主体自身的人格对应物,李白咏出了知遇难逢的苦闷。二诗宝剑化龙入水典故,突出了剑的母题与龙蛇原型的内在相通性。雷次宗《豫章记》的两宝剑化龙的典故,《晋书·张华传》、郦道元《水经注》也有异文,故事与春秋时吴越蛇崇拜、制剑传说有关[5]。
第二,剑蛇互化常与帝王威灵有关。赵匡胤的棍可远溯自刘邦到李世民的斩蛇(蟒)传闻。《延安府志》载安塞县有刻匣寺,碑记称唐太宗偕卫国公李靖征北番过此:“土人奏大蟒为害,太宗射蟒,入石罅(缝),挽其尾,化为剑,缺刃,按剑磨之,石为之亏。”[6]仿佛神明赐剑给创业帝王,剑是变形化为蟒蛇最终落入帝王之手,剑因帝王之威而更显灵性。后世“携剑飞空”书写,实由乘龙、骑乘剑所化之龙“人剑合一”而来,如高继衍《蝶阶外史》卷二则称四川典肆质古董,有客持箧索二百金,主者坚请开箧观验,客起箧见竹剑一,主者哂曰此物不值多金,客持剑一晃,“化为龙,乘之,夭矫凌空而去,箧至今尚存”[7]。
第三,龙与水、泉水崇拜等久远链接也常借助龙与剑互化故事,蕴含人、龙、水一体的生态观念。《说岳全传》中岳飞的沥泉枪就来自泉水,泉水的活力往往有赖于水中灵物。而明代的相关传闻还体现出明显的生命体共生观念。说天彭汉繁一带的观音泉四季水涌,泉中有巨鳝长三尺余,“尾端有锋,顶生二角,皆寸许,蜿蜒于泉水中”。农民龚某欲捕食,父老劝阻:此蛟龙,毁之而泉必竭。有人警告伤此灵物当有祸,可龚某不听,父老又运用众多典故相劝:“昔雷焕之剑,陶侃之梭,费长房之杖,皆器物类也,尚化为龙,矢此异形之物乎?抑闻东坡云:眉山青城邑,有牝豕伏地,化为泉,后有二鲤常游于中,故曰‘鲤泉’。又邵武山中,有买鱼得白鳝者,放之于井,后化为蛟,故曰‘鳝泉’。此皆载于群书,昭然可考……”[8]巨鳝被杀后果梦中怒责,龚某自詈死后雷震雹落,泉亦干涸。作为生态主体的巨鳝实有更大能量,且生命体还与泉水这一庄稼、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联系,可贵的“敬畏生命”思想之外,还蕴含着鱼类与龙、“器物”与龙等互化观念传统。何以许多宝贝兵器得之于水中?这真是一个饶有意趣的问题,岂非水、活水是生命之源?
第四,雌雄剑传说,体现出谪降世间的剑仙之传奇,增大仙凡互化能量。在清末王韬写世家子许玉林自倭国得宝刀,在虬髯的萧总戎看来不过一片朽铁,他把珍藏的“能斩妖辟邪”匕首相赠。许生路经楚南途遇女妖,后者呼来“赤精子”即数丈长大蛇,生立拔匕首斫之,裂帛声响,蛇截而为双剑,“制并古雅,似非时下物”,然而双剑却在峨眉山御妖时失落。许生的匕首引起为官的舅舅惊讶,原来“刀铭阳文”恰与舅女之匕首为一对,后者为峨眉山隐道人所赠:“此‘女聂政’也!何为在人间?”舅以女儿此匕首“殆雌雄作合之兆”,促成许生入赘,但不久夫妻“并失其首”,而匣中双匕首俱已羽化飞升至道人案上:“咸以为生与女皆剑侠者流,游戏人间,借尸解仙去。”[9]佛教转世观念与仙道谪降传说融合,纠结着雌雄剑与“赤精子”——大蛇化剑故事,剑仙修道与男女人物身世命运的联系若隐若现。
剑为蛇所化,显系兵器是龙蛇化身的一个亚类型,其实这并不限于剑,在后世的英雄传奇和以英雄为主体的历史演义小说里,更是极为形象地多样化呈现,突出显示了仙道与侠崇拜结合的文学传统,结合点即英雄与宝贝兵器不可分。《说岳全传》第四回写英雄来到沥泉洞,见石洞中伸出蛇头流涎滴下,岳飞以大石击中蛇头,星雾迷漫中蛇眼露光撞来,岳飞拖蛇尾一看原来是丈八蘸金枪,杆有“沥泉神矛”字[10]。这一神物的灵异性情,往往也与武侠英雄另一惯用工具——烈马的桀骜不驯仿佛。而一旦神物失去,也预示英雄厄运降临。《残唐五代史演义》第十八回写一个身穿黄衣的道人,当道向黄巢索还宝剑,“道人举起拐杖,望巢一打,巢即仆地。道人化阵清风而去。左右扶起黄巢,半晌方醒,腰间不见浑唐宝剑”。书中引诗称“道人夺剑数当亡”,解释为天不保佑。失剑为明显的不祥之兆,果然不久黄巢就兵败自刎[11]。但有时那特定的兵器,还可以应付不时之需,奇妙地返回其原型,从而化为龙蛇之形起到特殊功用。明代《东度记》写达摩禅师阐禅行法,梵志携道童在歧歧路村遇三五游浪少年,纠缠要比试武艺,道童拳脚、棍棒均获胜,众少年恼羞成怒竟执长枪戳,道童只得挥手将那枪棒“尽变作长蛇,张牙吐舌,直去咬那众少年”,使其慌怕求饶,梵志遂嘱道童收了法术,蛇又变回长枪[12]。
另一类英雄成长故事写获取神异兵器,还要拜师学艺,神物的获取更强化了学艺需要及紧迫感,而以神物出现为标志,引出了仙师授徒——英雄历练,实现了神异兵器又一重要功能。《万花楼演义》写一雪亮的白人引石玉交战,白怪且退且走,败倒后化为三尖枪柄,英雄石玉遂获得心应手的兵器[13]。随后鬼谷子又出现了,主动要收石玉为徒授其枪法。“天授兵器”与“仙师寻贤徒”母题链接[14],天授宝物往往要有“契机”,仙师传授宝贝兵器也多在贤徒艺成下山或蒙难之时。兵器龙蛇化引出得主,妖化兵器又构成了英雄学艺的需要,仙师收贤徒遂有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龙蛇化剑母题中,妖化的兵器在形制、功能,甚至拥有者等方面均存在限定条件,但有三点共性:一是物性相近,适应巫术的相似律,如龙、蛇等;二是妖化的兵器与使用者互补共生,剑为兵者“凶器”,以物自身的凶恶、奸邪以及超常生命力与杀伤力,隐喻剑客——英雄的嗜血性;三是龙蛇化剑母题与英雄、剑仙等是历史宿命的文化隐喻,襄助族群持久的文化自洽心理。
二、工具神化与英雄崇拜及其民俗观念
兵器,从本质和功能上讲,都无疑是人类生存斗争的一种工具,它的一再出现,说明人们是多么留恋那久远年代以来,社会生产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一次次工具——兵器的革新。于是,很早人们就有理由把工具——兵器对象化、情感化乃至人格化了。至于特殊的兵器,如剑,除了作为护身工具外,因形制、质料及特殊锻炼工艺而具有了神物特质。在龙蛇化剑母题中兵器的物性与人性相沟通,既渗透着原始宗教的意味,也部分代整体地折射出英雄的德性。作为传统英雄的“奇里斯玛”(charisma:神圣的天赋)人格标识,民间传说裹挟着神秘思维固化了兵器与英雄的对应关系,兵器的妖性与英雄的神圣性是一体两面、对立统一的文化存在。
一是工具人格化为神物,与其神格化交织统一。神话学家指出,技术发展的中介作用在工具发明及运用中可见:“工具被当做一种因其自身而在的存在,赋有着自身的力量;工具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反倒成为人受其意志支配的神或鬼——人感到自己依赖于它,于是就以种种具有宗教崇拜性质的礼仪崇拜它……祷告并非祈求某位远方的神来指挥这手中的武器——武器本身就是神,就是援者和救者。”而工具,“起源于某种文化英雄;这个英雄要么是神,要么是兽”[15]。18世纪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则从工具发明者的角度,说明了工具崇拜:“最初的勇士,最古代的英雄,技术的发明者,祭师,立法者,宗教的奠基者,占卜者,魔术师在生时都受到人们的盲目的崇拜,从同时代人那里获得超自然存在的物的光荣……”[16]把人的社会性力量、人的社会地位、职能与贡献作用都融进宗教中,并以此作为受到膜拜的标志。
二是神奇兵器之于英雄,既是其身份标志,又是力量象征。一般认为,中国原始宗教中的英雄崇拜有两类,一类是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作为崇拜者祖先;一类是生产及其工具的发明创造者(如有巢氏、燧人氏、后稷等)。《国语·鲁语》展禽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又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犯之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之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黄水而啄死,禹能以法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说明像黄帝、神农、尧、舜、、禹一类人物之所以受到膜拜,完全是因其对于社会的贡献,或安邦定国、辛勤于事,或者有所创造发明。
三是兵器与英雄共命运,有时甚至是其生命体的组成部分。即使在兵器这种特殊的工具闲置时,其神性仿佛持续潜存之,血崇拜往往强化、印证了兵器的灵性。明人《菽园杂记》载参将赵妥儿从土中得一刀,每当地方将有事:“则自出其鞘者寸余,鞘当刀口处常自割坏。识者云:‘此灵物也,宜时以羊血涂其口。’妥儿赖其灵,每察见出鞘则预为之备。以是守边有年,卒无败事……”[17]兵器上的灵气时时令主人警醒,不至于意外突发前无备。相传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就会鸣声示警:“大刀鸣如洪钟一般,大家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只见关羽突然感到头晕目眩,立刻倒地。周仓便用青龙刀将押来的奸细一下砍为两段,大刀立刻停止鸣叫,关羽也慢慢地苏醒过来。”[18]
四是民间传说固化了兵器与英雄的神秘关系,形成有影响力的思维惯性。李福清先生曾指出各民族史诗中:“壮士的武器和他的坐骑的描写通常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的平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一幅类似的图景。史诗英雄一般都配上独具特色的武器,他的马也具有神奇的功能。”据传说称关羽请铁匠打造宝刀,忽炉中迸出光芒直射天空,正在经过的一条青龙被斩,龙血浸染了刀鞘内的刀;有的传说称周仓献刀,上嵌青龙,原来他父亲打造此刀时,火球从天上落到刀上,刀面上就镶嵌了一条小青龙,刀就仿佛是青龙蛇化身,因这青龙系王母娘娘瑶池的守池龙,与赤兔(神龙下凡为马)相爱被谪下凡:“这些传说可能保存了一些较早的要素。”[19]所以,把英雄的兵器视为有生命的灵物,是一个具有延续力的悠远民俗信仰。
于是,兵器这一人们征服外域、捍卫家园的利器,它的工具性使用价值在缩小,而其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在扩大,作用很容易被夸大,与英雄崇拜互为“爱屋及乌”,于是它在民俗心理中愈加膨胀,必然被逐渐塑造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活跃在适合其生存繁衍的通俗小说中,还通过其传奇性和神秘信奉口头传扬互动,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自洽循环圈。故事的书写者和文化接受者有意选择龙蛇化兵器母题的思维惯性,对抗他者文化冲击,以致固步自封自我愉悦,有意摒弃实践差距的惊心动魄,用想象消解现实苦痛。
三、龙蛇化剑母题的现代性元素解构
工具本身从功能上说是人类征服世界不可或缺的帮手。但人不是单纯地创造了工具,他们对自己的创造物是有情感寄托甚至理想期待的。而在文学世界里,更将工具对象化,乃至神奇化,则不仅是对工具功能丰富的心理期盼,更是人们理想与实践的艺术化投射。实际上,作为民族性文化过程的艺术现象,龙蛇化剑母题在完善英雄形象的同时,还完成了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元素解构。这是民族文化自洽运行中矛盾对立又互为作用力的推进过程。
首先,龙蛇化剑母题,在古代小说作品中有着重要的文本结构作用和艺术表现功能。
一是母题具有预示作用,表示人物命运幸运或不幸陡转,某种重要变化要降临,来自谶言传统。明末《禅真逸史》写钟守净恩将仇报,向梁主进谗逼走林澹然,在寺中倒行逆施,后在大殿拜诵水忏时忽风作雾起,“正梁上飞下一条大蟒蛇来,遍体皆黄,亮如金色,双睛闪烁,口中喷火,身长十尺有余,昂着头张开大口,径奔钟守净……”钟躲在关帝神橱暂且偷生,其弄蛇乞丐出身的徒弟雷履阳被蟒蛇挥尾打死。蛇入荷花池,原来是林澹然的熟铜禅杖[20]。小说下一回禅杖缩入土中,引众人掘出的石碣有字:“少女树边目,人驮二卯哭。善者福自生,恶者祸相逐。”众僧明白林是好人,而钟为恶辈,铜杖化蛇预警为不祥之兆,后果寺毁身亡。
二是英雄的命运既然与其兵器紧密相连,那么,与古代传说中的“宝失家败”母题相关的英雄“剑(枪、刀等兵器)失人亡”模式相关。仿佛《说岳全传》中岳飞遇不测前沥泉枪无端被摄走,说唐系列的鸳湖渔叟《说唐全传》,也写尉迟恭在宝鸡山经过,山石开露石匣,匣中有白红两铁羊,道士李友白留下红的,白为尉迟恭收藏,李称“若要铁羊开,除非仁义血”,尉迟恭杀了名叫仁义的县差血浇铁羊才获雌雄二鞭。这鞭与英雄尉迟恭命运攸关,鞭在人在,鞭断人亡。需人血开启,似乎残留着某种神物的本性[21],但这里却没写鞭失英雄死,而是延迟到后面很久。尉迟恭还收服了金龙池内怪物,击败后才发现是匹黑马,据毛色名为乌骓马。于是英雄坐骑与兵器就被史诗手法书写成神赐配备,英雄的神格一面得以突出。而别本《说唐三传》写薛蛟问薛葵兵器有否,后者答在山里遇虎,追入洞中拿住虎尾拖出,老虎竟变成了两柄笆斗大的铁锤,薛葵得山中老道教习,锤法精通[22]。而薛蛟则拥有李靖赠的牛头马身的仙马及兵器,吃了李靖大仙之枣而“力长千斤”。
三是仙赐兵器往往在损坏或失去之时,也是英雄尘缘已尽之日,是为有得有失。前引小说还写尉迟恭要谏阻朝廷杀害薛仁贵,“他持竹节钢鞭闯宫击打止禁门,那鞭分为十八段。尉迟恭大惊:‘不好了,当日师傅有言说,鞭在人在,鞭亡人亡。’再看门上写着‘止禁门’,说道:‘宫中止禁门,凭你什么大臣,不奉宣召,不敢到这里,倘非宣召到此,就要斩首,我倚仗着这条鞭,如今断了鞭,焉能得出去……’”奏拜后便撞禁门而死[23]。于是故事情节遂变得较为完整,英雄与其兵器的共同命运具有复合性、连带性,照应了前面的母题昭示。无论如何,兵器的失去或毁坏,也仿佛就像英雄要复化为神,回到神境归位一样,结束了尘世一遭的旅行,完成了既定的光荣使命。禁忌,与“宝失人亡”母题也纠结一处。而梁武帝骁将昌义之任北徐州刺史,常派人将兵器铁扁担磨洗为快,一日扁担忽放白光,又一日有铮铮啸声,他认为“快则改常”,恐不能久,果不多时抱病而亡[24]。可见,海外学者统计的第302B型“英雄的生命和剑不能分开”母题中,仅列举陈石峻《泽玛姬》(藏族)[25],很不够。说明通俗小说母题研究仍任重道远。
四是该母题可对英雄形象起到烘衬、延展作用。龙蛇之类妖物作兵器的出现,往往必与英雄的出场乃至一连串的英雄业绩相关,兵器的奇异恰说明英雄不同凡响。薛尔曼曾指出这汇聚着多民族精神的一个共同信奉:“我们只要忆起很多历史的传说与仙女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了,在这些传说或故事中,英雄们也恰靠某种指定的工具或武器,完成光耀的伟业与行动,若以平常的武器或工具,他们好像就不能有这些功绩似的。”[26]难以想象,吕布没有方天画戟,关云长没有青龙偃月刀,张飞没有丈八蛇矛,窦耳墩没有虎头双钩……上述多民族的共同信奉之于中国古人,也不例外。古人的观念,每每标举所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以此推而广之,似乎某种兵器注定就是为该它所得、所用的英雄准备的。而英雄竟也非有此特定的兵器才能最充分、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神通。《后水浒传》写乐汤自述当年在黄河中见一物,忽沉忽浮如游龙般,捞出方知是一条浑铁棍,棍头字迹“配偶木易(杨),用之纵横”[27],后此棍果然落在英雄杨幺之手,杨被捕,棍一度失落,但最后还是又回到杨幺之手。龙蛇化宝剑,在侠义公案小说里还被渲染为英雄得蒙神佑,仿佛有意将神异兵器赐其铲平人世不平。《施公案》写张帮带在郑家花园见一妖物被吓昏,李公然赶来与妖奋力打斗,惯到太湖石上,不料妖竟变成宝剑,“青光闪烁,冷气侵人”,砍石如泥。后得剑鞘才知这是魏武帝青虹宝剑[28]。
五是母题对故事情节的勾连结撰作用。清人佚名小说《天豹图》第二十四回写,卢赛花被黑面妖精口吐的黑烟喷倒,陶天豹追赶,只见一只乌金锏,天豹猜疑“莫非此锏年久成精”,又来一妖持双锤来打,被击倒地变一锏,两锏分别标注“乾”“坤”,拜见仙师才知是祖公、镇国大将军所留。后卢赛花在陶天豹收妖得锏后动了“怜才思念之心”,画下天豹图像相思并借此与陶相认,天豹也以这神奇兵器平奸,得与卢小姐完婚[29]。前举《蜀山剑侠新传》写孙同康也在获神剑时服食剑柄仙藤灵汁仙药,功力大增,仿佛幸运不是偶然孤立降临,英雄获取神奇兵器时就应具有与神兵相搭配的神力,神奇兵器才不至于辱没。于是神奇兵器,就成为一个吸附和扩散力极大的意象乃至意象群,使侠义英雄功业叙事合情合理。
六是神奇兵器还往往沟通了艺术思维与仙话思维——神秘崇拜的联系,成为构成明清以降小说与民俗文化互动的母题之一。这里,借助特定的母题套路,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和侠义公案诸般题材的通俗小说,其通俗文学的共同性特征都被不约而同地调动起来,英雄形象描绘得以充分展开,奇迹般地获取兵器—使用兵器—无可挽回地失落兵器—结束英雄的生命历程,仿佛众多文本内在肌理的草蛇灰线。而这无可置疑是接受者最为关注、欢迎的主要关目之一,英雄命运的信号正是这样时隐时现,吸引着他们。而这些,其实单只是艺术思维还远远不够,母题正是起到了这种多方面沟通会同的美感效应。
其次,龙蛇化剑母题不仅是英雄形象审美生成的艺术技巧、个人命运隐喻,更是民族精神与族群文化的载体,具有文化隐喻意义。
一是作为民族性思维惯性现象的龙蛇化剑与英雄神化,是文化渗透的结果。早在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就载有“警恶刀”:“贵妃父杨玄琰,少时尝有一刀,每出入道途间,多佩此刀,或前有恶兽、盗贼,则所佩之刀铿然有声,似警于人也。玄琰宝之。”但是,刀枪一类兵器的鸣声却并不是都能从正面理解的,该书卷下载:“武库中刀枪自鸣,识者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之乱、大驾西幸之应也。”兵器这一特殊工具就很自然地有了某种预见——尤其是具有示警功能。不难看出,兵器的拟人化书写,尤其是妖化英雄兵器,以兵器的利己特性展示英雄的利他品格中的利己欲望,包括建功立业的欲望。对于兵器和英雄的关系,概言之有二:臣仆关系和合作关系。它待时而出,一旦英雄临近就毛遂自荐,仿佛寻求知遇的明主。《异说反唐全传》(《薛刚反唐》)写薛蛟薛葵打算除掉花豹山四神祠里享用童男童女的妖怪,他们学悟空、八戒那样扮童男童女埋伏,届时这尖头细身、两头大如斗、白面有毛、黑如烟煤的四妖认得是主人,都现出原形伏地下。薛蛟左手抓住白龙大王的滚银枪,右手按住一匹白银獬豸;薛葵左手拿住两柄乌金锤,右手扯住黑麒麟马[30]。这妖化的兵器与坐骑,后助两位英雄屡建奇功,夺回江山报仇,利己利他。《施公案》写施公在徐州巡视,夜见窗前怪兽“眼如铜铃,口似血盆,头若巴斗,一身的绿毛,约有七尺多长”,贺人杰追至斗姥阁;下一回写他将这个手持双锤的妖怪擒住,忽昏迷,清醒后细看膝下有两铜锤斑斓可爱,天明才见柄上刻字——“山东贺人杰用,凭此建功立业”[31]。母题渲染了斗怪得宝的传奇性和神秘色彩,“宝贝兵器神授”的悬念,往往持续到最后才揭晓。凭借兵器而建功立业,实现个体价值。尽管是“妖化的兵器”,却更全面地展示了人性欲望,解构了自身神圣,使英雄神化的文化自洽功能得以彰显。
二是借助原始思维的潜在影响,固步自封地在文化传统中循环,弱化着自我认知力量与自我超越。如金庸《碧血剑》第四回创造性地把兵器本为龙蛇所化作为一条隐伏线索,同洞穴秘笈母题结合。写袁承志在十三岁时发现铁盒《金蛇秘笈》,长大后练到金蛇剑法,顿悟金蛇郎君埋骨洞壁上的图形,来到实地拔出当年力弱未能拔出的剑柄:“那剑形状甚是奇特,与先前所见的金蛇锥依稀相似,整柄剑就如是一条蛇盘曲而成,蛇尾勾成剑柄,蛇头则是剑尖,蛇舌伸出分叉,是以剑尖竟有两叉。那剑金光灿烂,握在手中甚是沉重,看来竟是黄金混和了其他五金所铸,剑身上一道血痕,发出碧油油的暗光,极是诡异……”令人联想起宝剑金蛇所化的灵异、金蛇郎君的遗威。
这或许是人类的一个共同难题,亦即超越了族群阈限地的文化传承。《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写神赐摩西行神迹的权能,将摩西的杖变为蛇,神嘱摩西,拿住蛇尾,蛇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旧约·民数记》写以色列人出埃及途中辛苦抱怨,耶和华就派火蛇咬死了一些人,摩西祷告,耶和华命摩西造一条火蛇,摩西造一铜蛇挂杆上,凡被蛇咬者望见这蛇就活了。这体现出工具(神物)与使用者(英雄)之间的对应及前者对后者的烘衬。人类学家曾指出原始思维中的仪式:“在军事行动开始时,又有对马、武器、个人和集体的守护神的祈祷,用以迷惑敌人,使他失去防卫能力和使他的努力归于无效的巫术行动和经咒。”[32]借助母题在古代小说中广泛延续,巫术经咒驱使兵器活灵活现。巫术思维常通过母题的复制和衍化体现,而巫术信奉作为母题的核心内驱力,两者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综上,龙蛇化剑母题的文化自洽意义由此显现。在民族远古思维延续的前提下,这也是文化延展中对立统一、发展扬弃的艺术表现。
注释:
[1]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新传》,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58~65页。
[2] (清)吴璿:《飞龙外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3] 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页。
[4] (明)清隐道士(沈会极):《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
[5] 王立:《剑的母题原型与神物幻想》,《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32~38页。
[6] 陈民旭、高飞卫选注:《延安吟》,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
[7] 钱泳等:《笔记小说大观》(影印),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384页。
[8] (明)赵弼:《效颦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2~105页。
[9] (清)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9~12页。
[10] (清)钱彩等:《说岳全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1页。
[11] 王立:《明清小说中的宝失家败母题及渊源》,《齐鲁学刊》2007年第2期,第74~80页。
[12] (明)清溪道人:《东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15页。
[13] (清) 李雨堂:《万花楼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14] 刘卫英:《明清小说神授法宝模式及其印度文化渊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24~29页。
[15]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80~81页。
[16] 牙含章:《无神论与宗教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17] (明)陆容:《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18] 马昌仪:《关公的民间传说》,广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19] [俄]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尹锡康、田大畏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2~84页。
[20] (明)清溪道人:《禅真逸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
[21] (清)鸳湖渔叟(校订):《说唐全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
[22] (清)如莲居士:《说唐三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23] (清)如莲居士:《说唐三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24] (清)天花藏主人:《梁武帝演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03页。
[25] [美]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26] [英] 薛尔曼:《神的由来》,郑绍文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5页。
[27] (清)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91页。
[28] (清)《施公案》,北京:宝文堂书店,1982年,第688~691页。
[29] 侯忠义、李勤学:《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续(8)》,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11~212页。
[30] (清)如莲居士:《薛刚反唐》,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96~197页。
[31] (清)《施公案》,北京:宝文堂书店,1982年,第1046~1047页。
[32]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