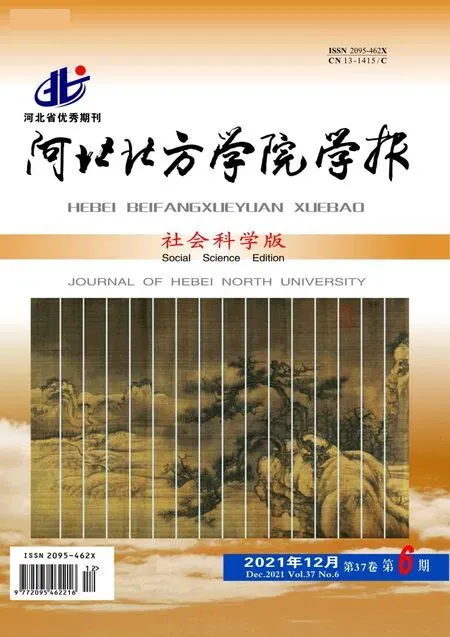东汉中晚期人才选拔困境析论
——以王符《潜夫论·贤难》为考察中心
熊 艳,桂珍明,夏保国
(1.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3.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东汉中晚期,出身庶族的下层知识分子王符在察举制发生蜕变而引发的“汉末选官危机”①下,深受人才选拔弊端之害。因此,他在《潜夫论·贤难》一文中针对以“贤难”为中心的人才选拔困境,批评“东汉时期颇为严重的嫉贤妒能社会风气”[1]43。文章以“贤难”为考察中心,结合史料探求导致东汉中晚期人才选拔困境——“贤难”的原因、具体表现及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得失问题,为研究东汉中晚期人才选拔困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贤难”的含义及其产生背景
王符秉持先秦以来的“尚贤”思想,关注人才的评价和选拔问题。彭丙成曾指出,“贤材主义的观点和思想不仅构成《贤难》《考绩》《思贤》和《潜叹》等众多篇章的主旨,而且直接或间接地贯穿于《潜夫论》的全书”[1]3,揭示了王符《潜夫论》一书中的“尚贤”思想倾向及分布情况。王符在《潜夫论·贤难》中,先辨明“贤难”的具体含义,再说明造成“贤难”的原因,最后指出历史上因“贤难”而带来的严重后果。
“贤难”既不是“贤材”本身禀赋难得,也不是“贤材”难求,其真正的含义是“为贤之难”,既有“贤材”处世困难,也有“贤材”容易被嫉妒戕害而遭难的两层内涵。
所谓贤难者,非直体聪明、服德义之谓也……故所谓贤难者,乃将言乎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而必遇患难者也[2]51。
东汉中晚期,人们行善积德都会被忌恨。“贤材”不敢表露自身出众的能力和德行,否则就会遭受祸患。这种现象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据《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记载,东汉中晚期“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3]1657。《党锢列传》亦载曰:“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3]2185一方面,外戚和宦官交结朋党以及任人唯亲,致使人才评价标准颠倒,选举制度也被操控,导致“选官腐败”;另一方面,士人被外戚和宦官排挤,他们愤起抗争并抨击时政。士人的上层掌握了人才品评的舆论权力,在国家评选官员时形成了“以名取人”的格局。而居于社会下层的庶族之士则因“士名不休扬,又无力援,仕进陵迟”[4]。总之,选拔制度的蜕变致使“官无直吏,位无良臣”,“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主之朝”[2]198,“贤材”在选官制度废弛的环境中自身安危难以得到保全,更遑论获得良好的上升空间。为进一步说明“贤难”根源于“嫉妒”盛行,王符用舜帝与伍子胥被“嫉妒”的事例进一步说明“贤难”的情形:
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诛,上圣大贤犹不能自免于嫉妒,则又况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虽有贤材美质,然犹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2]52。
“虞舜放殛”,指的是舜帝晚年被流放之事。《韩非子·说疑》记载“禹逼舜”[5],《史通·疑古》也有“禹黜舜而立商均”[6]的记录。“子胥被诛”则见于《史记·伍子胥列传》,《史记索隐》评价“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嗟彼伍氏,被兹凶慝”[7]2183,意在说明嫉妒与谗言导致了伍子胥的悲剧。虞舜和伍子胥这样的圣贤都不能避免“嫉妒”带来的危害,一般贤士的处境更加堪忧。“贤材”即便有能力和操行,也不能坚持正义,难以发挥其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究其根由,正是由于“嫉妒”横行。为说明“贤材”被嫉妒与迫害的必然性,王符还引用《诗经》为证:
《诗》云:“无罪无辜,谗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观之,妒媚之攻击也,亦诚工矣!贤圣之居世也,亦诚危矣[2]61!
“无罪无辜,谗口敖敖”,意在说明没有罪责也没犯错的人,同样会被众人的谗言诋毁。《汉书·刘向传》对此还加以引申,“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愬”[8]。照此看来,嫉妒者确实善于以谗言攻击“贤材”。随后,他还引述《诗·小雅·菀柳》“彼人之心,于何不臻”和“言其辗侧无常,人不知其所届”[9],指出人心的复杂性,感慨社会上嫉贤妒能的现象比比皆是,道出了“贤材”处境之艰。
处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败,暗君之所以孤也。齐侯之以夺国,鲁公之以放逐,皆败绩厌覆于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恶闻美行,政乱者恶闻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2]53。
王符认为,尚未出仕的士人不能坚持正道,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也不敢直言政治得失,致使朝堂昏暗腐朽。如齐简公与鲁昭公不听贤士之言而国亡身死;秦朝畏惧士人的议论而焚书坑儒,秦朝灭亡的教训也发人深思。君主及其臣属出于嫉妒与戒备不能把“贤材”吸纳进朝堂之上,而社会民众也轻视高尚的德行,遂造成了“贤材”处世之难的困境。
故所谓贤难也者,非贤难也,免则难也。彼大圣群贤,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据天官,柬在帝心,宿夜侍宴,名达而犹有若此,则又况乎畎亩佚民、山谷隐士,因人乃达,时论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钳口结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2]62。
王符再次重申“贤难”不是成材之难,而是难在不被嫉妒或被戕害。功成名就的圣贤地位显赫,仍避免不了因嫉妒而带来的灾祸。从东汉中晚期的现实看,处在山野的逸民隐士在选拔制度蜕变和“以名取人”的环境中更需要依靠别人的举荐才能达于朝廷,依赖舆论的称颂才能被社会信任。可见,他们所处的“贤难”境地比“大圣群贤”更加艰难。因此,贤士们的默不作声正是为了远离嫉妒和戕害。
二、“贤难”原因分析
王符在《潜夫论·贤难》中界定“贤难”含义后,还以历史上典型的史事为例,归纳出3种“贤难”原因。
(一)称人之长
王符以“邓通吮疮固宠”及其称誉太子之孝而遭到打击报复的事为例,介绍了“贤难”的第一种原因。
今世俗之人,自慢其亲而憎人敬之,自简其亲而憎人爱之者不少也。岂独品庶,贤材时有焉……故邓通其行所以尽心力而无害人,其言所以誉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尽其称,则反结怨而归咎焉。称人之长,欲彰其孝,且犹为罪,又况明人之短矫世者哉[2]54-55?
东汉中晚期的世俗之人不仅怠慢自己的父母,还反过来憎恨尊重和关爱自己父母的人。因为别人高尚的道德言行会让他们自惭形秽,这种情况在普通百姓和贤能之人中普遍存在。王符通过邓通侍奉汉文帝的典故说明“称人之长,欲彰其孝”的善意行为也会为自己带来罪愆。邓通能够尽心服侍文帝,甚至为其吸吮毒疮。汉文帝询问邓通谁是最敬爱他的人,邓通回答说太子。事实上,太子却做不到像邓通那样为文帝“吮疮”。等到太子继位时,邓通就因为此前称颂太子之孝遭到了打击报复。称赞别人的长处且彰显别人的孝行尚且会招来罪责,指陈别人的短处与矫正社会风俗则更会招致严重的祸患。
(二)言行触犯他人
“贤材”的“嘉言懿行”不仅会招致人们的嫉妒与谗毁,更会因此触犯他人而招致性命之忧。这是“贤难”的第二种原因。
且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誉人而已也,必有触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痈而已也,必有驳焉。然则循行论议之士,得不遇于嫉妒之名,免于刑戮之咎者,盖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为奴,伯宗之以死,郤宛之以亡[2]55-56。
王符指出,士人的贤能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言行方面。行为中正,不是简单地称誉别人;恭行孝道,也非单纯地吸吮毒疮。“贤材”的道德品行高尚,但这种行为本身就会令不如他的行为主体心生嫉妒,从而触犯他人。在当时,贤材因言行触犯他人是常态,而不被嫉妒或免于刑戮反而是侥幸。王符列出比干、箕子、伯宗和郤宛等圣贤史事,说明“贤材”因言行触犯他人而招致“贤难”。《史记·殷本纪》载曰:“(比干)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7]108。《左传·成公十五年》载伯宗“好直言”,“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10]473。《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则记载郤宛“直而和,国人说之……令尹子常贿而信谗。(费)无极谮郤宛焉……令尹使视郤氏,则有甲焉。不往,召鄢将师而告之。将师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恶(郤宛)闻之,遂自杀也”[10]789-784。在王符看来,比干、箕子、伯宗和郤宛被害皆源于“既患其正义以绳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职而策不出于己”[2]78。
(三)贤材内部争夺功名
王符揭露了“称人之长”与“言行触犯他人”是造成“贤难”困境的外部原因,还指出了导致“贤难”的内部原因,即“贤材”之间的争名夺利。这也是“贤难”的第三种原因。
近古以来,自外及内,其争功名、妒过己者岂希也?予以唯两贤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睢绌白起,公孙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宠禄争故耶?惟殊邦异途利害不干者为可以免乎?然也,孙膑修能于楚,庞涓自魏变色,诱以刖之;韩非明治于韩,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杀之。嗟士之相妒岂若此甚乎!此未达于君故受祸邪?惟见知为可以将信乎?然也,京房数与元帝论难,使制考功而选守;晁错雅为景帝所知,使条汉法而不乱。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谓见知深而宠爱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错既斩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卫身故及难邪?惟大圣为能无累乎?然也,帝乙以义故囚,文王以仁故拘[2]58。
王符以先秦与秦汉时期“贤材”间相互争夺的事例为证,说明因“功名”和“嫉妒”导致“贤难”问题的普遍性。范雎和白起、公孙弘和董仲舒同朝为臣,因嫉妒白起被范雎杀害,董仲舒被公孙弘陷害远离朝堂;庞涓和孙膑处在不同的国家,因嫉妒庞涓诱骗孙膑至魏国砍去他的双脚;李思因嫉妒而谋算韩非,将他招致秦国并杀之;京房和晁错都以才能受到君王的重视,京房被冤屈致死,晁错被腰斩;即使拥有王侯之位的帝乙与文王,也因笃行仁义而遭到囚禁和拘押。此外,王符还根据“贤材”被嫉妒与被伤害的情节轻重,区分出“身死”和“黜退”两种不同结果。
夫体至行仁义,据南面师尹卿士,且犹不能无难,然则夫子削迹,叔向缧绁,屈原放沈,贾谊贬黜,钟离废替,何敞束缚,王章抵罪,平阿斥逐,盖其轻士者也[2]58。
被伤害的情节较重者,如白起、孙膑、晁错和京房等,被残损肢体或付出生命的代价。被伤害的情节较轻者,诸如孔子、叔向、屈原、贾谊、钟离意、何敞、王章及平阿侯王仁等,在政治上遭受排挤或被贬黜。
三、东汉中晚期人才评价缺陷
东汉中晚期,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人才评价的缺陷与“贤难”现象紧密相关。社会评价的盲目性和人才选拔制度的蜕变,是造成人才评价缺陷的两大因素。
(一)社会层面人才评价缺陷
人才评价受社会环境及民间舆论的影响,这在东汉中晚期的“选官危机”中表现尤为明显。王符以社会舆论为切入点,并列举司原氏畋猎的寓言,旨在指陈东汉中晚期社会层面品评人才的过失。
且闾阎凡品,何独识哉?苟望尘剽声而已矣。观其论也,非能本闺之行跡,察臧否之虚实也;直以面誉我者为智,谄谀己者为仁,处奸利者为行,窃禄位者为贤尔。岂复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纲纪之化,本途之归哉[2]63?
王符指出,身处乡里的普通人大多只看到事物的表象,人云亦云。他们往往把当面称赞或阿谀奉承自己的人当成智者与仁者,把作奸谋利或窃取禄位之人当作能者与贤者。因此,当他们评价人物时,不能根据士人的实际言行来进行判别。那些靠虚假声誉而窃据高位的人根本不知道孝悌的本源、忠正的真谛、礼仪纲纪的教化以及人生正道的归处。此外,“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2]89是当时社会评价人才的真实情况,而王符所处的环境是“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3]1630,他出身“庶孽”且没有强力的外家援助,在乡里的舆论评价中“为乡人所贱”。东汉时期,社会舆论鄙弃知识分子不是个例,范晔在《后汉书·樊英列传》中评论道,“汉世之所谓名士者……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3]2724-2725。吕思勉认为,“所谓无行,亦不过不能修饰,以要世名誉,非必有恶行为乡里所患苦也”[11],点明了东汉时期社会舆论鄙薄寒门士人的实质。寒门士子没有财力与权势去取悦乡里民众,也无力结交权贵,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孝悌和忠正等美好品德也随之被淹没在世俗舆论当中。如王符在《潜夫论·贤难》中指出:
谚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伤世之不察真伪之情也,故设虚义以喻其心曰:今观宰司之取士也,有似于司原之佃也[2]65。
社会舆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王符引用谚语来说明没有主见且不了解真相的人随声附和他人的社会舆论现象,并指出世人痛恨这种盲目从众的现象已经很久了。王氏对这种不辨真假的人才评价标准深恶痛绝。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人们随波逐流的现象,他还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了司原随声跟风和逐鹿获猪之事。司原畋猎“鹿斯东奔,司原纵噪之。西方之众有逐狶者,闻司原之噪也,竞举音而和之。司原闻音之众,则反辍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恶之狶。司原喜,而自以获白瑞珍禽也”[2]65。司原在东边逐鹿,西边的众人在追赶一头猪,众人听到司原的呼喊竞相应和他。结果司原放弃了正在猎取的鹿,转而埋伏众人追赶的那头身上涂满白泥的猪,这让他很高兴,自以为猎得了白色的珍稀异兽。后来一场大雨冲掉了猪身上附着的白泥,他才知道所谓的“异兽”原来是只家养的公猪。王符所引谚语和寓言故事体现了社会从众心理对舆论的影响。赵凯在分析秦汉舆论特征时指出,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舆论一旦形成,往往具有满城风雨、全村犬吠的效果”[12]。以财力取悦民众或以权力交好权贵来提高名声的人正是借着社会舆论的盲目性获得高官厚禄,但当国家面临危难时,他们身上附着的“嘉言懿行”也随即会暴露出来。
(二)国家层面人才评价缺陷
王符在批评东汉中晚期社会层面的人才品评的缺陷后,将论述的重点转向国家层面。国家缺乏有效的人才辨别方式,官员嫉贤妒能阻塞人才举荐渠道,这是国家层面的人才评价的缺陷。王符进一步指出:
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见贤则不敢用,耳闻贤则恨不及。虽自有知也,犹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举,则亦惧失麟鹿而获艾猳。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风雨之变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两集,则险隘之徒,阘茸之质,亦将别矣[2]67。
东汉中晚期的君主亲眼见到“贤材”不敢任用,仰慕远方的人才却只能徒劳兴叹。虽然君主自己对“贤材”有一定的了解,但还要依靠群臣举荐才能任用,且还担心会出现司原那样随声逐响与跟风从众的问题。君主之所以难以辨别“贤材”的真才实学,是因为国家没有遇到真正的危难,“贤材”的才能难以凸显。国家一旦面临危难,朝堂政局变异接踵而至,那些心地奸恶与庸碌无为的人就会被甄别出来。
王符道出了东汉中晚期君主在贤材任用方面裹足不前与进退失据的窘境。在汉代察举制的制度建构中,臣属有为君主推荐“贤材”的义务。因此,士人需要依靠官员举荐才能被君主了解与任用。当时,“贤不得用者,群臣嫉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2]126,“当涂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于君以矫其邪也,故上饰伪辞以障主心,下设权威以固士民”[2]75。作为沟通君主和士人之间桥梁的大臣,一方面,他们因为嫉贤而阻塞了君主选拔“贤材”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们又以谗言掩饰自己的邪恶,对上编造虚假的言辞迷惑君主,对下滥用权力钳制士人和民众。有鉴于此,王符提出“圣王表小以厉大,赏鄙以招贤,然后良士集于朝,下情达于君也”[2]73,即圣明的君主应该通过表彰小行来勉励大德,以此招致“贤材”。只有这样贤材才会聚集到朝堂之上,民情方可传达到君主那里。
夫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啮贤,为祸败也岂希?三代之以覆,列国之以灭,后人犹不能革,此万官所以屡失守,而天命数靡常者也。《诗》云:“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呜呼!时君俗主不此察也[2]67。
众多小人在朝堂之上结党营私巩固权位,谗谄嫉妒之人如群犬狂吠般撕咬“贤材”导致国家覆亡的事例不在少数。夏、商和周的灭亡以及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覆灭,都与党争及妒贤紧密相关。“天命数靡常”出自《诗经》,“天命靡常”强调“‘天命’本身也是可变的”[13],意在说明国家要长久地保有“天命”,就要避免“贤难”,保证人才选拔制度公平公正。王符还以《诗·小雅·节南山》“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为证,指责昏君谗臣不吸取历史上国破家亡的教训。谗慝之臣对国家的生死存亡视而不见,昏庸的君主也不能明察和任用贤材,造成东汉时期国家在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这也正是《潜夫论·贤难》的主旨:“论蔽贤之为害,伤直道之难行。世不患无贤,而患贤者之不见察。”[2]52
综上所述,《潜夫论·贤难》是王符针对东汉中晚期人才选拔困境——“贤难”而进行的批评。王氏认为,国家层面的人才评价缺陷是:国家缺乏有效的人才辨别和遴选机制;居于君主和士人之间的官员出于嫉妒和朋党利益,未能很好地履行选贤与荐贤之责,致使选官制度腐败。社会层面的舆论评价导致“贤难”的人才评价缺陷是:社会舆论具有盲目性,普通民众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惑于表象,盲目从众,致使舆论导向鄙薄寒门士人。“贤材”间的相互竞争是“贤难”问题的内因,这种竞争也为“贤材”的仕进带来了困难。总之,“贤难”反映出东汉中晚期“选官危机”下人才选拔名实不符,寒门士人难以得到保护且难以获得正常仕进渠道的人才选拔困境。
注 释:
① 阎步克认为,东汉后期在王朝与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其主要的选官制度即察举制也遇到了“选官的腐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3个严重的危机。(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