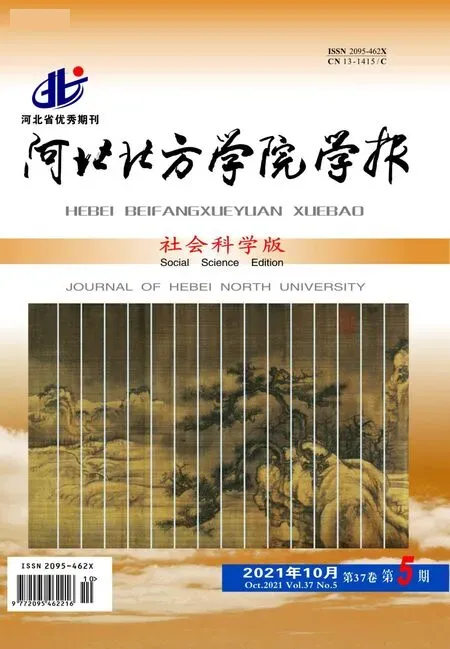后周高平之战新论
陈 巧 锐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对高平之战胜利的原因,传统史书和今人著述多着墨于周世宗柴荣以及赵匡胤等人的浴血奋战①。而对该战最为戏剧的一幕——身居马军和步军最高长官的樊爱能与何徽两人的临阵溃逃,学界通常只关注此事之后世宗对军务的整顿。清代赵翼云:“高平之战,(世宗)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1]541齐勇峰则从军制改革的角度出发,认为此事使世宗下定决心扩充殿前军[2]61。可见,大多数研究仅将此事视为世宗整顿军纪与改革军制的一环,却忽略了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重要意义。此外,侍卫亲军作为当时军队的绝对主力,大规模溃败却未导致战役失利,这更不能简单解释为世宗及其亲卫军的英勇。曾国富曾从北汉的轻敌与风向的偶然性方面寻找原因[3]82-83,虽另辟蹊径,但未能摆脱“危急之势,顷刻莫保,赖帝英武果敢,亲临寇敌,不然则社稷几若缀旒矣”[4]1513-1514的传统观点。诚然,柴荣和赵匡胤等人的英勇奋战能够简单勾勒出高平之战的主要轮廓,并为此后柴荣的改革和赵匡胤的易代张本。然而,历史事件的发展并非独立存在,高平之战只是当时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点。下文以侍卫亲军统帅樊爱能与何徽两人临阵哗变叛逃为中心,从另一个角度解释高平之战胜利的原因,以期还原此战的真实面目。
一、太祖与世宗之际的政局和禁军主帅选任
后汉末年,政治局势复杂,郭威以“黄袍加身”登上帝位。由于“被迫”继位,因此郭威于外未能安抚好河东刘崇,于内不得不采取部分妥协政策以换取重臣和藩镇的支持[5]152。从军事方面而言,郭威甫一继位,面临的军事威胁即有数次,《旧五代史》记载:
广顺元年春正月……湘阴公元从右都押牙巩廷美、教练使杨温等,据徐州以拒命[4]1462。
广顺元年春二月……晋州王晏奏,河东刘崇遣伪招讨使刘钧、副招讨使白截海,率步骑万余人来攻州城[4]1468。
广顺元年十二月……郓州奏,慕容彦超据城反[4]1479。
《资治通鉴》云: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6]9466。由此可见,仅广顺元年(951),便有两镇叛乱及刘崇的两次入寇,北汉与契丹的联合入侵威胁甚大,致使郭威几欲亲征。一直到次年六月兖州慕容彦超叛乱被平定后,郭威才将叛乱入侵的威胁解决。
国内政治问题也相当严峻,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峻与王殷两人尾大不掉和功高震主的问题。王峻时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郞、同平章事,以本官充枢密使,领兵抵御刘崇入侵,麾下兵士精锐,甚至能在随从郭威亲征慕容彦超的战斗中先登[4]1713。王殷则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邺都留守和同平章事。邺都虽在后晋时因魏博镇遭拆分后已势弱,但依旧为河北雄藩和河南屏障,且后晋以后多以中央禁军坐镇,郭威即曾以邺都留守身份镇邺。邺都的重要性毋庸多言②。但当时而论,单以邺都留守一职而言还不至于威胁到中央。王殷身为禁军统帅,又以侍卫司局随之,有指挥河北征镇戍兵之权[4]1626,这与郭威继位前以枢密使镇邺指挥河北诸州的情况如出一辙[4]1453。作为“佐命有功一体之人”[6]9493,郭威不得不采取策略将王峻和王殷各个击破。国内局势大致稳定后,广顺三年(953)二月将王峻贬至商州,并尽力安抚王殷。诚然,王峻与王殷不懂明哲保身之术,但作为世宗继位后的最大障碍,这二人也必会被铲除④。因此,显德元年(954)太祖认为“殷有震主之势”[4]1626,随即将王殷处死,为世宗继位后掌权铺平了道路。至此,后周政治初步稳定。但脆弱的稳定并未维持多久。后周显德元年(954)正月郭威病逝,二月庚戌,刘崇即联合契丹举兵南指,此时距离世宗继位还未足半月。《资治通鉴》云:“北汉主闻太祖晏驾,甚喜,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契丹。”[6]9501刘崇曾于广顺元年(951)大败,遂“息意于进取”[7]1479,此次入侵明显是想在后周“山陵有日,人心易摇”[4]1511之时以求胜利。
刘崇的想法大致无误。世宗虽欲亲征,但在朝堂之上受到很大阻力。《旧五代史》载:冯道等以帝锐于亲征,因固诤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悦而罢[4]1511。冯道等人作为数朝老臣以持重为己任,不欲世宗亲征。王夫之《读通鉴论》中所指出的“荣虽贤,不知其贤也,孤雏视之而已”[8]933,王氏此语指代的是所谓“武人”的看法,实际上朝堂之文士亦是如此认为的。因此,世宗只能力排众议,一意亲征。世宗此时的“力排众议”是具备前提条件的。首先,二王势力铲除后,郭威为世宗安排的军队辅政格局中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一职空置,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出镇,并提拔“素无大功”[6]9507的樊爱能和何徽两人为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为李重进,而殿前军此时还未作为与侍卫亲军等齐之军,在樊爱能与何徽等被提拔之日,李重进才由防御使进至节度使,身份获得提升,殿前军也才与侍卫亲军并驾齐驱。李重进虽年长于世宗,又由于是郭威外甥而身份特殊,然无功劳威望傍身。因此,当时的侍卫亲军由樊、何二人分别统帅,殿前禁军由李重进和张永德统帅。这是太祖以自己对世宗能力的了解而为其制定的一个权力能够平稳过渡却不需藉“元从功臣”辅政的另类“辅政格局”,也奠定了殿前军、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鼎足而立的局面[9]354。因此,在世宗继位至亲征刘崇这一段时间内,虽然世宗于朝堂尚无威望,但也没有任何“强臣”可以左右世宗之决策。其次,世宗将李重进提拔为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为当时侍卫亲军首要将领[10]13795-13796,将张永德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10]8914,获得了二人的绝对支持⑤。
概言之,太祖郭威临朝之时尽力剪除朝中具有潜在隐患的军政强臣,任用容易控制的将领。世宗在继承这一人事格局的基础上,任用有较大勋劳威望且和自己有亲缘关系的李重进和张永德掌管侍卫亲军与殿前诸班。世宗此举既强化了自己对禁军的控制,保障了朝中军政的较大决策权,又制衡了樊、何二人,使诸军相互牵制。
二、樊、何二将溃师原因再分析
关于高平之战的过程,《旧五代史》云:
(帝)乃令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李重进、滑州节度使白重赞将左,居阵之西厢;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将右,居阵之东厢;宣徽使向训、郑州防御使史彦超,以精骑当其中;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以禁兵卫跸。帝介马观战。两军交锋,未几,樊爱能、何徽望贼而遁,东厢骑军乱,步军解甲投贼,帝乃自率亲骑,临阵督战。今上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战士皆奋命争先,贼军大败[4]1512。
《旧五代史》对世宗临阵安排及战斗过程的描述比较详细,对北汉军大败的原因也作出解释,但对于樊、何二人“望风而遁”的原因却不置一词。加之樊、何二人均无传记,只能从史书中抽丝剥茧。相较而言,《资治通鉴》在记叙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但其语基本取材于北宋陶岳所著《五代史补》:
世宗之征东也,驻跸于高平,刘崇兼契丹之众来迎战。时帅多持两端,而王师不利。亲军帅樊爱能等各退衂,世宗赫怒……凯旋,驻跸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诛退衂者,乃置酒高会,指樊爱能等数人责之曰:“汝等皆累朝宿将,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者无他,诚欲将寡人作货物卖与刘崇尔。不然,何寡人亲战而刘崇始败耶?[11]29
《五代史补》成书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多采传闻,与正史或有冲突,但至少代表了当时人的看法。该书对于樊爱能等人行为的解释是“时帅多持两端,而王师不利”,“欲将寡人(世宗)作货物卖与刘崇”。根据当时战场情况,樊、何所领之右军作为刘崇第一次攻击的目标,并未有败象。从《旧史》所载:“贼骑来挑战,爱能望风而退,何徽以徒兵阵于后,为奔骑所突,即时溃乱,二将南走,”[4]1514可以看出当时状况。再者,“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辎重,役徒惊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莫肯奉诏,使者或为军士所杀”[6]9503。骑兵被两将所引南走,不但不奉诏,当遇刘词领后军至后还散布谣言称官军已败。骑兵如此,步兵则于战场上“千余人解甲呼万岁,降于北汉”[6]9506。因此,若称樊、何二人欲将世宗卖与刘崇或可,但二人因不利而退衂则实非。王夫之曾指出:“骄帅挟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雠其不轨之志;其战不力,一败而溃,反戈内向,殪故主以迎仇雠,因以居功,擅兵拥土,尸位将相,立不拔之基以图度非分。”[8]937如此看来,二人之所作所为恐怕正是妄图制造这样一场失败以渔利。但笔者认为分析这样一件险些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不能单纯从揣测的角度去简单解释二人行为的动机。若结合当时政治环境进行解读,也许更能接近事实真相。《资治通鉴》记载了当时的两件前后矛盾之事:(显德元年正月)庚辰,加晋王荣兼侍中,判内外兵马事。时群臣希得见帝,中外恐惧,闻晋王典兵,人心稍安[6]9499。可是同书同卷又云:军士有流言郊赏薄于唐明宗时者,帝闻之,壬午,召诸将至寝殿,让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汝辈岂不知之!今乃纵凶徒腾口,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赏,惟知怨望,于汝辈安乎!”皆惶恐谢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6]9499
细考上述二事,郊赏是显德元年(954)正月朔日,即丙子日,至庚辰令柴荣判内外兵马事已有5日。太祖责问诸将则在壬午,与柴荣判兵马事方过两日。因此,此流言离郊赏之日已较长,而离柴荣判兵马事时间较短。且明宗距此至少已有20余年,其间已历四朝七帝,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文中的“军士”是不满于郊赏还是不满于柴荣,抑或是于此时借题发挥。而《资治通鉴》所谓“人心稍安”在此则更显矛盾,不知其安于何处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随即出镇,并提拔资历相对较低的樊爱能与何徽担任马步军长官,将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李重进由防御使升任节度使。这很有可能是流言问题导致郭威亦对此事存有疑虑,并调整了禁军辅政结构。且当高平之战激战正酣之际,“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莫肯奉诏,使者或为军士所杀”[6]9506。战斗结束之后,“樊爱能等闻周兵大捷,与士卒稍稍复还,有达曙不至者”[6]9506。如此而言,在此次事件中下层军士显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可能是樊、何二人单独之决定。即便二人在军中早有基础,但若其下属均无叛心,仅凭樊、何二人是很难组织起这样的行动的⑦。但“流言事件”已经不可能寻找到真正的幕后主使,因此无论是樊、何二人所主导还是单纯地利用了士卒的不满情绪,都刚好可以解释“叛遁”的基础为何。
除此之外,《通鉴》还记录了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乙酉,帝发大梁;庚寅,至怀州。帝欲兼行速进,控鹤都指挥使真定赵晁私谓通事舍人郑好谦曰:“贼势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谦言于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为人所使,言其人则生,不然必死。”好谦以实对,帝命并晁械于州狱[6]9503-9506。
控鹤乃侍卫亲军之一部[12],其主帅赵晁于大战前所言之语,实际上是表示并不赞同世宗激进的军事策略。当然,这可能是持重之语,却由此犯了世宗当时对侍卫亲军不信任的“忌讳”。换言之,侍卫亲军在关键时刻,却始终没有与世宗保持一心。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一窥高平之战前部分侍卫亲军的心态。
由此可见,樊、何二人之“卖主”正是世宗“判内外兵马事”后的“流言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无论是否有人作祟,樊、何二人都被认为获得了侍卫亲军的支持,并利用了这样的情绪,而这却使得世宗对侍卫亲军起了猜忌之心,这是当时政治矛盾的集中反映。如果就此认为所有侍卫亲军系统均对世宗不满,可能有过度解读之嫌。然而,若说与此事所关涉的樊、何二人所领之侍卫亲军对世宗有所不满,当是无误的。
三、高平之战的胜利与世宗的未雨绸缪
侍卫亲军作为各王朝之战斗主力,在王朝嬗递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当时殿前军并未建立,由侍卫亲军的不满引发了一军之溃败,却并未导致战斗的失利,这在五代史上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后晋以来诸帝由于无法获得侍卫亲军支持而失败的事例不胜枚举。五代创业诸帝均是马上天子,半生浴血。就这点而言,世宗与他们相比还略显稚嫩。因此,高平之战胜利的真正原因不仅是因为世宗及其旧僚的浴血奋战,更是因为世宗早已凭借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判断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于世宗并非郭威子嗣,于后周立国未有寸功,在平判内外兵马事之前更是未曾领兵,与侍卫亲军全无关系。因此,“流言事件”也表明了侍卫亲军中一部分人对世宗的不满。而世宗作为雄才大略的帝王,反过来也并不信任侍卫亲军。如果从高平之战后侍卫亲军的高级将领全部改由殿前军军校升任来看,世宗对侍卫亲军的不信任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但若说高平之战前这种不信任已经存在,或许有猜测之嫌,那么可以根据一则史料以窥端倪。《旧五代史》云:
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趫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至有朝行杀夺,暮升军籍,雠人遇之,不敢仰视。帝意亦患之,其后颇有不获宥者[4]1511。
该事发生于显德元年(945)二月潞州奏刘崇入寇之后,相比十月高平之战以后的整军,此事往往被忽略。实际上,此次招募诸道山林亡命之徒显然带有临时救急之意。十月的整军,“(世宗)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14]103。又“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4]1522,一则需要试阅选择,二则侍卫亲军也进行了整顿。而二月的招募,则是“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4]1511。虽然世宗“意亦患之”[4]1511,但作为权宜之计,并没有对招募者进行选阅,而是将所募之兵全部充实进了殿前诸班之中,而侍卫亲军却被完全忽略⑧。此外,李重进本为殿前都指挥使,在世宗继位后却突然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这恐怕与世宗对侍卫亲军的不信任亦有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件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樊、何二人“素无大功”之语是出自张永德口中,但事实上,樊爱能等人随郭威由邺入京,属于郭威的核心将领,何徽更是在广顺元年(951)刘崇入侵时防御有功,若论功劳,樊、何二人虽无大功,但也当在张、李二人之上,李重进与张永德反而凭借外戚身份一跃而上。因此,此次任命或许也是导致樊、何二人不满激化的原因。
既然在战前数月世宗已经开始未雨绸缪,那么之后高平之战中的布置安排便不会令人惊奇了。一者,世宗将樊、何二人所领之军同放于一翼,而其余诸军却均为世宗继位前已出镇之节度所率领。如左军白重赞自广顺中已出任义成军节度使[10]9603,中军史彦超于广顺年间出任郑州防御使[4]1630,后军刘词时为河阳节度使[4]1629。至于李重进,先不论其外戚之身份,他除了在广顺二年(952)短暂担任过侍卫亲军马步都军头以外,其余时间均在殿前诸班系统中任职。因此,其本人以及其所携带之亲卫显然与侍卫亲军无太大关系⑨。故而在高平之战中,与“流言事件”有关系的侍卫亲军,有且仅有樊、何二人所领导的右军。由于世宗的以上布置,左军白重赞与李重进在右军溃败后“勒兵不动”[10]13976;中军史彦超“为先锋,先登陷阵”[15]1630;张永德所领禁卫诸人如赵匡胤、马仁瑀和马全义等人之力战史所明言,此不赘述;后军刘词更是不相信樊爱能等所言官军已败之言辞,反而“疾驱而北”[4]1629。故樊、何二人所为的影响范围只限于本部,在诸军中并未得到响应。二者,樊、何二人所领导之右军的人数并不多。据《册府元龟》云:四月戊申,命河阳节度使刘词押步骑三千赴雒州,皆樊爱能何徽之部兵也。上以既诛其主将,不欲加罪于众,乃遣词押领,分屯于雒州[16]472。又《通鉴》有“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6]9505和“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6]9506之语,可见樊、何二人身为侍卫亲军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所领兵数至多在四五千左右。而当时仅张永德所领殿前诸班已不止四千⑩人,遑论其余诸将所领之兵。高平之战中,樊、何二人不但溃败后冲乱己方阵型,还散布已方失利之谣言,这在战场上是十分容易引发更大溃败的,但结果却并未如此,这表示世宗从未将在京的侍卫亲军作为战斗主力,而是将其保持在了一个可控范围之内。世宗如此做的前提条件,除因殿前诸班实力已相当可观外,还因世宗做了预防性的“权宜措施”,即于显德元年(954)二月募兵大幅扩充了禁卫兵数量,加之旧僚集团的配合,才取得了高平之战的最终胜利。
综而言之,后周太祖郭威死前已将显性的对后周威胁最大的政治因素铲除,然而侍卫亲军对新君不满的隐形矛盾依然存在。樊爱能和何徽二将哗变叛逃的实质是部分侍卫亲军与新继位君主柴荣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五代史上并不罕见。世宗显德元年(954)的两次整军,其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扩充殿前诸班兵力以应对战争,后者则是战后军政调整的一部分。侍卫亲军虽依旧属于骄兵悍将,但战斗力已然下降,且中央对其的分化控制已卓有成效,他们已不能凭借一己之力对皇权造成威胁,但也无法为平定乱世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侍卫亲军虽名为“天子自将之私兵”[15]298,实际上却始终效忠于某个“个人”,而非“皇帝”。侍卫亲军始终带有深刻的地域及个人属性。相比侍卫亲军,殿前诸班明显更为依赖中央皇权,故而可以为现任皇帝提供更强大的支持。殿前军的成立过程很漫长,在高平之战的洗礼后才得以正式成军,并在此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与这些隐晦的政治问题相对应的,则是战后世宗对殿前军与侍卫亲军的大规模调整。其中韩令坤、赵弘殷、慕容延钊和赵晁4人分别升任龙捷左、右厢都指挥使,虎捷左与右厢都指挥使。至此,侍卫马、步军的高级将领全部由殿前军军校升任[4]1515。由此,造成高平之战后殿前军的全面崛起。可以讲,高平之战的胜利主要在于政治上的胜利与调整,也从侧面证明了后周时侍卫亲军不但战斗力已有所下降,而且朝廷对禁军的控制和分化也已经有相当成效,此后殿前诸班的成军已是水到渠成。
注 释:
① 韩国磐:《柴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日]栗原益男《乱世の皇帝:后周の世宗とその时代》,东京:桃园社,1979年;李小树、黄崇岳:《周世宗柴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文晓章:《乱世明君周世宗》,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② 后晋拆分魏博后,后晋高祖石敬瑭长期亲自坐镇邺都。后汉则以郭威领枢密使之任坐镇,郭威本人即为实际上之禁军统帅。
③ 孟庆鑫认为二王势力的铲除乃是郭威为柴荣之继位铲除障碍,然而当时柴荣作为郭威现存唯一具有继承权之人,其继位是顺理成章亦非二王所能左右的。关键点在于即使郭威在位,对二人之驾驭亦有难度,若嗣主继位其结果可想而知,或又是五代政权嬗递闹剧的又一再演,因此二人恐应作为柴荣继位后权力稳固之最大障碍方无误。齐子通也指出郭威控制王殷是因为自己也是从邺都南下而改朝换代,不希望自己去世后,邺都再生叛乱。孟庆鑫:《后周太祖郭威安排的辅政格局及其影响》,《兰台世界》,2017年第14期,第84-86页;齐子通:《如影随形:唐宋之际都城东移与北都转换》,《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二期,第70-87页。
④ 世宗继位,擢为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其广顺二年所担任的职位,乃是马步都军头,且不久便被转为殿前都指挥使。至于张永德,只有在李重进离职后方才可能担任殿前都指挥使,故该二人均为世宗继位后方提拔,而非太祖所安排。
⑤ 闫建飞已指出,五代藩镇军队禁军化后,天子取代节度使成为其利益保障者。而侍卫亲军司崛起后,军司长官更可通过军赏与士兵结成紧密关系。因此,柴荣郊赏士兵却发生了军士不满,更可以看出此时问题的严重程度。见闫建飞:《五代后期的政权嬗代:从“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谈起》,《唐史论丛》,2019年第二期,第116-129页。
⑥ 五代士兵家属大都在京师以为人质,故将领欲叛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下属的支持,此例甚多,如《旧五代史·汉高祖纪》:帝将发滑台,召将士谓之曰:“主上为谗邪所惑,诛杀勋臣,吾之此来,事不获已,然以臣拒君,宁论曲直!汝等家在京师,不如奉行前诏,我以一死谢天子,实无所恨。”
⑦ 此事王曾瑜先生也曾注意到,并指出周世宗是因为侍卫亲军“老少相半”方决意扩大殿前诸班的兵力。王曾瑜先生仅是从兵制方面去探讨,然而此事政治方面的原因恐亦不可忽略。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页。
⑧ 关于藩镇军或中央禁军武将拥有一定数量的亲卫军的问题,具体可参看[日]崛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中文译注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85-648页。
⑨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显德元年条,第9505页云:(太祖皇帝)又谓张永德曰:“贼气骄,力战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请引兵乘高出为左翼,我引兵为右翼以击之。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永德从之,各将二千人进战。
⑩ 范学辉认为,何徽、樊爱能等历朝宿将带头溃逃与赵匡胤等青年军官的挺身而出,是后周军界新旧更替矛盾的反映。这无疑是富有卓见的,但或许还未考虑到除此二人以外,也有其他的历朝宿将奋勇杀敌,因此该矛盾或许尚需商榷。范学辉:《高平之战与赵匡胤的崛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