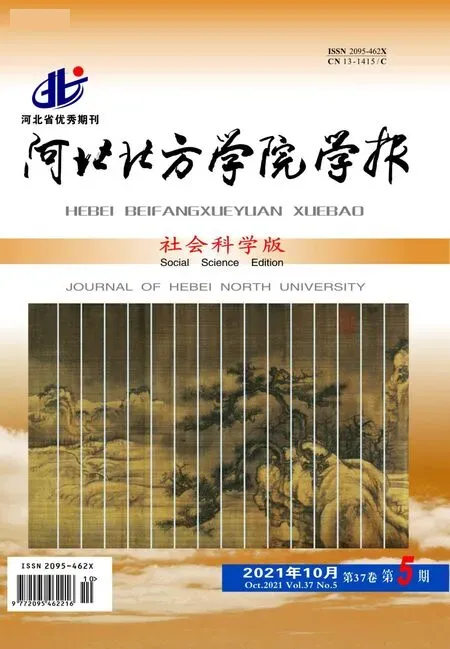浅析张说“天然壮丽”文学思想
李 秀 如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张说是初盛唐文学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历来受到学界瞩目。但后人对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文作品分类研究、与苏颋和张九龄等人的对比研究以及文学史地位与影响研究3个方面,对他的文学思想则关注较少,尤其对其“天然壮丽”这一文学主张未给予足够多的关注和论述。该文拟从“天然壮丽”的文学内涵出发,挖掘张说这一文学主张产生的主客观双重因素,并探析其在张说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和运用。
一、“天然壮丽”说的内涵
张说提出的“天然壮丽”文学思想值得关注,这一文学主张首见于《洛州张司马集序》一文:
“时复江莺迁树,陇雁出云,梦上京之台沼,想故山之风月,发言而宫商应,摇笔而绮绣飞。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灵仙变化,星汉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壮丽,綷云霞于玉楼。”[1]123
“天然”和“壮丽”是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诗歌美学范畴,但将两者连缀并举,张说是第一人。无论在张说的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中,“天然壮丽”都焕发出异于前代的新鲜色彩。
(一)崇尚“天然”
崇尚自然的至真之美由来已久,从道家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到《古诗十九首》的浑然天成,再到谢灵运“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清新风格,迨至初唐,追求天然文风几乎成了文坛共识。张说为文所崇尚的“天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文学观念,但在唐初政坛与文坛双重影响下,张说也赋予了“天然”文风全新的内涵。
“天然”的第一重内涵在于对自然之境的亲近与向往,这主要体现在张说的山水诗作中。张说的仕途可谓大起大落,他的山水佳作多成于被贬相岳和巴蜀期间。“常怀谢公咏,山水陶嘉月”,由于张说对谢灵运和谢朓的自然文风本就推崇备至,因此有不少学者将张说及聚集在其周围的一批诗人创作的山水诗看作是从二谢到王孟山水田园诗派之间不可或缺的一个过渡环节[2]。
“天然”的第二重内涵是感情抒发的纯粹真实。《洛州张司马集序》开篇即言:“夫言者志之所之……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张说的观点与《毛诗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3]相同,都认为文学作品创作的根源在于言志和缘情,而张说诗文发语天然的风格便根植于其内心对大唐盛世真挚饱满的热情。
“天然”的最后一重内涵在于追求超然物外的精神自由,这与张说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在《与凤阁舍人书》一文中,张说虚构了飞英子和灵风子两个可以御风而行的形象,文中他不仅追求肉体在自然界“翻飞而行,抟扶而上”和“簸芳万里,腾景千仞”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更企慕“无德色”和“无私心”的精神境界的自由,颇有庄子遗风。
(二)追求“壮丽”
“壮丽”,顾名思义为既“壮”且“丽”,两者表现出的美学特征似乎并不相同。《说文解字注》:“壮,大也”[4],后引申出强大有力之意,在张说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表现为磅礴的气势和雄劲的语言。同时,作为一位杰出的批评家,张说往往在对其他文人作品的评价中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5],张说将富嘉谟的文字比作万仞绝壁和万钧雷霆,高度赞扬了富文的雄壮气势。
“丽”,最初是偶对的意思,它作为文学审美范畴与汉赋的兴起关系密切。《文心雕龙·丽辞》有言:“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6]588,“丽”代表的是铺张恣肆的文风,是文辞的绮靡佳美和语言的巧妙精微。“壮丽”这一概念正式成为文艺美学范畴理应归功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归纳“八体”后称“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6]505,即“壮”与“丽”的结合是气势风骨与文采辞藻的水乳交融,是既文采斐然又气势壮大的审美趣味。
(三)嬗变革新
“天然”和“壮丽”这两个美学范畴虽然其源已久,但张说的文学主张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内涵,两者并举堪称是对盛唐诗歌美学最精当的概括。
张说推崇的“天然”不同于老子“见素抱朴”的朴素自然观,也不同于钟嵘所追求的“自然英旨”。首先,张说推崇自然,却不因此排斥声律或者否定辞藻的华美,这正是张说高于前人的地方。钟嵘的《诗品序》几乎对四声八病说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7],他认为声律论全然拘束限制了文章的自然之美。而张说却恰好相反,他指出“臣闻七声无主,律吕综其和,五彩无章,黼黻交其丽。是知气有壹郁,非巧辞莫之通;行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1]122。他认为声律可产生音调的和谐,构成文章的音乐美;华丽的辞藻可以构成文章的形式美;而“天然”追求的则是自由灵动的意境美,这3者不仅不会彼此矛盾,反而可以相辅相成,最终达到“完美”的境界。这正是对前人全面否定格律音韵和华美辞章的一次反拨。其次,张说对于“天然”文风的追求并不是以放弃艺术构思和技巧为代价的。相反,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级的艺术形式,是通过巧妙构思与提炼雕琢后形成的看似佳作天成、实则字字如金的艺术效果,这也是盛唐诗坛的整体审美理想。在《唐故凉州长史元君石柱铭并序》中,张说用“灵台云秀,绳墨之宰无施;雅韵天成,金石之师何力”[1]203赞扬元仁惠妙笔生花的才气,褒扬的正是作者能够炉火纯青地驾驭文字,乃至达到浑然天成和不着痕迹的艺术效果的高超创作手法。最后,张说的“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壮丽,綷云霞于玉楼”提出了将自然浑成与人力雕琢相结合的“天然壮丽”审美观。张说意在用《韶》《武》及自然界的云霞来指代感兴而发的天然之语,将钟鼓之音与雕梁画栋的玉楼比作构思精微的壮丽文辞,既肯定了发语天然的必要性,又说明了文采辞章修饰作用的不可或缺,昭示了盛唐文坛雄健清新而又兴象超妙的基本审美特点。“张说在唐诗史上的主要贡献尚不在其创作本身,而是在于其独特的地位、影响及其对众多士人的提拔、对艺术理想的指导。”[8]从该角度来讲,称张说为盛唐文坛的开基者和引路人毫不为过。
二、“天然壮丽”说的产生背景
“天然壮丽”说既是六朝隋唐文学思想历时性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受到张说个人经历与体悟的催化。
(一)革除六朝文弊与融汇南北文风
张说生活在初唐国力日盛的时代。当时,一方面,六朝绮靡文风的影响仍未消散,初唐文人追求文辞的秾艳仍是常态;另一方面,一批文人希望以复古革除文坛之弊,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也提出南北诗文取长补短的变革主张。
初唐之际,上层文坛仍有“风流初不废齐梁”的文风,而张说所倡导的“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此。当时,许多著名的文坛大家如陈子昂和四杰等人都致力于革除六朝文弊,一些全面否定六朝的偏激观念并没有正视六朝文风给唐代文人带来的正面影响。复归汉魏古文的确使盛唐诗文具有了刚劲风骨,但两晋玄风赋予了唐诗空灵飘逸的气质,宋齐声病衍生出唐诗格律和谐的音乐美,梁陈宫体诗也给予了唐诗含蕴细腻的风格,一味否定六朝文学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文学演进的客观规律。从该角度来看,陈子昂虽有“以风雅革浮侈”之功,但不可否认他有轻视形式技巧和全面否定六朝的倾向。魏征就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出过著名的论断:“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9]其实早在杨隋一统之际,要求南北文风“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声音就已显露,这种“取南朝之华美与北朝之意理,从而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10]的观念由来已久,并作为文坛共识影响着张说的文学观。
张说诗文“鼓天下之动”的气势是以盛唐建国百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国力昌盛作为强大的根柢的。大唐自建国到开元前期,国家在稳定的政治格局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期间虽有几次宫廷变乱,但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没有造成破坏。尤其是开元前期,君明臣贤,河清海晏,唐朝逐渐走向全盛,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蓬勃向上的积极精神。张说作为执掌文坛的一代文宗与出将入相的士族名臣,自然更为强盛的国力所鼓舞,其诗作更为豪情满怀、壮志凌云且气势磅礴。
(二)三起三落的仕途经历和朴素自然的美学体悟
张说一生虽历任要职,三居相位,但也有两度入蜀、钦州流放、留守东都和贬入相岳的落拓沉沦,这都对张说创作风格及文学思想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朝为官期间,张说创作了大量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作与赞颂公文,这些作品多骈辞丽句、声调优美且辞藻繁复,颇有秾艳靡丽的六朝格调。而去国久远时,张说又将满腔诗情寄于山水,在岭南及蜀中创作的诗文大多自然清丽与天真可爱,戍守边关时边塞风光的感染和战场厮杀的经历又带来字里行间的磅礴气势和刚劲风骨。张说无疑擅长对外物的变化和自身的遭际生发出情感的反应,并将其用巧妙的构思与流利的语言置诸笔端。可见,张说所追求的雕饰到极致而又不留痕迹的“天然”远不是思虑精苦的刀刻斧凿所能达到的,而是依赖于个人敏锐独到的感知力和超然神化的艺术天分。
在唐代“三教合流”的宗教背景下,张说对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有吸收涉猎,这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和文艺美学的思想渊薮。在《词标文苑科册》及《上东宫请讲学启》等多篇公文中,张说都强调了儒教礼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和“平和典雅”的风度对其文学审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在《蒲津桥赞》中极言“心平则应谐百神矣,气和则感生万物矣”[1]90的“心平气和”的创作方法。佛家和道家对张说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其对“天然”的审美追求。佛教思想传入中土后,为了避免深奥的义理和艰涩的文字造成传播障碍,对佛经的翻译多追求通俗易懂。到了唐代,“以心传心”的方式更使得释家思想进入通达流畅的日常境界。翻译经文的经历和与僧人的交流使得张说的文风不自觉地靠近佛教朴素自然的美学要求。道家提倡清净无为,张说在《与郑驸马书》中也有对道家思想的探讨与论述:“复命近於无有,知常其有知见耶……神不可穷而穷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为我用。”[1]128“神合”和“我用”的结合正是“天然”文学理论的生动写照。
三、“天然壮丽”说的文本呈现
“天然”境界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对自然风光的书写和对自然之境的刻画,而“壮丽”一词最初是用来形容宫室的宏伟壮大,因此更富含人为的意味。在张说的诗文作品尤其是应制诗中,这一主张最直接地表现为自然要素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
(一)自然风光与城市景观结合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以张说为代表的应制诗人群体在“天人合一”的指导思想下,在诗作中将坚硬的人工建筑与柔软的自然山水有机地组合在一起[11]。从作品内容来看,“天然壮丽”其本质就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美。
张说遭贬期间创作了很多描写自然之境的诗,这些山水诗格调清新,语言洗练,是体现“天然”文论观的绝佳例证。然而,真正展现“天然壮丽”整体风貌的文学作品非应制宴饮诗莫属,如《三月三日诏宴定昆池宫庄赋得筵字》:
凤凰楼下对天泉,鹦鹉洲中匝管弦。
旧识平阳佳丽地,今逢上巳盛明年。
舟将水动千寻日,幕共林横两岸烟。
不降玉人观禊饮,谁令醉舞拂宾筵[1]34。
华丽庄严的凤凰楼下是汩汩流淌的清澈泉水,绿意氤氲的鹦鹉洲中飘扬着丝竹管弦之音,美景环绕之下是载歌载舞不醉不休的酒筵歌席,人文之美在自然之境中摇曳生姿,是“天然”与“壮丽”的完美融合。《奉和圣制温汤对雪应制》《清明日诏宴宁王山池赋得飞字》和《晦日诏宴永穆公主亭子赋得流字》等应制宴饮诗大都以同样的笔法勾勒出自然与人文物我不分的“天然壮丽”的和谐景观。
(二)吟咏情性与记述事功并举
由于身在台阁,张说的诗文多表现出歌功颂德的功能,但其诗作并非是徒有格套的空文,而是饱含充沛的情感。事实上,张说的观点与钟嵘讲求的“直寻”是一致的,都认为诗歌应是“志之所之”和“吟咏情性”的载体。
在宾朋欢聚畅饮时,张说有“远山片云,隔层城而助兴;繁莺芳树,绕高台而共乐”(《南省就窦尚书山亭寻花柳宴序》)的欢欣;在绝美佳人英年早逝时,他有“天何以罚?神其忍之……此所以哀中之又哀也”(《延州豆卢使君万泉县主薛氏神道碑》)的遗恨;在面对战与和的矛盾时,他又有“臣闻小忿不忍,延起大患;小罪不宽,迫成大祸”(《并州论边事表》)的恳切。由此可见,真实生动的情感抒发是其“天然”文风形成的前提。
除了表情达意以外,张说还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应制诗与公牍文,其中不乏讲求社会功用的壮美之词,其表意抒情与润色鸿业并重的文学主张在《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中已有论述:“吟咏性情,记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人谓之文伯。”[1]182而《大唐封祀坛颂》恰是践行这一文学主张的杰出作品:
孟冬仲旬,乘舆乃出,千旗云引,万戟林行,霍濩磷烂,飞焰扬精,原野为之震动,草木为之风生。……万方纵观,千里如堵,城邑连欢,邱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乐过以泣,不图蒿里之魂,复见乾封之事。尧云往,舜日还,神华灵郁,烂漫乎穹壤之间。……铁马金镞,介胄如雪,旗帜如火,远匝于清禁之野[1]82。
文中铺绘了泰山封禅的宏大场面,蕴含着一代贤相目睹此情此景后的壮怀激情与自豪之感。其中“垂白之老,乐过以泣,不图蒿里之魂,复见乾封之事”一句更是形象地展示了强盛国力带给普通民众的慰藉与振奋。张说的诗作不仅彰显了颂体文“美盛德之形容”的赞颂功能,更以饱满的热情和激昂的文风勾勒出大唐国富兵强的盛世气象。
(三)言之有物与属词丰美兼顾
陆双祖评价张说的作品“属词丰美与风骨气势同兴,典则雅正与韵味无穷齐具,质朴适用与境界宏阔共存”[12],体现了张说在创作中对兼被文质的艺术效果的追求。如其边塞名篇《幽州夜饮》写道:“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首两句以景切入,奇拔壮丽;三四句饱蘸深情;五六句慷慨雄壮,显出苍凉悲音;末两句则托意深婉,又不失雅正之体。清人沈德潜云:“此种结后,唯老杜有之。远臣宜作是想。”[13]
全诗用浅率直接的语言表情达意,心怀庙堂之念溢于言表。除此作外,《送赵二尚书彦昭北伐》《幽州别阴长河行先》和《巡边在河北作》等边塞诗或想象边境厮杀的壮阔场面,或书写漂泊迟暮的边塞愁苦,或表达豪迈情调与忠勇之气,饱含深情又慷慨壮丽,颇显苍劲古意。
与前代颂文不同,即使是张说所作的一些润色王业的歌功颂德之作,也少有空泛浮靡的粉饰太平。如《开元正历握乾符颂》中:“伏惟圣上,聪明文思,道德之具也;豁达大度,皇帝之体也;艺总六经,汗光之学也;文通三变,魏祖之才也;缘情定制,五礼之本也;洞音度曲,六乐之宗也;神于孤失,黄轩之成也;圣于翰墨,苍顿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子孙众多,周文之福也”[1]78,便从文才、德行、学识和艺术等方面颂扬了玄宗的品质,并论证了其成为君主的合理性,诗作虽意在颂圣,但文中既有饱含深情的抒情言志,又不乏旁征博引的文辞才情;既有宏伟壮阔的雄健气势,又不乏中和典雅的文质彬彬。
综上所述,张说将“天然”与“壮丽”两种审美范畴连缀并举,既强调自然的神韵、天然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又注重文采的藻饰、音律的和谐和气势的壮大。“天然壮丽”的文学追求在继承前人优秀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又结合当时的文坛风气与改良需要进行了发挥与完善,体现了初唐渐盛时期文风转变的典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