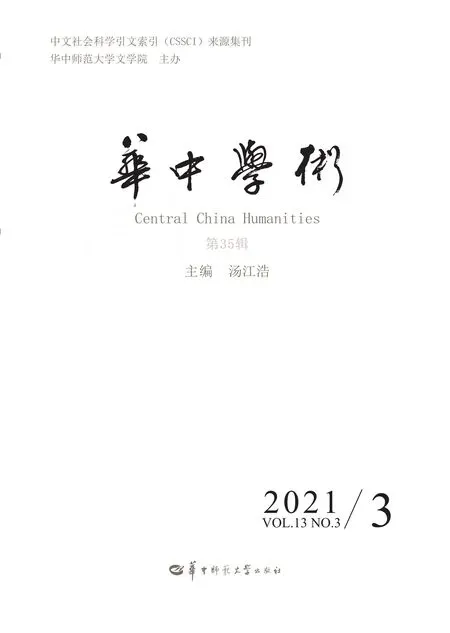论王家新的创造性译诗观
方 舟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2)
王家新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诗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外国诗歌译介工作,与北岛、西川、杨炼、臧棣、黄灿然等一道形成了90年代诗人译者群,承续了中国新诗史上诗人译诗的传统。王家新在三十余年的诗歌翻译生涯中,陆续翻译了策兰、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洛尔迦、布罗茨基、奥登等诗人的作品,并发表了不少理论文章,阐述自己对诗歌翻译中诸多问题的看法,涉及诗歌翻译的目的、翻译修辞、翻译语言、译诗的诗性、译诗与原语诗歌的关系、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等内容,而“创造性翻译”便是他提出的译诗观。作为一位德语、俄语水平无法直接而熟练地进行诗歌翻译的译者,王家新大多是依据原作并参看其英译版进行的,因此,如何最大限度保留原语文本的面貌与精神,译出原作中“诗”的实质是其最大的难题,这也是“创造性翻译”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王家新的创造性译诗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围绕原作的内核,在翻译中寻找、译出其固有的诗性,抵达原作的精神深处;二是对诗之语言的刷新,通过翻译为汉语诗歌带来语言更新和诗的新质。创造性译诗观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也存在着某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以王家新有关诗歌翻译的文章为研究对象,结合其诗歌翻译实践,梳理、研究其创造性翻译观,并进行理性反思。
一、对“诗”的寻找与翻译
王家新对创造性翻译的理解为:“‘创造性翻译’是在‘忠实’‘精确’和‘创造性’之间把握一种张力。”[1]关于翻译的忠实,雪莱很早便指出:“想要把诗人的创作复制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就好比把一朵紫罗兰扔进坩埚,还想发现原先色泽和香味的法则,都是痴人说梦。”[2]忠实作为翻译曾经的基础信条之一,在20世纪中叶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遭到“文化研究”派翻译批评的抨击,由此受到翻译界的质疑,甚至逐渐失去了其地位;而后出现的“译者中心”论也对忠实原则进行了批判。关于翻译的精确,王家新认为“不仅体现在词语、意象和细节上,也体现在语感、语气和音质上”[3],至于创造性则是翻译本身生命力的一种体现,因此在精确与创造性之间存在的张力,便是在不违背忠实的原则下,为译作赋予一定的生命,还原诗歌的神韵,在翻译中抵达原作的精髓。在王家新心中,诗歌翻译是独立于诗人的存在:“是你在翻译吗?是,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看,是诗在翻译它自己。是诗在翻译它的每一行。”[4]这种带有神秘的诗学观念强调的是“诗”的重要性,所以寻找“诗”,让“诗”现身是诗歌翻译的灵魂,也是王家新创造性翻译诗学观的核心。诗歌中“诗”的部分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因此有了弗罗斯特那句著名的“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如何翻译不可言传的“诗”就成为诗歌翻译中永恒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王家新诗人译者的身份便体现出其优越性。关于诗人译诗的问题,朱湘曾经提出:“惟有诗人才能了解诗人,惟有诗人才能解释诗人。他不单应该译诗,并且只有他才能译诗。”[5]由此看来,诗人译者能够凭借自身对于诗的理解,透过文字辨识其中具有本质意味的东西,即剥开表象,找到“诗”的部分。
“‘不同的——却又正是相同的’,这也正是创造性翻译给我们带来的诗歌。”[6]这是王家新对创造性诗歌翻译的评价,此处的“不同”在于语言间固有的差异所带来的阅读上的不同体验,“相同”则在于这种差异并没有磨灭作品本身“诗”的元素。这种创造性翻译的理念贯穿在王家新的翻译批评与实践中。雷克思洛斯在翻译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将原诗并不存在的“诸葛亮”放进翻译,并加入了“你”的人称代词,对此王家新认为这是“从原诗中产生了另一首诗”;雷克思洛斯大胆的翻译,在他看来“体现了一种深入本质、抓取原作精华和生命的方式”[7]。王家新并非没有认识到雷克思洛斯的翻译与原诗之间的差异,但是他宁愿将这种差异看作“翻译的发现”,即在翻译中辨认诗歌,找到作品中真正的“诗”的那一部分。当他得知译者王嘎对帕斯捷尔纳克《起航》的翻译“盐从天上滴落,絮语间/隐约传来机轮的轰响”是参考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时,他认为这是“神来之笔”,并直呼“这才是一个译者面对原文所做出的创造性反应”[8]。当他读到保罗·策兰所翻译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认为那种打破常规的翻译是对莎士比亚的重写,是“一种新的既忠实于原作而又无法为原作取代的诗”[9]。莎士比亚诗歌永恒的主题是生、死、爱等,策兰的翻译虽带有其个人强烈的晚期风格,但并未改变原作的精神内核,只不过是以策兰独有的、带有痛感的方式来表达莎士比亚的经典主题。也正因此,策兰对莎士比亚诗歌的翻译既忠于原作,又是原作所无法替代的。
如何寻找原作中的“诗”,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个挑战。王家新的译文大都参考了多个英译本,也在这种多方位考察、辨认原作的过程中,他的译作对原作精神面貌的还原度极高。王家新谈到对茨维塔耶娃《新年问候》的翻译时指出:“依据科斯曼的全译文,也参照了布罗茨基的部分英译及解读,重新译出了全诗。”[10]茨维塔耶娃的《新年问候》充满罕见的句式和节奏变换,因此带来了相当程度的阅读理解的困难。作为一名将生命奉献给诗歌的作家,完成这样高难度的作品也是一种献身。王家新在翻译时对原作怀有足够的敬畏心,为了对茨维塔耶娃的诗心进行还原,他努力保留原作的词语、句式等障碍。在完成这首诗的翻译后,王家新坦言:“仿佛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磨难,但又充满感激,甚至有点‘大功告成’之感。”[11]这样的翻译与其说是对原作精神内核的尊重,不如说是在贴合原作的内在灵魂,并赋予译文同样独立的诗性和生命力,而王家新所经历的受难般的翻译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茨维塔耶娃“献身”精神的还原。王家新在解读海涛翻译的俄罗斯诗歌时指出,通过英译本转译而来的作品是“借助英译本对心灵密码的破译”,并称:“经过这样出色的‘转译’,俄罗斯诗歌不仅没有‘丢失’,而且焕发了更多的新意。”[12]当王家新发现自己根据企鹅版詹姆斯·格林所转译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你们夺去了》,与海涛根据克拉伦斯·布朗和诗人默温的合译本所转译的同一首《农鞋大的土地》存在较大差异时,他认为:“这就是翻译所带来的丰饶和奇妙。”[13]从王家新的评判标准来看,不同版本的译本并无孰好孰坏之分,区别只是各自侧重点不一样,所抓住的诗的精髓不同。
王家新的创造性翻译观是在忠实与创造性之间寻找平衡:忠实的是作品的神韵、精神内核,即“诗”的部分;而创造性则是译者基于自身文化和语言修养,在寻求“诗”的过程中与原作者诗心相通,在得到原作“授权”的前提下,创造性完成与原作相匹配的作品。
二、刷新语言与诗
王家新从20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开始,便致力于从辨认“诗”的角度思考汉语自身问题,以诗创作担当汉语更新、发展的责任。90年代初,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发展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80年代朦胧诗歌那种政治抒情已经失去了表达能力,后朦胧诗发展也举步维艰,王家新开始诗歌翻译。他期待通过外国诗歌翻译,找到诗艺突破口,推动中国当代诗艺的发展,同时为汉语言诗歌带来新质。他曾经提出:“翻译的目的绝不止于‘忠实’地复制原作,它还必须以自身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为诗和语言的刷新而工作。”[14]因此,创造性翻译之于王家新,既是对“诗”的寻找,亦是对诗歌语言的刷新。
王佐良在《谈诗人译诗》中写道:“译者不仅是一个反叛者,而且是一个颠覆者。”[15]诗人译者在语言上往往能带来颠覆性的效果。关于郭沫若诗的语言,王家新认为其提供了“在中国诗中从未出现过的词汇、意象、语言节奏”;对于穆旦诗的语言,他认为“发掘了语言本身的潜能,也增大了诗的艺术难度和容量”,使得“汉语诗歌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16]。王家新承续了前人所开辟的语言探索道路,坚持用艰涩的表达来呈现原作,通过翻译探测汉语的诗性边界,而他的创作与翻译也的确为汉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语汇,为汉语带来了新质与生机。但在长时间的翻译工作后,其自身诗歌创作也容易显现出“翻译体”的特征,而这也是不少批评家对王家新的指责。对此王家新阐释了自己的看法:“正是这种带有异质性质的‘翻译腔’‘翻译体’,在悄悄唤醒和恢复着人民对诗和语言的感觉。”[17]在王家新看来,“翻译体”三个字不是贬低或者嘲讽,而是推动语言革新的方式:“‘翻译体’又有什么不好?多少年来正是它在拓展并更新着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而‘接轨’也并非为了成为别人的附庸。”[18]通过翻译更新现代汉语的翻译观,与鲁迅的翻译理念不谋而合:“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19]鲁迅一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致力于通过翻译来输入新的内容和新的表现法,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准则,强调“译的‘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的‘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20]。王家新在关于翻译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准则,借此警醒自己尽量规避那种为了合乎汉语规范而使语句变得通顺、流畅的翻译。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认为文学“对母语进行分解或破坏”,并且“通过句法的创造在语言中构建一种新的语言”[21]。这种看法强调了文学对语言的分解和再创造的作用,而诗的语言是一种追求破除既有语法的陌生化语言,每个诗人生存于约定俗成的日常话语之中,如何实现语言突破以走出惯用语言链呢?王家新认为翻译是最好的途径。本雅明提出“纯语言”概念,即那种使语言成为语言的“元语言”,它联系着译作和原作,“部分地隐含在原作中,在翻译的过程中,在不同语言的相互映照中,我们才得以窥见它”[22],译者的使命是使之萌芽、显现、生长。在这个意义上,译作是为了语言的成长,成为语言成长的组成部分,促使语言的更新,“以至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它承担起了一种特殊使命,这一使命就是密切注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并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23]。文学翻译是一种创作,所以译文必须具有文学性;翻译的特殊使命在于语言,就是注视原作语言,辨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承担自身语言的降生,也就是借原作语言创造出自己新的语言。王家新由此说:“在本雅明那里,翻译便成为语言的自我更新、自我救赎的最终归属。我本人十分认同这样的翻译观和语言观。”[24]他坚信翻译是外语和汉语之间的桥梁,通过翻译引进异质的语言,破除母语的结构、逻辑。他提道:“中国新诗史上一些优秀的诗人译者,从事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译出几首好诗,在根本上,乃是为了语言的拓展、变革和新生。”[25]当王家新读到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诗作《梦游人谣》中的“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时,他发出感叹:“这是对声音奥秘的进入,是用洛尔迦西班牙谣曲的神秘韵律来重新发明汉语。”[26]“重新发明汉语”是作为一名汉语诗人兼翻译家对语言的极高评价。翻译是为了语言的更新,语言成为翻译的重要目的,这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哲学基础上的翻译观、语言观。在王佐良看来:“译诗的时候,需要译者有能力找到一种纯净的、透明的然而又是活的本质语言——这又只有诗人最为擅长,因此就从语言来说,也需要诗人译诗。”[27]王佐良的观点体现出诗人译诗的使命,即诗人译者不应只满足于对具体作品的翻译,而是具备一种在翻译中刷新汉语言的意识与能力。
真正的诗的问题,体现在诗创作的内外部各种关系上,诸如诗人的态度、感觉与表达能力,诗人看待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诗人与其创作的文本的关系,诗歌创作的功能等等;诗歌有多复杂,诗歌翻译就有多复杂。王家新对翻译与语言的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与理解,其核心观点是诗歌翻译可以借助域外语言以质疑、破除母语中那些抑制表现力的惯用语言,重组语词,丰富语汇系统,简言之,就是刷新既有的语言系统。王家新认为翻译在文学中承担了一种使命,“这一使命就是密切注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并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28]。在他看来,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形式,所以译文必须具有文学性;认为翻译的特殊使命在于语言,就是注视原作语言,辨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承担自身语言的降生,也就是借原作语言创造出自己新的语言。“翻译家们走在这条道路上,那些以变革和刷新语言为己任的诗人也走在同样的道路上。”[29]王家新自己也走在这样的路上,诗人、译者和学者的身份,决定了他在翻译中进行理论思考,在翻译中探索语言更新与诗意更新的路径。
三、创造性翻译的反思
王家新的创造性翻译观,基于当代诗歌翻译问题,建构出原作与译作之诗性转换机制,回答了译作的诗性创造问题,为当代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思路,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然而辩证地看,这种翻译观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创造性翻译在理论上与“转译”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创造性翻译观强调的是对“诗”的忠实,也就是在“诗”的意义上忠于原作,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忠于“诗”的意义上增删文字,目的是为了“赋予原作以生命”[30],译出原作的诗意和生命力,这也没有问题,而且它们确实是诗歌翻译最应遵守的原则。但是,王家新的翻译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受到外语水平的限制,他的俄语、德语诗歌翻译多是参照英译本进行的。在他看来,“英文世界有许多优秀的俄罗斯诗歌译者,他们不仅更贴近原文,对原文有着较精确、透彻的理解(说实话,正是因为读了其英译,我在一些从俄语中‘直译’过来的译文中发现了比比皆是的理解上的‘硬伤’)……”[31]这段话值得商榷。首先,在俄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英译文“更贴近原文,对原文有着较精确、透彻的理解”?其次,既然俄语水平有限,那么何以认为从俄语直译过来的版本存在“比比皆是的理解上的‘硬伤’”呢?由此不难推断,在王家新的观念中,有关俄语、德语诗歌等的“创造性翻译”所忠于的对象,其实是他所参考的英译本,而非俄语或德语原文。从世界诗歌交往的角度看,转译有存在的价值与理由,可以在互文性意义上理解为不同语种诗人之间的互文性交往与对话;而且,强调转译中以“诗”为诉求的创造性翻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译诗的目的是“诗”,是创造出新的诗歌作品。但是,这种创造性转译出的作品,严格意义上讲,就不是译本所依据的底本之底本诗歌了。换言之,王家新依据英译本所译的德语、俄语诗歌就不能称为德语诗人的诗歌、俄语诗人的诗歌了。这个应该分清楚。所以,创造性翻译观对于转译而来的诗歌而言,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怀疑[32]。
第二,王家新以创造性翻译观作为诗歌翻译的评价标准,导致他的评判有时过于主观,难免出现矛盾。他关于卞之琳和穆旦各自翻译奥登的《战时》一诗的评述,就存在标准不统一的地方。“Far from the heart of culture he was used”是原文诗句,穆旦将之译为“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卞之琳的译文是“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穆旦的翻译主要是直译,“他被使用”读起来有些不知所云;而卞之琳翻译为“他用命”则属于意译,更贴近原文精神。王家新对卞之琳这一翻译不以为然——“且不说‘用命’‘场所’这类过于庄重的译语对原文的偏离”[33]——显然其评判标准发生了偏离,没有看到卞之琳在此处的“创造性”处理,而近乎偏执地对他所特别热爱的诗人穆旦的翻译大加夸赞。穆旦将“may also be men”译为“也能有人烟”,对此王家新称赞为“平添了汉语本身的诗意和形象感”[34];卞之琳将“daughter”译为“女娃”,王家新则认为,“无端地拉开了原诗中情感的距离,使原诗中那个面对无名士兵之死内心涌动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好为人师的老夫子”[35]。显然,穆旦所使用的“人烟”一词,为原作带来了中国诗词的意境,拉近了原诗与汉语的距离,属于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用语,与卞之琳的“女娃”具有同样的功能。而王家新的评论加入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其评述标准不统一,或者说与他自己的诗学观相悖。创造性翻译中的“忠实”追求译文与原作精神的契合度,以至于在评说相关翻译问题时,他主张为传达原作精神可以不拘泥于格律、韵脚等形式,认为一味追求形式贴合的翻译过于刻板,缺乏语言创造性。在评论卞之琳所译奥登作品时,他说:“他刻意追求与原诗语言格律形式上的对应,有时也不免陷入了翻译的误区。”[36]在评价穆旦所译济慈的《蝈蝈和蟋蟀》一诗时,关于译文中所丢失的节奏和韵律,王家新认为:“穆旦就这样忠实地传达原作的诗质和精神,而又不拘泥于原文,更没有掉进‘直译的陷阱’。”[37]并指出其对原作精神的高度把握和创造性翻译,是对译文形式上的某种“补偿”。叶维廉在翻译博尔赫斯的《渥品尼亚的士兵》时,将原作十四行诗的形式改变为自由式,在王家新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目的是摆脱原诗的形式框架而把其诗感呈现出来”[38]。先不论那些译文是否完全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和诗质,单就诗歌形式来看,形式对应着诗质与精神,而十四行诗是一种特殊的诗歌体,没有相应的形式就不是十四行诗;或者说对十四行诗而言形式就是内容,没有形式就没有所谓的精神和诗质了。翻译只求所谓的精神、诗质,舍弃形式也就舍弃了精神和诗质了。许渊冲曾经提出:“如果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忠实于原文的风格是一致的,那译文就应该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如果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忠实于原文的风格之间有矛盾,那就可以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39]即内容与形式出现冲突时,可以舍形式而重内容,但一般情况下还是应当兼顾二者。如果笼统地将译文对原作形式的随意改变看作一种创造性行为,显然是不合适的,它消解了语言的表达力。正是语言自身蕴含的强大潜力使其能够胜任不同形式,译者应当充分挖掘语言的包罗性来适应不同诗歌体裁与形式,这也是对语言诗性边界的一种探测。
有学者曾质疑王家新所提倡的“创造性翻译”和“转译”理论,认为“王先生的‘创造性’诗歌翻译理论,只会把对外国诗歌和外国诗人的研究变成对译者的研究”;关于转译问题,则说“想翻译曼德尔施塔姆,首先就要学俄文,而且要学好”;同时指出王家新“研究问题却总是脱离诗歌形式的分析”[40]。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质疑?首先,王家新将翻译视作再创造行为,强调译文对原作精神的传达,对“诗”的传达,抓住了诗歌翻译的目的与特征,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翻译的本质。相比于字句的准确性,对“诗”的创造性把握,无疑更科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创造性翻译的前提是不能脱离原作,翻译不是脱离原作的改写,而是以原作为底本的更深层次的把握与转换。这就需要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存在精神上的默契,且译者应具有极强的原文阅读理解力。其次,转译有利有弊,其优点正如王家新所阐述的,有些英译者对原诗有较为透彻的理解,参考多个译本,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原诗的精神内核,有助于在“诗”的层面“抵达”原诗。不足之处则在于,转译容易丢失原诗的语义信息,丢失原诗所表达的特别的诗意。王家新曾经说:“英美译者尤其是诗人译者在翻译观念上更大胆,也更看重在英文中重写原诗的可能性。”[41]那么根据英美译者这种“重写原诗”的版本所转译的作品,跟原作相比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它虽然有自己的诗意,但还是原来那首诗吗?王家新转译本的某些瑕疵显然与此有关。再次,关于韵脚、格律等诗歌形式的翻译,一方面,过于追求不同语种之间完全对等的形式转换,显然是不现实的,生硬的形式转换会给人生硬之感,也无助于“诗”的营造与传达;另一方面,以诗译诗,如果完全脱离原文的节奏与形式,只追求对精神的传达,那更不可取,因为很多时候诗歌的内容与诗质是通过韵脚的切换以及音节的轻重等来表达的。在郑振铎看来:“诗的音韵,就是人的内部情绪之表现,韵律之与情绪实有相密接,相依傍而绝不可分之势。如果诗的韵律已完全变而为别一种,诗的情绪又如何能单独的照原样的转移过去呢?”[42]由此可见,诗的形式绝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形式的完整呈现是对诗歌整体的把握,没有一定的形式也就失去了与之相关的内容与情绪,相应地也就没有“诗”了。
注释:
[1] 王家新:《“创造性翻译”理论和教学实践初探》,《写作》2018年第6期,第6~9页。
[2] 转引自包慧怡:《巴别塔的诅咒——诗歌翻译中的解谜与成谜》,《上海文化》2010年第3期,第69~75页。
[3] 王家新:《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第129~136页。
[4] 王家新:《诗学笔记》,《黄昏或黎明的诗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5] 朱湘:《说译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10页。
[6] 王家新:《一个译者和他的北方船》,《诗潮》2015年第4期,第115~119页。
[7] 王家新:《翻译:重新开始的诗——以雷克思洛斯对苏轼的翻译为例》,《写作》2021年第2期,第21~29页。
[8] 王家新:《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第129~136页。
[9] 王家新:《从“晚期风格”往回看——保罗·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第34~42页。
[10] 王家新:《茨维塔耶娃及其翻译》,《黄昏或黎明的诗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55页。
[11] 王家新:《为语言服务,为爱服务》,《黄昏或黎明的诗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
[12] 王家新:《一个译者和他的“北方船”》,《诗潮》2015年第4期,第115~119页。
[13] 王家新:《一个译者和他的“北方船”》,《诗潮》2015年第4期,第115~119页。
[14] 王家新:《语言激流对我们的冲刷——夏尔诗歌及其翻译》,《翻译的辨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350页。
[15] 王佐良:《谈诗人译诗》,《论诗的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页。
[16] 以上均出自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第24~34页。
[17] 王家新:《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第129~136页。
[18] 王家新:《取道斯德哥尔摩》,《坐矮板凳的天使》,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19] 鲁迅:《论翻译——答J.K.论翻译》,《文学月报》1932年6月第1卷第一号。
[20] 鲁迅:《几条顺的翻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21] [法]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22] 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第24~34页。
[23] 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第24~34页。
[24] 王家新:《翻译与诗建设》,见《黄昏或黎明的诗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25]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第24~34页
[26]王家新:《“新的转机”——1970年代前后“创造之手的传递”和新诗潮的兴起》,《名作欣赏》2020年第7期,第5~11页。
[27] 王佐良:《另一面镜子:英美人怎样译外国诗》,《论诗的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5页。
[28]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第24~34页。
[29] 王家新:《翻译与诗建设》,《黄昏或黎明的诗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83页。
[30] 王家新:《“创造性翻译”理论和教学实践初探》,《写作》2018年第6期,第5~10页。
[31] 王家新:《茨维塔耶娃及其翻译》,《黄昏或黎明的诗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53~154页。
[32] 2019年,王家新与汪剑钊之间关于俄语诗歌翻译之争,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论争。王家新是在“更高的忠实”意义上,以“诗”为翻译的目的;汪剑钊强调的则是俄语诗歌翻译就应该以俄语诗歌为底本,不能偏离俄语诗歌的固有语义和诗意。他们各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不同,谈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无法达成共识。他们争论的本是诗歌翻译中很重要的现象,但是彼此只是隔空喊话,没有直接对话,且太多意气用事,相互讥讽,问题没有真正展开。这是很遗憾的事。
[33] 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翻译的辨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80页。
[34] 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翻译的辨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77页。
[35] 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翻译的辨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80页。
[36] 王家新:《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第100~118页。
[37] 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翻译的辨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75页。
[38] 王家新:《从众树歌唱看叶维廉的翻译诗学》,《翻译的辨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130页。
[39] 许渊冲:《忠实与通顺》,《翻译的艺术(论文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21页。
[40] 丁鲁:《说说王家新先生的“翻译诗学”》,《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5期,第23~34页。
[41] 王家新:《一个译者和他的“北方船”》,《诗潮》2015年第4期,第115~119页。
[42] 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1921年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