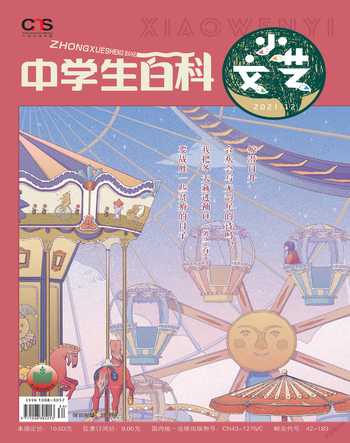鲸潜日升
苏思蓓
暑假前最后一天傍晚,程小童被爷爷黑着脸从班主任办公室揪回家。起因是在极限运动讲座上,他当着全市听课老师的面指出了徐老师的错误,说那号称自由潜水到202米深的视频不过是个笑话。
一路上爷爷痛心疾首地骂骂咧咧,程小童始终垂首不语,进了门洞才耐不住回嘴。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交锋,直到爷爷抖着手转开家里的防盗门,程小童看到那个正从沙发上站起身的男人,连珠炮样的话语突然全部哽在喉咙。
他已经很久没见过程子建了,久到他无法分辨与冬天相比,对方的形容是否也随着时间有所推移。深褐色的皮肤像在烈日下曝晒着的古铜,半袖下隐约可见大臂结实的肌肉。不知怎地,程小童一下想到被衣袖掩盖的文身,一头灰蓝色的鲸鱼,尾朝上,头向下,意欲循着手臂下潜,到深海去。
爷爷指着程小童,历数他这学期犯下的无数宗罪,脸上纵横的每一寸皱纹都跳跃着愤怒。程小童没敢看程子建,等爷爷的嗓子嘶哑到快支撑不住,而右手高高举起的时候,他灵巧地朝沙发后一闪一蹲,准备使出杀手锏喊娘。
没想到,那只手竟被程子建挡住了。
程子建对他说:“收拾下吧,跟我去北岛。”
这时程小童才确信他没变,话依旧少,仿佛多说一字就会散财千金。他声音沙哑,微微皱着眉,低垂的眉眼藏不住疲惫。
北岛是陈丽莎最后一次出海时驶离的地方。船只最后的定位出现在澜海中央,她再也不曾回返。其后程子建辗转寻她下落,无果,便只身去了北岛,似狠了心要在这片陌生的土地扎下根来。
十年前陈丽莎失踪时,程小童只四岁。之后的记忆里,母亲这个本该满盈温情的词语,于他只残余模糊的轮廓。程小童对她的情感复杂而微妙,陌生与亲近、甜蜜和酸楚杂糅其中,还有好奇。爷爷奶奶曾瞒他说陈丽莎生过大病,奔天上成了颗星,程子建则语焉不详,程小童只得求助于搜索引擎,反复借网络爬虫的触手在汪洋中抓取信息,终于将真相拼凑出大概。
二十年前学者斯蒂芬发现,18世纪初全球有二十五万头蓝鲸,不过三个世纪的工夫便被屠戮到只剩五千。他呼吁人们重视保护,阐明这会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怎样的危害,却没激起半点水花。斯蒂芬愤而从研究所辞职,成立了旨在保护濒危海洋生物的组织“海洋保卫者”。陈丽莎也是其中一员,十年前本是例行出海,不承想出了意外。
程小童也在检索栏里输入过程子建的姓名。那个寡言而强壮的男人竟创造过徒手深潜的世界纪录——112米。2013年,该纪录被一个英国人打破。有人在论坛上问起程子建的下落,回复说他早就退出了竞技圈,正在北岛教潜水。正如只头几年有人想着发帖纪念陈丽莎一样,随着一个个潜水新秀或初露头角,或挑战极限时遇难,更新奇的消息吸引着大家的眼球,不再有人提起程子建。人总是这样擅长遗忘。
和大多数人一样,程小童不能完全理解父母的事业。程子建在北岛的驻留有种偏向虎山行的意味。每每只能让爷爷去开家长会时,程小童都会有些怨言。
每一年,爷爷奶奶都在劝程子建回北城。殊不知程子建非但固执地留守,今夏还要将程小童一并带去。缘由无人知晓。夜里程小童悄悄摸到书房门前听他们说话,奶奶问:“你带他去北岛,是不是为陈丽莎的事?又是白费功夫!”爷爷说:“你找了她十年,还不够,还要拉上小童?让孩子永远别知道这些,不好吗?”
起初回答他们的只有沉默。透过狭窄的门缝,程小童看到书柜透明的门映照出三人的影子。直到秒针滴滴答答快转过一圈,程子建咳了一声,终于开口:“他得知道。”
两个老人的叹息,让程小童的心瞬时揪成一团。他忽地觉得害怕,却不知道自己恐惧的仅仅是叹气的声音本身,还是那些将被揭开面纱的、与陈丽莎有关的事情。
候机时程小童问:“我们去北岛做什么?”
程子建反问他想怎么安排。程小童被问得一噎,不知如何应答。他习惯了让自己随日子一天天向前挪移,像顺流跌下的一叶小舟。
“我不知道,”他只好如实说,“反正只要不用上学,怎样都是好的。”
程子建轻轻地、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
他望着舷窗外的蓝静默良久,然后说:“那我来教你潜水吧,带你看看我在那里的生活。”顿了一顿,续道,“你妈妈以前的生活。”
抵达北岛是在傍晚。金色的黄昏覆在低矮的建筑上。此间的房屋都被深色涂染,屋体棕黄,屋顶大红,程小童拖着行李走在狭窄的街道里,新奇地觉着像走进了一幅油彩画。
他们住在镇上的公寓,离码头只百米远。六月底还不到旺季,楼下餐厅里人坐得稀稀落落。距吧台近的人同老板娘閑聊,程小童在旁听得也清楚。老板娘在本地出生、长大,亲眼看着北岛从一个普通渔村蜕变成了潜水胜地。一对情侣问她有没有潜水教练推荐,她不及搭话,就有个爽朗的男声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程小童循着他们的眼神看去,才发现他所指的正是在对面吃着青木瓜沙拉的程子建。
不过这个夏天,程子建并没招收新的学员。程小童是他唯一的徒弟。第一课是潜水规则。程小童平日里懒得背书,但读过几遍潜规就能背个滚瓜烂熟,这可能与程子建拿生动的新闻配合有关。案例大都关于不遵循潜规可能招致的恶劣命运,小到在海下碰触动植物破坏生态,大到离水面五米时快速上升出现致死的动脉气泡栓塞。桩桩都比鬼故事还叫人毛骨悚然。
“这么危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潜水啊?”程小童趴在桌上不解地问。
“危险只是为了让人明白它的力量。海洋惩罚的是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程子建伸手推开窗子。夜间的海面遥遥,深蓝的颜色弥漫开来。海天交界处的雾霭泛着紫色和橙色的光,仿佛一个缥缈的梦境。
“等你下过水就明白了,那是个全新的世界,很难形容……每个人都能在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程子建说得很慢,像是沉浸在回忆的洋流中,“之前,你妈妈总盼着碰见鲸鱼。”
程小童只在画册里见过鲸鱼。程子建从朋友圈翻出一个视频给他看,说主人公之一便是今天餐厅里那个大嗓门的年轻人。他正在一块礁石前徘徊,全然不知背后有个庞然大物。经同伴打手势提醒才转头,不由得失声惊叫,摆动着脚蹼向远处游了几米远才回过神。两人相视,又看看那灰鲸,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几十秒后,程小童才敢将始终屏着的一口气轻轻地吐了出来。
“在这片海,肯定能碰上鲸鱼吗?”他怯怯地问。
程子建摇摇头:“也不是。之前要真能打个照面,你妈妈会特地在日历上画个记号,说这是幸运的一天。”
“要是真遇到了,千万别怕,”他说,语气严肃,“不要挡路,也不要逃,它不会主动伤害你。你可以和它拍照,不过要多留意周围环境的变化。”
程小童将手册倒扣在头顶,垂下的纸页盖住了脸:“其实我不想遇见它们。”
突兀地,程子建剧烈咳嗽起来。程小童挺起身看向他:“爸,你没事吧?”
程子建摆摆手,咳声却没有停歇的意思。他起来转身进了里屋。隔着一道木门,他的喉咙发出格外沉闷而混沌的声音。
三天后,小艇载着一船人往珊瑚岛去。同行的还有视频里那个年轻人。他正靠着船舷,迎风往嘴里送鸡肉卷,一见他们就兴高采烈地挥手打招呼。
他叫刘启北,买下了北岛一家潜店做老板。刘启北开玩笑抱怨说全因为程小童占了程子建的名额,有个慕名而来的学员没了着落,他才不得不勉强上阵做潜教。
那学员问:“不当潜教,那你平时做什么?”
“能做的事多了,我可以出来自由潜啊。”刘启北吞下最后一口鸡肉卷,声音含混不清,“往常这时间,我们还会出海追捕鲸船。”
“哇塞,能不能把我们也带上?”
程小童的眼睛一亮,刘启北却已经转过身去面向学员:“肯定不行,你当那是出去玩啊。这两年捕鲸船的武器比咱强多了,容易出事,出海前要做很多准备。”见学员神色失落,他拍拍那人肩膀,“但你放心,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咱们先把潜水练好了,包你学有所成。”
程小童将已经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半个多小时后,小艇抵达珊瑚岛。
三天来,程小童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buddy”。在潜水界,它指的是随你一同下潜的小伙伴。从对仪器的安全检查,到下水,再到出水全程的相互配合,你们都得相依相伴。你们的信任和性命全都交托给了彼此,如同一体。
程子建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将面镜挂在脖子上,左手拎住BCD(浮力调节装置)和呼吸器,右手提着脚蹼,再拿起配重,这样会更从容不迫。程子建叮嘱他一定要扣紧快卸扣,打开气瓶阀门,这些都是保命的关键。
他们按照“BWRAF”(下水前安全检查)原则互相检查装备,确认备用二级头的位置,才一前一后没入风平浪静的海面。飞鸟的鸣叫、均匀的呼吸与深蓝色海水的汩汩波动声渐次消失。当头颅顶部也彻底浸没在海水下时,世界寂静无声。潜水者仿佛涉足全新的王国。
这是程小童第一回下水,练的都是基础动作和手势。海底清澈无垠,只有水母和细小的游鱼做伴,一切都很顺利。末了程子建举起大拇指,手向上滑动,示意他准备安全上升。程小童比了一个“OK”的手势。他们保持匀速,浮出水面。
程小童没有遇见鲸鱼。
他很庆幸,又觉得失落。他摸不清自己是否当真盼着同它面对面的一天。
程子建的咳嗽始终没好,却仍没将烟放下。程小童给他念了遍生物课本上吸烟的危害,刺激呼吸道、致癌云云,他“嗯嗯”几声,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
程小童在网上查了药店的位置,傍晚步行去买治嗓子的药。夏日的黄昏来得很晚,他个子本来就高,此时影子被拉得很长。回程时他走在前面那人身后,玩一个古老的游戏。他变动着行走的轨迹,让自己的身影淹没在对方的影子里。忽地有人在背后拍他的肩膀说“嗨”,把他吓得一激灵,一脚从人行道踩到马路上。
竟然是刘启北。他笑着说正好要找程子建商量些事,便和程小童同路而行。
“老程总提起你。看得出来,你是他的骄傲。”
程小童脸一烫,垂下头:“没有,我学习很差的。”
“我猜你体育不错。”
“还行。不过这没什么用,除了跑步、跳远我什么都不会。”
“早前我也这么想自己。别急,日子还长着呢,慢慢来。”
程小童没说话,闷头往前走。两人拐过弯去,这条路很狭窄,他们一前一后,遥远的地方有人在用本地话唱歌。
“我还以为我爸在这儿沒什么朋友呢。跟他这种闷油瓶聊天可不容易。”
“那是我人缘好,”刘启北一挥手,“回头你跟我去吃饭,老板娘都能给咱免一道咖喱鸡的钱。再有……”
他停顿了片刻,脚步却没停,继续沿着狭长的巷道向前走去。
“我父亲也在十年前那条船上。”
程小童一怔,一时没往前迈步,过了几秒才追上去。
“所以你们都是因为这个才来北岛的,是吗?”
“嗯,还有其他人。”

刘启北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没点着,就用左手夹着。
“不过也不只因为这个,”他开口,说得缓慢,“在北岛更容易想起那场意外,但也更容易忘记它。在海上看的鲸鱼、鲨鱼多了,知道咱们对海底下的事有多无知,再看自己,就觉得人的一辈子太短了,什么都做不了。”
程小童小声说:“可要是等不到结果呢。”
“没事。就当我是来记住这些事的,忘了的人已经够多了。”
他们终于从百转千回的小巷里走了出来。傍晚的风暖洋洋的,程小童闻到了海洋腥咸的气息,混杂着炒菜的油烟味。亲切,却也混杂着某种感伤。
那晚刘启北和程子建谈了很久才离开。程小童躲在窗帘后面,看着刘启北的身影消失在被路灯映着的花团锦簇后头。又有咳嗽声在隔壁响起来。他想了想,来到程子建的房间,将牛皮纸袋子放在桌面上。
“你的药。”
程子建愣了一下,撕开用胶带封着的袋口,往里瞥见含片和止咳糖浆。“嗐,我没事。”他说,“老毛病了,不用你麻烦。”
“……你总撑着,”还嫌力度不够,程小童声音微弱地补充了俩字,“硬撑。”
程子建望向他,他却将眼神挪开去看窗外了:“你们又要去追捕鲸船了吗?”
“嗯,不过不急,应该得八月底。”
“我们在课上看过一个纪录片,”程小童没说那其实是他偷着搜来看的,“说那很危险。捕鲸队有枪,还有炮。非得去吗?”
他们沉默着。远方又有歌声传来,不知是不是之前那人,腔调倒是一样。尾音翘得欢快,几乎要跳将起来,高亢的音将破未破之际,却有一种别样的凄凉。歌声越来越近,两人的呼吸声被淹没其中,像拍打到岸边时崩解了的海浪。
当时程子建并未明说,可程小童已经知晓他的答案。
后来有天程小童问起餐厅老板娘,是谁在唱歌,唱的又是什么。老板娘告诉他,那是个傻子,六岁那年脑子被烧糊涂了。她想了很久这首本地民歌究竟该怎么用普通话翻译,末了说大概是秋时花谢,明夏再开,鲸鱼游去,还会归来。
歌名叫作《轮回》。
之后每天照旧潜水,程小童学得很快很好,他总能恰到好处地调整呼吸,每个潜降的动作都十分精准。有一回在水下遇了淤泥也没慌张,处理沉着妥帖。程子建的评价依然克制,刘启北则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认为这孩子天生就是潜水的命,该好好把老天爷赏的饭碗端稳了。这是程小童头一回在运动会之外的场合收获这样的夸奖。不过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如刘启北说的那样是个天才。你知道的,这种情商高的朋友总有个毛病,那就是旁人永远不知道他们的话里到底有几分真。
在程子建的抽屉里,程小童看到了一张从未见过的照片。此后他常想起照片上的母亲,她穿着高腰紧身牛仔裤和米黄色的短袖上衣,留着短发,眉眼弯弯如月牙。怎么说,好像她天生就应该笑容满面一样。有时候触景生情,程子建会提起陈丽莎,关于他们的相遇、下潜和远航。程小童将她与一切美好的意象挂钩,譬如冬日干燥的阳光,或者海上明亮的星辰。
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过去,直到八月中旬,他们在岸上接到刘启北的电话。他声音急促,说有两头鲸鱼被猎网缠住,困在了海上,需要帮助。
春夏之际,抹香鲸本该从靠近北极的海域向南迁徙,前往威力港附近繁衍,再携着幼鲸向北归去。不知道被什么阻碍了行程,这两头鲸鱼现在才游近北岛,渔网缠满它们的脊背。
鲸鱼比它们乘坐的快艇还要长,估计得有十多米。直觉告诉程小童应该后退到船尾,可他又想冲向前去看个仔细。抹香鲸的头连同小半边脊背浮出水面,喷出直冲天际的水柱,水落回海面时拍打起一片白色的水花,飞溅到快艇上,也溅落在程小童的衣服上。他想它的身体是冰凉的,突然很想跳进去触摸它来证实这猜测,很快又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一重又一重来自远方的海浪,正将它推向离船越来越近的方向,快艇不得不调转,从它的身前绕到侧边去,随着它的起伏向前漂动。
两艘快艇上共六个人,都会潜水,不过船上得留人照看,免得失控撞上鲸鱼甚至侧翻。刘启北和他的同伴已经穿上干式潜水衣。他朝这边船上打一声呼哨:“老程,咱一边管一头行吗?是现在动手还是等岸上的人来?潜教都在珊瑚岛,要等得个把小时才行,不知道它们撑不撑得住。”他向水下指了指,拧着眉,因阳光的直射微微眯起双眼。
程子建没立即答应他,而是半蹲下身凝视着海面。他又向刘启北确认了下情况。刚被发现时,鲸鱼还是有些紧张,翻腾过几次,但在长久的挣扎后它早就没了体力,不具备攻击性。

他问程小童:“跟我下去吗?渔网我来处理,你需要割开可能缠在我身上的部分。”
程小童点点头:“好。”
两个月以来,他们已经形成了某种“buddy”间的默契。潜入水下,他们自然地保持着距离。银白色的渔网在鲸鱼身上缠绕,细密的网像是蜘蛛织就,似乎还有不少堵在口腔,但因为它始终闭着嘴而看不确切。从鲸鱼身前经过时,程小童鼓足勇气与它对视,不知道是不是想得太多,他从它的眼睛里见到了惊恐,便没敢再看下去。
程子建打个手势,示意程小童跟在他身后,他们先游到鲸鱼的左侧。渔网实在纠缠得太过密集,没法找到某个引子将它自然地解下,只能用刀割开。程子建小心翼翼地把着渔网,提防着鲸鱼偶尔的摆动,横贯着把它切断。紧接着程小童将缠住他身体和手脚的渔网清理干净。慢慢地,鲸鱼身侧、顶部和两鳍上的渔网基本被完全剥落,一团夹杂着紫色与绿色海藻的白网被扔到了船上。
渔网只剩下嘴里的部分。两人游到鲸鱼面前时,程小童有些犯愁。可就在此时,鲸鱼竟然停下了刚刚的挣扎,将嘴大张开来。他几乎要惊叫出声,觉出一种令人心悸的兴奋。随即一种战栗涌上他的心头,他意识到程子建要将手探入鲸鱼硕大的口腔。
程子建注视良久,回身望向程小童。隔着潜镜,他隐约感到父亲似乎对他笑了下。程子建打个手势,让他不必担心。随后程子建扭转回身,将手伸进了鯨鱼的嘴里,触碰它泛着灰色的、弯钩样的牙齿。终于,银白的织网被全部掏出。
他们向侧边游去,程小童斗胆用手指拂过它的身侧。程子建举起右手,似是向抹香鲸致意。在陆地上,程小童从没机会目睹他这样俏皮的时刻。他们陆续浮出海面,向小艇游去。
“还好离海岸不算近,不然还得跟上次那头一样,操心怎么让它回到深海。”刘启北已经坐在艇上,他将潜镜与气瓶全部摘下,冲程小童竖起大拇指,“小伙子,干得不错啊。”
程小童低下头。他依然不习惯收获别人的夸奖,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回应才好。万幸在他没想出办法的时候,刘启北霍然站起身,朝着不远处的水面望去。所有人都被他的举动吸引了注意力。
两头抹香鲸起初仍半浮在海面上,间或朝天喷水,一如往常。渐渐地,它们的动作激烈起来,并排向前,身形缓缓起伏,一头拱入海面,宽大到如半边机翼的尾部腾起,然后头又拱了上来。原先平静的水面登时翻天覆地,雪白的泡沫不及破碎,就被新的泡沫挤开去。末了它们向下俯冲,整条蓝黑色的尾巴露出水面,原先向下卷着,后来全部舒展开来。伴随着那一字一样平整的边沿没入水下,水声咕咚,渐渐便没了声响,只剩清浅涟漪。它们显然已经回到千米以下的深海,消失不见。
程小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脖子前倾,微微张大的嘴巴无法合拢。良久他才将视线收回,渐渐返过劲来,觉出肌肉酸痛。在他身前,程子建已经脱去湿衣,穿一件白背心,裸露着双臂,一头鲸鱼赫然绘于其上,炽热的阳光刺在上头。他感到那些在心里堆积已久的灰暗情绪,怀疑、恐惧、羞赧等种种,全部消融,无所遁形。
他渐渐回忆起对鲸鱼的碰触。它如他猜想的那样冰凉,却又意外地坚硬。只是木着的手指还来不及仔细记忆这种感觉,身体就已经游到了几米开外。他难免觉得可惜,却又不逃避那刻的胆怯,而是让情绪自然地暴露在阳光下。他更多地觉得快乐,原来真的可以为它们做些什么。他还想再次遇见它,疯狂地想。这种念头沸腾着,像海下喷涌着熔岩的火山。
程小童离开北岛前那周,程子建与刘启北又踏上了“海洋保卫者”的大船。前一夜程子建收拾行李到很晚,最后才看到桌上那袋药。其实他并没有吃药的习惯,这种小毛病通常扛扛就过去了。可他还是从里面拿了一板含片,放进双肩包最外面的那层。他曾想过很多次,究竟该怎样向程小童讲述这一切,垃圾桶里的半封信和草稿箱中的邮件都见证了他的犹豫。最后他决定带程小童来到这里。他相信程小童会懂。
那时程小童就在门外,悄悄注视着他完成这一切。程小童心里有很多问题,有程子建能解答的,也有程子建解答不了的,可他没有说出口。他明白,总有些人要去做这些事,正如总要有人铭记十年前曾发生过什么那样。他没法,也不想如爷爷奶奶那样劝说父亲回北城去。
登上返程飞机的前一日,程小童跟着留驻潜店的潜教乔森乘船前往德查岛。乔森说那是最可能遇见鲸鱼的地方,但谁也没法打包票。程小童决定试一试。
海上阳光普照,白日湛蓝的海水闪耀得如同星空。跃入水中时,他产生了一种微妙的错觉,好像世界颠倒,无数细碎的繁星撒落其间。
他缓缓下沉,气泡向上升腾。这一回赶上沙丁鱼群,他悬浮在水里,鱼群非但不怕,竟靠近过来将他围堵。他觉着好奇,张开双臂,朝它们缓缓挪去。鱼群突似受了惊,绕了一个大圈,在他身侧旋转。圈子越来越大,一下转向,它们全都向远处游去,不久便全无踪影。
他并没遇见鲸鱼。乔森在水下冲他无可奈何地摊摊手,示意安全上升。
程小童向上浮动着,呼吸深长而缓慢。十五米,五米,他们做了两次安全停留。这将是今夏最后一次深入水下,他尽可能地延长着对每一秒的感受。他感到身体变得沉重,心却越发轻盈,纵使有一丝失落夹杂其中。
曾经他像无头苍蝇一样朝着四面砖墙鲁莽地冲撞,企图撞出一条他也不知通向哪里的道路来。可如今他置身于更广阔的天地。被海水包围时,所能做的只是缓缓上浮,离水面也离阳光更近一些。
他想到许多事,关于母亲,关于父亲,也关于自己。他想他还会再次回到这里,加入这漫长的寻觅,而陈丽莎并非唯一的答案。
抵达海面那刻,潜镜外一半天空,一半海水,海上与海下的世界交叠。瞬時的恍惚冲进他的脑海,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编织,他眼前浮现出这样的场景——
鲸鱼潜入海底,太阳高高升起。
编辑/胡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