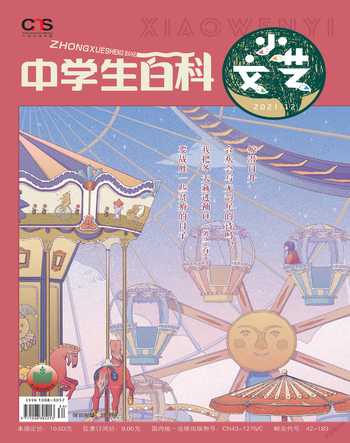鸡兔同笼
“大约在1500年前,《孙子算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书中是这样叙述的:‘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
那天我在地下室整理东西,偶然间看到小学五年级数学课本上的引序,多年前这个小城起雾而生冷的冬天,在我昏暗的视线里又一次变得清晰。
“鸡兔同笼的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懂了吧?”
下课铃声响起,数学老师推了推厚厚的眼镜片,转身准备离开。我抱着课本从教室最后小跑追上去,鸡兔同笼的问题我还是没有听懂。
“老师,为什么……”我的话刚从嘴边冒出,几个平日里深受老师宠爱的同学便围了上来,把我推开。我攥着笔怯怯地退到他们身后,一直等到上课铃声响起,数学老师抱着教案走进隔壁班,我又重新回到教室最后一排那专属“学困生”的座位上。
我从小就是一个笨孩子,也习惯了别人的冷漠。那些其他小孩一拍脑袋就能想明白的问题,我却怎么也不懂。
数学老师很喜欢叫学生上黑板去解答问题,谁越不会,她越喜欢叫谁。所以每次上数学课,我都垂着脑袋,不敢看她的眼睛。那时候,我常常被叫上去,在讲台上站小半节课也做不出来,粉红色的粉笔被我攥得满是汗。回到座位以后,那支粉笔在空中画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重重地落到我的发卡上。
“这么简单的问题,回回都不会,不会就去好好学啊。”
我埋着头,冬日的教室里阳光明媚。
回到家,我不敢跟爸爸说我在学校里经历的一切。那时候爸爸刚从部队转业回到我们这个三面环山的小城,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凶。他生气的时候会冷着脸很久都不跟我说话,会打我,我哭的时候他会大声地吼我,要我安静。并且,他对我的要求总是很严格,我不敢让他知道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始终都搞不明白。
直到月考结束,老师要求家长在考卷上签名,我才硬着头皮把那份不及格的试卷拿到爸爸面前。
我怯怯地望着他,鸡兔同笼的那道大题,我一分也没有得。我以为他会把我的卷子摔在桌子上,然后狠狠地教训我,可是没有。他把我的试卷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开始给我讲鸡兔同笼的题。
没过多久,白纸上就满是凌乱,而我的大脑也满是凌乱。我听不进去了,我能感到爸爸越来越焦急,可他没有生气,窗子外面雪花越下越大。我侧过身去看雪,那些玻璃窗里暖黄色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暗了下去,雪夜里飘浮着微亮的光。
那之后的好些日子,放学回家我都能看到房间门上挂着写满公式的小黑板。晚上我写家庭作业,爸爸就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看我的教辅书。他准备了三种方法为我讲鸡兔同笼的题。
“你看,假设鸡有X只,那兔就有(42-X)只……所以……”
一遍又一遍之后,我终于点头:“嗯,好像懂了。”
“那你来给我讲一遍。”他把粉笔递给我,我又一次语塞。
“你听着,我再讲一遍,假设鸡有X只,那兔就有……”
这样来来回回好多遍,我们都很疲惫了。最后总是爸爸妥协:“今天就先算了吧,你先去睡觉,明天继续。”我躺到床上,他房间里的灯还亮着,铅笔与纸张摩擦的声音消融进北方冬日的大雪里。
挨打也不是没有过的。有时候我们都不耐烦了,我撇着嘴把书狠狠地合上:“我不看了,学不会的。”爸爸冷着脸,而我越来越感到委屈,“我就是不会,就是不会。”他把书卷起来,重重地敲在我的头上,头发被敲得乱糟糟的,铅笔与草稿纸散落了满地,而那本印有鸡兔同笼练习题的教辅书,也被揉得皱巴巴的,还缺了角。

也是那年冬天的事情。院子里有几个同班的小孩,他们看我成绩不好又不爱说话,在下课的时候会像数学老师那样,把粉笔头扔到我的发卡上,然后哄笑着散开。后来他们开始问我要钱,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而我从来都不敢反抗。
我把所有零花钱都给了他们,还是不够,便偷偷从爸爸的抽屉里取钱给他们。后来爸爸知道了,他拉着我的手依次去敲那些小孩家的门,我怕看到那些孩子的脸,就躲在爸爸身后。他让他们跟我道歉,跟那些孩子的家长讲道理,月光映照着白雪,我在那些冰凉的门外感到安稳而不再害怕。
回家的路上,卖糖葫芦的老爷爷还裹着棉袄站在路边,他的小推车上插满了甜腻的梦。我举着一串寒冷而甜的糖葫芦,玻璃糖纸融化在嘴边,咽下去的,是无数闪烁而温软的星辰。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那道鸡兔同笼的数学题,也不再是解不开的谜。我不再那么怕他,也喜欢趴在阳台的窗子上,等夹着公文包下班回家的他,从口袋里掏出糖炒栗子或是小金橘给我。
高三那年,高考的可怖气息笼罩着我们。函数,不等式,平面向量,圆锥曲线……我再去问爸爸题,才发现,他已经不是我记忆中那个无所不能的爸爸了。
多年前那个抱着小学五年级数学课本的小女孩,如今在我的记忆里已遥远而模糊,可那些大雪纷纷扬扬的夜晚却总被点亮,在我生命的某一刻,与雪夜里的光相会。
编辑/胡雅琳
王彤乐,1999年冰月生于陕西宝鸡。现就读于西北政法大学。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扬子江》《诗歌月刊》《青春》《作品》《散文诗》《草堂》《山东文学》《散文诗世界》《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獲第四届陕西青年文学奖、“分享通信·尚5G杯”十大校园诗人称号、东荡子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