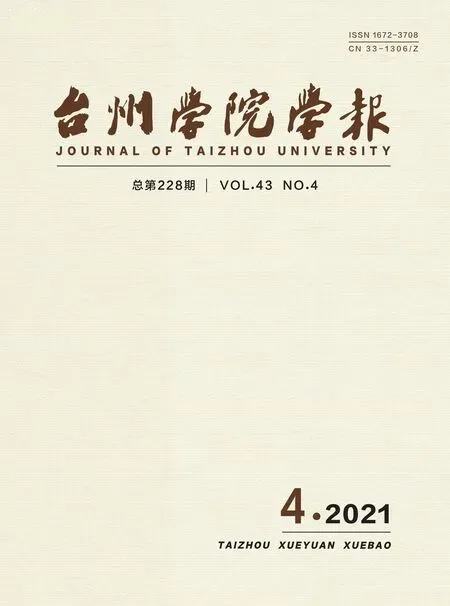“妖”言“怪”语
——论核心义对词义演变的影响和制约
叶 娇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妖、怪、精三个单音词在古代汉语中频见,常常组合成妖怪、妖精、精怪等复音结构,泛指大众熟悉的妖魔鬼怪。在推行唯物主义和科学教育的今天,这些词似乎本应消亡衰弱,但查阅当代汉语语料库,却发现三词不仅被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普遍接受和使用,而且构词能力极强,衍生出大量新词,妖股、妖市、怪咖、怪才、戏精、话精……一大群“妖”言“怪”语不断涌现。
受当代影视作品的影响,妖、怪、精的形象在传统的恐怖惊悚之外,反添可爱、美丽和多情之义。电影《捉妖记》中可爱的小妖胡巴,《西游伏妖篇》中萌萌的大鱼怪,《二代妖精》中美丽专情的狐狸精,都一改以往的面目狰狞、邪恶害人。相应地,词语的语义色彩也发生明显变化,“妖”言“怪”语不再是完全的贬义,而是朝着中性乃至褒义的方向发展。网名中自称妖精、小妖的有之,生活中以“妖”恭维女人的更是多多,似乎“妖”是女人的最高境界,“妖必美丽,妖必伶俐,妖必妩媚,妖必千变万化”[1]。其实,语义的变化只是一种表象,“妖”言“怪”语始终都未脱离各自的核心义。
核心义是前贤们从训诂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虽然由于研究目的不同,研究对象有别,核心义的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的界定。如郭在贻称之为“(词的)这种内部联系”[2],宋永培认为“是由本义蕴含的形象特征及形象特征凝聚的核心义”[3],张联荣则运用义素分析法,指出核心义就是“一个多义词的所有义位共有一个遗传义素贯穿其中”[4],王云路进一步总结提出“核心义”和“核心义磁场”的观点,明确“核心义不是本义……而是由本义概括而来,贯穿于所有相关义项的核心部分”[5]19。简言之,核心义就是多义词在词义演变过程中那个隐含和贯穿始终的语义特征。
一、最初的语源差异
在现代多数人的印象里,指称妖魔的妖、怪、精三词意义区别不大,形象也难区分,它们都能托为人形,善于幻化。强加区分,似乎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妖”的所指范围略广,涵盖了“怪”和“精”。如《西游记》中师徒取经途中一路所降的“妖”就既有白骨精,又有黄袍怪,还有狐妖、黄眉老佛、虎力大仙……“妖”统指一切,指称一切妖魔。但从词源上看,三者差异相当明显,有各自相对稳定的意义核心。
“妖”,原作“䄏”,始见于篆文。《说文解字·示部》:“䄏,地反物为䄏也。”段注:“经传通作妖。”[6]8《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杜预注:“群物失性。”[7]《资治通鉴·唐则天后长安元年》:“凡物反常皆为妖。”[8]本义为反常、不祥的自然或社会现象。后引申指迷信传说中害人的怪物。《风俗通·怪神》:“若叔坚者,心固于金石,妖至而不惧。”[9]进一步发展出装束、神态奇特,不正派等义。在所有义项中,有一个义素贯穿始终,就是反常,这正是“妖”的核心义。然经典多写作“妖”。《玉篇·女部》:“妖,媚也。”[10]本义为容貌艳丽,神态妩媚。因此妖常常又显示出女性妩媚惑人的一些特征。故“妖”的语义特征可概括为[+反常][+媚惑]。
“怪”出现更早,战国已见。《说文解字·心部》:“怪,异也。从心,圣声。”[6]509本义为奇异的,罕见的,形容词。《山海经·南山经》“水多怪鱼”下郭璞注:“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11]后指奇异的事物,名词。《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12]进而特指传说中的妖魔。《汉书·高帝纪上》:“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13]又产生出惊异、惊奇、害怕等动词意义。“怪”俗字作“恠”,从心,亦强调人的主观内心感受。王充《论衡·自记》:“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14]358明言“妖”偏于客观反常现象,“怪”侧重主观内心感受。所以“怪”的本质是对事物感觉不寻常,其核心义是“不寻常的感觉”[5]76。语义特征可标记为[+不寻常][+感觉]。
“精”也出现于战国。《说文解字·米部》:“精,择也。从米,青声。”段注作“择米也”[6]331,本义指优质纯净的细米。引申有纯洁、纯净、美好、精华、专精等义。东汉时也可指鬼怪。王充《论衡·订鬼》:“物之老者,其精为人。”[14]276“古人以为,物也像人一样,其实也有形体和灵魂的区别,所以年深岁久植物及无生命者其灵魂可化为动物或人,动物可化为人。这种动物或人即是‘精’”[15]。可见,“精”原是物之精灵,是经修炼后化为动物或人的一种鬼怪。石精、花精、河水之精,皆是。其声符“青”含有生机、美好、胜出等意,故引申指鬼怪的“精”多指年深岁久动植物及无生命之物,吸天地精华后所化成的超出同类之物,多具灵性。“精”的所有义项都离不开“超常、优质”这一核心义,语义特征可提炼为[+超常][+优质]。
二、使用中的词义混同
妖、怪、精三词本义有别,但在词义的引申过程中,都产生出灵怪、鬼怪一义,大致在东汉时已发展成一组同义词,影响至今。能发展成同义词的原因即在于三词的核心义中都有隐含的“不正常”这一特征,无论是“反常”“不寻常”,还是“超常”,皆为不正常。
文学作品的妖、怪、精形象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常托为人形,善于幻化,即都是人类眼中不正常之物类。如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称:“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16]此“精”假托人形,只有在镜中才能看到其真身原形。干宝《搜神记》卷十四:“汉献帝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无故瓮器自发,訇訇作声,若有人击……闻,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良久,于室隅间有所中,便闻呻吟之声,曰:‘哊!哊!宜死。’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了不相当,貌状颇类于兽。”[17]131此偷东西的“怪”平时无影无形,但中杖后亦能化身为一老翁。卷十八:“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17]165原形为斑狐的“妖”亦能幻化成书生。
不同于人类的,非正常的、善于幻化的妖、怪、精,常人实难区分,故后世典籍多加混用。
古籍中有“妖”“精”“怪”上下混用的。如《太平广记》:“荒徼之地,当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为乎?”[18]上句说“妖怪”,下句言“精魅”。又《警世通言·一窟鬼癞道人除怪》:“邪怪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19]
有标题与正文交错杂出的。如元好问《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犬精迷妇》载:“每至二更时候,有一物若巨板砖状伏于身上,不可动,至鸡鸣,物方离身起去。阿姑方悟,视起身下,白汁满席,方知为妖怪所惑。”[20]标题称“精”,文中作“妖怪”。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三“猿妖”条:“张韫甫言:嘉、隆间,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门梅庙烧香,为物所祟,每至辄迷眩,百计遣之不去。后部中一办事吏谙道篆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设坛行法,别以小坛摄怪。久之,坛内啧啧有声,吏复以法咒米,每用一粒投坛中,其怪即畏苦号叫,似不可堪忍者。问其何所来,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广将之江以北,道过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树杪,而此夫人经行其下,适有淫心,遂凭而弄之耳。’吏以符封坛口,火焚之,怪遂绝。”[21]题目为“妖”,文中皆作“怪”。
有同义相训的。《楚辞·天问》:“妖夫曳衒,何号于市”下,东汉王逸注:“妖,怪也。”[22]
甚有同一事同一物,妖、怪、精同义换用的。我们熟悉的白蛇传说中的主人公,在古代不同典籍中称呼就多有不同。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南山胜迹》:“雷峰塔者……吴越王妃于此建塔……俗传湖中有白蛇、青鱼两怪,镇压塔下。”[23]清陆次云《湖堧杂记》中“雷峰塔”条载:“雷峰塔,五代时所建,塔下旧有雷峰寺,废久矣。……俗传湖中有青鱼白蛇之妖,建塔相镇。”[24]但清玉花堂主人《雷峰塔奇传》第九回“游金山法海示妖”则作:“此妖非同小可,他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风洞修行的白蛇精,思凡下杭,在仇王府花园内栖身,更有丫环小青,也是蛇怪。”[25]这里,蛇怪、蛇妖、蛇精完全等同。
可以说,在民众口头叙述或是文人辑录创作时,“妖”“精”“怪”三词基本上是可以混用的[26]。
由此,同义连用现象频现。三个单音词常常两两组合构成双音词,成为构词的语素。《隋书·五行志》:“帝曰:‘门卫甚严,人何从而入?’当是妖精耳。”[27]前蜀贯休《赠钟陵陈处士》:“高吟千首精怪动,长啸一声天地开。”[28]《封神演义》第十六回:“子牙定眼观看,认得是个妖精,暗思:‘好孽畜?也来试我眼色。今日不除妖怪,等待何时?’”[29]《西游记》第八十二回:“那怪精没计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挣起来,把唐僧背在身上,拽开步,往外就走。”[30]961第八十九回:“行者正然看时,忽听得山背后有人言语,急回头视之,乃两个狼头怪妖,朗朗的说着话,向西北上走。”[30]1032《济公全传》第一五五回:“他本是韦驮转世,手使降魔宝杖,所有天下的精妖,皆属灵空长老所管。”[31]精怪、妖精、妖怪、怪精、怪妖、精妖,形式多样,反映出复音词产生之初语素组合的灵活和不固定。甚至还有妖怪精连用组合成词的,在民间文学中多有使用。如浙江海盐歌谣:“法海一见火直喷,骂声:‘白蛇妖怪精,禅杖棍子法力大,定斩你妖蛇不留情!’”[32]至今各地方言中仍保留此词。
三、传承中的词群衍生
在语言复音化的大趋势下,三词单用的情形越到后代越少见,当代语言中,仅存在于较书面化的语言或称谓中。但是作为构词语素,它们却异常活跃,不仅保留了大量古语词,还各自衍生出大量新词。
(一)“妖”词群。依《现代汉语词典》,“妖”族词14条:妖风、妖怪、妖精、妖媚、妖魔、妖魔鬼怪、妖魔化、妖孽、妖娆、妖物、妖雾、妖言、妖艳、妖冶[33]1521。作为构词语素的“妖”完全承袭古人对“妖”的贬斥,具有较强的贬义意味。即便是赞美女子艳丽、妩媚的“妖娆”“妖艳”等词,释义时也往往加上“不庄重、不正派”这样的修饰语。
但据全面反映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34],“妖”词群在当代社会使用极广,远超《现代汉语词典》所列,不仅语素组合更灵活,且语义色彩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微博、报刊、网络小说等领域中检索出的上万个“妖”为例①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所引新词出处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后文不再逐一标注。,当下的“妖”词群在语言组合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归纳如下:
1.继续作为单音词。这种用法主要用于指称,延续了“妖”的妖魔意义。由于古人对妖的认识为贬义,故仅见此妖、斯妖、那妖的搭配,用于指称对方或第三方,从未见自称用法。然当代却多以“妖”自名:或以网名形式出现,自称为“××妖”;或与指示代词“本”搭配,构成“本妖”,丝毫不见贬义,反有种自诩和自嘲的意味。
2.作为构词词素:结构上有并列式、偏正式。传统同义连用形成的复词保留至今的,全是并列式,新词的构成明显以偏正式为主,可细分为三类:
(1)形容词+妖:懒妖、忙碌妖、腐败妖、勤奋妖……②这一类组合单列出来似乎应视作短语,中间都可插入“的”进行扩展,但在语料库中出现频率较高,意义上具有稳固性和整体性,往往特指某类人,故这里将其视作新词加以讨论。
(2)名词+妖:猫妖、剑妖、电妖、雷妖、风妖、雨妖;人妖、国妖(国家的妖孽,指危害国家的人);棉被妖(赖床的人)、五毒妖(网络小说中的妖精类别)。
第(1)类新词,源于传统词语老妖、小妖、女妖;第(2)类新词,源自传统的水妖、蛇妖、鱼妖等。两类新词均是类推产生,语言构成上并未产生新用法,只是搭配范围扩大。不过,两类词的语义色彩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除人妖、国妖外(人妖,强调的是不男不女的性别反常,国妖重在突出危害国家之人的程度反常),贬义色彩明显淡化。即便是传统的老妖、小妖等词,也出现了旧词新用,由原先的完全贬义,转为中性或褒义。如《一“妖”在手哈恩不愁》一文:“中国队今晚仅仅凭借‘老妖’郝海东的唯一进球,在广州的天河体育场1比0击败科威特队,让人提心吊胆地赢下了冲向2006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35]此处的“老妖”毫无贬义,反成了经验丰富的代名词。而在“只是看起来好瘦,侧面好年轻哈,王叔叔是老妖”,“我要做不老的千年老妖”等语句中,“老妖”还代表着青春常驻。再看天使小妖、无敌小妖、萌小妖、国色小妖、纯情小妖、大头老妖等短语,其前的修饰语或显摆容颜,或突显特征,明显更多自褒色彩。
两类新词都以“妖”为中心语,形成前偏后正的格式。语言的类推机制推动着“~妖”式词语的孳生,语义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3)妖+名词:1)妖鸡、妖狗、妖刀(神出鬼没的战术)、妖股(股市上通常把那些股价走势奇特、怪异的股票称为“妖股”)、妖市(捉摸不透的股票市场,常常该跌不跌,该涨不涨)等。2)妖妈、妖叔、妖大爷、妖姨、妖哥、妖姐、妖同学、妖老师、妖货(并不是妖的货,而常用于昵称,指能诱惑他人的一类人;还可整个词作修饰语,如妖货老公)等。3)妖族、妖界、妖班(由仙班类推而来)、妖宝(对妖的昵称)等。
“妖+名词”的组合古已有之,如妖龙、妖人、妖道、妖女之类,但新兴语言中显然形式更为丰富。从第1)类可见,其组合的对象范围明显扩大,搭配对象已不限于熟悉的动物或人,还可以是刀、股、市等无生命之物。第2)类,更是完全创新,妖与称谓词组合,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情况。其创新的原因和“妖”语义的褒化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妖妈还是妖哥,一是思想、见解独特,观念新潮,二是行为独特、出人意表,会留给别人深刻的印象[36]。在熟悉的称谓前加上如此有特点的“妖”,更隐含赞扬和称许的意味,似乎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倍感亲近。第3)类则基于古人对神仙世界的描绘,类推创造出了一个妖的世界,贬义色彩基本消失。
总之,新兴语言中的“妖”词群有传承,更有创新。结构形式未有明显改变,但词语搭配范围和语义色彩有较大变化。搭配的名词、形容词范围增大,有较强的时代感。语义色彩改变最为明显,妖贼之类的詈语使用渐少,多数新词已向中性,乃至褒义转变。但无论怎么变化、搭配,却始终未脱离“妖”的核心义:反常。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反常事物和现象的接受度大大增强,自然“妖”语也不应再是一味的贬义。
(二)“怪”词群。《现代汉语词典》中“怪”族词共22条[33]477,除三词为动词词性、一词为副词外,其余为形容词和名词用法,意义均隐含着“不寻常的感觉”,表示怪异、古怪等。BCC语料库中“怪”词群相当丰富,为便于和“妖”“精”比较,这里仅列举其中的名词,从形式上分作“~怪”和“怪~”两类;同时按照语料库的分类,将出现于“古汉语”语料库中的认定为传统词,其他的为新创词。
1.~怪:传统词:精怪、神怪、鬼怪、诗怪、八怪、老怪、大怪、小怪;新创词:痒痒怪、饼干怪、树洞怪、盒子怪、大脚怪、长腿怪、大头怪、三大怪等。
2.怪~:传统词:怪事、怪物、怪话、怪象、怪癖、怪胎、怪人、怪兽;新创词:怪谈、怪招、怪才、怪叔叔(也被称为“怪蜀黍”,常用来暗示有恋童癖、异装癖,或有其他奇怪癖好的中年男子、诱拐小女孩进行侵犯的猥琐中年男子)、怪咖(有“怪胎”“另类”“怪人”的意思,通常指脾气很古怪,有怪癖行为的人。怪咖人群主要以年轻群体为主)。
两类“怪”词群从结构和组合形式看,古今并无明显差异,结构上除并列式外,基本上都是偏正式,或以“怪”为后置中心语,或以“怪”为前置修饰语。组合形式上都习惯与名词组合,除沿用的“老怪”“大怪”“小怪”是与形容词组合外,未见有新的形容词组合用法。第1类新创词最大的特点是音节的变化,三音节趋势明显,就连沿用的“大怪”也喜在前面再加数字,变成“三大怪”“六大怪”等三音节形式;且“怪”的形象迥异于传统的丑怪、害人怪形象,不仅没有令人产生恐怖,反似乎更赋予一些不好的或无生命的东西以生命,突显其客观特征,增添了几分萌趣和童话色彩。第2类新创词搭配对象上也无明显改变,都是和名词组合,只是更偏向于指人和人相关的行为;同时也反映出新词的出现和外来文化、方言融入密切相关。如“怪叔叔”一词源于日本动漫文化中的中年大叔形象;“怪咖”本是福州方言,以“咖”指人,同时又受台湾俚语“咖”指“角”,即“角色”意思的影响。
“‘怪’从心,属于心理动词,其本质是对事物感觉不寻常,因而其核心义是‘不寻常的感觉’。”[5]176尽管新时代中“怪”词大量涌现,然无一不统摄于“怪”的核心义之下,无论是“~怪”还是“怪~”,萌趣也好,奇葩也罢,突显的都是内心感受,让人产生不寻常的感觉。
(三)“精”词群。以名词为例,BCC语料库中的“精”词群同样可据其在词内的位置分后置、前置两种形式:~精、精~。
1.~精。这是传统文献中最常见的词形,现下沿用最多,且基本都是“名词+精”的形式。如:
(1)无生命名词+精:山精、石精、花精、树精、醋精、柠檬精等。(2)动物名词+精:蜘蛛精、狐狸精、蛇精、鱼精等。这一用法当代语言不仅沿用,而且搭配的名词范围进一步扩大,扩大至各种动植物,新出现了瓢虫精、蟾蜍精、蚊子精、耗子精、鸽子精等。(3)人事名词+精:祸精、人精、屁精;是非精、事儿精、谎话精、戏精、话精、钱精、排骨精等。(4)动词+精:杠精等。
第(1)(2)两类初看古今变化不大,语义上均突出“精”经修炼后,远超同类的非凡能力,结构上也都是常见的偏正式;但实则有些词已出现了语义转化和新用法。像第(1)类中的“醋精”,本指醋酸浓度很高的人工合成醋,但在现代语言使用中往往指经常嫉妒别人的人。“柠檬精”字面意思是柠檬成精,但由于柠檬味酸,与嫉妒他人时“心中酸溜溜”的感觉相合,所以“柠檬精”现多用来指称人、形容人,与“嫉妒”类似,颇含嘲讽之意;近来,贬义色彩不断淡化,有时也用在自己身上,表达对他人外貌、才华、物质条件或情感生活等各方面的羡慕,带有自嘲的意味。“我柠檬精了”就相当于“我羡慕了”。第(2)类中的“鸽子精”也早已不是成精的鸽子,而是转指长期频繁放别人鸽子的人。
第(3)(4)两类,时代特色鲜明,结构上已非简单的偏正式。如:祸精、人精、屁精三词明清时虽已出现,但或未完全定型,或使用颇罕,意义单一;而在当代语言中,形式更简洁、意义更丰富。祸精,源于明清小说中的闯祸精、惹祸精、撞祸精等动宾式短语,均不如现代凝缩后的“祸精”之言简意赅。人精,古籍中只见“害人精”一名,专用于指害人者,现则是磨人精、黏人精、缠人精、小人精等多个词的简缩形式,也专指一个特有心眼、特能算计、世事精明、不好糊弄、处事圆滑、从不吃亏的人;古今语义有较大不同。屁精,旧时是詈词,一指男妓、女性化男子;二指那些善于察言观色、逢迎拍马的马屁精,见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现除保留马屁精意思外,更偏于指机灵和捣蛋,连放屁都十分的精明。
第(3)类中除这三词外,其他诸词更是新搭配、新用法。是非精,贬义词,一是指爱搬弄是非,无事生事的人;一是指爱八卦的人。事儿精,北京人的口头禅,就是穷事特多的人。谎话精,指说谎成瘾的人。戏精,最早是比喻表演、演戏很厉害的人,后发展指生活中善于通过表演或模仿的行为,令人感觉像剧中演员一样的人;但在网络用语中,戏精又带有诙谐、搞笑的含义,用法有褒有贬,褒义就是单纯的赞美,很有戏剧张力的意思,贬义就是爱作秀,说得通俗一点可以理解为丑人多作怪①详参百度百科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8F%E7%B2%BE/16726749?fr=aladdin.。话精,一般用于贬义,话多令人烦的人。钱精,天大地大,唯有钱最大,誓与金银共存亡的一类人。排骨精,用隐喻的手法指称瘦得像排骨一样的人,是对减肥瘦身美女的戏称。
第(4)类的“杠精”,专指抬杠成瘾的一类群体。
2.精~。“精~”式名词相对罕见,常见的有:精商、精人、精丫头、精妮子。
精商:商界精英、商业大亨之义。如网络文章“一代精商杜月笙”“陈六子不愧为一代精商”皆是。精人:古指巫人、纯粹高尚的人;但现代意义产生很大变化,指精明的人。精丫头、精妮子常用以指称聪明伶俐的姑娘。
当代语言中的“精”族词,既有精明算计,又有机灵心细之意,与修炼成人的妖精已有较大距离,但其实同样延续了最初的语源义,始终未脱离“超常、优质”这一核心义。他们都是历练挑拣之后远超同类的一群人。
“精”族词在语言组合形式上同样既有对传统的沿袭,又有搭配范围的扩大、结构形式的创新。除妖精、精怪等由同义语素组合产生的传统词是并列式外,更多偏正式结构的类推构词,同时又出现了缩略构词和修辞构词,充分显示出新词群在构词形式上的丰富多样。
四、基因型的语义特征
初看上述词群,数量巨大,令人眼花缭乱,但细加梳理,不难发现,无论衍生多少新词,三类词群自始至终围绕着“妖”“怪”“精”三语素各自的核心义,从未脱离各自的核心义磁场。由此,即可断定,核心义对词义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衍生过程中产生的新词新义新用法多少都与核心义有一定的联系,只不过有的显明,有的隐晦。
正如张博所言,“词源义和本义的某些语义特征犹如生物体的遗传基因,在词语孳生和意义引申的过程中既绵延不绝,又渐次失落隐晦”[37]。所谓“犹如生物体的遗传基因”其实就是核心义。王云路明确指出:“在义素的层面,核心义可以看作是一个多义词的大多数义位共有的遗传义素,贯穿各个义项,既是推动词义引申变化的内在动力,又是决定词义演变方向的制约因素。”[5]16在词的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都会受到这一基因型的核心义的影响和制约。“妖”“怪”“精”这组同义词在当代的发展,可再举几例细加体会,进一步明确核心义的基因型特点,及其对区分同义词细微差异的重要价值。
《妖刀断了 佛心动了——评三星杯围棋赛》[38]一文中的“妖刀”,是围棋高手马晓春的绰号,因其棋风近乎“妖”,着法轻灵飘逸,迷惑性强,故围棋界以“妖刀”称之,体现的正是“妖”的遗传义素:[+反常][+魅惑]。《王蔷力克“怪球手” 晋级深网女单八强》[39]中的“怪球手”指打法奇诡、令对手害怕的罗马尼亚名将尼库莱斯库,以“怪”称之,显示的是其球风产生的[+不寻常][+感觉]。再看微博文字:“她是戏骨中的戏精——Meryl Streep新作《撒切尔夫人》预告片。她的名字,本身就代表了无可挑剔的演技水准。”“戏精”一词将梅丽尔·斯特里普的精湛演技尽情展露,反映的恰是“精”的义素特征:[+优质][+超常]。
至此,不难明白,泰国那些通过变性手术化身为女性形象的男子何以被称作“人妖”,盖因其反常且具女子妖媚之姿。《山海经》中那些长着兽头人身,或人头兽身,一身毛或者鳞片,一眼就能吓死人的物类为何叫作“怪兽”。而占尽某类事物优势基因,变得相对强大的何以被称作了“精”,传说中的蛇精、狐狸精皆聪明无比,即便是对人而言,比较灵性聪明的人当然也就是人精。因此,“人妖”绝不同于“人精”,“怪人”更绝非“妖人”。
这种或隐或显的“基因型的语义特征”,也有学者将其称作“传承语素的语义聚合性”,指出“语素从产生之初,便有其意义上的规定性”[40]。说法不同,却都道出了当代语言中新词衍生受构词语素核心义影响的本质特征,反映出词汇传承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语言发展的精细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