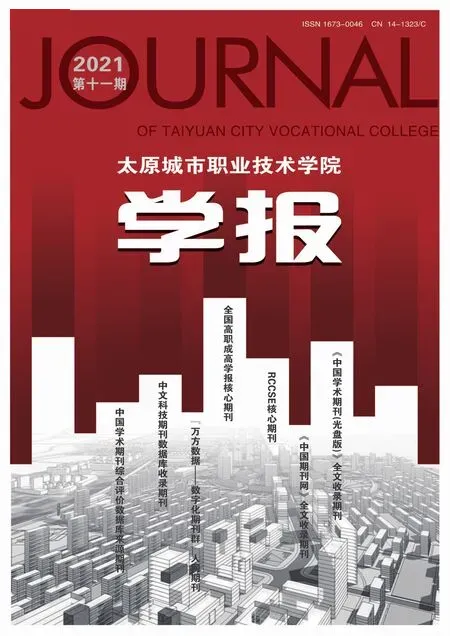电商平台限定交易行为的违法分析与法律规制
■王紫娇
(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限定交易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尤其在平台经济兴起的当下,平台经营者可以采用技术手段,通过屏蔽店铺、流量限制、搜索降权等方式来限定平台内商铺的交易行为,为本平台的经济利益“保驾护航”。随着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发展,限定交易行为也越来越集中发生在线上交易过程中,在电商促销活动(如天猫“618”“双11”)中最为常见,限定交易行为的典型表现形式即是电商平台的“二选一”行为。平台经营者实施限定交易行为的原因除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外,还在于经营者竞争意识的偏差。国内曾有电商巨头称,“二选一”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平台方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为商家提供交易机会,品牌商理所应当作出一些牺牲。但在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二选一”行为进行了违法认定,认为其构成垄断行为,作出了高达182亿元的行政处罚罚款。此案令学者们重新审视电商平台的限定交易行为,对此关注电商平台的限定交易行为,讨论其合法性,完善对其的法律规制显得尤为必要。
一、限定交易行为的基本概况
(一)限定交易行为的内涵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电商平台经营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消费者视线中,面对新兴的竞争市场,经营者为更大程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纷纷采取限定交易的方式占领市场。限定交易行为,简单来说是指经营者利用自身有利的市场地位,要求交易相对人只能与某个经营者或者不能与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排除或者限制同行公平竞争的行为。该行为既可能发生在网络平台上,也可能发生在线下实体交易过程中,但随着近些年来电商平台、移动数据的发展,这一限制竞争的交易方式越来越多地运用在互联网平台上,典型表现形式就是为大众所熟知的电子商务平台“二选一”行为。2021年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第15条明确提出了构成限定交易行为的考量因素、常见情形及正当的抗辩理由。《指南》表明了国家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关注,也体现了限制交易行为可能因排他性而阻碍市场竞争,例如“二选一”实质上就是一种排他性的纵向非价格限制,需要得到监管部门的重视和规制[1]。
(二)限定交易行为违法认定的复杂性
电子商务平台的限定交易行为在构成违法时,既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可能构成垄断协议,还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我国《反垄断法》对限定交易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第17条指出了限定交易的两种情形,即交易相对人“只能与提出限定条件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指定的其他经营者进行交易”。实践中由于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的地位、具体交易内容等情况的复杂多样,并非每一种限定交易行为都符合上述的两种情形,举例来说,“经营者要求交易相对人不得与指定的某一经营者进行交易”,这种对交易的限制也存在着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情形,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但却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形。同时,随着网络数据、技术条件的发展,限定交易行为有时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经营者如果不是通过签订协议等明确的方式对交易相对人进行限定,限定手段通常不易被察觉。不但需要说明的是限定交易行为只是对某一类交易行为的概括称呼,一些行为看似是经营者限制了交易相对人的行为,实际上可能并未影响到本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也就不属于竞争法上定义的“限定交易”。因此,不能对实践中所有涉及到限定交易的行为一概认定为违法,而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和构成要件加以分析判断,对真正的违法违规的限定交易行为进行规制。
二、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的要件分析
(一)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的基本要件
实践中限定交易的方式有多种,并非所有对交易的限制都构成竞争法上的违法,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同时,限定交易的行为可能违反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不同的法律规定对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的要件规定的不尽相同,因而对限定交易行为的违法性判断要结合具体的情形来判断。
首先,限定交易要求经营者实施一定的行为,且该行为达到了限制对方的效果,如经营者对交易相对人作出了限流、关键词屏蔽等制裁或在提供服务时恶意不兼容。如果行为人仅向相对人作出了明示或暗示的强制意思表示,而并未采取相关限制其交易的举措,理论上虽然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外观,但实践中较难认定为违法并对其进行规制。
其次,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还需要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后果,虽然特定的交易行为可能一影响到市场竞争,监管机构就会对此进行干预,但由于竞争的两面性,当代的反垄断分析总是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合理原则。合理原则要求在判定竞争过程中行为违法时要充分考虑行为意图、行为方式以及造成的后果。“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应当采用合理原则。在这种背景下,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包括限定交易的认定应当进行更多的实质判断。”[2]实质判断的一个关键即在于对存在竞争损害、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的认定,只有对竞争秩序造成了损害,反垄断相关的规制才会介入。
最后,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还要求行为人没有正当的抗辩理由。“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允许当事人提出‘正当理由’抗辩,垄断协议的认定也允许当事人提出豁免申请。”[3]限定交易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一方面这种行为可以增加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基于互联网交易中的“锁定效应”能够提高平台的整体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平台长期稳定地经营可以积累大量固定的用户,平台的行业竞争力增强,基于“网络外部性”原理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指南》第15条也列举了四项抗辩理由,并设立了兜底条款,因此在对限定交易进行违法认定时,还需要对行为带来的正负效应进行具体衡量,只有不存在正当抗辩理由时,才可能认定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
(二)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的特殊要件
《反垄断法》早已在具体条文中对限定交易行为作出了规定,第17条明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的交易行为”,由此《反垄断法》中的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的重要前提是,行为人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当经营者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从事限制交易相对人交易的行为,排除、限制竞争的可能性更大,且造成的危害更严重,因而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人采取的限定交易行为,可能由于其行为的不正当性适用其他法律,如可能会适用《反垄断法》中有关垄断协议的规定。除此之外,限定交易行为若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或《电子商务法》规定的违法行为,也不需要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要求行为人以不正当方式“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服务”,《电子商务法》在规制交易行为时要求“电商平台具有交易上的优势地位”[4]。因此,市场支配地位这一违法认定的特殊要件,只在《反垄断法》分析框架下需要考量,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的规制相较于另外两部法律更为严格,所以适用标准也更高。
三、限定交易行为法律规制的困境
(一)相关法律的适用存在交叉
限定交易行为由于自身的类型多样,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也并不局限,主要适用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领域的特别法《电子商务法》,还有一些配套的法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后者主要是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但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执法实践来看,二者的界限并非绝对的明晰。在对限定交易行为的竞争规制时,首先要确定适用哪一部法律,市场支配地位要件的有无为限定交易行为性质的判断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也只解决了初步识别的问题。当限定行为违反《反垄断法》时,往往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正当性,但在对不同法律涉及限定交易的主要条款进行甄别适用时,无论是技术上还是要件构成上都有较大的难度。例如,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偏向价格协议,而限定交易行为往往是非价格协议,垄断协议对限定交易行为的规范依据因此不太明晰,适用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只能适用兜底条款[4]。由于《反垄断法》关注的是违法性较严重的垄断行为,限定交易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框架尤其较难搭建,适用条件苛刻,并且几部法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界限模糊有所偏向。实践中由于规制条款过于分散,相互之间缺乏衔接性,导致对限定交易行为的定性缺乏体系性的法律框架和明确的适用指引。
(二)行为人市场支配地位较难认定
在《反垄断法》第14条的分析框架下,限定交易行为的认定首先需要认定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一直是学界讨论焦点。一方面,相关市场本身受到技术创新、行业交叉等因素的影响,界限愈发模糊;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使相关市场的范围更加难以界定。除了市场份额这一常用指标外,还需要“结合经营者的资财状况和控制数据的能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难易程度、相关市场的准入难度等因素来综合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5]。在电子商务平台领域,暂且不论相关市场的界定难,即使是能够确定经营者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也不必然意味着其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修订草案中还提出了“网络效应、锁定效应、规模经济”等因素,以期更好地认定互联网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网络新因素虽然对互联网中的市场地位认定作了进一步补充,但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一补充使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时要考虑的因素和难度变得更加复杂。
四、限定交易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
(一)引入“相对优势地位”概念
我国竞争法中只有市场支配地位概念,而未引入市场优势地位概念。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改时曾在草案中增加了“相对优势地位”条款,但因为学界和理论界争论过大,最终在草案送审稿中删去了这一条款。在理论上,学术界对相对优势地位作了诸多研究探讨,执法机关执法时也会考虑市场优势地位的存在,并且伴随着网络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困难,考虑引入市场相对优势地位这一概念或许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相对优势地位强调的是交易相对方对另一方的数据、平台等资源的依赖,界定起来相较于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较容易,不需要对相关市场、市场份额进行严格的分析认定。除此之外,二者还有一个区别在于相对优势地位主要针对的是交易双方之间,更具有个案针对性,市场支配地位更多的是市场中的竞争者之间的地位比较。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将相对优势地位纳入到反垄断法中进行规制,还可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框架进行借鉴[6]。我国也可借鉴域外的经验,结合国内理论成果、执法经历,在《反垄断法》或相关配套法规中引入这一概念,这将有利于限定交易行为的违法认定和法律适用。
(二)明晰竞争法有关条款的具体适用
限定交易行为在竞争法上的适用具体表现为:在反垄断法的分析框架下,如果交易双方基于合意达成协议、决定或者具有协同行为,应当主要考虑适用《反垄断法》第14条第3项“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如果行为人利用自身市场支配地位强迫处于较弱地位的交易方按行为人意愿进行交易,则可能适用《反垄断法》第17条第4项“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规定。在电子商务平台对于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如限流、恶意不兼容等,以达到限定交易目的的行为,可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中“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服务的行为”的规定。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二者的适用区别,前者强调行为人的市场支配地位,后者强调电商平台的技术手段,同时《反垄断法》因适用标准严格,违法性必须达到较高程度才可适用,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相较于《反垄断法》和《电子商务法》适用范围最窄、难度相对低。违法性的程度可通过行为人违法交易额、违法持续时间、限定交易范围等因素来综合考量。限定交易行为在适用《竞争法》规制时,最关键的即是对限定交易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分析,结合个案不同违法情形和违法程度作出法律适用,应当说二者在规制时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虽然界限不是绝对的明晰,但还是相对较容易达成协调。
(三)明确竞争法与《电子商务法》的规制范围
《电子商务法》主要运用于电子商务领域的违法行为,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看作是特殊法,是除竞争法外规制电商平台限定交易行为最为重要的法律,但《电子商务法》在适用时与《反垄断法》有重叠交叉部分。《电子商务法》第22条属于“转致条款”,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本质上还是对《反垄断法》的补充,一般在特殊的考虑因素下优先适用,如经营者的技术优势、用户数量等。第35条是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交易中附加不合理条件的专门规定,交易相对人如果不同意附加的条件,也可能造成限制交易的情形,在竞争法未引入相对优势地位概念时,该条可以作为对限定交易行为中相关市场优势地位认定的补充依据。但同时第35条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条款中的“不合理限制”和“不合理条件”语意模糊,对于限制行为是否合理的判断又容易与《反垄断法》第14条发生竞合,因此有必要对《电子商务法》第35条的内容进行限缩解释[7],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否则可能会造成架空《反垄断法》第14条的后果。此外,《电子商务法》规定中的法律责任较轻,面对限定交易行为对竞争损害后果严重的情形,在符合《反垄断法》规制要件时,应当优先适用更严格的标准和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电商平台限定交易行为的法律适用,首先要严格各种违法情形中违法要件的构成分析,对于兜底条款、补充性条款不能因其不是主要具体的依据就随意使用;其次,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相对而言较为容易,但这并不意味其为《反垄断法》无法规制的限定交易行为的兜底,该法中第12条第2款的“技术手段”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保护目标;最后,要注意《反垄断法》与《电子商务法》之间的竞合,在执法技术上可以采取限缩解释的方式对二者的适用进行区分,做好在电子商务领域二者的协调。
五、结语
近年来,电子商务平台的迅速发展使得市场竞争环境乱象丛生,限定交易行为早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一方面,对竞争秩序的维护、对消费者福利的保护要求我国竞争法不断细化、创新对复杂实际情况的适用;另一方面,网络平台、技术手段的发展也给经营者们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对限定交易行为的规制有利于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现实情况的复杂多变要求立法、司法、执法上更细致的规范、更明确的判定标准、更公平的考量因素,在面对多法交叉的情形时应当做到法律法规的协调和闭合,筑起规范的高墙。限定交易行为,主要还是在《反垄断法》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分析,同时执法机关应做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三者之间的衔接,使其无论是一般情形还是特殊状况,都能得到妥善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