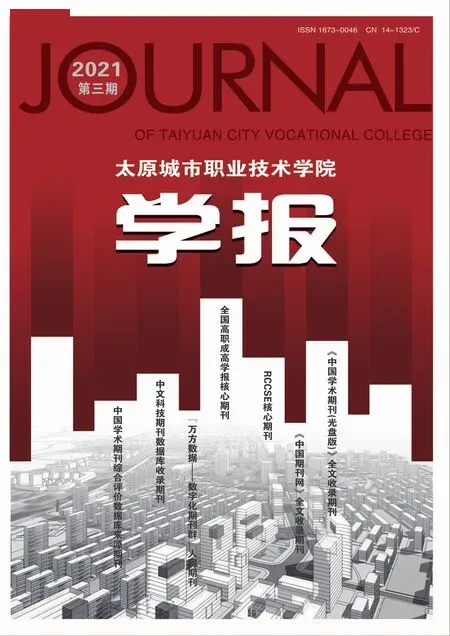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残障大学生生命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赵 星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辽宁 沈阳 110173)
教育就是培养人的活动,我国的教育体系在经历了传统的“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后逐步向素质教育转变,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中对学生素养的培养、道德的熏陶、身心健康的塑造,总而言之就是“全人”的教育。生命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实施的载体,生命教育已经成为了大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和终极性教育要求。近年来,我国高校大学生的“生命困顿”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全民族遇到重大的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的危机事件面前,越发突出了生命教育的重要性。2003年的非典、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两场巨大的公共安全危机事件面前,我们越发地认识到生命教育对于教育体系的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挑战。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特殊教育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特殊教育实施的对象具有保证自身安全的能力,具有应对危机的应激处理能力,具有在“危机”常态化社会背景下的维护自身健康和调整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能力。本文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残障大学生生命教育的课程体系。
一、积极心理学内涵解析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有一门关注人类优势发展与潜能发挥、培养人类积极心态与幸福感、挖掘人类发展力量的心理学研究的运动越来越影响人们的生活,发展的势头也越来越壮大,这就是积极心理学。最新的积极心理学研究从乐观主义研究的角度,认为乐观主义生命意义的研究就是要培养人们的积极态度,帮助人们甄别负面想法,改变对自己或他人具有伤害性的想法,调整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寻找主观幸福的体验,培养积极的、正面的解读事物的认知方式。所以,积极心理学的本质目标是寻求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文关怀,这也是积极心理学与生命教育在研究理念上的不谋而合之处。
二、残障大学生生命教育
(一)我国生命教育的发展
确切地说,我国的生命教育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借鉴国外生命教育研究的成果,结合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大陆(内地)开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根本就是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在开展素质教育的进程中,追求身心和谐发展的健康教育与知情行统一的全人教育必然成为教育的主题。相关的生命教育活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生命教育的内涵,探讨大学生生命教育缺乏的主要因素和原因,探讨生命教育的具体实施目标、实施内容体系及实施要求和效果的验证等[1]。其发展比较迅速,理论与实践研究经历了从引进到创新的过程。尤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了对于学生安全教育的具体要求。纲要中将对于生命的教育、培养学生安全观的安全教育、热爱祖国观的国防教育、生态观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教育共同写入发展的规划文件中,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内容也共同成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重大主题。这些要素将共同致力于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有机融合,共同致力于培养具有高尚道德、高水平智力结构、强健的体魄、高度的审美和价值观体系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此外,《“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也将老年人的生命教育内容写入规划,2016年颁发的《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也都有关于生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可以说,我们的政府已经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愈发地重视生命教育,生命教育也将被纳入公民的道德教育体系,通过心理育人的课题形式走进人民的生活和生命发展实际。
(二)残障大学生命教育的问题亟待解决
大学生这个群体,是一个主观上自我认知的成熟群体,在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对于我国的教育体系而言,生命教育在中小学有被提及,但是对于高等学校的生命教育就不那么被重视和“被需要”[2]。其实,对于高等学校中的残障人群体,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伴随着“危机”。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也许存在小时候因为被家人“过度保护”或“忽视”的危机,到了上学的年纪被同学“嘲笑”或“冷落”的危机,对于残障的自我认同的“危机”,家人对于自己残障的接纳程度的“危机”。在这样的过程中,残障大学生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的“励志成长史”也是一部具有“血泪的危机成长史”。所以,对于残障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和生命质量的问题是越发地需要我们关注的。大学生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自残”“自罪”“自杀”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一些暴力事件背后隐藏着他们对生命的漠视和冷漠,不禁更加地令社会为之痛惜,扼腕叹息于生命的脆弱。
生命是开展生命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任何的生命教育都是始于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理解,她是教育的原基点。生命的教育绝不是某一个学科和领域的“独宠”,它必然是涉及到人的生命活动开展的方方面面、综合诸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与生命有关的那些主题研究都纳入生命教育范畴,构建多学科的“限定”。针对社会治理中的一些乱象,如情绪失控对社会治安的影响、激情犯罪下的无法挽回的恶果、扭曲人性带来的危害性事件、漠视生命引起的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损害、价值丧失而导致的社会公德性问题、良知泯灭造成的犯罪性事件等,生命教育也必将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与我国的道德和法律等约束机制一道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剂良药。
大学生特别是残障大学生的生命教育目前还处于发展的雏形阶段,完整的生命教育体系课程也尚未形成各学校公认的标准和尺度,在教学的内容上也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和内容。因此,建构一套适合于残障大学生的生命教育课程体系尤为重要。
三、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残障大学生生命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积极心理学是追求人类获得快乐和幸福的一门学科,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下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感受自身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3]。而生命教育的意义也在于人们学会自我的关爱与照料,在不断提高自我效能感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生命价值,珍惜自身的生命意义[4]。这与积极心理学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所以我们探讨在积极心理学的视野下建构残障大学生生命教育的课程体系是合乎学科发展规律的。
(一)积极关系体系下,构建“了解生命之源、体悟生命之真”的生命探索课程体系
人类对于生命的认知,是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深入的过程。帮助学生用探索的心态了解生命起源之源、生命进化之艰、生命伦理之重,引发学生思考残障人士人类生命进化的关系。设置讲述生命故事环节,如“张海迪: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史蒂芬·霍金:当代的爱因斯坦”,让学生们在榜样目标的驱使下,坚定自己的成才理想。“生命真美好”之生命强音,以回音壁的形式帮助学生用“心灵鸡汤”润泽自己的心灵,开启自己“有意义的人生”。最后,在这一模块中,同学们还可以通过自我探索的方式,开展心理活动如“跟萨提亚学沟通”“探索生命的长度”来引导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热爱生命。
(二)在积极人格的基础上,学会“享受生命之善、扛起生命之责、抵御生命之艰”的积极心态课程体系。
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很容易把爱给了别人,却吝啬于把爱留给自己。以仁爱之心关照自己,寻求自己人生的积极意义是生命教育的出发点,教会学生尊重自身生命的尊严,认真体验生命中的幸福感受,学会抓住生命中的幸福瞬间。即便是自己尝尽了人生的苦涩,仍然要在逆境中尊重自己生命的存在价值。好好地爱自己、好好地生活是我们赋予自身的生命的权利,也是我们自身生命所扛有的责任,在各种危机和挑战面前,那些痛苦和眼泪将成为我们生命的“调味剂”。通过讲述“钟南山:新冠病毒疫情中的逆行者”“中国机长:敬畏生命”“黄美廉:一个热爱生命的残障人士”等生命故事,让残障大学生在自身的发展中,在自我的人格建构过程中真正地拥抱生命,热爱生活。用“怒放的生命”“寻找生命的出口”“生命且行且珍惜”等心灵鸡汤式的文字,给残障大学生的生命浇筑力量。在心理驿站中,通过“人生五样”“涂鸦日记”“自我催眠——给心灵放个假”等形式的自我心理放松技术,来建构积极人格,培养积极心态,拥抱自己美好的生命和积极的生活。
(三)在积极的情绪中,构建“发展生命之美、规划生命之梯”的积极情绪调整课程体系
“梅花香自苦寒来”,生命之美在于不向命运屈服的抗争精神,一个人拥有了乐观、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拥有了丰富、纯净、活泼的内心世界,拥有了开朗、幽默、机智,那么这个人脸上就会流露出灿烂的笑容,而这样一种乐观的心态,是很多残障人士所稀缺的,因而值得备加珍贵。构建生命教育系列课程,旨在于帮助残障大学生激发生命潜能,提升生命品质,在实践中接受挑战,在计划的制定中激发自己的潜能,打造更加出色的自我。
生命在于“真”,而情调在于“美”。体验生命的意蕴,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发现生命的“情调”,活出自己的生命情调。通过讲述“尼克胡哲:生命的演讲者”“谢坤山:台湾著名口足画家”等生命故事,用那些“美丽的生命故事”来鼓励残障大学生润色自己的生命。在“感悟生命之美”“规划今天的道路,走出明天的精彩”等生命的强音中蓄积自己的生命力量。通过精心设计的一些心理活动“彩绘曼陀罗”“踏上你心中的岛屿”等活动,让残疾大学生们在自己的心田中规划自己美好的生命节奏,演绎自己美妙的生命曲调。从而达到启迪残疾人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我自己”、实现“我之为我”的生命价值,展现出生命中全部的爱和闪光点,焕发出自己生命的光彩。
四、结语
对于生命教育的课程体系,我们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构建了积极情绪、积极人格、积极关系体系下的残障大学生生命教育课程体系[5]。对于课程的效果评估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进行评估。首先,残障大学生自身的自我评估。可以通过自我评价的方式,从认知和情绪的角度,观察其对于生命的理解和认同。其次,从量表和问卷的角度,了解残障大学生对于生命的主观幸福感、对于生命观的态度、对于生命价值观的评价等,作出相应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等反馈信息。再次,通过周围人的评价,从重要他人(老师、同学、家长)的视角看待残障大学生对于其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觉知和体悟。最后,通过活动的视角,从行为的角度来统计其对于生命教育活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可以开展一些生命教育类的团体活动,从残障大学生的参与程度和参与频次的角度,了解生命教育课程体系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