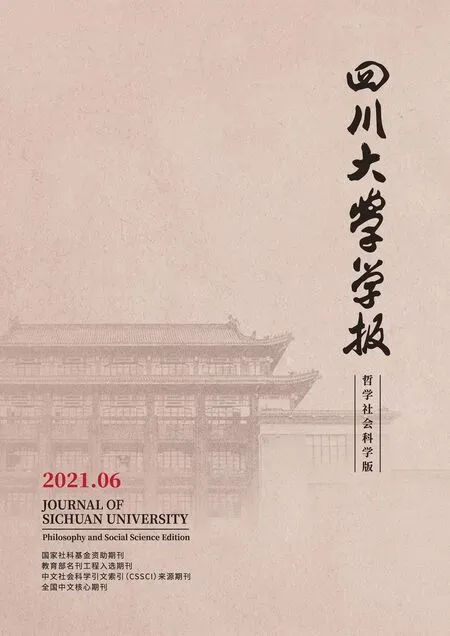文化转向与“经典”论争
——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论为中心的讨论
汤 黎
作为人类一种最为典型的精神产品,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文本环境的历史性,同时也是显示文化现实的重要方式之一。20世纪中期始于欧洲的文化研究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开始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如何影响文学的书写、传播、接受等环节,因为文学无论是作为知识还是作为文化构成要素,在历史发生学和认知谱系中均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具体来看,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可以体现在关于文学“经典”范畴的讨论上,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经典”范畴的拓宽和重新划分密切相关。因此,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文学“经典”等问题一直是核心议题。厘清这些核心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发展脉络,对理解和把握当代文论的理论话语,以及探明文论未来的走向,显然有着重要作用。
文学“经典”之争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文化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美国学界曾围绕文化、文学书写、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经典”等展开论争,产生了一大批关于“经典”的论著,(1)例如亨利·L.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的《松散的“经典”:关于文化战争的笔记》(Loose Canons:Notes on the Cultural Wars, 1992),讨论文化战争和拓宽“经典”的问题;约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的《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Cultural Capital: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1993),详细论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化资本阐释范畴中文学体制和“经典”之间的关系。此外,一些学者对“经典修正”(Canon transformation)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在其影响巨大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中表明了这一立场。反映出随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本边界的扩大、文化资本构成的变化等因素,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范畴,甚至“经典”本身所面临的诸多质疑。大致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也开始展开对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讨论。其中,以陶东风、周宪、金元浦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倡导推进文化转向的步伐。如陶东风认为,文化研究“有助于打破文学研究和批评,尤其是和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2)陶东风:《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文学前沿》2000年第1期,第193-194页。另外一些学者则对文化转向这一趋势仍抱有质疑的态度,如童庆炳就对“文化转向”以及文艺学的“扩容”和“越界”提出了质疑。(3)参见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97-98、102页。总体来看,对于文化转向这一议题,国内学者大多是梳理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及中国学界的理论接受状况,而具体讨论美国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者则相对较少,且偏重于对美国文学“经典”论争的研究上。(4)如程锡麟、秦书珏的《美国文学经典的修正与重读问题》(《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4期,第61-67页)从三个方面对20世纪60至90年代美国文学经典修正和重读问题进行了概述;季峥的《经典建构——以〈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研究为例》(《外国语文》2012年第3期,第20-24页)、金文宁的《从〈诺顿美国文学选读〉看美国文学经典重构》(《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30-38页)皆以《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为例探讨文学“经典”问题。尽管随着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关于“经典”的讨论日益广泛,既有对“经典”重构的呼吁,也存在捍卫“经典”的声音,(5)如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第6-9页;龙迪勇:《经典的黄昏》,《读书》1995年第1期,第141页;胡友笋:《经典的品性与守望》,《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54-156页。但在“经典”和学术体制、政治话语的关系方面尚欠透彻。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聚焦20世纪90年代这一美国文学理论范式冲突剧烈的时期,梳理其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经典”论争,探析其中所涉及的学术体制问题和政治话语。
一、文化转向与美国文学研究的范式变化
文学的活力来自其所属文化,文学书写与文化背景紧密关联,“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订的文化地形图上新的区域”。(6)沃尔夫冈·伊瑟尔:《走向文学人类学》,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王晓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98页。文学以突出主流文化尚未通达的领域为途径,改变了人的认知能力难以测定的、为表象所覆盖着的文化地图。文化研究涉及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以揭示和调和各知识领域的差异和分歧为目标,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研究重在考察文化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因而能够把文学书写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予以强化;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使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涉,两者之间未有明确界限。狭义的文学文本研究注重对文学语言、意象、诗学技巧、叙事策略等的分析,广义的文学文本研究则注重对社会公平性、性属、族裔、人类状况、身份等问题的探讨,就此而言,文化研究可谓是将文学日常生活化。文化研究探讨社会中的权力和知识、表征、意识形态、体制、性别与性属、全球化与区域化等问题,作为观察及阐释社会最有效模式之一,自有其深远的意义。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在美国有着其久远而复杂的原因。首先,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文化作用,因而固有的以文本、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范式,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开始被多学科跨界的研究视角所强势介入。人们并不满足于对作家进行传记式转述,或对文本内在的美学要素进行传统的审美解析,而是更关注其中所隐含的文化问题,包括“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区域群体的历史性境遇、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感知以及文化身份等重要问题。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激发了人们寻求新问题和新客体的兴趣,使注重意义生产的多领域跨界研究成为可能,也让学界开始重新思考“经典”及其与文化话语的关系,由此“经典”的再解读、“经典”形成(Canon formation)的研究等,均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此后,随着七八十年代批评理论之战的拉开,文学研究陷入了学术不稳定期,“经典”和“非经典”、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等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和淡化,经验主义认识论、文本的自足与自治、文本的统一等概念也不复存在。随之,文学研究的内容与疆界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可能性新范式而兴旺发达,意识形态、性属、身份、体制等概念在瓦解旧范式的同时又建构新的范式。文化转向后的文学研究以文本政治为核心,兼收并蓄,自90年代开始,诸如“愉悦、性别、权力、性欲、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7)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蒲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页。等与文化研究紧密相关的主题,在文学批评领域蓬勃发展。
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场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转型中,文学研究是导致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8)参见王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而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从后现代学派衍生出来的众多新兴理论学派都加入到文化研究的阵营当中。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Bernheimer Report)就以“多元文化”为标题,强调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直接挑战了在六七十年代所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精英文学传统,将文学语境扩展到文化、意识形态、种族及性别等领域,远远超出了作者、民族、时代及文类等传统研究范畴。(9)参见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王柏华、查明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2页。在此背景下,新的文学阅读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历史、文化、政治、地域、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与此同时,文化研究的兴起也为人文学科的阐释提供了新的来源——探寻文化、学科、知识的定义以及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并重新定义和形塑了文化领域。正是因为“文化研究是后现代学科的代表,也就是一个越界(crossover)、一个混合学科(hybrid discipline)、一个有创意的拼贴(innovative pastiche)”,(10)文森特·里奇:《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王顺珠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由此,文学研究不再仅强调高雅文化、道德规范、社会责任,而是一种多样化的、多元化的、混合式的研究。
然而,守旧派的文学评论家对这一时期的文化转向大多持反感的态度。如著名评论家埃登·亚当斯(Hazard Adams)就认为,“当今学术界的趋势是批评家花更少的时间讨论以前被称为文学的文本,而花更多的时间讨论各自的理论”,并且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者大都只关注政治和文化批判是由于60年代晚期政治和社会的动乱,而其持续的兴盛则是缘于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一代批评家所主导的理论兴趣。(11)参见Hazard Adams,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p.9, 6-7.在守旧派看来,人文学科研究已被市场和政治势力所主导,文学研究也难逃其宿命。他们一方面批判左派知识分子视文化政治由市场操纵、得到大众的认可则是一种“收买”的观念,(12)参见Michael Bérubé, The Left at War,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另一方面则遵循传统形式的学术体制,坚定地反对流行的理论范式。部分守旧派成员还热衷于回归新批评,坚信传统的“经典”文本体现了价值规范和想象经验,他们否定解构主义将文本意义消融于模糊的文本性的观点,同时也反对新历史主义将文本性延伸到社会语境的做法,认为批评的任务不是祛魅和破坏,而是阐明、解释和确定文本意义。
当然,守旧派的反对并不能阻挡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范式转换的大潮。随着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变化,批评家的任务也从以往单纯地对文学客体进行描述和评估,转向了更多更复杂的批评空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家、女性主义者、后殖民理论家、文化历史学家、流行文化学者、修辞学者以及左派后结构主义者等逐步形成统一战线,提倡文化研究。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末,美国大学中的文化研究热度也逐渐上升,涵盖并取代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后结构主义。此际,学界回避高雅文化而研究通俗文化算不上政治上的激进,或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而更多的是将之视为一门大众文化学科。作为一个信息资料丰富的跨学科领域,文化研究的实质是对文化实践和文化再现的学术研究,(13)参见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57页。“当文化研究开始描绘展露头角的‘新世界秩序’的全球文化时,学术界的文学视野进入了一个极度扩张的时代”。(14)文森特·B.里奇:《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王顺珠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因而,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对那些将文学艺术孤立化、神圣化的行为表示反感。如美国“当代学术左派”代表人物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在80年代的学术研究范围仅限于诗学,到了90年代就开始涉足生态、技术、知识分子等多样化的主题。罗斯的学术研究轨迹和范畴的变化,代表了其所处时代文学研究从文学文本扩展到文化文本的学术倾向。随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本内外边界的消失使得“经典”问题成为在美国学界最受热议的主题之一。
二、“经典拓宽”与“经典”之争
文学研究是“一个能够涵括种种意义、种种对象和种种实践的能指网络”,在一定时期内符合这一话语检验标准的文学作品被称为“经典”。由于文学批评话语并无明确“所指”,因而“经典”的涵盖内容也随着批评话语的变化而变化。(15)以上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第203、205页。文学的“经典”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经典”的判断标准也处于不断改变当中。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文本的“经典”化、文本内外的界限等问题遭受质疑,曾经由宏大叙事主宰的“经典”世界受到冲击甚至消解,“经典”的范围被扩大和改变,“经典”和“非经典”、中心和边缘的概念也都变得模糊不清。为了消除“经典”与“通俗”之间的界限,文化研究以通俗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寻求对社会基础、体制参数和意识形态效应的详细调查和评估。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意味着文学理论的规则和方法被运用到非虚构文本、流行小说、电影、历史文献、法律、广告等广义的文本当中。因此,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文学“经典”范畴的拓宽和重新划分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传统文学样式日益被边缘化的20世纪90年代,“经典”的价值和评判标准愈发受到挑战。早在70年代,美国学界已经出现“拓宽经典”(the opening-up of the canon)的呼声,众多评论家发起了一系列“打开经典”(to open up the canon)的活动,为“经典”范畴注入了更多元的文化色彩,比如纳入了更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的作品、许多原来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边缘文学及其他文化产品开始占据文学评论的阵地。(16)参见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0页。不少学者在建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也都积极拓宽文学的范畴,如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就明确指出:“文学从来就不只是上流社会的伟大作品的经典;它也是我们所说的‘少数’文学和‘流行’文学。然而,这个拓宽了的定义甚至也覆盖不了它的全部。它是一切作为社会实践的写作,……文学在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而且,它一直不停地在影响着我们。”(17)Frank Lentricchia,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157.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以“非经典”文化文本为客体的研究更成为普遍的潮流,文本的外化使得文学研究范畴扩大,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冲击也带来精英文化特权的丧失。与此同时,要求消除“经典”评判标准中的精英和等级意识的“去经典化”运动也在进行当中。(18)刘意青:《经典》,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
詹姆斯·D.亨特(James D.Hunter)研究认为,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战争的核心是“正统派”和“进步派”之间的矛盾,(19)J.D.亨特:《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安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5页。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典”之争自然也是如此。美国学界对文学“经典”的新阐释与文化转向息息相关,(20)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3页。80年代后期美国文学研究的重心已集中于理论探讨,90年代文学理论问题也随着文化转向有了相应地拓宽,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盖茨对非裔美国文学在理论上的建构。盖茨在《松散的“经典”:关于文化战争的笔记》中指出,美国的各种亚文化的增殖、文化的多元化让“经典”重构成为必然,而“经典”并非是不证自明的、绝对的或中立的。在他看来,西方所谓正统的“经典”是特权的、专断的,“回归经典”的号召实为重返白人中心主义的旧秩序,而其中的非裔美国人“被奴役、失去声音、看不见、不被再现、也不能被再现”。(21)参见Henry Louis Gates, Jr., Loose Canons:Notes on the Cultural Wars,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2, 35.与盖茨同道,格雷·S.杰伊(Gregory S. Jay)、杰拉德尔·格拉夫(Gerald Graff)、安妮特·科洛德尼(Annette Kolodny)等一众批评家,也都致力于将以往被边缘化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纳入“经典”的范畴。他们的“这些对于种族和性别的文化产品的理论描述,将有助于打破那些已经由白人男性建立起来的,在总体上作为美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真假参半的理论”。(22)弗兰克·克莫德:《经典与时代》,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实际上,80年代后期,艾瑞克·D.赫希(Eric Donald Hirsch)即已指出,人文学科应该多样化,因为文学、历史、人类学的特征之一,就是“他者性”(otherness)导向,文学“经典”一方面应当改变,另一方面又应当被抵制,才能适应多元化的语境。(23)E. D. Hirsch, Jr., Cultural Literacy: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p.26.
然而,在一些守旧派的批评家看来,“经典”重建造成了真正老“经典”的萎缩,而文化转向所带来的“经典”范畴的变化则会让文学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传统的“经典”标准和范畴不乏捍卫者。有些捍卫“经典”的批评家持较温和的态度,认为过去的“经典”选取并未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反倒是一系列冲击“经典”的潮流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反“经典”的派别实际上也默认了传统“经典”的存在。(24)参见刘意青:《经典》,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86页。但同时也有部分极端的保守主义(ultra-conservative)评论家强烈号召维护“经典”的纯粹性,回归单纯的文学审美。如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nett)就在其被保守派奉为指导思想的《恢复遗产:人文学科高等教育报告》中哀叹,西方文明的“经典”文本正在遭受批判,并且被更差和更不重要的文本所取代,因而他呼吁,曾经构成永恒真理和价值的文本必须代代流传。(25)参见William Bennett, To Reclaim a Legacy:A Report on the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1984, p.1.哲学家艾伦·D.布鲁姆(Allan D.Bloom)也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美国高等教育充斥着自由主义主导的各种“政治正确性”的教条,由此造成的反对欧洲传统和“西方经典”、排斥白人精英的倾向,最终将封闭美国精神。他认为,美国出现的种种新思潮引发了道德和社会问题,暴露出美国高等教育忽略人文传统而面临知识领域的危机。(26)参见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译序”,第10页。
此外,对于“经典修正”(Canon transformation)一些学者也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如耶鲁学派重要代表布鲁姆就拒绝将文学审美降为意识形态,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这在他的名著《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有充分反映。作为以往的解构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步入20世纪90年代的布鲁姆对当时的一些流行理论大都持批评态度。例如,他把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以及符号学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因为这些理论常常主张为了实现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而这是布鲁姆所愤恨的。在他看来,西方文学界的高雅品位业已丧失,低劣的文学和大众趣味充斥整个社会,“经典”已被“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他认为大众媒体的发展,是文学衰落的症候,也是进一步衰落的缘由,20世纪末是文学和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文学规范处于混乱当中:“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充满着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他指出,文学“经典”证实了文化焦虑,并给予这些焦虑以形式和连贯性,而世俗“经典”从来都是精英之作,且从未封闭过其疆域,所以“破解经典”之举实属多余。(27)以上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汪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409、416、26页。布鲁姆的批评话语透露出90年代美国文论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内在矛盾,即坚持审美理想和精英道路的保守派的反对理论倾向,同号召理论参与政治的理论支持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包括“经典”在内的种种论争,其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直存在的、对文学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功能的论争,从中也折射出人文学科危机之下文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必要性。
三、“经典”论争与大学体制
美国文学界的“经典”之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校园中的美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不可避免地和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相关联。格雷戈里·S.杰伊(Gregory S.Jay)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益激烈的文化战争业已入侵到美国文学的教学领域之中,诸如“文化遗产”“经典”“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主义”等术语的争论在课堂上频繁出现,文学教学成为将社会、政治、道德甚至宗教观念传授给学生的途径之一。(28)以上参见Gregory S. Jay, “Introduction: Making Ends Meet,”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War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 4-5.此前,保罗·劳特(Paul Lauter)已经指出,教育如同其他的文化体制一样,是一个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的权力场域,就文学“经典”的变化及其相关问题而言,既有布鲁姆和班尼特等知名的保守主义学者坚持“捍卫经典”,也不乏坚持文学批评精英化和专业化、致力于将各种“理论”渗透进人文学科的学者,以及希望建构以种族、性别、阶级等重视差异的文学课程、让大学更多地参与民主进程的学者。他还从文学专业化和“经典”的关系、大学和民主国家的关系等方面,讨论了美国大学文学体制与“经典”争论的问题,认为“经典”之争把文学研究从狭窄的专业化问题推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世界。在他看来,重构“经典”就应该努力反对那种以狭窄的视野来看待西方“经典”、只重视教学法视角而规避“经典”价值的学术形式主义实践,以及用新的“经典”来代替旧“经典”的做法,并且认为布鲁姆、班尼特等人所维护的“遗产”只是带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精英的文化遗产,而要避免“让美国精神走向封闭”,应该做的是接纳不同的话语。(29)以上参见Paul Lauter, Canons and Contexts,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ix,169, 285.
“经典”之争对大学教育体制的渗透不仅表现在课堂教学上,作为大学文学教材的各种美国文学选集更是集中体现了“经典”之范畴及变化。例如,著名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TheNortonAnthologyofAmericanLiterature)在1979年首次出版时,选入了22位白人女性作家和8位黑人作家;在1985年的第2版中则选取了23位白人女性作家、9位黑人男性作家和5位黑人女性作家;在1989年的第3版中选取了32位白人女性作家、8位黑人男性作家、5位黑人女性作家和1位墨西哥裔作家。到了1994年的第4版,增加了早期航海家叙事和印第安故事的篇幅,扩充了印第安土著的口头和书写传统,还加大了菲莉丝·惠特利(Phyllis Wheatley)、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凯特·肖邦(Kate Chopin)等人作品的篇幅,并增添哈丽雅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等7位新女性主义作家。1998年的第5版又增加了以少数族裔和女性作家为主的38位作家,早期后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也有所增加。从选集第1版主要以“欧洲的、过世的、男性的、白人的”作家为入选标准,到逐渐加大女性、少数族裔等弱势作家群体及其作品,并相应地缩减传统标准中的“经典”比例,可以看出其中的变迁。不仅如此,桑德拉·M. 吉尔伯特(Sandra M. Gil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bar)于1985年合编了《诺顿女性文学选集》(TheNortonAnthologyofLiteraturebyWomen),并在1996年再版,该选集意在为女性文学获取话语权,建构女性文学自己的“经典”谱系,收录了诸如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汤亭亭、格洛丽亚·安扎杜尔(Gloria Anzaldua)等非裔、华裔、墨西哥裔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1996年,盖茨和耐丽·麦凯(Nellie McKay)又合编《诺顿非裔美国文学选集》,选入120多位非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并以附光盘的形式展现了黑人口头文学传统。这些专集的出现,更明示了“经典”范畴和选取标准的扩大化。
同样著名的首版于1990年的《希思美国文选》(TheHeathAnthologyofAmericanLiterature),也致力于“重构美国文学文本”,把“经典”和“非经典”都囊括在内,以“尽可能地展现美国文化的多样性”的努力,试图解决大学文学教学中所关注的“少数族裔在哪里”“女性在哪里”等问题。这部多达5500页的文选的问世被视为一个重要标志,即白人话语所统治的美国文学“经典”与多种族文学遗产之间达成了妥协,同时也铸就了美国文化观念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呈现了对美国文学多样性的关注,可谓是一项“社会文学运动”。文选中选入了4位黑人男性作家和包括5位黑人女性在内的33位女性作家,让诸如“哈莱姆文艺复兴”等过去被压制的文学话语发声,还在增加边缘作家群体的同时,大幅缩减了以往的“经典”作家如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rancis Fitzgerald)等所占的篇幅。在1994年的第2版中,主编还宣称文选所呈现的美国文学的“新世界”团体是多种族和多文化的,包含了红色人种、白色人种和黑色人种的文学。(30)以上参见Paul Lauter, et al., eds.,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nd edition, Vol.2. Toronto: Heath, 1994,pp.xxxii-xxxiv, 18.在此后的几次改版中,选入的文学经典范围也一直不断扩大,纳入了庶民文学、女性文学、非裔美国文学、亚裔美国文学、西班牙裔美国文学等类型,并涉及种族暴力、同性恋、虐童等以往禁忌的题材,体现了“经典”范畴的扩大,以及其背后的文学话语更为民主化、多元化和某种程度上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此外,1987年首次出版的《哈珀美国文学》(TheHarperAmericanLiterature)也在序言中宣称要重审“经典”,以拓宽美国文学传统的固有疆界。为此编者们选入了印第安民间故事,以及西班牙裔和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混杂了从形式、社会历史、地理、种族、性别等不同角度进行的分类,抹去了以往固有的边界划分,其1998年的第3版涵盖了更多样化的文学传统和作家作品。
从“政治正确性”角度而言,少数族裔和女性文学选集为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补充性的叙述,更可以通过“补救愤懑”对“经典”进行重构。因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各类文学选集,大都关注建构和呈现以往在经济上和社会层面被否定、压制和边缘化的文化群体的文学叙事。到了2000年,马克·谢尔(Marc Shell)和沃纳·索勒斯(Werner Sollors)主编的《多语言美国文学选集:原著及英译》(MultilingualAnthologyofAmericanLiterature:AReaderofOriginalTextswithEnglishTranslations)出版,该文选发掘了许多非英语美国文学,从地理区域、类型和语言上打破了历史上以欧洲为中心、与英语相捆绑并限制在东海岸的文学,成为拓宽美国文学经典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以上这些选集前后相接续,又都以美国文学教材的形式进入教育体系,成为文学体制话语的载体。同时,这些文学选集在编选和改版过程中体现出的“经典拓宽”,也是“经典”论争的有力佐证,展现了美国学界重新叙述和重新建构“经典”,并以此突破体制化和固化的白人精英“经典”之尝试。
四、“经典”标准与政治话语
“经典”产生于权力与知识的合谋,“经典”范畴是权力话语的斗争场域,故“经典”问题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体制等问题密不可分,“经典”背后是不同的政治取向。由于“文学批评根据某些制度化的‘文学’标准来挑选、加工、修正和改写文本,但是这些标准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争辩的,而且始终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因此从某一层面而言,按照“制度化”标准而选取的所谓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实为特权阶层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刻形成的一种建构。(31)以上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第202、11页。批评话语本身是一个将符合其标准的文学作品首先“经典”化的文学制度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制度的规训和意识形态话语。“经典”之争是对过去的文学作品重新予以定位,而这种状况同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政治正确性”有关,正是在此背景下,“经典”所代表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被批驳为白人精英对边缘群体话语权的剥夺,而这种认识实际是对男性白人话语霸权的社会生成机制的反拨,体现了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焦虑的抵制。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带来了政治层面上的悖论,此种悖论与“经典”的论争也息息相关。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进程中,文本的泛化跨越了精英与大众、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从某一层面而言,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等同,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有利有弊。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在广告、时装、生活方式、购物中心和大众传媒中,审美与技术终于互相渗透了,而政治生活则被改变成了某种审美景观”。然而,在以消费主义、大众传媒等为主导的后现代文化中,政治意识形态从未缺席。后现代理论根植于一批具体社会实践和机构之中,其本身就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在众声喧哗的后现代语境中,理论之间的异质性和相互的矛盾增加了其指导实践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后现代理论提倡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又和社会实践脱不了干系。因而,文化研究的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总体化所带来的种种恐怖之‘激进’抵抗而提供出来”。(32)以上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第237、239页。文化研究的包罗万象,使得理论在超越文学文本的藩篱而进入生活方式、社会价值、群体认同等领域时,不可避免地同政治权力等问题相交织。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渗透到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立场、意识形态、社会力量、经济运行机制、传媒和符号的指意过程等因素都被纳入文学理论的范畴,让文学研究领域对权力与话语的关系空前重视。(33)参见王晓路:《理论与文本的悖论:当代西方文论的境遇》,《中外文化与文论》第 10 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7-186页。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涉与融合、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经典”评判标准的变化,都体现出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联。
“经典”评判标准和范畴,往往体现其时代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如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之争中,构建在身份基础之上的文化民主化的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认同,然而到了90年代,杰洛瑞就在其《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一书中指出,以身份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将少数群体排除在权力行使和政治表述的团体之外。他借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资本”的观念,提出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必须将文化资本的分配考虑在内,而不应仅将身份问题作为考虑的中心,并且主张把“经典”建构的问题与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联系在一起来理解。他认为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经典”才会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经典”范畴应当考虑到文学的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价值和功能,即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建构“经典”,将审美的和政治经济的双重话语视为客观的、历史决定的社会现实。杰洛瑞强调审美趣味的阶级性,推崇一种“自在的审美主义”(aestheticism unbound),认为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大众化是解决“经典”问题的根本所在。(34)参见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江宁康、高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他还将“经典化”置于文化资本的语境中进行分析,挑战了传统的“经典化”问题之理论框架,批驳了布鲁姆在讨论“西方正典”时把文化资本视为无意义的文辞的观念。(35)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410页。在文学体制化的进程中,文学“经典”作为文化资本的表征,承担着审美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双重功能。
“经典”作为政治话语的重要表征,与权力又形成同谋的关系。“经典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以别的方式去处理难以处理的历史沉积物”,而这也导致推崇“拓宽经典”的文学批评家试图把文学理论的“破坏性的和深刻的政治潜力”释放出来。(36)弗兰克·克莫德:《经典与时代》,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第55页。美国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界对“经典”问题的白热化讨论,反映了文学研究对象从文学文本外扩到文化文本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以及由此所释放的政治潜力和意识形态力量。因此劳特指出,对美国文学的重构应该将其视为兼具审美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商品。(37)参见Paul Lauter, “The Heath Anthology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in Isaiah Smithson and Nancy Ruff, eds., English Studies/Culture Studies:Institutionalizing Dissent,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181.受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的启发,文化研究运用调查、访谈、民俗描绘、话语分析、细读以及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等方法,关注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基本循环,并由此将所有的研究对象都纳入文化的流动,且在此流动过程中,商品化、常规化、吸纳、霸权以及抵抗等现象都会发生。研究对象的扩大化让“拓宽经典”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通过对已有众多方法的综合和以往被忽略点的关注,文化转向中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传统大唱反调。如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就指出,“经典”构建就是帝国构建,维护“经典”就是维护帝国意识形态,“经典”论争就是文化冲突。(38)参见Toni Morrison, “The Canon: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Vol.XXVIII, No.1, Winter 1989, p.8.
美国学界的文化战争体现了保守派与进步派的角力,在其背后则是文化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和政治意识形态之争。“经典”评判标准反映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内涵,“经典”领域是权力话语斗争的必争之地,它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展现的舞台,也是亚文化争夺的场域。作为批评话语中意识形态的载体,“经典”的选择和评判不仅表征着文学研究的学术体制,也从更大范围上映射出社会体制、文化秩序以及价值观念,体现出知识生成的社会机制。
结 语
人文科学的研究离不开互文的价值判断过程,其各个领域都与社会历史密切相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发挥着社会体制的功能。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盛促成了流行文化的胜利、文学“经典”范畴的扩大和文学批评方法的增殖,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受制于这一社会语境。同样,“经典”的构建和变化也是一种机构化和体制化的过程,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呈现着不同时代不断变化的审美旨趣、政治秩序、意识形态冲突、价值判断和社会文化走向等问题。质疑和挑战是“经典”修正的重要前提,而“经典”之争背后则是多元文化主义之争,是文化霸权之争,也是整个人文学科危机的表征。通过此表征来解析人文学科范式转换的必要性,由此探明文论未来发展的潜在方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探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界上述诸问题及其相互关联,爬梳文学“经典”同文化转向和体制话语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纵深上梳理文论既有发展同社会语境的关联性,探寻文论范式转换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