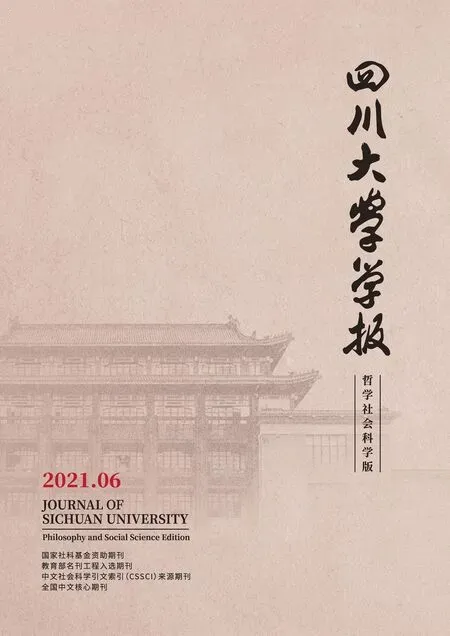论《尚书·洪范》福殛畴:手段、目的及其相关问题
丁四新
《洪范》是《尚书》的一篇,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纵观整个《尚书》学史,我们可以说,所谓尚书学,在较大程度上即尚书洪范学。洪范共九畴,其中福殛畴为终末畴,即为第九畴。在整个洪范九畴的思想体系中,福殛畴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从天子的统治或王的治理来看,它是赏善罚恶的手段;从个人的追求及其存在意义来看,它是臣民个人生存生活所追求的人生目的。而目前学界对于福殛畴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理解也很肤浅,甚至在相关文本的训释上都存在严重问题。以下,本文将逐步讨论福殛畴的文本问题,概括其思想,并梳理五福与六殛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以深化对于福殛畴思想的理解和认识。
一、福殛字义与福殛的来源
(一)福殛字义
“福”,现当代中国学者常常翻译为“幸福”一词。从古书来看,“福”更接近于福庆、福报之义。陈荣捷将“五福”英译为“the Five Blessings”,(1)陈荣捷(Wing-Tsit CHAN)英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10页。不过,对于“六极”,他英译为“the Six Extremities”,同时又以“a punishment for evil conduct”的括注补充之。括注的说明是对的,但“the Six Extremities”的英译是错误的。由此可知,陈荣捷并不知道此“极”字应当读为“殛”。这是比较准确的。一般说来,“福”是人类生活生存所追求的积极目的和正面价值所在,中国古人亦不例外。“福”是什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福”的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追求“福”?这些问题,都是人生哲学所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先看福殛畴“福”“极(殛)”的字义。“福”字,甲骨文和金文作:

“福”是一个形声字,从示,畐声。据《字源》,此字始于金文,(2)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页。不见于甲骨文。“福”字表示富、贵、寿考等因素齐备之义。《释名·释言》曰:“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多品”,即构成幸福的多种元素。“福”字在古书中往往有具体所指,而对于“福”字的具体所指,古书多有明言。《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韩非子·解老》曰:“全、寿、富、贵之谓福。”《礼记·祭统》曰:“富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古文字中的“福”字多用此义。《说文·示部》云:“福,祐也。”这是其引申义。本畴“五福”的“福”字,用其本义。“五福”义为五种福庆或福报,《洪范》已具体指明为寿、富、康宁、攸好德和考终命五者。
通常说来,“福”与“祸”相对。《说文·示部》曰:“祸,害也。从示,冎声。”灾害、灾难即为祸。通行本《老子》第五十八章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苑·权谋》曰:“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中山王厝壶铭文曰:“惟逆生祸,惟顺生福。”以上三例均以祸、福对言。
从《洪范》本文来看,“福”与“极(殛)”相对。反之,也可以说“极(殛)”与“福”相对。《洪范》“六极”的“极”字,孔《传》未训,孔颖达《疏》云:“‘六极’谓穷极恶事有六。”(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这是训“极”为穷极、穷尽。蔡沈《书集传》未解释此字,《汉书》等引经也未见训解此字。惟蔡邕《九惟文》曰:“六极之戹,独遭斯勤。”(4)蔡邕:《蔡中郎集·外集》卷一,四部备要本,第123页。这是将“六极”解释为六种困厄,但是从引文看,蔡氏并未直接将“极”字训为“困厄”。“极”字训为困厄,是不对的;训为穷极、穷尽,是不合文意的。“极”字的本义为“栋”(《说文·木部》),引申之有顶点、至、尽、穷、远、中等义,但它们都无法与“福”字义相对。笔者认为,“极”字当从孙星衍说,读为“殛”。孙氏《注疏》曰:“‘六极’之‘极’,《诗·菀柳》:‘后予极焉。’《笺》云:‘极,诛也。’《释诂〈言〉》作:‘殛,诛也。’言不顺天,降之罪罚。”(5)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1页。“殛”即“诛罚”之义。《庄子·盗跖》曰:“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郭庆藩《集释》引俞樾曰:“极当作殛。《尔雅·释言》:‘殛,诛也。’言罪大而诛重也。极、殛古字通。”(6)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92页。《尚书·康诰》曰:“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罚殛”连言,故知“殛”有惩罚义。“六殛”即六种惩罚,《洪范》下文具体指明为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六者。
此外,据《洪范》三德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等句,“福”还与“威”字相对。“威”即威力、威风之义。徐在国说:“威,会意字。西周金文从女从戊,或从戌,春秋金文从女从戊,或从戈,战国文字从戌。戌、戊、戈都是武器,以示威慑之意。本义盖威力、威风。”(7)参见李学勤主编:《字源》,第1091页。这个训解是对的。孙星衍引郑玄曰:“作威,专刑罚也。”(8)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第308页。郑玄即训“威”为刑罚。郑玄虽求之太过,然其意是也。《洪范》福殛畴云:“威用六极(殛)。”据此可知,“威”字义与“殛”字义当有所分别。“威用”的“威”字,更准确地说,应当训为威罚。
(二)福殛的来源
人所得福庆或所遭殛罚,通常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其来源和依据。在古人看来,“福殛”有四个来源。从终极意义上来说,“福殛”都来源于上天;或者说,它们都是由上天降下的。这一重来源是由古代浓厚的宗教意识所决定的。从政治来说,“福殛”来源于天子、人君或居上位者。据《洪范》第六畴(“三德”),箕子主张“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而“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因此严格说来,“福殛”来源于天子或王。从道理上来说,“福殛”来源于确定的准则和规矩。据《洪范》第五畴(“皇极”),这个确定的准则是“皇极”或“王道”。从个人来说,“福殛”来源于个人的德行和对于准则的遵守。据《洪范》第五畴,这个德行就是“攸(修)好德”,而所谓遵守即遵守“皇极”或“王道”。
据《洪范》原文,从整体上来看,“嚮用五福,威用六极(殛)”是从天子统治或治理臣民,以及臣民是否遵守及遵守如何之报应来说的,故严格说来,五福六殛属于统治或治理的手段,它们与其他八畴共有一个目的,即“彝伦攸叙”。不过,从臣民个人的立场来看,五福六殛又具有目的性,前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生活目的及其意义所在,而后者则是人们竭力避免的东西。五福六殛的目的性,也是不容忽视的。简言之,福殛畴既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手段,又是臣民所追求或遭受的人生目的。虽然手段义是主要的,但是此手段是建立在目的基础上的,是通过臣民所追求或遭受的人生目的而发生作用的。
二、福殛畴的文本与训释问题
(一)福殛畴的文本问题
“福殛”,即《洪范》第九畴,是终末畴“五福六殛”的省称。《尚书·洪范》曰:
(1)次九曰嚮(饗)用五福,威用六极(殛)。
(2)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修)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殛):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上引第一段文字,见《洪范》总叙部分,第二段即是本畴的具体文本。
先看本畴的文本问题。本畴与第五畴皇极畴、第六畴三德畴有直接的文本关系。《洪范》皇极畴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阙庶民。”所谓“五福”,即福殛畴所谓寿、富、康宁、攸(修)好德和考终命五者。《洪范》三德畴曰:“惟辟作威作福。”所谓“作威作福”,即所谓“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殛)”之义。另外,在汉代经师的解释中,《洪范》第八畴庶征畴与本畴亦有关系,所谓“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是也。《后汉书·杨震列传》曰:“熹平元年,青蛇见御坐,帝以问赐,赐上封事曰:‘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灾,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以此而观,天之与人,岂不符哉?’”不过,从《洪范》原文来看,庶征畴与福殛畴没有直接的文本关系。据笔者理解,五事畴、五纪畴、庶征畴属于一个系列,而皇极畴、三德畴、福殛畴则属于另外一个系列。前者置身于天人关系中,休征和咎征即是上天对于君王修身之五事的报应。这个系列完全符合君权神授说的逻辑,是为君王与天神的感应而设的。后者则单纯处于统治与服从的政治语境中:从天子统治或治理臣民来说,五福六殛是手段;而从臣民的个人追求来说,五福六殛则是人生的目的和价值。这个系列是为君王对臣民的统治或治理而设的。汉儒杨震等的解释将这两个序列混杂起来,应当说是不符合《洪范》原文意思的;但是,从逻辑上来看,这两个序列也存在一定的交杂和推演空间,这便是五福六殛能否作为手段施用于人君本身的问题。
“嚮”,简体字作“向”,《汉书·谷永杜邺传》引经作“饗”。“饗”是本字,“嚮”读作“饗”。“饗”的简体字是“飨”。《说文·食部》曰:“饗,乡人饮酒也。”“飨”在此是享受的意思,包含赐予之义。“威”,《史记·宋微子世家》《五行志上》《谷永杜邺传》引经均作“畏”。按,在古文字中,威、畏二字常通用;“畏”应当读作“威”。“威”是威罚、惩罚,而“畏”是使之畏惧。后者与经义不合。
“一曰寿”,《说苑·建本》曰:“(河间献王曰:)《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其所据经文作“一曰富”,次序有别。《史记·宋微子世家》及《中论·夭寿》引经,均作“一曰寿”。又,《庄子·天地》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韩非子·解老》曰:“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据此,《洪范》“五福”当以“一曰寿”为序。作“一曰富”,此别本也。
“攸好德”,《史记·宋微子世家》作“所好德”。按,“攸”作“所”,乃司马迁以训诂字改换之。其实,“攸”不能依训诂字换作“所”。“攸”应当读作“修”,前一字是后一字的初文,故“攸好德”即“修好德”。
(二)福殛畴的文本训释
再看本畴的文本训释。上文已训明“五福”的“福”字是福庆、福报义。“福”是人之所欲者,而“五福”是人之所尤欲者,故君王得以飨庆赏。(1)“寿”,即年岁得长或长寿之义。《说文·老部》曰:“寿,久也。”孔《传》曰:“百二十年。”下文“一曰凶短折”,孔《传》曰:“动不遇吉,短未六十,折为三十,言辛苦。”由此反推,大抵说来,孔《传》认为上寿百二十,中寿九十,下寿六十。但需要指出,此非古说,而是孔《传》的臆造。《庄子·盗跖》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论衡·正说》曰:“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二说均与孔《传》说不同。(2)“富”,指财物多或财物丰备。《说文·宀部》曰:“富,备也。一曰厚也。”“富”字其实兼具“备”“厚”两义。(3)“康宁”,即安宁。“康”是和乐、安定之义。孙星衍《注疏》引郑玄曰:“康宁,人平安也。”(9)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第319页。(4)“攸好德”,已见于皇极畴,云“予攸好德”。孔颖达《疏》引郑玄曰:“民(人)皆好有德也。”孙星衍从之,曰:“攸者,《释言》云:‘所也。’所好德,言好善。”孔《传》曰:“所好者德福之道。”(1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二,第384、383页。孔《传》与孙星衍说有所不同,孙氏以“所”字为句首语气助词,无义,而孔《传》则用为所字结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者同意孙说。俞樾则与上述两说均不同,他读“攸”为“修”,“好”为美好之好。刘起釪从之。屈万里从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说,其具体训解与俞樾同。(11)以上引文,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第320页;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2版)》,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俞樾:《群经平议》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页;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66、1196页;屈万里:《尚书集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25页。今按,当从朱骏声、俞樾说,“攸”读为“修”。“攸”读为“修”,出土文献多见。郭店简《老子》乙组曰:“攸之身,其惪乃贞。”上博简《彭祖》曰:“五纪毕周,虽贫必攸。”两“攸”字均读为“修”。《说文·攴部》曰:“攸,行水也。”其实,这个训解是错的。“攸”即“修”字的初文。《甲骨文字诂林》“攸”字条姚孝遂按语:“攸字,许慎以为‘水’者,实即彡之形讹,修字复从彡,是为蛇足,犹莫复增日作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会稽刻石之文有‘德惠脩长’,或作‘修长’,而原刻石作‘攸长’,诸家皆以通假说之,实则攸修为古今字,本无区分。”(12)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70页。又见李学勤主编:《字源》,第788页。“所好德”即“修好德”,与“恶”相对,是修养美德之义。(5)“考终命”,义为得成善终正命。孔《传》曰:“各成其短长之命以自终,不横夭。”(1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二,第383页。孙星衍《注疏》引郑玄曰:“考终命,考,成也;终性命,谓皆生佼好以至老也。”孙氏曰:“万物老而成就,是考终命也,……《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谓不为五刑所伤。郑说‘生佼好以至老’,谓此矣。”(14)以上两则引文,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第319、320页。“终命”是当时成辞,即善终其生命,或得享天年、自然终结其生命的意思。“考终命”与上文“攸(修)好德”相对,都属于谓宾结构。

总之,五福六殛的大意,当如孔颖达《疏》所云:“‘五福’者,谓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寿,年得长也。二曰富,家丰财货也。三曰康宁,无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终命,成终长短之命,不横夭也。‘六极’谓穷极恶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横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忧,常多忧愁。四曰贫,困乏于财。五曰恶,貌状丑陋。六曰弱,志力尫劣也。”孔《疏》有部分文字的训释是不对的,上文已指出,可以参看。关于五福六殛的用意,孔《疏》曰:“‘五福’‘六极’,天实得为之,而历言此者,以人生于世,有此福极,为善致福,为恶致极,劝人君使行善也。”孔颖达认为五福六殛的用意是“劝人君使行善也”,这其实本自汉儒的解说,而非《洪范》福殛畴的本意。关于五福和六殛各自的次序,孔颖达《疏》引郑玄曰:“此数本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为先。极是人之所恶,以尤所不欲者为先。以下缘人意轻重为次耳。”(18)以上三则引文,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二,第383-384页。蔡沈《书集传》曰:“以福之急缓为先后,……以极之重轻为先后。”(19)蔡沈:《书集传》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72页。皆可以参看。
三、 福殛畴的思想:嚮(飨)用五福,威用六极(殛)
(一)福殛畴的思想
从直接和间接角度看,《洪范》福殛畴的思想大抵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福殛畴是洪范九畴之第九畴和终末畴,而五福和六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从“嚮(飨)用五福,威用六极(殛)”来看,五福和六殛都是天子或君王用来统治臣民和治理天下的工具。“飨”与“威”都是动词,其施为者是王,其施为对象是臣民,很明显二者是统治与被统治、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从统治中或治理中的每一个体的生命追求及其存在意义来看,趋福避殛或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及其生活生存之目的所在。从这一点来看,福殛畴又为目的畴。而且,作为手段的五福六殛正是建立在作为目的的五福六殛基础上的。由于洪范九畴属于天子治理天下的九种大法,故五福六殛在《洪范》篇中首先是从治理手段来说的;其次,五福六殛又是从个人的生活生存追求及其存在意义来说的。两者结合起来,即可将个人的生活生存追求及其存在意义的目的转化为君王治理天下的手段。而天子或君王即因此人性需求及个人生活生存的目的而将其转化为赏善罚恶的统治或治理手段,使处于统治或治理中的个人之生活生存目的及其存在意义,和天子或君王的治理需要一致。应当说,这是一种内在、很高明的统治或治理思路,且此种思路属于因目的而生手段的政治智慧。
第二,五福六殛作为手段,与皇极畴、三德畴的关系很密切,这可以直接从《洪范》文本中看出来。《洪范》第五畴皇极畴一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二曰:“而康而色,曰:‘予攸(修)好德。’汝则锡之福。”这两段话与福殛畴有文本上的直接关系。皇极畴的核心在于“皇建其有极”或“惟皇作极”,此两句中的“极”字都是“中”或“标准”之义。据皇极畴可知,天子以五福赏赐臣民,又以六殛威罚臣民,其标准或依据即是“惟皇作极”。如果臣民协和于皇极,则天子赐之五福,如果不协于极,则天子威用六殛。而且,从天子统治或治理的角度来看,“修好德”是极为重要和极其关键的,它不仅是五福之一,而且是人成其为人的关键美行。这样看来,所谓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的五福,其实以“修好德”为中心。
《洪范》第六畴三德畴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这一段话,与福殛畴的文本关系是很明显的。“作福”与“五福”相应,“作威”与“六殛”相应,“作福作威”即“嚮(飨)用五福,威用六极(殛)”之义。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立君的根据在于君主对于全体臣民的福祉负责,他应当承担起统治或治理天下的政治责任。从目标看,皇极畴用“作民父母”的比喻来对天子所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作出很高要求。同时,在统御诸侯大臣和治理平民百姓的过程中,天子本人应当专擅天子之名分,因为名分即权力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不能被臣下所觊觎和僭用;否则,王权被觊觎和被僭用,即会导致王纲解纽和礼崩乐坏的末世局面。对于前者,三德畴谓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对于后者,三德畴谓之“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从三德到作福作威玉食,从作福作威玉食到“嚮(飨)用五福,威用六极(殛)”,这是一条线索。反过来看,五福六殛确实是天子统治臣下的手段和治理庶民的工具。
第三,在福殛畴中,五福与六殛两者有对应关系。它们的对应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文本上来看,五福与六殛是对应的。福殛畴先述五福而后及六殛,两者是彼此配合的关系。否则,单言五福而不言六殛,或者单言六殛而不言五福,文本就不是完整的。二是从性质上来看,五福与六殛也是对应的。五、六均为中数,五为天数,六为地数,故暗含阳生阴杀之义。福与殛相对,福为人所追求,是积极、肯定的目标;而殛为人所欲避免,是消极、否定的目标。三是从内容上来看,五福与六殛具有对应性。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五者曰五福,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六者曰六殛。虽然学者持说有不同,或有争议,但无一例外地都认为它们在内容上具有对应性。四是从用意上来看,五福与六殛也是对应的。对于人生而言,五福是对于人生目的及其存在意义的肯定,而六殛则是对于人生目的及其存在意义的否定。从天子统治或治理的角度来看,《洪范》曰“嚮(飨)用五福,威用六极(殛)”揭明了本畴的宗旨。
第四,福殛畴包含着“德福一致”的观念。这一点无论是从天子的统治、治理还是从臣民的人生追求来看,都是如此。上文已指出,“五福”以“修好德”为关键。皇极畴说,庶民因其“予攸(修)好德”,故天子得以“锡之福”。而在“惟辟作福作威”的前提下,所谓“德福一致”,指臣民修有什么样的好德,即有什么样的福报,不多也不少,不轻也不重,更不是相反。而作为执掌赏罚二柄的君王,其责任是实事求是和明察秋毫,根据臣民的德行功咎而相应地“飨用五福,威用六殛”。进一步,在现实层面上,尽管一个人的德福未必总是一致的,但是“德福一致”观念本身是颇有价值的,它是一种普世愿望,对于人生的意义和安顿都有重要作用。
(二)神性与否定
此外,关于福殛畴,笔者认为,还有三点值得指出:一是福殛畴隐含着对天子神性的肯定;二是墨家将祸福的来源完全归于天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王的政治权威和管治作用;三是庄子以逍遥无待之说超越了传统的“致福”观念,认为“致福”对于人的生命自由来说也是一种束缚。
先看第一点。五福的“寿”和六殛的“凶短折”,本是自然性、命定性和偶然性极强之物,然而据《洪范》本文,王却可以作用之,可以支配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因受命的背景也具有通天的神性。《洪范》序论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这两句话直接肯定了洪范九畴本身即是人君受命的象征,而由此可知,能作福作威的王即具有通天的神性。而由于具有此等神性,所以他能飨用寿福和威用凶短折。
再看第二点。墨子走向一个极端,将祸福或赏罚的主宰者和施为者完全归于神性的天或鬼神。《墨子·法仪》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同书《天志上》曰:“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同书《公孟》曰:“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自桀纣以下,皆以鬼神为不神明,不能谓祸福,执无祥不祥,是以政乱而国危也。”这三段引文都说明了,墨家将祸福或赏罚的主宰者和施为者完全归于上天或鬼神一方。这与《洪范》的区别很明显,《洪范》将五福六殛的主宰者和施为者归于天子或王,完全肯定了天子或王在人间的绝对权威及其超越能力。
最后看第三点。庄子及其后学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个人追求五福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五福并以为人生目的,这本是一般社会现象,常人均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但是,在先秦,庄子以一种崭新的生命观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庄子·逍遥游》曰:“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御风而行”,比喻列子超越了世俗价值观念的束缚,落实下来即指“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致福”即求福,而所求之福,当指寿、福、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五者。庄子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致福”的人生价值,但是“致福”同时将人限定在“世俗”的特性上而无法自解免。在致福之上,庄子认为人生有更高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是个体生命的安立和自由,是达到逍遥无待之境。在他看来,汲汲乎追求五福,这是对于人的生命的倒悬和限定,是对于人的生命之真的疏离和异化。这样,作为人生追求目的的五福于是被超越和解脱,而作为治术的五福六殛也因此丧失其神圣性和必要性。
四、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及其相关问题
(一)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
先看五福与六殛在内容上的对应关系。二者是如何对应的?不同时代及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和回答。今列四种看法如下:
第一种,见于《汉书·五行志》及郑玄注所述《尚书大传》。孙氏《注疏》引《汉书·五行志》曰:“视之不明,其极疾;顺之,其福曰寿。听之不聪,其极贫;顺之,其福曰富。言之不从,其极忧;顺之,其福曰康宁。貌之不恭,其极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极凶短折;顺之,其福曰考终命。”并评论说:“此盖刘向今文说也,与郑氏异。”需要指出,孙氏《注疏》所引《五行志》文字属于概引。据这段引文,刘向所说“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是:疾—寿,贫—富,忧—康宁,恶—攸好德,凶短折—考终命。孙氏《注疏》又述及郑注《尚书大传》,曰:“反疾为寿者,夏气得遂其长也;反贫为富者,冬主固藏;反忧为康宁;东方德,西方刑,失其气则恶,顺之则好德也;反凶短折为考终命者。”(20)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第319-320页。据此,郑玄注所说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是:疾—寿,贫—富,忧—康宁,恶—攸好德,凶短折—考终命。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上述两段引文所说的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是完全相同的。一般说来,注不违传,郑玄注所说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其实出自《尚书大传》,不一定是郑玄本人的看法。而伏生《尚书大传》的此种搭配法,此前已被刘向所继承。另外,顺便指出,上述两段文字均没有提及弱殛。
第二种,见于孔颖达《疏》所引郑玄说。孔《疏》引郑玄曰:“(郑玄依《书传》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罚。疾,视不明之罚。忧,言不从之罚。贫,听不聪之罚。恶,貌不恭之罚、弱,皇不极之罚。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则致寿,听聪则致富,视明则致康宁,言从则致攸好德,貌恭则致考终命。所以然者,不但行运气性相感,以义言之,以思睿则无拥,神安而保命,故寿。若蒙则不通,殇神夭性,所以短折也。听聪则谋当,所求而会,故致富;违而失计,故贫也。视明照了,性得而安宁;不明,以扰神而疾也。言从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从而无德,所以忧耳。貌恭则容俨形美而成性,以终其命;容毁,故致恶也。不能为大中,故所以弱也。”(2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二,第384-385页。其中,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是:凶短折—寿,疾—康宁,忧—攸好德,贫—富,恶—考终命。此种对应关系与第一种大殊,除了“贫—富”一对相同外,其他四对均不同。此种对应关系,比较可能代表了郑玄本人的意见。另外,郑玄虽然在本段引文中提到弱殛,但是它在五福中依然无对应者。
第三种,见于王安石《洪范传》。《洪范传》曰:“凶者,考终命之反也;短折者,寿之反也;疾忧者,康宁之反也;贫者,富之反也。此四极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犹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产,而继之以扰,则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恶,六曰弱。恶者,小人之刚也;弱者,小人之柔也。”(22)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五,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第697页。王安石关于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是:凶—考终命,短折—寿,疾、忧—康宁,贫—富,恶、弱—攸好德。
第四种,见于《朱子语类》所记朱子说。《朱子语类·尚书二》曰:“然此一篇文字极是不齐整,不可晓解。如 ‘五福’对‘六极’:‘一曰寿’,正对‘凶短折’;‘二曰富’,正对‘贫’,‘三曰康宁’对‘疾与弱’,皆其类也。‘攸好德’却对‘恶’,参差不齐,不容布置。”(2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049页。朱子关于五福与六殛的对应关系是:寿—凶短折,富—贫,康宁—疾、弱,攸好德—恶,但他没有将考终命一福和忧殛配对起来。今天,我们可以追问,在内心里,朱子是否将考终命与忧配对起来了呢?而它们又是否可以配对呢?笔者推测,对于前一个问题,朱子可能认为两者都不能配对,故在此段文字中,他没有提及它们;对于后一个问题,根据前三种意见来看,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需要指出,朱子的说法是在对话性的语录中出现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未必能够真正代表朱子意见。
总结上述四种意见,刘向、郑玄、王安石和朱子无一例外地都肯定五福与六殛具有对应关系,只是在如何对应的问题上,四人的看法各有不同。首先,第一种和第二种为一大类,属于汉人的说法;而第三种和第四种为另一大类,属于宋人的说法。汉人的说法属于经学,受到经典及当时解经传统的高度约束,且其知识背景及思维方式相同。宋人的说法虽然名为解经,但其实已经落入很强的说理意识中,王、朱二氏均据理而为之配对。不过,王、朱二氏的说法仍受五元思维的制约。其次,除了对“贫—福”的搭配完全相同外,四人关于其他四对的搭配均参差不齐,各不相同。最后,这四种福殛的具体对应都不尽合理,但程度有别。
笔者认为,从内容上来看,寿、考终命与凶短折相对,富与贫相对,康宁与疾、忧相对,攸(修)好德与恶、弱相对。凶短折何以与考终命相对?这是因为凶短折一殛包含非正命而死的情况,故应与考终命相对。康宁何以与疾、忧二殛相对?这是因为康宁包含健康和安宁两义,故应与疾、忧相对。恶、弱主要就生命气象和生命意志而言,故此二殛能与攸(修)好德相对。显然,笔者在此的说法已不再受五元或五行思维的局限,完全是从义理上来作理解和配对。
(二)五事畴与福殛畴的关系
再看五事畴与福殛畴的关系。上引刘向说和郑玄说都认为五事与福殛有因果关系。刘向说以伏生说为基础。伏生的搭配是:疾—寿—夏长,贫—富—冬藏,忧—康宁,好德—春、东、德,恶—秋、西、刑,凶短折—考终命。春生故曰德,秋杀故曰刑,这是运用了阴阳刑德理论,以与福殛畴搭配。在此基础上,刘向认为五事与福殛有因果关系,其具体搭配是:视不明—疾,视明—寿;听不聪—贫,听聪—富;言不从—忧,言从—康宁;貌不恭—恶,貌恭—攸好德;思心不容—凶短折,思心容—考终命。刘向说其实直接来源于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从原文看,《洪范》没有直接将五事畴和福殛畴关联起来;但是从道理上看,将五事畴与福殛畴关联起来是可能的。
不能不指出,刘向等将五事畴与福殛畴关联起来,实际上突破了《洪范》原文的界限。五事、五纪与庶征有因果关系,皇极、三德与福殛有因果关系,这两个系列的关系在《洪范》本文中是明确的。五事是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讲君王的修身,敬用五事则天应之以休征,否则天应之以咎征。庶征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因为天人感应而起谴告人君的作用。而对于“敬用五事”的“敬”字,汉儒又用“恐惧修省”四字来作解释。福殛畴与五事畴不同,《洪范》曰“向(飨)用五福,威用六极(殛)”,五福六殛是天子或君王用来赏善罚恶的,从《洪范》皇极畴、三德畴文本来看,都是如此。臣民遵从皇极,则天子赐之福,不遵从皇极则天子施用殛罚。然而,我们看到,汉儒打破了五事对庶征、皇极对福殛的《洪范》原文脉络,而将五事和福殛直接关联起来,认为它们也有因果关系。这样一来,天子修养五事如何,不但有庶征之应,而且有福殛之赏罚。进一步,汉儒的此种构想过不过分?符不符合皇朝逻辑?对于这两个问题应当如何作答,笔者揣测,即使是汉代经师也是比较惶惑的。不管怎样,五事与福殛的因果关系是由汉儒建构的,是汉儒的想法,但它不是《尚书·洪范》本有的思想。
不仅如此,按照夏侯始昌、刘向等人的逻辑,皇极、庶征也被汉儒一并加入此一新的解释体系中来。《汉书·谷永杜邺传》曰:
(谷永对曰:)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
《汉书·匡张孔马传》曰:
(孔光对曰:)臣闻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如貌、言、视、听、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谓朓、侧匿,甚则薄蚀是也。
《后汉书·杨震列传》曰:
(杨赐上封事曰:)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灾,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以此而观,天之与人,岂不符哉?《尚书》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征也。夫皇极不建,则有蛇龙之孽。
成帝建始三年(前30)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故成帝“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引《汉书·谷永杜邺传》一段文字即发生在此背景下。哀帝元寿元年(前2)正月朔日“日有蚀之”,十余日后傅太后崩,故哀帝征光“问日蚀事”。上引《汉书·匡张孔马传》一段文字即发生在此背景下。灵帝熹平元年(172),“青蛇见(现)御坐(座)”,故灵帝就此事询问杨赐。上引《后汉书·杨震列传》一段文字即发生在此背景下。从上引三段文字来看,五事、皇极、庶征、福殛被关联了起来,并明确构成了一个思想系统。而通过此四畴的关联,汉儒实际上将洪范九畴全部关联起来,纳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休征咎征和五福六殛的思想系统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汉儒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将《洪范》变成了展现君权、制约君权和如何谴告、赏罚人君的一篇核心文献。应该说,汉儒在较大程度上误读了《洪范》;也可以说,汉儒以君权问题为中心重新诠释了此篇文献的思想。
总之,《尚书·洪范》福殛畴既是手段畴又是目的畴。“福”是福庆、福报之义,“六极”之“极”当读为“殛”,“殛”是诛罚、惩罚义。“攸”是“修”字初文,“攸好德”即“修好德”,“好德”即美德之义。“五福”即五种福报,“六殛”即六种惩罚。“五福”以修好德为中心。在洪范九畴系统中,五福六殛既是个人趋吉避凶的目的,又是君王统治臣民和治理天下的手段,且君王专擅作福作威的权力。五福与六殛有对应性,但如何对应,汉宋儒者的说法不一致。从内容和义理上来看,寿、考终命应与凶短折相对,富应与贫相对,康宁应与疾、忧相对,修好德应与恶、弱相对。福殛畴包含着“德福一致”的观念,且暗中肯定了君王具有通天的神性。从《洪范》本文看,五事、五纪与庶征,而皇极、三德与福殛有因果关系,这两个系列的分别是很明确的。在汉人的解释中,五事、皇极、庶征、福殛四畴被关联了起来。而通过此四畴的关联,汉儒实际上将洪范九畴全部关联了起来,纳入了所谓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休征咎征和五福六殛的思想系统之中。实际上,汉儒在天人感应的思想背景下将《洪范》变成了一篇展现君权、制约君权和如何谴告、赏罚人君的核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