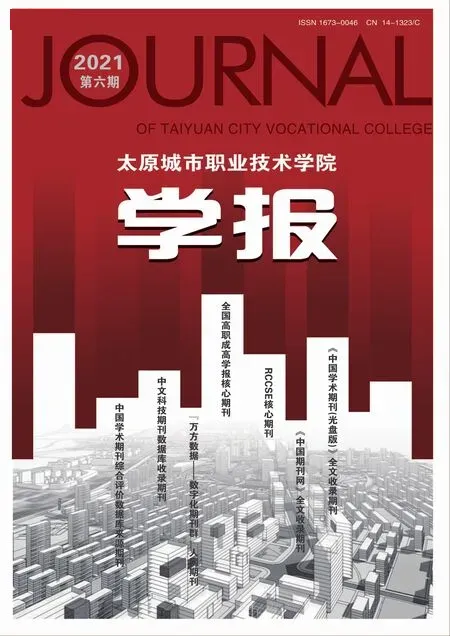“言不尽意”视域下古典诗歌的“留白”美
——以柳宗元《江雪》为例
■张贺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言意之辨是魏晋时期玄学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字面意义上来看,“言”指文字言语,“意”指思想情感,“言”是具体的,“意”是抽象的。言与意之辨最初活跃于中国玄学领域,当玄学家们逐渐把焦点转向文学领域中,“言不尽意”论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论观点。从先秦至唐宋时代,此论点多散见于文论家的言意之辨中,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理论阐述,因此,有必要以时间为顺序对“言不尽意”内涵的流变进行简要的梳理与分析。
一、先秦至唐宋时代“言不尽意”论内涵的流变
(一)先秦时期
“言不尽意”最初是哲学领域探讨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老庄就已提出相关论述。《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为可以论述清楚的“道”,称不上是真正的“道”,可以用语言明确命名的“名”,也不是真正的“名”,“道”和“名”是难以言说的。老子对“言意关系”的论述建立在以自然之道为中心的基础之上,虽然没有明确指向言意关系,但也是比较深刻的哲学思考。庄子承袭老子的观点并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庄子·天道》篇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他强调从书本中学习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语言不足以传达“意”的深厚内涵。“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语言表达得越丰富,则越有可能疏离本意,庄子指出了语言的局限性。老庄对于言意关系的论断或许有些片面,过于贬低了语言的作用,但是他的观点对于推动“言不尽意”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尚处于萌芽期,且此时文史哲之间的界限没有明确的区分。文论家们对于言意关系的论述虽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但是已初现端倪,此时言与意处于一个从哲学命题到文学理论的转换期。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史上是文学自觉的时期,文学批评不再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的绝对性,为政治转向缘情,文学的功利性降低,其本身的审美属性逐渐得到重视。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名士多喜谈玄,玄学作为老庄道学的变体开始蓬勃发展,言意关系论开始逐渐苏醒,进入诗学领域。
王弼援引自庄子的“筌蹄之言”,加以发展和深化,形成著名的“得意忘言”论。“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段是王弼对“言”“意”“象”的总结性论述,明确了“言”“意”和“象”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言”可以察觉“象”,通过“象”可以把握“意”,“意”在“言”“象”之外,要“得意”,必须“忘言忘象”,只有不受“言”“意”矛盾的束缚,才能求得真“意”。
王弼等人的主张多建立在哲学的层面,陆机的《文赋》则把“言不尽意”的思想引入文学领域。“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指出属文中会出现由于表达能力不足而致使文意并不能完全传达出来的情况,语言和思想并不具有完全的统一性,语言的表层含义之内往往蕴含深沉丰富的思想,使文学具有含蓄蕴藉之美。
刘勰也深刻地认识到言与意的矛盾所在,《文心雕龙》中言及了这一问题。《神思》篇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适,笔目知止。”人的思维具有开放性,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随万物神游,与风云并驱,具有超前性和无限性。而万物却须遵守一定的语法规则,相比来说,它具有滞后性和固定性,因此,“言须实而难巧”,以致言不尽意。刘勰指出了言与意的不统一性,并在《隐秀》篇中,通过“隐”和“秀”概念的提出,强调文学语言应具有生动、鲜明、含味曲包的诗性特征,注重语言对“神思”的表现力。“不尽意”论从哲学范畴进入诗学领域的过程中,刘勰在理论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唐宋时期
在总结前人理论经验的基础上,唐宋时期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们从言意之辨转向对意境论的关注,在理论上深入地探讨,“言不尽意”论的内涵更加成熟。皎然是中唐后期著名的诗僧和文论家,他的文学思想中融入了禅宗的一些概念,提出“缘境”“取境”“意冥”等文学思想。他认为读者要发挥主观意志,发现景物描写中的意境,强调诗句的情味不可言状,需要依靠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来感悟,方可获得言语所能传达之外的美感。司空图是晚唐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诗歌美学理论,主张在实际自然物的基础上,创造出超越时空性的“象”和“景”,尤其是“韵味”说,追求诗歌的含蓄蕴藉的韵味和清远自然意境。
宋代,在继承和发展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基础上,杨万里提出“去词”“去意”论,其《颐庵诗稿序》云:
夫者,何为诗也?尚其词而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
所谓“去词”“去意”即是指作诗不要拘泥于词和意,但是这里的“意”指诗词的表面意义,并非是意境,好的诗词重在创造出含蓄延绵、超越言象的意境。此外,陆游对江西诗派及其后人创作中“字字有来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反对刻意雕琢字眼,主张“工夫在诗外”,重视诗词的情感和意境。严羽在继承司空图和皎然等人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兴意”“兴趣”之说,崇尚诗歌的朦胧、含蓄、蕴藉之美。
先秦至唐宋,“言不尽意”论进入文学领域进而发展成为意境论的这一过程,是文论家们在承认语言表现力的不足的基础上,试图找到营造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理论探求,其界域的流变也是文论家们思想不断深化的认知结果。从总体上来看,言不尽意论指出了言辞和意念之间存在差距,认识到言辞并不能把意念完全表达出来这样一个特殊的规律。那么,如何通过有限的语言使古典诗歌传达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深远意境呢?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绘画中的“留白”技法给出了一种答案。
二、《江雪》的“留白”美
“留,止也。”(许慎《说文解字》)“白”,后来派生出“空白,空无所有”的含义,谭雪纯等人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给“留白”的定义是“说话或写文章时,有意不把话说完或说清楚,留下一定的空白,让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的一种修辞方式。”“留白”是中国传统绘画创作中的一种常用的技法,书画艺术创作中,作者为使整个作品画面、章法更为协调精美而有意留下相应的空白,以笔墨和形体的虚实变化来创造出独特的意境,给予欣赏者想象的审美空间,获得不能尽语言之事而传达出来的言外之意。绘画和诗歌同为艺术种类,自古以来便不是独立的分支,《论语·八佾》中: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始可与言诗矣”承接前文的绘画之语,孔子时期,就注意到《诗经》和绘画具有关联性,在表情达意上可以互相阐发。唐代诗人王维擅长在诗歌创作中使用“留白”的技法,创作出众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作品,如《山居秋暝》;宋代张舜民曾言:“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苏轼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之语。绘画中色彩交错、线条勾勒带给观赏者的印象是固定的,但是空白处却为欣赏者提供了一个偌大的驰骋幻想的空间,赋予了作品想象力、生命力和吸引力。
留白从绘画领域逐渐渗透至文学领域,日臻成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表现手法。中国古典诗歌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形式,由于篇幅的限制和文法的约束,它无法像小说一样长篇大论,也不能如散文一般极致地抒情。此外,诗人的情感具有复杂多变性,许多幽深内隐的情思难以直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言不尽意”的困窘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诗人常常通过“不写而写”“以实写虚”的方式,或使用象征、比兴的艺术手法,故意在文本中留下空白,意图通过有限的语言呈现情景交融的意境和委婉曲折的语义,即刘熙载先生所说的“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这和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手法是相通的,造就的作品往往蕴藉着更为丰富的审美意蕴。诗人如果拘泥于语言的表述,反而使得诗歌繁琐且枯燥。相反,依托简单自然的文词,留给欣赏者一定的思维空白场地,于自然而然不露痕迹中营造出高妙的境界,就能够将“意”从语言表达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试以柳宗元的《江雪》一诗为例论之。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是唐代诗人柳宗元于永州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虽然是简单的二十字绝句,却营造了一种宏大、空灵、虚清的意境。那么,这首诗是如何呈现留白的诗境的呢?
(一)语言上的留白
此诗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实”自然是指诗中的意象:千山、鸟、人、孤舟、蓑笠翁、寒江、雪,这些是实景。诗的开头两句利用人之退隐、鸟之泯踪制造出了绝对寂静之感。后两句,蓑笠翁在尾声中出场,只需一句空间,点到为止,人与景水乳交融,塑造出物我两忘之境。整首诗宛若一幅画,四句皆为画中景,除了这些意象以外,其余都是留白下的虚拟世界。“虚”景的呈现,则主要由雪来承担。“雪”被放置于整首诗的末尾,从意象特点来看,它带给了读者空蒙、清冷的心理感受。从色彩上来看,雪的颜色呈现出至白、至纯的特点,构成了留白世界的主色调。包罗一切、广阔纵横的雪与孤舟蓑笠翁的渺小形成巨大的视觉反差。对雪景的寡言叙述,犹如画中的简笔勾勒。简单的一“雪”字,却呈现了浩瀚无边的想象世界,我们无法断定这雪的边际在哪儿,正如李瑛《诗法易简录》云:“前二句不着‘雪’字,而的确是雪字,可称空灵,末句一点便足”。“孤”不仅用来形容“舟”,也是对蓑笠翁的描写。作者没有用笔墨描述渔翁的神情和语言,此时无声胜有声,省去的语言和神态描写正是诗人设下的留白之处。被“舍弃”的这部分并非不重要,而是一种不写之写。作者设下了悬念,能够引发读者的探索欲望,刺激读者猜测渔翁的神情和心理活动,人迹罕至之处,此老翁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孤身垂钓呢?竟不怕天寒地冻,不惧孤单寂寥,这比句句实写老翁更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张力。
(二)意境上的留白
“置孤舟于千山万水之间,而一老翁披蓑戴笠独钓其间,虽江寒而鱼伏,彼老翁独何为而稳坐于孤舟风雪中乎?世态寒冷,宦情孤冷,如钓寒江之鱼,此子厚贬时取以自寓也。”寒冬本不是垂钓的好时节,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诗人此举为何呢?联系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江雪》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805年—81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贞革新运动,但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压制,改革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流放十年,名为贬官,实则过着被拘禁的生活。政治的失意和环境的险恶促使诗人把理想志趣和人生价值寄寓诗歌中,排解心中愤懑。诗人内心情志的外化,是诗人兀傲不训的人格化身。尽管所处的是天寒地冻的环境,但诗人依旧岿然自得,这是一种不向污浊官场屈服的抗争,是一种孤独求索的决心,一种保持心中的理想与孤傲的志气,而这江雪何尝不可视作诗人品格的象征呢?《庄子·知北游》:“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雪”可洗涤污垢,使神志、内心保持纯正。清醒的诗人面对黑暗的官场,孰是孰非,孰黑孰白,心中自知,应当坚守这份至纯至净如雪一般的操守。
天地一尘不染、万籁无声,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无边无际的感官体验。渔翁孤傲清高、聊以自娱,形单影只却让人凛然不可侵犯,这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之美。留白下的江雪垂钓诗富有宏大壮美的意境,寒江雪和超然外物的渔翁是实景,至于大雪边际在何处、蓑笠翁垂钓的心理是虚景,虚实相生,读者想象的画面泛起层层涟漪,“二十字可作二十层,却自一片”。作者有意把诗人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赋予其极具象征性和暗示性的意义,意境上的“留白”应运而生。
从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不尽意”命题出发,“留白”一词的语义迁移为窥探《江雪》呈现的言外之意提供了视角支撑。“留白”技法渗透到诗作中,为读者探寻《江雪》“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审美意境提供了寥阔的想象空间,以有限、固定的实景,表现无限、灵动的留白虚景,实景是运用留白的基础,留白下情景交融的虚景强化了诗歌的意境。
三、中国古典诗歌运用“留白”技法的原因
古典诗歌中,言与意的矛盾始终存在。作者除了可以加强对语言的锤炼之外,“留白”更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那些因追求言外之意和悬念而设下的留白能拉动读者更加积极地参与文本解读的过程,为诗歌带来朦胧模糊的审美内涵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审美乐趣。清人郑燮认为:“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好诗在于它的含蓄蕴藉之美,留白下的诗歌因为语言的不完整性和诗人情感的隐匿性能够把读者带入犹如雾里看花的意境,为读者多角度探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提供了可能,带来古典诗歌含蓄蕴藉的审美价值和美学风貌。那么,中国古典诗歌为什么孜孜追求这种美学原则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撮要如下:
(一)含蓄蕴藉的审美功效
讲究含蓄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一贯思想,“含蓄”的基本特点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就是说,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意趣并不直接形诸文字,而是见于言外,通过间接的方式委婉地传达出来。文学话语中的蕴藉注重语言的审美效果,强调“若隐若现,欲而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这样便形成了言外之意的丰富多变”。含蓄蕴藉是指在有意境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艺术家所要表达的主观的思想、情感和感受,不是直接抒发或清楚地说出来,而是隐含在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中,隐含在情景交融的意境中。通过这种形象画面和情景交融的境界所表现出来的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就具有一种含蓄、蕴藉和朦胧的审美特征,“凡诗恶浅露而贵含蓄,浅露则陋,含蓄则令人再三吟唱而有余味。”
含蓄蕴藉的情思表达,是中国古代文论家推崇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自觉的审美追求。对诗人来说,他们可以在诗歌文本中运用开放性的创作手法,创造多层面立体性的诗歌艺术空间。对读者来说,鉴赏诗歌的过程就是参与一次意境的深层挖掘,读者必须抛开言辞的表层义,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究众多可能性。
(二)儒家诗学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中庸之道”和“温柔敦厚”,基于此基础上的诗学观要求“中和”,即中正适度、不偏不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求诗歌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要合乎“礼”的规范,劝诫讽谏态度要温和。在这种规定下,儒学家们依托“比兴”手法,意在托物言志,希望使诗歌获得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诗经》中运用“比兴”手法创作的诗歌自是不胜枚举,《楚辞》中“香草”“美人”的寓托传统,开创了中国抒情文学含蓄蕴藉的审美先河,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辞婉旨隐的艺术特点。儒家思想在封建统治中具有至尊的地位,在儒学的标榜下,其诗教对古代诗学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深受儒学熏陶的诗人们自然把含蓄蕴藉的诗风作为表现“温柔敦厚”的首选方式。
(三)佛道哲学思想的理论归宿
老子认为,作为生命本源和万物本体的“道”是不易表述的,在于世人的领悟。但是常人难以领悟,需要依托“象”这类具体的实物来表述抽象高深的语言,方能理解“道”的玄妙。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王弼认为象和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通过观意可以达意。“象”具有表征性和多义性,和比兴手法产生的艺术效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往往带来极具暗示性和模糊性的诗义。佛教在言意关系上的观点和庄子的“得鱼忘筌”论类似,竺道生认为“得意则忘象”“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禅宗标举“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越于文字。”“道”和“理”都是超越文字(象)的,无论是“传道”还是“悟理”,都要在把握“象”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诗歌的言外之意。佛道哲学思想关于象与意关系问题的论述对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鼓励了后世诗人追求“象外之象”“文外之旨”,一定程度上为“意境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资考据的归宿,是我国古典诗歌形成含蓄蕴藉、言微旨远风格的重要推动力。
要之,中国古典诗歌“言不尽意”的局限下,“留白”技法跨界借鉴于诗的创作之中,“不写而写”的写作手法以有限的内容表达了无限的诗意,营造了虚实结合、含蓄蕴藉的意境,是诗歌在“言不尽意”的缺憾下实现意境创造的艺术支撑,创造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