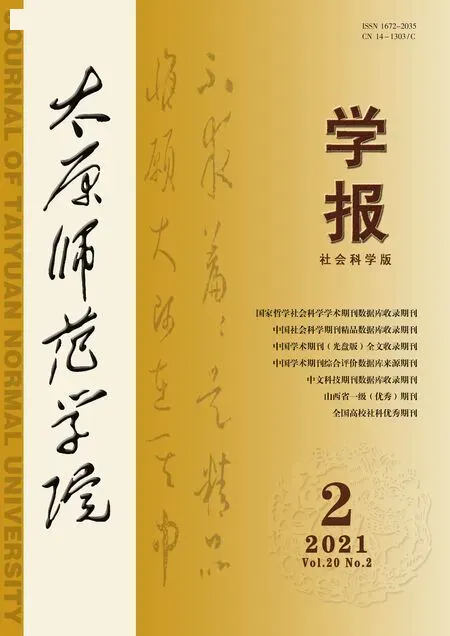叶燮的诗歌批评实践
杨 晖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视《原诗》为“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批评它不合传统评诗之法,但并没有否认叶燮的诗学观念及其批评实践。纵观全文,《原诗》当属“作论之体”,但也有大量的诗歌批评,提及的诗人达54人之多,其中汉代2人、六朝16人、唐代25人、宋代9人、元代与明代各1 人,涉及的诗论家无数。叶燮的诗歌批评实践集中体现了以“变”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及其“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的批评特色,具体表现在对诗论家与诗人的批评两个方面。
一、历代诗论家的批评
在叶燮看来,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批评,都要有“胆”,“无胆,则笔墨畏缩” (《原诗·内篇下》),不能自由发挥。他对历代诗论家之批评正体现了他“有胆”,但都过于苛刻,有失公允。
(一)对六朝唐宋诗论之批评
叶燮对历代诗论家评价不高,认为“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原诗·外篇上》)。他批评钟嵘、刘勰“吞吐抑扬,不能持论”,仅对钟嵘的“迩来作者,竞须新事,牵挛补衲,蠹文已甚”(《诗评序》)和刘勰的“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文心雕龙·风骨》)抱有好感,认为前者切中诗坛“好新”之弊,后者切中诗之本原,而除“此二语外,两人亦无所能为论也”(《原诗·外篇上》)。而对于汤惠休的“初日芙蓉”、沈约的“弹丸脱手”之评,以为“差可引伸”“非大家体段”。这一评价严重低估了《诗品》与《文心雕龙》的诗学成就,难以说服后人,也体现了叶燮对诗论家的偏见。
《诗品》与《文心雕龙》是中国诗学著作的代表,贡献卓越。清代文学史家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认为“《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1]559朱东润说:“吾国文学批评,以齐梁之间为最盛”,并称“论文之士,不为时代所左右,不顾时势之利钝,与潮流相违,卓然自信者,求之六代,钟嵘一人而已。”[2]44-45郭绍虞也认为,《诗品》与《文心雕龙》“此二书之所以重要,即应足以代表当时批评家之二派”[3]129。在郭先生看来,六朝人需要有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的指导,前者以《诗品》为代表,后者以《文心雕龙》为代表。他从时代需求肯定两著作的巨大成就,并进一步认为《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推粗以及精,敷陈详核,宁理密察,即传至现代犹自成空前的伟著”[3]121,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
叶燮则对钟嵘、刘勰的诗学成就一笔带过,只突出与自己诗学思想相通之处,遮蔽了二人其他方面的理论贡献。他说钟嵘的“迩来作者,竞须新事,牵挛补衲,蠹文已甚”一句来自于“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迩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诗品序》)句,认为自任昉、王元长以来,用词不以奇为贵,争相用典,渐成习俗,逸事过度,害了诗文。叶燮的“变而不失其正”的思维方式,对于那些一概求新求变者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所以他批评公安与竟陵“抹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但又“入于琐层、滑稽、隐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异,其过殆又甚焉”。(《原诗·外篇上》)在叶燮看来,“陈熟”与“生新”应相济,当“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原诗·外篇上》)。
再看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辞”与“骨”关系是“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肯定骨先于辞,即表达了文辞对骨的依赖,探究了诗之本原。这与叶燮对“质”“文”关系的看法基本相似。叶燮认为体格、声调与苍老、波澜等“皆诗之文也,非诗之质也;所以相诗之皮也,非所以相诗之骨也。”(《原诗·外篇下》)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松柏之“劲质”,“苍老”便无所依靠;如果没有水“空虚明净,坎止流行”之质,也难有“波澜”之美,所以必先有“诗之性情、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以为其质”(《原诗·外篇上》),方有体格、声调、苍老、波澜之文,文待质也。其实,钟嵘与刘勰在对“质”与“文”的论述上多有创举,遗憾的是被叶燮忽略了。
唐宋以来的诗论者也没有得到叶燮的重视。他认为“诸评诗者,或概论风气,或指论一人,一篇一语,单辞复句,不可殚数”(《原诗·内篇下》),仅提及皎然的“复变”,刘禹锡的“才”“识”,李德裕的“终古常见,光景常新”,以及皮日休对“才”之多元的表达等,认为是“异于诸家悠悠之论”;对于严羽、高棅、刘辰翁、李攀龙等则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特别是对于严羽,虽然叶燮赞同其“学诗者以识为主”,但对其“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观点表示反感。因为,这与他的“踵事增华”思想相冲突。叶燮重视“识”,认为无识,即“一一趋步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而有识,即使不趋步于汉、魏、盛唐,诗魔都能变为“智慧”,不害汉、魏、盛唐诗。在他看来,诗人有“识”,就可以在汉、魏、六朝、盛唐及宋之诗的面前作出正确选择,如钱谦益一样,将诗之不振归罪于严羽、高棅、刘辰翁等。(1)严羽《沧浪诗话》诗论、高棅《唐诗品汇》诗选、刘辰翁《须溪先生集》诗评,明后期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想的反驳,以上三位也受到影响。钱谦益《徐元叹诗序》:“自羽卿之说行,本朝奉以为律令,谈诗者必学杜,必汉魏、盛唐,而诗道之榛芜弥甚。羽卿之言,二百年来,遂若塗鼓之毒药。”(《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其在《题徐继白诗卷后》《爱琴馆评选诗慰序》中又对高棅、刘辰翁等作了类似的批评。
其实,对于各代诗家之批评,是肯定性评价还是否定性评价,不仅与批评者的针对性与目的性相关,而且与批评者的诗学立场观念相关;批评是否合理或有效,则需要时间的检验。叶燮对历来诗论家的批评正是如此。
(二)对近代诗论之批评
叶燮的《原诗》并不是针对六朝与唐宋诗论的,更多是批评明代及清初的诗坛,即他所谓的“近代称诗者”,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在《原诗》的开篇明确提出了“近代称诗者”之不足,他说:
近代论诗者,则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非是者,必斥焉。……自若辈之论出,天下从而和之,推为诗家正宗,家弦而户习。习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矫而反之者,诚是也。然又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说,其说胜,则出乎陈腐而入乎颇僻;不胜,则两敝。而诗道遂沦而不可救。(《原诗·内篇上》)
在叶燮看来,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主张诗三百、建安黄初以及初盛唐,然而诗沿袭已久,这种复古主义思潮影响了诗歌创作的正常发展,便有公安竟陵“起而掊之,矫而反之”。诗歌创作虽然能够跳出复古之“陈腐”,但又入偏奇之“颇僻”,或者“陈腐”与“颇僻”共存。他接着分析是因为称诗者“才短力弱,识又蒙焉而不知所衷”,既不知道诗歌创作演变之本在“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之理,也不知道“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分不清“沿”与“革”、“因”与“创”的关系,而“徒自诩矜张”,既欺骗了“他人”,也欺骗了“自己”。叶燮描述了诗论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提出产生之原因,针砭时弊。
而对于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提倡“文必先秦,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想遭到叶燮的强烈反驳,他不客气地说:“李梦阳、何景明之徒,自己以为得其正而实偏,得其中而实不及”(《原诗·外篇上》)。对于沿“前七子”而来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 叶燮认为他们“掇拾”前人之“皮毛”,但对于王世贞批评李攀龙的“剽窃摹拟,诗之大病,割缀古语,痕迹宛然,斯丑已极”给予正面的评价,认为“此语切中攀龙之隐,昌言不讳”(《原诗·外篇上》)。
在《原诗·外篇下》中,叶燮再次批评李梦阳、何景明,说他们理论上是以盛唐为尚,但在其创作实践当中,又学习了宋元习俗,指责他们对盛唐是“阳斥阴窃”或“阳尊阴离” ,分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欲高自位置,以立门户,压倒唐以后作者”等批评外因素之影响。
叶燮反对“伸唐而绌宋”的时风,认为诗有其演变的轨迹,踵事增华,以至于极。诗到宋,诗之变有其“理”,也有其“势”,即理当如此,也势必如此。他要求诗人应该正视这种演变,并给予其合理的评价,还宋诗以诗学的地位。对元人傅与砺《诗法源流》中“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人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的观点,叶燮提出异议,并列举唐人杜甫诗有议论,尤其五言甚,《三百篇》之“二雅”也有议论等为例得以佐证。
其实,叶燮批评近代称诗者的说服力还是不够的,理由有二:
一是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歧与间隙是存在的,而以“阳斥阴窃”或“阳尊阴离”斥责李梦阳、何景明,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叶燮说 “沈约云:‘好诗圆转如弹丸。’斯言虽未尽然,然亦有所得处。约能言之,及观其诗,竟无一首能践斯言者。”(《原诗·外篇下》)叶燮指出沈约提出的“好诗圆转如弹丸”之说,并没有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印证。其实,这在文学中极为常见。诗学观点的提出与当时的思潮有关。以明代为例,虽然前后七子标榜“复古”,公安竟陵提出“反复古”,但并不一定与其代表人物的创作实践完全相吻合,如清代陈仅在《竹林答问》所说的,“非特善评诗者不能诗,即善吟诗者多不能评诗”[4]2250。如果能阐释出诗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的一致性,似乎符合逻辑,但创作实践的复杂性并不是如此简单。两者的差异往往能给人以更加真实的感觉,也更加符合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的真实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也许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承认其间的差异性才是真实的还原,是可信的。因为,创作实践永远比理论丰富。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的一段表述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说:
自宋人好以议论为诗,发泄无余,神味索然,遂招后人史论之讥,谓其以文为诗,乃有韵之文,非诗体也。此论诚然。然竟以议论为戒,欲尽捐之,则因噎废食,膠固不通矣。大篇长章,必不可少叙事议论,即短篇小诗,亦有不可无议论者。但长篇须尽而不尽,短章须不尽而尽耳。……人但知叙事中之叙事,议论中之议论,与夹叙夹议之妙,而抑知叙事外之叙事,议论外之议论,与夫不叙之叙,不议之议,其笔外有笔,味外有味,尤为玄之又玄,更臻微妙乎![5]2333-2334
二是“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是从唐、宋诗比较中见特点,并不是说每一首唐诗、每一首宋诗都须具备此特色。我们不能忽视表述时的具体语境。叶燮以唐诗中有议论、杜诗中有议论、《三百篇》中有议论等为据来否定这种区别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正如在男女性别的比较中自然会凸显男女性别的差异,但如果将不同民族的男性或女性放到一起比较,那么,他们的性别差异可能会被淡化,而更加突出他们的民族差别。“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是讲其总的倾向,而不是说唐诗“不得不”以诗为诗,宋诗也“不得不”以文为诗。显然,叶燮批驳的正当性与科学性是有待商榷的。也就是说,叶燮在这里过分自信了!
叶燮对于诗评的方式也提出批评,认为诗如某某,或人或事或物等等,都是“泛而不附,缛而不切,未尝会于心、格地物,徒取以为谈资”,这种诗评,到了明代,“递习成风,其流愈盛”(《原诗·外篇上》)。叶燮借此表达了对这种诗评方式的不满。
总之,在叶燮看来,已有的传统批评思想与批评方法都不尽如人意,其批评的合理性不足,有效性不够,所以得出历来之评诗者“杂而无章,纷而不一”的结论(《原诗·外篇上》),要求他们为“诗道之不振”承担责任。
叶燮对历代诗论家的批评,一方面表现了他的胆识,坚持以“变”为核心,并以“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将批评对象置于绵延不断的历史轴上作出评判;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的批评弱点,即对于那些异己的诗论家少了几分宽容,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遮蔽他们思想中的合理元素。当然,叶燮对诗论家的批评既是真诚的也是勇敢的。对此,宇文所安给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把他说的“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的评价放到传统中国文学理论的语境之中才能体会到它有多么大胆惊人”,指出叶燮提出的观点,可以一劳永逸地避免个别看法所导致的错误和偏见。[6]547而叶燮正是这方面的尝试者,虽然被主流批评为“非论诗之体”,但也因此更加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叶燮的诗学批评,不仅有自觉的理论意识,更有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深刻反思。
二、对韩愈苏轼诗的批评
叶燮特别关注唐宋诗歌创作。他认为杜甫诗“独冠今古”,但“鼎立为三”中,唐人有二,宋人有一,表达了对唐宋诗人的高度赞扬。稍晚于叶燮的日本学者菊池桐孙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杜、韩、苏,诗之如来也;范、杨、陆,诗之菩萨也。”[7]226将杜甫、韩愈、苏轼三人诗喻为“如来”,当为创作之最高境界。缘其故,是杜、韩、苏三人的创作实践最符合他们的诗学要求。虽然叶燮高举杜甫诗,但在他以“变”为评价核心及其“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的批评特色中,韩诗与苏诗仍然光芒万丈。
叶燮对韩愈和苏轼诗之评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肯定韩愈和苏轼“变能启盛”
韩愈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虽有贬之“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冷斋夜话》引沈括语),有赞之“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但总体而言,其诗多以气势宏大与天真直率著称,如钱锺书《谈艺录》中所说的“豪侠之气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厉自温,与拘谨苛细之儒曲,异品殊科”[8]191。苏轼诗题材广阔,各体兼备,富于变化。宋人蔡絛称“东坡诗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9]257;李调元称“余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以其诗声如钟吕,气若江河,不失于腐,亦不流于郛。”[10]20叶燮也肯定韩愈诗,称之为“杰出”,当在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诸“专家”之上。
叶燮称道韩愈与苏轼诗能转风会,“变能启盛”,具有文学史意义,体现出他文学史家的眼光。叶燮认为,诗歌创作从天宝到大历、贞元、元和期间,诗风沿行百十余年,出类拔萃者甚少,诗之极衰,急需有力大者“起而拨正之”,或“弦而更张之”。当此时便有韩愈出,“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原诗·内篇上》)。诗之演变,长盛而衰,希求“变而启盛”。而在叶燮眼里,韩愈正是这位“力大者”,他转风会,“一人独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体之用,分条共贯,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也”。在他的带领下,“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他进一步称赞韩愈以“一人之力专,独立砥柱,而文之统有所归; 变盛者,群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诗之尚极于化。”(叶燮《已畦文集》卷八《百家唐诗序》)韩愈正是这样一位唐代贞元、元和间的“起衰者”,所以叶燮得出“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内篇上》)的结论。为此,陈寅恪《论韩愈》中有“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其地位价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11]。陈寅恪将叶燮在文与诗层面上的“变而启盛”提升到更广阔的文化学术史上的意义,对韩愈评价更高。
就苏轼诗,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认为,从韩愈开始的“以文为诗”到苏轼得以发扬光大,开启新的诗风,称赞苏轼“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左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12]1195,既指出了苏轼诗与韩愈诗之相关性,又突出了苏轼诗的特征。而就“诗变”而言,稍早于赵翼的叶燮在《原诗》中已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原诗·内篇上》)。他指出了苏轼诗题材广阔,嬉笑怒骂皆可入诗,随其触景生情,随意而出,肯定其为韩愈后诗之一“大变”之“盛极”,而“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余年而一变;或一人独自为变,或数人而共为变:皆变之小者也”(《原诗·内篇上》)。可见,苏轼诗影响到后世的百年,体现了其“变能启盛”的诗歌创作地位。叶燮在讲泰山云雾变化莫测后,特别提到苏轼的“我文如万斛源泉,随地而出”(《原诗·内篇下》),并以之作为自己论述天地变化莫测的有力证据。可见,叶燮用文学史家的眼光,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肯定了韩愈与苏轼能转风会,重启诗歌之盛,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二)称赞韩愈和苏轼“别开生面”
韩愈苏轼不仅能“变能启盛”,扭转诗风,而且都能做到“别开生面”,呈现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叶燮称道。
叶燮针对俗儒称韩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的说法,批评俗儒“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认为韩愈诗“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原诗·外篇上》),形成了如严羽所说的“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严羽《题柳柳州集后》),气势宏大。韩愈惟陈言之务去,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怪诞,以及语言形式的突破与变形等,在沿袭已久的诗风中扮演着“起衰者”的角色,以一人之力,独立砥柱,成为不袭古人而“转风会”的豪杰之士。他的五言长诗《南山》,全诗一百零二韵,长达一千余字,以其独特的连用七联叠字句和五十一个带“或”字的诗句,以赋入诗,铺写终南山之高峻,四时景象之变幻,气势如虹。其《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诗,显现出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有诸多“生新”的元素。另如《永贞行》《送无本师归范阳》等诗中求奇特、求新颖,甚至突兀怪诞之处也时有可见。在形式革新方面,如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所论述的,韩愈诗句法如“五言的诗句,大都是上二下三的,而他常有上一下四的”,章法如《南山》“这种连有或字五十个字以上,是很少见的”,用韵如《病中赠张十八》《忽忽》《嗟哉董生行》等“这些完全散文化的格式”也是不多的,被沈括概括为“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即在以上句法、章法、用韵等三个方面都有“不平常”的表现,也反映了在艺术形式上的别开生面。[13]482-483
苏轼诗也别开生面。叶燮说他开辟了“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好善而乐与,嬉笑怒骂”的生面(《原诗·外篇上》)。苏轼在其《答张文潜书》一文中曾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够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14]1461这里的“王氏”当指王安石。至于王安石是否真有“使人同己”倾向还另当别论,但他抹杀诗人创作的独特性这一点是不被苏轼看好的。苏轼说:“吾书虽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15]613此“不甚精”当属谦词,而“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倒是他一贯的追求。作为诗人的苏轼,既能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开拓新路。他的诗题材广阔,各体兼备,尤擅七言古体和律绝,风格也富于变化。钱谦益《读苏长公文》中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不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性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为,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牧斋初学记》卷八十三《读苏长文公》)可见,苏轼的确有其别开生面的贡献。
韩愈与苏轼能够“变能启正”“别开生面”,成绩斐然。他们都主张创新,反对蹈袭。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最。然则用功深得,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16]290可见,韩愈有着不与世沉浮的“求变”“求新”的自觉。叶燮曾说:“诗之亡也,亡于好名”,“诗之亡也,又亡于好利”。(《原诗·外篇上》)显然,韩愈既不为名也不为利。赵翼《瓯北诗话》卷三有“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12]1164在赵翼看来,韩愈学习李白与杜甫,特别见出杜甫诗之“奇险处”尚有拓展空间,并由此入手,自成一家。叶燮从诗歌创新的角度赞扬了韩愈诗。
苏轼也是全才文人,其诗、文、词的创作都有着文学史的价值。晚清词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黄庭坚称苏轼“文章妙天下”(《山谷论书》),且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有“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东坡先生传》)的记载。苏轼诗成果卓著,创新引路,为世人称道。现代学者胡云翼称赞苏轼“开辟宋诗的新园地,不让它永远依附唐人篱下,这便是苏轼唯一值得讴歌的伟大处所。”[17]52这里的“唯一”并不是说苏轼除此之外无其他建树,而是为了突出强调苏轼对宋诗发展的贡献,所以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说,苏东坡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18]436,评价甚高。
在叶燮看来,韩愈苏轼之所以能别开生面,是因为他们有才有力。他说:“韩愈、苏轼之徒,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载之。惟力大而才能坚,故至坚而不可摧也。”(《原诗·内篇下》)又说“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原诗·外篇上》),指出他们有其“才”,也有其“力”。当然我们读韩愈苏轼诗与文时,更能见出他们的“识”与“胆”。正如叶燮所云:“欲成一家言,断宜奋其力矣。夫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惟胆以张其才,惟力以克荷之。” (《原诗·内篇下》)而韩愈、苏轼皆具备“识”“力”“才”“胆”,一旦被现实生活触动,其思想、情感、词汇、句子等“劈空而起”。他们不是力弱者,“精疲于中,形战于外,将裹足而不前”,在创作中不寻求依旁;他们是力强者,“神旺而气足,径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奋然投足,反趋弱者扶掖之前”(《原诗·内篇下》)。所以,他们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因韩愈与苏轼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符合叶燮的诗学批评标准,所以得到他的高度赞扬。
其实,在中国诗歌史上为叶燮称道的诗人还有很多,但最能让他心动的还是杜甫、韩愈和苏轼三人,因为他们是“志士之诗”。在叶燮看来,人“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原诗·外篇上》)。他概括杜甫、韩愈与苏轼诗为“生面目”。“生”者突出其创新,“面目”突出其风格。李东阳《麓堂诗话》卷一曾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19]1386李东阳在此提出韩愈与苏轼对杜甫诗的继承性。日本学者长野丰山在其《松阴快谈》中也提出:“子美五七言古诗,惟韩文公善学之,至于五七律,未知属谁也。后人之诗不及子美,犹后人之文不及退之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惟二公足以当之矣。”[20]24
周振甫在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1993年版所写后记中提到钱基博在讲到杜甫诗风格时曾说:“韩愈、黄庭坚得其拗怒,白居易、苏轼得其疏宕”,即韩愈继承了杜甫的“拗怒”,苏轼继承了杜甫的“疏宕”,提及的也是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也就是说,叶燮喜欢这一路数。但因篇幅有限,被叶燮推为“独冠古今”的杜甫诗评价,笔者将另外论述。
总之,叶燮的诗歌批评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论诗者的批评与对诗人的批评。叶燮对历代诗论家评价不高,显示出他对诗论家批评的局限性。虽然批评总是离不开批评者的立场观念,但多少也显示出叶燮批评不切实际的苛刻。而他对于杜甫、韩愈、苏轼三位诗人的评价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重彩。正如蒋寅所说的:“杜甫承先启后,不仅集前代之大成,更开后世无数法门;韩愈惩于大历以来的成熟,一变以生新奇奡,遂发宋诗之端;苏东坡则尽破前人藩篱,开辟古今未有的境界,而天地万物之理事情从此发挥无余。”[21]78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