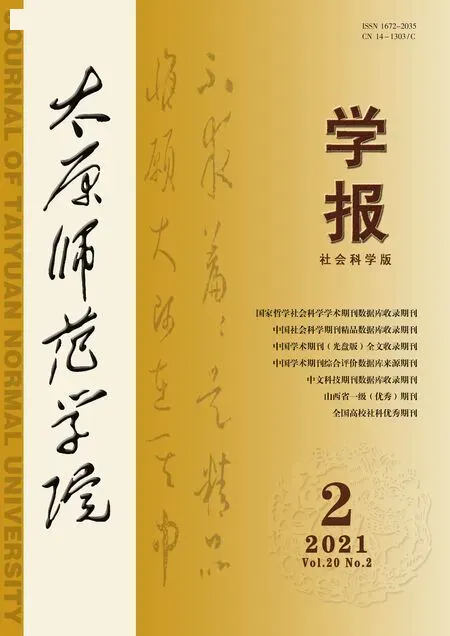从私奔叙事的改写看“三言”作者的性别立场
——以《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为例
袁田野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北京 100083)
本文以《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与同一故事题材的三个文本《鸳鸯灯》《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张生彩鸾灯传》进行比勘,从冯梦龙对这一私奔故事的改写入手,讨论“三言”作者的性别立场。《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出自冯梦龙纂辑的“三言”之《喻世明言》,其成书年代不详,刊行于明代天启年间。根据程毅中对《张舜美灯宵得丽女》题材来源的稽考,该篇目本事见《鸳鸯灯》,出自《蕙亩拾英集》。然而,《蕙亩拾英集》原文已佚失,现今能看到是《岁时广记》卷十二对《鸳鸯灯》这一篇目的缀辑。因此,《岁时广记》所辑录的《鸳鸯灯》应在《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醉翁谈录》壬集卷一)之前。这一故事入话为《张生彩鸾灯传》,收入《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改名为《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冯梦龙对此改动颇多。据现有研究对四部书籍成书时间的考证,可梳理出一条年代线索:本事见于《鸳鸯灯》(《岁时广记》卷十二),约问世于南宋嘉定年间;辟为《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醉翁谈录》壬集卷一),约问世于南宋嘉定年间;入话为《张生彩鸾灯传》(《熊龙峰四种小说》),刊行于明万历年间;收改为《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喻世名言》),刊行于明天启年间。
最初运用文献比勘的方法探讨“三言”性别话语的是学者刘果。刘果所著《“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一书通过文献比勘,发现“三言”的叙述者用主流性别规范对宋元话本中女性的失范行为进行了一次次修正。在对《张舜美灯宵得丽女》这一篇目的分析中,刘果通过将其与话本《张生彩鸾灯传》比勘,从殉情话语的解体、性别角色重塑两个方面分析了主流性别规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修正,刘果的研究为“三言”性别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将同一私奔故事题材的探寻延伸到了更早的时期,选取《鸳鸯灯》《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张生彩鸾灯传》三个文本与《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一文作一比勘,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三言”作者的性别立场进行补充说明和相关考证。
一、对女性主体性的削弱
通过对叙事作品中人物结构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三言”作者对女性人物主体意识的削弱。在《鸳鸯灯》与《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故事是围绕女主人公追求爱情的欲望动机展开的。男主人公张生是女主人公欲望的指涉对象。女主人公通过掷帕寻觅才郎,主动邀约情郎私会,最终跨越礼制的藩篱与情郎私奔,在以满足自身情欲诉求为目标的行动中,女性人物获得了主体性。通过比勘,发现《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对叙事的初始情景和部分情节作了改动。首先,《鸳鸯灯》是以女主人公掷帕这一事件作为初始情景,使女性人物成为了叙事的主体行动元。而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是以张生拾帕作为初始情景,叙事的主体行动元也由女子替换为张生。其次,在《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女子在与张生初次相逢时,通过“匀面”先行发出感情诉求。而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这一行为被删去,使人物的施受关系发生变化,削弱了女性人物的主体性。
(一)初始情景的不同安排
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初始情景中,张生拾到红绡帕,思慕绡帕主人,渴望与之相会。不同的是,在《鸳鸯灯》中,故事的初始情景叙述的是一位美妇人在寺庙中祈祷,取出红绡帕和香囊持在香上,默默地祝告,出门后故意把红绡帕和香囊掷之于地。我们可将两个文本中初始情景列表比较,见表1:

表1 《鸳鸯灯》与《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初始情景对比表
初始情景的不同安排会对故事的话语结构构成影响。如表1所示,在《鸳鸯灯》中,美妇人“默祝久之”的行动表现了她追求爱情的强烈欲望,也就构成了故事的意图因素。因此,在这个故事中,女子这一人物具有主体性,其扔下香囊与红绡的行为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变化与发展。这一行动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希望才郎拾到香囊与红绡后,接收到她所传递的情意,达到求爱的愿望。可以说,在这样的叙事安排中,女子充当着主体行动元的角色,拾帕人张生则充当着客体行动元的角色。与之不同的是,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出现在叙事开端的情景是张生拾帕,倾慕绡帕的主人,并采取行动,希望与女子相会,成就佳缘。此处,张生便充当了主体行动元的角色,而他追求的目标,即绡帕的主人则成为了其行动的客体对象。
《鸳鸯灯》产生于宋代,在时间上早于《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将《鸳鸯灯》中美妇人持香默祝和掷帕这一事件删削,或是出于作家增加悬念的艺术性需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人物的主体性。以男性人物张生拾到绡帕开始讲述故事,就使张生反客为主,成为了故事的主体行动元。
(二) 女主人公“匀面”行为的删削
《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与《张舜美灯宵得丽女》都详细描写了张生与红绡帕主人的相逢场景,对此,两个文本的情节大致相同,男女主人公初次相逢的时间都是十四日晚,比红绡帕上约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张生向女子表明身份的方式都是吟诗;女子都是托别人向张生转达邀约。
而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在于,《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多叙述了一个事件,即女子在马车中掀起车帘,持镜匀面,借机让所约之人看到自己的容貌,而张生见到女子容貌后大为动情,但急于无计通名,次夜才设法吟诗表明自己的身份。《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出自宋代的《新醉翁谈录》,在时间上较《张舜美灯宵得丽女》早,可见其女主人公“匀面”行为是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被删削了。我们可将两个文本中二人的相逢场景列表比较,见表2。
如表2所示,在《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张生遵守绡帕上所定赴约,果然守见了一辆灯挂双鸳的马车,车里的女子掀开帘子,持镜匀面化妆。此时,叙述者转到女子的内心世界,解释女子这一行为的原因,“意者,恐去年相约之人,未见奴面,故托以匀面,使人观之。生凝顾,但见花容艳质,赛过嫦娥,万姿千娇,不能名状。生牵役轻情,无计通意女郎”[1]97。在这一个版本的故事中,两人经过两次会面才互通情意,初次相见时,女子假借化妆来向众人展现自己的美貌,张生因此大为动情,第二天再见时才借机向前与女子相认。《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则删去了女子匀面一事,使张生在未得见女子容貌的情况下就主动吟诗通情,女子也未完全打开车帘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容貌,只是掀开一条缝隙“窥”张生。

表2 《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与《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相逢场景对比表
两相比较可知,在《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的相逢场景中,女子是先行施动者,张生则是受动者。女子通过展现容貌的行为先行发出了感情诉求,在获得张生诵诗回应后,马上提出进一步的邀约。而《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在删去女子匀面情节后,张生转为先行施动者,女子转为受动者,女性人物的主体性由此削弱。
删削女主人公“匀面”行为也体现了对女性行为的限制。南宋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社会对女性的限制逐渐严格,女性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被认为是不合礼法的,要求女性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在同样出自“三言”的作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叙述者就借蒋兴哥之口道出对女性的这一闺训:“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2]346此外,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女子也由《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的“遂启帘,顾之张生修眉俊目,骨秀神清,真风流之士”变为了“启帘窥生”,由大胆的顾观变为窥视,目光中隐含的情感也由直呈袒露变为羞于表达,这也是叙述者调和情与礼的表现。
二、对“情”的象征化处理
在这个以情爱叙事为主的私奔故事中,值得注意的是“情”的呈现方式。首先不可忽略的是诗歌入话的抒情作用,一者为男女主人公通情达意之媒介,二者亦可抒发人物的情感。四个文本皆以诗歌传情,所引诗歌也大体一致,但《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在诗歌内容上改动颇多。其次《张舜美灯宵得丽女》虽然与其他三个文本存在诸多差异,但将女子与张生相会时以道装掩红裳这一情节保留了下来。
(一)情诗的改写
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这一故事中,诗歌是男女主人公互通情意的媒介物,因此这一故事中的诗歌主要起到三个作用:一是在叙事上充当了事件发生的引子,二是抒发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三是表现人物的才情,呈现“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上溯到同一故事原型的其余三个文本《鸳鸯灯》《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张生彩鸾灯传》,发现四个文本故事中采用的诗歌在数量上存在差异,见表3:

表3 四个文本故事情诗数量分布表
如表3所示,对于女子题在红绡帕上的诗,《鸳鸯灯》中有三首,而张生的和诗亦有三首,共六首,应是对原作的全引。《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只引用了原作中的四首,在创作时间靠后的话本《张生彩鸾灯传》中只选取了其中两首入话。梁冬丽认为,小说对原素材中的诗词不能全引是因为受到篇幅限制,“如果全部选入,那么入话的篇幅将会很长,就会盖过正话的气势,那就喧宾夺主了”[3]78。
“三言”的《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也只选了两首诗入话,一是女子在红绡帕上的题诗,二是张生的和诗。将这两首诗歌与《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及《张生彩鸾灯传》中的原作进行对比,发现冯梦龙在选编这两首情诗的过程中,对原作诗歌进行了局部文字的改动,见表4:

表4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对原作诗歌的改动
原作诗歌中“囊里真香谁见窃”的“窃香”在古代社会有男女偷情之意,源自晋代“韩寿偷香”的典故。冯梦龙用“心事封”三字将“窃香”之意抹去,使情欲转化成了封存的少女心事。此外,原作诗歌中“殷勤遗下轻绡意”表现的是女子一种刻意扔下轻绡作为信引的行为,意图使情郎拾到绡帕,既可通晓她的情意,又可置于袖中作为定情之物,此中寄托了与情郎长相厮守的愿望,此意可结合《鸳鸯灯》中另外两首未删的诗看出。冯梦龙却用“聊作”二字淡化了原诗中寂寥女子渴望爱情的殷切情感,使女子主动求偶的行为转为一种含蓄表达,而这种矜持端庄的淑女形象显然更符合主流性别规范。
对于张生的和诗,冯梦龙也有所改动,将“琼体腻”改作“玉手封”。原作诗歌中的“琼体”与“杏腮”都是张生对遗绡女子的一种性幻想。“琼体腻”写出了女子胴体如琼玉一般洁白细腻的质感,冯梦龙将这个略显香艳的词语删去,应是出于净化文本的目的,侧面体现了作者以理性抑制情欲冲动的道德观念。
(二)隐藏于道装下的红裳
尽管这个故事在四个文本中存在颇多差异,但有一个情节因素却从头至尾都被保留了下来,冯梦龙对此基本未作改动。在故事中,女子与张生通情达意,让张生次夜在旧地等候。张生如约而至,却只等来一辆青盖旧车,车中坐着一尼。尼在车里招手示意,张生便随马车潜入寺庙。到了寺院中,尼卸去道装,忽见“绿鬓堆云,红裳映月”[2]479。“绿鬓堆云,红裳映月”八个字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一字不改地留存下来,无论作者有意或无意,其间却隐喻了一种跨越时空的隐秘同构。
道衣可视作一种特殊的服饰符号,不仅凝聚着宗教精神,而且意味着向内不生五情,不起妄念,保持心灵的清净无染,外在行动则需遵守清规戒律,一言一行都需严格遵守戒律。女子在外只有身着道衣才能避人耳目,也隐喻着妇女需要压抑自身情欲,用性别规范律己。
道衣之下的红裳更接近一种隐喻,即理学压抑不住人内心的真情,清净的道衣之下隐藏的是火焰般炽烈的情欲。尽管作者对“情”进行象征化的处理,但并没有否定“情”的合理性。正如冯梦龙在《情私类》卷末所作的批语,“人性寂而情荫。情者怒生,不可閟遏之物”[4]35。
三、对男性背弃情节的弱化
《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与《张舜美灯宵得丽女》都有女主人公在私奔后被弃于异乡这一情节。但将两个文本相对比,作者对男主人公背弃行为的态度却存在差异。《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的作者直接点出了张生的负心行为和道德背弃,并加以谴责。《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男主人公也存在背弃行为,但作者却意图为其辩白,通过渲染男主人公的痴情,弱化其背弃行为。下面将两个文本中的背弃情节对比分析,见表5。
如表5所示,在《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叙述者为了强调张生的负心,直接呈现了张生的内心独白:“李氏虽有厚恩,我往见,共受饥饿,死亡可待,不若辜负李氏为便。又况越英容貌聪慧,差胜李氏”[1]101。可见,背弃李氏是张生权衡利弊后的结果,一方面,抛弃李氏,迎娶富家女可使他摆脱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张生不顾李氏对他的厚恩和情意,用容貌等条件衡量两个女性,使女性成为物化的存在。

表5 《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与《张舜美灯宵得丽女》背弃情节对比表
对于张生的负心行为,女主人公李氏痛斥张生“辜恩负义”,新娶的妻子越英也并未袒护张生,“君既有妻,复求奴姻,是君负心之过”[1]102。最后,包公作为“公理的化身”对张生的负心行为作出了权威性的判定。可见,作者是从道德理性出发,透过不同人物的看法集中对张生的负心行为加以批判。
此外,通过刻画女主人公李氏的披心相付,也反衬出了张生的忘恩负义。张生对李氏多次发下誓言,当真正面临生存的艰难时,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弃。李氏的至情则与张生的薄情形成鲜明对比,她卖了曾保之如命的秀发,得衣数件予张生以备路上之需。张生一去不返,她也坚信张生不会负己,还担心张生会因饥寒困于路,“生衣薄天寒,裹粮不足,必是困于道路,乃能过期不归”[1]102,于是一路乞讨,踏上了寻夫之路。由此可见,作者的批判立场十分鲜明,并且意图通过表现李氏的忠贞来为李氏正名。作为李公的偏室,李氏以已婚女性的身份私奔,无疑要背上不忠的名声。在私奔后的故事中,李氏充当的是奉献者与守望者的角色,由弃夫私奔到乞讨寻夫,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但作者的思想仍不能超越封建社会制度的限制,即便对张生持批判态度,在结局部分仍安排李氏与张生和好成婚,使张生在负心后仍有个好结局。
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女主人公素香的被弃看似是巧合,实则是由张舜美间接造成的。在两人分散之后,张舜美没有按照两人约定好的方向前行,反而选择返回素香家里寻她。在张舜美的认知里,素香作为女性,适合她活动的领域还是家庭,即使暂时出走,但因其作为妇人“身体柔弱”,在外失去男性的庇护,便只能返回家中。另外,看到素香留下的鞋,舜美在没有获得确切信息只是听人谣传的情况下就认定女主人公已投水而死,而不去深究女主人公自戕的动机和可能性。他似乎默认了女性的脆弱、非理性和依赖,在违背礼制私奔后,只能以压抑自己的生命作为归宿。
从以下三个方面也可以推断出,作者是站在男权中心的角度支持张舜美的选择的:第一,在两人分散的场景中,故事外叙述者以权威的声音对女性人物的小脚发表了一番评论,“你道因何三四里路,走了许多时光?只为那女子小小一双脚儿,只好在屧廊缓步,芳径轻移,擎抬绣阁之中,出没绣裙之下。脚又穿着一双大靴,教他跋长途,登远道,心中又慌,怎地拖得动?”[2]481此处叙述者的评论进一步解释了张舜美的选择,即女性的小脚只适合在户内行动,不容许她们走出家门,长途跋涉。第二,尽管都离开了家庭空间的束缚,李氏与素香行动的自由程度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女主人公李氏出入市场鬻发换衣,后又一路乞讨寻夫,状告官府,行动的自由程度较高。与之相对的是,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素香在社会空间中的行动显得过分谨慎小心,严守女性在外“不抛头露面”的行为规范。对此,小说让素香乔装成男人出行。叙述者极力描绘女性小脚赶路的不便,又细细谈到素香行事如何谨慎,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女身,并为素香安排了尼姑庵作为唯一可容身的去处。身处尼姑庵同样也要遵守清规戒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女性人物的贞操与纯洁性。第三,在故事的结局部分,张舜美和素香回到家乡杭州后,径到素香家中投帖拜望,素香的父母见到少年夫妇俱喜,于是大摆筵席,作贺数日。在这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背后隐藏的叙事是,即使女性因追求爱情自由出走家庭,最终也还是要返回家中,获得自己父亲的允许,婚姻才算圆满。由此可以看出,《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作者认为女性的行动范围应限于户内,而家庭以外的社会空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女性一旦在户外空间失去男性的庇护,除非进入尼姑庵保持贞洁,否则便只有三种结局:返家、堕落或死亡。在这种认知的驱动下,作者才让张舜美做出了背弃素香的选择。
虽然致使素香被弃的原因是张舜美的男权意识导致的错误判断,《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叙述者却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男主人公张舜美,细细描绘张舜美因痛伤素香而患病,又如何怅然泪洒。叙述者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评价道,“相思相见知何日?多病多愁损少年”[2]482,在渲染男主人公的痴情时,弱化了他的背弃行为。
相比宋代同题材故事文本,“三言”中所体现的父权观念更为强烈,对女性的束缚更为严苛。“三言”的作者虽然肯定“情”的合理性,但同时也维护着压抑女性的礼制,在对私奔叙事的改写过程中,作者完全按照父权意愿雕塑女性,使其沦为被动的失语者。此外,作者还以妇人“小脚”“柔弱”作为借口控制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私奔也就仅仅意味着从父权的家门走向夫权的新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