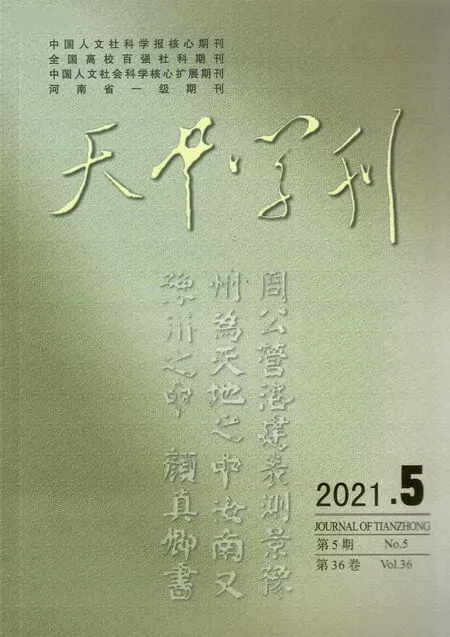个体诗意与共同体想象
——李佩甫创作论
王华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李佩甫涉足文坛30余载,其创作紧扣时代脉搏,与新时期尤其是21世纪以降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彼此呼应。作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李佩甫的文学世界却能同时从城乡两大空间汲取用之不竭的养分与力量。即便远赴省城生活和工作,其创作的坐标系也从未离开平原这一独特的审美空间,直至“平原三部曲”,李佩甫为自己贴上了平原叙事代言人的诗意标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李佩甫将对平原的想象与书写视作自己的文学使命与美学追求,不论是对共同体的想象还是对个体的述说,无不代表他对中原人性格抱有的诗意化理想。所谓的“一方水土”指的是共同体,所谓的“一方人”指的是个体,共同体和个体交织于由李佩甫建构的乡土文学空间中。
李佩甫的创作往往超越个体的得失,站在重构共同体的高度,在个体与共同体的碰撞与交织中反思时代精神与现实存在,想象并找寻回归家园的诗意道路。共同体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存在形态与组织形式,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共同体包含了人类存在的集体化传统常态与个体化新形态,以及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博弈,是理解李佩甫文学创作的重要线索。李佩甫通过自己建构的文学世界完成了对共同体的诗意化想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商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传统个体和共同体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蜕变与衰落,如何在充满碎片、解构与异化的当下继续表达乡土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与集体精神,是李佩甫一直在深入思索的问题,也是其共同体理想主义的想象根基。
一、小人物,大英雄
生长于城市的李佩甫是标准的城里人,但其创作的源头却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乡村。李佩甫擅长描写底层劳动人民的现实体验与边缘生活,其作品因对中原乡土文化母题以及中原人遭遇的空间挤压、身份迷茫、伦理选择等的深刻书写而备受关注。“作为人,我们既不能实现希望,也不能不再希望。”[1]李佩甫在挣扎,其作品在挣扎,作品中的小人物也在经受着来自灵与肉的双重考验与内外挣扎。李佩甫作品中的小人物大都是残缺的,有的生理上有残缺,有的精神上有残缺,有的身份上有残缺,但面对现实的苦难与命运的不公,他们又不得不承载中原人身上独有的坚韧、不屈与坦然。李佩甫试图借助小人物为中原底层人民发声,揭示中原文化及其地域精神本质上根植于小人物的自我肯定。对于小人物而言,他们对集体或共同体的本能渴望更加强烈,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重担,他们需要彼此守望相助以实现属于他们的共同生活。“就其存在而言,人是来自共同体的存在,他受到共同体的照料,并面向共同体的存在。对人来说,存在(to be)就意味着同其他人共存(to be with)。他的实存就是共处(coexistence)。”[2]共同体已经成为李佩甫笔下小人物最渴望获得的基本存在方式,他们看似个体化自由化存在的事实背后掩藏着对重构共同体的期待与坚持,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对未来的大胆设想和对命运的英勇抗争,他们成为来自底层有理想、敢行动的“大英雄”。
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形象、日渐凋零的乡村世界以及与乡村剪不断理还乱的城市边缘地带,无不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李佩甫小说中的小人物大都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的城乡空间错位感与地域陌生感,基于寻梦的渴望抑或迫于生存的压力,他们从乡村涌至城市,又从城市逃回乡村,在经历无数次往返之后,他们不仅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同时也给乡村空间带来了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骚动,这或许正是他们在夹缝与挣扎中的生存之道。《城的灯》的主人公冯家昌是标准的底层小人物,他利用参军等形式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和身份转变,成为4个弟弟心中八面玲珑的大英雄。“乡下小子”冯家昌虽有成功的骄傲与自豪,但作为乡村逃离者的他,最终还是因为在城市遭遇身份迷失和在故土遭遇精神困境而自责与忏悔,但已无法回到逃离前的过去。所以说,这种看似琐碎杂乱的城乡底层语境的建构,不经意间拉近了广大读者与小人物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也缩小了艺术审美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空间阻隔,使读者在无形之中感受到小人物背后的分裂、无助与漂泊,以及他们对平原精神的守望和平原人性格中的坚守。乡土是真正属于小人物的精神共同体,这同时给予他们成为时代英雄的巨大力量。
李佩甫大部分的小说都把小人物经历的现实磨难作为对中原精神的忠诚践行以及帮助他们实现从小人物到大英雄蝶变的必经之路。小人物的生活似乎总是不如意多于如意,尽管他们不得不忍受身体或精神层面的煎熬与摧残,但总是忍辱负重前行,延续着自己作为小人物应有的担当,并对由“真善美”构成的乡土共同体保持着坚守的初心,无论身处城、乡都表现出英雄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多少带有古希腊神话的悲剧色彩与英雄情结。《生命册》中身材异常矮小的虫嫂,外表看起来侏儒,内心却非常强大。为了供养三个孩子上大学,她放弃脸面与尊严,甘愿收破烂,以卑微的一生换取儿女的出人头地,最后用小人物的卑贱铸就了大英雄的崇高。李佩甫笔下的小人物有着很多共同的生命体验,他们大都生活在社会底层,有着不愿提起的过往;他们大都承受着现实的重压,有着不想触碰的灵肉伤疤;他们大都背井离乡怀揣梦想,有着不堪回首的经历与体验。他们是坚守乡村共同体的“老实人”,面对乡土巨变与时代机遇,拼命想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虽有犹豫、胆怯与退缩,但他们依然对未来抱有期望,希望自己踏出一条属于时代英雄的道路。小人物的一生虽缺乏真正的壮举,甚至处处留有悲剧的色彩,但正是这种悲剧化的体验为他们增添不少英雄的力量与气质。
古希腊以降,英雄在西方世界莫不遵循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提出的“隔离-启蒙-回归”模式,这样的英雄养成之路在中国底层英雄身上同样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甚至已经被贴上类似的标签。与毁于欲望的骆驼不同,《生命册》中“喝百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吴志鹏虽有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回馈故乡的决心,却一生漂泊于城乡之间,游离于自我之外,始终难以获得真正属于自我的身份认同,默默承受着小人物的酸楚与无奈,但其守护故土家园的灵魂却从来没有迷失。对李佩甫笔下的小人物而言,隔离意味着背井离乡挤进城市,努力为自己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启蒙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挣扎,一种“留而不能、走而不愿”的痛苦与徘徊;回归指的是在经历了城市的排挤、失落与失败之后,又一次回归曾经属于自己的现实空间,并希冀再次获得灵肉与身份的双重认同。毋庸置疑,小人物已经具备了成为“大英雄”的潜质,在他们看似平凡的空间经历中,内在精神的凝聚与升华被凸现出来。事实上,他们对乡土世界的逃离,是一种看似解构的重构,在经历一番或波澜壮阔或迷失自我的城市空间之旅以后,他们逐渐成为守护乡村共同体最后的英雄,这是一种滕尼斯式的对共同体的前现代解读。滕尼斯认为,和他人共处的愿望普遍存在于所有人心中,共同体如守望相助的和谐家园一般成为人们的集体精神与共存意志,并最终成为默认一致的存在状态与空间形态,具体到小人物身上正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以期建构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规范体系和空间秩序。
小人物身上的乡土标签应该呈现更深层的隐喻意义,也就是通过在城乡间的徘徊和挣扎,他们准确诠释了自己才是乡村共同体真正的守护者以及小人物身上具有的英雄精神。小人物建构了乡土文化的精髓,善良、淳朴、勤劳、正直的乡土品格在他们身上尽显,其内心对乡村共同体的共识早已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人物代表着乡土世界最原始最自然的力量,与乡村浑然一体,并由此获得诗意化的个体存在感与归属感,尽管这样的感觉并不一定真实可靠。李佩甫正是通过小说人物频繁地在城乡空间位移及随之做出的种种选择,一步步把生在农村的小人物练就成有担当、有情怀的“大英雄”,树立起一个个底层英雄形象。小人物的价值在于他们对内心的坚守、对责任的担当和对英雄的崇尚。李佩甫正是以小人物的视域,书写着底层个体对英雄主义的诗意想象与追求。
二、小体验,大伦理
小说是现实体验的记录,也是伦理精神的文本。李佩甫的创作聚焦于中原大地,以对中原人性格、精神和伦理的挖掘见长,作家本人对现实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观照充满明显的伦理想象,李佩甫“50后”和知青的双重标签为其文学创作中的伦理书写提供了现实契机。李佩甫善于捕捉各色人物的道德体验,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起带有“平原”气质的伦理精神。在其首部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中,李佩甫已经试图以伦理的视域看待商业浪潮对乡土世界的冲击与破坏。所以,“小说所叙之事,往往是处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情景之中的人的事,而这些事里不仅包含着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反应,也反映着作者的道德态度和道德立场”[3]。伦理共同体在李佩甫的作品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既有对传统伦理的坚守与升华,也有对新型伦理的解构甚至消解,或许这种包含着伦理异化元素的共同体更有可能再构成另一种形式的伦理共同体,因为共同体不仅是对共同点的概括,同时也是对异质性的吸纳与融合。基于此,伦理也好道德也罢,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并不意味着李佩甫是在鄙夷或要抽离道德,恰恰相反,在他的创作中,道德一直处于敏感的核心部位”[4]3。实际上,李佩甫在其作品中呈现出的道德观很多时候会被外界曲解甚至误解,他的本意绝不是要解构道德在当下社会的存在感与合理性,也不是要为道德式微找到现实的根基,而是努力为道德重构与复兴进行诗意化的想象和审美化的再构。基于此,乡土被李佩甫赋予伦理秩序重建的重任,这一点非常符合涂尔干对共同体的道德性期待。然而,乡村社会在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中出现道德失范、伦理失序等不和谐现象在所难免。涂尔干指出:“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5]这种规范体系正是一种道德共同体。很显然,与滕尼斯相比,涂尔干对共同体的态度更加积极和乐观,因为滕尼斯认为共同体“解构”本质上就是家园衰落与关系解体。
李佩甫在怀念或追忆传统伦理共同体的同时,也在努力将凌乱不堪的伦理碎片重新置于某种合乎理想或逼近现实社会的共同体框架内加以重组。正如滕尼斯从理论层面分出共同体与社会一样,其本意是为了在金钱至上、人情冷漠的现代社会中寻找记忆中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生活方式。“呼家堡人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只有一个声音的日子,如果这声音突然消失的话,呼家堡人倒不知道该怎么活了。”[6]呼家堡这种自上而下“步伐一致”的生活模式明显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绝非仅仅是作家个人的伦理理想,中原大地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李佩甫也早已形成儒家共同体的惯性思维,并直接影响其文学创作。“我的源头,也许缘自儒家文化的浸泡或者说是桎梏,这是锁链也是营养体”[7]。与儒家文化一样,李佩甫习惯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放在伦理的框架下建构,他们很难摆脱各种伦理阻力甚至困境,诚如《生命册》中被嵌进城市的吴志鹏,尽管已经拥有城里人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依然无法割裂与农村故土乡亲的伦理关系,他的肩上扛着自己根本无法承受的伦理之重。但是,这样的伦理压迫于他们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其中还包含着李佩甫对基于伦理共同体的诗意想象。
知青和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独特经历,使得李佩甫对琐碎生活的伦理化想象交织着诗意与纠结。这种个性化的伦理表达,精准表现出作家对平原大地做出的道德反应与伦理判断,诗意与纠结绝不是彼此对立的两级,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关系,这是作家赋予乡土世界的伦理理想。李佩甫指出,像他这样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受过理想主义熏陶或梦想教育的一代。这代人有底线,是相对保守又不甘沉沦的一代。在单一的年代,我们渴望多元;在多元化的时期,我们又怀念纯粹”[8]。这种看似矛盾的伦理理想,不仅是对乡土精神家园的守护,而且是对记忆中现实体验的回望,尽管在李佩甫看来它的根基已经被动摇,甚至摇摇欲坠。在《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中,尽管李氏的血脉依旧代代相传,但是困顿、逃离和遗忘已经充斥乡土世界变迁的全过程,传统经验不再是现实的参照,伦理道德不再是空间的秩序。李佩甫通过对传统与当代、祖辈与后代的糅合,实现了对家族变迁和时代裂痕的精神叩问与道德评判,其内心虽充满苦楚与感慨,却依然真诚而诗意地再现了乡土世界发展变化历史进程的原本面目,看似感性批判的背后蕴含着理性的审视。《城的灯》凸显了作家对伦理式微和精神贫瘠的深度思考,作品中的刘汉香正是作家力图通过审美再造拯救伦理共同体于深度解构的诗意努力。作为李佩甫心中伦理的诗意化身,刘汉香被放在一个不是圣女胜似圣女的位置上,身上被赋予太多的传统优点,这样的重压使得她无力承担,最终香消玉殒,但也因此成为作家笔下的诗意传说。纵观李佩甫的小说创作,他从未停止找寻道德复兴道路的努力,他的伦理理想在其对红旗渠精神的讴歌中抵达高潮。红旗渠精神不再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在今天被进一步凸显出来,抑或说红旗渠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生活的当下时代,我们的时代更需要红旗渠精神来滋养。从这个视角来看,红旗渠精神是李佩甫对道德伦理的理想化重构与诗意致敬。
李佩甫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建构一个诗意化的伦理空间,尽管他同时受困于自己想象的审美世界,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通过伦理拯救现代性道德困境的诗意努力。《城的灯》中被冯家昌抛弃的刘汉香,身上有着诸多中国传统的乡土美德,她勤劳勇敢、胸怀宽广,用个体的力量苦苦支撑着日渐衰落的传统伦理共同体,她不只是乡土伦理的挽歌,更是李佩甫拯救传统伦理的诗意呐喊。正因如此,伦理在李佩甫的文学空间中不只是一种规训力量,更多的是一种拯救手段。虽然这种对伦理的审美化重构不一定真实可靠,但却直逼作家内心为伦理保留的诗意空间,这绝不是李佩甫一厢情愿的呐喊,相反承载着整个时代对伦理的呼唤。面对现实伦理的无力甚至异化,或许审美化、诗意化的想象与努力更具震撼力,也更加符合时代的声音与期待,尽管这样的想象多少带有悲观的色调。《金屋》是一部充满焦虑、迷惘和恐惧的作品,在其中,传统的伦理共同体正在悄然坍塌,另一个由金钱架构而起的利益共同体正在迅速崛起,缺少了伦理支撑与精神支柱的乡民在寻求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弄丢了过去、迷失了自己。李佩甫对转型时代的揭露与批判可谓直指人心,在作家的心中,“金屋”正是对无法预言的平原大地的空间化美好愿望,然而理想再丰满,最终还要面对现实的慌乱与失序、过去的解构与逝去。“如果要为李佩甫的小说世界找到一个精神象征的话,那么这个形象就是大地。诸如《红蚂蚱 绿蚂蚱》中童稚天真的土地,《李氏家族》里埋葬先祖、繁衍生息的大地等。”[9]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原大地正是托起李佩甫伦理理想的诗意空间,所有的伦理事件、道德实践都建立在这片大地的基础上。如此众多的琐碎化生活体验,背后承载的是作家内心一直努力重构的大伦理。李佩甫对伦理的诗意想象虽遭遇过瓶颈却一直都有突破和超越,他试图以让筷子立起来的决心为这个社会想象并建构一个充满诗意与美好的伦理大厦。
三、小空间,大时代
李佩甫虽没有农民的身份,却有着对乡土世界的偏爱与执着,他对自己曾经生活的中原大地有着无限忠诚,这一切都取决于李佩甫的内心藏着一个童年的梦想。“在人类的心灵中有一个永久的童年核心,一个静止不移但永远充满活力、处于历史之外且他人看不见的童年,在它被讲述时,伪装成历史,但它只在光明启示的时刻,换言之,在诗的生存的时刻才有真实的存在。”[10]李佩甫始终把自己看作乡下人,流连忘返于狭小而又狭隘的乡土空间,对中原乡土世界的讲述充满着诗意与美好。李佩甫养成了每天饭后散步的习惯,“很多个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样在各个街头徘徊,想写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11]。正是由于频繁游走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李佩甫才能在其作品中完成对乡土空间的诗意想象与审美再现,使得其作品以小空间见证大时代,呈现出不一样的厚重与深度。
共同体空间和个体空间在代表客观存在事实的同时,也象征了一种精神层面或者文化意义上的营构。基于这样的认知,空间不再只是背景架构或方位参照,而是价值或意义关系建构的过程。李佩甫曾经说过,他的根在中原大地,他是这片土地的儿子,虽然他已经离家多年,但其内心一直都为记忆中的故乡留有空间,关于乡土的记忆挥之不去。与其他乡土作家不同,李佩甫的故乡既是城市的又是乡土的,出生在城市和下乡当知青的双重经历给他的创作带来更多、更大的空间想象。自带中原气息的《羊的门》,虽以“呼家堡”村这一小空间为主线,但它的外延却很大、很广,与外界的县、市、省甚至国家都有密切关联,所有发生在村子里的事情,都是对现时代的真实呈现。所以,李佩甫对乡土的记忆与想象表现为一种视域上的融合,换句话说,李佩甫对乡村的书写带有城市的痕迹,对城市的再现带有乡土的味道,这就使得其笔下的创作空间能够以小见大,真正做到基于某一空间点反映大时代。这种视域融合让作家游离于城乡空间之外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真正近距离感知城乡迥异文化的机会。
空间是承载小说叙事的地理性共同体存在形态。李佩甫始终在寻找不同空间下的共同体验,其作品包含的诗意既是语言层面的,更是情感层面的。虽然李佩甫的文学创作更多地聚焦于乡土空间,但他并没有无视城市化带来的空间位移与情感错位,无论其创作的背景在乡村,还是书写的对象是城市,读者都可以轻易感受到“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城乡共同体意象,这就使李佩甫在创作中呈现出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宽广的胸怀,他可以将复杂的现实和伟大的时代浓缩于某一特定的空间,借此赋予城乡巨变以共同体经验和诗意价值。《生命册》承载的现实空间明显要大于李佩甫过去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城市与乡村浑然一体、难分彼此,共同的命运推动城乡共同体的加速成型。城乡空间双重体验不仅呈现整体意义上的普遍性,而且具有个体层面上的独特性,这种对城与乡的双重体验和记忆同时蕴含着差异与融合的二维含义。换句话说,城乡共同体绝不仅仅建立在彼此融合的基础上,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现实背景下为共同体关系重构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李佩甫将创作的视域定格于乡野村庄或大街小巷这样的小空间,通过以小见大见证大时代所包含的温情与苦楚、现代与传统、诗意与失落,作家用自己既恢宏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处在频繁巨变中的大时代,将叙事的背景设定在看似狭小的复杂空间中,通过山川河流、村舍和大街小巷等小空间折射出大时代的众生百态和复杂人性。伦理裂痕、城乡差异、贫富悬殊、观念冲突和梦想迥异建构起一个充满选择、迷失和醒悟的现实漩涡。在复杂多变的小空间中,大时代的千姿百态得以全面呈现,既有人性的险恶与自私,更有生活本身的真善美。李佩甫笔下生存于各式小空间的人物,虽自带底层人的劣根,但他们人性的底色依然温暖有光,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大时代所需要的勇气、担当与使命。作家正是从一个个个体身上展开对共同体的诗意想象与理想化重构,其笔下的小人物虽来自底层、缺少话语权,却在大时代的洪流中生生不息,他们甚至已经超越个体的意义,具备了诗意想象和建构生命共同体的内涵。李佩甫用自己诗意化的情怀和朴实无华的想象讲述着属于中原人的好故事,却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不失美感的大时代。
四、结语
共同体作为一个现代产物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迹,它与作家想象的文学世界有着内在的复杂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已经成为个体化凸显和共同体式微的现实表征,个体逐渐脱离共同体并开始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自主权利与独立地位,个体的凸显导致共同体的暗淡与衰落。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又是一把双刃剑,个体在摆脱共同体限制的同时也失去了来自共同体的庇护,从而导致个体落入一种充满无序、不确定与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中。跳出共同体舒适圈的个体,看似获得了个体意义上的自由空间与自主生活,却不知不觉陷入另一个漩涡。现实的残酷和精神的迷失,使得李佩甫作品中的人物在逃离传统共同体后又开始怀念过去的美好与和谐,虽然身体与精神都难以再度返乡,但他们内心对共同体的想象与渴望却有增无减。
共同体和个体一道成为作家想象与叙述世界的两极,所有的人物都游走于两极之间,所有现实问题都与共同体和个体密不可分。于共同体和个体而言,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们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并无绝对差异与割裂。于李佩甫而言,乡村共同体象征着更多的东西,而非地理层面上的空间存在,正在“消失”的中原乡村被他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更像是身体与灵魂的诗意栖息地和无法舍弃的家园。作家以诗意想象的方式艺术再现的乡村共同体世界,既是一首伤感的田园诗,也是一首梦想的摇篮曲,正因如此,李佩甫对中原大地的艺术性想象与审美化再现的同时表现出深刻的批判意识与拯救精神。在看似“反乡土”的叙事过程中,李佩甫表现出对乡土世界极富诗意的怀旧与回忆,个体在迷失和逃离传统共同体的同时,又期待一个属于未来的全新共同体的出现。或许,李佩甫想要的正是一种身体上离乡而精神上返乡的诗意理想,这样的“矛盾体”使得作家在文学想象的世界里更加接近共同体。李佩甫小说中的人物在个体独立和集体认同的两难选择中,试图脱离某一个共同体的同时也在回归另一个共同体,这是作家的尖锐批判,更是作家的诗意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体与个体在李佩甫的审美世界里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个体对共同体的想象一直充满深情与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