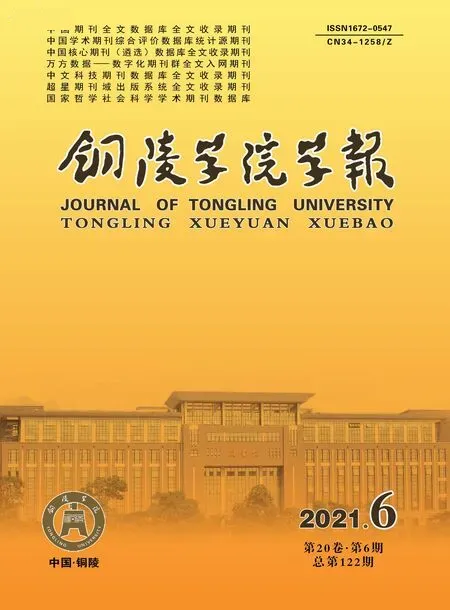论荀子之“雅”范畴
李 源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一、荀子“雅”范畴的义涵
早在荀子之前,“雅”概念就已经被广泛运用到语言、艺术的分类与品评上了。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王都京畿是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京畿一带的诗歌、音乐、语言也就成了当时的标准音,因此称作“雅诗”“雅乐”“雅言”。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1],所谓“雅乐”就是指当时京畿一带的正统音乐。孔子虽以“雅”论乐,却未见论人的事例。先秦其他学派也是如此。荀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正式以“雅”来评价人物品行操守并进行人格分类的思想家。他对“雅”之义涵做了明确界定,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隆礼义。在《儒效》[2]中,荀子以“隆礼义”作为区分“雅儒”与“俗儒”的标志,认为“雅儒”之所以为“雅”,关键在于能“隆礼义”,而“俗儒”之所以为“俗”,主要是因为“不知隆礼义”,致使“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在《修身》中,他也说:“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雅与俗(野)的界限在于“礼”,合礼则雅,反之则俗。总之,礼是雅俗之间最根本的界限,也是“雅”范畴的核心内涵。
第二,有正义。荀子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儒效》)这句话明确指出“无正义”者为“俗人”,也暗示“正义”为“雅人”之基本要求。在荀子看来,“正义”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品质,是高雅人格不可或缺的内容,缺之,就是一个俗人。荀子所谓“正义”是正直、无私之意。他说:“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修身》)高雅之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相反,那些鄙俗之人则“志不免于曲私”。
第三,轻外物。荀子说,雅人“内省而外物轻”《修身》。他比较雅人与俗人对待外物的不同态度说,前者虽然“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其穷也,俗儒笑之”,却能做到“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后者则“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儒效》)。高雅之士重内在礼义德道修养,轻外在名利富贵,内心充实而光辉,因而不为外物所役,即所谓“内省而外物轻”;俗人追逐物欲的满足,整天患得患失,寝食难安,即所谓“以己为物役”。
第四,积文学。荀子常用“文”、“文学”、“学问”等词来泛指文化艺术,认为这是雅人君子必须具备的素质,他所谓“雅文辩慧之君子”(《富国》),其实就是强调“文”对“雅”的重要意义。他在《儒效》中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所谓庶人“积文学”则可归为卿相士大夫,其实是反对以出身作为区分雅与俗的标准,而强调“文学”之于“雅”品格的重要性。在《性恶》中,他也说:“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更明确地指出“积文学”对“雅”之品格培养的重要意义。有“文”则雅,无“文”则俗。荀子曾批评“蔽于用而不知文”之人说:“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非相》)一个缺乏文化艺术修养之人,终身难免于俗。
第五,一表里。雅是主体人格中一种恒定的德性,荀子把这种恒定性称为“一”。他说:“曷谓一?曰:执神而固。”(《儒效》)“一”是一种恒定的德性,它表现为主体不论处于何种境遇,其行为总能在其人格力量的制约下而保持前后一贯,表里如一。荀子眼中的“雅儒”是“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儒效》),“雅儒”之所以为“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具有这种内外表里如一的品质。
二、荀子“雅”范畴的思想基础
荀子“雅”范畴与其心性论紧密相关。荀子心性论的核心是性恶论,此理论是建立在性伪之分基础之上的。在荀子看来,性是“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是人先天就具有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生物性本能;伪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是后天习得的道德理性精神。因此,性恶伪善(《性恶》)。由此出发,荀子认为,俗是个体之性、情、欲的外化,俗人之所以“俗”,是因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性恶》),而雅则是“以道制欲”(《乐论》)、“化性起伪”的结果。他说:“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赋》)雅与俗、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能否以“礼”来改造人性之恶。性得礼则雅,则君子;不得礼,则俗,则小人。总之,顺性则俗,纠伪则雅。
荀子“雅”范畴与其义利观也紧密相关。在义利关系问题上,荀子虽然不反对人之正常的利益欲求,但总体来说还是持重义轻利态度的。在荀子看来,“雅”与“义”相联,而“俗”与“利”相关。上文说过,荀子以“隆礼义”为雅,“不合礼义”则俗;以“轻外物”为雅,“隆富利”则俗。他还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荣辱》)好利是人之本性,生固如此,如果缺少后天的教化,再加上恶俗的熏染,此人就会成为唯利是图的小人、俗人。为了改变俗人“唯利之见”的本性,圣人制定礼义,化导情性,从而促使其由俗变雅。
公私是与义利紧密相连的一对范畴,中国哲学甚至有“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的说法[3]。既然荀子“雅”范畴与义利观紧密相连,那么它与公私观也必然不可分割。在荀子哲学体系中,“公”有公利、公义、公道、公平等多重含义,私也有私利、私欲、私见等多重义涵。“公”是荀子社会理想的根本特点。他心目中的“至道”社会:“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君道》)“公”不仅是荀子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还是其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品质。他认为君子应该“能以公义胜私欲”(《修身》),反复提倡“公正无私”“志爱公利”(《赋》)等。
对待公私的不同态度,是荀子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在《儒效》中,他根据对公私态度的不同,把人分为“众人”与“儒者”两大类:众人是俗人,他们之所以“俗”,是因为不能免“私”;儒者是雅人,他们之所以“雅”,是因为能“公”。可见,在荀子思想体系中,“雅”与“公”相关,“俗”与“私”相联,崇公抑私的基本立场决定了荀子褒雅贬俗的基本态度。
荀子“雅”范畴是建立在其“天人相分”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在荀子看来,“天”即“自然”,人虽然是“天”的产物,但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因为他除了拥有“天”所赋予的“气”与“生”之外,还拥有后天习得的“知”与“义”,因而高于自然,“最为天下贵”(《王制》)。荀子这种天人观,直接影响了他对雅俗关系的理解。
人既然是“天”的产物,人之性情中就难免含自然因素,所谓“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这些都是自然的,都是“人情之所必不免”(《王霸》)。但是,这些都是人最基本之生物性特征,如果听任这些自然因素发展的话,人就不能走出俗鄙、粗野的状态,荀子所谓“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所谓“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要想超越自然,走出粗野,就要用“礼”对人性加以约束与规范,即所谓“由礼则雅”,所谓“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
顺性则俗,由礼而雅,俗为“天”(所谓“人之生固小人”),雅为“人”,雅俗之别即是天人之分。以礼约情,以道制欲,使每一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其实就是由俗变雅的过程。
三、荀子“雅”范畴的思想实质
荀子“雅”范畴,反映了战国末期各诸侯国走向统一背景之下儒家学派对理想人格的期许,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具体而言,其理性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礼”的提倡。他以“礼”作为雅与俗之间最根本的界限,把“礼”视为雅的核心。他解释“礼”说:“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赋》)“礼”就是“理”,即一种人伦物理,理性精神。荀子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只有在理性自觉中才能由俗变雅,所谓“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荀子崇雅抑俗的基本态度,及化俗为雅的主张,实质上就是提倡用“礼”来约束人之情欲,使人由情感和欲望支配的感性状态进入由理智和意志支配的理性状态。
其次,对理与欲关系的理解。荀子主张“以理制欲”从而化俗为雅,并不是主张无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其“雅”论就失去了合理性,而成为非理性的主张。他在《解蔽》中说,“欲”是人性之必然,圣人在对俗人进行道德教化的过程中,不但不能去其欲,反而要“纵其欲,兼其情”,这里所谓“纵欲”、“兼情”不是一任其情欲的宣泄,而是适当满足其情欲的需要,同时还要“制焉者理矣”,即把情欲控制在理性法则之下。可见,雅人之所以为雅,不在于寡欲、无欲,而在于他能依靠理智的力量把欲望限制在礼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说,荀子所谓“雅”,其实是一种调节、制约人的本能欲求和冲动,从而产生超越本能需要的更高追求的理性精神。
第三,对个体社会性的强调。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是一个生物性存在,又是一个社会性存在。作为生物性存在,人摆脱不了追求情欲满足的冲动,而作为社会性存在,人又不能不受礼义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当人之个体性与社会性产生矛盾时,有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这种人就成了俗人;有人则“以道制欲”、“以理节情”,把自我情欲控制在社会规范许可的范围之内,这种人就成了雅人。荀子崇雅抑俗,并不是无视人之个体性,而是提倡个体性要服从于社会性。
最后,强烈的政治实践性。荀子生于诸侯干政、处士横议的战国末年,当时分封贵族政权大厦已倾,国民阶级蓬勃兴起,中央集权国家呼之欲出,这就要求在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方面也要相应地趋于统一,即荀子所谓的“政令以定,风俗以一”(《议兵》)。在此背景之下,荀子首倡“雅”概念来评价国民人格,以期规范国人的品行操守,并为统治者的人才任用提供参考,因此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目的。
“法后王,一制度”是荀子的政治主张,也是他区分“雅儒”与“俗儒”的主要标准之一。他在《儒效》中说:“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是雅儒者也。”可见其“雅”论的政治色彩。荀子“雅”论的政治性,不仅表现在思想层面,更表现在实践层面。在《儒效》中,他明确地说:“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可见,荀子以雅俗对人格进行分类,其目的在于为统治者任用官员提供借鉴,其“雅”范畴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四、荀子“雅”范畴的形成因素及实践意义
在社会生活、政治文化日益世俗化的战国时期,荀子提出“雅”范畴,其目的在于规范人的思想品行,稳定社会秩序,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荀子“雅”范畴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意义。关于“雅”之品格的培养,荀子也提出了具体意见。
荀子认为,习俗对个体人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举例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劝学》)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刚出生时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长大以后就形成了迥异于他族的性格特征,这完全是“教使之然”,即风俗濡染的结果。
不同族群的习俗塑造了该族成员独特的性格特征,即使是同一族群之人,其性格特征也不完全一样,也有雅与俗、君子与小人之分。荀子在《荣辱》中说,君子与小人,虽然在本性上都“好荣恶辱,好利恶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小人趋俗,“君子安雅”。何以故?他说:“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荀子认为,一个国家的风俗有美恶之分,美与恶往往是相互杂陈的。君子与小人,虽处同一国家,有着大致相同的风俗背景,但他们对风俗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君子亲近美俗所以“安雅”,小人流向恶俗所以庸鄙。“雅人”与“俗人”的区别正在于此。风俗的美与恶决定着个体人格的雅与俗,高雅人格的培养当然离不开美俗的熏陶。荀子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儒效》)个体先天之性虽恶,但在美俗的熏陶之下,其内心深处会产生对“雅”的认同感,久而久之就养成了高雅的品质。
个体高雅品质的形成,除受习俗陶染外,也离不开师法的教化,后者往往是通过前者而起作用的,这是因为师法在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荀子说:“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成俗,万世不能易也。”(《正论》)某种思想观念,经过圣王的提倡,官府的守护,到了百姓这里就成了不言自明、不能改变的习俗了。这里,荀子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一种思想观念在由制度化向风俗化演变过程中,师法所起的关键作用。他还说,君师应有辨别风俗美恶的能力,既要能“修政美俗”(《君道》),又要能“移风易俗”(《乐论》)。这也是在强调师法教化对美俗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师法的引导、教化之下,社会风俗趋于好转,从而为个体雅之品格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荀子说:“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儒效》)无师法教化,人就会纵其情性而流于俗鄙;有之,则能化性起伪,由俗变雅。因此,师法是“人之大宝”。荀子认为雅之品格的培养也离不开文学艺术的熏陶:“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大略》)玉琢成器,人学知礼,子赣、季路虽出身鄙野,但由于“被文学,服礼义”而由俗变雅,成为“天下列士”。荀子在《乐论》中系统阐述了音乐对培养高雅人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音乐由于具有“入人深”“化人速”的特点,因此是移风易俗,陶冶情操的重要工具。
荀子强调风俗的影响、师法的教化、艺术的熏陶对培养个体雅之品格的重要性,同时又认为,光靠这些外力的推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个体对美好习俗日积月累的自觉践行。上文提到所谓“隆积”,即是强调雅之品格的形成,是由于个体对美好风俗正确选择与自觉践行的结果。荀子追求成圣,认为“圣可积而致”(《荀子·劝学》),即人的主体价值在追求、选择、规划、实践和反思的环节中,可以得到展现和升华[4]。
在《儒效》中,荀子又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涂之人”即俗人,因“积善”而雅、而君子、而圣人,在这种长期的道德实践中,社会规范逐渐内化为个体的高雅品格。
五、结语
作为人格论范畴的“雅”,正式确立于荀子,它包含隆礼义、有正义、轻外物、积文学、一表里等五重内涵。荀子“雅”范畴是建立在其心性论、义利观、公私观、天人观等哲学问题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荀子“雅”范畴对后世国人的文化价值取向与理想人格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钱穆先生说:“欲知中国文化传统,雅俗之辨,涵有深义,不容不知。 ”[5]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好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想基础”,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因此,在全面复兴、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将荀子的“雅”范畴作为人格论加以探讨,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之一,彰显中华文化自信,促进中国话语的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
——五常市雅臣小学校教育剪影
——“绿筑迹 ——台达绿色建筑展”台达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