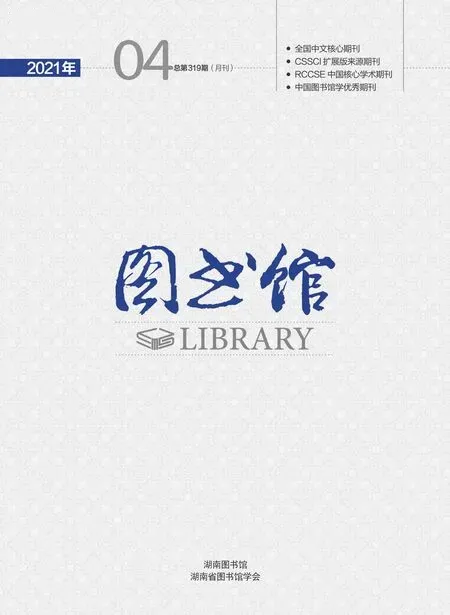耕读文化的前世今生与现代性转化*
刘亚玲 雷稼颖
(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 西安 71006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2018 年《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切实保护好优秀传统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辉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1]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变”、有“常”,我们要处理好“变”与“常”的相互关系,扬弃不合时宜的因素,继承优秀基因,大胆创新[2]。因此,厘清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前世今生,辨析其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与悖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符合新时代精神引领下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的“新耕读文化”,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1 耕读文化的前世——古代耕读文化的渊源及其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重视教化。《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3]《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孟子·滕文公上》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伏羲时代就有了向自然和天地万物学习的萌芽意识、神农时代就有了农业文明、尧舜时期就有了人伦教育的价值自觉。
耕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肇始于春秋时期管仲,他划分人民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孔孟进一步强化了耕读分野,孔子认为“耕”是小人的事情,“读”是君子的追求,二者不可兼得。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这一思想,认为人天生有两种,劳心者和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春秋时期耕读观念是相对立的,“读”被认为是高贵的事业,“耕”是卑贱的事情,并在民间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理念。
我国耕读文化虽源远流长,但真正走向成熟是在宋代。唐宋以前,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间有着较为固定的职业划分和等级秩序,士、农之间很难转化并相互融通,半耕半读主要集中在少数隐逸之士和学生身上。如“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等。这一时期,耕读文化主要特点是“读主耕辅”,耕种的目的是为了养学。如朱熹曰:“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6]但是,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和唐中后期门阀士族的瓦解,为士、农结合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大量的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入仕,大大激发了农民读书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另一方面大量落榜士子沉淀在农村,过着“半为儒者半为农”的乡居生活。中国耕读文化至宋代已经发展成为一股社会洪流,并衍生成宗法氏族式耕读传家理念,成为乡土中国文化的底色。这一时期,耕读文化的实践主体不仅是少数耕隐的知识分子,而呈现全民化趋势。士大夫阶层不再以耕作为耻,读书之余也经营农业。他们认为耕是生存之本,读是精神之需,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于儒家修齐治平的价值理想中。如陈著《本草堂》云:“世多多才翁,谁识识字农”[7],陆游诗云:“颓然静对北窗灯,识字农夫有发僧。”[8]苏轼也自称:“我是识字耕田夫。”[9]农民阶层不再以读书为无用,耕作之余又教导子弟读书。他们认为耕读不仅可以参加科举入仕,改变命运,而且可以明人伦,正家风。如《李氏长春园记》曰:“人生天壤间,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园池台榭可以日涉,有贤子孙诵诗读书,可以不坠失家声,此至乐也。”[10]宋代以后,江南一带出现了许多世家大族,如杭州赵氏、江苏常熟钱氏、无锡荣氏等,他们或秉承“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的治家之要,或秉承“养父母曲尽孝敬,涉书史体意入微”的家教传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蓄,成为当时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11]。
总之,传统耕读文化是建立在我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以村社为地理空间,以宗法氏族为单元结构,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亦耕亦读的文化生态模式。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有三重逻辑:一是古代科举取仕制度是其存在与延续的精神动力。传统耕读文化全盛于唐宋科举制度的建立,光宗耀祖、鲤鱼跳龙门、学而优则仕是其发展和存续的直接动因与首要价值。二是宗法氏族制度是其存在和延续的制度保障。宗法氏族制度是古代传统村落的基本组织形式,它不仅承担家族大小事务,也承担家族教育。每一个宗族都希望自己的宗族多出秀才、状元以此光耀门楣,也希望通过学习儒家伦理,尤其是“礼制”巩固宗法氏族管理秩序的合法性。因此,在古代,义塾、学堂、书院在乡村是很普遍的。三是乡绅阶层是其存在和延续的实践主体。在古代,乡绅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道德楷模和文化权威的代表,他们或是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或是有文化的中小地主,或是隐居乡村的文化名士鸿儒,或是赋闲在家或告老还乡的中小官吏,或是宗族德高望重的元老等,他们似官非官、似民非民,不仅是联系朝野的桥梁,也充当着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和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他们自身不仅是耕读文化的躬行者,而且是耕读文化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承担着教化民众、维护乡村秩序的功能,尤其是一些出身世家大户的乡绅,对区域性耕读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引领作用。
2 耕读文化的今生——现代耕读文化的变迁与撕裂
近现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宗法氏族的没落,乡绅阶层的消亡,传统耕读结合的社会基础被颠覆,耕读传家的价值理念和文教传统走向式微。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民进城务工潮的涌现,农村以农为本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以村社为地理空间,以宗族为单元的耕读文化被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场域和公民教育理念所替代,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碰撞过程中文化撕裂的状态。
第一,文化形态上,由耕读结合走向耕读相分。传统社会是以农立本、以礼治国的宗法制国家,与耕读文化有着自然的、逻辑性自洽。“耕”不仅是指耕地、耕田,还包括农耕基础上的一切生产劳作。“读”不仅指读书,也包括道德伦理和礼仪教化。耕读既是养家糊口的手段,也是传统伦理道德养成的基础。“耕为务本、读可荣身”“半耕半读”是小康之家最合宜的生存状态和价值选择。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打工经济的繁荣,“耕”不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改变,加上文化交流虚拟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挑战,进一步隔断了“耕”与“读”在时空上的关联,使耕读走向分离。
第二,文化内容上,由儒家伦理教育走向公民教育。传统耕读文化体现在内容上,就是以儒家“三纲五常”和“礼法”秩序为道德规范,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阅读对象,注重乡民的“礼”教和“重义轻利”“群体至上”的君子人格培育,其目的是教化乡民“重道德,守礼法”。如《易经·蒙卦》曰:“蒙以养正,圣功也。”[12]《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3]90但是,根植于市场化、全球化的现代乡村文化教育,其目的是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四有”公民为价值取向,其教育内容和知识体系远远超越了传统道德伦理教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教育空间也超越了传统村落,宗族——家庭式的封闭场域,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开放式体系。
第三,文化结构上,由前喻文化走向多元并喻文化。在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内容和形式相对稳定和封闭,传递模式单一。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教育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乡村社会耕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其世代相承的文化传承模式也被颠覆了。年轻一代逐渐成为文化传递的主力和担当,相互学习成为一种常态,文化传递由单向走向双向,由前喻走向并喻或后喻。
第四,实践主体上,由“男尊女卑”走向“男女平等”。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耕为务本,读可荣身”等耕读传家理念都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是被排除在“读”之外的。20 世纪以来,男女教育平等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妇女不仅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文化权益,而且愈来愈成为“书香家庭”“书香社会”“全民阅读”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许多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都开展了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儿童的亲子阅读、公益实践等活动。
3 耕读文化的转世——新耕读文化的现代传承与转化
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国要复兴的前提是乡村文化的复苏。”[14]因此,新耕读文化的复兴与重塑,要以传统耕读文化为“母本”,在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中,把适应时代要求的部分,重新“激活”,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力智力支持。
3.1 作为遗产的文化保护
耕读文化作为中国乡土优秀文化遗产,有三重内涵:一是纯朴自然、和谐恬淡的乡村生态环境;二是半耕半读、躬耕乐道的生产生活方式;三是建立在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文化样式。包括可用符号体系呈现的观念、制度、民间文艺、历史典故等;可用具体实物、形式等呈现的建筑、生产工具、服饰和家书家训等。20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耕读传统的解体,耕读文化已成为中国人心中难以续接的田园梦,因此,对其进行遗产保护已成为一种怀恋、一种寄托、一种唤醒乡村崇文重教、诗意栖居生活的良药。因此,建立以地方耕读文化为资源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展示馆,保护、整修保存较好的、典型的耕读文化古村落,开发以“耕读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旅游体验活动成为许多地方重塑乡村耕读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15]。
3.2 作为精神的文化继承
耕读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农耕文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形态,蕴含着丰富价值观念,内容涉及自然生态、社会伦理、精神信仰等多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非常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因此,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生态意识,推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价值观念,主张按照季节变化和时令节气安排生产生活,强调“务时而寄政”“使民以时”,形成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晴时耕作、雨时读书、天人合一的耕读传统和生态伦理,时至今日,对工商业文明和西方工具理性扩张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二,“孝悌为本”的伦理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宗族秩序和家庭伦理,而孝悌是家庭伦理的核心概念。如《孔子·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3]90在儒家看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悌为仁爱之本始,从孝悌之“亲亲”伦理,扩展到爱民爱物至普遍道德,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如,被后世誉为“古今第一完人”的曾国藩就认为“以耕读之家为本,乃是长久之计”,而“孝友”是家族长盛不衰之大德。他认为“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延十代八代。”[16]187现代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公民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正如《全球伦理宣言》指出:“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17]因此,“孝悌为本”的耕读传家理念,对我们今天的乡风文明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第三,“知行合一”的教育价值观。古代知识分子在长期的农耕生产实践过程中,一方面对农时、农事、农务有了基本了解,出现了大量的农学家、田园诗人,如农学家崔寔,根据自己的农耕经验写出了体农书——《四民月令》;晋代田园派诗人陶渊明,写下了反映田园生活体验和耕读志趣的著名诗篇《归园田居》《归去来辞》等;另一方面也养成了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优良作风。如《补农书》作者张履祥在他的《备忘录》中说:“学者肯去做功夫,方是学,如学耕,须去习耕。”[18]“耕读传家”作为乡民自修自学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不仅把农耕劳作纳入教育的范畴,而且把日常生活礼仪等也纳入教育的内容。如《曾国藩全集·家书》提到:“吾家子侄半耕半读……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16]187因此,传统耕读传家理念中,“耕”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仅指耕田,还常常以“耕”喻“学”,把“耕”譬喻为一种身体力行,勤奋治学的精神。如,汉语中形成的“舌耕”“目耕”“笔耕”等都是这种耕读精神的体现,这种重视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对我国现代提出的素质教育、全人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四,“自强不息”的生命价值观。耕读文化的根柢是农耕文明,而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需要不断和天、地、物及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如《易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铸就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生命价值观,这种生命价值观具有强烈的超越意识,衍生为中国人“贵生尚和”的生命伦理观。如: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9]《荀子·天论》:“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20]《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21]等等都是讲“生”与“和”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珍爱生命”“崇尚和谐”的生命伦理和价值取向,时至今日,亦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尤其是对后工业时代物欲横流、精神空虚、价值虚无以及意志颓废有很好的补弊作用[22]。
3.3 作为机制的文化转化
吉登斯指出,尽管我们生活在与传统对立的现代性“终结时代”,但“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23]。农耕文化作为延续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基石,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理念,也蕴含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村落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和教育智慧。
第一,它是农耕中国家教、家学、家风传承的基本形式。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家庭教育是国家教育的微观形态。“家教”和“家学”不仅是传承家风、敦化社会风俗的基本方式,还是把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内化为家庭道德和个人修养的有效途径。耕读传家是以“耕”为手段,以“读”为价值核心,为“生存”而耕,为“济世”而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将个体与集体、小家与大家相互贯通,形成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家国情怀意识。20 世纪以来,传统“耕读传家”理念虽然已经断裂,但是“书香传家”愈来愈受到重视。这就需要根据新时期乡村的实际和特点,吸纳传统耕读教育理念、机制,构建新耕读时代乡村家庭教育体系,使老百姓学有所教、读有所供、娱有所乐,乐有所得[24]。
第二,它是农耕中国乡村“家园共同体”的独特呈现。在传统社会,耕读传家往往是以地缘、血缘和亲缘构成的“家园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是一个守望相助的地缘、血缘、亲缘群体,也是建立在合理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耕”是为了解决家庭—家族—宗族内部的生养、生计、生产生活所需的经济基础;“读”是为了实现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仪教化和宗法秩序。它不仅体现在以家规、家训、家法为管理形式的宗族内部管理上,还体现在以“乡规民约”“义庄”等形式存在的乡村治理上。正如陈寅恪说的“所谓士族者,……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25]。 21 世纪以来,随着乡村基层治理行政化、内卷化以及无主体逻辑的加剧,重拾传统耕读文化“家园共同体”的活性遗产,成为乡村基层文化治理的一种趋势。如勃兴于21 世纪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乡村读书促进会、乡贤理事会等,都是中国传统“家园共同体”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展和升华[26]。
第三,它是农耕中国乡贤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逻辑。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官—绅—民治理结构。乡绅是融通、连接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官方与民间的重要纽带。他们一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乡情、热爱乡土,其在乡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们不仅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的代言人,还是乡村秩序、道德礼仪的捍卫者;不仅可以调节社会矛盾、邻里纠纷,还能影响一方乡土社会的道德走向,敦风化俗。即使社会更替,改朝换代,乡绅也能维护社会稳定、维持一方平安。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宗法氏族社会的解体,“乡贤”一词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材料》指出:“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7]因此,发现、挖掘地方能人、道德模范、行业领袖、文化名人、专家、企业家等,打通、构建、完善乡村文化治理嵌入机制,利用他们的知识、阅历、威望以及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和激励他们到乡村文化建设中去,既是对现代乡村基层民主治理的有益补充,也是传统乡贤治理机制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有效探索。如,近年来,陕西安康市政府倡导的“诚、孝、俭、勤、和”为主要内容的新民风建设,就是借鉴中国传统乡贤治理经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以村和社区为单位,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约四会”制。所谓“一约”就是“村规民约”,“四会”就是“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通过乡贤嵌入机制,实现以村治村、以民治民,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28]。
4 结语
总之,农耕文化是中国乡土社会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套厚植于百姓生活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系统和民间治理智慧。它既有原真性、原地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又有自身的变异性,尤其是进入“后乡土时代”的现代社会,旧的文明已经被解构,新的文明尚未确立,更要准确把握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新与旧的碰撞中,把握新耕读文化的核心要素,结合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保护、传承和重塑新时代耕读文明,在历史性的“宏大叙事”和地域性的“个性表达”中,探寻新耕读文化的遗产保护、历史因循和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