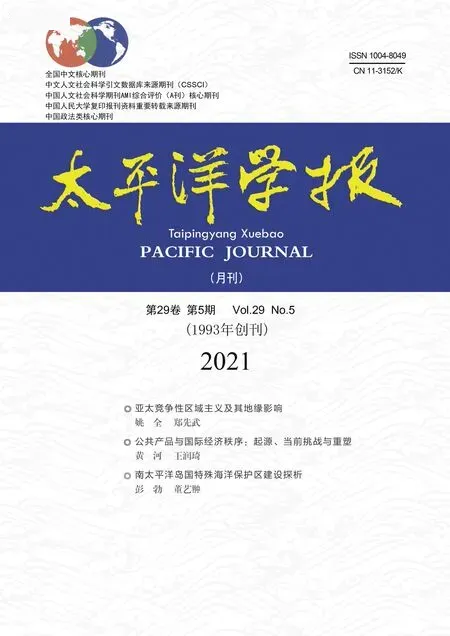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探析
彭 勃 董艺翀
(1.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316022)
随着人类海洋开发活动的持续加剧,全球海洋生态系统正遭受污染加剧、栖息地丧失、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等一系列人为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 年提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期望各国共同保护海洋生态文明,超越人类不顾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枯竭等传统利用海洋、开发海洋的模式,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从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的角度,均衡、全面地认识海洋。 虽然太平洋在世界四大洋中最为浩瀚、宽广,但诸多海洋国家同样面临海平面上升、渔业资源短缺、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生存问题。 尤其是南太平洋岛国①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南太平洋岛国是指大洋洲除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14 个岛屿国家,分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基里巴斯、库克群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纽埃、帕劳、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大洋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9 日。承受的生存压力最为突出。 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生态系统极为复杂、脆弱,加之南太平洋岛国均为典型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既对海洋资源极度依赖,又对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十分敏感,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系统成为南太平洋岛国的首要任务。 基于这种现状,南太平洋岛国在《2021 年蓝色太平洋海洋报告》中强调,南太平洋地区各国应积极参与海洋治理,继续维护和改善蓝色太平洋的健康、生产力和复原力。①“Blue Pacific Ocean Report 2021: A Report by the Pacific Ocean Commissioner to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Leaders”, Office of the Pacific Ocean Commissioner(OPOC), 2021.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诸多南太平洋岛国通过建立众多的保护区域,有效解决了栖息地退化和渔业资源衰退的世界性难题,一跃成为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的主力。②郑苗壮:“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呈现新趋势”, 中国自然资源报,2020 年 6 月 18 日。 http:/ /www.iziran.net/shendu/202006 18_125086.shtml。因此,分析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的现实动因、建设模式与未来走向,借鉴其建设经验,对于中国把握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未来走向及制定相关的海洋保护区政策,从容应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深刻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学术界关于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集中论述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治理。 有学者关注区域海洋机制,对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机制形成的历史和特征作了进一步的讨论;③曲升:“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机制的缘起、发展及意义”,《太平洋学报》,2017 年第 2 期,第 1-19 页。也有学者从治理客体出发,分析了南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渔业资源治理现状,并对中国的渔业资源保护提出了对策建议;④应晓丽、崔旺来:“太平洋小岛屿国家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 年第 9 期,第 70-77 页。还有学者从海洋合作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各国参与南太平洋岛国区域海洋治理的逻辑动因;⑤梁甲瑞:“中法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合作:内在逻辑与现实选择”,《海洋开发与管理》,2021 年第 2 期,第 41-48 页;余姣:“人海和谐: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海洋治理合作探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96-102 页;梁甲瑞:“德国参与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方式、动因及意义”,《国际论坛》,2019 年第 1 期,第 127-142+159-160 页。更有学者从全球海洋治理的角度出发, 结合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治理同全球海洋治理理论,论证南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并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活力;⑥梁甲瑞、曲升:“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48-64 页。此外,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也推动了南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⑦陈晓晨:“全球治理与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国际论坛》,2020 年第 6 期,第 119-136,159-160 页。但也有学者指出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治理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各治理主体之间联系亟待加强,综合性海洋治理仍任重而道远。⑧陈洪桥:“太平洋岛国区域海洋治理探析”,《战略决策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3-17+103 页。相较于国内,国外对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的研究相对丰富。 有学者认为在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需要最大限度地平衡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⑨Robertson, T., Greenhalgh, S., Korovulavula, I., Tikoibua,T., Radikedike, P., Stahlmann - Brown, P., “ Locally Managed Marine Areas: Implications for Socio-economic Impacts in Kadavu, Fiji”, Marine Policy, Vol.117, No.3, 2020, pp.103-114.也有学者认为南太平洋岛国旅游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是推动海洋保护行为的重要动因;⑩Mangubhai, S., Sykes, H., Manley, M., Vukikomoala,K., Beattie, M, “Contributions of Tourism-based Marine Conservation Agreements 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Fiji”,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171, No.2, 2020, pp.106-114.还有学者提出西方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援助为许多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持。⑪Bos, M., Pressey, R. L., Stoeckl, N., “Marine Conservation Finance: The Need for and Scope of an Emerging Field”,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114, 2015, pp.116-128.可以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 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一定程度上限制海洋渔业捕捞等人类商业活动,对岛国周边重要水体及相关的动植物群落、历史及文化属性等进行半封闭保护的特定区域。 其特殊性体现在岛国政府、部落酋长、宗教及非政府组织等建设主体多元化,传统管理手段与西方先进技术叠加的建设方法耦合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复合化,以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殖民文化等相互渗透的建设理念融合化。 同时还要看到,现有研究对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特征仍然缺乏一个有效把握,也未详细阐述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发展的现实动因与实际效果。 因此,本文在现有基础上,着重分析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特征和现实动因、模式与措施、建设效果,并研判其未来发展动向。
一、建设概述
“小岛国、大海洋”是南太平洋岛国的基本特征。①陈晓晨:“小国研究视域下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策略”,《国际关系研究》,2020 第 2 期,第 108-131+157-158 页。南太平洋岛国陆地面积较小,全部岛屿国家的陆地面积不到60 万平方千米,在广泛分布的几千个岛屿之中只有7 个岛屿陆地面积超过700 平方千米。②Tutangata, T., Power, M., “The Regional Scale of Ocean Governanc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45, No.11, 2002, pp.873-884.这些岛屿的面积自东向西增加,超过75%的陆地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较于较小的陆地面积,14 个南太平洋岛国宣布的专属经济区(EEZ)面积达2200 万平方千米。 广阔的海域面积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同时也意味着南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海洋。 可以说,海洋保护是南太平洋岛国发展战略中重点考虑的事项。
鉴于此,南太平洋各岛国积极进行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工作。 截至目前,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数量为430 个,总面积超过300 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球海洋保护区面积的11%。③数据来源为 WDPA, https:/ /www.protectedplanet.net/en,访问时间:2021 年1 月17 日。 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联合项目,是使用IUCN 和CBD 定义陆地和海洋保护区最全面的全球数据库。 不过南太平洋一些地方保护协议和社区管理海域未被纳入统计范围,但这些特殊海洋保护区的保护效果往往超过一般的海洋保护区,也是本文研究对象之一。其中,斐济的特殊海洋保护区数量为122 个,是南太平洋岛国中建设特殊海洋保护区数量最多的国家;库克群岛和帕劳都建立了覆盖整个专属经济区的特殊海洋保护区,且库克群岛特殊海洋保护区的面积达197 万平方千米,居14 个岛国最高;而瑙鲁则是众多南太平洋岛国中唯一没有建立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国家。 从管理上看,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已经从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多元主体管理模式,部落社区、政府、宗教及非政府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不少保护区因其基于社区的管理模式(CBM)而被世界各国仿效。
二、现实动因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旅游业和渔业的需求、非政府力量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和企业的诉求成为特殊海洋保护区的驱动力。 本文基于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二元视角分析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的现实动因。
2.1 内部动因
(1)经济驱动:旅游业和渔业影响
南太平洋岛国积极的海洋保护行动与其特殊的经济结构密不可分。 南太平洋岛国大多为群岛国家,人口广泛地分布在各个岛屿,国内交易和供应成本很高。 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地居民的生计与发展严重依赖海岸带和海洋资源。 南太平洋岛国经济主要包括旅游业、渔业、农业、养殖业、小规模制造业和相对较小的自给自足经济,其中旅游业和渔业是大多数南太平洋岛国的支柱型产业。 但过度捕捞、海洋污染等问题严重威胁了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威胁了这些岛国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设显得十分必要。
以帕劳为例,旅游业是帕劳岛国的第一大产业,是其收入和就业的主要来源,约占国内GDP 总量的50%。 帕劳拥有着太平洋地区最好的海洋生态系统,其中鲨鱼潜水作为旅游特色,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④Vianna, G. M. S., Meekan, M. G., Pannell, D. J., Marsh,S. P., Meeuwig, J. J., “ Socio-economic Value and Community Benefits from Shark-diving Tourism in Palau: A Sustainable Use of Reef Shark Population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145, No.1,2012, pp.267-277.但是,传统的商业捕鲨行为曾一度导致帕劳的鲨鱼濒临灭绝的困境。 2009 年帕劳宣布成立世界上第一个鲨鱼保护区,禁止一切商业捕鲨活动以保护濒临灭绝的鲨鱼。 时至今日,帕劳的鲨鱼保护区成功地保护了大锤头鲨、豹纹鲨、海洋白鳍鲨和其他130 多种鲨鱼和鳐鱼。 同时,禁止商业捕鲨这一行为并没有造成国内经济的严重损失,反而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为帕劳人民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岗位,得到了国内民众的广泛支持,并促使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到鲨鱼保护区的建设与治理中。 此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萨摩亚和马绍尔群岛也先后在专属经济区内建立鲨鱼和鳐鱼的指定特殊海洋保护区。
(2)政治推动:非政府力量影响
南太平洋岛国的政治情况复杂多样,既有类似美国的联邦政府,也有正式的“威斯敏斯特式”政府。 长期的殖民历史和财力单薄导致许多南太平洋岛国的政府管理能力薄弱,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往往落到非政府主体的身上。 社区居民、酋长、宗教和非政府组织都是与海洋具有特殊联系的群体,是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对海洋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关注。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诠释对海洋的保护。
南太平洋岛国长期以来深受土著部落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影响。 除了正式的“威斯敏斯特式”政府之外,许多岛国的政府成员本身可能拥有部落社区的身份,甚至是部落社区的领导人,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传统领导人由于在地方上具有极高的威望,是一些国家政府管理地方的得力助手。①赵少峰,于镭:“太平洋岛国酋长制的演化及其走向简论”,《世界民族》,2020 年第 3 期,第 11-20 页。传统观念倾向于海洋所有权归部落社区所有,这极大地激发了民间部落社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热情。②“State of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2020 Regional Report”, Apia, Samoa: SPREP, 2021, pp.59-60.部落社区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设管理,成为南太平洋岛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长期进行和维持的关键因素。
传统宗教组织,主要是基督教会对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尽管部落社区在最初创建和扩大保护倡议方面是热情的支持者,但其支持力度会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突发情况而增减。 同时,不同社区和部落在传统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海洋保护行为只是孤立片面地进行。 基督教会本身拥有巨大凝聚力,可以有效协调各个社区和部落。③Lyons, K., Walters, P., Riddell, E., “The Role of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Case of Forestry in Solomon Island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Vol.18, No.3, 2015, pp.342-360.不同的社区、部落因为相似的传教历史而拥有同一宗教信仰,让原本没有交互的部落和社区之间产生联系。 此外,宗教领袖在地方上具有极高的威望,可以团结各个社区和部落,使之从零散的保护行为上升为有组织、规模化的保护网络。
非政府组织也是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的重要一环。 其独特的影响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非政府组织拥有制定管理计划所需的人员、资金和技术,能够有效弥补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中资金和技术的匮乏,为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设提供支持。其次,非政府组织能够积极引导和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各项保护活动,在活动中提高民众对于海洋生态保护的认识。 最后,非政府组织通过自身渠道广泛吸引更多的权威人士关注南太平洋地区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2.2 外部动因
(1)资本推进:西方国家诉求
南太平洋岛国有着400 多年的殖民史。 虽然二战结束后各国相继宣布独立,但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冲击,许多岛国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西方国家在南太平洋岛国仍具有较高的话语权,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了南太平洋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 而且南太平洋的海洋战略部署是西方海洋强国的现实需要,特殊海洋保护区因其特殊的战略作用,成为各国的关注点。
西方国家的援助计划推动了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 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新西兰是南太平洋岛国的主要援助国,自身海洋安全或经济利益诉求是援助国为南太平洋岛国提供海洋保护资金的主要原因。 澳大利亚2017 年发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指出,维护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对于共处于同一片海域的澳大利亚极为重要。 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也期望通过与南太平洋岛国共建特殊海洋保护区,提升本国在太平洋海域的影响力。2008 年—2017 年近 10 年来,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为南太平洋岛国提供7 亿美元官方援助资金用于海洋环境和渔业资源保护,①数据来源:OECD, https:/ /stats.oecd.org/,访问时间:2021年 1 月 23 日。为诸多特殊海洋保护区提供建设和管理所需的资金和设备。 可以说,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和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南太平洋海洋生态环境,但也导致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资源政策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国家。
(2)技术拉动:西方企业诉求
西方企业诉求影响着南太平洋岛国政府的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政策。 南太平洋岛国海洋资源丰富,但各岛国资源开发保护能力薄弱,同西方企业合作建设特殊海洋保护区成为“双赢”选择。 2008 年,新英格兰水族馆、英国海洋中心与基里巴斯政府共建菲尼克斯群岛保护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②Rotjan, R., et al., “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hoenix Islands Protected Area”, Advances in Marine Biology, Vol.69, 2014, pp.289-324.新英格兰水族馆和英国海洋中心利用海洋潜标、自治式水下潜器、无人遥控潜水器等观测设备,以及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等近地遥感技术,依托覆盖“航空航天、海面、水体、海底”的全方位、立体化海洋数据监测系统,在位于夏威夷和斐济之间海域建立菲尼克斯群岛保护区。 新英格兰水族馆、英国海洋中心获得基里巴斯海洋油气资源的优先开采权,并在保护区决策上具有直接的影响力。③Mallin, M. F., Stolz, D. C., Thompson, B. S.,Barbesgaard, M., “In Oceans We trust: Conservation, Philanthropy,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hoenix Islands Protected Area”,Marine Policy, Vol.107, No.2,2019, pp.1-12.
三、建设模式
在诸多现实因素的推动下,南太平洋岛国积极推进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 在众多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实践中,以斐济、所罗门群岛、帕劳和库克群岛四个南太平洋岛国最具代表性,它们对于阐明政府和宗教以及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特殊海洋保护区功效等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 因此,解析这四个岛国独特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模式和具体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斐济模式——酋长驱动
位于南太平洋拉美尼西亚群岛的斐济,是覆盖332 个岛屿的群岛国家,其中100 多个岛屿有人居住。 地方集权和社会分层是斐济政治体制的显著特征,酋长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④Mills M., Jupiter S. D., Pressey R. L., Ban N. C., Comley J., “Incorporating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in a National Marine Gap Analysis for Fiji”, Conservation Biology, Vol.25,No.6, 2011, pp.1155-1164.斐济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极具特殊性,斐济是本地管理海洋区域(LMMA)的发起者,也是基于社区管理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典型。
斐济的酋长驱动模式经历四个阶段的演变。 上世纪90 年代以前,斐济沿袭着“百日哀悼酋长”活动。 当一个部落社区的酋长去世时,部分渔场划为禁渔区,以此表达对酋长的尊敬。100 天后该海域重新开放,社区收获鱼类举行宴会并结束哀悼活动。 这种暂时性的禁渔行为使得100 天禁渔期结束时捕获量增加,通常被社区民众视为酋长的“超自然力量”。 随着“百日哀悼酋长”传统活动的世代传承,社区民众逐步认识到较长或永久封闭部分近岸水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禁渔区的溢出效益。⑤Elodie Fache, Annette Breckwoldt, “ Small-scale Managed Marine Areas Over Time: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in a Local Fijian Reef fishe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220,No.3, 2018, pp.253-265.到了90 年代中期,一些科研人员开始在斐济进行各种以社区为基础的保护区项目,“百日哀悼酋长”这一传统的保护活动很快被他们视为项目的关键。科研人员开始与各个社区的酋长进行商讨,希望能进一步推广这种传统保护模式。 在他们的努力下,本地管理海洋区域模式产生,酋长与社区居民签订联合协议,永久划定一部分渔场(约10%~20%)作为特殊海洋保护区,其余部分留给社区成员捕捞作业,将最初临时性、不确定性的保护行为常态化。 2000 年,考虑到各个社区之间信息的闭塞,斐济政府联合酋长、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建立了本地管理海洋区域信息平台,旨在让各个社区可以在平台上相互学习并改善其特殊海洋保护区管理效果。 平台的搭建吸引了更多的成员关注斐济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并且数量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呈指数增长。①LMMA, https:/ /lmmanetwork.org/, 访问时间:2021 年 1月27 日。更多的管理方法也在平台中得到推广,包括限制破坏性渔具、减少陆上威胁、适应气候智能解决方案、备灾应急方案等。 到了2009 年,超过250 个社区已经建立了本地管理海洋区域,覆盖了斐济超过25%的近岸地区,②“State of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2020 Regional Report”, Apia, Samoa: SPREP, 2021, p.60.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初具规模。
目前,斐济所属岛屿已有420 多个社区酋长和居民协定的特殊海洋保护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为社区提供现代化管理技术和资金支持,目的是通过特殊海洋保护区的溢出效应提高捕捞量;保护区外的近岸海域留给社区成员捕捞作业,保障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各个特殊海洋保护区遵循传统创建仪式,不仅对封闭水域进行标记,而且举行正式集会并通知周边部落居民。 由于保护区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收益,越来越多的社区开始对这一模式进行效仿。
综上,斐济的酋长驱动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酋长在特殊海洋保护区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保护区的建设还有赖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人员等的现代化管理技术和资金支持。 可以说斐济的本地管理海洋区域模式是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成功范本,为世界各国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提供了指导方针。
3.2 所罗门群岛模式——宗教驱动
同样位于拉美尼西亚群岛的所罗门群岛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国内大多数人依靠捕鱼为生。 沿海渔业和海洋资源对于所罗门群岛人民来说极为重要,不仅供应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也是为数不多的现金收入来源之一。 和斐济不同的是,受定居模式和利益分配的影响,所罗门群岛邻近的村庄形成区域性部落群体。这些部落群体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且部落首领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意愿会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紧急情况而增减,但由于类似的传教经历,所罗门群岛部落首领和民众的信仰呈现高度一致性特征,基督教为国教。 由于缺乏人力、技术和财政能力,政府和地方的联系并不紧密,各个岛屿对海洋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更多依靠宗教组织,形成了特殊的跨部落水域的保护区管理模式。
基督团契教会(CFC)在所罗门群岛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会成立于20 世纪50 年代末,是一个将基督教教义和当地传统民俗结合起来的组织。③Shankar Aswani, Simon Albert, Mark Love,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Critical Insights for Effective Community-base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Melanesia”, Marine Policy, Vol.81, No.6, 2017, pp.381-391.虽然部落拥有陆地和海洋的传统占有权,但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的教会领袖,在当地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实际管理者。 教会领袖引进西方专业知识和技术管理特殊海洋保护区,同时保留当地部落的传统民俗,并将其与基督教的重要节日相结合。 每年的感恩节,教会领袖带领部落群体进行礼拜,感恩海洋的馈赠并为海上捕捞作业的亲人祈福;复活节期间,各个部落之间相互赠送复活节彩蛋,预祝部落民众的健康和海洋生物群体的繁荣;在最为重要的圣诞节,各个部落不仅为耶稣庆生,还在特殊海洋保护区内开展一系列联合保护行动,主教、部落首领和民众进行珊瑚礁的培育和鱼苗的放生。 此外,不同部落之间出现海域所有权分歧和争议时,教会领袖常会出面协调,运用教会教义和海洋保护理念缓和部落间的矛盾冲突。 因此,所罗门群岛的宗教驱动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方式既借助“上帝”的影响力、又注重现代管理技术的运用,还关注传统海岸管理方法的恢复,实现了三者的动态平衡。 通过宗教组织在各部落之间的协调,所罗门群岛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不再局限于单一部落所拥有的海域。 目前所罗门群岛已建立了超过70 个跨部落水域的特殊海洋保护区,覆盖了接近2000平方千米的近海海域。
3.3 帕劳模式——政府驱动
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帕劳,从1885 年开始,相继被西班牙、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殖民政府统治。 帕劳拥有着与美国高度相似的政治体制,国家宪法以美国的民主思想为基础,同时也尝试赋予习惯法和成文法平等的权力来振兴风俗习惯,①Tom Graham, Noah Idechong, “Reconciling Customary and Constitutional Law: Managing Marine Resources in Palau, Micronesia”,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40, 1998, pp.143-164.地方具有高度的自治权。 海洋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州政府,《帕劳共和国宪法》授予各州“12海里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资源(高度洄游鱼类除外)的专属所有权”。 同时《帕劳共和国宪法》还授予国会“管理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勘探和开发的权力”。 在州政府和国家政府的推动下,帕劳的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得以建立。
各州政府在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行使海洋资源自我管理权,到了90 年代中期,各州政府都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特殊海洋保护区并对区域内的渔业捕捞进行管制。 但是,1998 年的大面积珊瑚礁白化事件导致各州政府和国家政府开始反思现有的保护区体制的弊端。②Golbuu, Y., et al., “Palau’s Coral Reefs Show Differential Habitat Recovery Following the 1998-bleaching Event”,Coral Reefs,Vol.26, No.2, 2007, pp.319-332.一些议会成员指出,各个州政府互不连通的管理模式是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要建立连通各州保护区的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以推进帕劳海洋的可持续发展。③Gruby R. L., Basurto, X., “ Multi-level Governance for Large Marine Commons: Politics and Polycentricity in Palau ’ s Protected Area Network”,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Vol.36,2013, pp.48-60.帕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上作出的保护承诺也是推动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构建的重要原因。
2015 年,帕劳总统签署了《国家海洋保护区法案》,确立一个面积约50 万平方千米的大型海洋保护区,除20%的海域向当地人开放,剩余海域严格禁止渔业捕捞,尤其是外国渔船的商业捕捞行为。 国家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并将原本保护区的州政府管理机构嵌套在国家机构之中,标志着帕劳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由“点状式”步入“网状式”。 同时,政府认识到仅凭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无法实现保护的预期效果。 因此,在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建立之初,政府就通过州政府管理机构开通专门的渠道,鼓励社区居民针对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建设相互交流、提出建议,这极大地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在当地社区居民的呼吁下,许多传统渔业管理举措被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所使用。 例如,帕劳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名为“布尔”(bul)的传统,在鱼类产卵和进食期间留有足够数量的礁石区,以减轻渔业捕捞带来的损害。 目前,国家政府正在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内推广这一举措。
3.4 库克群岛模式——联合驱动
位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库克群岛是世界上海洋与陆地面积之比最高的岛国之一。 国内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极为重视。 在库克群岛,除了政府是特殊海洋保护区的有力推动者之外,非政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资源保护意识。 例如岛内的Te Ipukarea Society(TIS)组织成员信奉“土地和海洋资源是当代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④“We Do Not Own Our Land and Marine Resources but Borrow Them from Ou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Need to Leave Them in Good Condition”, TIS, https:/ /www.tiscookislands.org, 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1 日。传统领导人在库克群岛同样具有较高声望,岛内设有酋长院,由分散在各岛屿的20 位酋长组成,经常就海洋资源使用和传统习俗向议会和政府提出建议。 早在2012 年,库克群岛总理亨利·普纳在第43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上就提出建立大型海洋公园的目标。 随后的几年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传统领导人成立联合委员会积极开展行动,调查有人居住岛屿的产权归属,以确保国家对海洋公园的所有权。
2017 年,在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传统领导人等主体的联合推动下,库克群岛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涵盖整个专属经济区的特殊海洋保护区——马拉·莫阿纳(Marae Moana)海洋公园。①Henry Puna, “Rights of the Ocean Need to Be Explored,”SPREP, 2017Marae Moana 意为神圣的海洋,覆盖了国内接近200 万平方千米的专属经济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由单一国家保护和管理的特殊海洋保护区。 如何在广阔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内达到预期的保护效果成了库克群岛亟需面对的挑战。联合委员会希望通过协商和空间规划等包容性进程实现海洋综合管理和养护的模式。 马拉·莫阿纳定位于多功能型海洋保护区,特殊海洋保护区借鉴澳大利亚大堡礁分区管理办法,根据库克群岛人民的需要和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需求来划定具体功能区,覆盖保护敏感珊瑚礁的“禁锚”区域、允许动物繁殖的庇护所、保护鱼类家园或保护海龟筑巢海滩的栖息地保护区、可持续渔业区、禁止捕鱼区、锰结核采集区或禁采区,以及濒危物种保护区。 明确规定功能区必须经过当地社区、联合委员会及其技术咨询小组的同意才能建立。 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保护了境内61 个濒危物种,并制定海底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规划,明确禁止开采的区域。②“Biodiversity,” Marae Moana, https:/ /www.maraemoana.gov.ck/, 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2 日。政府、非政府组织、传统领导人等不同主体的联合管理,极大激发了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库克群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1 职业足球 英格兰职业足球俱乐部运动员培养体系基本上分为社区足球、进阶训练中心、精英训练组、发展训练组、足球学院和职业一线队6个层次。
3.5 效果评估
(1)建设成效
首先,经济效益明显。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有效增加了鲱鱼、鳕鱼、鲑鱼、鲭鱼、沙丁鱼、金枪鱼及比目鱼等经济性渔业资源,斐济、帕劳、库克群岛等岛国的渔获量平稳增长,南太平洋捕捞渔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近年来岛国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3%以上,渔业经济发展稳健。 另外,特殊海洋保护区的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海洋生物多样性,催生了休闲观光、旅游度假、渔家民宿等各种涉渔新业态,促进南太平洋岛国旅游业发展。 2013 年斐济德拉瓦卡岛和纳维蒂岛之间的曼塔岛(Manta)被打造成蝠鲼旅游胜地,海水、珊瑚和热带鱼成为岛国海洋旅游的标志性元素,2015 年,访问这里的游客人数超过5000 人,在半年内给当地居民创造了超过10 万美元的收入。
其次,海洋生态环境效益显著。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不仅保护海洋珍稀物种和提升生物多样性,而且防止了大面积珊瑚白化的再次发生。 目前,南太平洋诸多岛国的主要污染物入海量持续减少,近岸海域水质基本稳定,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增强,海洋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尤其是斐济、帕劳等岛国,通过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根据岛屿和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的逐步推进,帕劳和斐济再未发生过由于海洋气候变暖、海洋酸化及污染等因素造成的珊瑚大面积白化。 2018 年,南太平洋区域的珊瑚覆盖率达到26%,而这个数字在最新的报告中达到了30%左右,③“State of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2020 Regional Report,” Apia, Samoa: SPREP, 2021, pp.46-49.海洋生态环境系统已具备对气候变化的强大复原力。
最后,文化效应突出。 南太平洋岛国通过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保护了海洋图腾文化。 鲨鱼和鳐鱼一直是南太平洋岛国土著文化中的图腾象征,但由于所罗门群岛、库克群岛等岛国的鲨鱼和鳐鱼濒临灭绝,导致图腾文化也难以延续。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恢复了南太平洋海域鲨鱼和鳐鱼的种群,不仅让图腾文化在岛国继续传承,更让世界各国游客体会和了解到图腾文化蕴含的生态环保理念,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特殊海洋保护区图腾文化独特的信仰力量。
许多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模式被世界上其他各国所仿效。 其中以斐济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设模式最为明显。 本地管理海洋区域模式被认为是基于社区管理的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成功范本,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尤其是在东非、印度洋等地被广泛应用。①Kawaka, J. A., et al., “Developing Locally Managed Marine Areas: Lessons Learnt from Kenya”,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Vol.135, 2017, pp.1-10; Rocliffe, S., et al., “Towards a Network of Locally Managed Marine Areas (LMMAs)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PLoS ONE, Vol.9, No.7, 2014, pp.1-14.
(2)存在不足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设有其不足之处。 一方面,许多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是当地社区发起成立,监测和管理力量薄弱且需要依托外部力量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社区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也阻碍了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发展,斐济的社区体系问题尤为突出;同为社区原住民的斐济裔和印度裔在地位上具有明显的区别,社区的海洋属于斐济裔原住民,印度裔斐济居民作为弱势群体缺乏对社区海洋保护的积极性,造成在特殊海洋保护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部分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受大国影响明显。 帕劳明确规定严禁国外捕捞渔船在其特殊海洋保护区网络中的商业捕捞行为,但日本作为帕劳的主要经济援助国,取得了在特殊海洋保护区捕捞的特权。2019 年,帕劳政府决定为日本冲绳县的渔船提供作业水域,②“Palau Changes Ocean Sanctuary Plan to Allow Japan Fishing”, Phys.org, June 17, 2019, https:/ /phys.org/news/2019-06-palau-ocean-sanctuary-japan-fishing.html.既影响了特殊海洋保护区的海洋生物种群恢复,又打击了国内民众的热情和信心。 类似的情况许多特殊海洋保护区都有发生,库克群岛的马拉·莫阿纳特殊海洋保护区建立之初,联合委员会希望能够颁布禁令保护以锰结核为主的海洋矿产资源,但遭到了以澳大利亚为首的诸多国家反对,导致计划最后难以实现。
四、未来走向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在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前列。 可以预见,未来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会呈现大型化、多元治理、区域合作等特征。
4.1 海洋保护区规划:大型化
大型海洋保护区是指保护面积大于15 万平方千米的海域。③AN Lewis, JC Day, A Wilhelm, et al., “ Large-Scal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Guidelines for Design and Management”, IUCN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WCPA) and IUCN,Global Protected Areas Programme, 2017.早在2009 年召开的第40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期间,基里巴斯就在其提出的“太平洋大洋景观框架”概念中提到大型海洋保护区(又称太平洋弧)。④Jit, Joyti, and M. Tsamenyi, “ Evaluation of the Pacific Oceanscape to Manage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Ocean Environment”,Oceans, 2011.此后,帕劳和库克群岛先后建立了大型海洋保护区,并有效保护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资源。 斐济和萨摩亚也承诺将保护其境内30%的专属经济区,⑤“Protecting Fiji’ s Most Important Marine Areas”, IUCN,2020.其他诸多南太平洋岛国正规划建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网络。 由此可见,相较于小型海洋保护区,大型海洋保护区依托宽阔的栖息场所,将保护区内的物种数量和生境质量维持在较高水平,能够提供更多的“外溢”生物量并降低区域内物种受到边缘效应的影响,⑥De Santo, E. M., “Miss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Targets: How the Push for Quantity Over Quality Undermines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Vol.124, 2013, pp.137-146.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因此,海洋保护区大型化是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未来趋势。
4.2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多元治理
南太平洋岛国人民长期以来依靠海洋维持生计,人们对海洋环境及其保护有着深刻的理解。 部落社区管理海洋的制度,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护了南太平洋岛国的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①Patrick, Christie, et al., “Trends in Development of Coastal Area Management in Tropical Countries:From Central to Community orientation”, Coastal Management, Vol.18, No.11, 1997, pp.2271-2276.尽管在殖民主义、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传统的海洋管理制度面临挑战,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海洋资源管理制度日渐强化,但单一的政府主导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模式并未完全见效。②Timothy R, McClanahan, et al., “A Compariso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Coral-Reef Management”, Current Biology, Vol.16, No.14, 2006, pp.1408-1413.前文中,所罗门群岛将传统的海岸管理制度和现代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尝试,已成为众多国家、地方利益相关方、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捐助者探索的方向。 将注重社区和部落力量保护海洋资源的传统习惯模式与注重政府力量的现代管理模式进行有机结合,既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又传承行之有效的传统习惯做法,形成政府、社区、部落、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的治理模式,是未来南太平洋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发展方向。③Rohe, J. R., Govan, H., Schlüter, A., Ferse, S. C. A., “A Legal Pluralism Perspective on Coastal Fisheries Governance in Two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Marine Policy, Vol.100, 2019, pp.90-97.
4.3 公海保护区建设:区域合作
公海属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由于捕鱼行为不受任何国家的管制,导致海洋“公地悲剧”现象愈演愈烈。④侯芳:“分割的海洋: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的悲剧”,《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 年第 2 期,第 209-215 页。南太平洋地区存在四个带状公海,这些区域是高度洄游鱼种金枪鱼、剑鱼、马林鱼等的重点栖息地,也是国际渔业捕捞的重灾区,各岛国均希望限制公海的过度捕捞行为,实现渔业资源的长期养护与可持续利用。
区域化合作管理公海是未来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的重点工作。 第一,南太平洋岛国是一个整体,公海使他们连结在一起。水体本身的流动性和海洋的整体性导致单一国家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存在局限性,容易受到周边海域的影响,共同管理公海可以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进程。 第二,南太平洋岛国在公海区域合作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2013 年召开的第十届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上,各与会国已经就减少公海水域金枪鱼幼鱼的捕捞达成了共识,为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合作建设奠定了基础。
随着各国保护意愿的加强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南太平洋地区公海保护区建设将逐渐提上进程,有望成为继国内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之外,能够有效保护海洋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 同时,公海保护区建设也是打造南太平洋区域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关键所在。
五、结论与启示
进入21 世纪,全球海洋仍面临着巨大危机。 201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在2020 年前将海洋保护区面积增加到10%”目标至今无法实现,且单一的保护面积占比目标设置也使得全球诸多国家对海洋保护区规划与管理关注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国对海洋保护区的建设热情仍不断高涨。 南太平洋特殊海洋保护区的建设既是各岛国基于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做出的选择,也是以澳新为主的西方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决策。 未来的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将朝着大型化、多元治理和区域合作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并不断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动力。
总体而言,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不仅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更能推动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加快成型。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的经验对于共处同一个太平洋的中国突破海洋保护区的管理瓶颈、把握海洋保护区的未来走向以及制定相关的管控政策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借鉴南太平洋岛国海洋保护区建设经验,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1)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建立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运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平衡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势在必行。 海洋保护区数量和面积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当地居民、企业和政府在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保护过程中承担了额外的保护成本或丧失了经济发展机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参与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阻碍了海洋保护区的长期发展。 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还处在起步阶段,仅在部分海洋保护区有试点工作。 且相关立法体系并不完善,缺乏上位法与下位法的配套支撑。①赵玲:“中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1 期,第68-74 页。因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既是中国海洋保护区建设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公众参与海洋保护区治理的重要手段。
(2)公众参与保护区建设。 基层群众自发的海洋管理是降低海洋保护区建设成本,增加保护效率的重要途径。②高阳、冯喆、许学工、段晓峰、崔艳智:“国际海洋保护区管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海洋环境科学》,2018 年第3 期,第475-480 页。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国的海洋保护区管理方法已经从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多元主体管理模式,斐济保护区建设采用的就是部落社区酋长主导、其他主体参与的管理模式。 近些年来,中国的海洋环境不断恶化,海洋资源日益衰退。仅靠政府部门进行的海洋保护区管理工作难以实现其保护目标,将公众参与引入海洋保护区管理成为必然选择。 新时期中国的海洋保护区建设要格外注重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拓展公众参与的渠道,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应当积极引导当地居民以个人或组织的形式参与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过程,通过提高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推动当地居民的保护行为由自发走向自觉,③Jones, P. J. S., Qiu, W., De Santo, E. M., “Govern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Marine Policy, Vol.41, 2013, pp.5-13.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形式。 在发挥政府在海洋保护区的主体作用的同时,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保护的长效机制。
(3)注重当地特色。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还着重强调了当地传统民俗在海洋保护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海洋保护行为常以宗教民俗等形式呈现。 以舟山群岛为例,舟山市内有两大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即嵊泗马鞍列岛国家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浙江普陀中街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两大保护区总面积约752 平方千米。 当地渔民历来靠海吃海,对于海洋有着独特的情怀和归属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同时,舟山宗教文化极具多元性,兼容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他民间宗教。 宗教文化与海洋文化交织,产生了独特的海洋宗教信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渔民开洋、谢洋节”等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加深了当地渔民对于休渔期的认同感。 在我国海洋保护区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传统宗教民俗的传承,对于海洋保护区的建设有着推动和促进作用。
(4)加快海洋保护区体系建设,构建海洋生态环境综合管理网络。 由于海洋的高度关联性和系统性,海洋保护区应该嵌套在大型、多功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网络中。 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区实际管理工作由诸多责任机构负责,且相关职能部门缺乏宏观统筹授权,难以对各类海洋保护区的空间、职能进行实质整合。 2019 年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新华网,2019 年6月 26 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19-06/26/c_1210171088.htm。因此,成立国家专门管理机构,统筹海洋保护区体系建设顶层设计,采用统一分级与部门协作的管理机制,加强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海洋保护区的跨区域协同联动管理,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等刚性约束制度,搭建配套的信息平台,有效推动各个保护区的自我学习和改进,改变原有海洋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中呈现出的碎片化、零散化倾向,是推动海洋保护区由“点状式”步入“网状式”、由“数量建设”步入“质量建设”的关键所在。
(5)区域合作共建保护区网络。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区域合作共建保护区网络不仅对保护我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更是缓解国家冲突和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保护区建设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海洋保护区建设必然会从近岸向远海进行拓展,从管辖内向管辖外延伸。①匡增军,徐攀亚:“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第151-159 页。所以需要在加快本国专属经济区内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同时,在争议区域积极寻求合作、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和实施养护措施。 通过构建海洋保护区网络,增进与周边海上邻国技术与教育的交流互助,扩大资金支持,强化共同执法力度,提高海洋保护的默契性,最终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