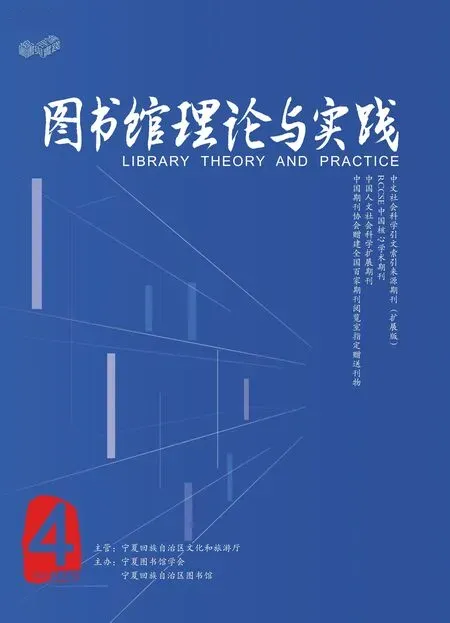古籍书名发展考略
黄 威,王士香(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1 引言
书名之于书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学界很早已经意识到了书名的重要性,余嘉锡《古书校读法》[1],张舜徽《广校雠略》[2]均辟专章探讨书名命名的一般性规律。其后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为归纳书名的命名方式,如程千帆将典籍的命名方式分为3类[3];杜泽逊将其细化为7类[4];曹之进一步细化为19类[5];叶守法则将书的命名方式归纳为15大类166小类,最为细致[6]。二为考释书名含义,鲍延毅《中国古今书名释义辞典》[7]、张林川《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辞典》[8]、赵传仁《中国古籍难解书名例释》[9]等均为此属此类。来新夏曾有建立“书名学”的倡议[10];杜泽逊也在不同场合援引程千帆“书名可以写博士论文”之语,反复强调过书名研究的重要性。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类似的研究与倡议似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学界更多时候还是把书名置于“日用而不觉”的位置,并未将其视为重要的学术话题加以深入探讨,目前尚无人对书名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是其显著表现之一。以1912年以前所刊古籍为材料来源,按时代顺序梳理我国书名发展演变情况,正是本文旨意之所在。
2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今天意义上的书名就已经存在,其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被古人认为是三皇五帝时期的典籍。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复出语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11]《周礼·春官·宗伯第三》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11]820虽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今已失传,无法判断是否如古人所说为三皇五帝之书,但四者作为书名在春秋时期便广为人知则无疑问。
“六经”书名则为今日确知的最早的一批书名。《庄子·天运》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12]《庄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此引述说明其时“六经”之书名已经形成。然而,先秦时期如“六经”之类汇编性质的书籍在当时仅占小部分,多数书籍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的,而“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1]211。此类书名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多摘首句命名。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史籀篇叙录》云:
古字书皆以首二字名篇,存者有《急就篇》,可证推之《仓颉篇》首句当云“仓颉作书”,《爰历》《博学》诸篇当无不然。观《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名书之通例也[13]。
王氏对字书命名规律的观点其实可推而广之,作为先秦时期古书书名的通则之一。只是这一规律并不局限于首二字,而是在首句中撷取若干字作为书名,即摘取开篇文字以名书为先秦时期书名命名的重要方式之一。
出土文献已印证先秦古书的这一特征。如,上博简《容成氏》一书全篇存53简,原有标题抄写在末简简背。全书讲了容成氏、尧、舜等帝王,其中容成氏为开篇第一个帝王,遂以该名命书,而这一书名更多是起统摄作用,并不能代表全书的内容[14]。又如,上博简《子羔》篇现存14简,此书采用问答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回答子羔关于舜如何从平民成为帝王的问题,篇题“子羔”抄写在第五简简背,被整理者命名为《鲁邦大旱》《孔子诗论》的两篇与《子羔》篇为同一人手迹,整理者认为“《子羔》是篇题,书于第五简之背,也可以看作与《鲁邦大旱》和《孔子诗论》合为一册的书题。”[14]183可见“子羔”并不能概括整个简编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因为子羔问答之事排在书籍之首,又以“子羔”二字开篇而已,为摘取篇首文字为书名之例。
摘取文章开篇部分命名的好处在于,从命名者角度看,这种命名方式易于操作,由于当时的很多书为语录、故事的汇编,内容庞杂,不具有一贯的主题,采用这种方式命名最为简单方便;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口耳相传还是先秦时期书籍传播的重要形式。清阮元《数说》就说:“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古人简策,在国有之,私家已少,何况民间?是以一师有竹帛而百弟子口传之,非如今人印本经书,家家可备也。”[15]在这种情况下,记诵对于书籍的使用者至为关键,而采用撷取开篇文字为典籍命名的方式,有利于记诵者回想书的首句,从而起到提示记诵的作用。
其二,书名并非书籍的必要项。仍以上博简为例,其中《子羔》《中弓》《容成氏》《曹沫之陈》等为有篇名者,但此批竹简中可确定完整而无篇名者尚有很多,如《柬大王泊旱》,此篇共23简,计601字,整理之前竹简保存在原出土的泥方中,因此保存十分完好,但此书全篇无标题,现题为整理者取全文首句而定[16]。又如《平王文郑寿》篇共7简,“皆为完简,各简文句相接,文意相连,均可通读。起首完整,最后一简文末有墨钩。”[17]说明此篇亦为完篇,但也没有题名,篇名为整理者命名。同时同地抄写的书籍,篇名有无不定的情况,表明此时书名的命名与题写均随意性较大,书名并非书籍的必要项。
3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书名发展的关键期,秦至西汉,书名沿袭了先秦时期的书名特点并有新发展。
其一,此时为典籍命名的情况呈发展趋势。从出土实物与典籍记述看,此时虽仍有一些典籍并无书名,但编撰书籍时为其命名已逐渐成为大势所趋。如《史记·陆贾传》载:
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8]。
陆贾的著述在当时已经被整理汇集,虽然我们无法从此段文字中判定“新语”一名为陆贾自命名还是他人所命,但其为12篇之总名则无疑问,这预示着书籍从单篇流传向整部流传的趋势,为此类典籍命一个统摄众篇的书名已成大势所趋。将睡虎地《法律问答》与张家山《二年律令》进行对比,这一趋势体现得更为明显。《法律问答》为秦简,原书并没有发现书名,其名为整理者所定;《二年律令》为汉简,“二年律令”为原书名,二书相较可以发现,它们的内容多有重合之处,后者概为前者经整理扩充后之本[19]。二者一无书名一有书名的现象,正是书名逐渐成为书籍必要项这一发展走向的表现。
其二,先秦时期,书名命名多随意摘首句为名,西汉以后这种命名方式仅存在于如《凡将篇》《史游篇》等字书的命名上,其他书籍已多不采用此方法命名。通过对出土秦、汉典籍的考察可知,自觉赋予书籍反映内容的书名,在秦及以后已成为普遍现象。如,在睡虎地秦简中,《语书》《效》《封诊式》《日书》(乙种)等书书名均为原有[19]418-422,这些书名均为对书籍内容的概括而非首句的摘抄。又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等书书名亦为原有,除《盖庐》为以书中提问人物命书外,其他书名均为对书籍内容的概括。据发掘报告,此批竹简抄写于西汉前期[19]437-440,正反映了秦汉之际典籍命名的新变化。
东汉时期则是书名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此时除集部典籍外,多数书籍已有统摄众篇的书名。《四库全书总目》云: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20]。
四库馆臣的结论可信从。虽然别集的产生是在东汉时期,但此时尚不普及,很多别集类著作仍无书名。如《后汉书·文苑传上》记载了东汉人杜笃、王隆、夏恭、夏牙、黄香、李尤、苏顺、刘珍、葛龚、崔琦、边韶等人的著述情况[21]。在记述中,杜笃《明世论》、刘珍《释名》这类非诗文类作品已专举书名;然而,在魏晋时期多以“某某集”的形式命名的别集,此时仍以文体或篇名类别分称,如“(王隆)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李尤)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等,反映出别集在东汉以前无书名的情况仍比较普遍。因此,余嘉锡说:“东汉以后,自别集之外,几无不有书名矣。”[1]217
造成东汉时期“统摄众篇”书名增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刘向父子的图书整理与编目工作。秦代焚书使书籍遭受到了严重破坏,汉成帝(前51—前7)有感于文籍散乱,曾命人进行搜求与整理。据《汉书·成帝纪》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22]刘向校书始于西汉河平三年(前26),其卒后由其子刘歆“卒父前业”,此工作前后持续二十多年,完成时已近东汉[23]。这一举措在书名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在刘向校书之前,书籍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汇集众篇整理成册的工作也已经存在,且这一过程也可能涉及到书名的定名问题。但由于此种行为多针对部分典籍,其搜集工作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多不完备,整理后书籍的传播也不广泛,所形成的书籍多为个人阅读、收藏性质,从篇目完整性、文字可靠性等方面看均非权威版本,其书名也就得不到广泛的认可。刘向《战国策书录》云: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24]。
在刘向为《战国策》定名之前,该书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诸多异称。这种情况正是当时书名不稳定的表现。
与前人图书整理相比,刘向父子的工作从规模、范围、持续时间、质量上均是空前的,很多典籍经此次整理后形成了定本。从书名角度看,汉代以前产生的很多著作,其书名就是在此次文献整理中确立的。正是西汉末的这次文献整理与编目工作,对东汉时期书籍命名产生了巨大影响。先秦古书由于流传特点,其内容多分合无定,书与书之间的界限也就相对模糊,李零说:“古书的编成也是将零散的篇章加以汇总。所以章句之与章句,章句之与篇,篇之与书,可以游离,造成篇题不能概括内容,章句不相衔接,篇与篇,书与书,内容出此入彼。”[25]文献整理使书籍内容趋于稳定,使书籍作为整体而界限明晰,书名与书籍内容就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对应关系。
其二,“立言”意识的觉醒。通过著述的方式以达到身死而名传于后世的意识,很早就已经产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1]4296-4297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个体无法通过“立德”“立功”留名时,通过著书以达到不朽便成为很多人有意识的选择。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吕氏春秋》、刘安编《淮南鸿烈》均有此意,二书当为吕、刘二人自行命名。然而,这种情况在东汉前为个别现象,因东汉以前学有师承,经师的言论是靠学生口耳相传或著于竹帛流传的,并不需要亲自整理就能达到立言的目的,像商人吕不韦、皇族刘安非儒师,无力著述却欲靠著书留名者为少数。东汉以后,专家之学渐衰,产生了一批王充《论衡·书解》所说的“文儒”,因“文儒”“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26],这就造成如果他们仍希望“立言”以不朽,就需要自行整理著述以期可以传世。因此,余嘉锡说:“文儒著书,无人可传,不能不自行编次。”[1]217在书籍写成投入流通领域时,为达到留名后世的目的,除书籍内容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外,还有两个因素极为重要:一为书籍的作者,另一即为书名。明确了作者才能达到传名的目的,而一个或鲜明、或新颖的书名是读者将书籍与作者对应起来,从而达到显名目的的关键。因此,我们认为“立言”意识的觉醒对书名的发展与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书名发展的成熟期。此时书名已成为书籍的必要项,无书名将不被视为书籍。统摄众篇的书名取代了“以篇名为书名”者,成为古书书名的主体,篇名则一般不再被视为书名。在此期间,发生在汉魏之际书写载体的转变,以及易代之际发生的书厄,对这一进程的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魏之际,我国书写材料经历了由简帛向纸转变的过程。东汉以前,书籍的主要载体为简帛,“简重帛贵”的现象使书籍的流通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时候学者仅传抄学习或需要的部分,故书籍多以篇为单位流传,“以篇名为书名”的现象普遍。纸的发明与改造使这种情况得以改变。从出土实物看,纸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但由于技术问题,此时纸的使用并不普遍,也没有用于书写领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和帝(79—106)年间,据《后汉书·蔡伦传》载: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25]2513。
正是蔡伦对纸的改造,生产出适合书写的“蔡侯纸”,从根本上改变了书籍的流通方式。纸张兼具价廉、轻便的优点,使书籍在传抄与携带的方便性上均有了质的飞跃。尤其是载体容量的增加,逐渐改变了书籍以篇流传的方式,变为以部为单位流通。当书籍以整部的形式传播时,出于称引或查阅方便的需要,给这些书籍冠以统摄众篇的书名就显得非常必要了。“纸的普遍使用与纸书的流行应是在东汉中后期(2世纪中叶),到汉末(3世纪初)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于三国后期(3世纪中叶)完成了简纸的转换”[27]。这一事件与书名成为书籍必要项的时间基本重合。可以说,纸简替代所造成的书籍传播方式的转变,为统摄篇章的书名取代“以篇名为书名”并使书名成为书籍必要项的直接动因。
然而,虽纸与简帛相比有轻便、价廉的优点,但人们长期对简帛的使用,使纸发明之初被视为较简帛低级的书写材料。《桓玄伪事》“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28]的表述,恰从侧面反映出“简帛主敬”的思想在当时可能广泛存在,而这一惯性认知对纸简互替的进程会产生负面影响,起到阻碍与延迟的作用。这时,发生在书写载体变革时期的书厄,在典籍制度的演进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据《隋书·牛弘传》,在隋代以前图书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破坏,牛弘称之为“五厄”:一为秦始皇焚书,二为王莽末年战乱,三为董卓之乱,四为惠怀之乱,五为侯景之乱与梁元帝焚书[29]。其中,第二次书厄发生在西汉末年,毁坏的书籍主体为西汉时期刘向父子整理的图书,此时纸张虽已发明,但并不适合大规模图书生产,图书的主要载体仍为简帛。因此,这次书厄破坏的书籍主要当为简帛古书。第三次书厄发生在汉魏之际,此时纸张作为书写材料已广为使用,但由于此前的图书积累,当时国家藏书仍以简帛为主。当统治者在战乱平定后再次汇集图书时,虽仍会搜集到前代简帛古书,但由于战乱图籍毁坏严重,数量可能较为有限;与搜集古籍相比,重新抄写制作的图书当为国家藏书的主体。由于此时纸张的生产技术已经成熟,以便携、容量大、价廉、易生产的纸张替代笨重的简及昂贵的帛来抄写书籍便成自然之选。牛弘在描述第三次书厄后书籍再次聚集时,有“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29]1299之语,这里的“古文旧简”当为搜罗的简帛古书,而“新章后录”或指采用纸张重新誊录的图书。这些再生产的书籍,无论是材质载体还是书籍形制,反映的自然是纸卷图书的形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简帛古书以篇流传、以篇题为书名的情况。可以说,发生在汉魏之交的战乱导致的书厄,对书名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5 唐五代时期
书籍在魏晋时期完成纸简代替,至唐五代时期书籍主要装帧形式为卷轴装。卷轴古书的书名与简帛时期相比在题写形制上有了显著的变化,即此时的书籍普遍同时题写首、尾两个标题,首题中的书名多为全称,尾题中的书名多为简称。如,英藏敦煌文献S.5674首题“孔子共项讬相问书一卷”、尾题作“孔子共项讬一卷”,法藏敦煌文献P.2302首题“佛说长者女庵提遮师子吼了义经”、尾题作“佛说庵提遮女经”等[30]。这一形式概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较为普遍,至唐代发展定型。在命名方式上,由于自魏晋南北朝时各种书名命名方式均已出现,唐五代时期在此方面并无创新。
然而,在唐五代新的社会环境与风气的影响下,此时的书名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其中,宗教类典籍为了标榜其重要性,普遍使用长书名成为其显著特点。唐代佛教典籍书名呈现出如此特色,一方面为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因为译经活动为将其他民族的语言译成汉文的过程,翻译势必要以原文献的书名为依据;另一方面,唐代崇尚奢华的风气也体现在了书名中,如为了体现佛教的尊崇地位,译经者往往给书名加上诸多表示尊崇、崇高等含义的修饰词语,这一点在汉文原创佛典中体现尤为突出,因而造成了佛教书名繁复、奢华的特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佛经典籍中书名多有此特征,如:英藏S.5475《坛经》,其卷首书目全称作“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法藏P.2382首题作“佛说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俄藏Ф092首尾全具,首题作“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第七”,其后以双行小字题曰“一名中度那阑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正名与异称均为长书名。
道教典籍多长书名的现象的原因与佛教典籍类似,也有标榜书籍重要的因素。唐代开国者为李姓,道教代表人物的老子亦为李姓,对道教的推崇影响了道教书名的命名,诸如《老子》被称为《道德真经》,《庄子》在唐代被称为《南华真经》,《列子》被称为《冲虚真经》等,均为唐统治者尊崇道教地位而命名。道教典籍也存在通过书名标榜权威性的现象,因此道教类典籍的书名与佛教典籍一样,都存在大量的长书名。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道教文献书名有此特点者如法藏P.2431为首残尾全,其尾题作“洞玄灵宝诸天内因自然玉字”;法藏P.2461首尾完具,首题作“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第四”,尾题作“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以上书名与佛教书名命名特点类似,均为长书名。
从上揭长书名可见,佛道类典籍书名的这种特点,是刻意叠加多种修饰成分所致。《坛经》的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南宗顿教”为宗派,“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所说法门内容,“六祖惠能大师”是说者,“于韶州大梵寺”是说经处,“施法坛经”为主名;《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智慧上品大戒”为主名,其前为修饰成分。在古书命名活动中,虽然使用核心词汇加修饰成分为书命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像佛、道类书籍为了标榜其权威性,在书名中不仅“人法双举”[31],事无巨细地将诸多信息均罗列在书名中,以至书名变得极为冗长的做法在典籍命名中仍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
6 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雕版印刷的兴起与繁荣使书籍由此进入了册页时期,这一进程对宋至清代书名呈现出的特征有巨大影响。同时,在印刷术普及的背景下,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具体历史环境对书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有影响。
其一,雕版印刷的广泛流行,使书名题写形制发生变化。印刷术发明以后,雕版技术的日趋完善使宋代以后的书籍较前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此时书籍逐渐出现了封面、书根、版心等可题写书名之处。书籍由抄写变为刊刻后,由于一副雕版要进行反复印刷,刻版时一般要比抄写更注重书写与版式的规范性,这样书名的规范性也随之进一步增强。在书版的不同位置刊刻上书名方便在刻印后阅读,使书名逐渐固定在封面、书根、版心等处。康安宁认为:“一部古籍的封面、书名页、序跋、目次、凡例、书口等处,都可刊印书名。通常情况下,封面、序跋、目次、凡例等处的书名,请名人题写,或非原书著者题名较多,与原书名时常有差异;书口等处,受位置条件限制,简略书名亦颇多;而正文首卷卷端之书名,一般是著者最后定稿时所确定的书名,或者是刊刻时刻印者最后审定之书名,其最接近、最符合原书著者及刊刻者的原意,书名原生态的可靠性最强。当然,特殊情况下,正文首卷卷端无法确定书名的情况下,也可以依正文各卷卷端及各卷卷末、目次、凡例、封面、版心等信息作为著录依据。”[32]
其二,宋代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出现大量以“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字样命书的书名。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纂图互注经子”条曾例举大量例证,如《纂图附释音重言重意互注周易》《纂图附释音重意重言互注尚书》《附释音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等[33],从叶氏所据具体书名可见,这种命名方式在宋代较为普遍。
其三,在宋代雕版印刷兴起后,书籍的批量生产促使图书买卖的商业行为迅速发展。书籍制造方式与生产目的的变化对书名也产生了影响。如“新刊”“新刻”“新雕”等均为雕版印刷书籍产生后才出现的书名用语。同时,由于图书作为一种商品成为书商牟利之物,因此也出现书商挖空心思以新奇之书名迎合读者的现象。如,《古今笑》为明冯梦龙采选各朝史乘、杂著及民间笑话而成的笑话集,又名《谭概》《古今谭概》《古今笑史》。李渔《古今笑史序》记述了该书书名的变迁史:是书编成后命为初《谭概》,因后销路不好重刻时改名《古今笑》,于是大卖,书商重刊时又在“古今笑”基础上添一“史”字,作“古今笑史”[34]。此为书商影响典籍命名的典型事例。此外,宋代书名中出现“新编”“新刊”“增订”“绣像”“评点”“新刻”“京本”等具广告性质的修饰语,如《增订汉魏丛书》《新编历法大成》《绣像忠烈全传》等,这类书名也多与书商密切相关。
书商早在汉代就有书肆买卖书籍的记载,但书商的发展壮大却是宋代以后之事,书商作为书籍命名的群体也当始于宋代,他们对书名中出现广告性质的修饰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书籍作为书商谋取利益的工具,为了书籍有个好的销路,他们往往挖空心思为它取个新奇之名以达到畅销的目的。这类书名在章回小说书名中极为盛行,为了吸引读者并与他本分别,书名前的冠词往往特别复杂。如,《水浒传》一书不同版本有《插图本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三槐堂刊全像水浒传》《新刻出像京本水浒传》等书名。清代对前代浮华奢侈的社会风气有所不满,加之清代朴学兴起,对书名的命名以平实为主,有返璞归真的趋势。但小说、话本等类书籍,由于面向人群为平民大众,为吸引他们购买以扩大销量,求新奇的特点一直承袭不改。
其四,宋代以后,人们自行整理文集成为普遍现象,与唐以前相比,此时别集书名反映作者自身情趣与观念者大增。如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别集类典籍书名以人名书的比例极高(这里所说的“以人名书”包括以姓名、官名、自号、谥号等反映作者自身信息的书名);而在《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中反映作者情趣、思想的书名比重增加。举例来说,北宋王禹偁以占卜而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小畜集》[35],书名与书籍内容并无直接关系,其关联源于命名者的主观赋予与阐释;宋车若水《脚气集》的命名,则是车氏“因病脚气,作书自娱,故名曰《脚气集》”[20]1047。这一现象表明,虽然早在东汉时期王融就给自己的作品整理后命名为《玉海集》[20]1271,但从汉代至魏晋六朝直至唐代,别集大多为后人在对前人作品进行整理后命名,故书名多直接以人名书,作者身前就自行整理作品并命名者为少数。宋代及以后,文人自行编撰文集的情况普遍,用书名追求新奇、标榜情操或表明情志的现象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