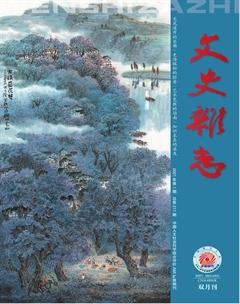阿尔芒·戴维:把熊猫介绍给世界(上)
孙前



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神父(1826年9月7日—1900年11月10日)是19世纪享誉世界的动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中国人很少使用“博物学家”的概念;而在西方世界,是极少有人能享有“博物学家”称誉的。
戴维神父同进化论学说创立者、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是同时代人。他们都有先辈是医生的家世,在青少年时代的共同兴趣都是酷爱动植物和大自然。当1859年11月达尔文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发表时,戴维认真地钻研过。1877年戴维的《中国鸟类》巨著(两卷本)发表后,轰动整个欧洲。达尔文也研读过这部著作。他们都是科学的巨人,推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进化论。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戴维;但是,戴维神父在中国的科学发现和建树,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中国文化、中国科学和中国人民的爱好之中。大熊猫、麋鹿(俗称四不像)、川金丝猴、扭角羚(野牛)、珙桐树(鸽子花树)等189个新物种,都是戴维把它们从深山野林和封闭的皇家苑林介绍到全世界的。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100多年前戴维在中国考察過,并有科学发现的地方,都成了当地旅游“龙门阵”中的金段子。
进入18世纪,西方掀起了“中国热”。百年后,德国大诗人歌德于1827年创作的《中德四季朝暮吟》组诗,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850年11月5日,身在巴黎的年轻的天主教教士阿尔芒·戴维向教会提出愿到遥远的东方去传教,尤其想到中国。但是教会发现了他在研究自然科学方面的能力,便于1851年把他送到意大利利古里亚的萨沃纳(Savona)神学院学习和教授自然科学。那里专门培养对自然特别有兴趣的年轻人。戴维说:“我在这里很满意我的地位,人家交给我的工作和事务都是符合我口味的,我没有什么要抱怨的,总之我不停地梦想着去中国传教。”在萨沃纳,为了方便学习,他着手建立各种科学收藏,并加强技术方面的业务学习,成了一位优秀的动植物标本制作师和研究助手。后来,在以他制作和汇集的标本基础上成立了市博物馆。在萨沃纳,戴维练就了弹无虚发的枪法和用口哨声可以诱捕鸟类、哺乳类动物的绝活。在这里的10年培训和工作,使戴维成为一位功底扎实的博物学家。以后的实践证明,终其一生,戴维都是一位博物学家和教育家。他重视知识,尤其是重视获得知识的过程和传授知识。
一、为什么到中国
用中国的古话说,此时的戴维,已是“玉在椟中求善价,剑在鞘中待时飞”。他等待着时机。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大门之后,西方世界才真正看清楚中国。1860年9月,英法联军又打到北京紫禁城,清朝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法国政府趁机要求在中国的教会尽快开办法文学校,传播法国文化,以同英国争夺在中国的影响。拿破仑三世在议会两院宣布:“在世界的尽头,我们刚刚向文明与宗教的进步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帝国。”
1861年,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博物学家亨利·米勒—爱德华兹(Hemi Milne—Edwards,1864年任馆长),向巴黎天主教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Etienne)请求,派传教士到中国进行科学研究。11月中旬,宗教界和外交界都选上了阿尔芒·戴维。戴维和其他传教士遂被派往北京,准备建立一所学院。
1862年1月,戴维来到巴黎,接受中文培训。2月,遣使会总会把戴维介绍给当时在巴黎的法国科学院名噪欧洲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博物学家。他们每个人都提出了需要了解和搜集的长长的名录。爬行动物学和鱼类学教授提醒注意中国北方的爬行动物、鱼类和两栖类。有专家提出,中国人培育的奇形怪状的金鱼会受到人们最热烈的欢迎。动物学家提出,要搜罗完整的哺乳动物标本和所有鸟类标本;无论是标本还是活物都需要。科学家们还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受到冰河作用太大影响的国家。它保存的动植物种类,对欧洲科研人员极具诱惑力。科学家们表示,会对戴维的科研工作提供资金上的帮助。戴维肩负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法国科学院通讯员、英国皇家动物学会通讯员的职责前往中国——虽然他身披着传教士的长袍。
1862年2月,36岁的戴维神父带着科学家们拟出的全部名单,从马赛登上了前往中国的海船。陪同他前往中国的向导是北京教区的穆利(Mouly)主教(1869年12月4日逝于北京)。他们经过5个月的艰苦旅行,几经辗转,于7月5日到达北京。
戴维到北京后先住在皇城北部的一座教堂,以后长期住在天主教北堂。早期的北堂建在中南海中海西畔的蚕池口(今国家图书馆斜对面),于1703年12月9日举行开堂礼,命名“救世主堂”。开明的康熙皇帝还亲撰匾额“万有真原”和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相贺。1827年,教堂被没收拆除;1860年又发还教会重建,终在1866年建成。1887年,皇家为扩建宫廷,补偿45万两银子,把北堂迁址到现在的西安门内西什库。从康熙帝允许天主教入京起,这一带就是天主教遣使会,即味增爵会的地盘。现在的西什库教堂内有两个皇亭,立有迁址北堂的记事御碑。在19世纪,天津教区属北京教区味增爵会管辖。直到1912年经罗马教廷批准,天津才设立单独的遣使会教区,首任主教是法国传教士杜保禄。
天主教在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教堂,是1605年在明朝万历皇帝批给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的住地基础上扩建的,称宣武门天主堂,又叫南堂。以后汤若望、南怀仁对此屡有扩建。
二、北方考察:把麋鹿介绍给欧洲
1862年9月,戴维考察了从北京直到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一带。
1863年,戴维考察了北京周边及京西的群山。6月1日,他从北京给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寄出了第一批包裹,包括蒙古的24只鸟和6只哺乳动物、中国的83只鸟的标本。亨利·米勒—爱德华兹收到后,立即于9月10日给戴维写信,高度评价这些高质量的标本,并认为有的鸟类标本是科学上的新种。信中说:“您在博物学方面的知识,您对于科学的热情是您研究成功的最可靠的保证。”对之期盼已久的法国及欧洲的科学家们,预感到戴维正在打开一座动植物宝库紧锁的大门。每一位科学家都写信鼓励戴维,并翘首以盼来自中国的更多好消息。
1864年5—11月,戴维考察热河地区。这年在收到戴维寄出的两批标本后,德凯纳于11月4日写信说:“中国的植物对于我们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兴趣;该国有许多东西,其中气候就同法国气候非常相似,这些植物差不多都可在我们这里引种驯化。无论是经济植物或者观赏植物,还是普通的植物,它们都有明显的用处。”
1865年初,戴维在考察中听人说起,在北京南海子的皇家猎苑中,养着一种叫“四不像”的动物,它的角似鹿非鹿,颈似驼非驼,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他寻找到机会,从墙头窥视了这种中国的特有动物(实为麋鹿),不由大吃一惊。据说他花了20两银子,买通守卫的军士,弄到了麋鹿的皮骨。1866年2月,他在寄往巴黎的标本里附着详细的说明书:“第2467号。驯鹿:雄性老鹿,雄性幼鹿,雌性成年鹿,头部分离。我已经在米勒—爱德华兹先生的好几封信里谈过这种驯鹿,认为它构成一种尚未描述过的物种。”“四不像”是中国人的称呼,戴维接受并宣传出去,认为它有鹿一样的角,牛一样的脚,骆驼一样的脖子,驴一样的尾巴。很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做出鉴定,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鹿科新种,因为是戴维发现,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戴维神父鹿”(Pere David Deer),也称“戴维鹿”(大卫鹿)。《自然公报》发出消息后,在欧洲引起轰动,都传诵说在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皇家禁苑中,养着世界独一无二的瑞兽“四不像”。各国渴望得到这种珍稀动物。法、英、德、比等国家的驻清公使馆通过戴维或官方渠道,在1866—1876年间,从南海子弄走了几十只麋鹿到本国喂养。
1894年,永定河水泛滥,冲垮皇家猎苑,100多头麋鹿被冲散,成了饥民的盘中餐。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德国军队就驻扎在南海子一带,把仅存的麋鹿杀掉吃肉,品尝珍馐。在无人知晓之中,麋鹿就这样在中国绝迹了。
1896年7月,作为钦差大臣的李鸿章到欧美五国访学。他到了法国,参观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园,看到很多中国动物,其中“见麋鹿成群,呦呦虞虞,不类欧洲之产,询之来自上林,则不觉愀然矣”。这是中国官员在欧洲见到麋鹿的首次记载。
19世纪末,英国乌邦寺庄园主人十一世贝德福特公爵把散落在欧洲各国仅存的18只麋鹿,全部高价收购到自家庄园喂养。据《我在中国三十年》的作者冰雪玉(玛雅博士)女士说,从1894—1899年,公爵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园就先后买了10只麋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乌邦寺麋鹿繁殖到88头,二战时已达255头。中国科学家薛德焴于1918年6月在《博物学会杂志》上发表《四不像之名称及现状》一文说,“而我国之四不像,亦竟与清室以俱亡。其幸而免者,受西人保护以延其残喘”。“热心国粹之君子,曷赴欧洲,设法逆输,使其再复旧土。”
1955年,英国伦敦动物园曾将两对麋鹿作为礼物赠北京动物园,但未能繁育。
1979年,中国动物学家谭邦杰呼吁麋鹿回归,要引进麋鹿喂養。英方积极响应。1985年8月24日,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十四世贝德福特公爵)将22只麋鹿无偿赠予中国,喂养在北京南海子。侯爵承担了麋鹿的全部运输费用,1987年又赠18只。江苏大丰、湖北石首也建起麋鹿保护区。到2018年,中国繁育、野放麋鹿达4000只以上。这是全世界濒危动物回归故地繁育成功的最典型范例。这些史料其实也讲述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戴维对麋鹿的科学发现和推介,麋鹿可能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865年,戴维发表了《华北自然产物和气候及地质情况观察》,总结了来华三年的考察成果。
1866年3月12日,戴维从北京出发去宣化府,修士舍夫里埃同行,沿途考察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内容。他们还先后考察了乌拉特、包头、鄂尔多斯、阿拉善、萨尔齐。戴维于10月26日回到北京寓所,结束为期七个月的考察。此间他曾一度发烧,卧床不起,被送到宣化府养病一个月。
戴维神父很严格地评估了他的蒙古(实指今内蒙古)之行:“1866年,我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了在蒙古的首次重要旅行。我在那里完成,并且寄往法国的收藏品是不太出色的。这片蒙古高原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令人绝望的贫瘠,然而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动、植物新种(一些从科学上来看,另一些则是从动物地理学上来看)。这是我付出辛劳的代价。很可能我的出征本来会取得科学上更大得多的成绩,如果那时中国西部没有叛乱的话。叛乱阻止我穿过甘肃,直深入到青海湖以西。正如我原来的打算:这个地区是尚未开发过的,很难行走,应该是隐藏着不止一类的新东西。”
戴维在中国的辛勤工作和重大发现,激起了欧洲博物学家和博物馆的极大关注和利益争执。巴黎的亨利·米勒—爱德华兹馆长以祈求的口气给戴维写信说:“求您不要向斯温霍先生或别的英国鸟类学者寄出任何东西”。“斯温霍先生不仅仅负责科学事务上的动物学,他还从事他弄到手的物品之交易。他寄出大批哺乳动物的皮张给伦敦和巴黎的商人”。“为了博物馆和法国出版商的利益,我们恳切地请求您慎重地寄出那些您认为适当的东西”。“法国的博物学家们如果见到外国人在新物种的发表上超过自己,那确实将会是非常难过的。他们希望由他们最倚重的博物馆的通讯员们的热情和知识来丰富科学。”以后,戴维把他于1866—1868年对中国的考察,写成《蒙古与中国旅行记》(《Journal of Travel in Mongolia & China》)发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