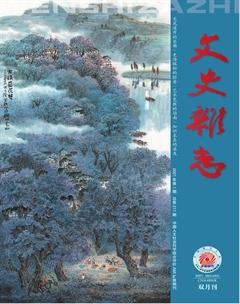李调元与乾嘉时代的川剧
张学君



李调元学识渊博,著述等身;但他不同于一般皓首穷经、心无旁骛的儒学之士。他有旺盛的求知欲望和十分广博的兴趣爱好,尤其对植根于民间文艺宝库的戏曲艺术,兴趣极浓,时有涉猎。一直到退隐回乡,他才得以沉浸在自己喜爱的戏曲艺术之中,至死不渝。
在李调元的有生之年,对川剧五大声腔中的雅部昆曲着力尤多;在与花部声腔交流过程中,对高腔、弹戏、胡琴戏喜爱有加,还组建新的花部伶班,专门排演精彩大戏,并着手改编了不少传统剧目。这期间,他与戏曲名家魏长生的交谊,对川剧艺术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一、在家乡创办昆曲伶班,成为川昆的发祥地之一
要知道李调元为何在家乡罗江创办昆曲伶班,得从明清时期昆曲的流行情况谈起。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创始人顾坚,自号“风月散人”,寓居江苏昆山,所创曲品被称为“昆山腔”或“昆曲”。及至明嘉靖年间,经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剧作家梁辰鱼及其他艺人改良创新,形成独特剧种。昆曲取材于乐府、杂剧,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昆曲唱词骈俪典雅、文采飞扬、韵味无穷;曲调细腻婉啭、幽雅动听,有“水磨腔”之称。昆曲唱法讲究行腔多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1];伴奏乐器有箫、笛、笙、琵琶、檀板等。同时,在舞台艺术方面,昆曲继承了宋元以来的戏曲遗产,创造出近乎完美的表演艺术体系,对清代以来的南北各地许多戏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清代前期的成都,随着南北各省移民汇集、城市工商业繁荣,娱乐业出现了兴盛局面。苏昆已随江苏、浙江等省移民传入四川。当时流寓成都的江南籍官员、幕僚较多,对昆曲情有独钟;本土官员、文人、学者,也因昆曲声腔优美、文辞雅训,喜欢观赏,尊之为“雅部”。作为阳春白雪的昆曲,摘取了锦城娱乐业的桂冠。面对花部秦腔、石碑腔、弋阳腔、楚腔荟萃的成都戏曲舞台,“梨园共尚吴音”[2]。
当时的曲会大多在官宦贵胄的府邸、私宅举办,谓之堂会。新年节庆、花朝月夕,一般省城督、抚两司署内例有堂会,或自养戏班,或雇佣外间戏班演出。堂会事宜“多系首县承办”[3]。四川总督署的堂会,自然由成都、华阳两首县轮流坐庄。每次演出,司道、大府、首县毕集,幕僚、清客如云,江南籍官员往往携带眷属赴会。男宾女眷中,不少人熟悉声乐、唱腔,演出时,或跻身乐队,敲击檀槽、丁宁,吹奏箫管、短笛;或客串剧中角色,各展其长,场面十分热闹。
乾隆时期,成都最活跃的昆曲演出团体“舒颐班”常在督署演出,著名昆曲演员彭四“扮生丑戏,机敏圆活”;花旦曾双彩“初出台时,貌美如花,一时无两,亦颇能画山水花草,见者欲以八百金买出之,班主不从。今彭、曾俱在舒颐班中。”他们的演出既为观众喜爱,也颇得川督保宁欢心。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保宁奉旨赴新疆督察屯户增拨地亩,曾经四次前往伊犁,驻节时间长达数年。彭四等名角都“随侍”左右。这批伶人后来回到成都,“技痒度曲,不惯闲也”[4]。
由此可知,在成都剧界,昆曲是一支独秀,在文化素质高的观众中,具有特殊魅力;士大夫观剧、度曲成风,闲暇“多为丝竹之会”。李调元盛年,正是昆曲兴盛于上层社会的时期。他适逢其会,乐乎其中;中年罢官回川,“谢却尚书锦江聘,却来村塾振金声”[5]。他婉谢川督李世杰礼聘锦江书院山长,却选择回归故里罗江家乡开办“村塾”,确乎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显得不合时宜。更有甚者,这个“村塾”不是传授四书五经,为科举制艺服务的私塾,而是教授梨园曲目的伶童戏班。他决心将自己余生献给让他陶醉的昆曲,亦曾以诗明志:
笑对青山曲未终,依楼闲看打渔翁。
归来只在梨园坐,看破繁华总是空。
生涯酷似李崆峒,投老闲居杜鄠中。
习气未除身尚健,自敲檀板课歌童。[6]
这是对自己闲居生活的自述。“梨园”是他自办的伶童戏班。李崆峒即明代著名诗人李梦阳,多才多艺,名列前七子,仕途坎坷,得罪权贵宦官,几遭杀身之祸。“杜鄠”即杜陵附近的户县,山野僻处。刚开始,他自娱自乐,“因就家童数人,教之歌舞。每逢出游山水,即携之同游。”[7]此后,李调元的乡居生活便沉浸在敲击檀板、浅唱低吟的乐趣中。他对戏曲艺术有浓厚兴趣,故曰“习气未除”,在归隐故里不久,就自创昆曲伶班,延聘精于昆曲艺术的江苏教师。其中一位名邹在中,吴县人,“侨居成都,善昆曲,延至家,教小伶”[8]。李调元招睐有戏曲禀赋的儿童学习昆曲艺术,进而教授昆腔杂剧。“家有小梨园,每冬月围炉课曲,听教师演昆腔杂折,以为消遣。”[9]他置办的伶班,教习地道的昆曲艺术,“先生实苏产,弟子尽川孩。”这是说,伶班聘请江苏籍昆曲教师,招收的学生全是四川儿童。“书塾兼伶塾,英才杂俊才。小中堪见大,此宜费栽培。”[10]因昆曲唱词典雅,學生得兼修古典文学;有了文言基础,对深入理解繁难曲目、唱词、道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伶童既读书可成英才,又学戏而成俊才,文艺双全,一举两得。李调元对伶童的培养途径,从素质教育方面下功夫,将文化课程作为艺术深造的基础;虽然花费时间较长,但效果极好。他的伶班按行当规范,从最初的10人左右逐步扩充至20人左右后,开始编排传奇大戏《红梅记》《十五贯》《汉贞烈》等古典杂剧。他又改编《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苦节传》等四大本。他记载剧目演出盛况说:“今年乙卯人日,自携家乐,邀何九皋同观(《红梅记》)。主人置酒其下,听演《红梅记》传奇,为作一律”,其诗云:
一样春风两样分,漫言间色夺缤纷。
浅深绛染江边雪,远近霞烘岭上云。
人依栏杆同笑语,天教阆苑入群芳。
当筵更奏红梅曲,要算霓裳再得闻。[11]
在这首诗中,李调元抒发了与友人共同观赏自己“伶班”首演《红梅记》传奇大戏的感受。舞台沉浸在春风荡漾、五彩缤纷的气氛中;故事在景物的季节变化中展开,剧中人依栏笑语,如同天上人间。当箫笛、琴瑟演奏出《红梅曲》时,观者感受如同霓裳羽衣舞再现人间。
除编演当时流行的昆曲剧目外,还有江苏昆曲名家、时任邛州知州的杨观潮所编《吟风阁杂剧》32种,这些杂剧“深得元人三昧”[12]。李调元又将戏曲名家李渔(笠翁)所著十种曲纳入,“令皆搬演”[13]。
昆班伶童培育成才后,须要舞台献艺,得开辟公开演出的场地。早年其父李化楠在家乡与友人重修梓潼宫,“兼修乐楼一座”[14],俗称“万年台”,每年庙会时节,用以酬神献艺。县北河村文昌宫,与李调元所居南村一水之隔,酬神演剧之时,“阖村士女,无不聚观”[15]。“当二月三日(文昌)帝君降诞,则(南北)两村之人及附近各村并走,相与焚香祝献,优伶歌舞以为乐。”[16]众多村民看戏,以致散场后蔗皮满地。他描述现场:“古寺僧稀松叶少,戏场人散蔗皮多。”[17]他后来又捐资修建五显庙、观音岩大殿,“每逢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乞灵报赛者毕聚,此日为之酬神演剧。其会之大,几与二月初三七曲山梓潼会等。”[18]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他與蜀中文士雅集,曾带伶班去成都浣花溪助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冬,率班去绵竹,为好友、知县陈湘维祝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应会首之约,李调元率伶班到绵州太平乡,为民间集资兴建的天池寺灵官楼落成献艺,演出《赤壁鏖兵》等三国戏。[19]李调元的伶班不仅在家乡罗江演出,而且“走州过县”,在安县、梓潼、什邡、绵竹、绵州、成都等地演出;因其伶童学有根底、演艺精湛,一时名扬远近,人称“翰林班”。
李调元凭一己之力,将苏昆移植到四川本土,培育出一批地道的昆曲艺术人才。有人记载当时民间演戏,也有昆曲班演出的实况:“尝观民间演戏,有昆曲班戏,多用〔清江引〕〔驻云飞〕〔黄莺儿〕〔白莲池〕等曲名。”[20]稍后在反清白莲教军中,也用这些曲牌名唱戏,与昆腔班相似,足见昆曲在四川地区已有一定的传播与影响。
但是,纯正的昆曲虽然声腔优美,文辞雅训,赢得士大夫阶层喜爱,却因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无法使城乡文化程度低的观众接受。这些观众很难听懂来自江苏的昆曲唱词和道白。当时就有人发现这一问题:“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如果)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21]必须解决语言障碍,才能使之融入民间娱乐文化。李调元自办的伶班主要是为罗江周围川西一带的家乡父老演出,必须让他们看得懂,听得清,才能广为流传。这些四川昆曲艺人为了争取更多观众和演艺市场,必然会将苏昆本土化,使之适合四川观众的视听习惯,这是川昆出现的历史条件。这一问题,李调元在与魏长生等花部名伶交流以后,深有所感,因此再办花部伶班以补美中不足。
二、关注名旦魏长生,再办花部声腔伶班
李调元任京官时,恰遇魏长生在京城献艺;与蜀中名旦魏长生的关注和交谊,是他放开视野,将兴趣扩展至花部声腔的一个重要情节。
当时乾隆皇帝喜好戏曲,宫廷庆典常有喜庆大戏隆重登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时北京城里是外地戏曲班部竞相献艺的场所,四川、陕西、安徽、江苏等省流行戏曲走马灯似地轮番上演,观者如云。
李调元与魏长生相识,大约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李调元时任京官,有机会观看魏长生搭班双庆部在京城演出秦腔《滚楼》。《雨村诗话》有魏长生在京城火爆演出的记载以及川旦走红的记载:
近日京师梨园以川旦为优人,几不知有姑苏矣!如在京者,万县彭庆莲、成都杨芝桂、达州杨五儿、叙州张莲官、邛州曹文达、巴县马九儿、绵州于三元、王升官,而最著为金堂魏长生,其徒陈银官次之,几于名振京师。《燕兰小谱》云:长生名宛卿,昔在“双庆部”,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22]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李调元虽然忙于宦海事务,但对常在京师演出的家乡戏曲艺人十分了解。对于当时名振京师的川籍名伶的出色表演,他是赞赏有加,耳熟能详。他很可能与时在双庆班的男旦魏长生相识。魏长生首创戏曲表演艺术的个性化路径,饰演的花旦表情丰富、做工细腻,唱词通俗易懂,腔调悦耳动听,并以胡琴、月琴伴奏,繁音促节,声情并茂;又勇于创新,将旦角包头改为梳水头、贴片子,并发明小脚踩跷技艺,为旦角舞台艺术增辉不少。
魏长生,因排行第三,人称魏三。其系四川金堂县人氏,幼年家贫,随舅父去陕西入秦腔班(同州梆子)学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他随双庆部入京,以秦腔戏《滚楼》“名动京师”,成为四大徽班进京以前,北京戏曲舞台上的佼佼者。其“色艺盖于宜庆、萃庆、集庆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京秦不分”。“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魏三者,无以为人。其徒陈银官,复髻龄韶秀,当时有青出于蓝之誉。”[23]吴太初《燕兰小谱》记载:“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24]当时荟萃京师的各省伶人,均向魏三及其弟子陈银官观摩学习。李调元不仅观看了魏长生在京师的演出,还吟诗一首,赞叹其精彩表演。可见魏长生的秦腔唱做俱佳,令他感动:
媚态绥绥别有姿,何郎朱粉总宜施。
自来海上人采逐,笑尔翻成一世雄。[25]
李调元对魏长生别具一格的表演艺术评价极高,认为从扮相到做功都极有魅力,倾倒观众,笑揄他“翻成一世雄”。魏长生似乎天生男旦,浑身脂粉气;但是,李调元有机会观看了魏长生另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后写道:
近见(魏三)演贞烈之剧,声容真切,令人欲泪;则扫除脂粉,固犹是梨园佳子弟也。效颦者当先有其真色,而后可免东家之消耳。[26]
这是他在观看魏长生演出《汉贞烈》(即《昭君出塞》)剧后的感触。李调元未料到魏才生竟能遍扫脂粉,不再是忸怩作态的红粉佳人。这对他广开戏路,是一大启发。只是魏长生后来终被禁演“淫秽之戏”,被驱逐出京。
魏长生无奈,只好南下搭班演出,在扬州加入江鹤亭的春台班。当时著名学者赵翼不仅了解他,还记下在扬州与魏长生邂逅的情节:
近年闻有蜀人魏三儿者,尤擅名,所至无不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后。余已出京,不及见。岁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余至扬州,魏三者忽在江鹤亭家。酒间呼之登场,年已将四十,不甚都丽。惟演戏能随事出新意,不专用旧本,盖其灵慧较胜云。[27]
由于魏长生演戏不专注旧本,喜欢创新,别开生面,遂在扬州又红极一时,当地花部和昆班伶人争相仿效。他以后辗转苏州等地演出,各地伶人受到魏长生高超演技和唱腔的影响,“转相效法”,“采长生之秦腔”[28]。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因清廷查禁更严,魏长生与其徒弟陈银官等被押回原籍。当时李调元已解职归田十年,往返罗江、成都间,他曾于新都见到陈银官,模样大变,“非复前观矣”。在他过金堂时,魏长生从成都写信给他,预约一见。李调元回复律诗二首:
魏王船上客,久别自燕京。
忽得锦官信,来从绣水城。
讴推王豹善,曲著野狐名。
声价当年贵,千金字不轻。
傅粉何平叔,施朱张六郎。
一生花底活,三日坐中香。
假髻云霞腻,缠头金玉相。
燕兰谁作谱,名独殿群芳。[29]
二诗表达了李调元对魏长生的深切怀念。魏长生故乡金堂县城又称“绣水城”。与魏长生相识,使李调元对秦腔、胡琴戏、高腔等花部声腔刮目相看。
从清初开始南北各省向四川大规模移民浪潮中,陕西移民入川最早。秦腔是由陕西移民传入四川的,清初已在川西各地社戏中演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时任绵竹知县陆箕永在竹枝词中即兴吟咏说:
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板檀槽柘作梆。
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30]
明末清初战乱以后,四川人烟稀少,陕西移民,特别是陕西商人最早入川,秦腔也因此最早传来。陆箕永做知县的绵竹县、魏长生的故乡金堂县、李调元的故乡罗江县,都是川陕商路沿途的重要城镇,也是秦腔首先传播的地区,城乡民众对秦腔耳熟能详。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上距李调元归里初创伶班的时间相隔十年有奇。他对戏曲的研究卓然可观,著有《雨村曲话》《雨村剧话》,将当时流行声腔、传奇人物和自己对戏曲的理性认识都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他不仅对雅部昆曲兴趣甚浓,对花部秦腔、弋阳腔、吹腔、女儿腔均有切实论述。他对戏曲的关注更上层楼,从情有独钟的雅部昆曲,扩展到花部声腔(包括胡琴、弹戏、高腔、灯戏)。他对原属秦腔的四大本《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苦节传》进行了改写加工,目的是供自己的花部伶班或附近乡班演出弹戏之用。[31]他回复当年同窗姜尔常的诗中,表达了自己不再过问宦海之事:“况有笙歌蛙两部,难离奴辈桔千头。”[32]“蛙两部”,指他的伶班从原有的雅部习唱昆曲外,又增加了一个习唱花部声腔(包括高腔、胡琴、弹戏、灯戏)的伶童班,正倾力营造雅俗兼备的班部。
三、李调元与乾嘉时代的川剧
李调元生活的乾嘉时代,已然盛世气象。鉴于四川遭受长时间战乱,清廷除实施近百年的移民政策外,还对四川实行特殊的田粮蠲免政策:“四川古称饶沃,国初定赋,以其荐经寇乱,概从轻额,故其地五倍江苏,而钱粮不逮五分之一。”[33]。四川地区经过百年之久的大移民和休养生息,人口、经济均大幅度增长。作为四川民间文化代表的戏曲,借助经济复苏和人口增殖进入全盛期。在全国三百多个剧种中,川戏在乾嘉时代已形成昆曲、高腔、胡琴、弹戏和灯戏五腔争辉的局面,多数班子仍以单一的声腔演出,如“老庆华班”专唱高腔,舒颐班专唱昆曲,魏长生的双庆部专唱秦腔(弹戏梆子腔),名角苟莲的乡班专唱高腔,张四贤的上升班专唱胡琴腔。乾隆年间,李调元在家乡庙会已耳闻“一唱众和”“节以鼓,其调喧”的高腔曲调。他在《雨村剧话》里考证高腔渊源:“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俗谓之高腔,楚蜀谓之清戏。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34]嘉庆《绵州志》记载:“乐部向有楚音、秦音,城乡酬神赛会在所不废。”[35]这里的“楚音”应是高腔,“秦音”应是弹戏(梆子腔)。年节岁时和赛神庙会,各地戏班皆有会首预约,定期演出。乾隆十四年(1749年)《大邑县志》记载:年节岁时“装扮杂剧故事,逐户盘旋,箫鼓喧阗”。酬神庙会,则在各省会馆演戏。季春初三日真武帝君圣诞,“楚人会馆、真武宫集梨园庆祝,城北圣母殿亦如之,观者如堵”。五月十三日,关圣大帝降诞,“秦、晋会馆工歌庆祝”[36]。同时顺应观众对演艺的多种需求,演艺圈开始从单一声腔的班部,向双声腔、多声腔班部转化。这就逐渐“将高腔、昆曲、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集于一班,或合于一台演出,形成集五种声腔于一个剧种的川剧艺术”[37]。
李调元的“翰林班”,即从单纯的昆曲班增办花部乱弹伶班,成功地转化为“昆乱不挡”的五腔共存川戏班。“翰林班”从最初的昆班扩大为兼容昆曲、高腔、胡琴、弹戏和灯戏的大戏班之后,即将五种声腔荟萃一班,旧称“风绞雪班子”。从李调元的大戏班搬演李渔的十种曲的归属看,确实体现了昆乱不挡:《比目鱼》(昆曲、兼唱高腔)、《蜃中楼》(弹戏)、《怜香伴》(弹戏)、《慎鸾交》(高腔)、《巧团圆》(高腔)、《奈何天》(高腔)、《风筝误》(高腔)、《玉搔头》(弹戏)、《意中缘》(弹戏)、《凤求凰》(又名《凤凰琴》,高腔)。[38]其中花部声腔,特别是最受民间欢迎的高腔竟占有六种(包括兼唱)之多,其次是弹戏占四种,昆曲只占一种,几成花瓶;而且与高腔平分秋色,原本是昆腔戏,已被高腔分享了。
为适应本地人口和外省移民“五方杂处”、习俗各异的娱乐需求,省城成都戏曲班部都在各省会馆竞演自己的拿手好戏,亦集各省地方戏之长,兼收并蓄,形式多样,昆、高、胡、弹、灯各展其长;加之剧目丰富,多姿多彩,深受群众欢迎。嘉庆初年的《锦城竹枝词》说:
见说高腔有苟莲,万头攒看万家传。
生夸彭四旦双彩,可惜斯文张四贤。[39]
苟莲官是专唱高腔的艺人,常年随乡班游走演出(跑滩)。其每进省城,则见挤墙踏壁,观者如云。彭四是演唱昆曲的生、丑行演员。张四贤在“上升班”中“扮净(花脸),唱胡琴戏,一气可作数十折,吞吐断续往往出人意外。性好读书,亦知作诗,茶园酒肆中,时与文人论文字,灯下高声颂唐宋大家古文數篇,习以为常,因有张斯文之目。”[40]
这就说明,乾隆后期,胡琴腔在成都周边的川西坝子方兴未艾。李调元说:“今世盛传其音,专以胡琴为节奏,淫冶妖邪,如怨如诉,盖声之最淫者。”这个“淫”字,应当理解为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翰林班与时俱进,排演了一批胡琴戏剧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李调元在金堂会见从北京归来的好友何云峰,得知朝鲜来华使臣入觐,他们能背诵李调元的诗歌,并打听李翰林的近况。李调元听后大喜,高唱胡琴二黄腔:“观君一举醉百愁,随我歌舞听丝黄。”[41]其时年节,迎神、报赛、宴会、酬宾,城乡聚落均有不同班子频繁上演精彩纷呈的大戏,如玉泰班二月沿街演出的“春台戏”(专为迎春或闹春而创设的城镇、乡村聚落的娱乐活动),时人有诗吟道:
玉泰班中薛打鼓,滚珠洒豆妙难言。
少年健羡多花点,学问元霄打十番。
戏演春台总喜欢,沿街妇女两旁观。
蝶鬟鸦鬓楼檐下,便益优人高处看。[42]
成都会馆、聚落演戏开场,一般不限时间,只要演出内容精彩,观众情绪就十分高昂。惟独陕西会馆规矩甚严,约定放纸爆为节,一、二、三爆后不开场,会首下次即不再招雇此班。时人有赞:
庆云庵北鼓楼东,会府层台贺祝同。
看戏小民忘帝力,只观歌舞扬天风。
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
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
成都年节盛行“社火”戏,艺人踩高桩,情景动人,热闹非凡:
迎晖门内土牛过,旌旆飞扬笑语和。
人似山来春似海,高妆女戏踏空过。[43]
各省客籍会馆是经常演戏的场所,各省客商习俗爱好不同,大多偏爱本省地方戏。成都陕西会馆最盛,馆内秦腔梆子最叫座。生活情调浓郁的四川灯戏也颇受欢迎,在年节岁时的车灯、采莲船边唱边舞。这正是:
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
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
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得是淫声。
《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44]
陕西会馆是陕西移民和商帮的聚集场所,节庆日都会有秦腔班子演出梆子戏。实际上经历了百年沧桑,秦腔已转化为弹戏,用板胡,俗称盖板子伴奏。灯戏起源于四川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俗称“梁山调”。元宵节前后,城乡都流行灯戏,《回门》(即《驼子回门》)、《送妹》(即《钟馗送妹》)是民间流行的灯戏,足见灯戏已成川戏声腔之一。
由此可知,多声腔的川剧是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产物,最初是各省移民从自己故乡带来了原汁原味的乡土戏,在客籍会馆或是移民聚落里举行庆典时演出。随着历史的推移,百余年后的四川社会,各省移民逐渐融合(老移民的后代、再传后代已经本土化了),从口音、身份到文化习俗逐渐趋同。乡土戏也在适应这种变化:苏昆转化为川昆,秦腔转化为弹戏(俗呼梆子腔),弋阳腔转化为高腔,甘肃西秦腔和湖北汉调、安徽的徽调转化为胡琴西皮、二黄腔,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演变。李调元在这种文化、习俗的变化中,是一位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从创办昆曲伶班开始,传播雅部苏昆,再转化为川昆;而后顺应移民社会文化需求多元化的趋势,将“翰林班”快速扩建为“风绞雪戏班”,成功转化为五腔同台、文武兼擅的川剧伶班。这个变化发生在乾隆晚期,应是川剧滥觞,即一个大剧种初步形成的时期。[45]李调元与他同时代的伶界好友魏长生等艺术家们携手合作,在这场戏曲艺术变革活动中相互启迪,共同努力,虽经艰难困苦,终成正果。他们在为当时观众展示丰富多彩的多声腔表演艺术的同时,也对精致、典雅的川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历史推动作用。
在以后两三百年间,代表川剧艺术不同流派的“四个河道”在器乐曲牌到唱腔和表演领域都各展其长:沱江流域的资阳河流派以特色浓郁的高腔戏表演艺术见长;岷江流域的川西坝流派以胡琴戏表演艺术见长,俗称“坝腔”;嘉陵江流域的川北河流派靠近陕西,受秦腔艺术影响,以弹戏表演艺术见长;重庆以及下川东流派地接两湖,受湖北汉剧、湖南湘剧、辰河戏影响,五种声腔兼擅,常带“川夹京”“川夹汉”味道。[46]四条河道在演出实践中得到广大戏迷观众的喜爱,都各自拥有演艺超群的名角、大师和传承体系,使川剧艺术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拥有上亿观众的大剧种。
注释:
[1]顾起元:《客座赘语》。
[2][21][28]焦循:《花部农谭》。
[3]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仁宗四年五月谕旨”。
[4]转引自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5]李调元:《童山诗选》卷四。
[6][13][15]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九。
[7]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
[8]李调元:《续涵海·新搜神记·梦魔》。
[9]李调元:《雨村诗话》卷六。
[10]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二十五。
[11]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四。
[12]姚燮:《今乐考证·著录四·国朝杂剧》。
[14][18]李调元:《罗江县志》卷七。
[16][32]李调元:《罗江县志》卷八。
[17]李调元:《罗江县志》卷九。
[19][38][45]蒋维明:《乾隆朝后期的“风绞雪”川戏班》,四川省民俗学会等编《川剧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9页。
[20][24][29][30][35][39][40][42][43][44]戴德源辑录《四川戏曲史料》第73页,57页,60页,38页,69页,74页,75页,73页,75页,76页。
[22]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一。
[23]昭梿:《啸亭杂录》卷八《魏长生》。
[25][26]李调元:《雨村诗话》卷十。
[27]赵翼:《檐曝杂记》卷二《梨园艺色》。
[31]蒋维明:《李调元对川剧的多方面贡献》,四川省民俗学会、罗江县人民政府编《李调元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28—137页。
[33]薛福成:《光绪元年上治平六策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一,《治法类·通论》。
[34]李调元:《雨村剧话》卷上。
[36]乾隆《大邑县志》“风俗·岁序令节条”
[37]胡度、刘兴明、傅则编《川剧词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
[41]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一。
[46]杜建华:《从川剧形成历史看传承发展路径》,《问道川剧》,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