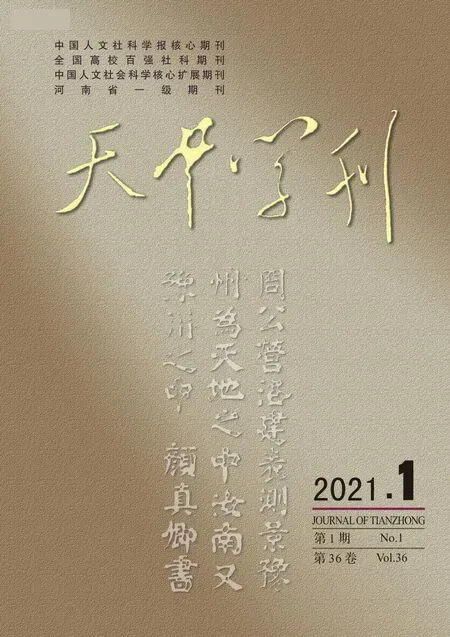克里木战争期间恩格斯论战争及其当代启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王晓红
克里木战争期间恩格斯论战争及其当代启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王晓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论创新基地,北京 100732)
恩格斯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所写的一系列军事评论文章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对战争的理解:战争是以利益争夺为目的的权力扩张,受制于国内政治制度,战争并非纯粹战场上的实力比拼,也与外交政策相互影响,战争期间媒体沦为政治工具。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恩格斯认为,随着利益冲突的不断升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表现不仅充分展示了其试图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也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将要面临的战争风险。
恩格斯;战争;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军事思想
19世纪中期,俄国与土耳其和西欧发达国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主要在克里木展开,因此也被称为克里木战争。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战争局势,写作了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军事评论文章,成为我们分析研究战争的理论依据。我们认为,战争并不是交战双方单纯在军事实力上的竞争,而是包含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力量的较量,战争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表现在国内政治力量和国际政治力量的角逐之间,是国内外各种力量平衡的复杂结果。了解战争的复杂性,才能更好地知道如何制止战争,为争取和平奠定基础。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笔者撰写本文,主要探讨恩格斯关于军事战争与军事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外交策略、媒体以及文化传统等之间关系的理论①,以作纪念,同时表达对时局的点滴认识。
一、战争是以利益争夺为目的的权力扩张
19世纪中期,庞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然衰落,法国在拿破仑帝国被推翻后元气大伤,英国专注于在海外扩张殖民地,沙皇俄国在镇压欧洲1848年革命后,巩固了其欧洲霸主地位,尼古拉一世雄心勃勃地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黑海作为通往地中海的咽喉和亚欧两洲交通要道,成为俄国虎视眈眈的目标,俄国若顺势攻下伊斯坦布尔,世界上也许会出现继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后的另一个强大帝国。
7.积极开展业主引导。当前,国内建设方常常要求设计、施工、采购分开进行,获取各专项优势资源,对于全盘交付的EPC模式怀有谨慎和质疑态度。建筑企业应发挥品牌影响力,对业主进行引导,配合国家政策导向推动有序市场的建立,有利于自身业务拓展,更有利于建筑行业的健康、多元化发展。
这一系列的试验,为掺砾心墙料的大型三轴试验的可行性提供了参考。而目前关于掺砾心墙料的冻融循环试验方面的研究不多,从黏土和粉细砂的冻融循环下的强度与变形、渗透性的变化规律,可以考虑不同掺砾量、冻结温度、冻融次数、围压等情况下冻融循环引起掺砾心墙料的强度与变形,以及渗透性的变化进行进一步的试验探讨,根据以上掺砾心墙的三轴试验需要注意的加载速率、砾石含量、围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合理控制这些因素对于冻融循环条件下掺砾心墙料的大型三轴试验的开展是可行的。
1853年7月,俄国以保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为由,突然入侵土耳其的属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法国的小拿破仑上台后,为了争取国内天主教人士支持自己当皇帝,照会奥斯曼帝国应当由法国天主教掌管伯利恒教堂的钥匙,土耳其惹不起法国就交了钥匙。耶路撒冷作为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的圣地,各国统治者都希望利用对圣地的控制以加强宗教统治并提高自己的政治统治。沙皇看到觊觎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就断然出兵土耳其。同年10月,土耳其对俄宣战。
强大起来的俄国自认为已经打破了欧洲的势力均衡,试图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争取更多的利益。尼古拉一世的真正目的是夺取对黑海尤其是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开拓通往黑海、波罗的海的通道,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这次战争的爆发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诉求。恩格斯在《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敏锐地指出,俄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吞并了土耳其和希腊以后,它就可以获得优良的海港,而且还可以从希腊人当中获得精锐的水兵。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它就在地中海的门前立定了脚跟;控制了都拉索和从安提瓦利到阿尔塔的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以后,它就可以进入亚得利亚海的腹地,窥伺着不列颠的伊奥尼亚群岛,并且只须36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马尔他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奥地利领地以后,它就完全可以像对待自己的藩属一样对待哈布斯堡王朝。”[1]18恩格斯预测,俄国在吞并土耳其之后也不会停止脚步,而是“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吞并匈牙利、普鲁士、加里西亚和最终建立一个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1]18。建立一个强大帝国,建立畅通的贸易通道,就是俄国这一时期竭力追求的政治野心和利益。
法国出兵不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更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1854年3月,小日罗姆·波拿巴的小册子揭露了一个事实,克里木远征是路易·波拿巴本人的创举。他清醒地认识到,“法兰西帝国的命运,现行社会制度的命运”[2]145都要通过战争来决定,这场远征决定着他个人和帝国的政治命运。在塞瓦斯托波尔久攻不下的时候,他甚至要亲自去克里木督战,因为通过留在巴黎来摆脱政治危机是不可能的;只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危机自然解除,而且他会被看作一个英雄,否则,他的帝国将会灭亡。因此,这次战争是波拿巴试图挽救帝国及其统治的战略性试验,他想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政治统治的矛盾。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惯用手法。
英国于1854年出兵援助土耳其,同样出于对自身利益目的的考虑,“正是……利益使它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1]14。土耳其是联通亚洲和欧洲的主要通道,“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能否指望它会敞开这些大门,让英国像过去一样,闯入俄国的贸易范围呢”[1]17?谁掌握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道路。同时,这两个海峡也是重要的军事要地。英国不可能放任这一交通要道被俄国侵占,放弃自己在亚洲的商业利益。因此,英国的出兵是必然的。
英国国内各界起初对土耳其的外交策略举棋不定。外交界一直认为应当维护“维也纳条约”所维持的现状,担心不维持土耳其现状,排挤土耳其人的统治,将会在巴尔干半岛引起大战。英国的亲俄派支持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认为维持现状不可取,从舆论上暗地里为俄国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做好酝酿。恩格斯则高屋建瓴地指出,“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1]37,历史的进程不可阻挡,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战争不会由于害怕战争、忽视现实而自动消失。
二、战争受制于国内政治制度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职责,还是对一个国家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外交政策、舆论民心等综合力量的全面考验。恩格斯对克里木战争中英国军事政治制度的弊端如何影响英军做了详尽的介绍评述。
英国军队的军事领导机关由四个各自为政而又互相掣肘的部门组成。这种制度在战争爆发后到处都显得无能为力,以至于“一个团可以不必向不同的各自为政的部门交涉的两件东西是找不出来的”[3]264。高级军官的提拔差不多只取决于资历或贵族关系,这必然会排斥很多有才能、有知识的人。军官的人数过多,训练制度和操典陈旧,导致部队的机动性非常差,以横队运动方法作为一切战术机动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有优越性,但在其他许多场合下并不有利。相比之下,欧洲大陆有些军队采用的纵队运动方法有更大的机动性,其队形在需要时也能构成横队队形。英国军队装备非常混乱,制服笨拙,辎重庞大,行军中实行的各种改进措施只能是暂时的,以往战争中获取的经验在之后并不能有效地总结落实为制度。
一是推进院厂结合。院厂结合是采油院立足油田大局、转变思想观念、服务油田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实现科研与生产有效对接的载体。采油院与各采油厂以“联合攻关、成果共享、责任共担”为指导思想,构建科研生产一体化的联合团队,建立与采油厂经常性工作对接机制,经常性地深入到所负责联系的采油厂了解开发现状、生产难题,系统整理后逐一确定解决问题的牵头研究单位,定期协调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有序开展。
如果说,军事政治制度对战争的胜负有直接作用,那么军事司令官是否能直接调度分配兵力,决定了军事命令的贯彻执行能否迅速有效,军需能否及时得到保障决定了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英国分权制衡的军事制度削弱而非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寡头政体加重了战争的消极影响,法案无法及时通过,贵族及其代言人而非专业人士在议会任职,因而无法对急需的事情做出正确判断,各方力量对抗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对战争这种需要及时做出决策的行动来说,这些都会大大削弱而非增强军队的力量。
恩格斯在《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这种军事政治制度给克里木战争中的英军带来的沉重灾难。英军虽然设有总司令,但这个总司令实际上什么都不能指挥,虽然步兵和骑兵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他,但炮兵、工兵和地道爆破兵完全不受他管辖;他可以发给每个步兵两个子弹盒,但不能发给他们步枪……“军械总工长”除了管辖炮兵和工兵外,也掌管大衣和枪械,因而一切军事行动都与他有关。军务大臣不能给任何一个部队下命令,但他可以阻碍任何部队的行动,如果他拒绝付钱,任何军事行动都无法进行。军队的给养由军需部负责,军需部隶属财政部,因此首相兼财政大臣可以影响任何军事行动,让军事行动延迟或取消。负责军队调动的陆军大臣掌管军队部署,但仍需要其他5个人的全体同意。这种相互掣肘制度的弱点在克里木战争中暴露无遗。每个人都只忙碌自己分内的事,谁也不想承担多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责任,都想把责任推给别人。于是,各个任务之间的衔接与调度分配就出现了问题。比如,轮船运送的储备品卸载在海岸上都已经腐烂了,还没有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军队住房不够;野战部队缺乏一切东西,而守备部队应有尽有等。军队管理上的混乱导致克里木的军队缺衣、缺食、缺住处、缺药品,以至于派往东方战斗的6万多军队,死者和病员加起来有43000名,而这其中“直接遭受敌人杀伤的还不到7000人”[3]633!最大的伤亡竟然是由军事制度造成的自损,这是英国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是战争史上以血写就的经验教训。军事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高效的军事制度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战争期间,英国政体的寡头性质对战争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议会中最重要的职位都委派给那些支持掌权者的各个财团的代言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维护的是各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利益,缺乏最起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英国议会成员名义上是由自己选区选出的,其实都是贵族及靠自己在当地的势力取得政治利益的人指定的。各个区选民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以及当选的议员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的比例并不恰当。议会效率低下,法案常常由于各方利益不均衡而无法通过,比如,1854年议会在常会期间提出了7个重要法案,结果其中3个被否决,另外3个被撤回,只有1个法案被通过,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议会工作在8月中断,在12月间再召集开会,为了通过两个刻不容缓的措施:外籍军团法案和以自愿方式利用民军在国外担任军事勤务法案。然而,这两个法案到写文章的1855年2月还仍是“一纸空文”[2]31。
更重要的是,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不仅是担心新生代外部审美的娘性倾向,更担心新生代内部精神失去阳刚之气。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就是阳刚之气,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立,也有“不阿权不阿世”的刚正,还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坚毅,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乐观。如果我们的民族失去了这样的精神品质,如果我们的男孩子失去了这样的价值导向,很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恩格斯认为,这是威灵顿公爵设置的僵硬不变的军事制度必然产生的可悲后果。“铁公爵”把滑铁卢会战胜利的全部光荣据为己有,成为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但是,他开拓进取的精神似乎在战争胜利后就不见了,剩余的就是维护自己的荣誉,甚至避免其他人有高于自己的成就。在他执掌军队的40年内,作为英国军队的实际指挥者,他设置的一切军队组织机构似乎都是为了相互掣肘。英国军队在他掌权的全部时期,除了伴随着工业和科学发展在技术上的改进,就没有做过任何一点多少像样的改善,制服、装具和一般组织都落在欧洲文明国家军队的后面。
三、战争与外交政策相互影响
战争不仅受制于国内政治,同样与外交策略相互影响。外交政策会影响战争,反过来,战争的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外交政策。这正如战争史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克里木战争期间,外交策略对战争的影响不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这当然与战争的进展、交战各方的战略目的以及希望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目的密切相关。
1.8 采后不注意保叶促根 冬枣采摘结束后,保叶促根为树体储存足够养分是来年丰产优质的基础,但很多果农采后不注意保叶,造成树体储存光合产物少,根系发育差。也有些果农秋季有机肥施入少,大量元素肥料施入多,不重视中微量元素肥料施入,营养元素不平衡,造成根系发育差,引起果实萎蔫。
英法出兵援助土耳其既是出于经济原因,为了亚洲贸易的畅通,以维护自己工业先驱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是为了政治诉求,稳定法兰西帝国及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外在化,是以强烈的暴力冲突为标志的一种夺取更大利益的斗争形式。
战争并非纯粹是交战双方战斗实力的角逐,也受外交策略的影响。克里木战争期间,许多战役、兵力调度等严格说来并非真正的战术,而是政治交易的筹码。俄、土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853年11月,俄军把8万人的军队带到瓦拉几亚,并在那里驻留了好几个月。这在战术上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那里远离帝国中心,且俄军伤员又多,兵力得不到补充,物资运输也困难。恩格斯认为,这只能解释为,俄国人相信“他们在英国政府内的朋友们的外交阴谋得逞”[1]532,这样的做法正是由于俄方以为外交策略能够达到其目的而轻敌造成的。1855年5月,在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中,战斗处于持续胶着状态,联军在弹药缺乏、火炮损坏的情况下,用减弱火力强度的方法延长炮击的持续时间。恩格斯指出,“这种做法是严重违背一切军事原则的”[2]234,其真正的原因是外交政治上的,因为此时维也纳会议正在召开,虚张声势的炮声是必要的。但对于战争而言,这种无效的炮击是白白消耗炮弹。因而,维也纳会议中断后,联军就不再使用这种无效的炮击方式,而是采取了更为坚决的行动,使用局部强攻、挖地道爆破夺取阵地、白刃战等更为激烈的攻击方法。
当然,把握战争的内在规律也会胜于外交策略。1854年,俄军围攻锡利斯特里亚是一场具有军事意义的行动。锡利斯特里亚是俄军通过巴尔干的重要据点,只有占领这里才能进攻瓦尔那,而只有占领瓦尔那才能穿过巴尔干,因此锡利斯特里亚对于俄军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场围攻战的主要意义与其说是战术上的,不如说是战略上的。若俄军占领锡利斯特里亚,那就差不多等于赢得了胜利,如果从此撤退则等于打了败仗。在这种情况,“不管怎样玩弄外交手腕,怎样贿买、怯懦和犹豫不决,但由于战争的内在规律的作用,我们已经接近到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3]295。因而,这次行动是在战争的内在规律而非外交手腕的作用下接近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爆发后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观望哪一方更有可能获胜,加入哪一方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而损失最小。恩格斯在分析克里木战局时指出,我们在听到奥地利已与西方强国联合的消息时的怀疑和犹豫是有根据的,因为如果战争的局势不明,维也纳内阁会继续保持观望,不会匆忙加入其中一方。因而,外交策略实际上也是由战争本身决定的。争取和平和支持是通过战争的实力打出来的,外交谈判只有建立在强大军事实力基础上,才能够争取利益最大化。赢者通吃、强者更强是战争不可避免的规律和结果,而不是外交谈判的结果。
四、政治、媒体与和谈
在战争中,媒体成为资产阶级获取利益的工具。交战者在国际上通过舆论占领道义制高点,如俄国以保护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徒为借口出兵土耳其,而各国在国内通过向媒体释放虚假信息以达到政治目的是常用的方法。战争的结局会影响内政,每一次战争失败,都将使执政者承受极大的压力。因此,英国内阁会对媒体释放虚假信息,或夸大积极信息,用某些表面成绩来掩饰自己在战场上的失败,以有利于国内的政治稳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的描述中,认为内容是决定形式的,内容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同时,形式也是反作用于内容的,是能够促进或者阻碍内容发展的。因此,在思想文化融入基层生产的过程中,载体的作用是万万不可小看的,它为枯燥、抽象的思想文化工作注入了生命的活力,找到了思想文化在生产经营工作中的切入点。
克里木战争期间,交战的双方都利用媒体稳定国内局势或者欺骗国内民众以鼓舞士气,因而出现了滑稽的一幕,一场战役,交战双方都宣称并庆祝自己的胜利。1854年,敖德萨战役结束后,英国和俄国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那么到底谁取得了胜利呢?恩格斯通过分析双方发布的正式文件发现,联军军队出现在敖德萨是为了要总督交出停泊在该港的英、法、俄的所有船只,作为射击不列颠军使旗的赔偿。但是,在战斗期间,只有两艘法国商船和两艘英国商船逃出了港口,还有7艘英国商船被扣留在那里。既然目的没有达到,那么联军就是遭到了失败。而英国却大吹大擂,实际上它这次的做法与过去的所作所为没啥区别,“公正的历史家一定会指出,英国在使用斗争最初阶段所特有的诽谤、诡辩、欺骗、外交手腕、军事吹嘘、谎言等手段方面同俄国是一模一样的”[3]248。英国媒体还在1854年底把同奥地利签订的微不足道的协定吹嘘为了不起的攻守同盟;曾虚假报道塞瓦斯托波尔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