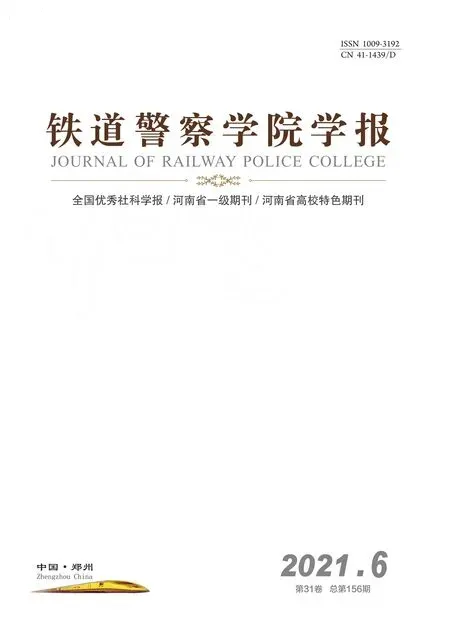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赵英杰
(铁道警察学院 侦查学系,河南 郑州 450053)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城市公共交通的利用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城市轨道交通应用越来越普遍。凭借运输量大、速度快、耗能低、安全性高、舒适度强等优势,城市轨道交通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城市内部的交通堵塞问题,同时也能丰富城市公共交通的组成结构,方便居民快捷高效出行。截至2021年6月,中国内地累计有48个城市投运城轨交通线路7957公里[1]。然而,昆明地铁脱轨事故、上海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北京地铁4号线电梯事故等运营安全事故的发生,也引起人们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广泛关注,其中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应当依照哪部法律规范进行执法和司法、如何保障受害人的权益等问题反响最为强烈。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虽然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变迁,但是相应的运营安全法律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不能及时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提供法律保障。因此,在建立健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法律体系的同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方面的立法也亟须跟进。
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立法的现状
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相关的交通运营安全法律法规却较为匮乏。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立法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的立法,二是地方层面的立法。
(一)国家层面的立法
就国家层面的立法来看,我国有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基本法缺失,也没有行政法规,目前仅有一部部门规章,即交通运输部于2018年5月21日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此外,有关部门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还出台过一些规范性文件,如《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地铁设计规范》等。在政策层面,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3月23日发布了《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该意见明确了建立健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标准体系要以运营安全为重点。
除专门性法律之外,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相关法律还包括生产安全、公共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其他领域的一些法律规范,体现在《安全生产法》《特种设备安全法》《消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文之中[4]。
(二)地方层面的立法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地方立法数量相对较多,已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城市大都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问题制定了专门法规。其中,有的属于地方人大常委会制订的地方性法规,如《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等;有的属于地方政府制订的规章,如《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办法》《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等。有的城市既有地方性法规,又有地方政府规章。虽然不同规定的立法位阶不同,但是同一城市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往往并无太大差异,只是在章节构成和语言表述等方面有所不同,不同城市之间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的章节构成也大同小异。已经颁布实施的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从内容上可分为运营前期风险防控、设备设施安全与维护、运营组织安全、应急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部分。
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可以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也就是说,上述行政区域可以根据当地的轨道交通运营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是上述行政区域以外的城市,是不具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立法权的,那么没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如何确保轨道交通安全运营有法可依,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总之,当前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法律体系中不但缺乏法律、行政法规,而且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也比较分散。若不有效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方面的立法进程,有可能对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事业产生消极影响,也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二、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层级较低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立法较为分散,至今仍然缺少全国层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问题进行统一规定。现有的法规主要来自地方性立法,立法层次较低。我国许多城市相继颁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目前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因为缺乏上位法的指导,因而在指导思想、篇章布局和机制规划等方面不够统一,在统一交通网络之内,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不利于执法、司法和守法。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立法层级过低,也不利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保护。
(二)法律规定命名缺乏规范性
不同城市对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同一位阶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命名不同。例如,对比《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单看三个地方性法规名称中的关键词分别是“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轨道交通管理”“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其囊括的内容应该不同,但是实际上其内容大同小异。同时,同一城市不同位阶法律名称也不统一。例如,北京市的地方性法规命名关键词为“轨道交通管理”,而地方政府规章命名关键词为“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但二者实际上都是对该地区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进行规制。法律规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应具有严谨性,法律规定命名不规范,不利于法律体系的统一。
(三)法律规范存在重复性
第一,法律框架存在重复性。同一地区不同位阶的法律文件存在重复。例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共七章七十八条,分为总则、运营安全风险前期防控、设备设施运行安全与保护、运营组织安全与服务、应急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部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共六章五十一条,分为总则、建设运营、运营管理、事故处理、法律责任和附则。通过条文框架对比可看到,二者总体都是针对运营前期、运营过程中及运营后期进行立法,存在重复性。在框架结构上,地方政府规章并未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只是语言表述不一致而已。
第二,规范内容存在重复性。例如,《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十八条前三项规定与《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前三项规定区别不大,尤其是前者第十八条第三项与后者第十三条第一项、前者第十九条规定与后者第十四条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虽然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但如果地方政府规章的内容完全照搬上位法的规定,可能会给立法、执法与司法造成较高的成本,乃至浪费法律资源。
三、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立法的关键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立法要在“以人为本、安全第一”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2018〕13号)规定:“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水平和服务品质。”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合理规划范畴,立法的关键大致包含明确规定主体资格、合理划定客体范围、科学界定权利义务、明确厘清法律责任和统一法律规范名称关键词等五个方面。
(一)明确规定主体资格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主要涉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乘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监督部门等主体。因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行业本质上属于服务行业,乘客的主体资格无需赘述,但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监督部门的主体资格却需要予以明确。首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主管部门应做好管理职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法应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的主体资格进行明确,也就是哪些行政部门对运营安全负主要责任、哪些部门起到辅助作用,以便将责任细化到特定部门,提高效率。其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主体资格需要通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基本法进行划定,同时可以借鉴我国《行政许可法》等部门法的经验,出台专门法律,对运营企业合格资质及企业工作人员上岗资格进行明确规定,同时,为了防止企业或者个人存在懈怠心理,法律应该明确规定主管部门需要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资质进行定期审核,对工作人员尤其是司机等操作人员的资质进行定期考核。再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监督部门的职责属于重中之重,是管理安全运营的最后一道防线。将监督部门明确化,有助于督促主管部门履行好职责,有利于把好每一道安全防线,将安全问题进一步抓牢、抓实,在安全问题上不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留有一丝松懈和大意。
(二)合理划定客体范围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是指一切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有关的内容,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质量安全、城市轨道交通专用设备质量安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安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内容。狭义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只包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也就是从乘客进入站台到离开站台期间的所有经营活动。笔者认为,应以广义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概念进行立法。首先,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质量安全、城市轨道交通专用设备质量安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安全、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均是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为核心,为运营安全所服务。其次,城市轨道交通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范围尽可能地扩大,在更大范围内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后,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未来无人驾驶技术很有可能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领域,采用广义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概念进行立法有助于维护法律稳定性,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工作,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
(三)科学界定权利义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法涉及的主体包括四部分,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乘客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监督部门,那么法律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这四方面主体从事运营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包括主管部门与运营单位的权利义务关系、运营单位与乘客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监督部门与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基于监督与被监督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乘客基于文明乘车的原则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等。
(四)明确厘清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规定是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立法内容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法律责任的规定要具体明确,需要规定相关人员责任、不同处罚措施轻重得当以及赔偿方式合理合法等方面。法律的规范作用在法律责任层面显示得淋漓尽致,任何一部完整的法律,法律责任的规定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律责任的明确性涉及该部法律的制定质量和效率价值,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关乎国家司法的公正文明。
(五)统一法律规范名称关键词
如前所述,将《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和《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三个规范性文件名称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可以得到“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轨道交通管理”“城市轨道交通管理”。“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应该包含本市区与轨道有关的所有交通运营安全,包括城际铁路,而《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了轨道交通是指地铁、轻轨等城市公共客运系统,不包含城际铁路。所以采用“轨道交通”命名,范围太广,远远超过城市轨道交通的包含范围,也容易与铁路领域立法产生冲突。“管理”一般是管理者管控他人行为进行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分析三个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其中不仅涉及管理,还包括公民的权利义务、乘车文明、法律责任等方面,采用“管理”这一关键词又容易将运营安全的范围不当缩减。综上,笔者认为法律规范的关键词确定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最为妥帖,行政法规可以命名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地方性立法可以命名为《××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或者《××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办法》。
四、完善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一)确定合理的立法模式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规定可以分布于城市轨道交通基本法的各个章节。目前其他国家或地区很少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进行单独立法,均是将安全纳入其中的某个章节或者分散于法律的每一部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涉及居民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与社会公共秩序稳定也存在密切关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2018〕13号)明确指出: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运行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2018〕13号)指出:“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骨干,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运行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安全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城市轨道交通从建设到监督,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对安全的考量,将安全贯穿于基本法的每一个章节,也是对“安全第一”原则的强化。所以,对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基本法制定而言,最优的选择是将运营安全部分分布于其各个章节。
(二)提高立法位阶
我国当前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法律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为主,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法律位阶高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国务院可以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基本法的立法理念以及基本法所包含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相关规定,针对运营安全的不同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出台相应的部门规章。各地区可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台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此可借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三)规范法律文件命名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法律的命名可参考我国铁路安全领域立法,对于行政法规,命名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较为妥当。如果地方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其内容如已经囊括了本地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管理规定,当地人民政府便可不再制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办法,但是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对于某些具体的安全问题出台地方政府规章,如可以制定《××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法》《××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四)避免法律规范的重复
法律规范的内容应围绕立法关键内容展开,避免重复,其框架结构完全可以借鉴《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框架结构,分为总则、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质量安全、城市轨道交通专用设备质量安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安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