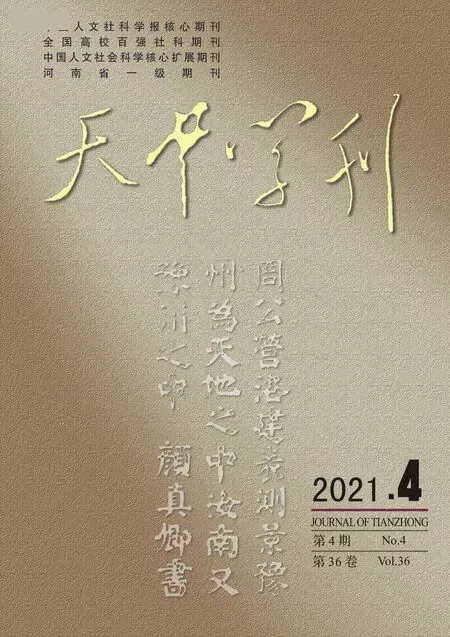王嘉《拾遗记》中的海外神仙世界
孙国江
王嘉《拾遗记》中的海外神仙世界
孙国江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拾遗记》是晋代道士王嘉所著的一部志怪小说集,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海外神仙世界的奇异传说。在这些传说中,王嘉展示了一个由远方仙境、不死仙药和海外异民构成的神奇世界。《拾遗记》中所载海外神仙世界既有对战国以来神仙家和方术士们所描绘的海外仙境传说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秦汉以后传入中原的域外故事的改编与重述,代表了当时人对于域外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当时人这种介于虚幻与真实之间的海外世界观,通过志怪小说得以保存和流传,《拾遗记》即是其中代表。
王嘉;《拾遗记》;海外;神仙世界
自战国中后期开始,神仙家和方士为寻求长生不老的帝王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海外仙境。秦汉以后,大量域外事物不断传入,刷新了中国人旧有的世界观,二者相结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关于海外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如王永平在《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古代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想象到探索、再到逐步认知的过程。传统中国的世界观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想象基础之上的观念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秩序’与‘华夷格局’。早期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与认识更多的是将客观认识与主观想象,甚至是一些道听途说或传闻结合在一起。”[1]26至魏晋时期,神仙家和方术之士造作的海外仙境传说与秦汉传入的域外故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带有博物性质的志怪小说作品,其中又以王嘉的《拾遗记》为代表。
一、《拾遗记》对早期海外仙境传说的继承与发展
《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嘉所著的一部志怪小说集。王嘉,字子年,生卒年不详,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晋书》有传。王嘉本为道士,常年隐居山林,《晋书》载其“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2]2496。《拾遗记》以时间为顺序,所记起于伏羲,迄于石赵,历述各代异闻怪事,其中记载的“远方异国”传说展示了当时人心目中奇幻的海外神仙世界。
早在先秦时期,关于海外仙境的传说就已经大量出现。按照神仙家和方术士们的说法,想要到达海外仙境,必须经历一段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海路,《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秦始皇派人寻找海外三神山,“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3]1370。这种玄虚缥缈的奇异景观,为海外仙境披上了一层神秘外衣。《拾遗记》中的很多故事,明显受到早期神仙家与方术士造作的海外仙境传说的影响。《拾遗记》中记载周成王时泥离国人来朝的故事称:“成王即政三年,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霆之声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涛之声在上。’”[4]49此故事中的泥离国人关于海路的描述,显然受到了《史记》中“三神山反居水下”这一说法的影响,并扩展为雷霆在下、波涛在上,借泥离国人之口更进一步强调了海外神仙世界的玄虚神妙。
同时,《拾遗记》在继承先秦以来海外仙境传说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很多秦汉以来的新内容,尤其是汉代以后不断传入的有关外域的信息。这些信息与神仙家和方术士们造作的海外仙境传说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故事。由于王嘉本人的道士身份,《拾遗记》中的这些新故事大多与长寿之国有关。《拾遗记》卷五载汉惠帝时泥离国人再次来朝的故事称:“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茧,牙出于唇,自乳以来,有灵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4]113故事中该泥离国人又自称曾见女娲蛇身及燧人氏钻木取火,以此显示他的长寿。《拾遗记》没有简单地继承前代的海外仙境传说,而是将神仙家和方术士们口中找寻不到的海外仙境具体化为海外的泥离国,又借看似真实存在的泥离国人之口诉说了海外神仙世界的奇异和海外异民的长寿,以达到增强海外神仙世界可信性的目的。
对于海外仙山,早期神仙家与方术士们往往语焉不详,而《拾遗记》则不同,其中大量吸收了秦汉魏晋作品如《山海经》《淮南子》《神异经》《十洲记》《博物志》等书中对于海外世界的描述,将海外仙山描写为生动而质实的可感可知之处。《拾遗记》中称蓬莱山“高二万里,广七万里。水浅,有细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净,仙者服之”[4]223,对方丈山和瀛洲也进行了同样细致入微的描绘,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书中对于员峤山的描写,《拾遗记》称员峤山上有不周之粟,“其粟,食之历月不饥”,又有“鹊衔粟飞于中国,故世俗间往往有之”,还引《吕氏春秋》中的内容进一步印证。之后,《拾遗记》又叙述了员峤山旁的“移池国”,其国“人长三尺,寿万岁,以茅为衣服,皆长裾大袖,因风以升烟霞,若鸟用羽毛也。人皆双瞳,修眉长耳,餐九天之正气,死而复生,于亿劫之内,见五岳再成尘。扶桑万岁一枯,其人视之如旦暮也”[4]229。通过这些描写,《拾遗记》为人们构建了一个似乎近在眼前的海外长寿之国。
总之,王嘉因其道士的身份,对前代神仙家和方术士们所创作的海外仙境传说十分熟悉,加之其长期隐居于长安附近,对汉代以来流传的域外故事亦不陌生。《拾遗记》对海外神仙世界的描述,实际上是在继承前代海外仙境传说的基础上融入秦汉以来的域外故事,并将二者结合后而创作的新故事。
二、《拾遗记》中的不死仙药与海外异人
战国秦汉之际,为了迎合帝王们对长生不死的追求,神仙家和方术士们杜撰了大量关于不死仙药的传说,而海外世界则是神仙家和方术士们口中不死仙药的所在地。秦汉以来的作品中大量记载了关于“不死树”的传说,《山海经》和《淮南子》中都提到昆仑山旁有“不死树”,《博物志》和《外国图》中则将不死树描绘为“食之乃寿”的长生之药。到了《拾遗记》中,“不死树”的传说被进一步细化,并与海外世界发生了联系,其中一则故事称:“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有祈沦之国。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4]123祈沦之国国人长寿的原因是其国有寿木之林。所谓寿木之林及不老树叶,显然正是“不死树”和不死仙药结合的产物。
《拾遗记》中还记载了波弋国神香的故事,该香同样有使死人复生的功效,甚至用这种香“熏枯骨,则肌肉皆生”。此外还有背明之国所出产的可以使人长寿的谷物:“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东,有背明之国,来贡其方物。言其乡在扶桑之东,见日出于西方。其国昏昏常暗,宜种百谷,名曰‘融泽’,方三千里。五谷皆良,食之后天而死。有浃日之稻,种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夭而有寿;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肠稻,食一粒历年不饥。”[4]131这些生长于海外的神奇谷物,同样具有使人长生的功效,仍然是海外不死仙药传说的一种变体。无论是寿木之林、神香还是神奇谷物,都将海外世界与不死仙药联系在了一起,为海外神仙世界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这些有关不死仙药的故事并非《拾遗记》的独创,而是在魏晋时期十分流行的传说。《海内十洲记》中记载了汉武帝征和三年,西胡月支国王派遣使者进献四两香料,这种香料“大如雀卵,黑如桑葚”,汉武帝最初以为是普通的香料,并没有认真对待,到了后元元年,长安城内兴起瘟疫,城中百姓死亡大半,武帝下令试取月支神香于城内燃烧,已经死去而没有超过三个月的人都活了过来,武帝才知神香的功效,但是这种神香最终却在府库中不翼而飞,汉武帝也在第二年驾崩。《海内十洲记》中还详细记载了这种神香的来源,称其出自西海聚窟洲人鸟山,山上有一种长相类似枫树的树木,名为“反魂树”,扣其树即可听到如牛吼的声音,取出树根用火煎煮成药丸,即成反生香,燃烧此香可以使死人复生。《汉武故事》中也记载了汉武帝时兜末国所献兜末香的故事,故事中的兜末香形如大豆,将其涂于门上即可“香闻百里”,后来适逢瘟疫流行,死者不断,取出此香燃烧,瘟疫流行便即停止。
这些关于不死药和反生香故事的背后,是西域药用香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香料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日用品,其主要的功能包括焚熏、佩戴、调味和医疗。在中国传统的香料中,焚熏和佩戴是最主要的使用场景,用于调味的香料则单独构成一个系列。而在医疗功用方面,中国本土香料虽然有时也可入药,但并没有由此衍生出神异的传说。与中国不同的是,中亚、西亚和南亚许多地区多用香料敬神,香料因此被认为受到神明的祝福而具有了超自然的神奇功效。同时,许多域外香料本身确实具有镇静、止血、消肿等药用价值,在古代中亚、西亚、南亚等地普遍被当作重要药物来源,不死药和反生香的故事应即由此产生。
除不死仙药以外,《拾遗记》中还记载了很多来自海外的异人。《拾遗记》中记载来自“扶娄之国”的异人,“其人善能机巧变化,异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中。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犀、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为虎、兕,口中生人,备百戏之乐,宛转屈曲于指掌间”[4]53。又记载来自“渠胥国”的异人韩房:“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虎魄凤凰高六尺,火齐镜广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语,则镜中影应声而答。韩房身长一丈,垂发至膝,以丹砂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可照百余步。周人见之,如神明矣。”[4]75从这些记载看,当时应该确实有精通幻术的海外异人来到中国献技,但其所使用的无非是类似于今天魔术表演的一些手法。但是在《拾遗记》的记述中,这些表演都成了来自海外神仙世界的神技。王嘉在《拾遗记》中对这些海外异人进行了大肆渲染,究其原因乃是魏晋时期的道教徒也大量使用此类幻术作为传教的手段,如《神仙传》中记载道士孙博可以“吞刀剑”“从壁中出入”,还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又载道士刘政可以“取他人器物,以置其众处,人不觉之”,这些道士们所表演的法术很多都是通过障眼法实现的空间转移或瞬间变换物品的魔术手法,其中一些内容在今天的魔术表演中仍然能够见到。道士出身的王嘉对使用幻术的海外异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既有自神其教的用心,也进一步增加了海外神仙世界的神异属性。
《拾遗记》所记载的海外异人故事最为神奇的是两位来自“浮提之国”的“神通善书人”,他们能“乍老乍少”,还能隐形出影,二人用四寸金壶中的墨汁在石板上写下老子《道德经》的注解约十万言,金壶中的墨汁写尽后,二人又“刳心沥血,以代墨焉”,所用灯烛中的油膏用尽后,二人“钻脑骨取髓,代为膏烛”,心血和骨髓用尽后,二人以丹药涂身,即痊愈如故,以此作为自己神奇法力的展现。实际上,《拾遗记》中浮提国善书人的故事与佛经有极大的关系,《贤愚经》中就有佛教信徒“剥皮作纸,析骨为笔,血用和墨”以记录佛法的故事,其后的汉译佛经中也多次出现此类说法,钱钟书先生即以为:“《拾遗记》卷三,二人乃‘佐老子作《道德经》’者,盖方士依傍释典‘以血为墨’之事,又割截‘阎浮提’之名,后世道书复掩袭之而托言出于《圣记》。”[5]1500《拾遗记》的作者王嘉本是道士,他将佛教“以血为墨”的故事与老子《道德经》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希望通过此类故事中幻术神迹的展现实现助推道教传播的目的。
总之,秦汉以后的域外传说本身就包含着很多神奇的内容,与道教徒所追求的长生久视以及用幻术传教的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道教徒的王嘉遂将二者结合,形成了《拾遗记》中关于海外神仙世界的神奇故事。
三、《拾遗记》中海外世界的虚幻与史实
与纯粹虚构的小说创作不同,六朝志怪小说的作者和记录者几乎都不承认其笔下的神异故事是源于虚构或杜撰,反而再三强调其所记之事即使不是亲眼所见,也是亲耳所闻。干宝《搜神记自序》自述其创作时称:“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6]19萧绮序王嘉《拾遗记》亦曰:“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4]1二者都反复强调书中所记神异奇怪故事是纪实而非杜撰,这些说法与他们笔下故事本身的神异属性是非常不协调的,但却代表了当时人对志怪小说的普遍认知。《拾遗记》中那些看似虚幻奇异的海外神仙世界传说,背后是秦汉以来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的宏大历史背景。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许多域外事物在古代中国都不常见。西汉时期,随着西域通道的打开,大量的外来器物、用品和动植物传入中原,这些曾经在中原地区难得一见的新奇事物迅速成为当时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自张骞通西域之后,人们对于外部世界认知的范围开始逐渐扩大。张骞分别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和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联合月氏、乌孙等国共同抗击匈奴。但是由于月氏、乌孙等国动乱导致国力衰弱,张骞的政治使命没能顺利完成。不过,张骞自西域带回了域外世界的情报,他所到之处包括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奄蔡、条枝、黎轩等国,打通了中国经中亚、西亚至南亚和欧洲的路线,并带回了葡萄、苜蓿、棉花、胡桃(核桃)、胡瓜(黄瓜)、安石榴(石榴)、胡萝卜、胡椒等多种域外事物,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不久臣服于东汉政权,北匈奴则继续在边境为患。东汉派班超等人出使西域并控制西域诸国,经几十年经营确保了西域道路的畅通,增强了东汉王朝与域外国家的联系。尤其是远隔大海的大秦国,汉代又称“海西国”,即今日所说的罗马帝国。由于交通不便,当地物产在传入中原的过程中被增加了许多奇异的传说成分,《后汉书》载:“大秦国……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市。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同时还把大秦国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联系:“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7]2919
此外,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地区在汉代被称为“天竺”或“身毒”,由于气候与物产与中原有很大不同,也成为殊方异物传说的重要来源,《后汉书·西域传》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㲪、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7]2921由于路途远隔,域外的物产与中国地区多有不同,域外传入的很多事物在当时都被视为珍物。加之语言不通,对于这些域外事物的记述和描绘亦有讹差,如《玄中记》记载大月氏有“日反牛”,能够割肉复生,“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复,创即愈也”[8]455,同时也提到汉人对当地人说起中国有能食桑叶吐丝织布的蚕虫,西胡人也不相信蚕真的存在。由于地域、语言的不同造成巨大的文化差异,从而产生奇异的传说,这些传说遂衍生出许多“殊方异物”的故事,并被当作奇闻逸事收录于六朝志怪小说之中,这就是《拾遗记》等志怪小说中关于海外神仙世界奇异故事的来源。
以《拾遗记》中关于玛瑙的故事为例,可以看到域外事物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生成奇异故事的过程。玛瑙是一种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玉髓类矿物,秦汉魏晋时期又被称为“马瑙”或“马脑”,《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曹丕《马瑙勒赋》称:“马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9]1441汉魏六朝时期,玛瑙在中国的产量不多,大部分都由域外传入,又由于玛瑙形态各异、变化多样,因此产生了许多关于玛瑙的神异传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认为玛瑙是由马的脑部变化而来的,《拾遗记》中就记载“码瑙石”出“丹丘之国”,并称其国人有善识马者,听马鸣叫即知马脑颜色,待马死后破其头出脑,即可制成“码瑙石”。除认为玛瑙由马的脑部制作而来的说法之外,还有传说认为玛瑙是由恶鬼之血所凝成或由罗刹恶鬼所造,《拾遗记》中又载另一传说称:“马脑者,言是恶鬼之血,凝成此物。”[4]19《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六引《凉州异物志》云:“方外殊珍,车渠马瑙。器无常形,为时之宝。视之目眩,希世之巧。罗刹所作,非人所造。”[10]3355这些神异的传说,都是域外事物在传入的过程中由于路途遥远和语言不通造成的以讹传讹,进而又演化成志怪小说中的神奇故事。
总之,《拾遗记》中虚幻的海外神仙世界既有继承自先秦神仙家、方术士的海外仙境传说,也有秦汉以来传入中原的域外事物,二者结合就形成了奇异的海外神仙世界。正如王青所说:“中土的人们首先感兴趣的并得以接触的事物之一是各种来自于西域的新奇器物。这种了解往往不完全本之于真实的知识,而是带有明显的误解、夸饰与想象的痕迹。人们通过独特的视角把自己的情感、愿望投射于来自于西域的器物,各种传闻与想象源源不断地进入历史,从而重新建构了一个西域世界。”[11]241很多域外事物传入以后,长期仅以贡品的形式存放于皇宫,流传范围也仅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普通百姓难得一见。久而久之,人们凭借想象并结合先秦以来流传的海外仙境传说,杜撰了大量关于域外事物的神奇故事。这些故事和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重述和改写,增添了许多细节,形成新的故事记录于六朝志怪小说之中,而王嘉的《拾遗记》正是此类作品的代表。
[1] 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齐治平.拾遗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李剑国.新辑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 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G].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9]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10]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I206
A
1006–5261(2021)04–0086–05
2021-04-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251)
孙国江(1983―),男,河北廊坊人,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